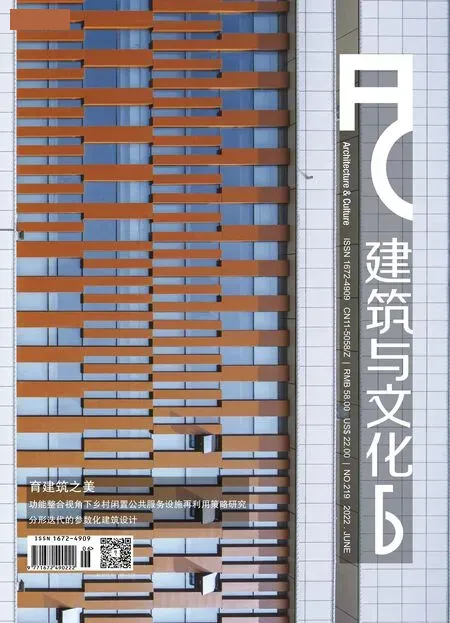城市老舊社區的參與式改造研究綜述
文/溫佳寧 湖南科技大學建筑與藝術設計學院
邵逸樂 湖南科技大學建筑與藝術設計學院 碩士研究生(通訊作者)
鄭可萱 湖南科技大學建筑與藝術設計學院
陳玲婷 湖南科技大學建筑與藝術設計學院
1 研究背景
隨著我國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老舊社區改造問題越來越受到政府的重視。近年來,公眾參與成為老舊社區改造的重要命題。2017年底,住建部在老舊小區改造試點工作座談會中提出“充分運用‘共同締造’理念,激發居民群眾熱情,調動小區相關單位的積極性,共同參與老舊小區改造”[1];2020 年7 月,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全面推進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工作的指導意見》中再次強調“健全居民參與機制”,提出“利用‘互聯網+ 共建共治共享’等線上線下手段,開展小區黨組織引領的多種形式基層協商,主動了解居民訴求,促進居民形成共識,發動居民積極參與改造”[2]。
“公眾參與”理念在20 世紀80 年代末被引入我國城市規劃學界,經過三十余載的理論與實踐探索,在城市宏觀規劃層面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正逐步深化到微觀的社區改造治理中。“居民共同參與”成為城鎮老舊小區改造的重要方式,國內各城區也隨之提出老舊社區參與式改造的創新理念與實踐方法。隨著國民自主意識的增強,我國借鑒國外地區的“參與式”規劃理論和實踐,結合自身的社區規劃建設和管制體制,開始探索屬于自己的社區更新方式,也取得了初步成果。尤其在一線城市的老舊社區改造項目中,開始涌現創新的公眾參與模式。但由于我國參與式設計起步較晚,理論基礎尚淺,關于參與的過程方法研究仍有欠缺,在老舊社區的參與式改造中仍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2 理論解讀
2.1 老舊社區的定義
老舊社區在《辭海》中的定義為:“老舊住宅單體及其居住環境在一定的自然地域空間、社會經濟形態和使用時間區段的整體功能狀態產生‘綜合性陳舊’過程的社區。”
2.2 參與式設計的內涵
參與式設計最早起源于20 世紀60 年代的計算機領域,是多學科發展的綜合產物[3]。楊沛儒在其研究中認為,公眾參與社區規劃是一個溝通行動的過程,強調設計方法的創新和專業角色的加入,將公眾參與作為居民的基本權利并滿足公眾的需要訴求,以實現更大的公共利益[4]。
參與式設計包含了“公眾參與”和“設計”兩個方面,目前沒有明確的界定范圍和標準化的操作模式[5]。參與式設計在老舊社區改造中強調社區居民對自身居住環境的改造需求,政府和規劃師在居民參與改造的過程中進行有效指導,以實現多元主體的共治。在共建、共享、共治的社會治理格局下,參與式設計在城市老舊社區改造研究中逐步發揮著重要作用,常見的參與式更新組織管理模式將“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模式相結合[6]。
3 國內外社區參與式設計理論與實踐發展研究
3.1 國外社區參與式設計實踐——以美國、日本、英國為例
20 世紀50 年代,美國開始出現“公眾參與”和“社區設計”理念。1988 年,西雅圖開展了改善社區的“鄰里計劃”,引導社區居民參與鄰里改善。1989 年對公眾參與的必要性制度上進一步確定[7]。社區規劃模式,以政府為指導并提供管理、監督和評估作用,以社區委員會為骨干,非官方組織為主體,居民為主要參與者和促進者[8],為社區居民參與社區規劃和自身權益的保護提供了更好的途徑。
20 世紀80 年代日本市民自行制定了《社區營造條例》,社區培育活動更具針對性和具體化[9,10]。通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建立了社區培育組織,使公民與政府部門實現了平等對話[11]。
英國以非政府組織為橋梁的公眾參與社區規劃模式在1960 年得到了政府的推廣,20 世紀80 年代后,公眾直接參與社區建設成為專業領域的主流[12],著眼于讓人們參與到自身環境的塑造和管理中,同時讓規劃建筑師與社區團體合作參與其中[13]。
3.2 國內參與式社區改造理論發展研究(表1)

表1 國內參與式社區改造理論發展(表格來源:作者自繪)
3.3 國內社區參與式改造實踐研究
我國參與式社區改造主要體現在社區花園、社區微小綠地和社區公共空間等實踐中,主要以北京、上海等發達城市為主,參與式設計理念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3.3.1 多元合作
2015 年,廈門蓮花香墅社區改造實踐,提出了構建以公眾參與為核心的政府、公眾、規劃師和社團等多元主體互動的平臺,根據居民的訴求與問題為導向組織公眾參與規劃[28]。2018 年天津風湖社區公園改造中,設計團隊搭建多方協商議事平臺,制定了參與式改造策略促使多元主體廣泛參與[29]。2020 年上海楊浦創智片區政立路580 弄社區更新中,提出建立多元化的公眾參與協作機制[30]。2021 年北京常營福第社區小微綠地改造中,力求突破自上而下的組織管理模式,以多元化的治理模式構建多方合作平臺[31]。
3.3.2 共建共享
2018 年,在上海社區花園系列空間微更新實驗中,劉悅來提出社區民眾以共建共享的方式進行園藝活動的方式[32]。2020 年,上海市貴州西里弄社區更新中,融入了“共享”的理念社區,同時還使居民自發形成了自我管理、自我維護的新模式[33]。
3.3.3 參與形式
2019 年,天津市迎水里社區參與式景觀改造中,提出“共同締造”的參與式設計工作坊模式,即通過互動式調查給出初步改造方案,而后進行會談協商改進方案的模式[3]。2021 年北京常營福第社區小微綠地提升中,提出參與式設計具體可以通過舉辦參與式工作坊、方案征集等形式激發參與者對社區公共空間的創造力[34]。
4 我國老舊社區參與式改造現存問題
通過對我國理論與實踐發展以及對比國外實踐總結可知,我國在老舊社區參與式改造中主要存在的問題有如下表現。
4.1 參與主體
社區居民是公眾參與的主體,也是公眾參與方式落實的具體對象。在我國,社區主要還是一個自上而下的結構單位。由政府主導的社區改造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滿足居民的訴求。由于對民意缺乏充分了解,政府部門在改造老舊社區的過程中往往比較盲目,容易出現各方利益錯位的情況。
公眾參與社區規劃成功案例的組織架構模式大部分是“政府+專家團隊+社區居民和組織”,三方共同協作,對推動公眾參與社區營造起關鍵作用。
4.2 參與意識
通過研究發現,進入21 世紀之后,由于城市規劃中興建、拆遷、安置、補償等直接涉及居民自身利益,居民參與的意愿才逐漸提高。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面臨新轉化,居民的參與改造積極性空前高漲。
由于社區管理模式固化,參與積極性沒有充分的渠道得以實現,居民實際參與度仍舊處在較低的水平。因此,怎樣提高居民實際參與度已經成為老舊社區參與式改造的關注焦點。
4.3 參與保障
從美國紐約、日本及英國社區營造中的公眾參與發展歷程來看,相關制度、法律法規、資金保障及監督體系是其成功的重要保障。而我國,雖然在2007 年頒布的《城鄉規劃法》中將公眾參與在城市規劃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明確,但未明確涉及到具體的操作方式。2020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全面推進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工作的指導意見》中提出健全動員居民參與機制,建立改造資金政府與居民、社會力量合理共擔機制并完善配套政策。雖然我國當前公眾參與的保障體系仍不完善,但可以看出政府部門已經著手于建立健全組織實施機制,推動各地確定改造內容和標準并給予資金支持,社區改造的參與保障正在被引起廣泛重視。
4.4 參與途徑
社區參與方式需要針對不同居民群體的特點,同時還應考慮居民對參與方式的接受程度。我國老舊社區的居民結構較為復雜,集中在老年群體及低收入群體上,入口綜合素質相對較低,理解能力和參與動力較為薄弱。
因此在老舊社區的參與式改造中需要提供針對這一人群特點的參與途徑,滿足簡單、通俗易懂的基本特征避免形式繁瑣或過多運用現代智能科技的參與途徑。
5 研究啟示
5.1 參與主體的明確界定
社區參與式設計的主體應為社區居民和自發組建的非營利性組織結構或團體。社區居民作為社區空間的實際使用者,應當廣泛參與到社區改造中來。與此同時政府應充分了解公眾的多元利益并提供有效的參與途徑。基于我國公眾參與起步較晚,正處于過渡階段的現實,公眾參與形式不能完全照搬國外“自下而上”的模式,其發展需要政府起主導作用,并提供可靠的保障支持,從而推動后期逐步轉變成居民自治模式。
5.2 參與意愿的滿足途徑
居民參與的落實需要暢通和豐富的參與途徑。就目前的實踐途徑來看,“參與式工作坊”在方案確定前充分調查居民需求,在確定初步方案后將設計和居民進行共同協商與修改,這一模式逐步突破自上而下的組織管理模式,展示了參與式改造目前取得的成效。此外,上海的“創智農園”也是一次較為新穎的嘗試,該模式利用社區園藝種植給居民充分的自我管理和利用空間。這些實踐都表明我國老舊社區改造中應該讓居民有參與到社區規劃建設的實權,同時也應重視專業人員在改造設計中的指導作用,對居民的改造意愿作出更為專業的設計。
5.3 參與保障的加緊落實
老舊社區的參與式改造需要保證居民表達訴求的方式有效性及參與程序規范性,并配以反饋機制。除了政府的保障支持外,在改造設計的過程中社區志愿者可自發組建社區發展社團等非營利組織(NGO)來完善組織保障,并對規劃設計的過程實時監督和評價。
5.4 后期問題的反思調整
由于參與式改造在老舊社區更新中發展的時間很短,必然會在實踐中暴露出一系列問題。例如,“創智農園”的實踐中項目實際落地與居民產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居民認為個人利益遭受損失等問題,仍然需要進一步反思及解決。諸如此類概念與實際之間的落差,必將是我們之后實踐中需要著重思考并改善的方面。
結語
綜上所述,雖然研究者已然重視對于參與式改造的研究,也取得了較為顯著的研究成果,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是理論上的分析與探討,具體的實踐相對較少。老舊社區的參與式改造目前正處于探索實踐階段,也存在很多尚待解決的問題。但相比以往社區建設模式,參與式改造把社區改造的主權共享給每一個參與主體,構建了多方包容的參與途徑。老舊社區的參與式改造模式,在未來有一片可預見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