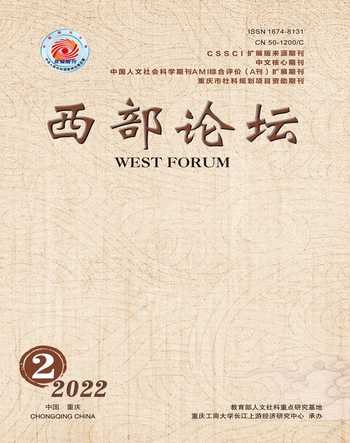就業歧視對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效應的影響
陳利鋒 張凱鑫 林柳琳










現實經濟中就業歧視的表現形式眾多,其中就業機會歧視是最為普遍的現象,即企業在招聘過程中主觀認定雇用某一類型勞動力將產生額外成本,導致企業對該類勞動力的雇傭量少于最優雇用量,進而使社會就業總量減少。基于此,本文構建無就業歧視和存在就業歧視兩種情形下的兩主體動態隨機一般均衡(TANK-DSGE)模型,運用脈沖響應分析和二階矩匹配法等考察就業歧視對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效應的影響,分析結果顯示:無論貨幣政策當局執行何種貨幣政策(標準泰勒規則、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無論是否存在就業歧視,擴張性貨幣政策均會促進產出、消費、投資、就業、物質資本租金率和整體物價水平等宏觀經濟變量增長;與無就業歧視的情形相比,存在就業歧視情形下擴張性貨幣政策對產出、消費、投資、就業的促進作用變小,而對物價上漲(通脹)的促進作用變大,即就業歧視會弱化擴張性貨幣政策的積極效應并強化其消極效應;就業歧視的存在會降低貨幣政策實施后產出和就業的持續性、提高通脹的持續性,同時也會擴大產出、就業和通脹的波動性。總體上看,擴張性貨幣政策對就業的促進效應在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下最強,且就業歧視的負面影響最小,因而選擇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可以更好地實現促進就業的目標;擴張性貨幣政策對產出的促進效應在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下最強,且就業歧視的負面影響最小,因而選擇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可以更好地實現促進產出增長的目標。
相比現有文獻,本文主要在三個方面進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從經濟政策有效性角度探討就業歧視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負面影響,二是構建TANK-DSGE模型考察就業歧視對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效應的影響,三是從提高政策有效性角度為不同宏觀經濟目標下的貨幣政策選擇提供理論參考。
本文揭示了就業歧視對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效應具有顯著負面影響。減輕就業歧視不僅有助于就業和收入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構建和完善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以不斷減少各種就業歧視。
關鍵詞:就業歧視;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效應;標準泰勒規則;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
中圖分類號:F820.1;F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22)02-0032-15
一、引言
就業歧視是現實經濟中一個常見的現象,并且由于其與社會公平之間的密切聯系而被廣泛關注(陸銘等,2012;劉超等,2020)。Atkinson(2015)指出,就業歧視不僅影響個體就業和收入,從宏觀層面上看還可能改變一國的宏觀經濟表現。Cubas等(2016)的研究表明,就業歧視造成部分勞動力天賦被浪費,降低了就業質量,進而不利于地方經濟發展。Card等(2016)和Hotz等(2017)分析發現,葡萄牙和美國勞動力市場顯著存在就業性別歧視現象,就業性別歧視不僅導致就業機會不平等,而且帶來更大的性別收入不平等。Kline和Walters(2021)的研究也顯示,就業歧視問題在美國顯著存在,而且就業歧視是導致美國勞動力市場復蘇緩慢的重要原因。王瑩(2016)指出,就業歧視違背社會公平的理念,不利于實現社會進步和經濟繁榮。劉超等(2020)認為,就業歧視降低了中國勞動力市場技能與就業崗位的匹配程度,不僅不利于實現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也不利于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張建華等(2020)分析發現,就業歧視對全要素生產率存在顯著負影響,不利于長期經濟增長。顯然,就業歧視不僅不利于實現社會公平,而且不利于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因此,研究就業歧視對一國宏觀經濟產生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事實上,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歧視問題一直是國內外研究者關注的熱點。其中,大量研究主要關注就業歧視對勞動者收入差距的影響,比如Demurger等(2009)、Wang等(2015)、孫婧芳(2017)和Combes等(2020)的研究均發現,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存在顯著的就業歧視引致的收入差距。不過,這些研究主要分析的是整體意義上的就業歧視對勞動者收入差距的影響。與之相關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歧視存在多種表現,比如部門歧視、年齡歧視、身份歧視等,這些不同種類的就業歧視分別會對勞動者收入差距產生怎樣的影響?部分研究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魏下海和余玲錚(2012)、陳利鋒(2020)指出,造成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就業歧視的原因在于正規部門與非正規部門的部門分割,由于部門分割導致進入正規部門存在多方面的歧視性條件,進而帶來不同部門間勞動者的收入差距。Zhong( 2011)的研究發現,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存在顯著的就業年齡歧視,且人口老齡化會加劇這種就業歧視現象,導致勞動者收入差距擴大。Meng和Zhang(2001)、Ma(2018)基于勞動力市場不同產業部門工資差距的動態變化趨勢指出,勞動力市場分割和就業戶籍歧視是引起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成因。一些研究則從微觀(如勞動者個體特征)角度分析就業歧視形成的原因。Demurger(2021)研究表明,個體的技能、受教育程度以及所在地區等特征與就業歧視密切相關,并且通過就業歧視顯著影響個體收入。還有部分研究主要考察就業歧視隨時間變化的動態趨勢。孫婧芳(2017)采用時間序列數據的分析顯示,城鎮農民工面臨的就業歧視整體上呈現下降趨勢,但其進入公有制單位仍面臨較強的就業歧視。吳彬彬等(2020)的分析也發現,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機會歧視呈現顯著的弱化趨勢。Demurger等(2019)的研究表明,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存在顯著的就業教育背景歧視,不過近年來在沿海以及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就業教育背景歧視逐漸弱化,技能水平成為企業雇用勞動力的重要標準。
基于現有研究可以發現如下事實:第一,中國城鎮勞動力市場存在就業歧視現象,但表現出逐漸減弱的趨勢。第二,無論是整體意義上的就業歧視,還是具體某個層面的就業歧視,都造成了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顯然,現有研究更多關注的是就業歧視對居民收入分配產生的影響,而較少關注其他層面的影響。在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研究中,宏觀經濟波動或者經濟周期是其關注的主要領域,然而,盡管就業歧視在各國勞動力市場顯著存在,但現有的新凱恩斯主義分析框架卻較少關注就業歧視對宏觀經濟產生的影響。有鑒于此,本文試圖構建一個包含兩主體的新凱恩斯主義(Two Agent New Keynesian,TANK)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模型(以下簡稱TANK-DSGE模型),并引入就業歧視:企業認為雇用其中一種勞動力將產生額外成本,導致企業雇用該類型勞動力的數量低于無就業歧視情形下的最優雇用數量(即就業機會歧視或就業機會不平等)。首先設定貨幣政策當局執行標準泰勒規則,進而比較無就業歧視與存在就業歧視兩種情形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為結論穩健性考慮,進一步基于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和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進行比較分析。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構建包含就業歧視的TANK-DSGE模型;第三部分對包含就業歧視的TANK-DSGE模型中的結構性參數進行校準,進而分析就業歧視對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效應的影響;第四部分為總結與啟示。
二、模型與假設
本部分構建一個包含家庭、企業和貨幣政策當局的TANK-DSGE模型。模型經濟中包含A和B兩類家庭,其中A類家庭占比為K。兩類家庭分別有兩類家庭成員H和L,兩類家庭中的成員H(即HA和HB)具有相同的生產率,而兩類家庭中的成員L(即LA和LB)則具有不同的生產率。為簡單起見,設定LA的勞動生產率高于LB。企業雇用來自兩類家庭的勞動力,但存在就業歧視:將所有類型為/的勞動力看作完全相同,認為雇用L類勞動力可能產生額外的成本,比如更高昂的培訓費用、培養成本等,導致企業對L類勞動力的雇用意愿下降,最終使該類勞動力的雇用數量低于均衡數量。
1.家庭
三、模型結構參數校準與動態分析
本部分首先對第二部分構建的無就業歧視與存在就業歧視兩種情形的TANK-DSGE模型中的結構性參數進行校準,然后比較無就業歧視與存在就業歧視兩種情形下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在此基礎上,引入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和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進一步分析就業歧視對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效應產生的影響。
1.結構性參數的校準
A類家庭占比為K,不失一般性,本文將其取值設定為0.5。依據陳利鋒等(2021)、鄧貴川和謝丹陽(2020)、吳立元等(2021)的研究,勞動力替代彈性系數η、時間偏好參數p、資本的產出彈性系數α、物質資本折舊率6分別取值為1.63、0.95、0.6和0.04;依據Ravenna和Walsh( 2022)的研究,H和L兩類勞動力的替代率A取值為3.16;依據張建華等(2020)、高文靜和施新政(2021)估算的結果,生產過程中H類勞動力的投入占比α和a分別校準為0.5和0.4;依據王凱風和吳超林(2021)的研究,產品替代彈性ε名義價格剛性θ分別校準為2.75和0.75;依據王凱風和吳超林(2021)、陳利鋒等(2022)的研究,貨幣政策參數ρ、r、r分別校準為0.8、0.25和1.5。
反映就業歧視的額外單位固定成本丁是在存在就業歧視時企業認為雇用L類勞動力存在的超額成本,只要丁取值大于0就存在就業歧視。丁取值不同,雖然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產生的影響可能存在數值上的差異,但分析結論不會有根本上的不同。因此,本文將丁取值為0.1。
2.模型動態分析
基于校準的參數進行模型分析,圖1分別給出了無就業歧視和存在就業歧視兩種情形下擴張性貨幣政策沖擊(1個單位標準差)的脈沖響應。可以發現,無論是否存在就業歧視,擴張性貨幣政策均引起產出、消費、投資、就業等宏觀經濟變量增加,同時引起物質資本租金率和物價水平上升(通脹),表明擴張性貨幣政策產生的宏觀經濟影響符合直覺,也與相關文獻的研究結論一致(Gali,2022;Ravenna et al,2022;陳利鋒等,2021; Andrade et al,2021)。
比較圖1中無就業歧視與存在就業歧視兩種情形下貨幣政策沖擊的脈沖響應可以發現,就業歧視顯著改變了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具體表現為:(1)盡管兩種情形下擴張性貨幣政策沖擊均引起產出、消費、投資、就業和物質資本租金率等宏觀經濟變量的增加,但比較而言,存在就業歧視情形下增加的幅度較小。(2)與無就業歧視情形相比,存在就業歧視情形下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對物價水平的影響更大,即物價水平上升(通脹)的幅度較大。
導致上述差異的原因是就業歧視阻礙了貨幣政策影響宏觀經濟的傳導路徑。當擴張性貨幣政策沖擊發生后,貨幣政策當局實際執行的利率下降,刺激企業擴大生產規模,因而企業勞動力需求得以較大幅度增加(經濟中總就業量較大幅度增加)。在無就業歧視情形下,企業依據成本最小化原則確定最優勞動力投入組合,各種勞動力的就業機會均相應增加,勞動者獲得的實際工資上升,推動家庭收入上升,進而推動家庭消費水平上升。與此同時,盡管擴張性貨幣政策會推動物價上漲,但企業生產規模擴張引起的總供給增加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物價上漲。與無就業歧視的情形不同,就業歧視的存在使企業默認雇用L類勞動力可能導致額外的成本,在依據成本最小化原則進行最優生產要素投入決策時,中間產品生產企業雇用的L類勞動力數量小于無就業歧視情形下的數量,因而擴張性貨幣政策沖擊發生后,經濟中總就業增加的幅度小于無就業歧視情形。對應的,家庭收入和消費的增長幅度也較小,同時,企業較小的勞動力投入增長導致總產出(也即經濟中的總供給)增長幅度較小,進而對整體物價水平上升(通脹)的抑制作用也相對較小。因此,與無就業歧視情形相比,存在就業歧視時擴張性貨幣政策帶來的投資、產出、就業、消費等增長較小,而引起的物價水平上升(通脹)較大。
3.二階矩分析
借鑒Gali(2022)的處理方法,本文分別采用宏觀經濟變量的一階自回歸系數和標準差表示其持續性和波動性,進而考察無就業歧視與存在就業歧視兩種情形下擴張性貨幣政策沖擊發生之后宏觀經濟變量的持續性和波動性特征,結果見表2。可以發現,在擴張性貨幣政策沖擊發生后:與無就業歧視情形相比,在存在就業歧視的情形下,產出和就業的持續性較低,而通脹的持續性較高,意味著就業歧視降低了擴張性貨幣政策對產出和就業增長的積極效應,并提高了通脹慣性;與無就業歧視情形相比,在存在就業歧視的情形下,產出、就業和通脹均具有較大的波動性,意味著就業歧視提高了擴張性貨幣政策帶來的產出、就業和通脹波動。因此,無論貨幣政策的目標是產出、就業還是通脹,就業歧視均降低了擴張性貨幣政策的積極效應。
4.進一步分析:其他貨幣政策規則的影響
上文的基準貨幣政策規則為標準泰勒規則,如果貨幣政策當局采用的貨幣政策規則與式(32)不同,就業歧視又將對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產生何種影響?如果貨幣政策當局將就業作為貨幣政策盯住對象,使貨幣政策直接依據勞動力市場就業狀況進行調整,那么就業歧視將如何影響這一貨幣政策的效果?為便于分析,借鑒Gali(2022)的研究[22],本文將這一貨幣政策規則稱為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定義N表示穩態總就業,那么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表示為:
式(35)中,參數ω反映貨幣政策當局對當期通脹的重視程度。如果央行以平均通脹為盯住目標,那么當期通脹的權重ω取值相對較小。為便于分析,不妨將其取值校準為0.3,這一取值意味著央行更加關注的是平均通脹。
圖2描繪了當貨幣政策當局分別以式(33)和式(34)作為貨幣政策行為方程時擴張性貨幣政策沖擊(1個單位標準差)產生的影響。顯然,無論貨幣政策當局執行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還是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擴張性貨幣政策均會引起產出、消費、投資、就業和物質資本租金率等宏觀經濟變量的增加以及整體物價水平的上升(通脹),這一發現與Gali(2022)以及陳利鋒和張凱鑫(2022)等的研究結果一致,且無論是否存在就業歧視,擴張性貨幣政策均會產生這些宏觀經濟效應。不過圖2顯示,無論貨幣政策當局執行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還是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當存在就業歧視時擴張性貨幣政策對產出、就業、消費、投資、資本租金率等宏觀經濟變量產生的影響均小于無就業歧視的情形,而對物價水平的影響則相反,就業歧視會導致擴張性貨幣政策引起更大幅度的通脹。
進一步比較就業擴展性泰勒規則與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可以發現,無論是否存在就業歧視,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帶來的產出增長和通脹幅度均較大,而就業擴展性泰勒規則帶來的就業和消費增長幅度較大。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是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使貨幣政策當局提高了對通脹的容忍度并放松了政策盯住的通脹目標,進而刺激投資更大幅度增加,投資更大幅度增加引起物質資本租金率更大幅度上升,最終推動更大幅度的產出增長和通脹。而在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下擴張性貨幣政策盡管對產出增長的作用相對較小,但會引起就業和消費更大幅度的增加,同時通脹幅度較小。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會引起更大幅度通脹,降低了家庭實際消費能力,因而這一貨幣政策機制下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消費的作用相對較小。如果貨幣政策當局采用就業擴展型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直接作用于就業,帶來經濟中就業的更大幅度增加,就業更大幅度增加又將帶來家庭收入更大幅度增加,因而消費也隨之更大幅度增加。由于消費與社會福利水平密切相關,因而從增加社會福利的角度看,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的宏觀經濟效應優于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
綜合圖1與圖2可以發現:如果貨幣政策當局以促進就業為目標,就業擴展型貨幣政策將是較優的選擇;雖然這一貨幣政策對就業的促進作用會因就業歧視的存在而被弱化,但其對就業的積極影響顯著大于標準泰勒規則和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如果貨幣政策當局以促進產出增加(經濟增長)為目標,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的效果則相對較好;盡管這一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會因就業歧視的存在而受到抑制,但是其對產出的積極影響顯著大于標準泰勒規則和就業擴展型貨幣政策。
表3對無就業歧視與存在就業歧視兩種情形下不同貨幣政策沖擊發生之后產出、就業和通脹的持續性和波動性進行了比較,可以發現就業拓展型泰勒規則和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均表現出與標準泰勒規則相同的效應趨勢:(1)從宏觀經濟變量的持續性來看,相比無就業歧視的情形,就業歧視的存在會導致產出和就業的持續性降低,而通脹的持續性則上升;(2)從宏觀經濟變量的波動性來看,相比無就業歧視的情形,就業歧視的存在會導致產出、就業和通脹的波動性增大。因此,無論是實施標準泰勒規則,還是實施就業拓展型泰勒規則和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就業歧視都會降低擴張性貨幣政策沖擊下宏觀經濟變量的持續性,并增強通脹慣性,同時導致更大的宏觀經濟波動。
貨幣政策沖擊下宏觀經濟變量的持續性可以直接反映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結合表2和表3可以發現:(1)無論是否存在就業歧視,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沖擊下的就業持續性最高而波動性最小。因此,如果貨幣政策以促進就業為目標,采用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的效果會更加明顯。(2)無論是否存在就業歧視,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沖擊下的產出持續性最高。因此,如果貨幣政策以促進產出增加(經濟增長)為目標,采用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的效果會更加明顯。但也應注意,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也會帶來較大的通脹和產出波動,需要加以適當防范。(3)從無就業歧視情形與存在就業歧視情形的比較來看,在標準泰勒規則、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下,產出持續性分別相差0.134、0.108、0.093個單位,就業持續性分別相差0.163、0.022、0.152個單位,通脹持續性分別相差0.184、0.119、0.137個單位,產出波動性分別相差0.044、0.046、0.043個單位,就業波動性分別相差0.059、0.014、0.77個單位。通脹波動性分別相差0.046、0.084、0.082個單位。可見,在不同的貨幣政策下,就韭歧視對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效應的影響具有明顯差異性,總體上看,就業歧視對貨幣政策就業效應的負面影響在施行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時最小,而對貨幣政策產出效應的負面影響在施行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時最小。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構建TANK-DSGE模型分析無就業歧視與存在就業歧視兩種情形下就業歧視對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效應產生的影響,主要結論如下:(1)擴張性貨幣政策的脈沖響應顯示,就業歧視顯著改變了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具體表現為:與無就業歧視情形相比,就業歧視的存在會弱化擴張性貨幣政策對產出、消費、投資、物質資本租金率和就業等宏觀經濟變量的積極影響,并引起更大幅度的整體物價水平上升(通脹)。(2)二階矩分析結果表明,就業歧視也顯著影響了擴張性貨幣政策沖擊后宏觀經濟變量的持續性和波動性,具體表現為:與無就業歧視情形相比,就業歧視的存在會降低產出和就業的持續性,提高通脹的持續性(增強通脹慣性),并增大產出、就業和通脹的波動性。(3)進一步的分析發現:無論貨幣政策當局執行何種貨幣政策(標準泰勒規則、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就業歧視對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都具有相似的負面影響,但影響程度存在差異。總體上看,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就業促進效應在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下最強,且就業歧視對其就業促進效應的負面影響最小,因而如果貨幣政策當局以促進就業為目標,就業擴展型泰勒規則是其較優選擇;擴張性貨幣政策的產出促進效應在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下最強,且就業歧視對其產出促進效應的負面影響最小,因而如果貨幣政策當局以促進產出增加(經濟增長)為目標,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則是其較優選擇。
盡管部分研究對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進行了批評(Billi et al,2020;Andrade et al,2021;Billi etal,2022),因為這一政策會導致通脹上升,但依據本文研究結論,當勞動力市場顯著存在就業歧視時,盯住平均通脹型貨幣政策并非完全不可取。現有研究基于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相關數據分析表明,就業歧視顯著存在于中國勞動力市場,結合本文的研究結論,減輕和消除就業歧視對于發揮貨幣政策的積極宏觀經濟效應具有重要意義。《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的發布無疑有利于加快減輕和消除中國勞動力市場上的各種就業歧視,進而有助于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在建設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大市場過程中,不但要通過市場機制的完善優化勞動力資源配置,而且企業也要摒棄勞動力偏見,切實基于各種勞動力自身實際的技能和素質進行用工決策。不過,各國政策實踐表明,完全消除就業歧視在短期內難以實現(張霞,2020;林文軍,2021)。因此,在貨幣政策實踐中需要依據宏觀經濟條件并結合存在就業歧視的現實進行科學決策,具體的政策操作取決于貨幣政策當局的宏觀經濟目標(就業或者經濟增長)。
本文嘗試通過將就業歧視引入TANK-DSGE模型分析就業歧視對貨幣政策宏觀經濟效應的影響,也存在一些需要改進和深化之處:(1)現實經濟中就業歧視的表現具有多種形式,比如性別歧視、戶籍歧視、教育背景歧視以及年齡歧視等(Khera,2016;鄭妍妍等,2020),因此,未來可進一步對多種形式的就業歧視進行量化處理并引入動態宏觀經濟模型中,進而更加全面細致地分析就業歧視帶來的影響。(2)現實經濟中個體之間在家庭出身、教育背景、身體狀況等方面均存在明顯差異,更加科學合理的建模方式是構建異質性主體新凱恩斯主義(Heterogeneous Agent New Keynesian,HANK)模型。已有研究發現HANK模型得到的結論比傳統新凱恩斯主義模型更加可靠(Auclert et al,2020;Debortoli et al,2022)。因此,可進一步將就業歧視引入HANK模型中進行分析。(3)在本文構建的模型中僅比較了存在就業歧視與無就業歧視兩種情形,而在現實經濟中就業歧視程度存在顯著的差異性,更為科學的做法是分析和比較不同程度就業歧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