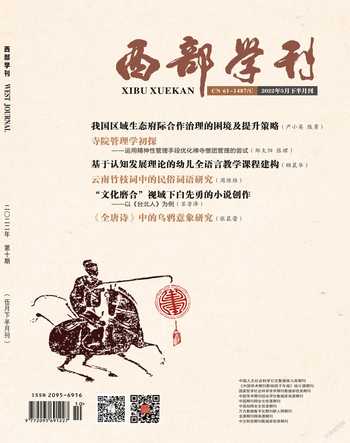馬克思與海德格爾人學思想研究
摘要:人學思想在馬克思與海德格爾的哲學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并且都與其語言觀有所連接。馬克思與海德格爾都對西方形而上學語言觀所認為的“語言僅僅是一種發出者的主體性活動”進行了批判,二者都不再將人當作西方傳統形而上學中的客觀對象,而是將人當作認識主體進行研究。但二者也有著極大的差異,一方面是海德格爾對“技術語言”的批判與馬克思對語言這一“獨立王國”的批判相悖離;在對于“本真的人”的落腳點上,二者的表述也大相徑庭,這是二者在人學思想上最大的分歧之處。
關鍵詞:馬克思;海德格爾;人學;語言觀
中圖分類號:B516.5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6916(2022)10-0160-04
馬克思的人學思想以及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都是哲學領域反復研究的內容,也總有學者對二者的語言觀進行比較研究,但在進行馬克思與海德格爾二者的比較研究時,二者的語言觀或是根本就沒有出現,或是僅僅作為論證的其中一條論據出現。二者作為對語言觀有著明確論述的哲學家——馬克思的“語言是感性的自然界”和海德格爾的“語言是存在的家”,其語言觀就體現著二者在人學思想上的異同。
二者共同的進步之處在于均通過對語言的解讀,成功地將視角從“人是什么”轉向“人的存在”本身:馬克思是通過語言與感性的人組成的客觀世界之間的聯系,將目光轉向現實的、感性的人;海德格爾則是通過追問語言本真的存在將目光轉向敞開狀態的此在。而二者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則在于對“人的存在”中的人究竟是具體的,還是抽象的。本文從馬克思與海德格爾的語言觀出發,分別探討二者語言觀與其人學思想的關系,并以語言這一概念為線索,對二者的人學思想進行比較研究。
一、人學思想在馬克思與海德格爾哲學中的地位
馬克思的人學思想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是十分重要的一個鎖扣。馬克思在《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曾對費爾巴哈的人本學唯物主義大加贊揚,甚至認為費爾巴哈關注到了所謂的“真正的人”,即“使‘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成了理論的基本原則。”[1]158但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第一條則指出了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的根本弊端,即他一直都只是將其當作認識的客體,但卻從未將其“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2]3。不難看出,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人學思想在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一切舊唯物主義哲學區別開來中具有不可撼動的作用,即歷史唯物主義中的人的主體性。另一方面,馬克思區別于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主義的最根本差別也在于其人學思想的內涵,即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是將抽象的人當作認識對象,馬克思則是將具體的人,即感性的人當作研究對象。
在研究海德格爾存在論的過程之中,總是避不開“此在”。海德格爾曾在《存在與時間》中提到過“此在”的重要性,他認為只有當此在存在時,才存在“存在”,而一旦此在失去了存在狀態,那么,諸如此類的東西也就失去了被領會的可能,并且一旦此在不再存在或是生存,存在者也就既不是敞開的也不是可遮蔽的了。那么我們在研究此在的過程中,“存在者”又出現了。因此,人們又總是不得不從追問存在者開始。海德格爾曾在存在與時間中寫下“人的實質是生存”[3]261,緊接著他寫道,“唯當存在者是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的存在者,存在之領會作為存在者才是可能的”[3]261。這也就意味著,當我們在探討海德格爾存在論時,如果想要理解“此在”,我們依舊還是要從人的存在出發,去追問存在者的存在。事實上,關于類似的表述在《存在與世間》這本著作中很多,海德格爾這也就不難看出人學思想在海德格爾存在論中的重要性。
二、馬克思的語言觀與其人學思想的關系
馬克思對于語言觀的論述大部分都集中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這部著作中,他在本文中對語言的產生、語言的歷史發展等都做了描述。在馬克思看來,語言從不是與生俱來的東西,語言與意識具有不可分別的緊密聯系,“語言是一種實踐的……現實的意識。”[2]34馬克思就曾寫道,“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2]525。語言從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它是受到人們需要的驅使,帶著幫助人們進行感性交往活動的任務產生的,即馬克思表述的:“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2]34而語言的產生和發展又同物質生活以及人們的勞動過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2]2這一點在馬克思的《手稿》中也有所體現。馬克思在《手稿》中還直言不僅是活動所需要的資料,就連思想家用以進行活動本身“都是作為社會的產品給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會的活動”[1]122。這也是說,馬克思的語言與人本身在來源這一層面實際上是同源的,即終究都來自于客觀物質世界中,且隨著世界的變化而發生變化。
而馬克思的客觀物質世界從不是機械的、一成不變的客觀對象,它是由現實的人的感性活動所組成的發展的世界,正如馬克思在《手稿》中的論述一樣“人的第一個對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1]129在這里,馬克思所描述的對象就是感性的自然界,而人們面對的感性的自然界恰恰就是由現實的人的活動所組成的。而緊接著馬克思就寫道,“語言,是感性的自然界。”[1]129因此,馬克思的人學思想從不是以抽象的人為元素,而是由具體的、感性的人作為研究主體的。
由此可見,馬克思的語言觀中實際上是包含著對人的存在本身以及人如何存在的理解的:語言與人的意識不可分割,語言以及意識又隨著是現實生活的變化而發生變化,現實生活即現實世界又是由現實的人的感性活動所組成的,那么,語言作為“思維本身的要素”自然就是“感性的自然界”的直觀體現。
三、海德格爾的語言觀與其人學思想的關系
海德格爾的語言觀在其存在論思想中也有多處體現。首先,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海德格爾提出語言的命運與存在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他甚至認為“發問存在的問題與發問語言的問題在最中心處將會交織在一起。”[4]而在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這部著作中,海德格爾又論述了語言與其存在論哲學有著密切的聯系。他認為“組建著此在之在、組建著在世的展開狀態的基本生存論環節乃事現身與領會”[3]202,“話語同現身、領會在生存論上同樣源始”[3]202,而“語言的生存論存在論基礎是話語”[3]202。由此可見,語言這一概念在海德格爾存在論中的重要程度。80253BB6-C083-4B3F-B36D-B6DC0592CF56
其次,在海德格爾的表述中,充滿了對語言本身所具有的生存論思想。一方面海德格爾認為“話語本身包含有一種生存論的可能性——聽”。在他看來“聽”在話語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當此在向某某東西聽時,此在是處于敞開狀態的,而且這種此在的敞開狀態是最首要的、本真的敞開狀態,因此海德格爾認為“這種能聽在生存論上是最原初的”[3]205;另一方面海德格爾認為話語的另一種特殊狀態即沉默也是生存論的元素,“話語的另一種本質可能性即沉默也有其生存論基礎”[3]206。在他看來沉默并不意味著“黯啞”,真正的沉默實際上是存在于真實的話語之中的“緘默”,而若想達到緘默,此在本身必須具有豐富的敞開或是展開狀態。總而言之,話語對于此在具有不可替代的構成作用,此在必然具有語言。
在“關于人道主義的書信”中,海德格爾對西方形而上學語言觀進行了批判,他對語言和存在的關系表述為“語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語言之家為家”。陳嘉映曾用海德格爾引用過的詩句對這部分進行解讀,“只有一個適當的詞把事物命名為存在者,這樣事物才存在。所有存在者的存在都居留在言詞里……然而,這種解釋法無異于把詩降為仆役。”[5]306海德格爾在這里實際上想要表達的是人們居于語言的“獄所”之中,人實際上只是“看家人”而非“創作者”。在海德格爾看來,形而上學在西方的“邏輯”以及“文法”形態中,過早地“霸占”了語言的解釋,這也就意味著語言實際上淪為了“技術語言”。海德格爾則希望將這種“技術語言”解放出來,還原成原處狀態,回歸到本初的本質結構。那么,在海德格爾看來,語言和人之間到底應是怎樣的關系呢?答案是“語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爾曾以“語言的本質”作為演講的主題進行演講,他提到過“經驗語言”這一概念,陳嘉映在《海德格爾哲學概論》中對此做出了詮釋,他寫道,“人說話,即使一言不發,即使一人默默勞動或自娛,人仍在說話。”[5]303這也就意味著,語言絕不是人的表達狀態,而語言也絕不僅僅是人的一種能力,語言作為一種存在本真的狀態,實際上是人的天性,“人在語言中有他最本真的居處”[5]304。而語言經驗與其他經驗是有著巨大差異的,語言經驗并非像其他學科抑或是生活經驗那樣通過經歷更多去獲得更多的經驗與知識,語言經驗絕不是獲得更多的語言知識,而是“要讓語言自己說話”[5]304。語言是物之外的存在,但語言又絕不是存在者。
總而言之,海德格爾語言觀與存在論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而探討海德格爾的存在論又必然要從追問存在者、追問此在開始。易言之,海德格爾的語言觀中是包含著對于存在的解讀的。
四、馬克思與海德格爾人學思想之比較
(一)二者一致之處——對于西方形而上學語言觀的批判
傳統西方形而上學的語言觀是一種主體性形而上學語言觀,即語言僅僅是一種發出者的主體性活動。但海德格爾的語言跟存在著者的關系實際上是“滋予存在者”,而非就是存在者。海德格爾認為語言就是語言,語言自己言說。馬克思的語言觀更加不是這種主體性形而上學的語言觀,在他看來語言的確是從主體發出,但并非是從主體出發,語言作為人們(馬克思在《手稿》中曾用思想家舉例)進行活動的本身,實際上是社會給予人們的。因為在馬克思看來,這種語言作為橋梁的活動實際上是一種社會的活動,人實際上是一種社會的存在物。當然二者在這一點上仍有區別,但無疑都是對傳統西方形而上學語言觀的批判,其具體差異在下文論述二者差異時進行分析。
馬克思與海德格爾的人學思想有著極為重要的相通之處,從對語言觀的表述就可見一斑。馬克思的語言觀中體現著其唯物主義精神,表現著不同于以往一切舊哲學的人學思想,即以感性的人為要素的客觀物質世界。馬克思不再把目光停留在抽象的人身上,而是將目光聚焦于每一個感性的、活生生的、現實的人。這就足以說明,馬克思此時已經不再向舊哲學那樣——“解釋世界”,而是去“改變世界”。而海德格爾更是通過其關于語言觀的表述,將自身的存在主義同西方傳統形而上學區別開來,他已經不再將語言當成禁錮人的工具抑或是牢籠,而是真正地追問語言的存在,也就是最本真的存在。這也就意味著,海德格爾也從追問“人是什么”,轉向探討最本真的存在,無論是語言的存在還是人的存在,都是如此。
簡言之,馬克思與海德格爾的人學思想與西方傳統的人學思想的根本不同之處在于,西方傳統的人學思想不曾脫離主客二分的視閾去考察人,而總是把人當成客觀對象,且不去考察人如何存在,而總是討論人是什么。二者都摒棄了傳統西方人學的弊端,繼而向著人本身回歸,不再把人當成客觀對象,任意的定義為精神、物質或是二者的結合體,而是將人作為認識主體進行研究,將目光從“人是什么”轉向“人的存在”本身。因此,馬克思與海德格爾的人學思想則向前邁進了一步,他們將人學思想從西方傳統哲學的認識論視閾轉向存在論視閾中去,這一點無疑是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的。
(二)二者相異之處
1.對“技術語言”的批判vs對語言這一“獨立王國”的批判
海德格爾在人道主義的書信中曾對成為某種主義的哲學進行批判,在海德格爾看來這是由于思想成為了一種技術,一種手段,語言同理,當語言成為了一種交通的途徑、一種媒介的手段,那么語言就成為了一種“媒介之役”,在海德格爾看來這將會導致“語言的墮落”——語言就此成為一種“技術語言”。由此可見,海德格爾實際上對于技術語言持一種否定的消極的態度。馬克思則認為語言是由于需要而產生出來的,因此語言從一開始產生的目的就是成為社會活動的橋梁,這并非是一種消極的技術語言,而是一種必要的手段。因此,馬克思在這一點上和海德格爾的傾向無疑是有所出入的。
既然在馬克思看來,語言從一開始產生就是為了成為社會活動的橋梁,這也就從側面說明了,馬克思從不認為語言是一個獨立的語言王國。馬克思還曾直言“無論思想或語言都不能獨立組成特殊的語言王國,它們只是現實生活的表現。”[2]525俞吾金老師曾提到:“古典詮釋學和當代詮釋學的一個通病是把語言視為獨立王國。”事實上海德格爾同樣也具有這一傾向,從上文提到過的海德格爾認為“語言就是語言,語言自己言說”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在海德格爾看來,語言實際上就是一個獨立的王國。這一點上二者的差異也是十分顯著的。80253BB6-C083-4B3F-B36D-B6DC0592CF56
2.“本真的人”的落腳點——二者不可逾越的鴻溝
但是,二者的人學思想也具有不同之處。二者雖然都向著人本身回歸,將視角聚集于本身,但其回歸的落腳點依舊有所差異,即馬克思是向著人的感性活動回歸;而海德格爾則是向著源處的存在回歸。這就是說,即便二者都把目光聚焦于人如何存在,馬克思的落腳點即感性的人是具體的;而海德格爾的此在則仍是抽象的,這通過二者的語言觀就能說明。上文提到過,在馬克思看來,語言是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演變的,即具有歷史性。因此馬克思提到的人必然是感性的活動的人,是具有歷史性的人,而海德格爾的此在則仍停留在抽象的人中。換言之,盡管馬克思與海德格爾都將人作為認識主體進行研究,但是馬克思將每一個感性的人當作認識對象,但海德格爾僅僅是將抽象的人當作認識對象,他并沒有將每一個感性的人看作是研究的對象。當然這與二者出發點不同的原因密切相關,馬克思與海德格爾雖然都不同于西方傳統形而上學的觀點,但海德格爾是為了構建后形而上學推翻西方傳統的形而上學;而馬克思則是為了人的解放對西方形而上學進行批判,因此二者的落腳點也必然有所差異,這恰恰是二者在人學思想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結語
通過對馬克思與海德格爾語言觀進行分析,可以看出二者的人學思想雖然有著十分重要的相通之處,但同時也包含著不可逾越的巨大差別。馬克思與海德格爾對于傳統西方形而上學的超越不容小覷,但從馬克思的人學思想角度出發,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思想仍然具有著不可忽視的缺陷。事實上,馬克思與海德格爾的人學思想都并非是完備無缺的,其深層次的意義還有繼續發掘及發展的無限可能,就像馬克思的語言觀一樣,二者的人學思想也必然要隨著歷史的變化而不斷豐滿。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馬丁·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M].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4]馬丁·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M].熊偉,王慶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57.
[5]陳嘉映.海德格爾哲學概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2005.
作者簡介:周家盈(1997—),女,漢族,黑龍江哈爾濱人,單位為黑龍江大學,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
(責任編輯:楊超)80253BB6-C083-4B3F-B36D-B6DC0592CF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