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革命大歷史
奧戴德·蓋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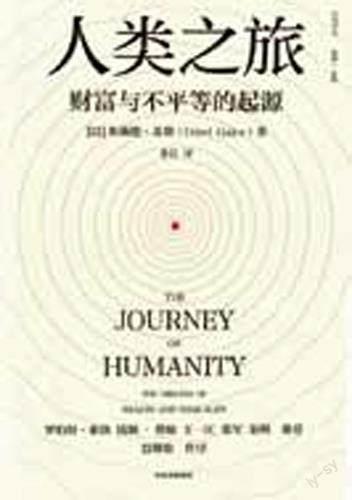
1989年,在多年干旱之后,以色列北部加利利海的水平面大幅下降,暴露出一個有23000年歷史的小型村落的遺跡。
考古學家在此發現了6間保存較好的小木屋的殘余,還有燧石、骨制和木制工具、珠子以及人類骸骨。
乍一看,這似乎是一個典型狩獵采集部落的定居點。考古學家深入挖掘,他們發現了驚人的先進技術的證據,例如收割作物的鐮刀和碾磨谷物的磨石,此類物品此前只出土于晚得多的年代遺址。
“奧哈羅二號”遺址的證據表明,村莊居民種植、收獲小麥與大麥的時間,比過去公認的提前了大約11000年。
這個村莊,在幾代人之后被燒毀和廢棄了。大規模農業的最早證據,則來自它附近的考古遺址,例如約旦河谷的耶利哥、大馬士革附近的阿斯瓦德。
那么,為什么農業革命首先發生在這一地區?為什么其影響會如此深遠?
農業革命
針對為什么歷史上的大多數強大文明興起于歐亞大陸,而非撒哈拉以南非洲、美洲或大洋洲的問題,賈雷德·戴蒙德(美國演化生物學家,《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給出了一個有意思的回答。
戴蒙德提出,歐亞大陸較早出現農業革命,是源于生物多樣性和大陸走向。
他認為,農業革命最早出現在大約12000年前的肥沃新月地帶,是因為那里有類型豐富的可馴化動植物品種。
地球上的大顆粒野生谷物中,有相當多最早是在肥沃新月地帶種植的。
人類農業的初始作物,包括小麥、大麥、亞麻、鷹嘴豆、小扁豆和豌豆,還有多種果樹,以及綿羊、山羊和豬等各種動物,都在這個富饒地區最早被馴化的。
同時,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生物多樣性,促使東亞和南亞在大約10000年前獨立發展出農業。
世界其他地區同樣嘗試去馴化野生動植物,然而,那里生物對適應的抵抗,阻礙或拖延了這一過程。
肥沃新月地帶的野生谷物價值較高,相對容易馴化,可以通過自花授粉來繁殖,蛋白質含量較高,并適合長期儲存。
在肥沃新月地帶種植小麥和大麥幾千年后,中美洲的居民才成功馴化玉米。類似的困難妨礙了其他作物和樹木的馴化,并依然在產生影響,例如橡樹。
橡果是美洲本土居民的一種重要食物來源,他們發明了去除其苦澀單寧酸的辦法。
可馴化的動物種類則更為有限,在各大洲之間差別懸殊。
到農業革命發生的時期,非洲和歐亞大陸的動物,都與不同人類物種共同生活了數百萬年,不斷調整適應他們日漸發達的狩獵策略。
在大洋洲與美洲,人類是在發展到相當成熟的階段才抵達那里。當地的大型動物,沒有充分的時間適應較為發達的人類狩獵技能,多數在首批狩獵采集部落抵達后不久便走向滅絕,沒有生存到人類社會開始馴化野生動物的時代。
戴蒙德認為,歐亞大陸較早轉型到農業時代,與第二個地理因素有關,即歐亞大陸形狀的東西走向。
歐亞大陸主要沿著水平軸延伸,很大部分區域位于相近的維度,有著類似的氣候條件。
在農業革命時期,這有利于植物、動物和農業實踐在廣大區域內的傳播擴散,新的農業技術與新近馴化的作物可以快速而廣泛地推廣,沒有重大地理障礙。
相反,非洲大陸與美洲大陸基本上沿著南北軸延伸。
蒼蠅之害
農業革命的興起,存在地理的偶然性。
工業革命前,牲畜是世界許多地方開展農業耕種的基礎。動物不僅是重要的食物來源,還提供紡織用的纖維、作為運輸工具。
在歐亞大陸,牛是農業革命的核心要素之一。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脈,羊駝與美洲駝是負重牲畜,以及羊毛與肉類的來源。在阿拉伯、撒哈拉與戈壁的沙漠中,駱駝不僅馱著人群穿越荒野,還提供了旅途中需要的皮毛和乳汁。
不過,地球上有一個地區嚴重缺乏牲畜:在北方的撒哈拉沙漠與南方的卡拉哈里沙漠之間,跨越非洲東西海岸的一大片陸地。在歷史上,這個地區的人口也相對稀少。
為何會缺乏牲畜呢?答案在于一種不起眼的蒼蠅。
采采蠅在非洲中部的濕熱環境中大量繁殖,以吸食人類與動物血液為生。它是一種致命寄生蟲的介體,后者會導致人類染上昏睡病(或稱非洲錐蟲病),也會讓山羊、綿羊、豬、馬和其他牲畜染上類似的疾病。
這種寄生蟲會殺死某些被感染的動物,削弱存活者的產奶量與力氣,使人類社會無法依賴那些牲畜。
采采蠅不是拖累非洲經濟發展的唯一昆蟲。
某些氣候條件下生長的按蚊,能夠把瘧疾傳播給人類,也給那里造成了嚴重威脅。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東南亞和南美洲受瘧疾影響的地區,嬰兒死亡率很高,得以存活的兒童也經常被持續的認知缺陷困擾。
這一風險還迫使父母們增加生育子女的數量,削弱他們對子女人力資本投資的能力,降低女性的教育和勞動參與率。
最近幾十年來,醫療領域的突破,已制約了其他傳染病對經濟增長的副作用,可由于缺乏有效的瘧疾疫苗,在其流行的地區,這種疾病仍妨礙人力資本積累與增長過程。
除傳播疾病的昆蟲外,其他地理因素同樣對經濟發展有影響。
在鐵路與飛機運輸發明之前,靠近海洋或通航河流是開展貿易、傳播技術與獲取海洋資源的一項關鍵優勢,對發展進程與國家形成有重要意義。
先發優勢
農業技術以及馴化動植物的更快普及,對歷史進程作用巨大。
它給歐亞大陸文明帶來了技術領跑優勢,優勢一旦取得,后續更是倍增。灌溉和耕作等技術創新,產生了更多的農業收獲,使人口密度得以提高。
勞動分工能夠促進開發更高效的生產方法,以及產生不從事食物生產的階級,從而推動知識創造乃至技術的繼續進步。
就這樣,一種進步帶動另一種進步,肥沃新月地帶的文明,開始興起世界上首批城市和建筑奇跡,冶煉銅和后來的鐵,并發明文字書寫系統。他們還設計出了促進增長的制度,倡導財產權利與法治的概念,支持資源的高效利用。
之后的發展道路,也經常遇到強勁的逆風。
人口密度增加、動物馴養擴大,讓人類更容易暴露在細菌與病毒的威脅之下。
歷史上某些破壞力最大的疾病,如天花、瘧疾、麻疹、霍亂、肺炎和流感,最初都起源于動物疾病的變異,在農耕或畜牧社會中傳染到人群。在短期內,這些疾病引發了大瘟疫和極高的死亡率。
較早經歷農業革命的人群,發展出抵御此類傳染病的更強免疫力,最終幫助他們接受了城鎮中的惡劣疾病環境。
在人類戰爭史上,勝利者經常是那些攜帶最致命病原體的一方。
例如,在16世紀,西班牙人攻擊了美洲最強大的兩個帝國,即位于今天墨西哥的阿茲特克帝國和如今秘魯一帶的印加帝國。
西班牙人帶著天花、流感、斑疹傷寒和麻疹病毒登陸,這些疾病此前從未在美洲出現。
無數阿茲特克人很快因此喪生,倒數第二代國王奎特拉瓦科(Cuitlāhuac)似乎也未能幸免。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率領的征服者們,有自身免疫系統的保護,并配備先進技術,得以迅速把中美洲最強勢的帝國降伏。
大多數記載稱,印加帝國的皇帝瓦伊納·卡帕克(HuaynaCapac),是在1524年被肆虐帝國的天花或麻疹擊倒,他的兒子們隨即陷入爭奪繼承權的混戰之中。在北美洲、太平洋群島、南部非洲和澳大利亞,當首批歐洲人登陸和打噴嚏,把來自歐洲的病菌播撒出來后,大量土著人口遭遇了滅頂之災。
在每個大陸,較早的農業文明往往利用更多人口和更先進技術,來取代狩獵采集群體,把某些群體驅逐到偏僻角落,摧毀或合并另一些群體。
在有些情況下,狩獵采集者接納了農業,較為自愿地改變了自己的生存策略。
事實上,當歐洲人抵達時,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某些土著人群,已經在數千年前轉型成農業社會,但這依然為時太晚。
征稅作物
向定居農業轉型,是技術發達的文明興起的必要條件,歷史卻說明這還不能算充分條件。
例如,新幾內亞島的居民與尼羅河三角洲的埃及人,在幾乎同一時期發展出了農業。
古埃及成為世界最早的帝國之一,通過嚴格的政治等級秩序實行統治;新幾內亞的農業生產率提高,卻使那里的高地人群被分裂,陷入頻繁的部落戰爭,沒有發展出超越部落層面的集中權力。
這一令人費解的格局是如何形成的?地理因素,尤其是不同地區土生土長的農作物類型,同樣能夠提供一個可行的解釋。
剛剛實現向農業轉型時,大多數社群仍保留著基本部落結構。
在人數僅有數百人的社群里,幾乎所有人都與本部落其他成員熟識,而且經常存在親緣關系。通常而言,每個社群都有一位出眾的領袖,負責執行基本的規則,組織需要聯合的公共行動。
人口密度一增加,新的組織架構開始出現。
通常來說,農業社會政治發展的下一個階段是酋邦(Chiefdom),這是一種包含多個村落或社區、由一位最高領導管理的等級社會。
酋邦最早出現在肥沃新月地帶。
隨著該地區的社群日漸壯大,人們需要經常同親屬圈子之外的人打交道。為促進廣泛的合作,這些更復雜的社群發展出了新的特征:長期且往往世襲的政治領導人、社會階層分化與決策集中化。
地位的區分又得到文化習俗、信仰與實踐的強化和固化,往往帶有宗教性質。關鍵之處在于,這些等級社會通常征收稅賦或什一稅,以養活精英階層,并支持興建公共基礎設施。
自從酋邦出現以后,它們存在的必要條件都是征稅能力,若沒有這一點,很難維持幾千人規模以上的政治實體。
在農業發展階段,稅收主要用收獲的農作物來繳納。因此,稅收的實施和效率取決于所在地區的主要作物類型。
在比較發達的古代文明中,農業主要依賴谷物,而非利用塊莖和根莖的木薯、甘薯和番薯等。
谷物的測量、運輸和儲存要容易得多,因此更容易征稅。有歷史證據顯示,土地適合種植谷物的地區更容易產生復雜的等級制社會。
相反,收獲物以塊莖和根莖為主的地區有更簡單的社會組織形態,類似于牧人或游居者的社群。這些地區的統治者征稅較為困難,甚至較早經歷農業革命的地方也沒有發展到這種城邦、國家和帝國更復雜的等級社會。
結構化的政治實體有能力蓄養軍隊、提供公共服務、維護法律和秩序、投資人力資本、執行商業合同,所有這些都有利于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
因此,土地適宜種植谷物還是塊莖作物,對國家形成、知識創造與技術進步具有重大作用,進而影響推動人類歷史前進的巨型齒輪的運轉速度。
文化塑造
著眼未來、立足長遠的心態,是實現經濟繁榮最重要的文化特性之一,影響著我們對儲蓄、教育、開發和采納新技術的態度。
這一文化特性的起源,可溯源到農業及其地理環境。
農作物產量差異,或許是不同地區出現不同的面向未來態度的根源。在農作物產量更高的地區,投資策略可能收益更大。
顯然,農作物產量在各大洲內部和之間的分布并不平衡。
具體來說,在公元1500年之前,歐洲(大麥)和亞洲(稻米)的主要作物,在每畝土地上能夠產生的日均潛在熱量幾乎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主要作物(豌豆)的兩倍,所需的種植時間(從播種到收獲)卻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二。
實證研究發現,在每個大陸中,起源于農作物潛在產量更高地區的族群,往往更具有長遠眼光(在排除其他地理、文化和歷史因素的影響之后)。
對當代在美國和歐洲的第二代移民的研究發現,他們面向未來的傾向,同父母來源國而非自己出生和長大所在國的潛在作物產量相關。
就是說,作物產量(及背后的農業氣候特征)對面向未來傾向的影響,不是地理因素的直接效應,而是包含于文化中,代代相傳。
農作物把地理條件轉化為文化特性,不只是通過產量,它們要求的耕種方式也在發揮作用。
來自中國各地的資料表明,土地適宜種植稻米,因此需要彼此共享的大規模灌溉系統,這有助于培育相互協作的集體主義文化;如果適宜種植小麥,因此所需的協作程度更低,這導致了更具個人主義特征的文化興起。
跨國比較也發現,適宜勞動密集型作物種植的土地,與更具集體主義特征的文化興起相互關聯。
在地理條件中,我們還可以找到有關性別文化特性的源頭。
1970年,丹麥經濟學家埃斯特·博賽拉普(EstherBoserup)提出的假說認為,各地區如今對待職場女性的態度差異,源于前工業化時代的不同農業耕作方式。
她解釋說,因為各地區的土地特性與主流作物不同,某些地區的農民用鋤頭和耙子翻地,其他地方則用牛馬拉動的犁。
利用犁和控制牲畜需要相當大的上肢力量,因此在使用這一耕作方式的地區,男性擁有更顯著的身體優勢,女性在歷史上更多限于從事家務勞動。博賽拉普指出,土地是否適宜使用犁來耕作,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性別之間的勞動分工。
來自世界各地農業社會的證據,支持了上述觀點。
采用犁的地區始終有著更鮮明的家庭內部勞動分工:男人主要從事農業,女人主要做家務。
在使用鋤頭和耙子的地區,男人和女人往往分擔農業勞動,從土地整理到播種收獲,以及取水、照看奶牛、收集柴火等,大多數家務勞動仍主要由女人承擔。
許多性別偏向與犁的使用有關。這或許可以部分解釋,為什么歷史上較早和較多使用犁的地區,例如南歐、中東和中亞,女性面孔更少出現在職場、政界和企業董事會之中。
優勢消退
在大約1萬年的時間里,幾乎所有地方,幾乎所有時期,農業革命的擴張都在上演。
在東亞,農業革命于大約1萬年前在中國北方展開。
語言學證據顯示,隨著農民涌向南方,他們沿途取代了大部分狩獵采集部落,以及較落后的農業社群。
在大約6000年前,從中國東南部遷入的農民到臺灣島上定居。
大多數研究認為,這批移民及其后裔,即南島人(Austronesians)利用航海技術在島嶼之間旅行,到達如今的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再跨越更廣闊的海域,向東抵達夏威夷與復活節島,向南抵達新西蘭,向西抵達馬達加斯加。
幾千年來,世界上較早經歷農業革命并享有谷物稅收便利的地區,確實有著更高的人口密度和更發達的技術。
早期文明出現在肥沃新月地帶,顯然不是偶然,任何隨機事件,都不可能讓撒哈拉沙漠的中心地帶產生并維持強大的古代文明。
然而,得益于地理條件、較早進入農業革命并形成國家的許多地方,今天卻處于相對貧困的狀態。
肥沃新月地帶是農業革命與早期人類文明的搖籃,它現在并未處于經濟繁榮的前沿。經歷農業革命的時間,土耳其與歐洲東南部,比英國和北歐國家要早數千年,如今也更為貧窮。
實證研究表明,農業革命發生的時間,對前工業化時代的生產率有顯著影響,這一效應在公元1500年后已消散。過去500年,農業革命的效應為什么會減弱?這一時期發生了什么變化?
從16世紀初以來,隨著創新活動從鄉村轉向城市地區,農業部門(耕種)的經濟重要性開始逐步走低,人力資本密集和技術為本的城市部門變得欣欣向榮。
于是,較早開啟農業革命反而產生了一種負作用。
農業的比較優勢,讓這些社會專門發展這個產業,延緩了城市化步伐與相伴的技術進步,推遲了人力資本形成和人口大轉型的到來。
隨著城市部門對新技術發展的重要性提高,農業生產比較優勢的副作用,變得更加突出,較早開啟農業革命的技術優勢則逐漸減弱。
城市和海洋國家,也開發出能夠更好地利用全球貿易的技術和金融工具,殖民時代到來,專業從事農業部門的不利影響被進一步強化,也更多地抵消了過去的領跑優勢。
不過,制度和文化演進,乃至農業革命,從來都是歷史整體過程的推進速度以及各國和各地區差異格局的關鍵決定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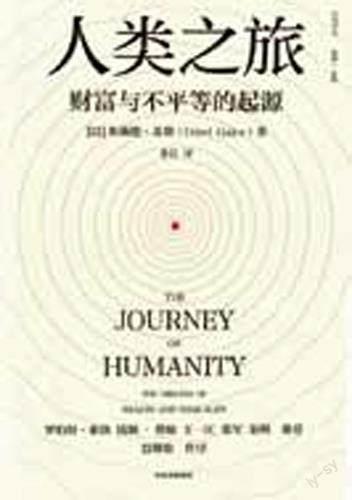
本文選編自《人類之旅: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奧戴德. 蓋勒著,余江翻譯,中信出版社授權刊載,2022 年8 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