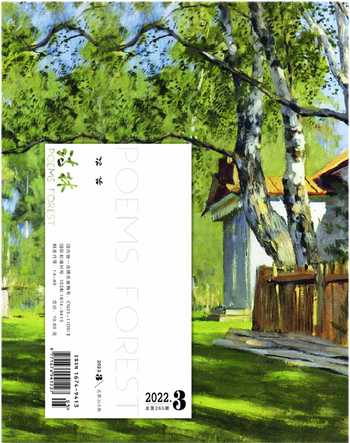重新發現詩人孫基林
趙思運
最近十年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新詩界的學者越來越多地顯示出詩歌創作的才華,構成了一個豐富的詩歌譜系。這貌似異軍突起的現象,細究起來,恰恰表征出一個常識——詩學研究永遠以詩性創造的感性經驗作為先導,很難想象一個優秀的新詩學者卻缺乏詩歌創作經驗,在這個學者型詩人譜系中,孫基林無疑是尚未引起充分注意的一位。
雖然孫基林只“泄露”出創作于20世紀80年代的部分詩作,但可以窺見,其詩歌創作的基因很大程度上全息投射到了后來的研究之中。在他的生命年輪的核心,詩歌的感性經驗和詩性創造力構成了不可遏制的詩學胚芽。隨著季節輪換,詩性創造的感性力量伴隨著學術理性的積淀,同步交融,茁壯成長,其詩頑強地通過詩學研究的年輪輻射出來。
孫基林的詩歌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敘述性,《原野上的葬儀》即是如此。他的詩歌敘述技術迥異于傳統的敘事詩。傳統的敘事文體往往更注重敘事要素,即使新詩的敘事也講究內容的具體性和逼真感;孫基林的詩歌敘述,則更加注重敘述的整體性和象征性。對敘述藝術的實踐,為孫基林后來開創的新詩敘述學體系奠定了基礎。豐沛的創作體驗,使得孫基林的詩學建構不是純粹的學理演繹,而是感性實踐與學理演繹雙重視域的交相輝映。這種詩學與實踐的互文性,我稱之為詩學重瞳現象。
孫基林的詩學重瞳現象還有一個表現:他的詩歌創作較早地突破了朦朧詩的意象詩歌模式,開啟了第三代詩歌的口語表達式。這種詩歌實踐的過渡性,使他更真切地洞徹了朦朧詩的內在緊張性與詩學困境,較早地敏銳于第三代詩歌的發生肌理與文本肌質。他在80年代的詩歌創作,似乎預示了他最早在《崛起與喧囂:從朦朧詩到第三代》中確立的當代詩學格局與詩學走向。
他的詩歌風格體現了從朦朧詩潮到第三代詩潮的嬗變特點,帶有詩歌史的刻度意義。在語言表達方面,孫基林的詩作具有意象詩與口語詩過渡的轍跡。《黃昏的小樹林》是典型的意象抒情,帶有夏多布里昂筆下的唯美的死亡詩意;《原野上的葬儀》主要是意象敘事特征。這兩首詩更多地表征出朦朧詩群的共性。
孫基林的詩讓我想到韓東的創作,二人確實具有可比性。20世紀80年代初期,他們一起在山東大學讀書,一起創辦“云帆詩社”,韓東是以決絕的態度試圖與傳統的題材實現斷裂,拆解了深度模式和不確定性,剝離物性與文化的粘連關系。如果說韓東的策略是“反題”,那么,孫基林的策略則是“正題”,是建設性的。兩人殊途同歸,實現對于傳統詩歌意象的“疏離”。
孫基林的詩歌實踐與詩學研究之間的重瞳現象,我們也可以做一些隱喻性的解讀。在上古神話的記載里,有重瞳的人一般是圣人;但在現代醫學的解釋里,這種情況屬于瞳孔發生了粘連畸變,從O形變成∞形,但并不影響光束進來。我想,在詩人的眼里,在詩歌學者的眼里,建立敏感的雙重“詩性視野”,突破常規意義的“正確性”,這種“畸變”恰恰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