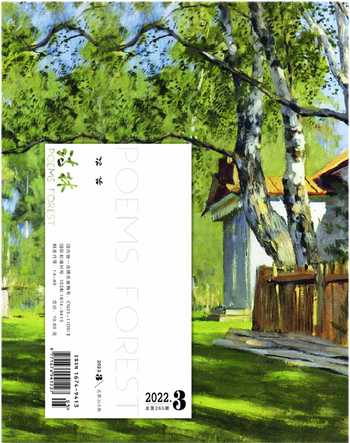論“第三代詩”的本體意識
孫基林

“第三代詩”作為一種開放的并漸次生長著的詩體形態,雖然至今仍不能說已然趨于完結,但它畢竟正在成為傳統而匯入詩的歷史之中。因而,當我們今天再次面對和返觀“第三代詩”的歷史情景時,至少可消解先前那份置身其中的最初的驚奇、無奈以及或褒揚或貶抑的情緒因素,而得以客觀理智地去審視、闡釋或給予某些價值的認定。當然,給“第三代詩”一個適切的歷史定位,或許還需要時間和距離,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返轉身去,僅僅等待那雙無形的歷史之手的裁定。歷史不過是一個綿延著的時間過程而已,事實上,我們時代的認定也是歷史認定的一個不可逾越的環節。因而,我們有責任站在歷史的視角,作出我們時代所能有亦是所應有的種種陳述。正是基于此種認識,本文試圖從文學發展史的向度,切入“第三代詩”的文本形態和詩學結構之中,從而揭示出它給詩壇乃至整個文學史帶來的某種新的藝術質素。
在我看來,一部文學史應該是不斷陌生化的歷史,而“文學史意義上的寫作”,應該是于傳統之外,提供一種新的文學思想、藝術形態或某種新的質素。“第三代詩歌”是一種真正的文學史意義上的詩歌寫作,其根本在于它給詩歌及文學提供了一種關于“文學本體”的觀念。正是在此種意義上,人們才開始意識到,“詩就是詩”不只是一種無意義的同語反復和游戲,它本質上揭示了一種新的詩學態度:詩即是詩本身,而不是它之外的別的什么。一種真正的文學本體論思想正是由此而確立的。先前的中國文學,即便包括現代主義的實驗性寫作,也大多是以認識論作為主旨的,其目的和功能在于如何去認識和評價生活,如何在接受域內產生一種教化和訓導效應,并以此作為作品結構、敘述或意象、語式生成和組構的核心及焦點。一部作品的價值首先不在或者根本不在文本自身,而是在它文本之外表現了一種怎樣的思想意識形態,揭示了多少認識生活的所謂真理和途徑,而讀者又能從中獲得多少教益和現實指導意義。作品僅僅被視為一種工具,是可以于獲得它的實質之后隨意棄置不顧的。比如在“第三代詩”的近景朦朧詩那里,作為一種現代審美思潮,其根本所指仍是在文本之外的主體理性和批判層面,因而,對生存的揭示也僅僅在其認識的意義和價值深度,依然缺乏一種詩的本體意識。新一代詩人已開始意識到,這種被稱為詩的東西,似乎始終是在詩之外的,詩人亦在詩外駐足、游蕩,一經覺醒,自然便有著一種返回詩性本原的沖動和吁求,于是一種詩的本體意向便滋長起來。面對詩歌,詩人們開始發出詰問:詩究竟是什么?它難道僅僅是提供一種認識生活、評價生活的載體和工具嗎?在他們看來,這顯然不是詩的本性。詩不是詩之外“所指”的那個價值深度,不是一種社會和政治的意識形態,或文化與倫理的宣諭形式,詩就是詩本身,是詩之所以為詩的具有本原存在形式的“詩自體”。一方面,它與生命或事物的本原存在有關;一方面,它又是一種語言形式。它是以本體為主旨的以語言形式顯現的存在本身,因而具有一種存在與語言同構一體的本體性特征。
由此看來,“第三代詩學”的本體論,既是以生命或事物的存在為本體的,又是以語言形式為本體的。就存在本體論而言,它首先表現為一種自覺的生命意識的勃興,這種非理性的感性存在形式是對理性自我的反撥與悖逆,它標志著新時期以來人的又一次凱旋與拓進。如果說“自我”作為朦朧詩所表現的最初的人本或主體性形態,第一次真正地揭示了人走出群體之后所享有的那份高度自由和權力,即人所持有的自主認識、把握甚至主宰世界、事物及周圍一切的特權,那么,生命則是在主體性神話或者說自我的神話破滅之后,人的又一次真正的回歸與還原,即回歸到本來的自己,還原到生命。人類似乎該確立這樣的信念:人終究不是萬能的,并不能主宰一切,甚至也不能主宰自我,首先是置身在世界中的感性存在著的生命形式。這種生命意識自然是在生命與文化、感性與理性相對立的情境中被確立的。第三代詩人似乎普遍存有一種對抗文化傳統的叛逆情緒,他們不情愿納入文化預設的秩序和模式之中,也不愿過多地接受傳統的預制和洗禮。他們相信一個不受既有的文化、理論和體系浸染的人,一定是一個煥發著自由創造活力、充滿著無限可能性的生命體。
因而,回到生命便是拒絕文化而返回創造的本原或本原的存在之根。這種以生命為本的存在本體論詩學,自然十分關注“此在”的生存狀態、原生相的生命情態與充滿生命意味的感覺和行為,并由此確立了我們時代一種新的情感和時間觀念,即所謂“新感性”和“過程意識”。人,說到底是一種感性的存在物,因為他首先在這個世界中存在,并感受著、欲望著、行動著,當然他也有思想、有理性,但這些并非存在的本原,因為理性只是在感性之后并由它投入或遺留在歷史中的積淀物,它能使人敞亮,但更能使人遮蔽,除此并不能說明更多的什么。理性時代過于看重理性,事實上只能以犧牲現世的生存為代價。理性主義者將諸如感性與理性、此岸與彼岸、現在與未來、現象與本質、過程與目的等二元對立的天平總傾向于后者,似乎人在現世的感性生存僅僅是為了尋找一個結果或達到一個目的。事實上生命不過是不斷綿延著的感覺過程,它不會以某一個終點作為存在的理由、價值和意義,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就在過程之中。“此時此地”綿延著的感覺過程是生命的本相和存在狀態,也是詩人生命本體論的根性所在,這在韓東、于堅那里都曾有過精到的表述。正是由此,第三代詩人才真正回到了感性,回到了此岸,回到了現在,回到了現象和過程之中,讓生命的自身呈現與言說在體驗與描述中,真正揭示生命存在的本質。
持有存在本體論的詩人,既有偏于生命體驗的,又有偏于事物描述的,如楊黎等一些詩人。他們既受到海德格爾基礎本體論與現象學的影響,又吸納了法國新小說的藝術觀念,通過懸擱或中止傳統的價值理念以及既定的邏輯思維范式對事物的“遮蔽”而回到事物本身,使事物呈現出本原的“此在”狀態。如“前文化還原”理論,即是將人類世界還原到宇宙中的事物。在詩人們看來,世界已是一個被文化語義化、數理邏輯運算化了的異化的世界,只有回到事物本身,才能“直指生生不息的前文化領域”,抵達本真的存在及創造之源始。為此,他們甚至不惜拒絕“作為‘載體,負荷‘別的什么”的語言而回到“僅僅表現著它自己”的事物,“就像用海水表現海水,用沙漠表現沙漠一樣”。然而,詩的言說終究是不能避免語言的,回到事物只能是回到語言的及物性。因而,他們盡可能追尋一種“特別的說”去接近本真存在的物,比如廢除語言中形容之類的價值詞語,就如我們不說“這是一枝美麗的玫瑰”而只說“這是一枝玫瑰”一樣,只有“存在”才是它的本質,它存在于那里,是無所謂美麗還是不美麗的。這與羅伯·格里耶的“事物”觀是相類同的,正如巴爾特在《物的文學》中論說格里耶的小說時所說的那樣:他取消了物的隱喻的任何可能性,拒絕和消解了那些格式塔式的形容詞的誘惑,他的描寫只停留在物的現場和表面,沒有厚度,沒有深度。因為它并不意指除了自身之外的任何其他東西,也不將讀者帶入某種功能的或實體之外的領域。海德格爾說:人類的狀況就是此在。羅伯·格里耶在讀到《等待戈多》時曾引用過這句話。事實上,羅伯·格里耶的物也是這種此在的事實。作者的全部藝術就是賦予某種“此在”,并剝奪它“某種東西”的屬性。第三代詩人消解事物之外或“某種東西”的深度屬性,同樣是為了回到或還原到事物此在或原在的本真形態。一如楊黎筆下的《冷風景》,它既不表現“某種東西”的深度,也沒有任何情態傾向性,只是描述觸目所見的風物,我們置身其中,也僅僅是置身在物之中而已。這種物的此在的本體論與生命此在的本體論看似不同,然事實上生命和事物也是同構一體的,因為我們是以生命的形式與事物相連接的。一方面生命以感覺的形態呈現事物,另一方面事物又是生命存在的一種對象和形式,二者只是從不同視點切入宇宙中本原的“此在”自身,因而并沒有質的區別。
“詩即是詩”,其另一內涵是說,它的呈現形式是語言,就如前述已不可避免地言及語言一樣,回到生命或事物,即是回到語言。語言與存在的同構性,使“第三代詩”的語言意識與傳統語言觀有了本質不同。現代語言哲學不再把語言僅僅視為一種指向語言之外的某種東西的工具,所謂“得意忘言”。現代語言哲學認為,語言是生命和事物存在的一種形式,世界不是語言表述的對象或語符之外的那個“所指”,它就存在于語言之中,世界和語言是同構一體的,猶如大師們所言,“語言是存在之家”,“我的語言的界限意謂我的世界的界限”。因而,生命和事物的存在也只能是一種語言的存在。“詩從語言開始,到語言為止”,這種表述揭示了“第三代詩歌”最本質的語言觀念,并由此確立了以語言為核心的本體論詩學,從而提出了獨標高致的詩學概念,即語感。語感是存在與語言渾然整一的交互狀態,它既是一種存在本體,又是一種語言本體,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第三代詩學也是一種語感本體論詩學。一方面,它是語言中的生命感、事物感,是生命或事物得以呈現的存在形式,就如詩人們所說,“在詩歌中,生命被表現為語感,語感是生命的有意味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純粹的語言形態或稱元語言,它是在消解了意象的觀念或理念之后還原和最終抵達的一種本真語境,或是在本原的生命或事物中的一種言說形式。因而,在語言形式這一層面上,語感是與意象相對立的詩學范疇。傳統的意象本質上是一種觀念形態,它的核心是指向語符之后的那個深度意義和觀念的,因而,它尤其看重象征、隱喻、變形等藝術手法。比如“玫瑰”,作為意象,重要的不是“玫瑰”這個語詞,也不是一枝“黃色的玫瑰”或“紅色的玫瑰”本身,而是“玫瑰”所指稱和象征的意義:愛情。再如隱喻的隱含內容、變形的主體性張力,均是如此。可見意象所終極指涉的是一種二度所指的觀念形態,而語感是一種語言形態,或語言所呈現的生命形態和事物形態,它的本質是回到自身。因而它反對象征,拒絕隱喻和變形,就如“玫瑰”僅僅表示一枝黃色或紅色的玫瑰自身一樣,它拒絕二度所指,并將一度所指僅僅還原為能指,或者說它已經消解了語言的符號深度,堅持語詞的及物性或指物性,拒絕一切觀念和文化語義的介入,在返回語言本體的同時,抵達生命和事物。這與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的符號學似乎是相悖的。索緒爾曾一再強調,語符是與實在無涉的兩面的心理實體,“語言符號連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稱,而是概念和音響形象”,其中“概念”的抽象性形態自不待言,即使“音響形象”,在他看來也“不是物質的聲音,不是一種物理的事物”。為此,索緒爾及法國一些符號學家一再告訴人們,“要認識到語詞和事物、符號和指示物之間有一個無法跨越的裂縫”,“符號并不指向事物,它們表示概念,而概念是思想的方面而非現實的方面”。因而,他們把語詞和事物的同一性觀念,“當作過分唯物主義的和頭腦簡單的東西而加以拒絕”。第三代詩人似乎是一群十足的唯物主義者,他們樂意并執著地認同語言的及物性或指物性,堅持在語詞中去感受生命的意味和事物的特性,而將概念和思想拒之于大門之外。第三代詩人這種獨特的語感詩學,或許更多地得益于另一位語言哲學大師海德格爾,他堅持語言和存在的同一性觀念,認為正是語言構成了人的此在的基礎,“第一次使人有可能處于存在的展開狀態之中”,人、事物和世界均存在于語言和詞語中。他反對預定的僵死的觀念對語言的支配,而追尋一種澄明的本真語言和原始意義,即“語言言說”,而不是富有主體性的人在言說。只有“語言言說”,才會向人和諸事物發出召喚,使之進入并被“純粹地說出”,成為澄明無遮蔽的存在之顯現。“第三代詩”的語感就是這種澄明無遮蔽的本真語言和存在之顯現,詩人們或者將生命投入純粹感覺性的語言言說之中,使之處于存在的展開狀態,體驗著并被呈現著;或者去除一切價值定格和形容反映,以一種無遮蔽的原始本真語言,對事物給予第一次命名;或者將世界和事物還原為一種超語義存在的聲音,讓人傾聽到一個本原宇宙的天籟……這一切,都呈現出一種純粹的語感狀態,讓人在本原的語言言說中,進入生命和事物。
語言、生命和事物,這些“第三代詩學”不可逾越的本體性語辭,雖曾在諸多場合或語境中被反復言說過,但對它在新時期文學本體論變革中所承負的角色及其意義,人們卻似乎并沒有給予應有的認識,這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