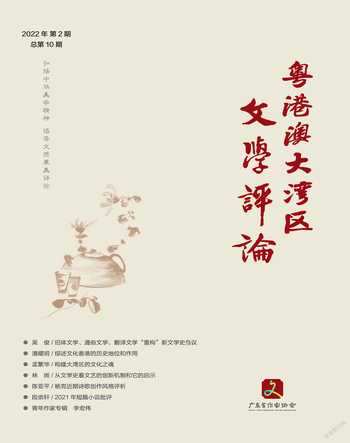上學謠:獨特的中國式童年吟唱
摘要:《上學謠》創新性地以林林總總27個動物、植物、日常生活用品、自然物象做講述者,承載了壯族獨有的文化記憶。主人公的命運、鄉情風俗、歷史傳說、神話故事、生存境遇,在作者筆下渾然天成,極大地拓展了小說的深度和廣度。這種獨特的文本,充分發掘兒童天性和兒童的主體性,更加貼近兒童。作者在小說中以善與愛澆灌敘事,傳遞著每一個孩子都應被善待的樸素情懷。民族性和地域性是《上學謠》另一標志性的特色。27個敘述主體如同27支不同顏色的彩筆,在表現人物的同時,也把現代化背景下的鄉村風土風俗,描繪成一整幅新時代童年版的壯鄉“清明上河圖”。
關健詞:成長;獨特;創新;壯鄉;融合
胡永紅的長篇小說《上學謠》,是一部體現脫貧助學主題的兒童文學力作,獲第十一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作品講述了父親早亡、母親出走改嫁的壯鄉少年人火龍,與奶奶水仙阿嬤相依為命,在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大時代背景下,得益于黨和國家的脫貧政策,在政府資助和鄉親們的關愛下成為壯鄉第一個考上縣重點高中,繼而成為走出壯鄉的第一位大學生的故事。展現了在黨和政府領導下脫貧致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美好畫卷。
《上學謠》寫作手法獨辟蹊徑,大膽而富有開拓性,以奇趣奇特的27個物化視覺敘事方式,展現了壯族少年火龍的成長,此讓這部作品具有了別樣的陌生、趣味、豐滿和厚重。《上學謠》是兒童文學邊界抒寫的又一次挑戰,當然也挑戰了我們的想象力。
27種物化視覺講同一故事,作家在拓展文學敘事空間的同時,找到了藝術創新的突破點
翻開《上學謠》,讓人眼前一亮的是小說獨特的文本。作者獨辟蹊徑,在以獨特的敘事角度建構中,運用了林林總總27個物化視覺做講述者。在同一時間和空間中,講述同一個故事,讓壯鄉的山川草木、萬事萬物逐一顯現,溫暖潤澤,以多個物化視覺展現了面貌迥異的山區壯族少年火龍的成長故事。
這27個既非物的視角又非人的視角建構的小說,既不是動物小說,也不是童話、更不是科幻或魔幻文學,而是別具一格地采用了物化視角的手法,調動起27種壯族文化、民俗元素,以27種視角綴連起整部作品。這些壯族文化、民俗元素中,有鄉間生活的日常——斗笠、水牛、木屐;有亦真亦幻的神話傳說——雷公、雨神、太陽鳥;有嶺南地區的自然物種——南竹、香禾、芭蕉;也有壯族特色的文化符號——標話、嘹歌、壯錦……
由此可見,《上學謠》的文本,以及敘事角度和敘事立場都與傳統的兒童文學作品完全不一樣。這在中國兒童文學,乃至在中國文學歷史中是獨一無二的。
在《上學謠》中,作者把主要敘述精力放在主人公火龍的成長經歷上,為了讓故事更加緊湊,27種物化視覺講同一故事時,前面的事物在講述完故事之后交由后面的事物講述,使主人公火龍的故事“無縫銜接”地按時間順序自然地延展下去,不做交叉、重復,從而保障了故事的延續、流暢和可控。
27個物化視覺講述時或多或少都會有“自我介紹”,它屬于少年火龍日常生活中的某種構成。它有趣味,有知識點,有生活性,無論是神話傳說,還是民風民俗民情,以及鄉村景致的描繪,都與講述者以及講述者講的內容有一定的關聯,讓故事具有了較強的張力和立體感。
比如,小說開篇“黑狗”一章,講述了雷公和狗頭王的傳說,引出了下雨天火龍因為沒錢買雨傘,只能戴著壯族人祖輩用竹篾編成的、刷著桐油的斗笠上學。在撐著花花綠綠雨傘的同學們的異樣眼光下,火龍強烈地渴望也擁有一把雨傘。于是,“黑狗”的敘述讓讀者從這一細節,了解到壯鄉傳統文化、生活習俗,也看到了貧困狀態下少年人火龍的窘迫和拮據。
接著是“雷公”講述壯族創世主布洛陀的傳說,“大禹真的是他阿爸鯀生出來的?”小伙伴們的質疑,讓火龍想起自己在外打工久未回家的爸爸,還有因此出走改嫁的媽媽。
然后是在殯葬隊伍的鼓樂聲中,從披麻戴孝地被綁在祠堂前臺邊一根柱子上的“水牛”的敘述視覺,讓讀者感受壯鄉葬禮風俗,并指向火龍爸爸礦難身亡,水仙阿嬤和鄉親們不想讓幼小的火龍過早面對不幸,把他反鎖在家里的畫面。
而通過“荷花”“響石”的接力講述,我們看到了鄉政府干部和鄉親們關愛失去爸爸和失去母愛的火龍的畫面。鄉干部六叔公送去了救濟金,鄉村們還把火龍家菜地已經蔫黃的菜摟走,補種上郁郁蔥蔥的新鮮蔬菜,讓火龍賣了菜有錢去買雨傘。也看到了品性善良、高尚、堅忍的水仙阿嬤,當村干部設法為她領取了撫恤金時,她堅決不收。但是,當村子要籌資修水渠、建水壩的時候,水仙阿嬤卻堅持從綿薄的生活費中捐出了自己的份子錢。在政府、在鄉親們和水仙阿嬤的扶助下,火龍不再一味抱怨戴斗笠上學給自己帶來的苦惱,開始通過自己的努力擺脫貧困、改變命運。
從接下來一系列物化視覺講述中,我們還看到了成長路上火龍自強不息的堅實腳步……
同類題材的小說中,作家講故事的同時,也會努力加入諸如鄉土人情等材料。但因為手法單一,令這些材料往往像貼圖一樣,讓人難免有一種硬塞進來的不適。
而從《上學謠》27種被賦予了言說能力的事物的敘說中,我們卻可以讀出它的趣味和魅力。27個物象,既是故事的講述者,也是參與者和旁觀者;既承載了壯族獨有的文化記憶,也推動故事向前發展,建構著與之相關的風土人情、歷史傳說、神話故事、生存境遇、現實狀態……主人公的命運、鄉情風俗在作者筆下渾然天成。通過27個物化視覺繪形繪聲繪色,多層面、多角度、多色彩的講述,讓原本有點單調、枯燥的素材有了更強的質感,極大地拓展了故事的深度和廣度,使小說所要傳達的意趣和思考有了多向的厚重。
創新,是為了更生動更直觀更立體更全方位地向讀者展現來自現實生活的各種素材
用27種物化視覺講同一故事,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創新的嘗試。“筆者曾經問胡永紅《上學謠》為什么要采用這種文本,她的回答很簡單,就是為了更生動更直觀更立體更全方位地向讀者展現來自于現實生活的各種素材。”[1]
胡永紅一直以來積極參與扶貧助學活動,她現在還有一位貴州省長順縣的一對一的助學對象,那是一位小女生。而《上學謠》的人物原型是懷集縣下帥壯族瑤族鄉的祖孫倆——廖月明婆婆身處逆境,仍含辛茹苦把孫子陳蒙偉養育成人,而后成為第一位從古老壯鄉走出的大學生。祖孫倆自強向上的故事感動了作家,同樣感動作家的,還有那厚重多彩的壯鄉風土風俗和人情。
有沒有一條更好的途徑,把這些感人的素材融入到小說中,讓小說中的人物形象豐滿多彩,讓少年人的成長敘述更靈動趣味,特別是讓壯族民族文化遺產能在小讀者心靈深處留下美好的印記。
胡永紅告訴筆者:“如果只是把這些材料簡單地硬塞進來,小說會變得枯燥,但如果讓壯鄉里的各種物象站出來成為講述者,這樣會不會更親切自然更生動有趣呢?”胡永紅“嘗試著寫了幾章后覺得有意思,于是就這么繼續寫下去了。”[2]
為了讓小說更靈動更真實地反映生活,也為了更貼近孩子的心靈,胡永紅選擇了創新性地以27種物化視覺講同一故事這種獨特的文本。
創新,是一種創作手法,也體現了作家為少年兒童“蹲下來”“彎下腰”的寫作境界。胡永紅一直主張充分發掘兒童天性和兒童的主體性。她認為:兒童文學作家要當好孩子們成長路上的“點燈人”,就必須增強自己的使命意識、人文擔當與社會責任感,扎根生活,深入到校園、山村去。只有與孩子們同生共息,深入到孩子的心靈里和靈魂深處,熱愛孩子,了解孩子,才能寫出喜孩子所喜,樂孩子所樂,想孩子所想的優秀兒童文學作品。
為了寫好《上學謠》,胡永紅不但親力親為參與扶貧助學,還曾六次來到山村里,和壯鄉孩子打成一片。她不但進入到壯鄉孩子的內心世界,也讓她對壯族文化和中國鄉村的社會形態有了更深刻更立體的了解。因此,在《上學謠》中,我們總能感知到胡永紅一直在壯族文化內核進行敘事,深層次、多角度地通過一個個真實的細節,為我們解讀豐富多彩的壯鄉文化。
作者在《上學謠》中完全不按兒童成長小說的套路模板,而是創造性地讓黑狗、雷公、水牛、斗笠、葫蘆、壯錦等27種物化視覺講述故事,讓故事更奇趣跳脫,也讓火龍、水仙阿嬤、六叔公、李靜老師等角色都鮮活靈動地呈現在讀者眼前。
筆者曾就能否流暢地閱讀《上學謠》咨詢過一些小學生,發現因為這種敘事方式和不斷轉換的27個物化視覺講述所產生的新鮮感,或者說是陌生感,不但滿足了小讀者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與小讀者的心理距離更近,更具真實感和可信性,也更有震撼性,更容易產生共鳴。
由此可見,胡永紅這種獨特的文本,并不是為了賺噱頭,也不是為了炒作,而是來自作家“緊接地氣”,從壯鄉脫貧助學第一線汲取豐厚的現實生活素材和把握大量地域文化沉淀后產生的自信,更源自作家對文學的敬畏和藝術追求。
作者以善與愛澆灌敘事,傳遞著每一個孩子都應被善待的樸素情懷。這應該是最本色的寫作
《上學謠》無疑是一部苦難題材的成長敘事,作家的目光鎖定在中國古老壯族鄉村,一個當下小讀者有點陌生的時空,塑造了火龍這樣一個純善的鄉村少年形象,并借著火龍的人生際遇,直面苦難,審視成長,向讀者展現出一條獨特的少年兒童成長路徑。
27個故事敘述者的與眾不同和敘事立意的獨具匠心,使作品中的人物從一開始就顯出了獨特的個性。作者筆下的少年火龍和他的小伙伴們,用天真體會繁難的世事,在溫情中實現自我成長。作者始終通過不同物化的視覺,用富有詩性的敘事,走筆于一種視野高遠、胸襟開闊的富有格局的寫作。
《上學謠》直面不幸,卻又巧妙地避開了以悲情賺讀者眼淚的老套路,充分展示了作家的藝術人格和情懷。小說寫到了人生的困苦、寫到了父親早亡、母親出走改嫁,寫到了火龍因為貧困被個別同學歧視,但他并沒有被艱難困苦打倒。隨著敘述的深入展開,構成了下有蔓上有瓜、前有車后有轍的小說藝術邏輯,進而強化了作品的藝術真實性。
正如第十一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頒獎典禮《上學謠》的頒獎詞所述:“作者以善與愛澆灌敘事,傳遞著每一個孩子都應被善待的樸素情懷。”這應該是最本色的寫作。
《上學謠》圍繞著主人公火龍展開情節,從形形色色不同物化的視覺中,作者打破敘事范式的窠臼,追求一種干凈單純的內核,所以寫得樸素,只為從容地講好一個成長的故事、一個耐讀的故事。故事通過27個視覺娓娓道來,如數家珍,雖無驚濤駭浪,卻能柔婉地延綿到心靈深處。在這些富有趣味的敘述中,真實地抒寫和記錄了火龍從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的成長過程。
小說向讀者展示了火龍與水仙阿嬤在壯鄉古屋里抱團相處、相依為命的貧困而快樂的時光。火龍是一個自強自立的孩子。作者沒有花過多的筆墨去描寫主人公是如何削發明志、鑿光夜讀,而是寫了火龍摸黑在江邊撒網捕蝦、在田地里照黃鱔,去鎮上換錢給水仙阿嬤買件過節的壯服;阿嫲日漸年老,年紀小小的火龍主動幫阿嬤干農活,“火龍初學耕田時,犁過的田就像苦瓜面上的瘢痕,或大或小,深淺不一。”但火龍堅持不懈,“眼看越做越像樣子”,小小年紀便成為干農活的一把好手。為湊夠學校的住宿費,火龍還瞞著阿嬤在木工坊打短工,最后在老師的幫助下,在學校圖書館擔任了兼職管理員,搞衛生、整理圖書……
通過黑狗、雷公、水牛、斗笠、雨傘、銅鼓等多種物化視覺的敘述,我們還體味到一種久違的,由文學帶來的溫暖。古今中外,能夠打動人心的文學作品,大多具有溫暖的文化品質和人文關懷。火龍正是在水仙阿嬤和鄉親竭盡全力小心呵護下成長的,其間飽含的艱辛苦困都被作者一一輕快帶過,使得整個小說的走向毫不苦澀,且頗具喜感。特別是通過不同的物化視角帶出那些好玩、趣味盎然的小細節、小故事,以及經典金句,常常會讓人在閱讀中忍俊不禁。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每一個個體的成長都會受到身邊某些人的影響。同樣,在兒童成長小說中,主人公的身邊總會出現一些擔負著成長“引路人”使命的角色,他們的存在,構成了主人公的成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們各自有著不同的身份和鮮明的品格,在主人公生澀懵懂的成長過程中,他們總是無時無刻出現在主人公身邊,通過各種方式完成對主人公的使命。
其實,兒童文學作品不能沒有成年人物的描寫。有些兒童文學作家在創作時,經常殫精竭慮地致力于刻畫兒童人物形象,而忽視了孩子周圍的成人形象,致使作品質量下降,這是不應該的疏忽。兒童文學作品中,成年人的人物形象刻畫,同樣十分重要,能起到綠葉托紅花的作用,為作品增色。《上學謠》中的水仙阿嬤、鄉干部六叔公、李靜老師等就有這樣的效果。
水仙阿嬤是《上學謠》里最重要的“引路人”。她文化不高,但有著壯鄉人善良、高尚、堅忍的品格。水仙阿嬤的兒子,也即火龍的爸爸因礦難亡故,熱心的村干部為她申領了撫恤金,她卻堅決不要。“我們有手有腳,不能伸手跟人拿,拿慣了要不得。”
水仙阿嬤智慧樂觀,從不怨天尤人。上了縣重點中學后,火龍學習遇到了困難,念不下去有點焦慮的時候,“做人做事要有恒心,能挨得過清苦艱難才能做成事咧。好比竹子……”水仙阿嬤以壯鄉常見的南竹生長期為例,通過南竹的生長過程,啟發火龍認識了成長是一個漫長且艱苦的過程,需要時間,需要耐心,還需要堅持和付出。水仙阿嬤還用壯族狀元公莫一大王“種竹造神兵”的傳說,讓火龍記住了做人要像竹子那樣有氣節,不怕強權。
村干部六叔公也是無時無刻地關注關愛著火龍,當火龍吃力地幫水仙阿嬤犁地時,犁在地里像生了根,拔不起拖不動,六叔公看到了就會過來幫忙;還有悄悄把一雙嶄新的白球鞋塞進火龍課桌抽屜的李靜老師、把自己飯盒的肉硬要勻到火龍的飯盒的小伙伴毛任男,以及那些為了不讓火龍傷心,刻意把火龍爸爸亡故的消息隱瞞,然后都爭著到劉老師那里頂替火龍爸爸,在火龍的作業、試卷簽名的村民們,也通過各種物化視覺,一個個鮮活靈動地展現在我們眼前。
《上學謠》以多種視角對火龍的成長環境進行鋪陳渲染,在當地黨和政府,以及水仙阿嬤、鄉親們、老師同學們的幫扶下,少年人火龍從青澀一步步走向成熟,成為下帥村歷史上第一個考入縣重點高中的壯鄉少年,最后還通過努力考上了省城大學。
時代為作家們提供了廣闊而宏大的生活場景,成長不再只是孩子們的事兒,我們的國家、社會也在不斷地成長、進步
時代為兒童文學作家們提供了廣闊而宏大的生活場景。兒童文學創作領域對現實主義精神的書寫與弘揚是近年來的主流。隨著更多關注現實、關注童年,富有新意的現實主義兒童文學作品不斷涌現的同時,也帶來了某種題材不乏趨同之作與概念化書寫。如何捕捉日趨多元、個性的兒童心理與童年人生,如何在大時代視野下突出文學對當下的觀照?
《上學謠》很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作者創新性地通過27個物化視覺,從不同的角度描繪了既有歷史背景下的時代影像,也有基于個體童年的個性化抒寫。而這些抒寫,更多著力呈現了童年的情感性,并通過童年的情感性觀照當今的社會性。這讓《上學謠》與一些僅僅以底層奮斗、自強不息為主脈的兒童成長小說有了不一樣的情懷。
作者沒有去著力描寫政府扶貧助學工程的大場景、大事件,而是潤物無聲地通過對各種生活細節,從細微之處觀照中國社會的大變革、大發展、大繁榮的偉大進程。在《上學謠》中,成長是一個社會性的話題,我們可以從小說中孩子們成長的一個個細節,感知到中國城鄉的觀念、經濟、生活也同時在成長、變化。
翻開小說的第一章,在“黑狗”的視覺里,我們看到了少年火龍因為水仙阿嬤沒錢買雨傘而深感苦惱;從“斗笠”視覺更看到,火龍的斗笠、蓑衣在同學們“一堆花花綠綠的雨傘中,真是很不應景”。甚至當火龍成為全村第一個考上縣重點高中的孩子,到縣城上學時隨身的行李也僅是背上一個很“另類”的破舊背簍。但是,當火龍考上大學要到省城念書的時候,水仙阿嬤給準備的行裝里,是“一床絲棉被面、兩個枕頭、一對麼乜(用艾草和各種藥材制成的香囊,可以驅蟲止癢)和一雙鞋子”,還有一幅漂亮的壯錦。
也就在火龍考上大學的“這年夏天,白水河的高塘大壩建成了,都說是‘廣東第一壘石高壩,堪稱‘粵西北葛洲壩”。壯鄉里“家家的送電完成了,整晚上都可以通電;家家的自來水管接好了,擰開了水龍頭,就看得到嘩嘩的白水流淌”。
火龍家更是裝了電話,在省城讀大學的火龍想念水仙阿嬤時,再用不著靠郵遞員花十天半月傳遞信件,只需一個電話便可聽到水仙阿嬤的聲音。
壯鄉在變、壯鄉人在變,壯鄉人的觀念也在變。“各鄉寨都有好消息,當兵的,上大學的,還有像毛任男謀到工作的”,呂格旋入伍從軍,果果做起了小生意,壯鄉人不用再走火龍爸爸為賺錢謀生,給私礦老板打工命喪黃泉的老路。
火龍的中學同學,黑人黑戶的超生少年瑞瓜不再用躲躲藏藏,而是堂堂正正地走進了大學學堂。曾被視作迷信的鄉俗再次成為鄉村們的喜慶節日,還辦起了歌圩,“附近鄉寨上萬人趕來,歌山匯海,熱鬧非常”。好一幅鄉村脫貧,共同走上小康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美好畫卷。
沒有大事件、大場面,也沒有概念化的人物,更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設計,在小說呈現的多個節點、空間、物象中,壯鄉少年火龍和他的小伙伴們的成長,表達的不再是個人的人生經歷,而是伴隨著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歷史洪流,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去。
胡永紅一直力圖告訴人們,成長不再只是孩子們的事兒,我們的國家、民族也在不斷地成長、進步。于是,這部兒童成長小說便以審美方式承載了對人類命運和民族歷史的思考,走向更為宏大的文學表現空間。
獨特的地域文化和鄉土人情孕育了主人公歷經磨難,自強不息,不懈追求的獨特性格和氣質。這幅明快的畫面指向壯鄉少年的成長,更指向中華民族的精神傳承和中國社會未來的發展走向
民族性和地域性是《上學謠》另一標志性的特色。《文藝報》主編、作家梁鴻鷹就曾以“物博志、風俗畫、地方志、生物志、地方語言庫”[3]來評介《上學謠》。如梁鴻鷹先生所述,作為一部以壯族山村為地域背景的兒童小說,胡永紅把《上學謠》打造得好像一部壯族民俗風物志。她用一種近乎虔誠的筆法,以多種物化視覺的寫作手法貫穿全文,將壯族鄉民的日常生活、神話傳說、民俗習性、飲食起居等各方面勾勒得淋漓盡致。既富含風土人情與民族特色,又彰顯創新寫作的努力與嘗試,更兼具主題性與文學性。27種視覺物化寫作,如同27支畫筆,以不同的色彩、線條、角度,細致充分地對壯鄉的人文、地理、風物、名勝進行全景式的掃描,繪制成一幅新時代童年版的壯鄉“清明上河圖”,也讓《上學謠》極富畫面感。
通過不同的視覺描繪出的畫面,孩子們的純真天性和鄉村不老的民俗,以及滿紙濃郁的泥土氣息,彌漫著壯鄉萬物花開的馥郁、神秘之氣。于是,昨天的神話,今天的歡笑,留下了美好的印記,成為主人公成長過程中的寶貴財富。
胡永紅在以濃墨描繪壯鄉風景、風情、風俗的時候,更著眼于告訴讀者,獨特的地域文化和鄉土人情孕育了主人公歷經磨難,自強不息,不懈追求的獨特性格和氣質。
對壯鄉人而言,下帥鄉的山水是壯胞們的詩意棲居地,白水河承載著渡船,也承載著壯鄉人走向更遼闊的未來。壯族少年火龍從下帥鄉寨走出山村、走向縣重點高中,再走向省城的大學堂……這幅明快的畫面指向壯鄉少年的成長,更指向中華民族的精神傳承和中國社會未來的發展走向。
兒童文學與影視創作的同步實踐,在這兩種文藝形式的轉化、融合中實現了更廣泛、更深入的作品傳播
27個跳躍、閃動著的敘述視覺,在不同的時間節點和空間講述故事,讓《上學謠》有著比傳統兒童小說更多的鏡頭感,也更靈動、更跳脫有趣。而這種鏡頭感,顯然有助于小說文本向影視劇轉化。根據胡永紅兒童文學作品《上學謠》改編,并由胡永紅親自擔任編劇的電影《紅尖尖》已經在2021年10月在全國正式公映。而電影《紅尖尖》(英文名THE BAMBOO HAT 斗笠)也先后獲得七個國家十三項國際電影獎,成為中國現實主義題材兒童文學作品改編成影視作品的一次成功范例。
當下圖像影音的傳播影響力毫無懸念地超過了文字,作為新興人類的兒童乃至青少年,他們被時代裹挾已經從出生及成長伊始,即進入了全面的讀圖時代。
在這種情勢下,兒童文學應與時俱進,積極尋求生存發展路徑,拓展傳播空間,擴大社會影響力。而兒童文學原創作品的影視改編,以及兒童文學作家對影視創作的介入,無疑是拓展傳播空間的一條重要渠道。
但是,目前一些兒童影視作品,即使是一些獲獎的電影、電視劇,往往存在成人化傾向的毛病。究其原因,又往往是由于兒童文學作家缺席兒童影視作品的創作或改編。習慣成人影視創作的編導們,因為對孩子缺少接觸和了解,往往過度強調教育性而舍棄兒童本位性。他們要么擺出一副老夫子臉孔對孩子說教,要么變身“小大人”捏著鼻子裝兒童腔,導致一些兒童影視劇偏離了兒童的審美。
兒童文學向影視劇拓展傳播渠道,需要這兩種藝術形式之間的深入交流、融合,以更好地發揮各自特點和優勢。兒童文學作家基于長期親近孩子,對孩子有較多的了解和理解,而由他們親手改編或編劇的影視作品,基本都能較好地保持兒童本色。因此,應鼓勵更多兒童文學作家直接參與到影視劇本的創作或改編,通過改編、嫁接、融合等方式,把原創兒童文學文本轉化為影視劇本的重要資源。這不僅可以大大改善目前兒童影視劇的劇本荒,還拓展了兒童文學的疆界和傳播空間。通過雙方有效對接,互惠互利,使兒童影視劇從兒童文學原創文本中獲得源頭活水。
胡永紅一直著力兒童文學文本與影視劇本創作的同步實踐,在這兩種文藝形式的轉化、融合中實現了更廣泛、更深入的作品傳播。之前胡永紅親自操刀的兩部由小說改編的電影《我的影子在奔跑》《瑞喜愛小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而由《上學謠》改編的電影《紅尖尖》的成功,也再一次證明,兒童文學與影視創作的同步實踐,將有助于提升兒童影視劇的品質,更為廣東乃至全國的兒童文學作家拓展傳播空間樹立了標桿。
《上學謠》線索多元飽滿,審美價值高,語言立體化、戲劇化,小說的厚度和張力都令作品可讀耐讀。而獨特的27種物化視覺敘述,優化、豐富了當代兒童小說文學元素,是一首名副其實的中國式童年吟唱。
[注釋]
[1] [2]李國偉:《讓人眼前一亮的創新文本》,《少男少女》,2021年第2期。
[3] 《浙少社的這本主題出版物,靠什么贏得專家們的青睞?》,《出版商務周報》,2020年12月1日。
作者單位:廣東省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