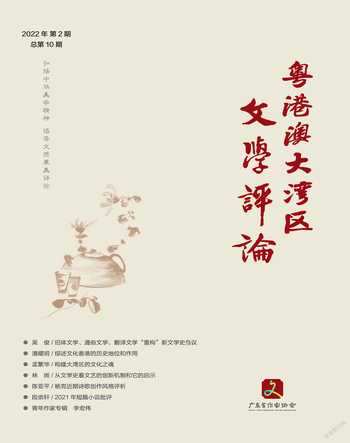“家原型”視角中路遙的《人生》
摘要:“家原型”中的父子沖突都帶有隱喻。當高玉德說出一番道理后,高加林放棄對高明樓的申訴,去適應“農民”生活,雖心有不甘,但無可奈何,說明他內心認同了父親所說的規則,同時深埋了人生隱患。《人生》中三個逆子,走出家庭,卻沒能找到自己真正歸宿,這是“家原型”對逆子出走的另一種處理方式。此前的“家原型”中,還從未有過引路人和敵對者你中有我,相互膠著的狀況。
關鍵詞:《人生》;路遙;“家原型”
個人與家的關系,一言難盡,千回百轉,也是文學創作的重要母題。20世紀以來,宗法家族逐漸解體,被小家庭取代,發生巨大變遷。與此同時,傳統與現代撞擊,沖突不斷,體現于家庭內部。20世紀文學中,《家》《財主底兒女們》《紅旗譜》《白鹿原》《豐乳肥臀》等,以史詩手法,描繪百年來家族命運,形成譜系,得名“家族小說”。[1]家族故事不斷疊加,構成“家原型”,與社會歷史結構互文。原型批評是文本闡釋視角之一,故“家原型”的使用,可豐富對作品認知。《人生》是當代文學史名作,得到過不同視角的闡釋。本文擬采用“家原型”視角,考察《人生》研究中曾被忽略的元素,以期揭示這部作品的多面性,對其有更深入理解。
一、“父子沖突”
《人生》開端就爆發了一場父子沖突。高加林代課教師的職位被村長高明樓的兒子取代,他難以接受,怒不可遏,要去拼命,被父親高玉德阻止。“家原型”中,父子沖突是常見情節,一般用來隱喻兩種觀念的碰撞。《紅樓夢》中,賈政秉持學而優則仕的觀點,看到寶玉每日混在脂粉群,荒廢功課,所以將其痛打。寶玉身上,已經體現出現代自由意志,與賈政的期望格格不入,父子沖突在所難免。《創業史》中,梁三老漢的愿望是發家致富,希望兒子梁生寶能夠襄助自己,完成夙愿,但梁生寶已經成了“國家的人”,另有想法。梁家父子沖突,是走不走合作化道路的爭執。《人生》中高加林和父親高玉德的沖突,同樣是類似模式,但父子二人所代表的觀點,發生了時代更迭,而父子沖突的解決方式,更值得分析。
父親高玉德代表了高家莊既定秩序。高家莊是1980年代初期一個落后的山村,沿襲著傳統生活方式,啟蒙的春風步履蹣跚,還未吹拂到這片古老土地。高明樓是村長,把持權力,因為兒子三星畢業沒有工作,就頂替了高加林的代課老師職位。高加林不服。高玉德“揚起那飽經世故的莊稼人的老皺臉”,對兒子有一番教育,說出的就是秩序:“你聽著,你不光不敢告人家,以后見了明樓還要主動叫人家叔叔哩!臉不要沉,要笑!人家現在肯定留心咱們的態度哩!”又跟老伴說:“家林他媽,你聽著!你往后見了明樓家里的人,要給人家笑臉!明樓今年沒栽起茄子,你明天把咱自留地的茄子摘上一筐送過去。可不要叫人家看出咱是專意討好人家啊!唉!說來說去,咱加林今后的前途還要靠人家照顧哩!人活低了,就要按照低的來哩……加林媽,你聽見了沒?”[2]高玉德是一家之主,言行代表了既定家族文化,而他力主忍讓,則是評估事件后的策略。如果任由兒子去折騰,不但不能改變現實,甚至會招來報復。小說明確說,村長高明樓是高家莊的“大能人”,權勢中心,他預備了窯洞,條件優越,專門給來村的縣、公社干部使用,還巴結到了縣、市的領導人物。在村里,他與號稱“二能人”的首富劉立本聯姻,把勢力范圍擴得更大。高明樓的大兒子娶了劉立本的大女兒劉巧英。“‘大能人和‘二能人一聯親,兩家簡直成了村里的主宰。全村只有他們兩家圈圍墻,蓋門樓,一家在前村,一家在后村,虎踞龍盤,儼然是這川道里像樣的大戶人家。”(第12頁)由此可見,在高家村,高明樓及其代表的傳統宗法勢力很強大,遠非高玉德家所能抗衡。另一事例是,高明樓的兒子做代課教師沒多久,就調到了縣里農機局機械化施工隊,負責開大型拖拉機,而那個代課教師職位,由劉立本的三女兒劉巧玲接任。因此,高玉德認為,高加林不能去反對高明樓,這是基于兩家實力做出的判斷。
家族之間通過聯姻方式,結成政治、經濟同盟,是傳統社會常見行為模式。美國學者柏文莉的《權力關系——宋代中國的家族、地位與國家》關注了這個問題,揭示出古代政治精英和地方精英“如何通過科舉、婚姻、經濟紐帶相互扶持以鞏固和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3]。《紅樓夢》中,賈王史薛四大家族互通姻親,形成牢固利益集團。階層相同,門當戶對,是兩家聯姻的基礎。《人生》中,這種傳統社會結構未隨現代而消退,仍然發揮著巨大作用。即便在縣城,也能看到這種模式。黃亞萍家族中,父親是縣武裝部部長、縣委常委。黃亞萍與高加林是同學,卻能在縣城的廣播站工作,不能不說有家族力量的支持。張克南的家世也很好,母親是藥材公司副經理,所以他畢業后去了副食部門工作。“兩家四個大人的關系也親密得如同一家人一樣”。(第126頁)黃亞萍回家,媽媽拿出一件衣服說,“克南他爸去上海出差給你買的,克南媽才送來的,你試試……”(第129頁)小說中,黃、張兩家的四位父母都認可他們的戀愛,樂見其成。可以想見,如果黃、張二家聯姻,將是縣城中非同小可的勢力。易言之,從高家村到縣城,所通行的原則并無不同,而且深入到家族內部,體現在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之中。
高加林已經意識到自己與眾不同。他如精神貴族,俯瞰村中的高、劉兩家。“他已經有了一般人們所說的知識分子的‘清高。在他看來,高明樓和劉立本都不值得尊敬,他們的精神甚至連一些光景不好的莊稼人都不如。高明樓人不正派,仗著有點權,欺上壓下,已經有點‘鄉霸的味道;劉立本只知道攢錢,前面兩個女兒連書都不讓念——他認為念書是白花錢。只是后來,才把三女兒送去學校,現在算高中快畢業了。這兩家的子弟他也不放在眼里。高明樓把精能全占了,兩個兒子腦子都很遲笨。二兒子三星要不是走后門,怕連高中都上不了。劉立本的三個女兒都長得像花朵一樣好看,人也都精精明明的,可惜有兩個是文盲。”(第12頁)但是,他并非從理論上批判高家村的既定秩序,也沒有改變秩序的愿望,這才是癥結所在。他很清楚自己為何淪落,但并不拒絕背后的規則,于是打算給遠在新疆的叔父寫信,“告訴一下他目前的處境,看叔父能不能在新疆給他找個工作”。(第13頁)高加林受到挫折后,穿上叔父送給自己的黃軍衣,出門種地,用隱喻的方式“改換”身份。后來,借助叔父的影響,高加林得償所愿。“他從自己人間天上一般的變化中,才具體地體驗到了什么是‘后門——后門,可真比前門的威力大啊!”(第104頁)他接受了來自“后門”的優惠,等于承認通行于高家村的規則有效。在婚姻上,同樣如此,他聽到黃亞萍談論父母,忽然暴躁:“你父親肯定不會接受我!他們要門當戶對的!我一個老百姓的兒子,會辱沒他們的尊嚴!”(第138頁)可見,高家父子爭吵的原因,不是兒子由于個性成長而“弒父”,而是不同家庭之間因政治、經濟而造成分歧。家族沖突時,家庭成員間往往保持一致,共同對外。從這一點來說,高家父子不會爆發不可調解的矛盾。
“家原型”中的父子沖突都帶有隱喻,《人生》也不例外。高玉德、高加林之間的沖突在電閃雷鳴之夜發生,但并不激烈,草草結束。當高玉德說出一番道理時,高加林并沒有反對,而是在這場父子沖突中敗下陣來。他放棄對高明樓的申訴,去適應“農民”生活,雖心有不甘,但無可奈何,說明他內心認同了父親所說的規則,同時深埋了人生隱患。路遙出身農村,經歷一番波折后上了大學,通過個人奮斗改變了命運。來到大城市,但他始終沒有因自己變為城里人而丟棄家族意識,反而與他們保持了密切互動。他寫《平凡的世界》時,得到弟弟幫助,鄭重在創作談《早晨從中午開始》的篇首寫上“獻給我的弟弟王天樂”。路遙在原生家庭中,習得了社會經驗:“童年。不堪回首。貧窮饑餓,且有一顆敏感自尊的心。無法統一的矛盾,一生下來就面對的現實。記得經常在外面被家境好的孩子們打得鼻青眼腫撤退回家;回家后又被父母打罵一通,理由是為什么去招惹別人的打罵?三四歲你就看清了你在這個世界上的處境,并且明白,你要活下去,就別想指望別人,一切都得靠自己。因此,當七歲上父母養活不了一路討飯把你送給別人,你平靜地接受了這個冷酷的現實。”[4]路遙對家庭關系包括父子關系的認知,或多或少會遷移到《人生》。高加林人生目的在于通過個人奮斗,改換農民身份,獲得尊嚴,但并未意識到,這是一項艱苦的“現代工程”。就此來看,高加林在《人生》中的“現代”并不徹底,因為他并沒有多少自己的主張,也無法與“父親”決裂,尋找自己的道路。
二、三個出走的“逆子”
以往的“家原型”中,形成了一個離家出走的“逆子”譜系。“逆子”反對“父親”,不遵從既定家庭秩序,離家出走,奔向自己的未來。《紅樓夢》中的寶玉,飄然而去,了卻塵緣,不知所終。《家》中的覺慧,坐上一條小船,離開自己憎恨的家,奔向遠方的希望。《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逃出地主家庭,走上革命道路。《創業史》中的梁生寶,為躲“抓壯丁”離開家庭,受到組織影響,轉化為堅定的黨員干部。可以看到,譜系中的“逆子”通常承載著作者的理想。他們出走后的行動,也隱喻著對原生“家”的否定,而建立新“家”的渴望與舉措,正是作者認可的未來。就此來說,《人生》寫了三個敢于挑戰原生家庭的“逆子”,他們的命運也體現著路遙的思考。
高加林不僅是高家,而且是高家村的“逆子”。他很清楚,自己必須離開高家村,“只要高家村有高明樓,他就非要比他更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樓他們強,非得離開高家村不行!這里很難比過他們!他決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會的面前,和高明樓他們比個一高二低!”(第13頁)高加林不認可“家”,因為他不認可“家”的既定秩序。在高家莊,他無力效仿譜系中的前輩梁生寶,借助外力的支持,改變面貌,只能像高覺慧和林道靜一樣,選擇逃離。高加林并不迷惘,他已經有了精神上的“家”:現代文明。他有很好的衛生習慣,懂得用漂白粉改善水質,喜歡讀書寫作,熱衷討論國際時事。他陶醉于縣城的現代生活:“他對這里的一切都是熟悉的,親切的;從初中到高中,他都在這里度過。他對自己和社會的深入認識,對未來生活的無數夢想,都是在這里開始的。學校、街道、電影院、商店、浴池、體育場……生活是多么的豐富多彩!”(第19頁)出走的“逆子”再度組織家庭時,一定是按照自己意愿,與原生家庭截然相反的。高加林雖然對家不滿,走出了家庭,但并沒有接受和攜帶“現代”觀念。“現代”可以分為現代生活和現代思想,不僅包括科技進步帶來的生活方式,還有以人的覺醒為中心的啟蒙意識。他崇尚城市的“現代”生活,僅僅是渴望擁有,并未獲得精髓,也從未想到,身在農村一樣可以擁有“現代”意識。因此,他最大的愿望不是離開家,而是拋棄農村人的身份。面對成立家庭的可能性,他內心有一個聲音,時刻提醒他放棄巧珍。“他甚至想覺得他匆忙地和一個沒文化的農村姑娘發生這樣的事,簡直是一種墮落和消沉的表現;等于承認自己要一輩子甘心當農民了。”(第48頁)“他還年輕,只有二十四歲,有時間等待轉機,要是和巧珍結合再一起,他無疑就要拴在土地上了。”(第48頁)在高加林看來,選擇巧珍就等于選擇農村。相反,如果選擇黃亞萍,就可以遠走高飛,去更大的城市,有更好的前途。借助城市姑娘的力量,改變自己命運,這個理念同樣體現在他本人的經歷中。[5]因此,高加林離家出走,尋找城市姑娘為伴侶,成立新家,并非出自啟蒙思潮下的“現代”意識,而是個人奮斗的路徑之一。
劉巧珍和黃亞萍,是走出家庭的兩位女性,她們的命運,更有隱喻意義。女性文學研究者認為:“‘五四女作家以女兒的感受,女兒的話語否定批判著封建父權歷史對女性的第一道禁令——未嫁從父,修改著歷史對女性從出生起的言語規定。作為叛逆的女兒、自由的女兒的女性作家們,以筆創造自己新命運的第一步。沒有這樣一個叛逆女兒的傳統,中國現代文壇上大概也便不會出現真正的成熟的女人及女性群體。”[6]不過,很顯然,女性解放是一場漫長的革命。《人生》用劉巧珍、黃亞萍兩個出走的逆子形象,回應了這一問題。劉巧珍是高家莊首富劉立本的二女兒,家庭條件很好,但沒有文化。仿佛是尋求一種補償,“她決心要選擇一個有文化,而又在精神方面很豐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侶。就她的漂亮來說,要找個公社的一般干部,或者農村出去的國家正式工人,都是很容易的;而且給她介紹這方面對象的媒人把她家的門檻都快踩斷了。但她統統拒絕了”。(第29頁)她與高加林一樣,對“現代”的理解并不全面。高加林的“現代”意識,深深吸引了劉巧珍。巧珍為了跟高加林好,配合他的“現代”,不惜犧牲名譽。巧珍家中,也發生了一場“父子”沖突。巧珍學高加林,開始刷牙,遭到父親批評。巧珍立刻嚷起來,指責父親不供讀書,毀了自己一生,令父親無可奈何。父親讓步,同意她刷牙,但建議在家,別出去。巧珍說:“讓他們笑話!我什么也不怕!我就要到鹼畔上刷!”(第43頁)從“父子沖突”的意義上說,巧珍獲得勝利,并且走出家庭,獲得了“現代”的權利。巧珍的“現代”,在于女性敢于與家庭決裂,毅然出走,打算主宰自己的愛情與命運。巧珍深知,她處于村人的目光下,名聲將受損,但并不懼怕,反而為自己走出家庭而驕傲。“巧珍是驕傲的:讓眾人看看吧!她,一個不識字的農村姑娘,正和一個多才多藝、強壯標致的‘先生,相跟著去縣城啰!”(第75頁)20世紀類似的故事,在高家莊重演,一個女性為尋求愛情和“現代”,離家出走。子君、林道靜、巧珍,不同時代的女性,為了自己的命運,對“黑暗”的家庭,做出了義無反顧的抗爭。作為反例,《家》中梅表姐、鳴鳳,由于無法走出家庭,釀成悲劇,引頸就戮。至少這一刻,巧珍對得起“現代女性”四字,勇敢離開家庭,至于此后的命運,另當別論。黃亞萍同樣是一名家庭的出走者。她是江蘇人,出身干部家庭,高中時隨父親來到本縣,因此,身上有城市、遠方氣質。黃父是武裝部部長、縣委常委,往來者皆為高干,馬上要轉業到南京。此前,黃亞萍是家庭中的乖乖女,與門當戶對的張克南戀愛,走向父母為她選擇的道路。當高加林來到縣城后,黃亞萍發現自己更愛“男子漢”性格的他,于是跟張克南提出分手。每個出走者,都有一次跟父親的沖突,黃亞萍也不例外。父親對她更換男友不滿,認為她游戲人生,“你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思想!你們現在這些青年人真叫人痛心啊!垮掉的一代!無法無天的一代!革命要在你們手里葬送呀!……”(第140頁)黃亞萍立場堅定,堅決反對父親干涉,終于如愿以償,與高加林在一起了。黃亞萍和高加林熟悉和追求“現代”生活,思想合拍。他們的戀愛很具有“現代”感,令人側目,“全城人都在議論他們,許多人罵他們是‘業余華僑。但是他們根本不理睬社會的輿論,瘋狂地陶醉在他們羅曼蒂克的熱戀中。”(第145頁)盡管他們可以借助經濟條件獲得“現代”資源,但他們并未意識到,“現代生活”方式并不等于“現代”。
此前的出走者,身上都攜帶了作家賦予的使命,立意在于形成對比,改變原生家庭的基因。林道靜出走后,與余永澤先戀愛后分手,轉而選擇盧嘉川、江華,走上了革命道路,改換了身份。檢視劉巧珍、黃亞萍,她們雖離開家庭,卻仍然秉持了“父親”的邏輯。《人生》中,她們各自暢談了對未來家庭的設想,卻并不批判和改變原生家庭理念。劉巧珍愿意給高加林舒適的生活,“咱農村有山有水,空氣又好,只要有個合心的家庭,日子也會暢快的……”(第36頁),“你在家里呆著,我給咱上山勞動!不會叫受苦的……”(第37頁),“等咱結婚了,你七天頭上就歇一天!我讓你像學校里一樣,過星期天……”(第53頁)她理想中的家庭,并無更多“現代”成分,反而有男尊女卑的影子。早在“五四”時期,魯迅在《傷逝》中,就借子君、涓生的經歷,反思了“娜拉出走后怎樣”,并讓子君“死去”,指出他們不過是走了舊路,反抗家庭無效。果然,劉巧珍很快嫁給馬拴,并要求舉辦舊式婚禮,將自己追求的“現代”棄置腦后,重回傳統懷抱。相比而言,黃亞萍的承諾側重個人發展,并因此打動了高加林。黃、劉的家庭暢想,內在本質相同,都是提高個人生活質量。不同的是,黃亞萍設計的是大城市的生活,而且給高加林發揮空間,“咱們在一塊生活吧!跟我們家到南京去!你是一個很有前途的人,在大城市里就會有大發展。我回去可能在省廣播電臺當播音員;我一定讓父親設法通過關系,讓你到《新華日報》或省電臺去當記者……”(第133頁)但是,這種設想建立在高加林擁有城市戶口的基礎上。黃曾因“個性解放”與父親發生過沖突,并取得勝利,但遇到現實問題,也不得不退卻。父親在高加林事發后,與黃亞萍又有交談,“這件事我已經考慮過了,這次你最好能聽爸爸的。咱們馬上要到南京,那個小伙子是農民,我們怎能把他帶去呢?就是把他放到郊區農村當社員,你們一輩子怎樣過日子,感情歸感情,現實歸現實,你們應該……”(第165頁)黃亞萍沒有再堅持,順從了父親,實現了“父子”和解,放棄了自己的“現代”追求。
《人生》中的三個逆子,走出家庭,卻沒能找到自己真正歸宿,這是“家原型”對逆子出走的另一種處理方式。逆子失去目標,中途返回(“死去”),也隱喻著作者的判斷。從思想層面說,三人對“現代”的認識受到時代局限,他們只能先彌合城市/農村間的身份鴻溝,才能考慮如何獲得個人的解放。現實中,路遙對青年身處的語境極為熟悉,“高加林、劉巧珍、黃亞萍等都是好人,但性格中都不同程度潛含著悲劇性和庸俗性的因素”,“通過這個不幸的故事使人們正視而且能積極地改變我們生活中許多不合理的現象”。[7]就此來說,《人生》的安排類似《傷逝》,用逆子出走后的失敗,引發人們更多思考。事實上,《人生》當時得到很大關注,正與青年悲劇的廣泛性有關,“是制度/文化的‘歷史遺留物的存在,扼殺了一代青年的合理性欲望和夢想”[8]。路遙讓逆子“死去”,處理為悲劇,不止為了賺取讀者眼淚,還隱藏著自己強烈的現實關懷以及理性希冀。
三、“引路人”和“敵對者”
為了讓家族故事伸展,走出封閉結構,作者通常會設置家庭外的人物,即“引路人”,幫助主人公克服困難。引路人是先知、代父、幫手,獨立于家庭之外,具有指引作用,隱喻著作家認可的理念。《紅樓夢》中的一僧一道就是引路人,帶領寶玉游歷人生,最終“好便是了”,遁入空寂。《青春之歌》中,代父是革命先行者,盧嘉川、林紅是林道靜的樣板,指引她的方向。同時,也會出現“敵對者”、反派,為主人設置障礙。一般來說,主人公總是借助引路人,戰勝敵對者,完成預設目標。
作品中的德順爺爺,充當了高加林的引路人角色,同時也是高加林的“代父”。德順爺爺是愛的化身,如同神靈,施舍給每個人,普惠蕓蕓眾生。“德順老漢一輩子打光棍,有一顆極其善良的心。他愛村里的每一個娃娃。有一點好東西,自己舍不得吃,滿莊轉著給娃娃們手里塞。尤其是加林,他對這孩子充滿了感情。小時候加林上學,家境不好,有時連買一支鉛筆的錢都沒有,他三毛五毛的常給他。加林上中學時,他去縣城里賣瓜果,常留半筐子給他提到學校里。”(第46頁)德順爺爺一直庇佑著高加林。他最早指引家林,認為他和巧珍是“實實的天配就”,并跟他們說,“娶個不稱心的老婆,就像喝涼水一樣,寡淡無味”。(第87頁)他對愛情的追求,影響了高、劉兩人,促使他們勇敢面對村人眼光,走到了一起。聽到高加林與巧珍分手消息,他與高玉德一起去縣城,訓示加林,盡顯代父功能。他說,“你把良心賣了!”“巧珍這么好個娃娃,你把人家撂在了半路上!你作孽哩!加林啊,我從小親你,看著你長大的,我掏出心給你說句實話吧!歸根結底,你是咱土里長出來的一棵苗,你的根應該扎在咱的土里啊!你現在是個豆芽菜!根上一點土也沒有了,輕飄飄的,不知你上天呀還是入地呀!你……我什么話都敢對你說哩!你苦了巧珍,到頭來也把自己害了……”(第148頁)從這番話看出,德順爺爺對加林的行為不滿,認為他不再珍重鄉土,缺乏道義。果不其然,高加林栽了跟頭。他重新回到高家村,萬念俱灰,又受到德順爺爺指引。德順爺爺告訴加林,讓他放開心胸,重新開始“活人”。他如同加林的人生導師:“德順老漢大動感情地說著,像是在教導加林,又像是借此機會總結他自己的人生;他像是一個熱血沸騰的老詩人,又像一個哲學家;那只拿煙鍋的、衰老的手在劇烈地抖動著。”(第182頁)由此,德順爺爺確定了他在《人生》中獨一無二的地位,而他的主張,也代表了路遙對這場戀愛的看法。他的指引顯然發揮了作用,“高加林一下子撲倒在德順爺爺的腳下,兩只手緊緊抓著兩把泥土,沉痛地呻吟著,喊叫了一聲:‘我的親人哪……”(第184頁)
德順爺爺是普通老農,并無高深文化,為何能夠指引加林,成為《人生》中的智者?顯然,他承載著路遙的預設。德順爺爺是一位鄉土哲學家,立足于土地,愛護著土地上每一個生靈,因此,承載著鄉土文化的美德。對錯誤的包容,以及活下去的生存哲學,是他對高加林的最大啟迪,而這一切,都建立在簡單的善良之上。在德順爺爺看來,無論如何,不應該喪失生活的希望。他對加林說:“就是這山,這水,這土地,一代一代養活了我們。沒有這土地,世界上就什么也不會有!是的,不會有!只要咱們愛勞動,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再說,而今黨的政策也對頭了,現在生活一天天往好處變。咱農村往后的前程大著哩,屈不了你的才!娃娃,你不要灰心!一個男子漢,不怕跌跤,就怕跌倒了不往起爬,那就變成個死狗了……”(第183頁)這段話如同宣講,不像出自一位老農之口,更像作者的心聲。雖然安慰了加林,但指出的方向是讓加林留在土地,建設農村。德順爺爺無疑是路遙的代言人。《人生》發表后,路遙知道有人批評他,認為不應該讓高加林回歸土地,但不以為然:“高加林為什么就不應該有一點所謂的‘戀土情結?即便這土地給了他痛苦,但他終究是這土地養大的,更何況這里有愛他的人,也有他愛的人。他即使想遠走高飛而不成,為什么就一定要詛咒土地?如果是這樣,那這個人就是精神變態者,而不是一個正常人。任何一個出生于土地的人,都不可能和土地斷然決裂。我想,高加林就是真的去了聯合國,在精神上也不會和高家村一刀兩斷。”[9]《人生》中,德順爺爺就是土地的象征,這個“無家”的老光棍,守護著鄉村公序良俗,恰是“家原型”中不可或缺的家文化的精神核心。
高加林回歸土地,因為德順爺爺是他的引路人。但是,《人生》有一個重大空缺:高加林的“現代”引路人是誰?“現代”以來,鄉土發生巨大變遷,影響了農民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正是對“現代”的理解局限于物質(城市),因此,高加林的人生追求發生了錯位,也缺乏發自內心的精神力量。高加林到縣城圖書館后,沉浸在閱讀中,享受著美妙生活方式,但是,他不能從中提取出有力的指導思想,所以,當他走出圖書館,又成了賣饅頭的農民。一個可以與德順爺爺抗衡的引路人,始終沒有出現在他的生活中。高加林渴望“現代”,改變自己精神生活貧乏的現狀,離家出走,但是,他離家后,所處的鄉土文化語境沒有改變。他在閱讀中體會到的“現代”,只不過是虛幻的夢境。高加林只能通過“現代生活”,確認自己“現代”,這是一種誤解。他近距離接觸了“現代生活”,“黃亞萍把他帶到了另一個生活的天地。他感到新奇而激動,就像他十四歲那年第一次坐汽車一樣”。(第145頁)但是,黃亞萍并不能通過給他思路,充當他的精神引路人。“現代”引路人的缺失,表明路遙更關心“城鄉交叉帶”的沖突,不打算延展空間。他從農村上了大學,費盡周折,深知其中艱難,因此沒有動用這個經歷,刻意把高加林留在了農村。[10]
《人生》中,“家原型”中的“敵對者”卻很復雜。高加林“走后門”,違規參加工作,結果被退回,因此,敵對者分明是照章辦事。但是,不能忽視,高加林命運的轉折,是一個偶然事件。高加林與黃亞萍戀愛,惹惱了張克南媽媽。她調查出了“走后門”問題,不顧兒子勸阻,寫信告發,導致高加林被退回農村。問題在于,按高加林能力,完全勝任記者職位,只因他是農村人,因此被拒之門外。像高加林這樣有才華的農村青年,缺乏的并不是依靠暗箱操作才能獲得的記者工作,而是依靠自己能力可以實現人生價值的機會。相對而言,無法給予機會的現實,才是高加林真正的“敵對者”。
作品中的悖論就此出現了。高加林的“家”中,既有敵對者高明樓、劉立本建立的現實體系,又有溫暖他的德順爺爺和巧珍的人性善良,誰會勝利?此前的“家原型”中,還從未有過引路人和敵對者如此膠著,你中有我的狀況。如果按照《人生》結尾提示,可以做出預測,高加林將重返代課教師崗位,繼續教書,因為德順爺爺和巧珍都去跟高明樓講過。這意味著,故事回到開端:高加林做回農民,而高明樓仍是高家村的主宰,一切照舊。以高加林的性格,他怎么可能滿意這樣的結局?路遙可能也覺察出問題,故把最后一章注明“并非結局”,為讀者留下了想象空間。高家村里,引路人和敵對者之間的斗爭,不會有答案,無論誰勝利,高加林都是失敗者,這是作品中無解的問題。
四、小結
從“家原型”角度說,《人生》體現了類型小說的許多元素,并做出了自己處理,成為這個敘事傳統中的一部分。路遙讓高加林、劉巧珍、黃亞萍三個青年踏上了啟蒙道路,離家出走,卻又給他們一個悲劇結果,使他們重新回歸原生家庭。追求現代之路變成了青春期的沖動,令人扼腕。他們回到了“家”,但經歷一番風雨歷練,已經不再是從前的自己。因此,所有的研究者達成共識,都不去預測高加林后來的“家”。路遙同樣如此,他本來打算寫《人生》續集,后來放棄了。
[注釋]
[1]關于“家族小說”,已經出現不少研究成果,如《家族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曹書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被“家”敘述的 “國”——20世紀中國家族小說研究》(劉衛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等。
[2]路遙:《人生》,《路遙全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頁。下文引文出自該書的,僅在文中列出頁碼,不再注釋。
[3][美]柏文莉:《權力關系——宋代中國的家族、地位與國家》,劉云軍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封二。
[4]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全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37—38頁。
[5]路遙與朋友交談時,并不掩飾想找城市女朋友,以便離開農村。海波回憶說,自己建議路遙找本地女孩做妻子,“他一聽竟然生氣了,反問我說:‘哪一個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學?不上大學怎么出去?就這樣一輩子在農村漚著嗎?”海波:《人生路遙》,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頁。
[6]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 現代婦女文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頁。
[7]路遙:《關于電影〈人生〉的改編》,《路遙全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頁。
[8] 賴寧、張均:《路遙創作〈人生〉的材料來源》,《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年第5期。
[9] 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全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頁。
[10]張艷茜:《1973:作家路遙的高考》,《南方文壇》,2021年第1期。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