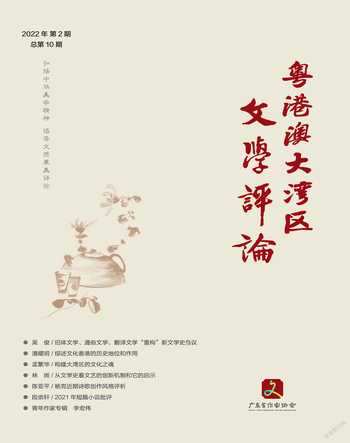從文學史看文藝的創新機制和它的啟示
林崗
摘要:古人對易道周流深有體察,就像古代文論里的通變論就是詩文領域的創新論,它是文論里創作論的基本命題。但文藝史上還存在另一種古人未曾討論的創新機制,它雖超出創作范疇但仍屬于文藝的創新現象。這種創新機制在詩文作者個人求新求變的主動意識之外,由無意識的“跨界”,變換原來的寫作賽道,不自覺之間實現了文藝創新。了解了文藝史,明白了創新現象的機理,今天的作者可以變被動為主動,在創作中為我所用。
關鍵詞:通變;創新機制;雅俗;自在;自為
科技和文藝恐怕是人類工藝和精神活動里最講究創新的兩個領域。無論兩個領域的創新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長江后浪推前浪的鐵律都支配著這兩個領域的人類活動。一旦創新活動停頓下來,科技這個“第一生產力”就止步不前,而文藝則只能重彈“老調子”,作家只能重復自己。科技被人類的好奇心和市場活動驅動著進行創新,而文藝為作者的激情和讀者觀眾驅動著進行創新。你不創新,舊技術就被淘汰。你不創新,作家和作品無從獲得應有的價值和位置。可以說,創新的價值和意義無論對于科技還是文藝都是同等重要的。
從歷史看,與古代中國技術長期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不同,文學的創新老早就成為命題,進入了文論家議論探討的視野。這就是古代文論持久探討的“通變”命題。在古代生產技術屬于日用百姓,“勞心者”可以不察不知不關注,但詩文屬于安身立命的“三不朽”之一,士大夫是用心講求的。所以他們早早知道“立言”而傳之久遠,其秘訣在于“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1] 然而古代文論家是將創新作為創作論問題來探討的,所說的“通變”只在創作的范疇得到討論,換言之“通變”只是詩文作者必備的本領。如劉勰論通變:“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2]那些能懂得通變道理的文士,其創作走得更遠。而那些走不遠的,寫作有時而窮的詩文作者,就在于他們沒有掌握通變的方法。“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途,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疎耳。”[3]古人文論的通變思想,當出于易道。《周易》有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4]對天道周流不息,往復變易的觀察,已經深深楔入中國人的文化深層心理。它能化入文論之中,成為古代文論創作論的基本命題,是毫不奇怪的。然而,因為通變局限在創作論的范圍,一旦說到如何才能通變,文論家所能指出的具體門徑,也就無非回歸“文統”,謹守經典,博覽精閱,變文為質,師法古人這幾項。這些門徑固然有其道理,對某些詩文作者,尤其是初學者是有效的。但這些通變的門徑在歷史上到底發揮了多大的作用?我以為不能高估,尤其是不能認為古人的通變論就說盡了文藝創新的道理。這并不是因為古人的通變論錯了,并不是因為古人所論的通變門徑與事實不符,而是因為古人將文學的創新僅僅置于創作論的范圍來探討,其眼光還是顯得受限了。通變固然在創新的范疇,但似乎不是文藝創新的全部。還有,就創作而論,詩文作者能接受和領悟通變的道理僅僅觸及創作者主體理性的層面,至于具體的創作者能否將這個通變的道理落實在創作中,還存在個人才華的問題。這不是理性層面能解決的。道理再正確,方法再得當,奈無才何?以創作的眼光看,作者最后能否實現通變,最為重要的因素并不是懂得不懂得通變的道理,而是文學的才華到底如何的問題。若是缺乏文學的才華,懂得再多的通變道理也是白搭。所以古人以通變論文學創新,只觸及到了文學創新的部分問題,決沒有窮盡全部。以創作的通變論創新,固然有其道理,但也未必盡然。如果我們跳出創作論,以史的眼光觀察文學,與創作通變論不同的文學創新景象赫然出現在我們的面前。我把它稱作創新機制,因為它超出了作者創作的領域但也屬于文藝的創新現象。其中的道理也值得我們略加闡述。
文學史上,我們看到與創作者主動“通變”不一樣的文學創新,這類創新通常是在無意識中實現的。創作者為料想不到的文學新現象所吸引,逸出了原來的規范軌道,無意中走到了一片寫作的新天地。用通俗的話說,就是不知不覺中更換了賽道,既沒有謹遵經典師法古人,也沒有主動求變,但事實上卻實現了文學的創新。當然就創作者無意識這一點而言,所謂創新也是我們事后看出來的。這種創新頗有黑格爾“自在”概念的味道,它雖然不是主動求新求變那樣“自為”的創新,卻也通過漫長歷史的積累,實現了文體、題材和風格的創新。一部豐富的中國文學史提供很多這方面的案例。比如五言詩的出現,那是詩史上劃時代的大事。它當然不是哪一位詩人求新求變的結果,五言體首先出現于民間樂府詩,然后文人士子仿效試作,逐漸完善而成為詩體的主流,其間跨越百年。詞、戲曲、話本的演變大體上也經歷了類似的故事。這種類型的創新如果給個說法,可以稱為更換賽道式的創新。它在創新的方向、方式、途徑和實現的效果上都不同于創作論意義的“通變”,我們有必要好好認識這種文學史上存在的“自在”式創新機制,這對于今天的文藝家進行文藝創新是有好處的。
中國文藝自古以來就存在雅俗分治的格局。雅俗分治意味著由文體、表現方式、修辭乃至用詞等不同構成的趣味差異各有其存身的天地。雅的在社會上層,滿足富有教養、斷文識字的貴族上層文人士大夫的文藝需要;俗的在社會下層,滿足那些不識字、缺乏教養的百姓的文藝訴求。雅俗分治的格局演變出來的一個結果就是雅的文藝流行一段時間就凝固、僵化起來,難以獲得持續下去的動力。古代文論的“通變論”其實就是針對此種局面而提出的挽救之道,期待身處文統之內的士大夫具備自覺意識,在雅的文藝凝固僵化起來的時候扶衰救弊。至于這種雅的文藝在流行中易于凝固僵化的原因,乃是因為它們本來就不是面對著生活的“原生態”,比較高高在上,流行既久,就陷于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境地,失去再生的動力。然而與此相反,俗的文藝因為在民間,它雖然粗俗、幼稚但不凝固、不僵化因而呈現生機勃勃的面貌。粗俗的生命力在俗文藝里是不缺乏的。如各地域的民歌,陜北的酸曲、青海甘肅的花兒、兩廣的客家山歌等。由于雅俗分治的格局,新文體新風格的形成往往在民間。它們活躍、有生機,但粗糙、幼稚、不完善,反映的是民間社會的趣味。雅俗相較正用得上一句老話,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單純執著于雅俗在審美上的長短,我以為并沒有大的意義。我們需要觀察的是雅俗文藝在歷史上的交往和互動。這里需要強調一點,雅俗分治并不意味著雅俗隔絕。分治只是指出了趣味分層的狀況,分層不是隔絕。雅文藝歷史上對俗文藝的影響主要便在于觀念的示范和導向方面,可以說雅文藝的觀念內容很大程度上規范了俗文藝,滲透了俗文藝,它起著示范的作用。俗文藝史表明,通俗作品無論在趣味上如何“出格”,但極少見它們非難或違背儒家倫理和傳統的道德信條。趣味可以不同,反調近乎罕見。即使有一二個例,也屬于“正統的異端”。可以說雅俗兩者在意識形態上根本就是一體的,從這種一體性中可以看出雅文藝對俗文藝的示范和導向的影響。
雅俗分治又不隔絕的格局無形中給文藝創新開出了一片天地。處于社會上層的雅文藝當然是規規整整毫不紊亂的。當它的文統生機勃勃的時候其文藝創作也是生機勃勃的,然而當承平日久,它逐漸進入凝固僵化狀態的時候,情形就起了分化。一方面是堅守文統的士大夫打出以復古為革新的旗號,在“通變”的范疇內尋求出路。這種復歸元古、師法古人由文歸質的文學思潮,在漢唐宋明清都曾出現過,它是上層雅文藝內部發生的演變。另一方面是富有文藝修養士大夫當中的有心人,他們轉向民間的俗體文藝模仿學習,汲取俗文藝在表現方式、題材、修辭等養分,為己所用,以自身深厚的文藝教養改造俗體形式,由此實現文藝的創新,給文壇帶來清新的面貌。這些文人士大夫之所以能這樣做,雅俗分治但不隔絕格局的存在是一個前提。在歐洲就很難設想這種文藝上雅俗滲透的情況出現。因為歐洲的文藝傳統,其雅和俗,不但分治而且隔絕。雅和俗不但是趣味的差異,而且也是階層的隔絕。平民的趣味、文藝形式和修辭不存在進入貴族和僧侶欣賞的渠道,就像它們的戲劇傳統里悲劇和喜劇的截然劃分一樣。但是中國的文藝傳統與此不同,文藝固然有雅俗,趣味固有不同,但社會存在強大的上下層溝通機制,像儒家所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5]就是一端。雅文藝的趣味和形式,它們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開放性。當原本屬于俗文藝的文體、表達方式和修辭得到文人雅士的改造提升,它們也能登堂入室,迅速成為上層審美追捧的對象。假以時日,原本屬于俗的,日后即變身為雅。
如果追溯動機,士大夫當中的有心人當初也不像現今文藝家那樣立意創新。他們往往對文藝趨向的變化,觸角并不是那么敏銳。只是他們比較放得下文人雅士的架子,虛心看待周邊的新事物;或者即使依舊端著文人的架子,但有今日當做今日事的隨機應變能力,不被舊的條條框框束縛住手腳。于是邁得開不尋常的步子,模仿、學習民間俗界流行的文體、風格、文藝形式。他們只要能寫出足夠有新意的作品,自然就引來了更多的效法者,不斷實踐,不斷完善,從而提升了俗界文藝形式的文藝性。其中好的作品在文藝史上獲得長久的名聲。中國文學史上,這樣例子比比皆是,大家耳熟能詳。由于文獻疏于記載,很少留下具體的人名,今天還說得出姓甚名誰的鮮少,但案例卻是俱在。比如詞,它的前身原本流行于唐代絲綢之路各節點城市歌樓酒肆的尋歡酒宴,為胡姬藝妓所演唱,樂器、樂曲多來自西域而融匯華夏。這種文藝形式,不但流行于社會下層,而且舶來色彩濃厚,是典型的俗文藝。它們與正宗文體的詩文分屬不同的藝文天地,但身處文化大熔爐長安的士子,得意或失意的,無不出入酒肆歡場,耳聞目染,或一時技癢,或為情所動,為自己為歌女譜將起來,變身為歌詞作者。當時隨作隨毀的當不計其數,那些僥幸流傳下來的,就成為詞,一種此前未有的抒發情感的文藝形式。今天我們能讀到的“詞祖”是李白的《憶秦娥》,既有才子傷情,又飽含英雄氣概,末句“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意境何等雄闊。又如,話本乃至章回體小說的產生,也與此相去不遠。它淵源于佛教傳入中原時行腳僧向百姓宣講佛本生故事的底本,我們今日還可于敦煌變文看見其輪廓。行腳僧的傳教行為無形中帶起了口頭講故事的風氣,引來了下層文人的模仿,于是故事題材由宗教向世俗轉移,敦煌變文中又有講史一類。這意味著口頭講故事這樣一種佛教東傳輸入的表達方式,不僅脫離了宗教傳播,而且被民間說唱藝人加以本地化。到了宋元時期,口頭講故事的風氣流行,部分失意文人更加以模仿,孕育了話本、擬話本乃至章回體小說。如果沒有文人加入這個行列,那口頭講故事也許就停留在說唱的階段。又如,古代文學批評的評點方式,明以前僅用于詩文。晚明才子金圣嘆,才高傲物,屢考不第,作文嘲笑考官,是典型的落魄文人,但他將自己原本擅長批點詩文的批評方式,創造性地運用于批評當時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章回體小說。他應該不是第一位評點通俗文體的人,但他把這一批評方式做得爐火純青,別開生面,成為一位通俗小說的批評大家。上述例子,都是在新的表達方式、題材、修辭等已經存在的情況下,不行舊路走新路,更換了賽道,無意中創新了文藝。古代文人能夠這樣做,站在他們本身的立場,眼光向下,汲取文藝“原生態”的養分,這是最重要的。
客觀上,古代文藝史上的雅俗分治和交流融通給中國文藝帶來了源源不斷創新的土壤。然而土壤的存在不等于現成的創新,就像有了一片土地并不等于一定能獲取收成。就算在古代也并不是任何一位作家都能利用好歷史機緣給他們提供的條件,絕大部分作家還是習慣于原來的軌道,對創新機會的悄然到來渾然不覺,更何況那些客觀上更換了賽道的作家也多在無意識中實現的。所謂機緣巧合,偶然性的因素扮演了創新更重要的角色。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今天可以勝過古人。中國從百年前的農耕大國已經變身為工業和科技大國,科技和生產力的極大進步已經使得創新意識深入人心。文藝創新包括文藝評論的創新已經成了我們共同的話題。這就說明現當代的文藝創新,它不再是“自在”的,而是“自為”的。主動而有意識地進行創新實踐已經變成文藝領域的普遍現象。當然這并不是說已經不存在提升創新意識方面的問題。作家對創新的自覺性能從“自在”的狀態提升至“自為”的狀態總是對文藝的正向發展有好處的。
除了變“自在”式的創新態度為“自為”式的創新態度之外,實際上現代中國社會的文藝創新土壤比之古代中國社會不僅遼闊得多,而且肥沃得多。這要拜科技改變人間的強大能力所賜。社會學上,用第幾次“浪潮”、第幾次“產業革命”來形容當今科技給予人類社會的影響。不用叨念那些詞語,用我們日常生活的感知就能領悟如今正處于科技力量強有力塑造我們生活的年代。這種改變既給文藝創新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伴隨從未遇到過的挑戰。比如日漸成熟的網絡平臺,它本來只是信息傳輸的技術,并不屬于文藝。但文藝作品從來都存在傳播的問題,網絡技術的出現不但創新了文藝的傳播方式,而且借助這種傳播方式催生出新的表達方式,一大批寄生于網絡天地的文藝表達形式,如網絡小說、中短文藝視頻、虛擬畫廊等如雨后春筍般冒出頭來。它們一如古代通俗文藝,雖不入于大人者的法眼,但卻異常活躍,生命力強大。在技術的周期之內,它們的生存是沒有問題的,隨著技術的迭代,它們的形態當然也將隨之改變。無論如何,我們今天面對由科技催生的新的表達方式及其文化,是不是有幾分像前文討論的雅俗分治的格局?其實這就是一種新時代文化上雅俗分治的狀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是不是也由此存在一片文藝創新的沃土?我認為是的。現代科技為文藝發展創造了另一個“民間”,不同于自古以來的山村鄉野的民間,它是技術的“民間”。這兩個民間都可以為文藝創新提供營養豐富的“原生態”。要實現具體的文藝創新,文藝家們如果能睜開雙眼,邁開雙腿,走向這兩個“民間”的大地,就一定能實現其創新的目標。其實文藝界的有心人已經嘗試這樣做了,只是這片文藝創新的沃土還未被充分認識而已。當然也要知道,技術雖然是中性的,但它創造改變的可能性越大,也意味著借助它進行改變的風險越高。在這種情況下,文藝創新很可能走向單憑著創作者空洞暢想的途徑。如果創新搞成創作者海闊天空的造作,那這種自我臆想出發的創新就不會是真正的創新,只是泡沫式的空洞的把戲。在創新意識高漲的今天,尤其需要避免空洞、為創新而創新的“創新”。
總括文學史呈現的文藝創新機制,它一直在兩個層次進行。一個是創作主體自身通變的層次。這個層次的創新多與經驗的積累,與對先在傳統的體悟師法有關。在文藝史上見到的“中年變法”“衰年變法”現象,就屬于這個層次的創新。但文藝史上還存在另一種更換賽道式的創新,它跨越原來的文藝趣味層次和表現方式,進入原來不熟悉的初生的文藝天地,以自身的教養趣味提升原來的表達方式,從而實現文藝創新。其實人類的生活無論古今,那些在生活里展開的粗糙幼稚不成熟的形式、表現媒介和風格一直存在。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向在“原生態”蓬勃生長的文藝汲取創作的養分,效法和學習其中有益之處,不失為一條可以借鑒的途徑。只要有志的創新者有足夠的思想和文藝覺悟,有足夠的藝術敏感性和趣味的辨別能力,就一定能夠發現這些粗糙幼稚和不成熟的形式、表現媒介和風格有價值的地方,也一定拋棄其中的糟粕和無聊的成分,從而完成文藝的創新。
[注釋]
[1] 陸機:《文賦》,見郭紹虞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7頁。
[2][3]劉勰:《文心雕龍·通變》,見范文瀾注本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519頁。
[4] 《周易·系辭下》,見《十三經注疏》上冊,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74頁。
[5] 《禮記·大學》,見《十三經注疏》下冊,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673頁。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