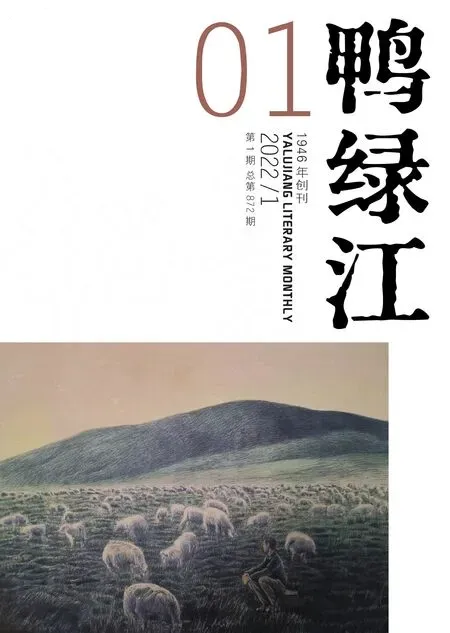那些中魔的人
《饑餓藝術家》:饑餓藝術家
讀卡夫卡小說給人的最大震撼是,他筆下的人物都在跟某種外在于自己的力量較量、抗爭,最后又都無不歸于失敗或者失意。中魔,在這里意味著,那些人物幾乎身不由己地走向了存在的反面,自己成了自己的敵對者;更關鍵之處還在于,他們似乎不變成異己者,就無法分享和滿足自我的價值。就像《饑餓藝術家》里那個表演者,沉迷于饑餓表演,如癡如醉,不能自拔。不是觀眾需要他那么忘我投入,他們不過是走過來看看熱鬧,然后溜之乎也。可是表演者卻把表演當成了全部的生命意義和終極歸宿。他在分不清生活目標和生活本身的界限上著迷了、中魔了,就像一個酒鬼,不曉得酒只是生命的道具,而不是生命的全部依托。
年輕那會兒,讀《饑餓藝術家》,會讓我不自覺地聯想到凡·高、果戈理,還有西蒙娜·薇依這些人的獻身。他們忠實于自己的人生目標和理想,為此受盡苦頭,他們某種程度上是藝術或者哲學的圣教徒。果戈理和西蒙娜·薇依最后是餓死的或者死于營養不良,為了信奉上帝的救贖之恩。他們甘愿做迷途的羔羊,甘愿奉獻自己的殘軀,只是在上帝鞭影的抽打下,才獲得了心理和命運的雙倍恩寵。納博科夫在《尼古拉·果戈理》一書的開端就為這位大作家的死用足了筆墨,“‘個人的絕食抗議’(病態憂郁的他試圖以此對抗魔鬼)導致身體徹底枯竭”。至于西蒙娜·薇依在自己的筆記中曾有過這樣的話:“祭品:除了‘我’,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獻出。”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她什么也沒吃,只喝了一點水和茶。她為不進食找的理由是,當她想到法國人在法國挨餓時,她就不能吃東西。”(參閱雅克·卡博《信仰與重負》)相比之下,凡·高則是把全部的熱情和信念抵押給了自己的畫布和畫筆,用于描繪永恒自然和人類自身那無窮無盡的美,而他絕望中的燃燒,稱得上是在火光中拾取麥穗和栗子的真正實踐。這些為信念而生而死的人,于我心有戚戚焉!
但是,卡夫卡的小說只是提供了具體情節,其意味或者寓言般的昭示,卻是個人所得不同。何況隨著年齡閱歷經驗還有理解等因素的加入,個體的閱讀,其實也多呈現出前后判斷上的迥異差別。
后來,當我再讀《饑餓藝術家》就冷靜些了,多了一層警惕,多了一份質疑,也多了難以名之的某種憂慮。
圍觀者和被圍觀者,之間其實是有藩籬的,隔著人性和社會體制的墻。
當受苦受難,成了時尚的表演,那么藝術家投入得越死心塌地,就越是悲劇,超過一定界限,還有可能淪為喜劇甚至鬧劇。
尤其當表演者覺得自己的表演還不到位,還有空間施展最后的伎倆之際,他其實已經異化了。生命本身的價值被生命外部的幻象包圍了。卡夫卡看到了或者預先感知了整個20世紀的存在夢魘和精神夢魘。一切內在的價值最后都被外在的表象所驅使所駕馭所征服。饑餓藝術家最后死在“找不到適合自己口味的食物”的絕望里。作者在小說的結尾才道破故事的玄機。饑餓和饑餓感并非一回事。前者是真實發生的,后者出于想象。但問題是,一旦對饑餓的想象,保持持久的興趣和習慣,那么即便真實的饑餓來了,你也找不到回應的動力了,換言之,一個人也沒有胃口去打敗它了。
人類中魔容易得很,解除魔咒卻是無比艱難的歷程,或許甚至要付出一代乃至幾代人的生命代價和精神磨難。
《王佛脫險記》:王佛
中魔的人會有怎樣的表現呢?有時候這恰恰是故事的敘述起點和動力源泉吧。在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的小說《王佛脫險記》里,那個老畫家王佛似乎就活在畫里,他的畫仿佛就是魔法的源頭、橋梁或是再生之地。
東方文化、東方經驗對于西方許多作家無疑構成了精神存在之謎的誘惑。尤瑟納爾本人也像個猜謎者,用她的短篇小說集《東方奇觀》對于異域的文明鏡像和光影、故事和人物進行了一次冒險,一次越位、換位的審美挑戰和超越。
許多年前,我就迷上了尤瑟納爾的故事。尤其是《王佛脫險記》,里面創造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幻境,那幻境的妙處是誰讀了都渴望成為其中的人物,也好跟著故事中的幻想擁有那種超能量。
這時候讀者跟著小說走,跟著人物活。
也就是說,一個好的作家首先應該為讀者提供魔法或者魔方,讓人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尤瑟納爾在故事情節結構上常有出人意外甚至超凡入圣之妙筆點染人物的命運和歸宿。
在尤瑟納爾的講述里,主人公王佛活靈活現,如醉如癡地沉迷于宇宙之道、人生之道,它們的聚焦點就是畫幅和線條,就是顏色和光影動感。換言之,作為探索外部世界的人,王佛“愛的是物體的形象而不是物體本身”。
西方小說大師的作品,好像都有一個宗旨,就是試圖探索生命的迷局,制造命運的迷宮,或是尋找到超越現實圍墻的一架梯子。
在尤瑟納爾的故事格局里,讓王佛面臨死亡威脅的是他的畫,最后拯救他出逃的也是畫。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東方玄機,在這位法蘭西女文豪看似悠閑別致實則密不透風危機迭現的筆調里,獲得了藝術美學的大膽嘗試和出新。
王佛迷畫至深,早就超出了常人常理常態。作者沒有明寫,卻以暗示和別人的目光來體察。就是通過他的弟子林的一舉一動的細節發現來烘托渲染老師的藝術法眼和著魔的心態。
林在富有舒適的家庭中長大,嬌生慣養的生活使他成為一個膽小的人,害怕昆蟲、雷電還有死人的面孔。
他和王佛的相遇是在一家小酒店,酒酣耳熱之際,兩個人打開了話匣子。王佛指點著林,讓他發現喝酒的人被熱酒的騰騰煙霧暈化的面孔上所具有的那種美,“被火舌輕重不勻地舔摸過的醬色肉塊的光澤,還有那桌布上的酒漬,狀如凋謝的花瓣,現出一種雅致的玫瑰紅色。一陣狂風吹破窗紙,暴雨飄進了室內。王佛俯身指點著林觀賞那一道道青灰色的閃電。林驚嘆不已,從此他不再害怕暴風雨了。”
尤瑟納爾用細筆微雕的寫作方式引發了人物情感的微妙波瀾,還有情節上的著意鋪墊,為后續故事的展開埋下了精到的伏筆。
林一旦愛上了王佛的畫,甚至是畫中人,比如他那以自己妻子為原型模特的作品,就勢必冷落現實生活中的人,導致她有一天吊死在開著粉紅色花朵的梅樹枝上。“王佛為她作了最后一幅畫,因為他喜愛呈現在死者臉上的那種青綠色彩。他的徒弟趕忙替他調色,這工作要求他那么聚精會神,使他忘記了為自己的亡妻流淚。”
世間多有中魔的人,讓他們彼此相遇,互相中魔,這是小說家們最渴望干的一件事了。
尤瑟納爾將故事安排在了漢王國。那里的皇帝要殺王佛,理由是他從小被父皇封閉在內宮里,不準跟人接觸,每日就是面對著王佛的一些畫,打發一日長于百年的孤寂落寞的時光。漸漸地他迷上了那些畫的色彩和線條,以至于后來宮門大開,他走入了日常自由的世界,卻改變不了心中的幻念,看所有的景、所有的女人都找不到王佛畫里面的美。在把王佛和弟子林抓住后,他對老畫家坦言相告:“最值得統治的帝國只有一個,那就是王老頭通過成千的曲線和上萬種顏色所進入的王國。只有你悠然自得地統治著那些覆蓋著皚皚白雪終年不化的高山和那些遍地盛開著永不凋謝的水仙花的田野……”
接著弟子林被殺掉,王佛被皇帝要求畫一張從前未曾畫完的畫,然后也會被弄瞎眼睛,處死。這剩下來的畫,讓王佛最后一次走近畫布,拿起筆,畫他生命最后一刻的素材、色彩和線條了。
生死攸關之際,老畫家“擦干了眼淚,微笑了起來,因為這小小的畫稿使他想起了自己的青春”。
明知道畫完畫就得死,可是在自己喜歡的美麗的勞作中猶如夢境一般的狀態里死去,這不就是一種魔法般的生嗎?
畫到高潮,故事也將至頂點,那畫出來的一葉扁舟竟然活起來,變成真的,“附在船夫槳柄上的水珠還在顫動哩”。當時是在朝廷的宮殿上作畫,這會兒大臣們在身齊肩頭的大水中懾于禮儀不敢動彈,原來已經燒得通紅的用來燙瞎王佛眼睛的烙鐵早已在劊子手們的火盆中冷卻了……
也許中魔的人都會遇到魔法奇跡般的救贖,這是小說的謊話,還是小說家按照人類理想邏輯及其信條編織出來的夢語呢?
到了結尾,弟子林居然也奇跡般生還,跟師父一起駕著一葉扁舟隨風遠去,逃離了災難和死亡。其實他們是消失于畫面里,消失于自己癡迷和愛著的精神王國、自由王國。在那里,客觀和現實的界限松動了,變成了可有可無的背景和遠景。
《渴睡》:瓦麗卡
契訶夫說,寫作應做到使讀者不需要作者的解釋。這話打通了小說藝術的最后一道玄關。
寫小說可以裝神弄鬼,可是寫到自在之處,還是得向人家契訶夫看齊。
就是說那些真正美妙的故事是讓人親近的,能看懂,并且領會到人生的一點一滴的道道。
汝龍翻譯的《契訶夫短篇小說選》,一直是我珍藏的最愛翻看的書之一。另一本是葉君健譯的《安徒生童話》。
一個職業是醫生,一個是鞋匠的兒子,也許他們的耐心細致溫良謙和,保證了他們寫故事總是講究平視的角度,從來不居高臨下跟讀者兜圈子。
《賣火柴的小女孩》的講法其實跟《萬卡》的講法幾乎像是同一顆心靈的跳動,它們觸摸到了人類最慈悲的心腸、最悲憫的傷感。
人到中年,讀此類作品,居然還能在神經末梢上如蕩秋千,在閱讀深處,為自己點亮溫情的燈盞,甚至偷偷地掉落幾顆淚花。
這里我要說的是契訶夫的《渴睡》,它就像一根小蠟燭閃爍著屬于自己的光亮,然而,它燃起的生命的光點卻是那么晶瑩透明,牽動你的五臟六腑,讓你去跟著惋惜嘆氣,甚至捶胸頓足。
故事講一個叫瓦麗卡的十三歲的小姑娘給人家當保姆,由于夜里實在太困,結果無意間掐死了主人的孩子。這又是一個中魔的故事。你讀了,你就相信故事里的女孩只能如此,她這么做就是她的宿命。因為中魔的人通常管不住自己,無論身體還是內心。
小說寫得精簡沉郁,通篇散發著契訶夫式的想象力、觀察力和細節之美。
有時候力量是無聲的,不用大驚小怪,也用不著虛張聲勢。契訶夫的寫法跟他的人格緊密相關,用20世紀美國文學批評大家萊昂內爾·特里林的說法,他不動聲色地拒絕“英雄模式”。而他的個性和特質則可以用“謙遜”命名。
以一個孩子的感覺和視角來看待大人的生活和世界,領會里面的殘酷、邪惡、溫情和詩意,在這個表面上看來不起眼的短篇里,呈現出難得的本色和力道。
夜間,搖籃,里面躺著個小娃娃,瓦麗卡哼著歌,哄他睡覺。神像前面點著盞綠色的小長明燈,繩子上晾著小孩的尿布和一條很大的黑色褲子,房間里很悶,有一股白菜湯的氣味、做皮鞋用的皮革味……由背景和氛圍引出人物的動作、性格、矛盾,然后推動著情節往前推進。
但是,且慢,契訶夫在強化瓦麗卡著魔于睡覺的急迫性和無比的渴望時,卻用了大量的類似于主觀鏡頭的心理畫面,這讓他的小說有了跳躍感和張力結構,有點像后來的意識流文學的筆法,簡直太奇妙了。
實際上,作家是在讓兩個時空里發生的事兒交互著并置著重疊展開,一者是粗暴的主人,無論是男的還是女的,呼喝著,申斥著,指令她干這干那——抱孩子、生爐子、燒茶炊、刷雨鞋……另一邊是布滿稀泥的寬闊大道上背著行囊的人和自己的陰影一起倒下去貪婪嗜睡的情態,還有父親生病的場面,死去的凄涼,其間穿插著母親跑前跑后、一連串的奔忙勞碌以及禱告的影像幻覺。契訶夫將兩者都處理成瓦麗卡半睡半醒之際的“腦子里合成的幻影”。不斷交錯疊加的幻影,仿佛兩股勢力糾纏著女孩的神經、意識和下意識,如此將渴睡感推向了她人生崩潰的邊緣。
“睡吧,好好睡”“我來唱個歌”……小女孩瓦麗卡對著搖籃里的娃娃近乎絕望地央求。漸漸地她身心里有一種強大的不可控的中魔的力量在醞釀、發酵,她清楚了那讓她無法入睡的敵人就是搖籃里的小東西。她必須而且只能去做點什么。契訶夫說,“這個錯誤的念頭抓住了瓦麗卡”,引爆了她命運里的導火線。
小說一再寫到長明燈照出來的一大塊綠色斑點。正是在此映射陪襯烘托之下,《渴睡》才如魂靈附體一般展示了一個實在無法再拒絕睡眠的孩子的悲劇歷程。沒有說教,沒有解剖,只是帶著光亮亮的詩意的筆觸牽動著讀者細若游絲的閱讀神經。
“她笑著,擠了擠眼,伸出手指頭向那塊綠色斑點威脅地搖一下。瓦麗卡悄悄地溜到搖籃邊,彎下腰去,湊近那個娃娃。她把他掐死后,趕快往地下一趟,高興得笑起來,因為她可以睡覺了。”
這看似杯水里的風波恰恰印證了契訶夫永遠的藝術風格追求——任何一種懸念,最后的解開,都跟人物最渴望實現的人生目標和心理欲求直接相關。
《好人難尋》:老婦人
奧康納在她孤寂的莊園里喂著幾只孔雀,帶著宿疾,用文字打發著百無聊賴的日子。她是天主教徒,心懷善念,并不時按照禮儀為人類祈禱。但是,她筆下的故事卻是如此邪惡,甚至令人不敢直視。
《好人難尋》是她的王牌小說,各個選本都無法割舍的杰作。我一讀傾心,繼而不寒而栗。為自己同類的愚蠢、邪惡,還有身不由己的盲從,那是惡魔般的天然力量賜予的。神明的救贖總是晚了半截,讓人甚至覺得救贖的不可信。
喜歡將自己筆下的人物打入地獄,這明顯構成了奧康納藝術存在的戲法。由于她入戲太深,并且總是渴望著以自己的故事寓意昭告世人走向宗教信仰的必要性。
有時候作為讀者,我們會徘徊在教義和文學閱讀的邊緣上,選擇哪個才是生命的路標所在。我自己是選擇了小說的魔法,覺得魔法才會讓我跟著文學著魔,而情感和理智也才會隨之翩然起舞。
《好人難尋》不是道德倫理方面的見縫插針的控訴或者提醒,它的內容和形式感造就了小說在精神深度上的詭譎和變異。
老婦人、兒子、兒媳以及他們的三個子女開車上路旅行,卻沒想到半途碰到了“格格不入”(也有人翻譯成“不合時宜”)等三個殺人慣犯,從而展開了富于思辨性的心理和情感上的較量。最終惡占據了上風,全家人罹難,這個滅門案就此告終。
從一開始,那個老婦人就顯得多嘴多舌,興奮得過了頭兒。過于憧憬什么事,好像多半會在失落或者懊喪中告一段落。這是小說習慣運用的模式,也是人生通行的慣常軌跡。
人物一旦著魔,就會失控。理智往往等不到醒悟的時刻,而命運就把他們帶上了歧途或者絕路。
老婦人如果不是個話癆,要么就是出于恐懼感,而下意識在第一時間里說出了“格格不入”的身份,那么,或許故事會是另一種走向。
讓人滑落到無底深淵里的把戲,注定是喜歡玩水的人的自信或者自以為是的心理預期造成的命中率極高的偏差。
奧康納的小說,將老婦人的中魔狀態刻畫得如同幽靈上身,具有無與倫比的在場感。我們讀著其中的每一段每一處,就覺得自己也仿佛進入了跟魔鬼談心的時段時態。
她從遇到“格格不入”那當兒,就格外討好人家。既然命運的籌碼壓在人家一邊,一個束手待斃的人還剩下什么希望呢?也就是盡量拖延死神的光臨吧。于是我們看到老人家開始了中魔般的恭維和取悅對方。可是她除了說“你是個好人”“你一點兒都不兇”之類的顫顫巍巍的昧心話,或者懇求對方禱告、禱告,又能做些什么?
在奧康納的世界里,惡人好像值得同情,好人卻乏善可陳,怎么回事呢?
那個“格格不入”痛說家史不說是聲淚俱下,可也足以撼動人心。反之,老婦人的說教,卻像一篇冗長而乏味的布道,聽了只會讓人反感膩歪。
不好,眼看著奧康納要把我們引向了超越通常人類善惡之分的臨界點,但是,接著毀滅發生了,“格格不入”和他的同伙殘忍地處死了包括孩子在內的無辜人們。這樣原本看似有理的狡辯,一瞬間又失去了值得同情的依托。
奧康納的近乎鬼魅邪惡的故事實在是給我們提供了惡人臉上卻籠罩著天使光環的表象。仿佛一場殘殺是上帝讓他們干的,只為了讓愚昧的人類從此能幡然醒悟走上朝圣之途。老婦人的中魔和中邪,在作者眼里就像個笑話或者笑料。你討好惡,只會惹禍上身,這是弱者價值觀倒錯的喜劇樣板,活靈活現,卻不差分毫。
當然,奧康納的故事具有某種潛在的多義性。怎么解讀,跟閱讀者的身份、氣質和心理準備和預期直接掛鉤。
如果你覺得,老婦人最后時刻在生命攸關的狀態下,低聲說:“哎呀,你是我的兒呢,你是我的親兒!”然后伸出手去摸“格格不入”的肩頭,正是在這一刻,她才真正找到了精神皈依的支點,隨后在殺手的槍擊下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救贖,那就有點《約伯記》里的況味了。神拿約伯的孩子當祭品,約伯承擔了這致命的懲罰,而沒有一點兒怨言和委屈感。老婦人肉身死掉了,靈魂卻超升到另一個世界,難道這就是奧康納想表達的中魔?
《黑暗中的笑聲》:歐比納斯
納博科夫是在果戈理和契訶夫之間博弈,他選擇了前者的譏諷和灰色幽默,發揚了后者的優雅和雍容。他的筆更是毒辣,老謀深算,他的《黑暗中的笑聲》設計了一場令人驚心動魄的欲望,詭計的騙局,讓每個讀到的人都知道自己的腳下有可能是地獄和深淵。
三個人物都是玩火者、中魔人,他們聚在了一起,能沒有好戲看嗎?
歐比納斯是這三個人里的核心,因為他為了欲望而失掉了自知之明,因為他愚蠢,結果成了陰謀家手里掌控的玩物和寵物。
另外兩個人,瑪戈,還有雷克斯,引逗著歐比納斯,上演了一出堪稱精彩的荒誕的悲喜劇。
要說的是,《黑暗中的笑聲》寫成五年后,作家本人有過一次婚外戀,這么說,該小說是作家現實生活的預演。好在納博科夫最終為了他的薇拉,舍掉了情人,又一次回歸人生“正軌”。后來,更出名的《洛麗塔》,出版的扉頁題詞里就寫著“獻給薇拉”。薇拉,是納博科夫夫人。
作家當然深諳人生人性之道,以及種種伎倆。這方便了他們在藝術上創造和發現。
《黑暗中的笑聲》無疑為我們精到傳神地勾勒了欲望的深淵和存在的邊界。有人當年曾以“許多瘋子,更多瞎子”來比喻外國經典作品里的人物形象構成序列的特征。譬如,李爾王是瘋子,俄狄浦斯王是瞎子。
到了這部作品里,雷克斯和瑪戈就是瘋子,歐比納斯則是瞎子。他一開始是在心理上瞎掉,在書的結尾處,則因為一次車禍,成了生理上真正的盲人。納博科夫非凡的諷刺和酸辛的幽默由此可見一斑。
《黑暗中的笑聲》故事緣起于歐比納斯在黑暗的電影院里邂逅穿黑色著裝的引座員瑪戈從而一見鐘情,陷入不能自拔的愛欲淵藪。兩個人邂逅的地方叫“百眼巨人影院”。如果看完全書,你會覺得這名字起得很好玩,歐比納斯遇到瑪戈中魔之后,兩只眼睛全然導入完全休眠的狀態,那跟百眼巨人無所不在的透視力恰恰形成一種調侃和幽默之間呈現出的絕對反差和對照。瑪戈風情萬種、年輕孟浪,卻是情場上的過來人,深諳吸引男人之法之道。再加上后來半途殺入的前男友雷克斯的加盟,兩個癡迷著魔的“瘋子”搞出的惡作劇,與歐比納斯這樣的愚癡型傻瓜兼“瞎子”自然會碰撞出那些令我們目瞪口呆、怦然心跳的劇情。
該小說從藝術風格和結構上看屬于戲仿體,仿效20世紀二三十年代爛熟的電影情節,也就是三角戀故事演繹的命運傳奇。但是在內在骨子里,納博科夫挖苦揭示呈現的還是人之欲的黑暗、詭譎和迷離。當然這里有果戈理式的反諷,男女情感世界的錯位,陰謀和狡詐支配下的道德倫理的失衡狀態,以及鬼氣上身的不由自主的幻滅感。但是在某些近乎透不過氣來的章節段落的間歇,作者也不失時機恰到好處地為我們帶來契訶夫式的悲憫、憂傷和溫情的調子。
一般來說,納博科夫長于諷刺、挖苦、揭底,以老辣惡毒嘲弄為寫作之能事,但是這家伙偶爾心軟下來,亦有純真浪漫幻美的一面。亨伯特之愛洛麗塔,是與童年小女伴的早逝的憂傷相起落消長的。而在《黑暗中的笑聲》里,歐比納斯的女兒伊爾瑪不多的出現,也難得地帶給閱讀者一種人生誠摯值得感恩的錯覺。尤其是寫伊爾瑪患病發燒做夢的情景,“夢見和爸爸一道打冰球。他笑了,跌了個四腳朝天,把大禮帽也摔掉了。她也摔了一跤。冰上冷極了,可她卻爬不起來……”這樣的細節插入到幾乎是幽暗擋住了生命溫情的任何一個角落的字里行間,會讓我們格外懂得即便殘酷冷峻如納博科夫者,還是愿意為人性的善意美好純真留下一塊可資回味咂摸的地盤。
為某個人某種事情著魔、中魔,這是人性永恒的困局。
納博夫在科剖析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的講座里,指出三種因素造就一個人,即遺傳因素、環境因素,還有未知因素X。而后者構成了決定性地將人推入某種命運的基礎。
歐比納斯的困于欲望,也是自身充盈的某種鬼魅一般的魔力將其征服而導致了他無法迷途知返。其實機會是有的,尤其是女兒病故以后,他的茫然惶惑的人生前景本來可以有個急剎車,回到從前的軌道上,去跟妻子伊麗莎白重歸于好。但是,那個不可知的魔,還在他體內翻騰,天使的微笑并未裸露出來,還被死死地壓在塵埃之下。
命運之神抑或死神正在不遠處召喚著歐比納斯前行,不到墓地不死心,不見棺材不落淚,中魔的人都會這樣的。于是我們看到他在意想不到的車禍中瞎了眼睛,而在盲目而近乎殘酷的情感游戲里,他又怎么能夠逃開或者躲過雷克斯和瑪戈兩個眼睛明亮內心卻無比暗淡的壞蛋的要挾、耍弄和謀害呢!小說寫到最后一頁,用了電影特寫鏡頭一般的樣式,“椅子——倒在一個男子的尸體附近,那男子身穿絳紫色衣服,腳下一雙軟拖鞋。看不見手槍——壓在他身下了……”
《黑暗中的笑聲》,我讀過三次,每一回都仿佛落進精神深淵般的陷阱里,然后等著納博科夫把自己撈上來。
【責任編輯】刁長昊
作者簡介:
劉恩波,評論家,供職于遼寧省文化藝術研究院。著有文論隨筆集《為了我們豐盈地生存》《捕捉》,長篇小說《十一月的雨》,詩歌作品集《一地霜月》等。曾獲第七屆遼寧文學獎、第三屆遼寧文藝評論獎、《中國詩人》25周年優秀詩評家獎和《當代作家評論》2018年度優秀論文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