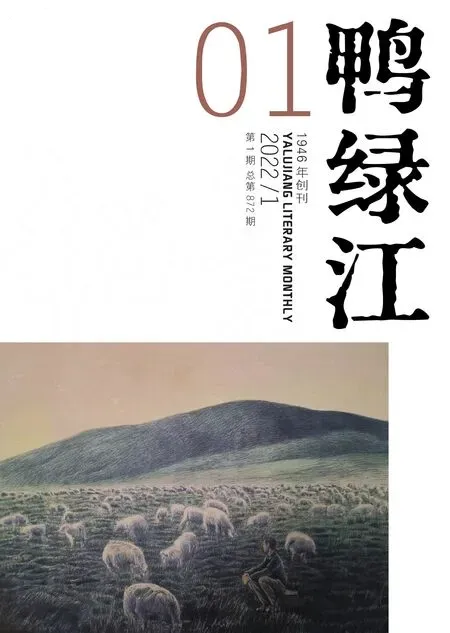歷史情境重建的當下立場
在歷史長河滾滾向前,當代文學逐漸歷史化、經典化的今天,重新審視“革命歷史小說”和“軍旅文學”這樣的文學概念時,應該更多一分歷史的同情與理性的客觀。誠然這些概念的生成裹挾了一些逐漸為時代摒棄的泥沙,但不能否認的是,概念背后是一脈深厚的譜系,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歷史表達方式與美學理念。當我們重返1950年、1980年乃至1990年等文學史產生重要變革的節點,“革命歷史小說”和“軍旅文學”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展示著其強大的影響力。進入21世紀后,許多作家、評論者都在有意重新梳理這一譜系,并以此實現推陳出新,傅汝新的長篇小說新作《一塘蓮》(花城出版社,2021年9月版)同樣顯示了這一領域的實踐與探索精神。
1
表面上看,《一塘蓮》并不回避重大歷史事件,從1945年抗戰結束到1951年鎮反運動,其中的人物無論何種身份,都伴隨著歷史一同成長,隨著歷史的波瀾而動蕩,對現實主義和唯物史觀有深層的依戀甚至依賴。在歷史洪流面前,幾乎沒有人能夠避而遠之,雖然有人是主動投身歷史激流,有人則是被動卷入歷史旋渦。但深入閱讀不難發現,小說對歷史的觀照并不是從后人總結的歷史發展規律入手,而是采取了鎮海寺農村盧氏三姐妹的角度,用一種體驗式的敘述,帶領讀者體驗了20世紀后半葉中國社會的激蕩歷史。全書以四十多萬字的容量,講述了矛盾沖擊密集的六年歷史。作品呈現出了浩蕩之態,閱讀過程十分順暢,這種閱讀體驗與其書寫方式密切相關。
既然是選擇了盧氏三姐妹作為主角,那么主體情節的展開必然是以女性平民的視角為中心。隨之而來一個問題,就是傳統的、純粹軍事書寫的敘事模式幾乎無法適用,畢竟女性即使上了戰場,也很難出現在一線。堅持傳統模式,必然會沖破現實主義預先設定的范圍,但無論是革命歷史小說還是軍旅題材無疑都始終奉現實主義為圭臬。針對這一點,也有作家提出過革新的想法,不過終未形成定論。《一塘蓮》對既定模式有突破,但不是顛覆,就集中體現在維持了現實主義創作精神方面。
全書一共五十二節,涉及的場景很多,有戰斗前線及“準前線”、作為戰場組成部分的“后方”、只同“生產”和“生活”相關聯的農村以及處在中間地帶的鄉鎮,當然這些場景的功能性也并非變動不居,而處在一種緩慢流動的狀態。其中屬于純粹戰場環境的大約不到全書五分之一,大量篇幅屬于另一種典型意義層面的“地方書寫”。這樣同主人公身份的設定完美貼合,同時也在順從現實主義規則的前提下呈現了另一種革命軍事題材的樣貌,既是一種總結,也是一種預期。這是因為,作為革命歷史小說的軍旅題材,究其發端,軍事報道的色彩較為明顯,書寫者多是戰場親歷者,因此戰斗場面和軍隊訓練及生活占比更多。在英雄視角之外的平民視角也基本是男性視角,比如一名農家子弟扛槍戰斗的經歷,比較少出現一種外置視角,其中蘊含一個革命歷史話語方式的預設,即每個人都不可避免,也應當參與到革命洪流中,參與歷史進程從而改變包括自身在內的社會現狀。關于女性的革命體驗則相應地出現了空缺,便產生了歷史敘述的分歧。
作為20世紀后半葉中國革命中的普通鄉村女性,盧氏三姐妹因其普通和普遍而獲得了典型性。同時也因為她們的生命并不能被革命戰爭完全概括,革命敘事便出現了一個缺口,這個缺口如同篆刻藝術中人為設置的缺口一樣,令革命敘述顯現出了留白之美。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敘事看似在說明革命歷史不是全部和必然,卻恰恰更能體現出證實而非證偽的意蘊,因為即使如盧氏三姐妹這樣并未直接投入一線戰斗的女性,也并非傳統敘事模式中作為“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功能性作用的女性角色,似乎與革命歷史、革命戰爭毫不相關。盧四自賣他的花生米,三姐妹自卷她們的煙,完全可以與世無爭地過著穩定的生活,但卻確確實實地與之發生了或被動或主動的關聯。事實上,我們在理解中國20世紀發生的左翼革命時,也不能對各個元素分解開逐個看待。如同那個廣為傳播的關于淮海戰役勝利的著名論斷,其實說的并非戰役本身,從越來越多發布的資料和研究來看,戰場上的精準指揮、隱蔽戰線的情報搜集包括戰場上的勇武果敢堅定,對戰局的作用更重要,但那句論斷的意義在于道明了革命敘述的基本邏輯,即整體性思維的廣泛運用。大生產、邊區民主、動員機制、組織學習等等這些看似并非戰爭組成部分的元素,其實恰恰是革命戰爭的重要機制。一部多數內容在進行“周邊講述”的小說,看似是軍事題材的非典型敘述,其實恰恰切中了革命戰爭的肯綮。一如小說所呈現的,我們看到的革命戰爭,只是龐大冰山的一角,支撐它的乃是充滿生命力的民間大地與普通民眾。不但如此,三姐妹從鄉村走向城鎮乃至城市的過程,也論證了現代國家生成過程中的城市化進程的歷史必然性。由于這是一部關于革命歷史和戰爭的小說,城市化進程同時與革命歷史、革命戰爭建立起了關聯,它通過藝術化的形式告訴讀者,宏觀上的現代國家建立、中觀上的城市化進程和微觀上的個體生命體驗與革命戰爭有著千絲萬縷、互相聯動的復雜關系,這對我們全面認識近現代史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另外,《一塘蓮》作為一種預期,作為一種召喚,正是基于對文學史傳統的總結歸納。全書最為直接的緊張激烈恐怕是第四十三節“劫獄”,說這是一次準軍事行動,因為我方幾乎沒有正規部隊介入,但戰場描寫得錯落有致,又給人充分的軍事題材作品的滿足感。可以說《一塘蓮》蘊藏著兩種軍旅文學的發展方向,即基于一種整體性的歷史脈絡的書寫,當然這種書寫也包含著英雄史觀和平民史觀兩種傾向立場,以及更為純粹的軍事文學,同樣并不排斥“爽文”的寫作。這部小說是將這些各有重點地結合起來,這也是令其在一眾同類作品中頗顯新穎的奧妙所在。
2
從全書的總體結構來看,情節基本圍繞盧氏三姐妹展開,伴之以適當的插話和回溯,讓四十余萬字的篇幅并不顯出冗余拖沓。同時因為情節動力源是三姐妹而非一個人,又令情節線索并不呆板,有了跳躍的靈動。情節線之間的轉換也恰到好處,所有這些配置讓小說顯得節奏錯落有致。在這種節奏下安排四十余萬字的豐富內容,既能保證信息的充分供給,設置的懸念最后一一“填坑”,又體諒了讀者的閱讀體驗。關于“快節奏生活下長篇沒人看”的言論,無論向市場妥協還是食古不化、頑冥不靈,都不是一種可取的姿態。《一塘蓮》中的歷史觀、價值觀乃至民間傳統思維都通過藝術化符號傳遞,沒有說教,加上故事本身的友好度,都使其真正做到了守正同時創新,而不僅僅是喊一聲口號那么簡單。
作者有意識地將三姐妹向典型人物的方向靠攏,而沒有處理成別的樣貌。三人有女性天然的一些特征,比如感性、善良、重情感、對家依戀、向往英雄等,對政治及革命戰爭的傾向也不是從理念出發,而是出于基本的下層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過由于年齡和經歷的不同,還是呈現了性格上的微妙差異。老大盧芳更為沉穩、隱忍、顧全大局,也正因此她的情感經歷是先結婚再有情感,并且其婚姻完全是因為方七爺對父親和三妹慷慨大義相助而促成的。老二盧秋雖然也是情感較為內斂,也不喜言談,但是內心活動很多,有自己的主意,一旦堅定起來誰都難以勸服,性格原因加上鄭重的神秘消失,導致最初的萌動沒有實現,后來因為知道田鎮長酒后失態,克制住了自己對后者的情感,轉而嫁給在病困時期照顧自己的老實人車站老張。細思之下盧秋內在的韌性是令人驚嘆的,尤其是這種韌性來自她內在的獨立人格。當然三姐妹在這一點有相似性,即使是最為隱忍的大姐盧芳,也能在完全不熟悉方七爺內在的情況下下定決心出嫁,在方宅沒有變故的前提下毅然出走尋找蘇西坡,走進新社會后回到方七爺身邊并堅守到后者過世。而盧秋則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更能展示出體內蘊含的能量。盧云更是敢愛敢恨,喜歡卻因沖動回絕高團長,為了營救高團長又多次出讓自己的身體,后被高團長安排嫁給小蔡,又主動掙脫不合適的婚姻,與仰慕的英雄田鎮長一起生活。田鎮長犧牲后,她終于和高團長一起消除心結而結合。雖然各自都有曲折經歷,這與時代翻覆下個體隨之震蕩相關,但表面上來看,盧云確實更為波折,相應地也更顯出她鮮活的個性。三姐妹不同的性格和人生經歷,已經具有了很大的覆蓋面,更豐富地展現出普通民眾特別是女性在革命史中的反應與體驗。
三姐妹身邊的男人們也是各具魅力、各有特色。方七爺是個傳統社會里的角色,黑白兩道通吃,行走江湖靠的是仗義疏財、一諾千金,當然也有賭博這樣的不良嗜好,以及娶三房這樣的舊社會常見落后習俗。可以說,方七爺和老樹皮是管窺左翼革命之外領域的一個途徑,通過這樣的人物設定,20世紀40年代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得以呈現。不過方七爺與老樹皮還不同,作為鄉紳,前者有著比后者更深邃的洞察力和更全面的知識結構,有自己明確的目的性和方向性,不是僅僅為了生存。作者對這個人物的處理頗有意味,既寫了他強悍的一面,又沒有忽略其仁慈的一面。對待家庭內部的情感糾葛和恩怨矛盾,沒有顯示出傳統家族掌權者的暴戾乖張殘暴,而是給予充分自由,在他費盡心力最終也沒有子嗣這件事上,也沒有過多表現他的衰敗頹唐,這些同其“混社會”時的瀟灑果決一起豐滿了人物形象。比較《罌粟之家》里的家族內斗,無關優劣,體現出的是作家不同的秉性和時代對藝術品定型的不同影響,畢竟歷史細節實在過于繁復,能看到同一書寫對象的不同處理,是讀者之幸。
如果要在全書人物中找一個情節思路的人格化表征,那無疑是田鎮長,他無疑是全書最具有包容性也最難以評價的一個形象。盧秋喜愛他,盧云崇拜他,田鎮長作為基層行政干部,在體察民情、穩定社會、發展地方經濟特別是支援前線方面幾乎無可挑剔,不但對整體大局和本地定位了然于心,而且有熱情、有想法且有執行力。同時作為轉業軍人,他一直向往重回部隊,無論是組建當地民兵武裝,還是策劃并與方七爺共同領導對高團長的劫獄救援,都體現出軍人履歷賦予其的出色的戰斗素養,特別是后來率領公安局隸屬武裝大隊保衛地方社會穩定、保障工業發展所立功勞,都突出展現了個人的全面才干。但這樣一個堪稱完美的人卻發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嚴重失誤,酒后失態將于主任錯認為盧秋而將之占有,令其懷孕。《亮劍》之后至今熱度不減的“李云龍熱”,作為現象有兩個層次,首先是受眾接受層面的追捧和同人再創作,其次是創作層面的大量模仿,一批出言不遜、渾身小毛病卻英勇作戰且戰績喜人的形象紛至沓來。《一塘蓮》恰好形成某種反撥,田鎮長溫和儒雅、幾無缺點、技能全面卻偶然犯錯,并且是無法忽視、影響了許多人命運的非原則性、非政治性錯誤。與對方七爺的處理方式類似,作者沒有任何對田鎮長的道德批判或情緒化書寫,他后來的命運也是一言難盡:雖然同于主任關系略微僵硬,但很喜歡孩子;雖然同盧秋未能結合,但收獲了盧云從崇拜轉換來的愛意;雖然一家三口短暫歡愉,但終因鎮壓土匪不幸殞命。作品呈現出來的不是說教,沒有勸誡,更遑論開脫或批判,而是呈現了生活本身的糾結狀態,無所謂好,也無所謂不好,只是讓看到的人留下一聲沉重又不失釋然的喟嘆,或許這正是歷史書寫的精妙所在了。
相比之下,高團長就是一個更為純粹、簡單的人了,懷揣理想,充滿熱血與正義感,這種軍人形象我們在傳統的革命歷史題材中十分常見,如此設計能夠安撫習慣于既有軍旅題材的讀者,符合一般性的閱讀經驗。常年身處軍隊的人,或許就是比地方工作的人更為單純,他們接收到的信息大多是理想主義的教育和上級下達的命令,不像后者需要處理許多紛繁復雜的人事、銜接新舊不同的社會。可以說,高團長是沒有轉業的田鎮長,田鎮長是走出部隊的高團長,這也就能理解為什么盧云開始崇拜高團長,后來對田鎮長也有了類似的情感。總之,《一塘蓮》對人物的塑造都是十分用心的,這些人物在動態上服從于整個情節發展和整體思想傳達,在靜態上又從不同側面折射出社會的截面與變遷。
3
在一些細節方面,這部小說也呈現出了不少新意。已經形成定論的革命歷史題材的軍旅文學模式,基本是歷史必然論貫穿到底,人物的言行都有很強的指向性,或者是經過帶領達到這種狀態,配合英雄形象的塑造,體現出陽剛的崇高之美。《一塘蓮》從整體上來說,延續了這種預設,雖然沒有刻意突顯,但還是能感受到。不過它的美學體系并不單一,畢竟采取了軟性的盧氏三姐妹的民間視角。田鎮長改任武裝大隊長積極平定匪亂,但在最后一次戰斗中因為交換人質,誤判土匪示威性地開槍會打到女兒,飛身撲去,不想女兒沒事,自己卻因為前撲而中彈。因為是個人誤判,雖然奮不顧身也并不顯得多么英勇,犧牲也就并未顯出特別的悲壯。這讓歷史講述在宏大敘事的基礎上增加了新的方式,同時也讓講述本身更加引人回味和深思。
如果說田鎮長的崇高形象細節的削弱處理,由于其本人存在瑕疵而導致弱化本身具有一個“針對弱化的弱化”,畢竟即使沒有這一筆,他也因為醉酒行為不能被稱為一個完人。高團長的形象雖然沒有這么多層次,但基本比田鎮長更為正面一些,特別是雙塔鎮大捷出奇制勝、指揮若定,得到了首長的贊賞。不過在一次營救行為中,交火負傷,有趣的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交戰雙方不是敵我,而是營救者和被營救者,同時還連帶傷及高團長的隱私部位。誠然最終雙方互相一笑化解誤會與尷尬,但事情本身仍顯得頗為滑稽,事件受到了降格處理。后來高團長拒絕盧云的示好,甚至強令其同小蔡成婚,很難不懷疑是心理創傷的表現。一些作家曾經討論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問題,《一塘蓮》倒是很包容,兩種歷史觀都能接納,宏觀上仍是必然性,但細節處加入的偶然性因素讓人物和歷史更加真實可觸,反過來穩固了必然性的宏觀敘述。
這種多元化的歷史觀也體現在方七爺身上。1951年的鎮反運動使方七爺卷入其中,他被盤山公安局定罪為“反革命分子”,半年后死于獄中。其間盧芳奔走相助,希望幫助方七爺澄清歷史,也得到了高團長的聲援,但無濟于事。由于此前大量篇幅寫到方七爺的開明進步、同情革命,甚至多次參與營救革命軍人,因此對最終判決的評判很自然地寫在了每一個讀者的心中。不過作者在此用超然到不落痕跡的敘述語言描述這些過程,同時有意識地并立兩種話語模式,人為制造一種“話語裂隙”。通過重寫文學史之后又一波“十七年文學”研究熱,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在不同材料中發現過當時主流小說存在的話語裂隙現象。如果說當時的話語裂隙屬于某種“政治無意識”,那么《一塘蓮》這樣有意為之就頗有意味了。通讀全書不難發現,作者始終不急于親自現身對人事進行臧否判斷,而是盡可能還原歷史,留下一副“公道自在人心”的架勢。這里也是如此,巧妙運用話語裂隙,意在表明歷史并非能以三言兩語的對錯論之,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盡量呈現歷史的豐富復雜性,還原每個人所有言行及境遇的歷史語境,方能更好地貼近歷史以及歷史中的個人。作者有強烈的對歷史的同情,既包括對個體的理解,也蘊含著對時代的理解,這便是小說呈現出來的豐富性。
不得不說,雖然這是一部主要書寫革命戰爭及其附帶的社會改造的小說,但其對作為改造對象的傳統社會有著精彩的描摹。一方面,比如寫到方七爺為了繁衍子嗣變得瘦骨嶙峋,與其穿衣在外的神奇截然相反,寫盡了“身體”和“身份”的沖突,也就是自然性和社會性的沖突,隱喻著傳統社會的內在凋敝。另一方面,作者也表達了對大宅院內受到文化禁錮的女性的深切同情,并描述她(們)由內而生的自主意識的覺醒,這也正是左翼革命動員機制的人性基礎。對革命對象不是批判而是理解,充溢著人文關懷,也傳達了思想立場,這都得益于作品的革新與包容性。
《一塘蓮》還積極引導對革命歷史的軍旅題材這樣的文學史概念的深入思考,在作者看來,雖然這個概念已經實現了歷史化,但并非沒有進一步挖掘內涵的可能。雖然小說直接的戰斗描寫不多,但是與軍事活動、軍旅生活相關的敘事卻無處不在。由于戰爭年代軍隊的戰略目標和戰斗任務使其經常處在不同距離的輪崗或流動中,加上對游擊戰的熟練運用,更不會教條主義地局限于一地,很自然地見多識廣。軍隊內部有一套屬于自己的話語,確切地說是軍事語言與政治語言的混合態表達方式,久而久之會令身居其中的人習以為常并加入其中,這一點至關重要,不僅僅是語言問題。田鎮長在婦女干部培訓班開班儀式上講到東北的政治態勢及軍事部署,在座的年輕女性無動于衷、不明就里,展示的是一種前現代狀態,世界與“我”無關,或者世界于“我”而言“并不存在”。初到部隊的盧云最早接觸的是小王,她“自由自在地游來游去”,這種已然脫離鄉土、去除了土地依附性的獨立人格,以及侃侃而談、縱橫捭闔的言辭,都讓盧云贊嘆不已。由于軍隊的特殊屬性,對偏居一隅的平民而言,前者其實是一扇世界的窗口,軍事和政治話語傳達著諸多關于“世界”的知識,并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傳播其世界觀,打破原有的地方性的意識和認知,讓參與的人了解歷史發展的前因后果,以及個體和歷史的關聯。
在總體的人物關系設定上,方七爺、田鎮長、高團長這些深刻影響、徹底改變了鎮海寺甚至遼南地區的關鍵人物,通過三姐妹變成了“一家人”,田鎮長親口道出“主要原因是盧氏三姐妹,是她們把我們聚攏到了一起”,完成了點題,“國族革命”敘事就被置換成了“家族革命”。三姐妹看似沒有做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通過這樣的命運連接、話語置換,也促成了一件件大事發生,這正是革命敘述的題中之義。如果看到軍隊的話語系統塑造能力,通過語言改造個體,甚至直接說具有啟蒙意義,那么在某種意義上“軍隊”和“文學”就是同構的。
作者著力塑造的田鎮長可謂軍隊知識分子,同樣,蘇西坡這一人物的設置也至關重要,其當為革命知識分子陣營。田鎮長作為軍人不遺余力地對鄉土進行現代性的啟蒙,對應的正是蘇西坡作為知識分子的啟蒙。以往我們大多關注知識分子的啟蒙,忽視了軍隊同樣發揮了這一歷史職能。盧芳對蘇西坡的好感,與盧秋對田鎮長的喜愛、盧云對高團長的崇拜,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在于后者能給予前者一種前所未有的提升與引導。作者通過耐心的敘述,其實比較了軍隊啟蒙和知識者啟蒙兩種方式的差異。知識者啟蒙是我們更為熟悉的,他們對知識的把握更深入、更成系統,對個體的教育更全面、影響更深遠。相比之下,軍隊啟蒙盡管不那么知識化、系統化,但恰恰因為這種“不精深”以及話語的模塊化而更容易得到普及,由此便能快速大量復制,這一點則是學院派的學者不能企及的。現代史進程,不可缺少現代革命的參與;知識者啟蒙的同時,也需要軍隊啟蒙的加入。
曾經在文學史上大放異彩的革命歷史小說,在經典化后不可避免地陷入模式化的困局,因此在叢書總序中兩位研究者在梳理經驗基礎上積極探索新的發展空間。其中提到的諸如“對歷史祛魅”、重建“個人化想象”以及“現代性”角度的反思與重構,確實是這一領域發展節點的幾個關鍵詞。《一塘蓮》的出現表明,已經有人在這條路上開始奮力實踐,在反復嘗試用不同的方式構造歷史語境的同時,融入了鮮明的當下立場,或許這正意味著某種轉機。
【責任編輯】陳昌平
作者簡介:
艾翔,青年批評家,1985年12月生于新疆烏魯木齊,先后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文學博士,天津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中國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