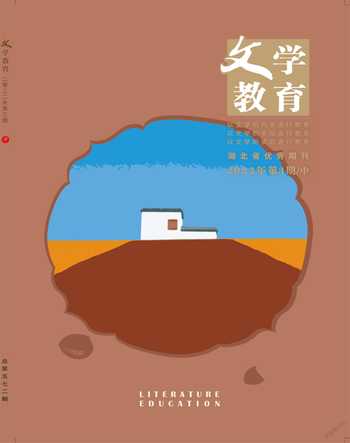李商隱詩的個性特征及其成因
豐曉流 王宏瑋
內容摘要:李商隱的詩歌由于意象迷離、廣納比興、典故縱橫等而導致了極具審美意義的“亂辭無緒”之現象,其成因不出人生際遇、審美個性及時代折射等。
關鍵詞:李商隱 詩歌 人生際遇 時代 審美 折射
王國維在談及南宋詞人姜夔的詞作時,曾經不無遺憾地說:“雖格調高絕,然如霧里看花,終隔一層。”[1]其實“霧里看花”未嘗不美,真正巧妙的“隔”不是壞事,正如蘇格拉底所說的“郝庫利斯石”,它“不僅能吸引鐵環本身,而且把吸引力傳給那些鐵環,使它們也象磁石那樣,能吸引其它鐵環。”[2]如此環環相吸,自然能引起讀者浮想聯翩和敏銳感應,“隔”從何來?可見,只要朦朧得法,也可以成為好詩。李商隱的詩即是如此。
表面看來,李詩“瞻萬物而思紛”[3],擅長將富于變幻的意象錯錯落落地組織成“百寶流蘇”[4]:或步步紆回,或層層重迭,或來之無端,或去之無跡,蝶夢迷離,鵑聲悲切,孤鴻欲問,蓬山萬重……亦或處處設典,句句比興,問楊柳“如何肯到清秋日”,嘆鶯啼“有淚為濕最高花”。如此等等,其幻象之凄迷,變化之多端,亂辭之無緒,實乃如秦觀之詞“霧失樓臺,月迷津渡”,令人難以捉摸,在感知中遭遇“隔膜”。然透過依稀影象的樓臺津渡,卻可以使得人們更敏銳地想象到記憶中印象最真切、興趣最濃郁的樓臺和渡口。鑒賞者可以把真感情滲透到“霧”和“月”中,展開幻想,創造出為自己所眷念、神往的樓臺、渡口,從而“花須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二月二日初》)。正如清代詩論大家葉燮所說:“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維,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為至也。”[5]李商隱之詩即是如此,詩人憑借其極具幻象的“亂辭無緒”,在黃昏凄艷的晚唐王朝中雕塑出了自己獨特的“綠暗紅稀”之美。那么這種極具審美意義的“亂辭無緒”緣何而生,是詩人“有心插花”還是“無意為柳”,筆者試圖作出以下之分析。
一.根源于詩人生平的悲劇遭遇
《錦瑟》一詩,古來聚訟紛紜,有人說是愛情詩、詠懷詩,也有人說是詠物詩、游仙詩,更有甚者,說是愛情、詠物、、詠懷、游仙兼而有之。試想,古代傳說中的蝴蝶已經撲朔迷離,卻又偏偏出入于詩人的凌晨殘夢之中;一個古代帝王的失國,恰恰是托為暮春杜宇的悲啼;蒼茫大海之上,明月照著珠光和淚影;深埋著藍田玉的泥土中,又冉冉升騰起無從掩抑的光彩,如此等等。這里的韻味、狀貌、神采不僅相得益彰,竭盡變化,而且又深深地應和著詩人心靈的節奏起伏,一個凄怨、美麗、富于詩意的古樂器承載了如此多的“絮果蘭因”、神話傳說與悲歡離合,難怪后人仰其項背而仍不得其要旨。筆者認為,詩人“中路因循”和“才命兩妨”(《有感》詩:中路因循我所長,古來才命兩相妨)是此類詩歌“破繭而出”的主要原因。
處于牛李黨爭夾縫中的李商隱,終其一生四十幾年,幾乎可以說與兩派爭斗相始終。再加上甘露事變后宦官勢力愈益猖狂,朝官互為傾軋,有增無減。在一場大屠殺和翻云覆雨的政治漩渦中,盧仝慘死了,白居易變得膽小怕事,李德裕遠竄到紅棉花開、鷓鴣飛舞的南荒了……黑白不分,直言遭禍。詩人早年寫《有感二首》和《重有感》時那種少年氣盛、無所顧忌的氣概,不能不隨著世故的增長和“腐鼠”勢力對自己折磨的增加,多少有所收斂,至少是他不能不重新選擇一條寄托遙深的道路了。于是,“直面慘淡的人生”和回避現實的矛盾,兩者之間,不能不要求他抉擇。盡管在他心中,王屋山上的“白道青松”還分明留下記憶,可是自己畢竟是“愛君憂國”的,所以有“我欲乘風歸去”的苦衷。這是他在《偶成轉韻》中曾經自我表白的,也可以說是他畢生的艱難心事。就在這樣的矛盾心情中,他一方面固然要用清新的目光去批判現實,但卻又不得不和晚唐的某些詩人一樣,用他們精心構成的藝術羽紗編造出一個美妙的精神避難所和藝術的七寶樓臺,作為苦悶象征和心靈浸潤,也作為理想的寄托。李商隱在政治上遭受到一連串的排擠、打擊,被卷入黨爭的漩渦深處,不都是和締婚王氏有關么?他的“華年”之憶,不正是既寓家國之傷、也抒身世之憤么?不幸的婚姻和坎坷的仕途原來如此緊密。清人趙執信曾推崇吳喬的“詩之中須有人在”的話并加以發揮:“夫必使后世因其詩以知其人,而兼可以論其世。[6]”斯言極是也。
二.固化于詩人的性格、氣質。
李商隱十歲喪父,在就學時代便挑起撫養家庭的重擔。生活煎熬和人情冷暖把一個孤貧無依的孩子培養得多愁善感,世故人情更是早熟,使得他更需要家族親人的溫暖。特別是有一件事值得我們注意,當他母親去世丁憂后一段時期中,他先后為親人營謀葬事達五起之多,連一個小侄女寄寄的死,都為她寫下了一往情深的祭文。這就更可以看出詩人在那個世情淡薄的社會中,特別需要得到“宗緒衰微”的家族的慰藉。他對于這些鐫印著辛酸、惆悵的少年往事,一方面誠然感到凄涼,但另一方面卻又偏要深深地沉浸其中,經過精細入微的體驗,鑄造出一些既與嚴峻現實有間隔而又隱約地透露出對當前自我心影沉潛觀照的朦朧意境。
縱觀李商隱時代,正是中唐詩歌向晚唐詩歌過渡的時代。時代的苦悶導致了這一時期的詩人們在詩歌創作中傾心于內心體驗和藝術技巧的錘煉,斯時,“為時而著”的新樂府高潮早已趨于沉寂,連“魯殿靈光”的白居易都心安理得地在洛陽府邸“安營扎寨”,唱出“知足樂天”的閑適與恬淡。年輕一輩的杜牧、李商隱、溫庭筠們雖“書生意氣”但又有何良方“揮斥方遒”?雖然也共通于“感時花賤淚,恨別鳥驚心”的傷痕,但三人折射時代、社會,共鳴人生的方式卻大相徑庭——杜牧把“作賦論兵”和“聽歌縱酒”集于一身,懷著跌蕩坦率的豪情唱出“十里春風”的“揚州綺夢”;溫庭筠則選擇了“歌臺舞榭”或“荒村茅店”通曉音律地吟誦,留給時人亦或后人“風塵仆仆”的身影與“頹唐”的情調;而李商隱卻是那么執著而惆悵地留戀著“樂游原上的夕陽”,綿邈而深沉的彈奏著那象征著華年如水的“錦瑟”。顯然,這是三人創作道路和感情氣質并不相同使然,三種不同的個性特征使相同的“時代光感”產生了三種迥然不同的折射,亦或可以說三種不同的個人氣質選擇了不同的時代“線條”、“意象”、“色彩”淺斟低唱。清初錢謙益如是說:“義山當南北水火,中外箝結,若喑而欲言也,若魘而求語也,不得不紆曲其指,誕慢其辭……此亦風人之遐思,《小雅》之寄位也”[7]。此乃正是對李商隱個性特征在其詩歌創作中的“委婉”、“曲折”之投影。
三.“成像”于晚唐時代的“群體感傷”
1.“成像”的“背景”條件
德國美學家里普斯總結過“堵塞性”產生的悲劇性法則——災難加強了價值感。晚唐的詩人們大都醉心于唐王朝開元、天寶前的光榮史,希望它永遠“蕩蕩乾坤大,瞳瞳日月明”(杜牧《感懷詩》),然越是醉心于唐王朝昔日的輝煌,人們的向往便越是受到遏制、障礙、隔斷,從而形成理想與現實的堵塞。正是這種堵塞,又自然不自然引發人們對“堵塞”前的懷念,而隨著堵塞的加深,懷念的痛苦更為加深。隱居在山西老家的司空圖給自己莊園的亭子題名為“休休”,這二字背后的“懷念”冷嗖嗖直逼人眼,甚至連貴為節度使的風雅詩人高駢都直言不諱地供認“將軍醉罷無余事,亂把花枝折贈人”(《廣陵宴次戲贈幕賓》)。
由此可見,越是土崩瓦解,越是歌管紛紛。對如夢如煙的開元、天寶元年盛事的回溯,幾乎成為晚唐詩歌的普遍題材。這應該可以說就是詩人“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缺陷與悵惘所產生的背景(《樂游原》)了,只不過李商隱所目擊的“夕陽”已經不比李白登宣州謝朓樓時的“江城如畫里,山晚望晴空”,也不比李賀的“白景歸西山,碧華上迢迢”了。即使同詩人自己的《行次西郊》相比也不再有“此地忌黃昏”的滿腔憤慨。顯而易見,除詩人內心深處不可排遣的凄惋外,此“夕陽”還飽含了李商隱對唐王朝盛世的緬想,恰恰是一位晚唐初期文人的緬想。雖說夕陽西斜,但畢竟還沒有到司空圖用“休休”一詞作為他園亭題名的時代。天際斜陽,終于留下了幾分“可憐的鮮艷”色彩。鮮艷,驅使他們醉心于鏤金錯彩;可憐,說明那些金彩透露了黃昏晚照。“狂來筆力如牛弩”(《偶然轉韻》),這是詩人長期沉浸在綿邈意境中陡然爆發的驚呼,然而這驚呼卻轉眼為嚴酷現實所壓垮。詩人有時簡直是消沉得不想歌唱了,因為他感到“徒勞恨費聲”歌唱只是白費。
顯然,這不是李商隱一個人的思想狀態,它是文人在夕陽猶好而終近黃昏時分的普遍苦悶,也是在夕陽的回光返照中對虛弱美、病態美的追求。
2.“成像”的“光感”條件
如果僅僅只有晚唐時期的“群體感傷”,或者這一時期的詩人群體僅僅只限于感傷而沒有形成“停車坐愛楓林晚”的時代氛圍,那么也不可能孤立地產生李商隱詩歌極具審美意義的“錯辭無緒”;如果沒有晚唐整個詩壇在詩歌創作、詩歌評價上的系列艱苦探索并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也不可能有李商隱綿邈朦朧的“標新立異二月花”。對詩歌藝術規律探索的熱衷,促使當時一些詩人耽于苦吟。賈島的“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寄柳舍人宗元》),李頻的“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轉引《北夢瑣言》),李賀的“嘔出心始已”,杜牧的“苦心為詩,惟求高絕”(《獻詩啟》),都可以說明把詩歌當做生命或刻意寫詩,已經成為當時的風氣。
唐人的詩歌理論原來是沿著兩條道路發展的:一條是從陳子昂、白居易到皮日休的道路,側重于詩歌的現實內容與社會意義;另一條則是從皎然到司空圖的道路,對詩歌的藝術性進行苦心探討,并結合佛家的“境界”學說,提出了意境的理論。苦吟風氣無疑是和側重藝術一派相通的。皎然曾經對“不要苦思”說進行過反駁,認為“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至于那種“有似等閑,不思而得”的作品,只是另一種“高手”的事。由此可見,取境的生面別開和富于錘煉,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晚唐詩歌藝術有走進象牙塔的某些傾向,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作為中國美學傳統之一的意境理論,促使中晚唐詩歌創作積累了一些比較自學的實踐經驗。否則,晚唐末期司空圖的《詩品》要概括二十四種意境和風格,是不可能的。
李商隱顯然是屬于側重藝術的一派。但從他的詩歌看來,卻又絕對不同于苦吟者的推敲。他之所以可貴,是把體驗自己情感和外在事物的精切,同“韻外之致”結合起來,把刻鏤深細的形貌和意在言外的韻味結合起來。刻鏤深細反映了晚唐詩歌藝術的精致,但刻貌取神卻更遠溯于殷璠所倡導的“比興”之說,有異于“輕艷”之詞。難怪李的愛情詩突出精神美,而很少象一些香奩體的庸俗瑣屑的描頭繪足了。由于李走的是“興象”一路并和“意境”攜手,這就很自然地形成綿邈和精細相結合的特征。用司空圖的話來說,是“近而不浮,遠而不盡”。巴山夜雨,漲滿秋池,這不是眼前歷歷可見的景物么?然而輕輕一轉,同一巴山夜雨,卻又經過時間推移,成為陳跡,成為來日緬想中閑話的內容。當然,這還只是一種假想,一種盼望,通過“適當”的搖曳生姿而體現了空靈的境界。
這是李商隱淵源屈原和經過長期流鶯“巧囀”的辛勤探索而形成的藝術特征,但也反映了中唐詩人圍繞詩境說而探討的藝術理論在晚唐初期的寶貴實踐。
3.“成像”的“聚焦”條件
倘若只有晚唐時期的“群體感傷”與晚唐詩人的“群體探索”,而沒有晚唐時期城市經濟的相當繁榮,沒有這種相當繁榮的城市經濟所帶來的旖旎風光,那么也就不會涌現晚唐進士階層“裘馬輕狂”的“詩歌原型”;也就不會產生奢靡、精致、光怪陸離的“詩歌意象”。自然,李商隱“離奇的幻想、大膽的比興、凄迷的編織”等也便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現摘錄張籍之弟張肖遠的《觀燈》一詩作為此種繁華之極的見證:
十萬人家火燭光,門門處處見紅光。歌鐘喧夜更漏暗,羅綺滿街塵土香。
星宿別從天畔出,蓮花不尚水中芳。寶釵驟馬多遺落,依舊明朝在路旁。
京都長安的早春又是怎樣的呢?——想得芳園十余日,萬家身在畫屏中。[8]
東都洛陽又是:九陌鼓初動,萬車輪已行。[9]
第一商業都市揚州的繁華隨手拈來,便有張祜的詩:
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
還有王建的名作:
夜市千燈照碧云,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
以上羅列,均為中唐以后社會繁華的“藝術紀錄”,它顯然不同于過去以金粉馳名的南朝綺羅的留影,那時,南朝的繁華還缺少中晚唐夯實于城市經濟基礎之上的通都大邑的絢爛色彩,因而“鮑照、沈約”們的審美感受也就不可能象中晚唐詩人那樣豐富,他們不可能渲染出一個城市、一個時代的整幅畫面,從而形成更高級的人化了的自然[10]。
晚唐詩人卻做到了。李商隱正是在這樣一個“日下繁香不自持”(《曲池》)的特定時代,孕育了他的“已聞佩響知腰細,更辨弦聲覺指纖”(《楚宮》)的敏銳、細致的藝術感受的。李商隱顯然將這種時代折光拌和著自己的創作個性,從而編織出串串重重疊疊、大大小小的“珠鏈兒”。
綜上所述,李商隱詩所呈現出的極具審美意義的“亂辭之無緒”,實乃詩人人生際遇、審美個性、時代風情所自然折射,鑒賞者若能知其人,論其世,析其時,那么就會練就自己文學鑒賞中的“已聞佩響知腰細,更辨弦聲覺指纖”的審美敏感度,從而達到文學鑒賞中的最佳境界。
參考文獻
[1]王國維.人間詞話[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9.
[2]柏拉圖.文藝對話集[M].北京:群眾出版社,1990,7.
[3]陸機.文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
[4]敖陶孫.詩評[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7.
[5]葉燮.原詩內篇[M].濟南:齊魯書社,2001,5.
[6]趙執信.談藝錄[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9.
[7]錢謙益.注李義山詩集序卷十五[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9.
[8]施肩吾.長安早春[J].全唐書卷五一七.
[9]于武陵.過洛陽城[J].全唐書卷五九五.
[10]吳調公.論李商隱的創作個性及其時代折光[J].文學遺產,2009,(1).
(作者單位:襄陽職業技術學院;湖北省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