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讀者感知覺系統的魔術師
趙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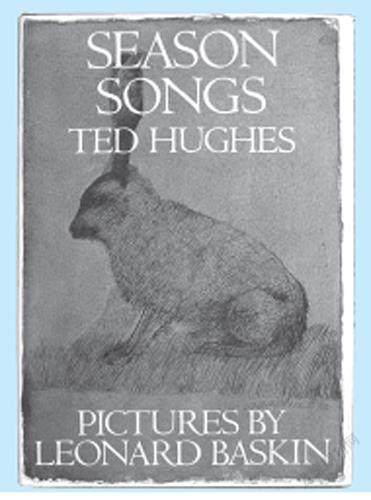
輕輕一聲轟響,它們將你卷入
其精神失常,匯聚起一個逃出生天的摩天輪
噩夢—尼亞加拉瀑布
扇動著上舉的轟鳴雙翼—復歸坍塌
地球上的多數宜居環境中,都有鮮明的四季輪轉。古人觀星,發現北斗七星斗柄指向依時有別,遂將四季更替稱為斗轉星移;現代人認定,地球繞日公轉致太陽在南北回歸線間的往返移動形成春夏秋冬。全球隨季節流轉的物候、氣候變化規律,乃是地球生靈所能感受到的最直接、最根本、最重要的生存環境。動植物、鳥類、昆蟲、水文、氣象在氣候的種種條件變化中,度過自己的四季,有生之歡欣,成長之苦惱,變形之令人驚異,死亡之無從規避。
在特德·休斯(Ted Hughes)的《季節之歌》(Season Songs)中,首先來到世間的是三月里降生的小牛犢,一個光閃閃的造物,可人得就像電影里的小爵爺方特洛伊,他從一開始就穿著他最好的衣服—“他的黑塊塊,他的白片片”,“在他短小利落的形象中閃閃發亮”。然而,生之美好、成長之茁壯、競爭性的頑強生命意志,無時無刻不隨身攜帶著生物自身的死亡趨向;最可悲的是其社會性,養牛的產業,“他的整個種系”,都是“被縛牢”在產奶場和屠宰場的大機器上的。
悲劇性的歸宿既已鎖定,該如何度過步入屠宰場之前的有生之涯?被屠宰的牲畜,是《季節之歌》中不時出現的主題之一,也是人類役使自然的象征。在當代生活中,沒有了古人為平衡捕獵、食用動物而進行的獻祭程序,缺少了這精神性關聯,食用菜畜變得天經地義。這使得人作為地球主宰者存在的同時,也切斷了自己從自然生物界而來的血脈根源,是人類精神性本體種種“斷根而亡”的表現之一。
休斯總是在詩歌中反復強調當代人類處境的這一悲劇性,在兒童詩中他也從不回避它的殘酷。因為對他來說,兒童并不缺乏理解力。他對待兒童的態度,是既不屈尊俯就,設定他們只能領會明亮、美麗、幼稚、小清新;也不把他們當作微縮小大人,他們是“兒童是成人之父”意義上的兒童,對所有來到自己面前的事物,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兒童的感受力在很多方面都值得大人學習。他們看事物往往會像剝去皇帝的新裝那樣毫不留情,成人則因經驗所致的心理防御系統而失去了這種直接性。
《季節之歌》也常常不被當作兒童詩看待,原因之一在于休斯使用的是兒童和成人(體內的那個兒童)可以共享的通用語言—在愛的直接交流中呈現的“意象和感知覺的某些波長”。這一波長區域的捕獲是休斯兒童詩歌大獲成功,被兒童、成人廣泛接受的基礎。
三月在繼續,接下來出場的是一條三月里的河,此時正是她走過枯冬的寒磣破敗,生機乍現的時候。從形銷骨立的貧瘠中走出的豐肥河流溢出“一窖藏不住的鱗莖毛茛”,像一頭純銀的母豬般的鮭魚……其新生的蓬勃勢能仿佛是微服巡游的“大海之大能陛下”。冬春之對立、死生之冰炭,自然法則以一條河流的嬗替戲劇年年巡演。
既是因季節之冬,更是因人類的無情濫用而致“病弱已久”的地球,在三月的手術過后,在陽光的灌注滋養中,讓人寬慰“她不會死了”(《三月的清早與眾不同》)。休斯在看似絕望的事物中找到他的關注主題,在死生交替的雙聲部韻律中定下春之基調。這一基調也是休斯四季之聲的基調,是他所有自然詩歌、動物詩歌的基調:自然,是永恒的生與死的角力場;生之欣悅、死之悲憫的張力閾是心靈劇場里恒常不滅的純詩。
四月的第一天,看上去和冬天里一樣光禿的橡樹,突然間就徹底不同了。全部的春之生命活力已在枝丫間呼之欲出,整個橡樹,帶著在休斯靈魂中的凱爾特古老神圣性,成為他眼中蘊蓄著“無形強光”的一枚“隱形的太陽”。如果說不是人人都能感覺到這些內在于橡樹的強大生命光芒的觸碰,那么當春天的特快列車呼嘯而過,少女懷春般為他守候著的橡樹滿樹葉片的“臉紅和騷動”,則是當事人、過來人都能會心一笑的妙喻。(《騙局》)
四月是世界的生日,大自然賜予禮物的季節,萬物在此時更生,連民族自豪感此時都參與到新生之春的合奏中,日后的“英國桂冠詩人”休斯始終以兒童“詩教”為己任,在不落痕跡中讓它隨春風化育:
……一陣風潮、騷動
騰卷南方
那光亮如銀的
紫羅蘭絲綢—那是自英格蘭
所有文雅哺育的
郡中世家提升起的
一派溫柔。
然而更重要的詩性化育,無疑是對兒童想象力的培養,使他們學會保持創造力的流動與鮮活。緊隨上節之后的春天,便是喧鬧孩子撒歡般脫了韁的春天:
當燕子剪斷約束住世界的弦索
斑尾林鴿拍打翅膀幾乎翻著跟頭飛行
你只是無法點數緊隨其后混亂中的萬物
像整個馬戲團隨著鐵環滿地翻滾
這股生氣進入到了夏天,就難免更沖動、奔放、熱烈、豐饒。有“以數以百萬計的他之贈禮”“令富饒的夏季大海/再富裕一百萬倍”的鯖魚,有在愛欲驅動下如被魔力附身的神廟舞者一般的鴿子,有像只燕子一樣輕盈、到處翻飛、工作了整整一夏天的夏之本身,有收獲時節向地球航來的火紅滿月“獲月”令虔誠的人們去榆樹和橡樹林中跪伏夜禱……夏之生氣,淋漓盡致地體現在了休斯當作夏之精靈來描寫的雨燕身上:
掠過院中的石頭,它們迸發出
彈片四射的恐怖。咧著青蛙般大嘴,
戴著高速路護目鏡,國際盜匪們—
在三四股鐵絲般尖叫擰成的套牛繩上
相互交錯爭先
在它們死亡的飛車道上180°打輪急轉。
它們猛擊飛過,箭羽剛硬,
在凜冽空氣中順風轉向,在房頂上空上下翻飛。
然后再次消失。它們沖飛的勞作余天空一點黑痣,
它們極端的、輕捷急停的瘋狂
還有它們旋轉的刀片翼翅
迸射進碧空,星點閃耀—
不再是我們的了。
被這般描寫的雨燕在一個沒有雨燕知識的人看來,只有瞠目結舌的份兒,心里還免不了嘀咕,一只鳥兒,至于這么彪悍嗎!不幸的是,作為譯者和筆者的我,就正是缺乏這一知識的未曾見過雨燕的一代城市居民,所以這一段的翻譯對我而言,是整書中最難處理的幾處之一,因為知識儲備不夠。休斯熟悉的雨燕、鯖魚、三文魚、椋鳥等的稟賦習性,以及他親歷農場生活對馬牛羊等的親近了解,都不在我的知識系統之內,這使得常常是理解的困難超過了語言表面的困難,語言從來傳達不了你不能真正理解的事物。
于是我暫停翻譯,先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搜讀、觀看各種關于雨燕的知識、視頻。這才驚異地發現,這種叫聲尖銳刺耳、翅膀如同鐮刀的鳥類是地球上的鳥族飛行冠軍之一。它之所以俗名“swift”(疾速的),正是因為它的特性:不停息地在空中快速盤旋、飛翔,幾乎從不落到地面或植被上,有許多雨燕甚至在空中過夜,這也是為什么在《捕獵夏天》中,詩人寫它“邊睡邊飛”。雨燕屬的學名,來自希臘語的“Apus”,意義亦是“沒有腳的鳥”。古人命名事物多是倉頡造字式的“觀鳥跡蟲文”而后落于心理感受。雨燕屬中的褐雨燕飛行時速最高可達352.5公里/小時,相當于一架低速飛行的飛機。知此再看休斯詩歌,將可以和飛機比比速度的鳥類比作垂直線上的瘋狂飆車族,只能說一點也不過分—F1賽車在人造地面上也只能突破400公里/小時。如果沒有建立起這樣的理解,譯到該詩最后,恐怕也聯想不到,詩人將那只未能起飛便墜毀了的新生雨燕比作“我的小小阿波羅”。這個貌似漫漶的比喻,其實非常切情切景,詩人用作暗喻的是在測試時于地面上發生事故炸毀的“阿波羅1號”飛船,故而此處當譯作“我的小小阿波羅號”。
休斯果真是一位悉心感悟自然生物的詩歌導師,一位巫靈式的長于接通生物內在生命力量的詩人。翻譯《季節之歌》,于我而言,也是一趟跟隨休斯學習自然生靈的詩性之旅,補上在童年時代缺少的一課。
在《季節之歌》中,于春天,休斯處理的是重生及其艱難性的主題;夏天,是實現春之豐饒、收獲和達至其最大值的主題;秋天,是自然的衰敗和腐化;冬天,面對的是自然的沉寂和存在物的消亡。
休斯季節詩的寫作開始于一九六八年,最初是為白金漢郡奇爾特恩區小米森登村(Little Missenden)有古老傳統的秋收豐年祭(Harvest Festival)活動而寫的五首秋季歌,五首詩集結發表時都以第一行詩代題目,分別是后來的《樹葉》《七愁》《保衛者》《某天來臨》《雄鹿》。
這里再就版本問題交代幾句。在英國,《季節之歌》由費伯出版社先后出過三版:一九七六、一九八五、二○一九年版。本中文版的翻譯是依照費伯社二○一九年版加上此前出現在《春夏秋冬》和第一版中的《捕獵夏天》《保衛者》《雄鹿》《兩匹馬:1-5》四首詩,因而本中文版收詩三十七首。
按照猶太人的傳統,新年始于秋季,一日始于黃昏,休斯的季節歌寫作實際上也是始于秋季,始于《樹葉》一詩。這首詩可以說是整本詩集的由來。最初寫出來為孩子們在節慶活動中演唱的《樹葉》一詩改編自兒歌《誰殺了公雞羅賓?》(Who Killed Cock Robin?)。這首英國兒歌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最初收錄于一七四四年出版的《大拇指湯米好聽歌曲集》(Tommy Thumb’s Pretty Song Book),一本大小適合于兒童手握的漂亮小書。
公雞羅賓是誰(一說是知更鳥),原型兒歌的意義是什么,已然失落于歷史的煙塵,被籠罩在了神秘當中。但是“誰殺死了樹葉?/我,蘋果說,我把它們全殺了”。這樣的來回往復、一問一答的結構,顯然是完全保留了原型詩的結構要素,“誰殺了公雞羅賓?/我,麻雀說,/用我的弓和箭,我殺死了公雞羅賓”。《樹葉》也保留了原型詩中大多數的提問,或只稍作改動,“誰來接住它們的血?”“誰來織它們的裹尸布?”“誰來給它們挖墳墓?”“誰來給它們當牧師?”“誰來做主祭?”“誰來抬棺?”“誰來唱贊美詩?”“誰來敲響喪鐘?”并且為提示新作所受到的原作影響,最后由知更鳥(羅賓)來敲響喪鐘。
除了《樹葉》一詩有顯而易見的兒歌來源,《金色男孩》有約翰·巴利科恩(John Barleycorn)的神話來源,《秋日自然筆記·3》中核桃追求成長為另一棵樹的過程采用了童話形式,《季節之歌》里的多數詩歌,并沒有體現休斯慣于使用神話、創造神話的詩歌雄心。這個階段的兒童詩寫作,對休斯來說,是在完成對抗上帝的《烏鴉》(憑此休斯成了一位大詩人)之后一個精神狀態相對放松的時期。如他在《樹葉》中所暗示:“誰來給它們當牧師?/我,烏鴉說,因為眾所周知/我研究《圣經》徹底之至。”休斯徜徉在田野、農場、院落、房舍周圍,將自己沉浸于更新自然感受、重獲養分之中,同時也更新著自己的詩歌語言。所以,盡管這本詩集屬于兒童詩范疇,語言難度卻明顯高于《烏鴉》,隱晦的修辭和巧妙的措辭每每令譯者絞盡腦汁,以期獲得在漢語中可以被當作詩來接受的傳達。當然整本詩集在節奏、用韻等很多聽覺設計上,休斯追求的效果是“在兒童的聽覺范圍之內”,很多歌謠模式和韻腳鮮明的詩在召喚英語讀者將其大聲朗讀出來。比如《某天來臨》的重復詩節和復沓用韻。這方面詩歌要素的傳遞,恰是翻譯之天然所短,翻譯永遠只能是照顧“意義”在先,聲音考慮在后,聲音要素只能依從譯入語的條件而定。湊韻譯出的詩作幾乎無一不是失敗之作。
因為文化的異質性,中國讀者可能對約翰·巴利科恩未必了解,這里也略作一介紹。這個人名是“約翰+大麥粒”的意思,約翰是英語中擬人化時的通用名字,就像德國人的漢斯;長期以來,大麥粒都是麥芽酒的關鍵成分,可以說,沒有大麥粒就沒有低度啤酒和蘇格蘭威士忌,所以,巴利科恩可以是酒精的委婉語。蘇格蘭大詩人羅伯特·彭斯于一七八二年寫有《約翰·巴利科恩:一首謠曲》,通篇把大麥的生長全程作了擬人化的描寫,生之維艱和人對之的殺戮盡用充滿了斗爭的殘酷性。彭斯的創作對巴利科恩形象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采用的故事是本來就有的民間傳說,早于他創作一百五十年前,這個名字就已經進入英語方言為人所知。后來,在杰克·倫敦的小說、史蒂芬·溫伍德的歌詞,以及休斯的《金色男孩》等不斷出現的文學再創作中,共同的主人公約翰·巴利科恩,都隱喻、強化著大麥種植、生長、收獲和酒精蒸餾的循環及其性質中所具有的憤慨、痛苦、死亡和重生主題。可以說,歷經磨難而頑強不息的約翰·巴利科恩形象是一萬兩千年人類的大麥種植歷程在英語文化中結出的一顆文學象征寶石。
休斯在秋季詩篇的最后《大麥》一詩中,再寫大麥,將其作了女性王國的比擬,詠贊了這些“受雇于大地,受雇于天空,/受雇于大麥,成其為大麥”的女王們是如何度過嚴冬、劬勞生長、威武成熟傳承下整個大麥王國的。豐收、勝利的圖景,是天地間的一場浩大舞蹈:
她們就這樣贏得了她們的王國。
然后她們穿戴金甲,準備加冕。
每一位都帶刺、披羽,如一支柔美的武器,
戴上她之王國的王冠。
然后全部女王們的遍布田地
回旋在一場舞蹈中
和她們看不見的舞伴,風
天地間一個獨舞者。
大麥就是這樣傳承下了大麥王國。
作為休斯復雜性程度最高的兒童詩,《季節之歌》的意象系統、音步韻腳韻律體系都相對更追求精準,具有腳踩大地、扎根于地球特性和人類生活的特點;不像他其他的兒童詩集,有的更追求文字游戲的快樂狂歡,有的著力于創造更為異想天開的出奇意象。因而這本詩集中的很多動植物形象、季候特征、人的行動場景都具有精神延展性,深入開掘了場景可能的和內在的精神本質。
如他的《秋日自然筆記·5》,詩中場景無非是詩人在蘋果樹下燒一本快照相冊。在這一場對某個不再有價值的東西施行的簡單火葬中,詩人執一根樹枝,面對過火的相簿冊頁,“灼照的眩暈中,我勸誘它頑固的羽毛”。在他身后的深秋果園,大自然的背景里“所有能夠逃離的事物,現在安靜地遷徙”。當詩人看著燃燒的相冊“焦黑皺縮/成灰白的飄落。簇聚之物的核心過火硬化”,很自然地便生發出哲思“萬物//都需經此。每一粒子/及其閃現。萬物必定離去”。在照相鏡頭般掃過火中的自然場景后,最后的特寫是“一只驚慌的烏鶇,精瘦、警覺,數落/到處緩慢的曝光起底—逃離,歸來”。人及其行動完全地融合在以相機鏡頭效果記錄、感知、衍伸、開拓出的季節肅殺收尾戲劇中,一首以火葬為象征形式的關于消逝的哀歌。
《秋季自然筆記·4》是我作為詩人最佩服的休斯季節詩章之一。作為一個詩人,意味著首先你的感知覺系統是與眾不同的,憑此你加速造化、放緩神明、變形萬物、創造出另一個世界。當這個新世界與原生世界的千絲萬縷關聯能被人一眼看出,你會成為一個可以深入人心的藝術家,如果不容易看出,你的傳播會受到局限。休斯這首詩的前三節堪稱是藝術家感受力工作的杰作,很少有人能感知到一棵在風中起伏的繁茂榆樹“周身的飽滿繃緊嗡嗡如鳴”,更少人能感受到此時的榆樹“如一艘風帆悉張的航船”;而當這個詩人的沉重感受進入物我合一、大海地球合一的恍惚幻境:
因為大海是一艘航船的根
因此地球也是我的根。
當樹身的膨隆(海浪的翻涌)從榆樹頂托起烏鴉
樹干和桅桿都是我的家,它們搖晃我,它們提供我給養。
你知道他有幸遇到了神來之筆,這是真正的來自無意識能量的靈感在工作,因而詩句會有一定的不確解處,這屬于真正的詩之神秘。作為詩人,你也會知道,你有幸獲得這種詩的時刻,太少太少。括號中的增譯是為了體現休斯一語寫雙意的能力,不增此,你在漢語里不會感受到他感受到了什么。詩歌翻譯,首先在于深入透辟的“理解”,包括理解詩人心靈的創作機制和創作過程。這一理解,高于理解字面語言本身。
休斯的詩歌通常讓人感覺到它們被一種不停息的、急迫的能量所驅策,這很大程度上來源于詩人對“想象”運作的倚重,這是他衡量人是否具有積極的內在生命的一個標桿。詩人常常予以譴責的是科學“準確記錄事實”的做派已深入到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技術化時代人類的心靈充滿了內在的怠惰和對世界的疏離。人作為生物性的精神存在,必須以其內在活躍性去實現與世界的創造性相遇,否則便是錯過今生。這種“想象”運作結出的碩果有時是極度震撼的,如在描繪以鋪天蓋地的群飛為特色的椋鳥中(《椋鳥駕到》):
現在是群情沸騰跳蚤的特寫。
現在是一陣寂靜—
末日恐慌的這群諦聽了一瞬。
然后,輕輕一聲轟響,它們將你卷入
其精神失常,匯聚起一個逃出生天的摩天輪
噩夢—尼亞加拉瀑布
扇動著上舉的轟鳴雙翼—復歸坍塌
于神經質的原子們
無法操控的重量。
只有大力神般的詩人,才能以其想象之力舉起神經質的群飛椋鳥創造的摩天輪噩夢—在雙翼上舉的同時又坍塌下落的一匹尼亞加拉大瀑布!這不是椋鳥的奧秘,而是心靈遇合椋鳥才能在創造中實現的奧秘,屬神的作為。休斯靠著這樣的詩性作為,啟迪著兒童的靈魂、開發拓展著他們的想象空間,期許“每一個新的兒童都是自然糾改文化錯誤的機會”。
《季節之歌》結束于《溫暖與寒冷》一詩。前三節每一詩節的開頭四行通過冰凍和與鋼鐵有關的意象描繪了冬天的冰冷苦難。然后是以“然而”開頭的兩節四行詩:“然而鯉魚在它的水深處/像行星行于天宇。”借此展示自然世界的另一面向,動物們做好了對冬之寒冷的應對準備,盡管有的帶著蒼茫無助“野兔沿公路走失/像根扎向更深處”。在詩的結尾、同時也是整本詩集的結尾,休斯以其典型的黑色幽默風格擴展出人的意象,“流著汗的農夫們/在夢中翻身/像公牛在烤釬上”。一方面睡夢中的溫暖農夫形象給予讀者以安慰,同時詩人又似笑非笑地提醒讀者人類也是動物。
時間與季節是凌駕于一切之上的無處不在的力量,時間不會放過任何事物,但時間的活力是如此迷人,正是它,是休斯季節詩的魅力之源。冬天過后便是春天,當你讀到最后又可以回到詩集最初,重讀新生命的降生,或者帶著你已被更新了的感知覺系統開始寫一首自己的新生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