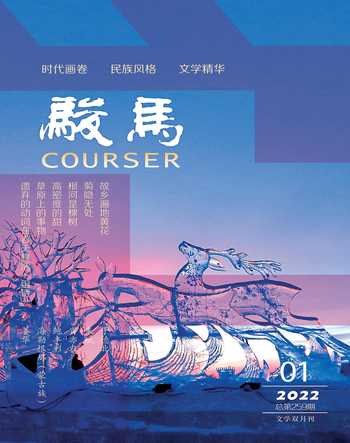高密度的甜
鮑豐彩
一
它們細長堅韌的藤條蔓過地壟,爬過山坡,在一片砂石土粒之間,演繹自己如鄉間父老一樣強悍的生命力。
紅薯,在魯東南的鄉下,被人們更通俗地叫作地瓜。顧名思義,地里結出的瓜。簡單的兩個字,盡顯莊稼人的憨厚、樸實。這些跟土地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莊稼人,春種秋收,用力氣和汗水跟土地交換斤兩,不需要拐彎抹角。
土地饋贈給莊稼人的瓜多種多樣,有西瓜、甜瓜、冬瓜、南瓜、苦瓜……這其中,地瓜因其產量高、質地硬、甜度和營養價值俱佳,當之無愧成為眾瓜中的主食。這種在四百多年前傳入中國的食物,一旦在魯東南丘陵地帶扎下根來,便迅速地開始繁衍生息,砂石地、黏土地,它無所挑剔。地瓜對土地的鐘情程度,達到了不分貧富的境界。
栽地瓜、刨地瓜、切地瓜、曬地瓜皮、收地瓜皮……在所有的農作物中,地瓜算是種植工序最繁瑣的一類。現在我想要梳理這道繁重農事的起點,是從一個地瓜在冬天的妥善收藏開始寫起,還是從一棵瓜秧在春天的入土開始呢?人們在秋天收獲,冬天貯藏,春天育秧栽培,夏天勞作,然后等待收獲。在春夏秋冬的輪回中,選擇哪一環開始,仿佛都是不夠完滿的。
母親最擅長解決這樣的問題。每一年,她選擇這個圓形繁衍周期的起點位置都不太相同。如果頭一年的收成好,母親就會多留一些地瓜做種。這時候地瓜的一生,就是從冬天開始計時。如果收成不太如意,母親就把地瓜悉數加工,儲藏或者售賣。來年的春天,她會再去集市上買一些地瓜秧。這時候,地瓜的一生從春天開始計時。這是每一個鄉間母親在日久天長的勞作中實踐出來的智慧,只有她們能算得清那些地瓜的一生。
栽地瓜也麻煩,一棵一棵地管著,每一棵都得上心,扒窩、栽秧、上藥、澆水、培窩,順序是固定的。前一步做后一步的引子,后一步將前一步妥善安置,穩扎穩打,每一步都不容亂。
其他的作物只需要大水漫灌,而地瓜卻需要一棵棵單獨喂水。母親在前面扒窩,我跟在母親后面栽秧,弟弟跟在我后面上藥,父親跟在弟弟后面澆水。我們四個人像車間流水線上的工人,分工明確,各司其職,有條不紊地,在一棵棵瓜秧面前反復彎腰、起身、彎腰、起身,像是周而復始的叩拜。
多年以后我跟隨自己的同鄉遠赴青島做暑假工,在飾品廠寬大的工作臺上穿針引線,我的身體也一直在重復著童年時地瓜地里的姿勢。我要在一顆顆珠子被機器送到面前的時候躬身,抓起來,快速穿線,然后再放下。然而那些冰冷的珠子卻不能給予我以長久的慰藉。我與這些五顏六色的圓形,關系實在單純。我只需要跟每一個保持幾秒鐘的接觸,然后換來幾個月的生活費,從此天涯陌路。它們不會像那些地瓜秧,以一己之力串聯起我們一家人的節奏與憧憬。它們也不會像那些地瓜秧,把我們的力氣和心思一起埋在地里之后,選擇某一固定的時刻,回饋給我們以高密度的甜。
生長的過程是緩慢的,沉默的,秘而不宣的。這些被小心翼翼一棵棵單獨照管的秧苗,將在以后五個月的時間里,經歷一場自上而下的蛻變,如同它的祖先們之前經歷的那般。它們首先從身體里伸出根莖,牢牢地抓住這片土地,再用自己的觸手圈出更廣大的領地,一棵與一棵之間可以相互勾肩搭背、分庭抗爭,甚至勢不兩立,以強韌有力的莖宣告自己的野心。而土地之上的這個過程,通常是與土地之下的另一場運動齊頭并進的。在那里,在土石砂礫圍堵的暗處,一棵幼小的根苗已經初具蓬勃的使命,它要將天地的血脈與靈氣,幻化成身體里一次次細小的膨脹與爆裂。它們橫向突圍,它們縱向開拓,它們躲過石塊的圍追堵截,它們在一場場春風和一次次秋雨中,最終完成了自己。
二
刨地瓜最好的時機是霜降前后,被霜打過的地瓜秧,全部的甜和香都藏進了地里。這是土地與莊稼人約定好的時間節點。
刨地瓜的第一件事情是扯斷地瓜秧,露出一條條的溝壟。在鄉下,很多真相都是只需要費一點力氣就能夠揭示的。就像扯斷了地瓜秧,我們就能夠看清楚,哪一些壟上的地瓜急于暴露自己,哪一些壟上的仍舊羞澀,隱而不發。
地瓜秧從自己的塊根出發,四面埋伏,縱橫交錯的觸手相互纏繞,父親用镢頭勾住其中的一處,就能把整片的地瓜秧扯起來。他往前走兩步,再猛地一拽,整片的地瓜秧就被扯斷了。這是一場人與地瓜的拔河較量。較量的結果,就是父親朝著粗糙的手心啐一口唾沫,搓一下手心,握住镢頭,選一個地瓜壟,穩穩地刨下去。
刨地瓜的镢頭不同于一般的镢頭。鄉下人的智慧在農具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揮。最開始用的镢頭是一塊整齊的長方形鐵片,鐵片頂端鋒利尖銳,但是齊整的頂端容易誤傷地瓜,甚至將地瓜整塊切斷,漏出乳白色的斷面和汁液。再后來,人們就發明了一種叉狀的镢頭,將原先的整塊鐵片改造成了三根叉,這樣能夠避免對地瓜整齊的誤傷,從而盡可能地保證地瓜外貌的完好。很多時候,鄉下人對于糧食的珍視程度甚至超過了自己的孩子。就像父親可以放任我們幾個孩子在地里瘋跑,被藤條絆倒,滿身灰塵,卻不能容許一棵出土的地瓜受到半點擦傷。
刨地瓜是一件技術活。小孩子沒有資格插手,但是每個孩子都對著那把高高揚起的镢頭暗自神往。那個時候,地瓜金貴,是土里的黃金。這樣神圣的工作一般由男勞力來完成。刨地瓜的過程像極了開禮物盒。多年后,我帶著兒子站在商場一個華麗的盲盒柜前,掃一下二維碼,兒子就會選中自己喜歡的盒子點擊,“哐啷”一聲,柜子底下就會掉落出一個盒子,兒子驚叫著打開,滿是未知的驚喜。每當這個時候,我總是會想起小時候那些被埋藏在土地里的驚喜。你不知道一镢頭下去,刨出來的會是怎樣的數量、形狀和大小;你也不知道,這里的土地會聯合一棵瓜秧,回饋給你怎樣的波瀾。那些被土坷垃沉甸甸包裹著的地瓜,在天光大開之前秘而不宣,它們在黑暗中慢慢發酵,讓自己一點點地膨脹起來,結實起來,收集風聲雨聲雷聲,再凝結成最后那點高密度的甜。膨脹的過程需要極具功夫的火候,膨脹得慢了就會顏面掃地,長得太著急了又會破相,肚子上裂出一道道的疤痕。火候的拿捏與取舍,會在秋收時刻一一真相大白。
我們緊跟在父親的身后,目光跟著父親的镢頭起落,驚呼著撲上去。我們家刨地瓜一直保留著一個傳統節目,就是選出每年的地瓜王。我跟弟弟在父親和母親的屁股后面寸步不離,掂量著每一個地瓜的大小。勝負的砝碼緊握在自己手中,這極其考驗我們的智慧。
后來我偶然在一份中學生讀物上讀到了蘇格拉底教育自己學生的故事,這個睿智的老人,讓自己的學生們在果園里走一遭,并且只能摘一個自己認為最大的果子出來。走到盡頭后,每個學生都對自己的選擇不甚滿意。有人遺憾自己錯過了更大的果子,有人懊惱自己決斷得太早。而同樣的心路歷程,在兩千多年后魯東南山區的地瓜地里,仍舊被幾個滿身黃土的孩子粗糙地演繹著。
這是與地瓜相關的所有工序里面,最讓我們神往的一道。那些從父親的镢頭下面滾出來的地瓜,最大程度的滿足了物質匱乏時期我們亟需擴展的想象力。這些形態各異的塊根,不遺余力地與我們產生了某種默契:有長鼻子的老鼠,有戴眼鏡的貓,有奶奶家的那盤石磨,還有安徒生童話中那個擰著鼻子的老巫婆。幸運的話,如果一塊地瓜正好長在兩個斷面整齊的石頭中間,它的肚子就會長成薄薄的一片,弟弟說那像他在二大爺家里見過的一種健身啞鈴……每當這時候,陽光就會很暖,風也不緊不慢地吹。那些新翻出來的濕漉漉的泥土,在太陽和風的輕拂下,很快干透了身子。我們要先把這層曬干的泥土擦干凈,露出地瓜鮮艷的紅色外皮,然后堆放在一起。母親總會喊:慢點扔,別磕壞了。
現在,它們緊緊地靠在了一起。這些曾經遙遙相望的手足們,終于肩并肩密密地挨著。這樣的親密時刻,彌足珍貴。天地之間,只有這一堆堆山丘一樣的塊根,在這個時刻,互訴衷腸,互道珍重。
三
你見過那種明晃晃的鍘刀嗎?它可以高速地為十幾個地瓜上刑,干脆利落,毫不手軟。
這樣的鍘刀,已經許久沒有出現在新世紀秋收的舞臺上了。幾年前我曾經在本地一個農具展覽館里看到過它。一個圓形的鍘面,上面對稱地分布著兩個刀口。鍘面上的木質已經蒙塵老化,然而那兩片長條狀的鍘刀,仍舊寒光四射。這是被多少地瓜的汁液喂養過的刀口,能夠在刀光劍影之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地瓜厚薄均勻地切成一片片白亮亮的地瓜皮子。
多年前我們就是這樣分工合作,將這口鍘刀綁在一個獨輪車上,推著這輛車依次碾過一整片土地。鍘刀的背面有一個木質搖把,切地瓜時只需要用力轉動這個搖手,就會有源源不斷的地瓜皮,混合著乳白色的漿液,從鍘刀口背面傾瀉而出。這條白色瀑布傾斜的速度與力度,完全由控制搖把的那只手來決定。
有幾畝地的地瓜等待著這只手的統御。循環往復的機械勞動,完完全全地抵消掉了勞動的美感。投入到鍘口里的地瓜大小不一,它們像一個個勇士,前仆后繼,抱著必死的信念,想要在幾次擠壓與受刑后玉汝于成,涅槃重生。碰到個頭小的,只需要在鍘刀下滾過幾圈,就把自己滾成了薄薄的幾片。如果碰到個頭大、力氣足的,這就變成了一次力量的抗衡。那只手會青筋暴起,鋒芒畢露,向著一個切口反復的沖擊、傾軋,讓那個負隅頑抗的大個頭,最終折戟沉沙。
這場攻伐之術的結局,則是滿地成堆的地瓜皮子。經過了幾個工序,這些剛剛從土里翻身的肉身,暴露出自己的五臟六腑,又被鍘刀逼出了內心的白,以更加赤裸與坦誠的姿態,再一次跟土地親密接觸。
但凡見過秋收時刻曬地瓜皮景象的人們,一定會為這一片片浩浩蕩蕩的白色海洋而振奮,而贊嘆,而心魄蕩漾。整片大地都是安靜的,沒有絲毫風浪。女人們會雙手抄起一堆堆剛剛切好的地瓜皮,以自身為原點,向四周拋灑。這樣的勞作極具藝術性和觀賞價值,她們用手默契地配合著那一片白,散落成扇形圓形,均勻、規整、姿態優美。她們像一個個撐著船的水手,一點一點揚起白帆,這個過程是緩慢而有力的。現在,千帆競發。這時候風就來了,浪也翻滾起來了,白浪滔天。天氣好的時候,遠遠地你還會看到那些由地面蒸騰而上的水氣,將整片海洋氤氳在一片如夢如幻的霧氣之中。
收地瓜皮則全看天氣,那時候村里有鑼。晚上下雨了就開始敲鑼,全村齊上陣,在暗夜里靠一雙手完成這場黑暗中的戰役。雙手與土地經過千萬次的密切接觸,產生了默契,我們在黑暗中就能夠自動給地瓜皮分類:這個已經干透了,這個水分還太大。
每個人的前面都有兩個筐。一個裝已經曬干的地瓜皮。獲得了這種身份證的地瓜皮,就可以直接入袋,歸倉。而另一個筐里,裝著還未完全交出水分的地瓜皮,它們還沒來得及成全自己,因為土坷垃或者同伴的遮擋,它們還保有一棵鮮嫩多汁的心。這樣的分類務必心思縝密地完成,以防那些未干的地瓜皮混到封閉的尼龍袋里,用自己的水分漚爛其余的一片,殃及無辜。
這時候地里就只剩下手指和土坷垃碰撞的聲音,手指和地瓜片碰撞的聲音,以及地瓜皮和地瓜皮碰撞的聲音。
地瓜皮是緊貼著地面的,這對人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時候的莊稼人就變成了另外一種生物。他們齊齊地蹲在地上,雙手和雙腳緊緊并攏在一起,雙腳負責緊跟雙手的節奏,慢慢向前移動,絕不拖泥帶水。這是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這是莊稼人與土地的沉默契約。
同樣的工作在白天則會變得悠閑很多。只要干透了,只要沒有雨,莊稼人不怕它在地里待得時間更長一些,莊稼人有的是時間跟它們耗著。這是一年中從土地里打撈上來的最后一份戰利品,他們愿意放慢收獲的喜悅。
四
還有一些鐵石心腸的地瓜,靠自己卻根本熬不過一個冬天。
這個時候就需要地瓜窖上場了。
在我們村西坡的地頭上,散立著許多高高凸起的水泥臺。水泥臺圍成方形或者圓形,以不動聲色的外形,圍剿著地下七八米深處的寒氣。這些呈L型走向的地瓜窖,從土地的淺表一路拐進土地深處,然后在L型的尾部,擴充高度和寬度,一個像模像樣的地瓜窖就完成了。接下來,這些蘊藏著高密度甜味的根塊,將會在這個時間和空間的膠囊中,完成甜度最終的提純。
挖地窖是個大工程。全家老少齊上陣,鐵锨、镢頭、鑿子一并出力。這是象征著一個家庭生命力的浩大工事,通常要跨越整個冬閑的時節。男人在這塊土地上開掘,一米、兩米……寒風呼嘯的時候,一滴汗摔進土里砸出坑來。風還在吹,這時候已經吹不到男人的頭頂;汗還在落,一滴汗落下去的時候還要跟紛紛揚揚的塵土同歸于盡,它們將深入這塊土地的腹部,生平第一次見識到腳下土地最縱深處的紋理和溫度。挖到最深處的時候,在窖上面的女人會垂下一根近十米長的繩子,繩子兩端都打好結,等女人手里的繩子只剩下一個結,男人在下面喊“握住了”,工事就到尾聲了。這時候北風也吹夠了吹累了,剛剛調轉了身子,春天就來了。
那些剛剛見識了這個世界的紅色根塊,就是在這樣的地窖中完成身份轉換的。經過一個冬天的歷練,來年春天,它們就會搖身一變,成為繁衍另一代地瓜的起點。這個時候,我總會想起武俠劇中那些閉關修煉的絕世高手。他們要把自己與世隔絕,自我修煉,自我助益,在緊要關頭自我激勵和鞭策。那扇門開啟之前,沒有人能猜透里面的劇情。他們在密室里痛徹心扉或者肝腸寸斷,俠骨柔情或者百煉成鋼,我們一無所知。出關之日,那扇門隆重地開啟,這個時候就會有慢鏡頭,看著那扇厚重的石門緩緩移動,絕世高手從衣衫微露到天光乍開。這時候,所有的劇情謎底都被揭開了。
也有一些地瓜不成器,熬不過冬天,就從內而外地腐爛了。在功成之前,它自己先走火入魔了。而那些順利出關的地瓜,我們則會給予它更隆重的稱呼:地瓜老母。從別的老母身上脫離,再成為另一個輪回的老母,只需要熬過一個寒冬。細細想來,世間很多事物的成敗,大抵也都是依循著同樣的道理。
春天來的時候,母親就要打開窖口的封蓋,劃亮一根火柴,扔下去。火柴在膽戰心驚中翻過十幾個跟頭,有一些沒有見底就已經熄滅了。必要的時候,母親要用火柴點燃一把捆好的柴草,再次扔下去。這些柴草氣勢洶洶,它們緊緊抱成一團,以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一路呼嘯著跌入黑暗。母親仔細觀察著火焰的長勢:如果火焰落底后仍舊在燒,人就可以放心大膽地下窖;如果火焰落底后瞬間熄滅,母親就會在窖口坐上一會兒,等待窖內外的氣流充分交換。
在我們村,從村子一路往西,跨過一條河,爬上一道坡,就能看到一片片這樣的地瓜窖。它們的開口矮墩墩地趴在土地上,匍匐著,盡量用低到塵埃里的姿勢掩藏自己。很多時候,它們更像是煙囪的反義詞。你看村莊里那些高聳的煙囪,它們站在屋頂的上面,比屋頂還要高,這還不夠,它們還得讓炊煙繼續助長自己的聲勢,順著風向,往東西南北開拓。它們讓自己爬過樹梢,直至統御整個村子才肯罷休。與這些極具張揚性的煙囪相比,地瓜窖算得上虛懷若谷了。是的,除了虛懷若谷,我想不到更恰當的詞語來描述它們在這片土地上的姿態。
我對地瓜窖膚淺的認識一直保留了許多年。它們掏空自己,它們掩藏自己,它們吞納寒氣暑氣,它們是甜蜜的通道。直到一樁本地新聞震驚了整個村子,包括我,我才開始明白,虛懷若谷的同時,它也包藏禍心。
早先,村子里還沒有代步工具,一對新婚夫婦步行去趕集,途中在一個地瓜窖的水泥臺上休息,一不小心,新婚耳環掉進了窖里。新郎自告奮勇下去撿耳墜,幾個箭步落入黑暗后再也沒有了聲息。新娘呼喚幾聲沒有回應,脫下紅色高跟鞋也跟了下去。趕集的人們注意到了擺在窖口的那雙鞋,繼而發現了雙雙窒息而亡的夫婦。
這口醞釀著甜蜜的地瓜窖,原來也一直在覬覦著甜蜜。隨著從它的身體里掏出的甜越來越多,它也要開始吞進去更多的甜。這樣的無私奉獻與霸道攫取,在同一個時間與空間的隧道中對峙。我因此也開始陷入了一種人生中最朦朧的價值判斷之中——那些給予我們的,同時也可能剝奪我們。
那段時間,在我輾轉反側的夢境中,那一口口地瓜窖就像一個個黑洞洞的眼睛,從幽暗的地底凝視著我,然后讓我迅速跌落下去。我感到自己下墜的失重狀態,像母親手里那根微光搖曳的火柴,又像那捆并未扎進的柴草。更多的時候,我在夢里面向青天,看著那個洞口越來越小,越來越遠,一股快要被淹沒的窒息感一擁而上,然后就有一只紅色的高跟鞋砸下來,我大口喘息著在清晨醒來。
不遠處的大地之上,那些腹內空空的地瓜窖,眼神幽深似浩渺的星空。
五
父親的三輪車翻在溝里的時候,一車斗的地瓜四散天涯。
那時候父親剛剛買上了村里第一輛農用三輪車。農閑的時候用來拉活掙錢,農忙的時候更是派上大用場。正當血氣方剛的盛年,那時候的父親覺得自己無所不能,那輛三輪車更強有力地讓他佐證了這一點。翻車事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剛下過雨,到地頭的土坷垃路被沖得破敗不堪。車斗里裝滿了豐收的地瓜,父親一路駕駛著三輪車過關斬將。在一處被雨水沖垮的路面上,路一側就是一條幾米深的土溝。我跟弟弟坐在三輪車的副駕駛,跟著三輪車左右搖晃。那些讓我揪心與恐懼的狹窄與凹陷,都被父親輕松化解。我碰到父親肩頭的時候就會抬眼看他,我的高大帥氣、無所不能的父親。車子就是在這個時候傾斜的,輪胎順著路面右側的凹面滑下去,一直滑進了幾米深的土溝里。
父親把我和弟弟從車窗里拉出來。一直跟在車后面的母親沖我喊,快去叫人。我背著弟弟向村子里走,一路走一句喊,喊了幾聲天就黑了。那時候人們都回村子休息了,我在坡上就能看到家家戶戶的朦朧燈光。他們正坐在燈光下彈土,嘮嗑,他們看不見一個九歲的小女孩背著四歲的弟弟在喊,他們也看不見一輛裝滿地瓜的車正翻在溝里。弟弟開始哭,我說弟弟別哭了,我們找到人就可以把車子抬出來了。終于喊到一個趕著回家的本村大伯。那時候人的力氣還不值錢,時間也不值錢。他騎著自行車說你先回去,我去村里叫人。
我跟弟弟就蹲在坡上等,我不敢回去。我怕回去了他們來了找不到地方,我更怕他們蹲在燈光晃動的飯桌上不再回來。
天上的星星已經很亮了,我看到黑暗中有幾個村里人從路的另一頭走來。他們的身上一律扛著工具,那些帶著長長的木把手的工具,之前在地里翻出過泥土、花生、豆蟲也翻出過一家人生計的工具,現在成為黑暗中他們身體上旁逸斜出的部分。現在他們要用這些農具,幫助我們跟一輛三輪車較量一番。
我背著弟弟,一路領著他們走到地頭。弟弟已經哭累了哭乏了,他在我的背上昏昏欲睡。遠遠地我就看到三輪車的兩個前照燈射出奪目的光,像一把劍斜插著刺向幽遠的夜空。父親和母親已經把四散的地瓜重新撿回來。我看著這些大人們一起鏟土、墊石頭,一起喊口號,一起用力。我覺得他們挖了好久也抬了好久,最終三輪車奇跡般地穩穩落地。父親跟鄉親們點頭、揮手、致謝。父親又坐上了駕駛室,我仍舊搶著坐到副駕駛,母親抱著已經睡著的弟弟坐后座。我無所不能的父親,載著我們一家人,載著一車地瓜,搖搖晃晃地回家去。
磨面機開到了我家門口,但出車的父親還是沒有回來。我參與過地瓜從地里到家里之前的所有過程,唯獨這最后一項我很少參與。與前幾種相比,這是一項需要極好體力和耐力的活計。
母親在頭上扎了個紅色頭巾,又甩給我一個,她示意我照著她的樣子扎起來。這樣,母親就取代了原先父親的角色,而我得完成母親的部分。我忙著把一堆堆地瓜皮裝進袋子再由母親扛到機器前面交給師傅。這是一種爭分奪秒的工作,沒有人催你,但是機器隆隆的震動聲讓你手上的動作不敢怠慢。在半個小時的轟鳴和震動中,母親大聲地催促。她的聲音要蓋過機器的聲音才能夠準確無誤地傳達到我的耳朵里,命令我也像機器一樣完成她的那些指令:先裝左邊的,不用太滿,舉起來給我,別放地上,動作麻利點……
等機器的轟鳴和振動終于在一片煙塵四起中靜止下來,我的身體仍然處于一種持續的高強度的振動之中。我的嘴巴和鼻子里,全部都是混合了泥土灰塵和地瓜粉塵的粘稠物,它們堵塞著我的呼吸通道,讓我一個勁地咳嗽,嗆得眼睛里一片模糊。
在淚眼朦朧中我看向母親。她似乎比我淡定得多,她不咳也不嗆,低著頭忙著收拾戰場。她把一袋袋的地瓜面從外面搬進屋里。剛剛能搬得動一袋地瓜皮的母親,現在已經搬不了一袋地瓜面。她兩個膝蓋前傾,頂住袋子,連拉帶拽地緩慢移動著這些一百多斤的重物。我想上去幫忙,母親沖我揮揮手說,去洗洗吧。我看到她的膝蓋上,抵在袋子上的部分,粘上了一片灰蒙蒙的粉末。
這些質地細密的粉末,最終將在母親斷斷續續的咳嗽聲中,變成我們餐桌上的煎餅、甜香濃稠的粥,以及雞鴨鵝狗的飼料。大地之上,那些一一豐盈起來的事物,也都遵循著這樣普遍而單純的道理,在一次次時間的熬煮中,變稠變甜。
責任編輯 麗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