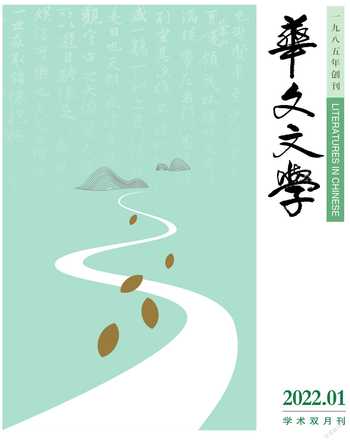華人抗日史書寫與“雨林美學”新變
2022-03-24 08:32:16黃育聰
華文文學
2022年1期
黃育聰
摘 要:馬華留臺作家張貴興于2018年推出長篇小說《野豬渡河》。在小說里,張貴興以砂勞越被日軍占領的“三年八個月”為中心,試圖揭開婆羅洲隱而未現的華人抗日史,在剝除隱喻與再造寓言的基礎上,重新思考與建構“雨林”美學,寫出華文文學世界里的人類共通經驗。他的嘗試既是對自己“雨林”美學的一種新變,也為華文文學新題材的出現開辟了道路。
關鍵詞:張貴興;《野豬渡河》;華人抗日史;“雨林美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22)1-0065-08
在沉寂了17年后,馬華留臺作家張貴興于2018年推出了長篇小說《野豬渡河》,以其綿密詭異的文字,縱橫開闔的故事結構,書寫出此前未曾深入涉足的婆羅洲華人抗日史,努力嘗試建構新型的“雨林美學”。張貴興在“馬華文學”里舉足輕重,自1980年以《伏虎》登上文壇,受臺灣不同文學獎的提攜,逐步形成自己的主題:中華文化的體驗、婆羅洲記憶與華人的移民史。1992年,張貴興推出《賽蓮之歌》,開始有意識地將“雨林”的壓抑與沖動,熱帶動植物的張揚與腐敗同少年蓬勃的情欲相融合,令人耳目一新。1996年,張貴興推出《頑皮家族》,嘗試將華人拓荒史隱喻在夔家家族史里,充滿了開辟天地的勇氣與污血。此后,他還陸續于1998年推出《群象》,2000年出版《猴杯》及2001年面世的《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形成所謂的“雨林敘事”系列,被王德威稱為:“當代華語世界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①
“馬華文學”以椰風蕉雨的獨特意象引人注目,代表作家李永平、張貴興、鐘怡雯、陳大為和黃錦樹等卻是長期寓居臺灣。……
登錄APP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