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應對單邊數字稅對我國跨國數字企業的沖擊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市場與價格研究所,劉方、楊宜勇
本文節選自《中國投資(中英文)》, 2022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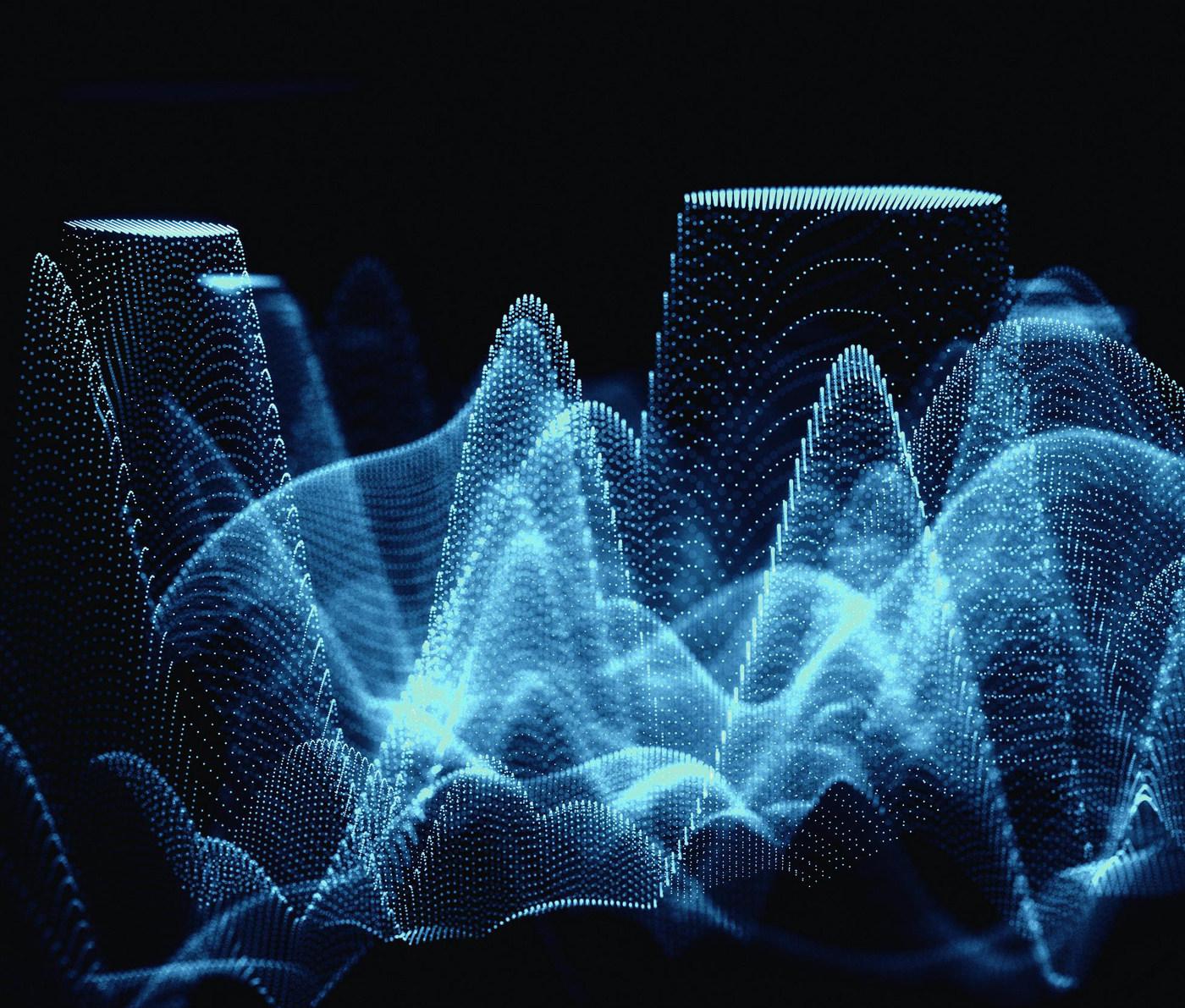
當前,全球數字經濟迅猛發展,數字經濟的出現改變了全球經濟價值創造、轉讓及分散的方式,對國際稅收核心規則形成了巨大挑戰,運行了百年的跨境企業所得稅國際征稅規則已無法適應經濟數字化下新的價值創造方式。數字跨國企業不需要設立常設機構,長期依靠用戶參與活動創造價值來賺取巨額的收入。根據現行的聯結度和利潤分配的國際稅收規則,由于缺乏稅收實體,產生巨額利潤的跨國企業在用戶創造價值的管轄區繳納極少的稅收,甚至通過一系列手段逃避在利潤來源國的納稅責任。這樣的狀況凸顯了現行國際稅收規則在數字經濟環境下缺失的公平性,同時,由于巨額的利潤沒有公平地在各市場轄區國征稅,造成跨國數字企業與市場轄區內其他企業以及跨國企業間稅負的不平等。例如,歐盟委員會對轄區內跨國數字企業的納稅情況進行調查,發現歐盟轄區內數字企業的實際平均稅率為9.5%,而傳統企業的實際平均稅率為20.9%;跨國數字企業的實際平均稅率僅為10.1%,而跨國傳統企業的實際平均稅率為23.2%。
從實踐來看,數字稅主要適用于以用戶參與創造價值為特征的部分數字經濟活動,征收對象為在線廣告服務、在線中介服務(社交網絡、交友網站等)、 在線市場(多方銷售平臺等)、數據傳輸服務等。同時,征收國普遍都將數字服務收入作為稅基,并且以一定規模的跨國數字企業在全球范圍內的年度總收入和在本國提供數字服務取得的收入作為征稅門檻。稅率設置在2%~7.5%不等。
從數字稅本身來看,數字稅是數字經濟發展較弱的國家為了彌補現行國際稅收規則對數字經濟發展的不適應性,避免大型跨國企業依據現行國際稅收規則逃避在本國的納稅責任,加 之全球性解決方案又無法在短期內出臺的情況下實施的無奈之舉。數字稅不是一個完美的方案,已經表現出了較強的扭曲性。另一方面,從我國來看,由于政策原因,目前一些跨國數字企業尤其是平臺企業并沒有進入我國市場,它們利用國際稅收規則漏洞在我國進行利潤轉移的問題并不嚴重。此外,雖然我國在當前全球數字經濟布局中位居第二, 并出現了騰訊、阿里巴巴大型跨國數字平臺企業,但是由于相關征收國的稅征收認定標準較高,我國跨國數字企業還未納入征稅范圍。 基于此,結合我國減稅降費的背景,我國不具備征收數字稅的條件。但是,考慮到數字經濟的發展對我國稅收治理帶來的挑戰,我們必須在現有的稅收制度框架下,加快完善符合我國國情的數字稅制,確保數字企業與傳統企業稅負相同,促進數字經濟和稅制體系的均衡發展。
從各國數字經濟征稅措施來看,各國對數字經濟征稅尚未達成一致協議,且都存在著一定的單邊稅收保護主義。基于此,我國還要未雨綢繆,積極應對單邊數字稅對我國跨國數字企業的沖擊。要借助雙邊、多邊稅收協定的效力,加強與采取單邊數字稅國家的合作,在協商談判中努力為我國跨國數字企業爭取稅收權益,為跨國數字企業提供更加寬松的國際營商環境。同時,應督促企業將稅收管理上升至企業戰略層面,對于在全球范圍內開展數字經濟業務的企業,應積極應對國際稅收規則的變化。
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穆光宗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我國積極老齡化戰略研究”后期成果
七普數據證實,中國已經掉入 “超低生育率陷阱”,進入低生育時代的中國開啟了人口學意義上的風險社會,超低生育率會引發系統性的社會風險。三孩政策是生育政策優化的進一步體現,雖有重要意義但其提升生育率的作用不可高估。保持近更替水平生育率是實現人口均衡發展、持續發展和優化發展的人口學條件。三孩政策體現了改革的包容性和生育的多樣性,其真實的受益群體應該是極小眾群體。
之所以說超低生育率是未來中國最大的人口風險,是因為它是元問題,也是東西方趨同的人口生育大趨勢。譬如,少子老齡化、人口性別失衡以及空巢化等系統性人口風險的根源全在于生育率的日益走低。所以,發達國家和社會都困擾于低生育,但似乎又很難擺脫。發達國家的超低生育率會引發系統性人口風險。超低生育率一旦形成,就會陸續產生人口萎縮的源頭效應、人口虧損的隊列效應、人口失衡的結構效應、人口一代更比一代少的代際效應、低生育引致更低生育率的內卷效應。
生育的源頭效應類似于上游效應和水龍頭效應,因為生育從根本上決定人口的未來。無疑,超低生育率從源頭上威脅著人口發展的持續性和平衡性。倘若保持目前的超低生育水平,預測的結果是,三百年后中國人口將銳減至2800萬上下,這并非危言聳聽。人口變化是有規律可循的,這是長期低于更替水平且處于超低水平的生育率長此以往必然會出現的人口大雪崩結局,而當下的中國正處在百年人口大變局的前夜。只要人口的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人口負增長的歷史拐點就會到來。從2020年出生量1200萬和死亡量1000萬左右來推算 (兩者已非常接近),未來兩三年內極可能迎來中國人口增長由正轉負、由盛轉衰的重大轉折。
超低生育的隊列效應是指隨時間的推延,同一隊列人口因為死亡的機制而不斷有人退出,“低生育-少子化-少勞化”的邏輯是必然呈現的。現在的青年人口虧損是因為十多年前的低生育,而當下的超低生育率意味著今后勞動年齡人口供給的減少。所以,為防止出現過于嚴峻的人口虧損問題 (尤其是青年赤字和人力短缺),中國需要樹立 “人口儲備”的戰略意識。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張弘
本文節選自《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21年第6期
冷戰結束后,原蘇聯東歐國家在政治上無一例外地都采用了西方國家的政治模式,都實行代議制、三權分立和政黨政治等制度。但政治轉型的效果卻各不相同,有的國家平穩地實現了政治轉型,有的國家則仍處于混亂的政治困境中。烏克蘭的政治轉型歷程較為曲折,經濟上淪為后蘇聯國家中最貧困的國家之一,政治上寡頭政治一直盛行,政治秩序長期混亂,政治腐敗現象泛濫。烏克蘭為政治轉型研究提供了難得的反面案例,不僅因這個國家有著較為復雜的地緣政治環境,還因其寡頭利益集團對國家政權的俘獲和掠奪,導致國家的治理水平較差。
第一,“轉型觀念”決定政治轉型模式。“華盛頓共識”不僅是經濟轉型的模式,在政治轉型上也具有重大影響力。小國家、大市場的自由市場理論也是導致國家政治轉型混亂的重要原因之一。俄羅斯和烏克蘭在20世紀末都形成了寡頭資本主義,經濟遭遇了長達十年的大衰退,而且政治腐敗現象較為嚴重,社會矛盾尖銳,街頭抗議頻發。
第二,資本主義模式是影響國家形態的客觀因素。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斷“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烏克蘭再次得到驗證,寡頭資本主義造就了依附型國家形態。寡頭利益集團對國家權力的俘獲和控制就是寡頭政治。寡頭政治不僅導致憲政民主制度周期性崩潰,而且還威脅憲政民主制度的合法性。當人民失去公平和正義后就會選擇體制外抗爭,街頭暴力騷亂就是對寡頭政治的極端反應。
第三,政治精英是影響國家形態發展的主觀因素。寡頭政治在烏克蘭政治中長期盛行還與烏克蘭政治精英的素質有較大的聯系。政治精英集團的貪婪和平庸使得他們在公共(民族)利益和集團利益之間選擇了后者,主動放棄了國家權力的獨立性。
37225002185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