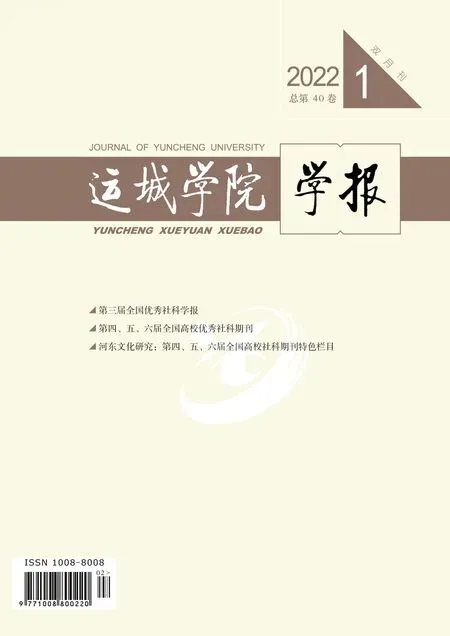論陸機詩之“隱秀”
——兼論“隱秀”特征與其人格精神的內在關聯
馮 佳 佳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西安 710018)
在中國文學史上,對陸機的評價褒貶霄壤,而對其詩歌藝術特征的諸多概括,似皆不如“隱秀”二字恰當。“隱”與“秀”早見于先秦典籍,而“隱秀”并用于文學品評之中,則最早出現于劉勰的《文心雕龍·隱秀》篇:“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奧而派生,根盛而穎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也。隱以復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1]351-352“隱秀”這一美學范疇雖然直到南朝時才提出,然而其所包含的詩歌美學意蘊在陸機的《文賦》中已早見端倪,并成為其詩歌創作中的自覺追求。陸機詩歌的“隱秀”特征,是在其“隱秀”人格的影響之下形成的。以“隱秀”來概括陸機詩歌的美學特征,可以克服單純從技巧方面分析陸詩的片面性,能從創作者的人格特征、精神氣質和創作心態的角度,把握陸機詩歌的真正特征和詩史意義。
一、文之英蕤,有秀有隱
何謂“隱秀”?周振甫云:“隱就是含蓄,有余味,耐咀嚼。秀就是突出,象鶴立雞群,是一篇中的警句。”[1]350詹锳曰:“‘重旨’就是‘復意’,就是說文章要有曲折重復的意旨。”[2]1484“從秀字的本義,《隱秀》篇又引申出兩層意思。一層是秀出,就是‘獨拔’,也就是‘卓絕’,是說它超出于其他部分之上;另一層意思是秀麗,所以才‘譬卉木之耀英華’,或者說是‘英華曜樹’。”[2]1485要之,“隱”即含蓄委婉,曲折多義又韻味無窮;而“秀”則除了有“獨拔”“顯秀”之意,指的是一篇之中的警句,還兼具秀麗、美好之意。“隱秀”即指詩歌作品含蓄深婉又精警遒麗。
就陸機現存作品來看,其詩中大都充滿了濃重的壓抑情緒,或是抒發對時光飛逝的感嘆,或是嘆息盛衰難測、禍福無常,或是抒發功業難成的慨嘆。詩中情感往往來去無端,不知憂從何起,思從何來,少有和樂之作,但情感的抒發大多含蓄委婉,帶有文士的雅正、莊重。比如他的擬樂府詩《董逃行》:
和風習習薄林,柔條布葉垂陰。鳴鳩拂羽相尋,倉鹒喈喈弄音。感時悼逝傷心。日月相追周旋,萬里倏忽幾年。人皆冉冉西遷,盛時一往不還。慷慨乖念凄然。昔為少年無憂,常怪秉燭夜游,翩翩宵征何求,于今知此有由,但為老去年遒。盛固有衰不疑,長夜冥冥無期。何不驅馳及時,聊樂永日自怡,赍此遺情何之?人生居世為安,豈若及時為歡?世道多故萬端,憂慮紛錯交顏。老行及之長嘆!(1)本文中所引陸機詩歌皆引自楊明《陸機集校箋》,后不再重復注明。
開頭幾句寫“和風”“柔條”等春日生機勃勃的景象,筆鋒一轉,忽然感物傷時,嘆息日月相替,人事更迭,盛時一去不還。少年時無憂無慮,壯志滿懷,而如今已垂垂老矣,內心變得凄然悲痛。既然流逝的時光抓不住,那么“何不驅馳及時,聊樂永日自怡情,赍此遺情何之”?然而表面上這樣寬慰自己,卻依舊無法開懷,憂思欲克難克。結尾思緒再轉,由對往昔的回憶回到現實,感嘆世道紛亂,英雄暮年。詩人心情沉重,思緒萬千,情感一直處在起伏的狀態,曲折纏綿,一唱三嘆,但是詩中情感表達點到為止,含蓄克制。故劉勰《文心雕龍·體性》云:“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1]257
世間萬物都能觸發詩人敏感的內心,而這些深沉復雜的情感皆蘊藏在陸詩繁密的意象和典故之中,含蓄曲折,耐人尋味。在陸機的許多詩歌之中,花鳥蟲魚等意象無一不寄托著自己的情感。如“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贈從兄車騎》),“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擬行行重行行》),“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為顧彥先贈婦二首》其二),以孤獸、飛鳥、游魚、晨風和星辰作比,或寄托自己的思鄉之感,或抒發思婦的思念之情。而因其“才多”“才繁”,所用比興亦不落俗套。如“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人生當幾時,譬如濁水瀾”(《擬青青陵上柏》),陳祚明《采菽堂詩選》評此句:“‘濁水瀾’比意亦晦”[3]323。再比如“我若西流水,子為東峙岳”(《贈弟士龍》)一句,巧妙地將眼前之景和腦中之思化為心底之情。有時整首詩皆用比體,含蓄地抒發內心的情感。最為典型的當屬《園葵》一詩:
種葵北園中,葵生郁萋萋。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歲暮商猋飛。曾云無溫液,嚴霜有凝威。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蕤。豐條并春盛,落葉后秋衰。慶彼晚凋福,忘此孤生悲。
通篇以“園葵”自喻,前六句寫葵生北園,似言自己由吳入洛,蒙受君主恩澤,后半篇寫季節遷逝,暗指自己遭趙王倫之難。“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蕤”一句,寫自己為成都王穎所救,心念其恩德。全詩雖用隱喻,但情感婉曲誠摯。
典故的運用也是造成陸詩“重旨”的原因之一,如其《折楊柳行》一詩:
邈矣垂天景,壯哉奮地雷。隆隆豈久響,華光恒西隤。日落似有竟,時逝恒若催。仰悲朗月運,坐觀璇蓋回。盛門無再入,衰房莫苦闿。人生固已短,出處鮮為諧。慷慨惟昔人,興此千載懷。升龍悲絕處,葛虆變條枚。寤寐豈虛嘆,曾是感與摧。弭意無足歡,愿言有余哀。
對于此詩的旨意歷來有不同的解釋,主要的分歧在于對“升龍悲絕處,葛藟變條枚”一句的理解。歷代研究者均認為“葛藟”“條枚”語出《詩經·大雅·旱麓》:“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而對“升龍”一詞則理解各異。曹道衡認為“升龍”的典故出自《史記·封禪書》(2)“升龍”:《文選·張衡<西京賦>》:“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李善注《史記·封禪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曈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后宮從上者七十度馀人,龍乃上去。”,“升龍”即指天子,此句指帝王升遐,故此詩當作于晉武帝薨后,元康初年賈后殺楊駿之時。(3)詳見曹道衡.陸機的思想及其詩歌[J].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6(1).而郝立權則持有不同觀點,他在《陸士衡詩注》評此句:“其感于趙王倫篡位之事乎?”[4]楊明則繼承此觀點并進一步解釋。他指出魏晉時期的詩歌中“升龍”一詞“皆泛指君子之出處行藏言,不專指圣人、天子”。“趙王倫廢賈后,殺張華,旋即篡位,張華于陸機有知遇之恩,機頗敬重之,而又不得不順應趙王倫;倫誅,機為齊王囧下獄。是其進退失據,不知所依之心情可以想見。此詩正反映此心情,而不必定其為何事而作。”[5]406故認為本詩作于趙王倫篡權之后。或暗指西晉朝堂的動蕩多變,或感嘆自己進退兩難的艱難處境,此即所謂“重旨”。壓抑難言的情感蘊藏在模糊多義的典故之下,使得詩歌整體呈現出一種含蓄深蕪的風格。
對于文章的布局而言,警句秀出于全篇,是詩文中最出彩的地方。陸詩中的警句隨處可見。如“攬衣有余帶,循形不盈衿”(《擬行行重行行》),通過描寫衣裳來表現人的消瘦,側面突出對遠行人的思念。陳祚明《采菽堂詩選》曰:“‘攬衣’二句,秀琢。”[3]321又“輕條象云構,密葉成翠幄”,“山溜何泠泠,飛泉漱玉鳴”(《招隱》)兩句,十個字就勾勒出一幅清新秀麗的山間隱逸圖。陳祚明評:“‘輕條’二句,新秀。‘山溜’二句,警亮。”[3]324再如《擬東城一何高》中的“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楊明注引王闿運語:“詠露至此,亦是一奇”[5]325。不少詩句不僅深刻警策,而且妍麗精工,當真稱得上佳句。如《擬青青陵上柏》中:“飛閣纓紅帶,層臺冒云冠”,運用“纓”與“冒”兩個動詞,將臺閣宮殿的壯美錯落描寫出來,動靜結合,筆下的洛陽繁華景象都變得鮮活生動起來了。再如《擬西北有高樓》中“芳氣隨風結,哀響馥蘭若”一句,以聲比色,香氣如蘭,清商幽發,于華美之外又加入藻思,全篇雅致妍麗。陸詩中的秀句,雖不至于膾炙人口,但仍對后世產生深刻的影響。如“別日何早會何遲”(《燕歌行》)一句,后世梁武帝《丁都護歌》有“別日何易會日難”,李商隱《無題》詩有“相見時難別亦難”,均從陸機此句化來。再如“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為顧彥先贈婦詩二首其一》),后世謝朓“誰能久京洛,淄塵染素衣”(《酬王晉安詩》)正用此也。
陸機不僅重視詩中個別句子的精致完美,而且追求詩歌整體的自然混融。《文心雕龍·隱秀》篇開篇即言:“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可見“隱”與“秀”是一對并蒂蓮,是一株英蕤的兩個方面,好作品要同時兼具這兩種特質。而“隱秀”亦不是“隱”與“秀”的簡單疊加,詩歌缺少秀拔之句就易流于平淡和深蕪,而一味追求秀句,破壞了詩歌整體的和諧,則會導致文辭浮艷雕琢,唯有二者自然融合,篇與句連、氣韻混成方為“卓絕”之秀句。陸機雖未在自己的美學思想中明確提出“隱秀”理論,然而他作為“隱秀”審美觀念的先行者,其文學創作中已經出現“隱”“秀”兼具的佳作了。如《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二:
遠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幾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詩人入洛途中跋涉山川,旅途艱辛。夜晚抱孤影而眠,白日于巖石之下駐足,聽風吹山林之聲,內心充滿無限的鄉思之情。寧靜的夜里月光澄澈,晶瑩的露珠靜靜地墜落。然而他的內心深處并不似這夜晚般寧靜,離鄉已遠而前路未知,孤枕難眠,只能起身撫衣,獨自冥想。通篇未見一字提到“離別”和“故鄉”,情感抒發含蓄克制,但是思鄉之情已溢滿全詩。“清露”四句造語秀拔清新,為全詩之警句,詩歌意境自然混融又韻味無窮。
二、“隱秀”:陸機詩歌與人格的共同特征
詩歌風格的形成有多種因素,而詩人的人格精神對詩歌的內在氣質和外在特征的影響不可忽視。聯系時代背景來分析,可以發現陸機一生都在“隱”與“秀”之間游走,其詩的“隱秀”特征與他四十年的人生行跡相呼應,是他“隱秀”人格的映射。以“隱秀”來概括陸機詩歌的美學特征雖然不同于以往人們對陸機的諸多評價,但實質上卻是對陸機詩歌和人格的真正理解和精準把握。
陸機出身于江東望族,“少有異才,文章冠世”[6]1467,憑靠先天的家族優勢和自身極高的文學天賦而“獨步江東”,是當之無愧的“東南之寶”。他文武兼修,在父親死后與族內兄弟“領父兵為牙門將”[6]1467,似初生英甤挺秀于江東之地。少年人的豪氣和慷慨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可以窺見一斑。在《辯亡論》中,他以壯闊之筆敘寫漢末群雄并起的情形:“于時云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群風驅,熊羆之眾霧集。”又以闊筆描寫赤壁之戰的過程:“魏氏常籍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4)姜亮夫判定《辯亡論》為陸機未入洛前的作品,約作于晉武帝太康九年。詳見氏著《陸平原年譜》第38頁,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本文采用此觀點。氣勢浩大,鋪張揚厲,描寫吳國得江東、成三國鼎立之勢的歷程,頗有漢賦之風。
西晉平吳是陸機的人生轉折點,往日英姿勃勃,意氣風發的天驕少年變為“亡國之余”,而吳國的滅亡不僅使陸機“被服冠帶麗且清,光車駿馬游都城”(《百年歌》)的個人理想破滅,也使陸氏這一文武兼修、忠貞義烈的百年世族由盛而衰,這對具有強烈的家族意識的陸機無疑是一種沉重的打擊。遭此劇變的詩人雖未在詩中表現出明顯的悲痛,但殘酷的現實和巨大的落差不能不對他敏感的內心產生影響。在這種難以承受的痛苦中,年輕的陸機、陸云毅然承擔起入洛求仕以重振家族的重任。在當時的情形下,“吳人進入仕途或憑借特招,或憑借干謁顯貴以引薦。”[7]故二陸只能“退臨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6]1467,通過修習才學來獲得機會。陸機在華亭期間的具體文學活動不得而知,但通過《文賦》中的只言片語可以窺探到其當時的狀態:“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凝神寂慮、摒除見聞,內心逐漸走向虛靜,以專注之心久立天地之間,潛心典籍之中,在無形無聲之中的清虛之境索求精妙之文。曾經慷慨張揚的江東少年變為潛心典籍、閉門苦讀的亡國文士,漫長的修學歲月逐漸養成了陸機“隱”的人格特征。《說文》曰:“隱,蔽也”[8]。《爾雅》曰:“瘞、幽、隱、匿、蔽、竄,微也”[9]37。“隱”有隱蔽、不顯露之意,故可以用來形容心靈的虛靜幽深和精神氣質的深沉內斂。
入洛后的陸機置身于動蕩不安的西晉政壇之中,在不同的政治勢力里游走,如履薄冰,其內心世界愈發復雜幽深,詩中的情感也變得更為曲折深沉。晉武帝死后,朝堂愈發動蕩,先是權臣外戚相爭,而后又是宗室傾軋。元康元年,賈后誅汝南王亮及楚王瑋,持續十六年的“八王之亂”爆發。世道離亂,朝政混亂,文士多遭殺戮,難以保全自身。在這樣一個僅持續五十多年卻殺戮不斷的朝代,陸機身處于政治權利的漩渦中心,即使內心有再多生的憂慮和死的恐懼,也難以奏出過于激昂、直抒胸臆的聲音,其心曲只能百轉千回地傾瀉于詩歌創作之中。如其《猛虎行》一詩: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饑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崇云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弦無懦響,亮節難為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開頭四句故作壯語,頗有一股浩然剛毅之氣。而后轉慷慨豪壯為沉吟低徊:“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生逢亂世,世無明主,他當然明白要苦守心志,然自己遠離故土而羈旅多年,心懷壯志,又如何能輕易退卻,故隱忍而迫于時命。仕途之路艱險困難,如在野獸滿布的地方生存,而日月空馳,風云變幻卻功業難成,進不能伸志,退不能保節,內心充滿了悲憤無奈。忽筆鋒一轉,氣勢減弱,情感收斂,欲噴薄而出的傾訴只剩下嗟嘆:“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自己終究屈于世俗,世網嬰身而愧對古人,立于這種處境之中,如何能將胸襟打開?全詩情感郁勃卻又極盡克制,讀來竟有沉郁之感。
除了表示隱晦、隱蔽外,在中國傳統思想中,“隱”還具有“蟄伏未發”“伺機而動”的人格美學內涵,即當現實情況不理想時,能夠隱伏起來,保存自身,積聚力量以到達自身的理想狀態。《周易》有云:“天地閉,賢人隱。”[10]32又“初九曰:‘潛龍勿用’。”[10]2《論語·泰伯》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11]這種隱顯舒卷是千年以來君子立身處世的法則之一。華亭十年是陸機一生中最重要的時期,在這十年間,他閉門修學,韜光養晦,伺機而動,無疑有“隱伏”之意。而從人格美學的角度來看,“秀”則可以表示人格的超拔和能力的出眾,內涵與“現”“顯”相似,有“顯露”之意。秀的本義是谷物抽穗,《爾雅·釋草》:“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9]265《廣雅》:“秀,出也”。[12]后逐漸引申為秀出、秀拔等意義。中國古代哲學中有“以‘隱’致‘顯’”的思想,其淵源可以追溯到《周易》中卦爻的變化。《易傳·系辭上》有:“探賾索引,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兇,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10]289-290《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13]以“隱”為基礎,能夠使幽深隱晦的事物彰顯出它原本的深奧與博大。而“隱”能致“顯”,亦能致“秀”。這樣看來,“隱”“秀”二字并非是簡單的并列關系,“隱”是潛藏的、蟄伏的,“秀”是超拔的、顯露的,而“隱”又能致“秀”,故二者是相反相成的。陸機修習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挺秀于西晉文壇,以文進仕。而華亭十年雖然漫長沉寂,但無疑為他日后入洛后“譽流京華,聲溢四表”[14],“文藻之美,獨冠于時”[15]打下重要基礎。
陸機這種“隱秀”的人格特征對其美學思想和詩歌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文賦》云:“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平凡的山石河川因蘊藏著璞玉而寶珠而光輝秀媚,沉寂的華亭故里因隱伏著二陸而名聞天下,故表面上看似平淡的文字也因其潛藏的佳句而大放光彩。陸機以“玉”和“珠”來比喻文章中的秀句,主張詩文中要有警策之句。他在《文賦》中提出:“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強調警句的重要性。陸云《與兄平原書》亦云:“《祠堂頌》已得省。兄文不復稍論常佳,然了不見出語,意謂非兄文之休者。”[16]301“出語”相當于警句,即指出陸機詩歌創作注重警句安排。而“玉”“珠”的產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經過“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收視反聽,耽思傍訊”,“傾群言之瀝液體,漱六藝之芳潤”等一系列的準備工作,方可產生“苕發穎豎”的秀句,這無疑另一種意義上的以“隱”致“秀”。
陸機一生的思想發展和詩歌創作都與其內在的人格精神有密切的關系,他在三國歸晉的特殊時代背景之下所形成的“隱秀”人格,進一步影響其美學觀念,使“隱秀”逐漸變為他在文學創作中的一種自覺追求。
三、陸詩“隱秀”之美的詩史意義
陸機之前,曹植憑借其“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17]117-118的詩歌美學特質,獨冠于“彬彬之盛,大備其時”的建安詩壇,開創了一代“壯美”詩風。“壯美”中的“壯”一方面指曹植詩中充滿風力和骨氣,豪壯慷慨又情悲意壯。另一方面,“壯”又指詩中情感充沛。陳祚明《采菽堂詩選》云:“真切情深,子建所長。”[3]163方東樹評曹植詩:“情之美性。至語,千載下猶為感激悲涕。”[18]在做到“骨氣奇高”和情感充沛的同時,曹詩又辭藻華麗,聲色和諧而不流于粗豪,故在“壯”之外,又兼具“美”。在他的詩中,既有充盈天地之間的宏偉壯麗,又有遨游八荒的縱情恣肆,具有一種壯美的美學品格。
鐘嶸對曹植評價極高,稱其為“建安之杰”,甚至把他比作文學領域的周、孔:“陳思之于文章,譬人倫之有周孔,麟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17]118而鐘嶸認為陸機的詩歌承繼于曹植,《詩品》:“其源出于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美”[17]162。他以“太康之英”來評價陸機,將陸機和曹植并提:“故知陳思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17]34這表明在鐘嶸看來,曹、陸二者在詩歌成就和詩歌貢獻方面具有相似性,都是一定時期內超越其他詩人而存在的杰出者。陸機確實在用詞、煉字、追求聲律和對偶等方面受到曹植的影響,其《門有車馬客行》《日出東南隅行》等篇目皆有模擬曹植的痕跡,學界對此早有論述,在此不再贅述。然陸詩雖脫胎于子建之詩,卻在繼承其詩歌特質的基礎上,獨辟詩歌“隱秀”之美,開一代詩風之先。
將曹陸二人的詩歌進行對讀,可以明顯感受到“隱秀”與“壯美”不同。曹詩中情感慷慨激昂,直抒胸臆,而陸詩在情感表達方面更為含蓄內斂。如將曹植《門有萬里客行》和陸機《門有車馬客行》相比,前者質樸,頗有樂府民歌之感,情感簡單、直白;后者在描寫上則更為繁復,講求辭藻和鋪陳。“拊膺攜客泣,掩淚敘溫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凋喪。”陸詩雖為擬作,但是詩中滲透著陸機濃重的身世之悲,相比曹詩而言,情感更為深沉悲郁,克制壓抑。更為重要的是,“壯美”更偏重于一種健美英朗之感,氣勢上慷慨剛健,文采上富麗宏博,是一種直白,華麗的美。而“隱”表示情感的含蓄婉轉,“秀”有清秀拔俗,纖巧清麗的感覺。與“壯美”相比,“隱秀”更強調內在精神氣質和風致氣韻的婉轉風流。比如同為描寫女子的《美女篇》和《日出東南隅行》,二者均源自古樂府詩《陌上桑》,但是各自卻呈現出不同的風貌。曹植的《美女篇》描畫了一幅“美女采桑”圖,依次描寫美女衣袖下的素手,身上佩戴的各色飾品,以極其濃烈的色彩塑造了一個亮麗華貴的女子。這位美好的女子不僅有艷麗的外表,又頗具豪氣,為追求高義之人而遲遲不肯婚嫁,然而深夜又憂愁遺憾,獨自嘆息。詩作中的美女是詩人的化身,他如筆下的佳人一般內外兼修,心懷壯志而追慕道德高尚的人,卻始終難以在政治上實現自己的理想,故詩中托美女以自喻,言語之間頗具一股傲然、高貴之感。較之曹植的《美女篇》,陸詩致力于以繁密之筆來描寫佳人的美目、蛾眉、鮮膚以及儀態與神情等等,又不厭其煩地對佳人們的舞姿進行刻畫,在遣詞造句方面比曹詩更為精雕細琢,詩歌中自有一種細碎之美。他連用六個“清”字,又兩次以“清川”“清湍”來寫美人之倩影,筆下的佳人容顏清麗,性情嫻靜,柔情似水,于光澤明艷之中更添幾分婉約沉靜。陳祚明《采菽堂詩選》稱此篇“撰句矜秀”,“較陳思饒靜氣”。[3]301
陸詩的“隱秀”與曹詩的“壯美”從外在形式看是詩歌美學風貌的不同,其實質則是二者人格特征和創作心態各異。曹植生活在任性縱情,酣暢人生的建安時代,其詩大都辭藻華美,筆法多樣,筆調慷慨酣暢,情感激烈外放,這與他身上積極進取的精神、崇高的精神品質和難以企及的生命強度高度契合。而隨著三曹、七子的相繼離世,悲歌慷慨的建安時代逐漸落下帷幕,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正始詩人登上了詩歌發展的舞臺。險惡的政治環境和玄風的逐漸盛行使正始時期的詩人不復建安詩人的激情和豪壯,他們在對哲理玄思執著追求的同時,也使詩歌逐漸走向曲折隱晦。陸機詩歌的含蓄深婉,正是受到了正始詩風的影響。建安時期的慷慨悲涼與抒情外放,經歷了正始這一充滿哲思、清虛玄遠的時代沉淀,最終在西晉的政治土壤中變為陸機詩歌中的“隱”,昔日詩文中風流自賞的“三河少年”亦變成了虛靜深沉,頗有憂生之嗟的憂患士人。
顯然,陸詩是在建安詩歌和正始詩歌的共同影響下形成的,是對二者的吸納和繼承。他一方面發展了建安文學重藻飾、重形式的傾向,致力于對詩歌外在形式技巧的探索;另一方面延續了正始詩歌的曲折隱晦,將詩中的情感表達得含蓄深婉,從而形成了精警遒麗,含蓄深婉的“隱秀”詩風。而其描寫自然景物時的清麗筆調,又使陸詩于富麗之中帶有一股清新之感,影響了后世謝靈運等人的山水詩創作。
陸機筆下常有片段式的清澄詩境出現。在《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二中,詩人描寫了一個月朗風清的夜晚:“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靜謐的夜晚,月明如水,晶瑩純潔的露珠在夜風中墜落,營造了一個清冷素潔的意境。再如“山溜何泠泠,飛泉漱玉鳴。”(《招隱詩》)輕快的山泉水擊打在山中巖石之上,發出如玉盤般的泠泠輕響。整幅畫面色調清淡,聲音清越,一股清涼之感撲面而來。陸詩中多用“清”“素”“寒”等字眼,如“和氣飛清響,鮮云垂薄陰”(《悲哉行》,“素秋墜湛露,湛露何冉冉”(《猛虎行》)。以“清”字為例,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共收陸機詩109首,僅帶“清”字的篇目就有32首,其中不乏一首詩中重復出現,如《日出東南隅行》一篇,全詩共用了六個“清”字。雖然陸詩中的一部分“清”并非用于山水景物的描寫,但是在中國詩歌史上如此大規模、頻繁地使用“清”字的現象還是第一次。而一些作品即使全篇不見清寒意象,也同樣具有清新之感。如《班婕妤》一詩中最后四句:“春苔暗階除,秋草蕪高殿。黃昏履綦絕,愁來空雨面。”造語清麗,婉秀如南朝宮怨詩。陸云曾評價陸機的文章:“兄文章之高遠絕異,不可復稱言,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耳。”[16]304
魏晉以來,雖然自然景物開始較多涌入詩歌之中,如吳喬所言:“十九首言情者十之八,敘景者十之二。建安之詩,敘景已多,日甚一日。”[19]33但是其大多仍作為抒情言志的工具,未成為獨立完整的審美對象。正始時期,嵇、阮筆調湛然澄凈,嵇康的“目送歸鴻,手揮五弦”已經體現出類似后世山水詩中超然玄遠的意味,然其二者側重在作品中塑造自己內心逍遙清虛的世界,詩中明秀蕭然的山水景物意象較少。但虛靜朗澄的心境無疑是發現自然之美的必要條件之一。“人只有達到忘卻自我的境界,才能認識‘天籟’,這一說法已經為后世的山水審美觀奠定了哲學基礎。”[20]“晉人以虛靈的胸襟、玄學的意味體會自然,乃能表里澄澈,一片空明,建立最高的晶瑩的美的意蘊。”[21]361陸機正是在近似于“坐忘”境界的“隱”中去感悟自然。他“佇中區以玄覽”,在“收視反聽”“耽思傍訊”中“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宗白華說:“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21]368悲郁的詩人借景物之變來抒發自己內心壓抑的情感,進而對季節遷逝、宇宙人生生發出無窮的悲哀,而在這無窮的哀嘆之中也發現了山水的清新秀麗。
結語
陸機以其作品篇章之富,詩歌水平之高達到了當時文壇的最高水準,成為太康詩風的杰出代表。然而詩歌史上對這位“太康之英”卻褒貶不一,爭議頗多。六朝和隋唐時期人們對陸機的詩歌普遍有較高的評價,自宋以后,批評的聲音逐漸增多。不少評論家在肯定其“才高詞贍”的同時,認為陸詩情感貧瘠,缺少真實感情的抒發,而對于功名的過分執著也使得其不為大多文士所推崇。然所病即所長,圍繞陸機而產生的贊賞與理解,批評與歧誤,都側面表現了其詩在魏晉六朝詩歌發展過程中無法忽視的作用以及其沉靜內斂、深邃宏博的人格魅力。作為曹植之后的又一位詩壇冠冕,陸機在繼承曹植詩歌的基礎上又進一步超越和創新,將自己生命中的獨特經歷、文學個性以及時代氣質融入詩歌創作之中,最終形成了陸詩獨特的“隱秀”之美而凌凌乎秀出西晉諸家之上,對后世山水詩創作亦產生了久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