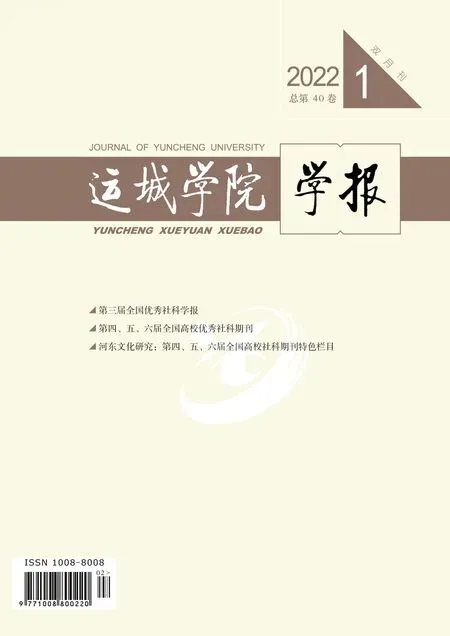“天人不相預”“天人相濟”與唐宋儒學進路
張 麗
(運城學院 中文系,山西 運城 044000)
天人關系是中國哲學和文化中的重要和基本的命題。天人關系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提出展開與當時社會的主要問題息息相關。在唐宋時代特殊的語境下,柳宗元和司馬光分別提出了“天人不相預”和“天人相濟”,其天人觀既代表對當時普遍問題的關注,也表達出一定的知識理性和政治理性,共同構成了新儒學發展很重要的基點,影響宋學深遠。
這一時期思想文化領域的成就賴于眾多思想家在歷史變革的合力下共同推動,但兩人的貢獻尤為突出。柳宗元以元氣論為天人觀的哲學基礎,極大消解了漢儒以來的神學觀,對理學的氣本論有直接的影響,其出入三教的思想也啟發理學的體系建構。司馬光游離于理學宗師的身份,與北宋五子相比,理學體系建構尚薄弱,但其思想如“天人相濟”,實以禮為內核,長其善而去其惡,以學治心等,極富有理學精神,在理學發展過程中不容忽視。宋史學者漆俠高度評價司馬光:“在經學上的成就足以成家,對宋學的發展也產生了重要的作用。”[1]366
柳宗元和司馬光的天人觀在唐宋思想領域較為突出還在于他們不僅僅是思想家,更是仕宦經歷豐富的政治家,有較高的政治視野和學術地位,其天人觀的闡述不只是思辨領域的推進和理論建構,而是體現出鮮明的政治理性和現實政治的實踐性,有助于儒學發展起非止于倫理本體的內省之學,向經世致用開發。因而本文的論述重在探討兩人是在什么樣的立場和語境中闡述天人觀,又以何種方式踐行他們的天人思想;他們在政治主體精神高漲、政學兼行、自覺的哲學思辨意識等方面雖有相似之處,但對天人關系的知行存在理論的分野,對這些問題的分析期望有助于深化唐宋儒學發展的內在理路。
一、天人不相預與天人相濟
(一)柳宗元“天人不相預”的思想淵源
柳宗元在《答劉禹錫天論書》中提出“天人不相預”的觀點,云:“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2]503,此說認為,生植與災荒出自“天”,而法制和悖亂當屬人事,兩者互不干涉,各司其職。“天人不相預”觀點與柳宗元對天的認識密切相關,他在《天說》《天爵論》《時令論》上下、《斷刑論》及《貞符》并序等篇目中都闡發了對“天”的認識。《天爵論》云:“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2]51,《天說》云:“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2]286,《天對》中認為天地未形成之前,“曶黑晣眇,往來屯屯,龐昧革化,惟元氣存”[2]228,提出了“惟元氣論”,即天和萬物一樣,都是由元氣構成的,強調天是一客觀存在的物質實體,不可能有意志,有道德屬性來主宰人類社會,更不具備賞功罰過的能力,因而人非受制于天。可以發現,柳宗元天人觀的闡釋中,“天”的范圍較以往有所縮小,“人”的范圍和作用卻擴大了,肯定天人各自的運行規律,否定和剝離了天的神秘性,對人類歷史的發展進化有更客觀的認識。
從思想淵源來看,荀子的天人相分和王充元氣自然論都對柳宗元有借鑒意義。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著名論斷,認為天有自己的運行規律,人要“明于天人之分”,才不會對天寄予無妄的依附。荀子還進一步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即不是隔絕天和人,而是說人可以通過有意識的社會行為發揮主觀能動性,對自然和社會產生作用,進而使“參于天地”成為可能。柳宗元明顯受到荀子的影響,《封建論》中說:“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2]44,在天人觀問題上柳宗元很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王充的天人論思想對柳宗元也產生了較大影響。《論衡》自然篇中王充提出天道自然即無為,以萬物之生,皆稟元氣,以此質疑“天人感應”和“君權神授”。王充這一思想無疑動搖了天命論的神秘和政治權威,援引道家思想探索天之自然性的理論思想對柳宗元亦有啟示意義。不過王充對天的認識尚不清晰和深刻,在反對天人神命之說的問題上,并未明確指出漢儒的價值根源一歸于天這一關鍵點,消解天人感應的同時未能自覺追尋新的價值之源,且對孔孟原始儒學心性論發展甚少。
“天人不相預”提出的語境。柳宗元的天人觀產生于安史之亂后復雜的社會文化環境下,代表著當時文儒對自然和天命、天道和人道等持續性命題新的思考,在與韓愈、劉禹錫等人的論辯中柳宗元進一步豐富了天人思想。韓愈對天的看法似不確定,既有自然性的一面,如《原人》中說:“形之上者謂之天,形之下者謂之地”,又有明顯的天命意識,《與衛中行書》云:“凡禍福吉兇之來,似不在我。”[3]217韓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天有賞罰功能,人道對天道無能為力。柳對此說進行反駁,云:“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2]286柳宗元對韓愈的駁論主要在于,柳認為天地元氣陰陽亦是自然物質,并不具備賞功罰惡的功能,否認推天引神說,據此,人事禍福非天人感應,功者自功,禍者自禍,這是人發揮主觀能動性進行社會行為的結果。韓愈重視“天”的權威神性,柳宗元則重視人之現實主觀性。在批判天意、天命神學論上,柳宗元和劉禹錫是高度一致的,都認同天道和人道有不同的運行規律,但劉認為天與人是“交相勝”的。柳宗元正是在對此說的回應中,提出天人各行不相預的觀點。《答劉禹錫天論書》云:“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為惡,人恒為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與人為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其事各行不相預”[2]503,稱劉說有“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之嫌。
以柳宗元、劉禹錫等為代表的天人觀折射出中唐士人較為進步的社會歷史觀和對一些社會思想及現實問題的批判思維。任繼愈先生對此高度評價,“(中唐)通過對當時天人關系的討論,把人們對天命觀的懷疑和否定引向對漢以來整個儒家經學傳統的懷疑和否定。”[4]534他們天人觀的認識和討論實際上推進了中唐的儒學轉型。
(二)司馬光的“天人相濟”
“天人相濟”的內涵。司馬光對天的認知有些矛盾,既認為:“天者,萬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違……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5]1504此說充滿天命論色彩,但司馬光論天又有自然性的一面,《潛虛》中提出“虛”和“氣”。在天人關系上,司馬光非唯天命論之。對天命的理解上,司馬光基本與孔子重人事,輕天命存而不論的思想一致,《原命》中說:“夫天道窅冥恍惚,若有若亡,雖以端兆示人,而不可盡知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是以圣人之教,治人而不治天,知人而不知天。”[5]1402《迂書·天人》中說:“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斂藏;人力之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5]1508,提出“天人相濟”思想。司馬光既相信天命的決定作用,又認為人不是完全被動的,人有主動適應改變能力,此說是在不否定天命的前提下,不否認人為,極大降低了天命之為的偶然性和任意性。“天人相濟”不同于天人感應。天人感應思想集中體現于董仲舒的學說中,董仲舒認為:“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遵也。”(《春秋繁露·郊義》)[6]541“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春秋繁露·玉杯》)[6]33將天神秘化、人格化和道德化。董仲舒還提出:“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類相動》)[6]484從同類相動、物類相應等說明天人一也,來彰顯天的意志。
司馬光天人相濟思想與《易經》在宋代的發揚密切相連。《易經》說的“道”異于老子、孔子之“道”,包涵會通天道人道且生生不息的宇宙觀和辯證思想,此思想在宋儒之前并未受到重視。宋儒大多表現出對易學的關注,注易成風,但大都淡化思辯色彩,這與他們以易學義理重建儒學的努力不無關系。受此影響,司馬光提出天人相濟的天人觀有兩層哲學內涵:
第一層,在天人問題上,司馬光沒有把天進一步神秘化,而是發揮易學推天道以明人事思想。司馬光撰寫《易說》三卷,《系辭》兩卷,認為王弼對周易老莊式的玄渺注解并未切近易之微言大義,司馬光從天地人會通角度解說周易,并進一步闡發其天人觀,《溫公易說》云:“天以陰陽終始萬物,君子以仁義修身,以德刑治國,各有其事也”[7]28,他對易說“出于天,施于人”的思維特征有深刻的認知,強調人事也有主觀能動性,突出人的價值。
第二層,從司馬光的天人思想可以看出,宋代思想家在復興儒學過程中,在思想領域一直探索儒學新價值和現世倫理秩序的本體層面依據。張岱年先生說:“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宇宙的第一原理也就是道德的最高準則,認識真理的方法也就是道德修養的方法,這在先秦儒家、道家的學說中,在宋明時代的哲學中,表現最為明顯。”[8]125司馬光天人相濟的天人觀是包涵道德維度的宇宙觀,其話語系統就成為一種被設定的和諧。在對天的理解中,司馬光提出“虛”,云:“萬物皆祖于虛”[9]295,又由虛派生出氣、體、性等,司馬光認為虛不僅僅是萬物生化的時空幻境,而且具有本源本體的性質。虛與極同,“易有太極,極者,中也,至也,一也。”[7]77對于人道之本體“虛”的指向,司馬光又提出“其惟綱紀乎,綱紀立而治具成矣”[9]296,內涵天人秩序的一致性。通過人道對天道模擬,司馬光在對天人關系認知和發展中建立起道德最高準則的理論進路,建立起現世倫理政治秩序之本體論基礎。
與柳宗元重視天的自然性,非所以盡天人之際相比,司馬光思想中,天既有自然規律的意義,又有道德標準的涵義,并且司馬光更重視天道的秩序,將天道、天理融入德性道義,從天道世界觀人生觀的精神空間和實踐意義上重塑儒學。
“天人相濟”提出的背景和意義。司馬光對天人關系的闡述蘊含北宋中期內憂外患下的探索。有學者指出:北宋思想體系建立集中于兩點,一個是要為統一社會成員的意志以配合政治上的高度集權專制,找到神圣性的最高依據,提供哲學理論的證明;再一個是理想人格的培養。[10]155司馬光復興儒學的抱負,是基于鮮明的抗衡佛教,維護儒學主體的立場,他對天道恒常的思想承繼包含著對當時現實政治絕對合法性的支持,這對穩定北宋政治秩序是有現實意義的。從“天人相濟”可看出,與其他宋儒重視精神世界的內省不同,司馬光更重視具體現實情境中人道對天道的踐行。司馬光反對北宋前期官場佛道思想彌漫,儒家事功精神缺失的時風,認為不能摒棄現實生活,尋求非理性的超越。在《顏太初雜文序》一文中他闡釋自己對“儒”和“所求之道”的看法,提出真正的儒士是要有儒家精神的,不僅要學道,而且要踐行之,達到自我實現和經世致用。司馬光的政治實踐尤為重視人倫和維護封建統治,以重振儒學為出發點,構建社會應然的理想體系,在這個方面看司馬光的天人觀實際上為封建社會后期的等級秩序和政治社會提供了理論根據和哲學基礎。
柳宗元“天人不相預”和司馬光“天人相濟”天人觀的表述看似矛盾,但從儒學思想螺旋式的上升來說,兩者都是儒學發展的重要節點。我們知道北宋中期儒學復興上承中唐而來。宋人繼承了中唐文儒力求擺脫經學束縛,打破天命神學的桎梏,著意建立利于解決現實問題的思想理論內核。兩人的天人觀體現出唐宋思想家緣于深厚的政治理性和知識理性來探索人道天道問題,從儒學內部進行反思和革新,并且對佛道思想都有批判借鑒,因而能生發新的理論視野和現實意義。
二、兩人天人觀內在理路的差異
(一)柳宗元重“勢”
柳宗元繼承發展了自荀子、王充以來的元氣論,并充分利用唐代自然科學的成就提出新的天人觀,與其天人觀相呼應,柳宗元提出“勢”。《封建論》中柳宗元云:“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2]43柳宗元將封建這種人類歷史的發展變革,歸因為非圣人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使然,是勢也,并說“勢”體現的是“生人之意”。之前的思想家對勢也有所認知,如《孟子·孫丑上》:“雖有智慧,不如乘勢。”《老子·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這些勢論都側重客觀形勢,外在環境。相形之下,柳宗元對勢的理解更具有哲理性,是認識論上的極大提升。在柳宗元的其他論著中,也貫徹此思想,《天說》:“功者自功,禍者自禍”[2]286,可視作對“勢”的注解。《非國語·三川震》更是連用八個“自”,“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游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2]748來說明自然萬物的形成變化都有其客觀規律,非承天的意志而來。結合“勢”可以更清晰的看出柳宗元天人論的主要思想是強調社會現象的內在動力在于人自身,所以不能依賴于“天”。“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詳于天。”[2]22柳宗元認為變禍為福,易曲成直,不在天命而在人力,人力可為,但亦有所不為,為與不為就需要大中做指引。“圣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2]55柳宗元認為要尋求真正的圣人之道、大中之道,需重振以仁義為核心的五常,并據此作為人事的原則駁斥漢儒的祥瑞災異論,“茍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圣人之道,不亦遠乎”[2]53。
柳宗元強調天之客觀自然,人之主觀能動,將兩者置于互不干涉的領域,這與他在現實政治中跌宕起伏的經歷和力求改變言天不言人的治政原則分不開。在《貞符》中柳宗元云:“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2]18從歷史背景來說,柳宗元的天人思想反映了中唐以降伴隨著傳統貴胄的衰落,中小地主階層想要獲得政治話語權,推進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呼聲。他認為要發揮生人之意去革新政治而非延續天命史觀、英雄帝王史觀的以威以怪來繼續強調等級和特權統治。
(二)司馬光天人思想之遵“禮”
禮是貫穿司馬光史學經學思想的核心,司馬光以禮統攝萬物,思想中多處提及禮的價值功能和現實意義,認為“國家之治亂本于禮,而風俗之善惡系于習”(《謹習疏》)[5]603,“禮法者,柱石也”(《司馬光集·進五規狀》)[5]536,在司馬光看來禮規范社會秩序,是綱紀,是等差,尊卑之義也是禮之本,維護禮就是維護等級秩序,就是立綱紀。《溫公易說》中云:“禮者,人所履之常也……夫民生有欲,喜進務得而不可厭者也,不以禮節之,則貪淫侈溢而無窮也。是故先王作為禮以治之,使尊卑有等,長幼有倫,內外有別,親疏有序,然后上下各安其分而無覬覦之心,此先王制世御民之方也。”[7]19司馬光重視以禮維持君臣士大夫和庶民之間的尊卑有序,進而建國馭民發揮重要的政治功能。
不僅如此,司馬光認為禮代表社會秩序的最高原則,對禮經世致用的功能認識與其天人觀結合起來,便是以人道補充天道,通過禮制途徑,恪守禮,使天道在人道的實現成為可能,這樣禮就具有了自然秩序和社會秩序的雙重意義,將禮內在的社會規范道德特質提升至宇宙本體普遍性的意義。正如有學者評述:“司馬光著眼于天人之合,一方面援引天道論證人道,另一方面又按照人道來塑造天道,因而在他的天道觀中蘊含著人文的價值思想,在他的人道觀中蘊含自然法則的客觀依據,天人不二,相互滲透……”[11],司馬光通過禮實現了天道與人事之間相互滲透,達到了宇宙論、方法論、價值論的統一。
司馬光不僅從道的高度研究禮的精義,而且嚴格履踐禮,在建立和推行禮的內在機制上,司馬光認為“治國首先正人君”,奏章《三德》中云:“臣竊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仁君之仁也……”[5]527,諫言皇帝要按照禮的要求來修德治國,“上行下效謂之風,熏蒸漸漬謂之化”。這是封建社會后期,權利高度集中的絕對君權趨勢下,對君權的限定。司馬光認為政局的長期穩定真正依靠的是德,這是非先天命定的,司馬光特別強調統治者的道德影響和表率作用,即以統治者的德行感召力推動王道政治的運作,而不是單純的利用權力和法規,這樣就把道德教化與政治運轉相連,也是儒學從禮樂思想的經典形態向道德規范轉移的表征。
前代的禮治教化主要對應貴族,隨著唐宋社會階層間的流動和變動加劇,禮從士庶天隔,不下庶人向庶人階層日常生活滲透。司馬光尤為重視家禮民禮,《居家雜儀》《溫公家范》中儀禮記載均為日用切要,謹言慎行之事。與以往家訓家規在實踐主體和理念上有了很大改變,雖仍限于家庭主體的日常倫理,但非專為一家一宗族所制,而是旨在規范所有的家庭主體。司馬光將個人、家庭的道德完善視為規范整個社會關系的基礎,擴大禮所對應的主體對象至整個社會。
柳宗元關注天的物質性自然性,而不是哲學意義上的天,消解了作為最高權威的主宰之天和作為倫理道德本原的義理之天,以“勢”為武器破除束縛庶人參與現實政治和政治體制革新的思想障礙。在“天人不相預”的前提下,道德倫理和政治倫理關聯不大。而在“天人相濟”的前提下,一定程度會強化道德在個體生活及社會現實政治中的文化功能意義,極易將道德倫理擴展到社會和政治領域。兩者都對儒學的發展方向提供了指導,此后的宋學既從儒學內部創制出一個連貫個體與社會政治結構的價值體系,同時又強化了儒學走向泛道德化傾向。
三、兩人的天人思想與體用落實
柳宗元和司馬光都不是單純的在形而上學視域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他們很重視體用落實。在他們身上體現出唐宋文儒艱辛的理論探索,期望為當時的社會困境找到變革的依據和理想的發展模式。司馬光重視宗法倫理和社會秩序,為重建秩序尋求理論支撐;柳宗元則更多地關注破除天命桎梏進行革新。二人理論有差別,但兩者都對天人關系進行有價值的整合建構,為人和社會的現實存在尋找可靠的理論根據,其天人觀都蘊含豐富的社會歷史內容和對時代命題的積極回應。
首先,兩人都呼應了中唐以降的疑經思潮,推動了變古之風。晚清學者皮錫瑞評唐宋經學:“自《正義》《定本》頒之國胄,用以取士,天下奉為圭臬。唐至宋初數百年,士子皆謹守官書,莫敢異議矣。”[12]207傳統的謹守官書,對傳經解經的重視,很容易束縛經學的正常發展,抑制對儒學的承繼和創新,削弱儒學作為一種社會政治倫理學說本身應具有的經世致用。當社會面臨重大變革,社會統治體制的整體功能衰退,儒學未能對失序的社會狀況做出說明時,這種缺失更為明顯。唐宋以柳宗元和司馬光為代表的士大夫深刻意識到面臨時代的多重變革,儒學須從尋章摘句中解放出來,恢復其內在的社會功用和道德實踐性,深層次的探索心性并回應現實的社會問題,才能有新的突破。因此,柳宗元在學術上和行事原則上追隨春秋學派,突破株守章句,依據大中之道重振儒家大義。司馬光則援佛道入儒家,闡釋和發展了中庸思想。
其次,柳宗元和司馬光的天人觀體現了唐宋社會變革下士人的政治和文化主體意識漸趨增強。這一時期士大夫群體作為社會生活的主要推動者,區別于之前的“封建貴族”“士族門第”及以人身依附為特征的仰祿之士,可以說是正身之士的代表,突出特點為現實政治的訴求強烈,責任感明顯;以道進退而非爵祿。《邵氏聞見錄》記載神宗問程顥,“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后者回答,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13]1766這則著名軼事較為形象地說明了當時士大夫鮮明自覺的政治主體意識。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云:“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2]480,司馬光自述其志,“臣自結發從學,講先生之道,聞君子之風,竊不自揆,常妄有尊王庇民之志。”[5]1072他們均秉承了儒家強烈的事功精神,具有傳統儒家積極入世、濟世的淑世情懷。尤其司馬光處于北宋較為寬松的政治文化環境下,更容易激發起復興儒學,重建合理政治秩序的積極治事態度。加之柳宗元和司馬光兩人都有豐富的社會閱歷和仕宦經歷,對社會弊端有真切感受,對時代問題看得深遠,自覺的批判意識使他們的天人觀和對儒學發展體系的認知都區別于單純的經學家。
再次,他們的探索促進天人觀自身理論的演進。柳宗元和司馬光都將天人思想用于指導實踐,通過天人關系的思考反觀儒學自身,豐富了天人論的層次和內涵。他們對天人關系探索遠超出漢儒對人與自然的認知,而且超出純粹形而上學的思維,明體達用,體現出新儒學的發展趨向。
張躍贊譽柳宗元思想,稱之“沖破經學的藩籬,進行了大膽的理論創造”[10]48。柳宗元還原“天”元氣自然性的同時解構“天命”,將天人關系重心由“天”對“人”的主宰向“人”主體活動能動性轉移,為彰顯人道提供理論支撐。其天人觀不僅對當時的社會實踐有指導意義,也啟發了人們的理論思維和解決問題的現實能動性。
我們知道原始儒學缺乏嚴謹細微的思辨理論體系和形而上學的追問,宋以后儒學發展存在融合佛道的趨向,同時又竭力擺脫佛道影響,如李澤厚先生所說“宋明理學的這種吸收,改造和批判主要表現在,它以釋道德宇宙論、認識論的理論成果為領域和材料,再建孔孟傳統。”[14]221綜合司馬光對天、天命、道等觀點來看,司馬光雖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存在,但非唯天命論之,而是肯定天道存在,并努力將天道與倫理相連,得出道德不是人類自身產物,而是宇宙法則在人道的再現,這樣使道德具有了權威性和普遍性,由自然本體回歸倫理本體。司馬光的天人觀很重要的一點,即提出德行根源不在客體,而在主體自身。《中和論》中司馬光說:“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已”[5]1453,治方寸之地即治心,通過治心,達到天人合一,再建孔孟之道。借鑒佛、道的理論和重釋周易,司馬光在道、理、心、性、氣等概念上開拓新義,進行形上層面的理論建構,推動傳統儒家學說不再拘守于政治倫理等領域,在修身成德及思辨之域更進一步。勞思光指出了宋學的這一內在轉變,“蓋自宋至明,中國思想家欲脫離漢儒傳統而逐步求價值根源之內在化,宋明理學即此內在化過程之表現。”[15]88司馬光“天人相濟”的思想正處于宇宙論向形而上學觀的過渡,兩者有混合,將重點落在內圣上,而宋儒正是承內圣之學而發展。司馬光構建天人觀的直接動機是重建綱常秩序,將個人道德修養與社會政治問題相結合,以儒家倫理道德作為核心因子重塑社會政治人格。這種經世致用之道與形上思辨、治心的結合,使司馬光天人論區別于單純的天人感應論。“天人相濟”思想還包含同于天的境界,以及實現這個過程中人應當追求和達到的一種超越境界,這又延伸出新儒學的內在超越性,從天而人,在理論建構和視野上引導了儒學體用發展。
結語
天人關系是中國古代哲學的基本命題,有相當長的理論認知發展的淵源,柳宗元和司馬光的天人觀體現了一定歷史進步性,兩人都政學兼收并蓄,基于較為深刻的哲學底蘊和對現實的批判精神及自覺的儒學自我革新思想,他們提升了天人論的理論和實踐高度,不僅為其現實政治的踐行提供了哲理基礎,而且強調“人”之道德主體性和歷史主體性,體現了唐宋儒學由外向內對心性之域拓深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