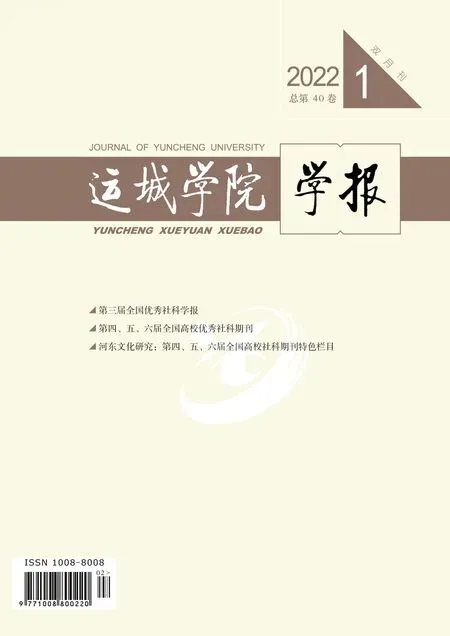后稷感生神話的形成與經(jīng)史差異
黃 震 云
(中國政法大學(xué) 中文系,北京 100192)
后稷是商周以來的農(nóng)神,也是周人的始祖,為五帝之一的帝嚳之子,因此,非常著名。又因其母親履帝武敏歆而生,所以又充滿神話色彩。而后稷為什么叫這個名字,似乎很少有人知道,更別談研究了。后稷的名字在經(jīng)典中最早出現(xiàn)的時候名為棄。考《尚書》云: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谷。”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1]6-7
由《尚書》記載我們看出,周棄按照舜的安排,負(fù)責(zé)糧食生產(chǎn)與親和教化、士安國體,成為三大任務(wù)之一。后稷的生平事跡記錄最詳細(xì)最早記錄的是周代《詩經(jīng)》的雅頌之章。其中有多篇作品涉及后稷,而《詩經(jīng)·大雅·生民》設(shè)為專章,說: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dá)。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shí)覃實(shí)訏,厥聲載路。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shí)方實(shí)苞,實(shí)種實(shí)褎。實(shí)發(fā)實(shí)秀,實(shí)堅(jiān)實(shí)好。實(shí)穎實(shí)粟,即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獲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fù)。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2]190
詩歌說,在克禋克祀的狀態(tài)下,姜原履帝武敏歆,生下后稷。由于經(jīng)受很多曲折,所以稱為棄,安居在有邰。后稷的農(nóng)業(yè)才華的發(fā)揮,得到人們尊敬。到胡臭亶時,后稷肇祀,成為周代人祭祀的始祖。漢代的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jì)》中則記載為“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3]111“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nóng),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nóng)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谷。’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3]112《集解》說祖,始也。周代的始祖生在邰,在稷之后再立,所以叫后稷。
記錄雖然有些出入,但后稷被封棄于邰,然后號曰后稷,則完全一致。這是最早出現(xiàn)的后稷兩個字。但是,《史記》顯然從《尚書》文字,因?yàn)闆]有解釋,所以,學(xué)術(shù)界認(rèn)為后稷的名稱是帝舜給的封號。至于為什么給這樣一個封號,則說不清楚。其主要原因一是后稷的相關(guān)資料比較少,二是在文字的理解上主要受《詩經(jīng)》的影響,難以作出判斷。從號曰后稷看,前面的汝后稷播時百谷是后面封為后稷的原因。過去我們讀到這里都覺得拗口,但并沒有理清含義。根據(jù)文章看,汝顯然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說你后稷,播時百谷。播時百谷就是時播百谷,意思是根據(jù)農(nóng)時農(nóng)性種植,發(fā)展農(nóng)業(yè)。既然稷神從來就有,那么,在后稷之前還有先稷,不是主觀意義上的神祗,也就是真實(shí)的稷的存在,也是著名的農(nóng)業(yè)專家,后稷在稷的后面,所以叫后稷。當(dāng)然,后稷和稷一樣,只是神名,不是本名。但是,后稷在夏以后才有這個稱呼。《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說:“顓頊?zhǔn)嫌凶釉粻罏樽H冢补な嫌凶釉痪潺垶楹笸痢4似涠胍病:笸翞樯纭pⅲ镎玻辛疑绞现釉恢瑸樯琊ⅲ韵囊陨响胫V軛壱酁轲ⅲ陨桃詠盱胫!盵4]383所以,對后稷進(jìn)行祭祀應(yīng)該從商朝開始。
中國祭祀稷神由來已久。考《孝經(jīng)》《左傳》等書說:“五谷眾多,不可遍祭,故立稷而祭之”。這些都是后來的猜測。考《獨(dú)斷》說:“稷神,蓋厲山氏之子柱也,柱能植百谷,帝顓頊之世,舉以為田正,天下賴其功;周棄亦播殖百谷,以稷五谷之長也,因以稷名其神也。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地。”[5](850)83記載和《左傳》一致。那么。厲山氏之子究竟是誰呢?考《潛夫淪·五德志》說:
初,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故立以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之興也,以棄代之,至今祀之。[6]386
稷是五谷之神。又《左傳》(昭公廿九年)說:“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4]383《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nóng),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7]255詩《閟宮》鄭箋云:“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后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疏引《尚書》云:“稷為司馬,契為司徒”。又《獨(dú)斷》說:“稷神,蓋厲山氏之子柱也,柱能植百谷,帝顓頊之世,舉以為田正,天下賴其功;周棄亦播殖百谷,以稷五谷之長也,因以稷名其神也。社稷二神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5](448)9
根據(jù)資料,有天下的厲山氏之子柱為原來的稷神,稱為田正。從以上分析看出,在夏朝衰亡以后,不再祭祀神農(nóng),殷商開始重新祭祀,所以稱后稷,周人開始祭祀后稷,相比較,后稷為新的稷神。照這樣說來,后稷成為稷神不是在舜的時代,而是其于商朝開始,然后周代繼續(xù),漢代延續(xù)了這樣的傳統(tǒng)。《漢書·郊祀志下》說:
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谷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紼而行事。’圣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后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谷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8]1269
又《禮記正義》說:
《春秋傳》曰: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著眾,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nóng)祀棄。“故祀以為稷”者,謂農(nóng)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者,是共工后世之子孫為后土之官。后,君也,為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為配社之神。“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者,嚳能紀(jì)星辰,序時侯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jié),故祀之也。“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者,堯以天下位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禪舜而老,二十八載乃殂,是義終也。[9]502
關(guān)于立稷的原因,《孝經(jīng)》《風(fēng)俗通》等書都認(rèn)為,“稷者,五谷之長,五谷眾多,不可遍祭,故立稷而祭之”。由上述我們看出,祭祀稷與封官稷,是人副天命的產(chǎn)物,最初的稷不是舜的安排與命名,而是厲山氏之子柱,能植百谷,帝顓頊之世,舉以為田正,所以是稷神,后來,周棄長于農(nóng)業(yè),在舜時為農(nóng)官,所以叫后稷,這里的后就是先后的意思。但在夏朝被廢除。“胡臭亶時,后稷肇祀”,也是通過一定的儀式,大概到胡臭亶時后稷成為新的農(nóng)神。而在夏朝末年,稷一度被廢。被廢的原因,是柱不起作用,夏代干旱了七年,稷沒有發(fā)揮作用。而稷不可能在祭祀時大家到一起祭,所以立一個形象,而這個形象全國一樣,三禮中采用的也是這種辦法。所以,后代的小說《西游記》中的土地神都一個樣。
但《全上古三代漢魏六朝文》在后稷名下注說,后稷的后是主的意思,就是說后稷就是主稷,顯然不是先后的后,而是諸侯的侯之意了。劉向《列女傳》卷一棄母姜嫄說:
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當(dāng)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后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傴翼之。姜嫄以為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饑,汝居稷,播時百谷。”其后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為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頌曰:棄母姜嫄,清靜專一,履跡而孕,懼棄于野,鳥獸覆翼,乃復(fù)收恤,卒為帝佐,母道既畢。[10]3
由此說看來,后稷的后還不僅僅是時間先后,實(shí)際上還有在稷地為諸侯的意思,也就是說后稷的后是王侯的侯的音與義了。根據(jù)周代的慣例,生為官,有成就以后,在死后作為神,往往成為祭祀的對象,如大司樂死后為樂祖。后稷顯然是祭祀對象為稷神,所以,《尚書》《史記》的后稷的后可以理解為主,也可以理解為諸侯的侯,是邰的一個地方。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因?yàn)楹髞砗箴⒌匠樗就剑苑Q為后稷,所以,之前應(yīng)該在地方。他作為稷神后稷的時候是在商代古公時代。所以說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后稷應(yīng)該說是先后的后,但是好多事情,剛好吻合,所以到周朝在理解時可以考慮不是簡單的先后的后了。
對于后稷的出生,均言感“巨人跡”生。孫作云考證姜原履的就是熊跡,源于周民族的熊圖騰崇拜。是有道理,但是時代不對,因?yàn)楹箴⑹撬磿r代的人,那時侯的圖騰不是熊,而資料的意思也并不是說真的去走熊的腳印,而且也不應(yīng)有那么大的熊,那么這個熊很難確定。《史記》以《詩經(jīng)》為基礎(chǔ)原型描寫了殷商和周始祖的感生神話,但在《史記》中表達(dá)已有所不同,《詩經(jīng)》中姜原是履帝武敏而孕,《史記·周本紀(jì)》則改為姜原踐巨人跡生后稷。并且《詩經(jīng)》中沒有提到殷周始祖的父親,而《史記》中則明確指出二者的父親都是帝嚳:“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姜原為帝嚳元妃”。這里有種種復(fù)雜關(guān)系,因此產(chǎn)生了種種矛盾,漢代以來已然。由經(jīng)典作為最初的根據(jù)看,司馬遷改這些不是根據(jù)事實(shí),而是根據(jù)漢代的政治需要。這毫無疑問。但是,這種需要不是司馬遷能夠決定的,而是以當(dāng)時的傳說和統(tǒng)治者的言論為基礎(chǔ)。
《史記·三代世表》云:“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跡者,欲見其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3]487按后稷的事跡,除了《生民》記載比較詳細(xì)外,還有《文王》等,也表達(dá)了與《史記》幾乎相同的說法。《文王》說: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jì)濟(jì)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2]190
根據(jù)《文王》來看,周過去的不顯,主要是帝命不時。不顯,也就是后顯,還是后來的顯,后來殷商后裔說無念爾祖也是處于帝命的原因。實(shí)際上就是說,大人跡是天意,是代表天的行為。實(shí)際上,履帝武敏歆的帝與玄鳥生商的帝為同一個人,都是帝舜。
楊建軍《后稷感生神話考》一文,對周族始祖后稷的感生神話的某些詞句作了考釋,并認(rèn)為《史記·周本紀(jì)》中的后稷感生神話不同于《詩經(jīng)》中《生民》的后稷感生神話,認(rèn)為是另一異文,可惜異文沒有流傳下來。[11]文章中有很多合理的成分,但是,對此表達(dá)猜測居多,難以認(rèn)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態(tài)度非常嚴(yán)謹(jǐn),也花費(fèi)了全部心血,注重實(shí)證精神:“余嘗西至空峒,北過逐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fēng)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考信于六藝,夫?qū)W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選擇材料以雅馴為標(biāo)準(zhǔn):“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論次,擇其言尤雅者。”[3]46同時,《史記》中亦有不少神話描寫,二者明顯相悖,實(shí)際上這是當(dāng)時的歷史環(huán)境下司馬遷史學(xué)思想的反映,也是《史記》魅力的藝術(shù)體現(xiàn)。
《史記》中的神化表現(xiàn)并不多,主要集中在開國帝王或者民族始祖。之所以這么做,主要是證明劉邦感生神話的合理性,因此,關(guān)于感生神話的資料主要來自經(jīng)典,但又有所改變。
《史記》以《詩經(jīng)》《尚書》為基礎(chǔ)原型描寫了殷商和周始祖的感生神話,但在《史記》中已有所不同。《詩經(jīng)》中只是帝命玄鳥生商,但具體形式不清楚,而《史記·殷本紀(jì)》中則以為簡狄吞玄鳥之卵而契生。《詩經(jīng)》中姜原是履帝武敏而孕,《史記·周本紀(jì)》則改為姜原踐巨人跡生后稷。并且《詩經(jīng)》中沒有提到殷周始祖的父親,而《史記》中則明確指出二者的父親都是帝嚳:“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帝嚳元妃”。這里有種種復(fù)雜關(guān)系,因此產(chǎn)生了種種矛盾,漢代以來已然。司馬遷將殷周寫成姊妹倆的后代,實(shí)際上是一種諷刺。
《史記·三代世表》云:“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按諸傳說,咸言無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于《詩》謬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于孵,后稷人跡者,欲見其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3]487這些話連褚先生都不信。那后稷的帝武敏、巨人跡,又變成了人跡,皆一事多傳。司馬遷當(dāng)然知道這些不可信,也曾多次表示鬼神荒誕的東西他不取。但劉邦有意將歷史神話化,漢武帝強(qiáng)化了這一思維,出現(xiàn)天人感應(yīng)的政治思想與格局。與司馬遷“究天人之際”的寫作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說,司馬遷不相信荒誕的鬼神存在,但又必須服從當(dāng)時的政治,同時天人感應(yīng)就是他究天人之際的重要內(nèi)容,今天看來未免荒唐。也就是說史學(xué),不能簡單看作一個學(xué)科,還與時代密切相關(guān)
至于為什么本于經(jīng)典又不一致,資料顯示,這是一事多傳,也是神話形成的規(guī)律,還有作者的故意。就是說在《詩經(jīng)》《尚書》時代,這些感生神話是含糊不具體的,到《史記》時代已經(jīng)具體化。其原因就是那些是原始的神話,在形成以后,又經(jīng)過傳說補(bǔ)充發(fā)揮,于是顯得更具體,更豐富,更周詳。司馬遷對此作出了取舍,其原則如上說考信于六藝,以雅馴為標(biāo)準(zhǔn)。但是,不排除他在取舍時具有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