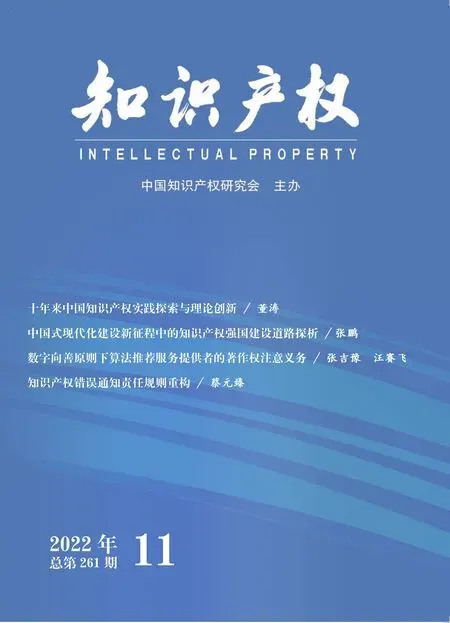元宇宙時代的版權理念與制度變革
初 萌
內容提要:數據驅動變革創作方式、技術賦能提升用戶地位、全民創作突破演繹限制,是元宇宙時代創作行為的三大突出特點。在理念層面,元宇宙發展引領了創作者中心主義理念的“復興”,強化了創作主體地位之平等,從而凸顯了版權保護的人本主義面向。由于虛擬人的本質仍在于對人格要素的商業利用,當前尚無賦予虛擬人獨立人格之必要性。在制度層面,應當同時考量技術的賦能作用與限權作用,有針對性地打造“技術 + 規則”二元互動體系,強化版權的公共文化面向。元宇宙引領的新潮流也有助于澄清版權保護的邊界,彰顯版權制度的理性色彩。
引 言
網絡技術的發展經歷了從Web 1.0到Web 2.0再到Web 3.0時代的演變:Web 1.0以“只讀”為特征,用戶只能單向度獲取網絡信息;Web 2.0在“讀”的基礎上增加了“寫”的功能,用戶可創建內容并實現交互,但規則主要由互聯網平臺制定;Web 3.0以基于區塊鏈分布式存儲技術而建立的“去中心化”網絡為典型,代表著更大程度的開放與共享,強調用戶擁有自主權。①參見姚前:《Web 3.0:漸行漸近的新一代互聯網》,載《中國金融》2022年第6期,第14-15頁。當前大火的“元宇宙”概念,正是Web 3.0時代的產物。
“元宇宙”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美國科幻作家尼爾·斯蒂芬森撰寫的小說《雪崩》,它描述了人們生活、工作的線上世界。這部小說囊括了移動計算、虛擬現實、數字貨幣等場景,勾勒出元宇宙的基本雛形。元宇宙并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但總體來看,它整合了網絡運算、人工智能、電子游戲交互應用、區塊鏈、物聯網等各種技術,呈現出虛實結合的樣態;它為用戶提供沉浸式體驗,人們可以數字替身等方式與其中的物體進行互動。元宇宙的本質在于借助區塊鏈技術,使這個虛擬世界中的一切數字存在都具有了唯一性、獨特性和資產屬性。②參見劉煒、付雅明:《祛魅元宇宙》,載《數字圖書館論壇》2022年第7期,第2-3頁。這也是人們持有NFT(non-fungible token,即“非同質化代幣”)數字藏品、沉浸于元宇宙游戲及打造自我虛擬形象的重要原因。
元宇宙產業潛力巨大,這可從其分支產業“數字人”的發展中窺見一斑。在2022年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局印發的《北京市促進數字人產業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中,“數字人產業”的概念被提出,凸顯了其經濟價值。③參見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局:《北京市促進數字人產業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載北京市人民政府網2022年8月3日,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208/t20220808_2787958.html.“數字人”也可稱為“虛擬人”。數據顯示,在娛樂需求增加、人工智能等技術不斷迭代的背景下,我國虛擬人產業高度發展——2021年中國虛擬人帶動產業市場規模和核心市場規模,分別為1074.9億元和62.2億元,預計2025年分別達到6402.7億元和480.6億元。④參見艾媒咨詢:《2022—2023年中國虛擬人行業深度研究及投資價值分析報告》,載艾媒網2022年4月22日,https://www.iimedia.cn/c400/85066.html.毫不夸張地說,元宇宙產業已成為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技術的革新總是帶來知識產權理念與制度變革,元宇宙的興起概莫能外。在專利權、商標權、版權三大領域中,版權所受影響尤甚。這是因為技術方案、產品設計、商業標識保護的是實用價值,而作品受保護是源于其美學價值。數字經濟發展存在虛擬經濟與虛實結合兩個主要維度,前者的價值主要依托于版權而實現。當前的虛擬偶像、沙盒游戲、NFT等商業模式所產生的知識產權問題也主要集中于版權領域。因此,本文主要以版權為切入點,探討元宇宙時代知識產權的理念與制度變革。
一、元宇宙的版權之維
(一)數據驅動變革創作方式
表演型虛擬人興起,是元宇宙時代的一大亮點。早期表演型虛擬人以初音未來、洛天依為典型,其依托計算機動畫、動作捕捉等技術而呈現出擬人化的樣態,根據指令展開表演。現在流行的表演型虛擬人則更具交互性,例如湖南衛視《你好星期六》節目引入的虛擬主持人“小漾”便能夠向同臺主持人提問、回答,且神情更生動,肢體動作更自然流暢,帶給人們真切的互動體驗。隨著技術的革新,虛擬人的運用不再局限于表演領域。2021年作為虛擬學生亮相的“華智冰”,由清華大學、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以及小冰公司共同研發,其不僅擁有強大的快速學習能力和記憶能力,還可進行“創作”活動。
虛擬人與真實人類的差異逐漸縮小,離不開人工智能技術的運用。人工智能的“創作”能力亦由此而生。與人類創作相同,人工智能“創作”也經歷了輸入、分析和加工、輸出三個階段:首先,大量輸入相關數據,為后續的學習過程提供素材;其次,從數據中提煉出基本寫作方法,在學習中將素材消化、吸收,并以貫穿同一主題、思想為目標對基礎創作元素進行新的排列組合,實現數據的再加工;最后,對表達一定主題、思想的“作品”進行輸出。所謂的“獨創性”主要存在于分析和加工過程之中。這一“創作”過程與人類創作的不同之處,主要在于人類創作是思維運作的結果,而人工智能“創作”行為本質上是由海量數據所驅動的。通過深度學習技術的加持,現階段的人工智能已經能夠在海量數據的訓練中提取出模型特征和最有利的參數,實現對數據或實際對象的抽象表達。⑤參見付文博、孫濤、梁藉、閆寶偉、范福新:《深度學習原理及應用綜述》,載《計算機科學》2018年第6A期,第11頁。相反,若不存在海量數據,人工智能則難以實現有效輸出。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此前被拍出43.25萬美元高價的人工智能繪畫《埃德蒙·貝拉米像》,就是在向人工智能程序輸入超過1.5萬幅人像進行訓練后,才最終得以實現與人類創作的畫作難以區分。⑥參見袁野:《人工智能“入侵”繪畫圈》,載《青年參考》2018年11月1日,第10版。雖然我們常以“神經網絡”描述人工智能學習過程,但這并不能改變其模擬屬性,數據驅動的人工智能尚不能夠像人類一樣思考。
伴隨著人工智能廣泛運用于元宇宙相關產業,以及擬人化的虛擬人之興起,“創作者”的界定成為必須回應的問題。無論是作為人工智能產物的虛擬形象本身,還是虛擬形象借助人工智能技術而產出的“作品”,都不再是人類完全掌控之下的產物,而是賦予了計算機程序一定的“自主權”。正如學者所言,在這樣的“創作”過程中,“藝術家們已經不是簡單地將計算機視為畫筆一樣的工具,而是試圖創作程序,讓計算機能夠一定程度上獨立作畫了”。⑦參見陶鋒:《人工智能視覺藝術研究》,載《文藝爭鳴》2019年第7期,第75頁。人工智能“創作”削弱了自然人與作品獨創性之間的連結,對現行以自然人創作為根基所建立的版權制度⑧雖然各國著作權法都規定了法人作品或者雇傭作品等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享有著作權的情形,但這些作品最終的創作者仍為自然人。例如,美國版權法將受保護的對象限定為“作者的原創作品”(original works of authorship),這就要求背后有一個人類主體的存在。17 U.S.C.§102 (a); The Compendium of U.S. Copyright Office Practices, 313.2, https://www.copyright.gov/comp3/chap300/ch300-copyrightable-authorship.pdf.提出挑戰。而具備人之樣態的虛擬人是否能夠被賦予主體地位,又會對權利架構產生實質影響。除此之外,海量數據獲取行為的合法性問題也有待進一步澄清。
(二)技術賦能提升用戶地位
元宇宙發展的高級樣態是互聯互通,這與當前各自為戰、缺乏兼容性的網絡平臺生態存在本質區別。互聯互通意味著資產能夠跨越平臺界限,流向最珍視它的主體,進而實現資產價值最大化。這一方面需要明晰元宇宙中資產的性質,另一方面需要為之配置交易權能。就前者而言,元宇宙中的數字資產由個人掌控,參與者可通過私鑰的方式實現對資產絕對的、排它的占有權利,⑨參見鄧建鵬:《元宇宙及其未來的規則治理》,載《人民論壇》2022年第7期,第33頁。這一觀點已為學者所接受。就后者而論,在游戲、數字藏品等領域已有此類交易實踐。在游戲領域,以Sandbox、Horizon Worlds為代表的元宇宙游戲都內嵌了交易系統,允許用戶將游戲中生成的資產進行販賣,用戶相對于平臺的自主權得到極大提升。這也使得游戲產業鏈逐步呈現出游戲運營平臺作用淡化、生產關系重構、利益向用戶傾斜的特點。⑩參見陳溢波、吳可仲:《元宇宙改造游戲生態:利益將向用戶傾斜》,載《中國經營報》2022年1月3日,第D06版。在數字藏品領域,國外不少NFT數字藏品平臺開放了二級市場,實現NFT對應資產的流轉和增值。根據知名研究機構Messari的報告,截至2021年底,全球NFT二級市場交易規模已經超過150億美元,而一級市場交易規模僅為20億美元;?Tim Fries, Total NFT Secondary Sales Have Now Surpassed $15 Billion, The Tokenist (8 December 2021), https://tokenist.com/total-nft-secondary-sales-have-now-surpassed-15-billion/.NFT流通的價值釋放作用得到凸顯。沿著技術發展的道路,互聯互通使用戶對虛擬財產的權益從“擁有”“獲取”延伸到“利用”領域,財產權的三維價值?參見易繼明:《財產權的三維價值——論財產之于人生的幸福》,載《法學研究》2011年第4期,第74-85頁。得到完整體現,這要歸功于技術的賦能作用。
與之相關的一個問題,是虛擬財產屬性的進一步明晰。關于虛擬財產的定性,主要爭議在于其應當被界定為物權還是債權——主張物權者強調用戶對虛擬財產的支配,主張債權者則從聯網要求、平臺限制、用戶協議等維度指出用戶對虛擬財產掌控的受限性。?參見林旭霞:《虛擬財產權性質論》,載《中國法學》2009年第1期,第90-93頁。元宇宙的技術方案已然跨越平臺限制,廣泛的交易實踐更使交易物的物權屬性凸顯。這便是用戶主權的物權維度。用戶主權的另一維度體現在版權領域,指向用戶對其創作的作品的掌控權,其原因在于互聯互通的大趨勢對平臺封鎖的正當性提出挑戰。平臺通過用戶協議獲取用戶作品獨占性許可、實現鎖定效應的實踐,日益呈現出與元宇宙發展趨勢相背離的特點,對用戶構成不公平的限制。此類許可通常免費實施,使用戶與作品傳播后續的收益完全隔離,這也導致對用戶主權的剝奪更為凸顯。
雖然我國元宇宙產業的發展現狀離互聯互通及用戶主權的實現仍有一定距離,但相關政策已經對這一導向進行了明晰。例如,上海市提出將數字市場IP培育工程作為重點工程,“探索建立多方參與、互聯互通的數字創意聯盟鏈體系”?參見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印發促進綠色低碳產業發展、培育“元宇宙”新賽道、促進智能終端產業高質量發展等行動方案的通知》,載《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報》2022年第14期,第14頁。“鼓勵企業與成熟平臺開展生態合作,探索建立統一平臺體系和認證模式,實現互聯互通、相互調用,打造以用戶為中心的全場景智能服務”。?同注釋?,第18頁。《北京市促進數字人產業創新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在“基本原則”部分提出要“構建以數字內容生產和數字資產流通為主要內容的新型產業體系”,并在“主要任務”部分提出要“研究跨渠道、跨平臺、跨設備的版權溯源機制、維權機制和多元共治的著作權保護體系”。?同注釋③。實踐層面,區塊鏈技術及智能合約也為創作者與消費者建立直接關系搭建了橋梁,為減少平臺“抽成”提供了技術方案,創作者權益的維護具備了落地的現實性。
(三)全民創作突破演繹限制
元宇宙時代用戶主權的進一步延伸,體現為作品使用者對他人原創作品的積極建構。早期的表演型虛擬人實際上是“一個產生歌聲的引擎”,其全部可能性已蘊含在程序之中。與之相對應的是強調作品是內在的東西得以外化的浪漫主義作品觀,這種觀念主張從作者與作品的關系角度來解釋作品。?參見陳杰:《論著作權法視野下的作品觀》,載《知識產權》2012年第6期,第17頁。現在的虛擬偶像則突破了傳統的“明星”打造流程,大有從官方推動演變為大眾推動的趨勢。以“粉絲”為代表的用戶群體在新舊媒體的相互碰撞、草根媒體與公司化大媒體的相互交織、制作者與消費者權力的互相作用之中,逐漸扮演起作品創作者、文本意義積極建構者的角色,?參見宋雷雨:《虛擬偶像粉絲參與式文化的特征與意義》,載《現代傳播》2019年第12期,第27頁。實現從創作者權利到消費者權力的反轉。這一權力反轉也得到了結構主義理論的支撐。根據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觀點,語言是一個自我指稱的、具有特定結構的符號系統,作者的創作需要遵循這一系統及其結構的限制。這一被共享的系統及其結構也為人們理解具體文本含義、實現從強調“作者”到強調“文本結構本身”的轉變提供了可能性——作品的中心意義不再是作者的靈魂,而是更深層次的文本結構本身,作為作者的主體便被有效地消解掉了。?參見[英]特雷·伊格爾頓:《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伍曉明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110頁。伴隨著現代文學理論“全神貫注于作者”“絕對關心作品”?同注釋?,第73頁。的階段之終結,從作者中心轉向讀者中心的趨勢開始顯現。其主要表現之一,即關注讀者的主觀能動性在建構作品意義方面的作用。
結構主義為使用者對作品意義的積極建構提供了理論基礎,參與文化則為使用者這一行為的動機提供了解釋。如凱文·凱利所言,我們正穩步邁向一種網絡世界所特有的、數字化的“社會主義”,?參見[美]凱文·凱利:《必然》,周峰、董理、金陽譯,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頁。作品在分享和互動的過程之中逐漸脫離與作者的關聯,不斷被注入新的內涵,這便是參與文化的內核。在這一過程中,越是被廣泛使用的作品元素,越成為參與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像基因一般具有了自我復制的潛能,?有學者使用了“迷因”這一概念來表示文化傳遞單元或者模仿單元。迷因這個文化單元的行為與基因一模一樣,有通過自我復制確保自身生存的屬性。參見勞勃·蕭爾:《原創的真相:藝術里的剽竊、抄襲與挪用》,劉泗翰譯,阿橋社文化2019年版,第170-171頁。成為人們交流的剛需,發揮精準表意的功能。電視劇《歡樂頌》中“五美”形象被用于保險產品宣傳?參見東陽正午陽光影視有限公司訴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不正當競爭糾紛案,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7)京0105民初10025號。、金庸小說中經典人物形象被用于創作新的作品?參見查良鏞訴楊治等侵犯著作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6)粵0106民初12068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參與文化引領了全民創作潮流,作品演繹的限制被突破,原始形象的人設也在不斷的演繹中逐步豐滿。
參與文化在元宇宙時代亦有突出體現。從本質上說,元宇宙時代是人類社會在一定社會交往和實踐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歷史形態,是人們在共同參與的過程中營造出來的環境。?參見藍江:《元宇宙的幽靈和平臺—用戶的社會實在性——從社會關系角度來審視元宇宙》,載《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第13頁。元宇宙中井噴式增長的創作素材為再創作提供了極大便利,交互體驗感的上升則進一步激發了再創作的熱情,參與文化為自身發展找到了嶄新的土壤。諸如Soul捏臉師、Decentraland創作者等元宇宙內容制造者已經能夠實現收益變現,共建、共創、共生的元宇宙精神正在逐步成型,“版權作品使用共識”?參見尤杰:《“版權作品使用共識”與參與式文化的版權政策環境》,載《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第123-125頁。的進一步推進指日可待。職是之故,構建符合參與文化的權利行使規則,成為版權法上的新課題。
二、回歸人本主義版權保護理念
(一)創作者中心主義“復興”
技術的運用總能帶來人類社會的進步,但技術對不同主體的賦權卻是不同的。Web 2.0時代使平臺掌控力凸顯,Web 3.0中的互聯互通、資產跨平臺交易、用戶主權則見證了創作者地位的崛起。創作者中心主義順勢而“復興”具備了基本前提。
理論上,創作者是著作權法上最為重要的主體,也是激勵理論的主要作用對象。但從歷史上看,創作者的保護卻是依附于投資者和傳播者而開展。英國1709年頒布的《安娜女王法》雖然首次確立了作者在著作權法上的主體地位,但作品能否出版及發行范圍均由掌控媒介的出版商所決定。從動機來看,作者地位的提升最早源于出版商獲得永久壟斷性出版權的訴求,版權語境下的“作者”呈現出功能化、符號化的特點。[27]參見徐小奔、陳永康:《作者的功能化與人工智能“機器作者”的承認》,載《中國版權》2021年第2期,第41-45頁。這也被《安娜女王法》生效后的一段時間內,作者團體并未獲得更多利益的事實所證實。如今,人類社會已步入大傳播時代,但專職編輯、自由媒體人依舊被束縛于著作權制度下職務作品的規定以及合同條款之中,向雇主、平臺交出作品掌控權。實踐中,創作者保護權益組織的缺位、體現實質公平的示范條款的缺失、關于創作者權益保護的強制性規定的闕如,使創作者獲益權難以真正實現。[28]參見易繼明、初萌:《論人本主義版權保護理念》,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第170-173頁。創作者與傳播者在共生狀態之余,也呈現出一定的對抗色彩。
元宇宙時代,技術成為這一關系的“破局者”。作為改變世界的重要力量,技術使人們對事物的認知發生改變;但從另一個視角觀之,特定技術的運用本身就是一定意識形態的體現,這是由技術的社會屬性所決定的。技術的社會屬性強調技術產生和運作中人的能動因素——基于建構主義的立場,人類能夠通過設計來控制技術的運作,進而表達他們的價值取向。[29]參見初萌:《知識產權法的人本主義倫理轉向——以建構主義的技術觀為視角》,載《科學學研究》2022年第8期,第1347頁。具體到元宇宙、區塊鏈,其本身就是去中心化的技術架構方案,體現出解構平臺、解放創作者的價值取向。在具體運用中,平臺網絡外部性對創作者的吸引力逐步“祛魅”,創作行為本身所帶來的價值進一步彰顯。根據權利與貢獻相匹配的原則,創作者中心主義開始逐步為人們所接受。試以網絡游戲直播畫面的著作權為例作分析。較早研究這一問題的學者多認為玩家僅對游戲平臺預設元素和場景進行調用,其行為缺乏獨創性,不能作為著作權人;即便是主張玩家可以成為網絡游戲直播畫面演繹作者的學者,也出于對平臺付出巨大成本的事實、利益平衡的價值取向、用戶協議約定的著作權歸屬等因素的考量,認為不應由玩家享有游戲直播畫面的著作權。[30]參見馮曉青:《網絡游戲直播畫面的作品屬性及其相關著作權問題研究》,載《知識產權》2017年第1期,第10-11頁。伴隨著沙盒游戲、元宇宙游戲的興起,用戶在游戲中呈現個性化表達的空間顯著提升,越來越多的觀點開始支持用戶與網絡游戲平臺共享版權,甚至由用戶作為演繹作者獨自享有演繹作品的著作權。[31]參見焦和平:《沙盒建造類游戲整體畫面著作權歸誰?》,載《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22年8月25日,第007版。這一轉向在游戲平臺用戶協議中也有所體現。例如,《我的世界》游戲服務協議就規定了用戶享有版權的兩種情形,一是對基于游戲元素創作的新內容(又稱為“用戶改編素材”)與平臺共享版權,二是針對獨立創作的素材(又稱為“用戶素材”)獨自享有版權。[32]參見《網易游戲使用許可及服務協議》,載網易網,https://protocol.unisdk.netease.com/release/latest_v15.html,2022年10月27日訪問。
從觀念到實踐,微粒化、去中心化的技術架構對平臺權力的解構得到了積極回應,這一發展趨勢顯然是符合版權保護的本旨的。雖然平臺對作品傳播功不可沒,但無作品也就無所謂傳播,版權的激勵作用最終仍需落實到創作主體之上。在技術加持之下,我們或許可以宣告:屬于創作者的時代真正來臨了。
(二)虛擬人獨立人格證偽
創作者中心主義在人工智能、數據驅動的時代依舊彰顯,否定人工智能的獨立人格即為典型體現。關于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可版權性,主要有肯定說與否定說兩種觀點。主張否定說者,或認為人工智能創作是應用算法、規則和模板的結果,沒有為人工智能留下發揮其“聰明才智”的空間,故不滿足獨創性要求;[33]參見王遷:《論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在著作權法中的定性》,載《法律科學》2017年第5期,第148-155頁。或主張人工智能生成作品中不存在思想或情感的表達,對其保護不符合著作權法的基本目標。[34]參見劉銀良:《論人工智能作品的著作權法地位》,載《政治與法律》2020年第3期,第2-13頁。上述觀點要么將人工智能界定為作為客體的軟件,要么否認其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故而具有否定人工智能獨立人格的指向性。持肯定說者一般采取客觀的獨創性判斷標準,且多數學者認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版權并非歸于人工智能,而主要應歸于人工智能研發者或者對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產生作出實質性安排的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組織。這一論斷背后的邏輯在于:其一,需要激勵的并不是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行為,而是人工智能研發行為;其二,作品獨創性離不開人的意志對人工智能內容生成活動各個環節的干預和控制。[35]參見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著作權認定》,載《知識產權》2017年第3期,第3-8頁;孫正樑:《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著作權問題探析》,載《清華法學》2019年第6期,第197頁。這些觀點揭示了既有法律主體與人工智能生成物之間的關聯,并證實了現有法律框架足以解決人工智能生成作品問題,既然如此,沒有必要再探討人工智能獨立人格。
元宇宙時代,人工智能與虛擬人的結合帶來了新的問題:在上文的分析中,人工智能與真實的個體并不存在直接關聯;然而對虛擬人而言,上述預設并不成立。恰恰相反,虛擬人總是具有人的樣態,甚至可以像自然人那樣在元宇宙世界中“擁有”財產、簽訂協議。有鑒于此,有學者已經提出“虛擬人應當具有獨立人格”的觀點。[36]參見楊延超:《網絡時代論元宇宙中的民事權利》,載《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第33頁。與之相反的觀點則主張虛擬人的人格表象僅為自然人人格在元宇宙中的自然延伸,其行為亦屬于自然人行為的自然延伸。[37]參見李佳倫:《網絡虛擬人格保護的困境與前路》,載《比較法研究》2017年第3期,第197頁。
本文認為,上述觀點均有片面性。一方面,虛擬人在元宇宙中的行為并不能等同于自然人的行為,也未必能夠體現自然人的意志。當虛擬人實為人工智能的產物時,其形似自然人的表象并不能改變最終作品的數據驅動屬性,這也就意味著其生成的作品并非特定自然人精神和情感的體現。但是,若因此而承認虛擬人的獨立人格,卻會引發人格混亂和沖突,貶損真實世界中創作者的權益。試想,若以自然人形態存在的虛擬人因不良數據的輸入而產出不符合核心價值觀的作品,發表有損他人名譽權的言論,形象的關聯性也會導致自然人聲譽隨之降低。更有甚者,獨立人格的確立意味著需要在自然人的人格權與虛擬人的人格權之間進行平衡,這無疑也會對自然人的人格權產生一定的損害。
將虛擬人定位為“人格要素的商業利用”,是更為可取的選擇。人格要素的商業利用突破了“人-物”二分的界限,財產權人格理論為這一突破提供了正當性。這一理論認為財產與人格之間存在內在關聯;人的自由意味著需要給他以外部領域,物則在人的意志中獲得它的規定和靈魂。[38]參見[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52頁。同樣,將虛擬人界定為財產并承認其中人格因素的存在,并不存在理論障礙。我國已有學者指出,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財產、寄托特定人情感的財產、源于特定人身體的財產和源于特定人智慧的知識產權都屬于具有人格利益的財產。[39]參見易繼明、周瓊:《論具有人格利益的財產》,載《法學研究》2008年第1期,第3-16頁。虛擬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自然人的性格、氣質、肖像、聲音等品質,其中不乏人格象征意義的體現。不過,無論從學理觀點還是法律規定[40]例如,我國《民法典》第1183條第2款規定:“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義的特定物造成嚴重精神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此處的“被侵權人”通常指的是特定物的物權人。來看,提出“具有人格利益的財產”主要是為了保護財產權人的人格利益,而虛擬人產業中的人格利益保護卻有兩種面向:一是在虛擬人的行為由對應的自然人控制時,促進自然人人格利益在虛擬空間的實現;二是在虛擬人的行為不受自然人控制時,解決他人對虛擬人的財產權與自然人人格權之間的沖突。若將虛擬人界定為具有人格象征意義的財產,并不能夠反映出上述第二種面向。“人格要素的商業利用”更能全面體現所欲保護的法律利益,且與積極的自行使用或許可使用、消極的禁止使用一一對應。對虛擬人作出“人格要素的商業利用”的界定,同樣能夠實現賦予其獨立人格所可能產生的理論優勢——維護自然人自由擴張的權利、維護分屬不同世界的成員的信賴利益。[41]同注釋[36],第33-34頁。至于實現的具體路徑,則是基于虛擬世界的特性對自然人的人格利益進行必要的擴充,并且基于人格權對財產權的優位,[42]參見王利明:《邁進數字時代的民法》,載《比較法研究》2022年第4期,第24頁。在虛擬人與自然人行為不具關聯性時對其財產權人施加維護自然人人格利益、進行區分性標記等義務,我國《民法典》關于“一般人格權”[43]我國《民法典》第990條規定:“人格權是民事主體享有的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等權利。除前款規定的人格權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產生的其他人格權益。”其中第2款是關于“一般人格權”的規定。的規定已經對此預留了空間。鑒于現有法律的充足性,現階段尚無必要賦予虛擬人以獨立人格。
(三)強化創作主體平等地位
人本主義版權保護理念的第三個具體維度,是平等考慮在先創作者與在后創作者的利益,這也是元宇宙中用戶主權的進一步延伸。
在“版權人—傳播者—使用者”的三維關系中,傳統版權理念更為關注前兩者的利益,這直接體現于《著作權法》的具體規定之中。《著作權法》第10條明確列舉了著作權人享有的四項精神權利和十二項財產權利,并以“應當由著作權人享有的其他權利”作為兜底條款,從而為著作權隨技術發展而擴張提供了法律依據。在鄰接權部分,該法雖僅為出版者、表演者、錄音錄像制作者、廣播組織等傳播者賦予了有限的幾項權能,并未規定兜底條款,但由于版權人與傳播者之間通常存在版權轉讓、獨家許可等關系,傳播者往往成為版權經濟利益的事實掌控者。而使用者的利益則主要在思想表達二分法、零星的合理使用以及著作權保護期條款中,以反射利益的方式體現。這種反射利益存在受益人不確定、相對方不負有義務、受益人不享有救濟權等特點,[44]參見朱理:《合理使用的法律屬性——使用者的權利、著作權的限制還是其他》,載《電子知識產權》2010年第3期,第11-18頁。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版權人采取的技術措施。對于元宇宙中的作品創作而言,由于我國尚未引入“轉換性使用”、合理使用“四要素”等兜底式規定,且缺乏關于創作演繹作品的法定許可條款,借用原作品元素創作新作品的使用者往往只能借助涉及“介紹、評論”的合理使用條款而豁免;而司法實踐對適用這一條款的要求較為苛刻,不僅對使用的數量、質量提出要求,而且一旦不存在不使用涉案作品即無法表達主題的情形,通常即可宣告侵權成立。[45]參見唐亮、長沙廣電數字移動傳媒有限公司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案,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20)湘知民終675號。隱含在我國《著作權法》中的制度觀念凸顯了在先創作者與在后創作者利益之間的不平衡。
在互聯網時代,參與文化的興起使人們從理念上穩步邁向數字化的“社會主義”,作品的易獲取性、易拆解性以及創作工具的便利化加劇了這一態勢。對融入參與文化中的人們而言,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可能成為創作與交流的素材;至于是否享有版權保護,則在所不問。文化發展與版權保護的潛在沖突由此而生。[46]參見初萌:《全民創作時代短視頻版權治理的困境和出路》,載《出版發行研究》2022年第5期,第69頁。參與文化的另一個側面是經濟收益對創作的激勵作用弱化,更多的大眾創作是在創作熱情、積累知名度、獲得認同感等需求之下完成的。一邊是在后創作者對寬松版權環境的渴求,另一邊是版權保護對在先創作者激勵的減少,版權法動態效率的實現需要在理念上作出平等保護在先創作者與在后創作者利益的轉變。在元宇宙時代,這一要求更為凸顯,具體體現在如下方面。其一,元宇宙中的互聯網信任和分布式治理可以促進人們之間的平面溝通和社會交換,進而更容易形成人與人互動的場域;[47]參見季衛東:《元宇宙的互動關系與法律》,載《東方法學》2022年第4期,第27頁。在元宇宙的組織運作模式中,每個個體都可以自主決策、自由創作,在新的傳播價值鏈中找到合適的生態位,生產和傳遞數字資產、數字內容的創意及價值,[48]參見喻國明、陳雪嬌:《數字資產:元宇宙時代的全新媒介——數字資產對傳播價值鏈的激活、整合與再連接》,載《出版發行研究》2022年第7期,第26頁。參與文化的重要性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二,依托區塊鏈技術,人們能夠實現以類似于物權的方式控制數據、資產、身份、NFT等數字權益,基于物權優先于著作權保護的理念,[49]不少學者對物權優先于著作權的理念進行了論述,這一理念集中體現在發行權用盡原則以及作品原件所有權人特定行為的豁免。我國《著作權法》第20條規定:“作品原件所有權的轉移,不改變作品著作權的歸屬,但美術、攝影作品原件的展覽權由原件所有人享有。作者將未發表的美術、攝影作品的原件所有權轉讓給他人,受讓人展覽該原件不構成對作者發表權的侵犯。”如學者所言,這一規定“較嚴重地限制了著作發表權的效力”。參見韋之:《試論著作物權》,載《中國版權》2021年第2期,第33頁。但也正因如此,該條非常明晰地體現了物權對著作權的優先地位。當知識產權與物權發生沖突時,知識產權通常需要讓位給物權。參見劉春田主編:《知識產權法》(第6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24頁。附著于這些數字權益之上的著作權也應適當限縮。其三,元宇宙的價值目標在于以去中心化的方式避免寡頭壟斷,使私有財產從屬于共同的使用權,盤活資產的流動性,塑造“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共享和服務文化,[50]參見李國權:《元宇宙是一種超越現實和虛擬兩界的宇宙》,載中金網2022年4月20日,https://www.cngold.com.cn/202204208704773886.html.此中的平等取向必然要求削弱版權的獨占性。
三、因應技術賦能的制度變革
(一)推動智能合約標準化,打造“技術+規則”二元互動體系
理念的踐行最終需落實到制度層面。從定義來看,制度代表著集體行動對個人行動的控制,[51]參見[美]康芒斯:《制度經濟學》(上),趙睿譯,華夏出版社2017年版,第80頁。它是人們行動的模型和可能的行動框架——人們總是在制度的框架內與其他人一起組織他們之間的互動。[52]參見[美]詹姆斯·E. 赫格特:《當代德語法哲學》,宋旭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50頁。制度是由規范構成的,它們決定了哪些事情可以做、誰可以做、如何做,是一種價值取向的體現。
制度的規范屬性意味著它與互聯網、元宇宙中的架構存在區別。正如互聯網的架構拓寬了人們交往的場域,使陌生人之間的匿名交流成為可能,而網絡安全相關法律制度卻提出了“后臺實名”的要求。同理,元宇宙中區塊鏈技術不可篡改、自動執行的邏輯也并不意味著意思表示瑕疵無法補救,智能合約的效力仍須依法認定,[53]參見郭少飛:《區塊鏈智能合約的合同法分析》,載《東方法學》2019年第3期,第12-13頁。版權法、合同法的基本原則具有適用的空間。架構本身是中立的,智能合約加持之下的架構運作樣態則體現了組織、運用架構者的意志,因而往往不是中立的。以“規訓”智能合約促進人本主義理念的制度化落實,要從賦權與限權兩個維度思考智能合約可能的運作方式,推動智能合約標準化。
從賦權角度,智能合約至少在如下方面呈現出向平等、公平的交易結構演化的趨勢。首先,自動執行機制的內在取向是及時履行,其具備比擬于自動售貨機的屬性,因而節約了合約執行的監督成本,使得侵權、違約在一定程度上變得不再可能,進一步保障了創作者的利益。其次,去中心化的架構一旦與權利公示系統相結合,并輔之以自動執行機制,作品傳播也就不再需要依附于大的內容平臺,創作者有望從格式條款的束縛中解脫。再次,智能合約的具體內容隱藏在代碼之中,代碼化的執行機制對合同條款具有解釋作用。概言之,對于自動執行機制中并未囊括的執行方式,可自行排除于合同許可、轉讓的范圍之外。例如,若合約僅能實現對存儲于特定網絡空間的作品復制件的歸屬的轉讓,則不應被理解為交易雙方就版權授權達成了合意。這種解釋符合“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余”的解釋規則,有助于防止因語詞概念模糊而帶來的相反解釋。如此解釋,亦最為契合“將未明確許可、轉讓的權利解釋為未轉讓”[54]我國《著作權法》第29條規定:“許可使用合同和轉讓合同中著作權人未明確許可、轉讓的權利,未經著作權人同意,另一方當事人不得行使。”的立法本意,實現對創作者權益的周延保護。最后,智能合約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著作財產權體系之不足,例如可針對數字藝術品的每次轉讓設置將交易增值部分按一定比例分配給創作者,使創作者獲得實際意義上的追續權。
從限權角度,智能合約的技術措施和格式條款屬性需要警惕。版權法上的技術措施指的是“用于防止、限制未經權利人許可瀏覽、欣賞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或者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提供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的有效技術、裝置或者部件”,[55]參見我國《著作權法》第49條的規定。技術措施以有效性為保護前提。智能合約的自動執行機制能夠將作品獲取權限封裝于智能合約的框架之中,若非破解則無法獲取作品,從而呈現出技術措施屬性。技術措施雖然極大地提升了版權保護效率,但其對公眾權益的侵蝕也引發了巨大爭議。在元宇宙時代,智能合約對用戶接觸作品權利的控制和合理使用的限制,與用戶主權的興起、參與文化的盛行格格不入,需要警惕。無獨有偶,鑒于智能合約通常為提供方自行編寫,其本質上屬于以技術方式體現的格式合同,并未留下自主協商的充分空間。例如,技術人員完全可以以技術方式將原作品封鎖起來,使用戶無法實現進一步的再創作。為充分釋放元宇宙中數字版權資源的價值,我們迫切需要打破版權封鎖生態,充分吸納技術人員、元宇宙版權產業鏈中的主體及相關公眾,制定順應開放創新生態的智能合約標準體系,實現技術與規則的二元互動。
(二)明晰著作人格權邊界,為二次創作解套
在元宇宙時代,用戶在已有作品基礎上創作出演繹性作品已十分普遍。考慮到演繹權可能對在后創作行為產生阻礙,學理觀點和司法實踐已提出限制在先創作者權利的解決方案,[56]關于這一問題的探討,See Omri Rachum-Twaig, Copyright Law and Derivative Works: Regulating Creativity, Taylor &Francis Group, 2019, p. 4;李穎:《信息網絡傳播權案件中行為保全適用問題的若干思考》,載《版權理論與實務》2022年第6期,第32頁;初萌:《全民創作時代短視頻版權治理的困境和出路》,載《出版發行研究》2022年第5期,第65-71頁。本文對此不再贅述。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這種二次創作行為可能存在侵犯修改權及保護作品完整權的風險,即便行為人已經獲得演繹權的許可。[57]參見張牧野與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等侵犯著作權糾紛案,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民事判決書(2016)京73民終587號。對這一問題的學術探討較為匱乏,這兩項權利的邊界仍需進一步澄清。
如學者所言,修改權一直是一項被解釋得十分混亂卻很少被認真研究的權利;[58]參見李琛:《論修改權》,載《知識產權》2019年第10期,第37頁。保護作品完整權無出其右。對于這兩項權利的內涵,多數學者從作品與作者之間的關聯出發,強調作品是作者的“精神之子”,作者對其表達享有自決權,[59]陶乾:《不同使用方式下保護作品完整權的侵權判定標準》,載《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第76頁。能夠對作品的展現方式實施控制。學者的主要爭議在于這兩項權利所能施加控制的程度:一種觀點將控制的行為局限于可能損害作者名譽的歪曲、篡改,即采客觀標準;另一種觀點并不考慮歪曲、篡改行為是否損害作者名譽,即采主觀標準。無論是主觀標準還是客觀標準,在適用于二次創作情形時,都會存在一個突出的問題:為維護原作者利益而犧牲作品可能含義的社會最大化實現。
在伽達默爾對康德藝術觀的解讀中,我們能夠看到作品脫離作者之后的無限潛能。他指出,康德眼中的藝術作品是天才的作品,藝術作品作為完美的出色物和典范的標志,就在于它為享受和觀賞提供了一個源源不盡的逗留和解釋的對象;一切作品都是片段的,需要讀者去完成它們。[60]參見洪漢鼎編著:《〈真理與方法〉解讀》,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100頁。按照這種觀點,藝術作品與一般制作物不同,后者具有一種目的,當它們滿足了規定給它們的目的后,制作活動就結束,制作物也就完成了;而藝術作品根本不會有此目的,對它可以無止境地加以解釋。[61]同注釋[60]。如上文所言,結構主義的作品觀為這種解釋提供了可能。而作為作者產物的作品,一旦進入社會交往、參與文化的具體語境,其意義的實現便更多依賴讀者而展開。羅蘭·巴特提出“作者已死”[62]羅蘭·巴特指出,無論作者是否在生理意義上死亡,我們在理解文本的時候都不應將作者置于重要位置,文本可以脫離作者而存在。See Laura Seymour, Macat Analysis of Roland Barthes'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Macat International Ltd., 2017, p. 10.的論斷正是基于此理。作者與作品之間既相互呼應,又相互平行:[63]參見張明:《重審“作者已死”:論作為“伴隨文本”的作者與作品》,載《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第151-152頁。從作品產出的角度,作者與作品是呼應的,這也是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背后的基礎邏輯;從作品的獨立價值來說,作品又是與作者平行的,這勢必在一定程度上對著作人格權提出挑戰。為了在平衡利益的同時,充分挖掘文本的社會價值,著作權法在設置著作人格權條款時應當同時考慮這兩個維度。
那么,我們應當如何在作品同作者的人格連結與作品價值的最大化實現之間取得平衡呢?本文認為,借鑒商標法中的“公眾誤認”標準不失為一個良方。具體而言,對是否侵犯修改權或保護作品完整權的判斷,應當以一般公眾是否會對作者所欲表達的觀點、闡釋的理念及傳達的情感產生誤解為標準。對于演繹作品,只要一般公眾能夠清晰地認識到其并非原作者所創作,那么所謂的歪曲、篡改便只是作品可能含義的另一種展現,即便改動后的作品反響欠佳,也由于欠缺與原作者的直接關聯而未導致產生誤解其原意乃至影響其聲譽的損害,故而不構成侵犯著作人格權的行為。
為進一步闡釋上述觀點,本文試以電影《九層妖塔》為例作一分析。該電影改編自張牧野(筆名天下霸唱)創作的小說《鬼吹燈之精絕古城》。電影上映后,有不少網友直言“這不是鬼吹燈”,并強調“再怎么改編精髓不能丟,不能讓路人看完電影后認為鬼吹燈講的是外星人的故事”。這些評論都認為電影存在對原作的篡改,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一評價也恰恰證明了評論者對原作的理解并未因電影而受到歪曲。而對于并未看過原著小說的人而言,只要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智,便理應知悉原作與改編后的作品之間是可能存在差異的,畢竟“在原作品基礎上貢獻了新的獨創性表達”這層含義已經被寫入改編作品的定義之中,改編作品總是會對原作品作出一定程度的改變。即便如此,只要演繹作品作者在作品中明確其并非原作品本身,一般公眾通常不會產生誤認,在本文提出的判斷標準之下便不存在侵犯修改權及保護作品完整權之虞。將這一解釋廣泛適用于元宇宙中的二次創作行為,有利于促進作品價值的釋放和用戶主權的實現。
(三)引入“作品使用”概念,澄清版權法的規制界限
關于因應元宇宙技術發展的版權制度變革,學界當前的討論集中于四個維度:一是探討“虛擬數據作品”是否具有可版權性;[64]參見楊吉:《論〈著作權法〉對“元宇宙”作品及其傳播的規制》,載《中國版權》2022年第3期,第17-22頁;李曉宇:《元宇宙下賽博人創作數字產品的可版權性》,載《知識產權》2022年第7期,第20-46頁。二是研究人工智能文本與數據挖掘是否構成合理使用;三是分析用戶二次創作行為的轉換性以及享有侵權豁免的可行性;[65]參見袁鋒:《元宇宙空間著作權合理使用制度的困境與出路——以轉換性使用的界定與適用為視角》,載《東方法學》2022年第2期,第44-57頁。四是考察NFT數字藏品交易這一新業態所涉版權問題[66]參見初萌、易繼明:《NFT版權作品交易:法律風險與“破局”之道》,載《編輯之友》2022年第8期,第96-104頁。。除最后一個問題是涉及版權新業態的應用性問題之外,前三個問題具有共同的理論指向——版權法的規制界限。澄清版權法的規制界限不僅能夠解決元宇宙所引發的所謂“新”問題,也具有面向未來更多技術可能性的啟示意義。
對版權法規制界限的確定,既要考察其制度目的,也要結合權利客體展開差異化考量。從根本上說,商標權、專利權保護的客體,或強調符號與商業主體之間的關聯,或注重先進技術的生產和運用,因而具有很強的實用價值,能夠滿足人們的某種欲望;而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的作品則重在滿足心靈的旨趣,這種旨趣與欲望無關,且要排除一切欲望,[67]參見[德]黑格爾:《美學》(第一卷),朱光潛譯,重慶出版社2018年版,第44頁。其目的在于“喚醒各種本來睡著的情緒、愿望和情欲,使它們再活躍起來”[68]同注釋[67],第55頁。。從美學理論出發,可以認為專利權、商標權的客體滿足于人類“占有和利用的欲念”,服務于人的需要;而受版權保護的作品對人的滿足則“沒有對欲念功能”的關系,一部作品并非為其他實用性目的而存在,而是“因為它本身”可以引起的快感而重要。[69]同注釋[67],第70-71頁。與之相應,我們之所以要激勵作品的創作,也并非因為作品可以發揮任何實用性功能,而是因為作品對人的吸引力,以及對精神文化需求的滿足。從這一區別出發,作品本身對受眾的吸引力,應當成為確定版權法規制界限的核心要素。
將直接使用了作品對受眾吸引力的行為界定為“作品使用”,并以之作為版權法的制度主線,元宇宙引發的許多“新”問題便能夠迎刃而解。具言之:其一,作品對受眾的吸引力在于其所表達的內容、傳遞的情感,這與作品是以實體還是數據的形式存在并無關聯,元宇宙中作品的可版權性自無疑義。其二,元宇宙中人工智能在訓練中對作品的使用,雖然從形式上看可能涉及復制行為,但并不能夠使受眾感受到作品的吸引力,故不應屬于受版權法規制的行為,應當納入合理使用范疇。只有當人工智能輸出、傳播的作品存在侵權風險時,才應將這一輸出、傳播行為納入版權法規制。[70]參見初萌:《人工智能對版權侵權責任制度的挑戰及應對》,載《北方法學》2021年第1期,第138-150頁。其三,對于用戶在元宇宙中的二次創作,若創作的作品與原作品存在極大的內部距離,使原作者對受眾的吸引力在新作品中黯然失色,或者不易為公眾所覺察,[71]參見易磊:《〈德國著作權法〉自由使用制度研究》,載《蘇州大學學報(法學版)》2019年第3期,第89-90頁。這種二次創作便不應受演繹權控制,而屬于用戶的創作自由。事實上,“作品使用”概念的引入并非空穴來風,學界廣泛探討的“轉換性使用”概念已有此意;無論是指向使用作品并非為獲取其中內容的目的轉換,還是對作品的使用產生了與原作品截然不同的新含義、新價值的內容轉換,其所針對的都是“作品使用”。由此可見,“作品使用”其實是比“轉換性使用”更為基礎的概念,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對版權保護本旨的把握。除輔助合理使用的判定之外,“作品使用”概念的引入對網絡空間復制行為版權法內涵的確定以及作品含義的澄清也都具有啟示意義,這一概念的包容性和前瞻性能夠為版權法應對技術變遷提供有益的指引。
(四)試點“監管沙箱”,探索版權交易與金融風險切割的具體路徑
作為元宇宙中的重要分支,NFT數字藏品交易在我國迅猛發展,在NFT以數字藏品的形式在中國正式上線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我國各平臺發售NFT數字藏品的總市值已達到1.5億元。根據Valuates Reports發布的報告,預計到2028年,NFT市場規模將增長至73.908億美元。[72]《預計到2028年NFT市場規模將增至73.908億美元》,載NFT之門網站2022年6月22日,https://nft.yxyygzs.com/index.php/800/.如果說NFT唯一性、稀缺性、不可分割性的特點,為數字資產的存儲、流轉及數字經濟的發展打開了想象空間的話,NFT價值的充分實現則更多依賴于二級市場交易的放開。
目前,我國國內監管政策尚未作出明文規定,但NFT二級市場的合法性空間仍不充分。[73]參見蘇宇、李懷勝、陳吉棟等:《NFT政策研究報告》,載《上海法學研究》2022年第11卷,第146頁。2022年2月18日,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了《關于防范以元宇宙名義進行非法集資的風險提示》,對編造虛假元宇宙投資項目、打著元宇宙區塊鏈游戲旗號詐騙、惡意炒作元宇宙房地產圈錢、變相從事元宇宙虛擬幣非法謀利等違法活動進行了警示。總的來說,這一規定并未直接觸及NFT數字藏品二級市場交易的合法性問題,該領域的相關政策依舊存在盲點,需要進一步澄清NFT的法律屬性以及金融監管的行為邊界。
從版權的角度,NFT二級市場交易只是改變了存儲在特定網絡位置的數據文件的訪問、歸屬權利,能夠確保作品復制件在同一時間僅由一個主體享有,因而并不涉及復制行為。更確切地說,它對應的是一種新發行模式,它使用戶可以像擁有一件實體資產一樣對數字藏品進行收藏和使用,[74]同注釋[48],第27頁。呈現出所有權應有的樣態。正因如此,這一交易完全可以與轉移所有權的線下發行行為進行類比。發行權用盡原則因而具有適用的前提。[75]參見初萌:《論發行權用盡原則在網絡領域的適用》,載易繼明主編:《私法》(第32卷),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232-251頁。唯不同者,線上復制件不會毀損的特性使得二級市場能夠與作品的一級市場形成完全競爭關系,因此或許有必要通過采取技術措施的方式,對二級市場交易次數施加一定的限制。如此一來,NFT數字藏品二級市場流通的版權障礙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但即便如此,其中的金融風險依舊存在。以NFT為載體的數字藏品容易產生高溢價,用戶實際上可以通過NFT交易完成資金流轉,從而具備了從事洗錢等違法犯罪活動的可能性。[76]同注釋[73],第139、151頁。對于這一問題,關鍵在于為NFT轉售價格尋找價值支撐,這就需要將平臺的品質控制和數量控制、版權作品本身的審美意義所帶來的價值與其可能的金融風險進行有效切割。
為貫徹包容審慎的監管理念,適時開啟元宇宙監管沙箱,是在商業模式野蠻生長與控制風險之間尋找安全可持續方案的一種有益嘗試。有條件的地方金融監管部門可采取成立工作組的方式,制定試點方案,選取有意愿的元宇宙企業進入監管沙箱,在可控范圍內試驗包括二級市場交易在內的商業模式,逐步探索并厘清元宇宙金融監管的界限,在確保金融安全的同時,回歸數字經濟的本質——交易,進而促進元宇宙中作品價值的充分實現。
結 語
元宇宙是一個創作資源充分涌動、作品的生產要素功能充分施展的時代。用戶主權、參與文化的強化,平臺壟斷地位的削弱,共同促成了自然人版權主體獲益權、表達自由權利的實現,這一發展趨勢符合人本主義版權保護理念的本旨。順應這一潮流,版權制度需要相應作出變革。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中,技術可能的賦權作用與限權作用需要同時納入考量,版權的公共文化面向需要進一步強化。與此同時,元宇宙引領的新潮流也有助于澄清版權保護的邊界,彰顯版權制度的理性色彩。雖然本文將視點聚焦于版權,但元宇宙所引領的萬眾創新、協同創新潮流對所有知識產權具有共通的啟示意義——從許可權、禁止權轉向獲益分配權,或將成為知識產權制度變革的一條基本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