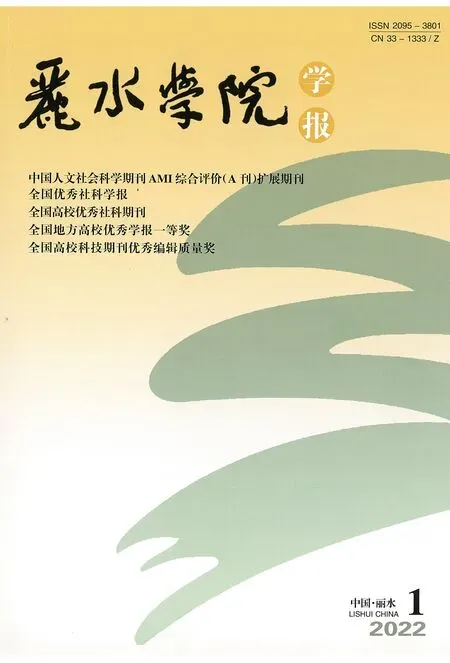殖民與德化的帝國觀比較分析
——評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
呂承文
(南京審計大學國家治理與國家審計研究院,江蘇 南京 211815)
英國政治學者邁克爾·曼在他的著作《社會權力的來源》(叢書共四卷)深刻地研究了“社會權力”及其演變。關于對社會權力的理解,學界觀點不太統一。曼的“社會權力”概念事實上是基于一種宏觀視角抽象形成的,并與人性密切相關,主要是指一種“為了自利的權力”和“有組織的權力”[1]13-15,它的分層理論產生了四種類型構成——意識形態權力、經濟權力、政治權力、軍事權力。
曼的四卷巨著著墨描繪了自原始社會至2011年以來的近萬余年的政治史畫卷,并創造了一套政治演變史的理論解釋框架。他的研究可以被定性為多元學科的、綜合領域的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同時也包含了定性與定量分析研究。曼的理論體系建構,帶有非常明顯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影響的痕跡,他熟悉地應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唯物辯證法和階級分析法,雖然,曼看上去并不是那么推崇馬克思。此外,歷史制度主義分析法的廣泛使用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當前,已有學者對曼的四卷著作進行專門評述,史煥高(2010)從政治學視角評述了第一、二卷[2],李鈞鵬(2014)從價值角度評述了第一卷[3]。2015年以來,邁克爾·曼的第三、四卷中文版陸續在大陸出版。筆者囿于閱歷及學功,只得選擇性品讀全書四卷,并作出粗淺的介紹與評析,以饗讀者。
曼全書的理論框架可以概括為“一綱四維”。一綱者,是指曼在書中所欲追求解答的核心問題,即“社會權力來源為何”,如圖1 所示。四維者,是指曼對社會權力進行細分的四大主要內容,依次為意識形態權力、政治權力、經濟權力、軍事權力。曼并沒有明確告訴我們這四種社會權力流變的歷史次序,何者在前,何者在后,但這并不意味著曼可以放棄對四種權力的邏輯關聯及相互影響的充分解釋。曼的理論工具本身是存在前提的,而且,這個理論工具在本書的作用體現在被用來闡釋不同時期的國家類型的產生及發展,換句話說,只有把這個理論工具放置在具體的歷史案例中才能有效檢驗它自身的真理性。

圖1 理論工具的簡化示意圖
在政治學中,不可思議地存在一種矛盾現象:我們嘗試在國家產生之前探究權力的本源,卻又不自覺地將權力與國家本身緊密聯系在一起,似乎,離開了權力國家的本質就難以得到體現,至少難以直接觀察。曼所要探討的社會權力限定于宏觀的政治學之中,即社會權力的來源,并探究各類社會權力組織(如政治/黨、國家機構、物質的軍事力量)對四種社會權力的占有及掌握情況。換句話說,社會權力的來源與四種權力分類本身與國家密不可分。國家的一種特殊歷史形態即為帝國,帝國的討論不僅能反映國家形成的內部社會權力變化(國家崛起),也能體現出國家之間的外部社會權力競爭(列國爭霸)情況。本文選取帝國觀作為曼的書評切入點,正是基于這個考慮。
一、帝國觀的形成:國家與權力的聯系
關于國家如何演變為帝國的探究被曼很好地貫穿于整部叢書之中。國家的定義通常是四要素說,即領土、人口、管理、文化,任何國家,無論古代現代,還是大國小國,都一視同仁地受到這個概念的界定。國家并不是無生命物,它是由生活在同一片區域有著共同的文化(語言、文字、信仰、習俗)的人們通過一定的政治統治和行政管理形式組成的活的運作系統。由是,因人性會對人發生作用,面對有限資源,人的貪婪欲望總呈現無底洞態勢,無論在古代世界還是現代世界,小國爭相崛起成為大國,大國之間相互爭霸,搶奪霸主地位以牢牢掌握社會資源的主宰權。帝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大國之間權力角逐的爭霸產物。
西方的帝國概念源自拉丁文imperium(羅馬帝國意義上的治權),本指官員所行使的權力,而由官員行使權力的空間范疇視之,它同時具有了地域空間的內涵,所反映的是治權在不同地理范圍內的實踐。古代文獻提及治權時常加一限定語“domimilitiaeque”(國內的和戰場的),將治權分為國內治權(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治權兩類。在羅馬城內行國內治權,在羅馬城外行軍事治權,由此可見治權在民事領域與軍事領域并置[4]。
作者著重分析的是二戰(1945)以來人類歷史的發展狀況。曼認為,在他劃分的這一歷史時期,國家類型基本以資本主義的生產性經濟帝國為主,簡言之,即是國家及其權力皆為經濟服務。那么,該時期社會權力中的經濟權力似已凌駕于其他三種權力之上。在二戰以前,國家基本以政治權力突出的傳統帝制國家為主,一切皆圍繞著政治統治而服務,軍事權力(征服)成了政治權力的小伙伴。盡管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也出現過這樣的傳統帝制國家,如日本人在二戰期間建立的東亞海陸帝國,那也不過是一種“回光返照”。
相比之下,日本人在二戰時期塑造帝國時采取的軍事征服手段顯現得簡單粗暴,在這一點上,英國人更顯得技高一籌,他們知道如何對四種社會權力搭配使用,比如,政治上的分而治之,經濟上的援助,意識形態上的選擇代理人,等等。所以,不難理解,為什么英國人總是在世界格局中充當贏家。英國人聰明地意識到,“與其教會本土人自治,不如讓他們加入到我們的政府中來”,這正是英國人對殖民地與附屬國實施的柔性羈縻戰術。中央集權(體現為政治權力)是國家迅速強大崛起的前提,所以,“歐洲人扼殺19 世紀祖魯人、索科托人、馬克普迪和阿散帝國等邁向中央集權的運動,從而終結了非洲土著成為世界經濟行動者的機會”[1]30。
如果說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國家間處于熱戰狀態,國家通過軍事權力來促進政治權力擴展的政治目標;那么,二戰結束后世界進入到一個以意識形態權力為國家間競逐資源途徑的嶄新時期,即冷戰時期。整個世界幾乎圍繞著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而被人為劃分為兩大國際帝國主義陣營。事實上,意識形態已成為當代國家統治與爭霸世界的高明工具。
中外學界對意識形態的態度是矛盾且曖昧的。學界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者,如王惠巖(2006)認為“如果單純使用‘政治態度’、‘政治價值觀念’、‘意識形態’、‘民族心理和文化模式’等概念,都難以完整地概括這種關系,因此,人們開始使用‘政治文化’這一新的概念,用以表達和研究影響政治體系運作的上述因素”[5]。由于政治文化是“一定的文化在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6],所以國內學者都認為它具有鮮明的階級性,而且,作為國家的主流政治思想觀念,政治文化在本質上與意識形態極其類似[7]。在西方,政治文化被認為“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8],但這個概念(政治文化)卻也似被“刻意”回避了。事實上,意識形態屬于哲學范疇,最早由托雷西使用,包含了對事物的感觀思想,是觀念、觀點、概念、思想、價值觀等要素的社會存在的總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意識形態被定義為“社會再造的工具”,這樣就自然地成為一種工具,更符合邁克爾·曼的立著初衷。
筆者認為,社會權力的四大權力通常是共時存在的,不管它們之間是此消彼長還是相生相長的關系,它們都“不是單一社會整體的維、層次或要素”[1]13。總之,四者皆須為國家的政治目標實現而發揮作用,這種帝國觀是建構于國家之上的權力觀。由此,曼的社會權力劃分是從恩格爾問題——“經濟權力決定一切”開始的,但是他卻得出了韋伯式的否定[1]18。西方殖民者(如老牌英帝國)搭配使用四種社會權力,對即將產生的國際新秩序中世界資源的調整與再調整及占有、利用、控制,正是曼意義上的帝國現象。
二、帝國觀的偏執:殖民主義與西方中心
曼在國家研究上延續了西方政治學傳統,研究對象從“國家”擴展到“帝國”。盡管曼否認布勞特的“歐洲中心論史學家”的指責[1]12,然而曼的西方主義里包含著與生俱來的羅馬帝國情愫。這是因為西方的帝國概念是從羅馬帝國的治權(作為羅馬官員的至高權力)概念中衍生出來的。曼在第三卷中列舉的現代世界帝國正是從古代世界帝國中進化而來,主要包括直接帝國(指直接控制海外領土的大帝國)與間接帝國(指利用本國意識形態權力實施宗主國影響的帝國)。曼又在第四卷中進行了帝國類型的豐富與擴充:(1)非正式帝國:通常對附屬國采取有限的經濟強制;(2)非正式的炮艦帝國:實施直接的軍事干預;(3)近世的非正式帝國:實施隱蔽的政治控制;(4)經濟帝國主義:采取完全的經濟強制。從本質上看,所有類型的帝國都有著共同的政治目標,即實現世界霸權,獲取世界資源分配的主導權。曼所作的帝國類型劃分不過是從四種權力途徑出發設定實現霸權目標的手段性種類。西方的帝國的存在就是為了擴張而服務的。羅馬帝國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是擴張性的權力帝國而非類似東方世界的防御性的領土帝國。
西方帝國觀是在對羅馬帝國認知基礎上將權力行使范疇擴大到地理空間范疇后形成的,而且作為權力觀的衍生品,在包括羅馬本土以及擴張的殖民地的統治上,西方人對羅馬帝國的形成歷史應然地帶有鮮明殖民主義的帝國觀,并且傾向于強加于其他的非西方世界,致使西方中心主義現象屢屢發生。澳大利亞學者布雷特·鮑登(Brett Bowden)在自己的專著《文明的帝國:帝國觀念的演化》中認為文明三要素是經濟文明、社會文明和法律文明,并將帝國與這種文明的內涵聯系起來,但這種文明是建構于西方中心主義之上的。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達爾文在《未終結的帝國》中構想了英國人的帝國觀,這是一種建立在往昔曾作為英帝國殖民地的當今英聯邦國家的統治與管理之上的國家政治觀。所謂“帝國觀”就是人們對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的一種國家類型的帝國的政治態度、觀念及思想等。
在作者看來,自二戰以來現代世界出現過的現實帝國主要是:第一種是已衰落的英帝國(二戰以后,英帝國霸權全面衰落,只剩下微弱的意識形態影響,主要體現在英聯邦國家);第二種是盛極一時卻終而解體的蘇聯帝國(筆者并不以為蘇聯的帝國滅亡在意識形態,而恰是它混淆了四種權力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第三種是仍然活躍在世界政治舞臺的美帝國。
1945年以后歐洲霸權全面衰落,世界主導權落在美、蘇之手,后來又完全為美國所支配。時常扮演世界警察的美帝國(非殖民地帝國或代理人帝國)、與蘇聯帝國類似的傳統形式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它們的特征主要是:(1)美國的帝國疆域里沒有直接的或間接的殖民地,“它對整個帝國疆域的運作涉及從完全臨時性殖民地(非正規的帝國)到純粹的霸權,完全臨時的殖民地通過調節、征服和撤軍的順序而形成”[9]30。美國人只會向當地灌輸本土意識形態,使之精神上美國化,以實現精神控制的高明統治術。(2)美國仍然會適時通過戰爭(軍事權力)來體現自己的霸權,“美國會時不時發動重大的政府戰爭,但這不是為了建立殖民地,而是在建立代理者之后即行離開,但通常會在當地保留軍事基地”[9]31。(3)美國的帝國領域中有它無數的債權國或債務國,比如,20 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末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國通過實行美元金本位政策來達到控制世界金融的目標,隨后的馬歇爾計劃也變相地以經濟援助來攫取殖民地或附屬國及其他國家的各項特權。
美國的帝國形式及保持,正是通過合理巧妙地使用四種社會權力而實現的。在政治學的國家學中,國家利益通常是擺在國際交往首位的,這使得傳統的目的性帝國才逐漸分化為曼在書中列舉的手段性帝國。美國人作為英國人的后裔,又是技高一籌。他們的聯邦政府又比英國人的君主立憲政府多了不少集權因素和民主因素,竟讓兩種天然相斥的政治因素巧妙結合起來。正是如此,美國人自二戰后,取得了比19世紀的英國人更大的帝國成就。兩次世界大戰讓人類遭受了慘痛教訓,以致軍事權力很少乃至不被經常使用,取而代之的更多是政治權力的使用。政治權力的恰當使用,實足使意識形態領域的勝利更加鞏固,民主曾是蘇聯帝國的話語霸權產物,自由是美帝國的話語霸權產物,自蘇聯解體后竟全部為美帝國“收割”,這說明意識形態從一開始就是為政治權力服務的。如今,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卻將之當作思想武器,正在向東方世界發起進攻;這種思想武器殺人不見血,比導彈厲害百倍。社會公民權在戰后興起,它很難說是意識形態的專利。事實上,兩種主流意識形態都不排斥它,甚至將之作為攻擊對方的有力武器。
曼在洋洋灑灑地描繪完上述歷史長幅畫卷后,定下結論:“我描述了意識形態范圍擴寬厚又變窄的過程,資本家的勝利和苦難,國家之間戰爭消退并為和平或內戰所取代,國家公民權的加強,除一個帝國之外其他所有帝國為民族國家所取代。”[10]這一個帝國即是我們熟悉的美帝國,它正在享受著全球化的政治福利。
玩弄意識形態權力的帝國通常也會被意識形態戲弄。從意識形態上來講,帝國一詞早已失去其古樸的含義,暗含了臭名昭著的“帝國主義”意義。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n)說:“皇帝和帝國當然是古老的,但帝國主義卻是相當新穎的。”從19 世紀90年代開始,“帝國主義”一詞“突然變成一般用語”,他還借用一位英國自由黨員的話說:“(它已)掛在每個人嘴上,用以表示當代西方政治最有力的運動。”[11]古老帝國的輝煌與榮耀被19 世紀末人們對帝國擴張的恐懼取代。西方帝國的意識形態,或者他們所謂的文化輸出,即是打著反對獨裁的名義在搞獨裁。無論是正統的古羅馬帝國,還是現代的杰斐遜所言的“自由帝國”[12],事實上都是一種基于西方文化基礎上的意識形態產物,這對他們建立實體的帝國形式起到了重要作用。
“冷戰期間,美國的盟友都是君主,蘇聯的盟友主要是帶有更加進步目標的城市民族主義者。然而,由于缺乏民眾的支持,這些政權都走向了專制。”[9]156在選擇代理人的策略上,美國人與蘇聯人都犯了錯誤,前者選擇了正統卻腐朽的政權,后者選擇了革命輸出卻因內戰不得人心。曼宣稱冷戰的結束是一種意識形態權力的政治結果。那么,首先須看看當代世界有何種思潮已被確立為意識形態。除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外,他還列舉了新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新凱恩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保守主義。
“共產主義的終結是美國的勝利”,“共產主義的滅亡主要是因為其內部矛盾,主要是經濟和經濟方面的矛盾,并因此導致意識形態的解體”[9]166。蘇聯雖解體,東歐已劇變,但這不能說是共產主義理想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正確造成的。理論從來是指導實踐而不是相反,如果現實出現了理論所未能預料的失敗情形,有一種可能是:理論實踐者的錯誤認識及其指導下的錯誤做法。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20 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們,當時它是與蘇聯的經濟成功和軍事實力聯系在一起的。然而,當蘇聯發生經濟蕭條且不能維持其軍事力量時,這種吸引力也就隨之消失了。西方的價值觀和體制已開始吸引其他文化的人們,因為它們被看作是西方實力和財富的源泉[13]73。在前共產主義國家,宗教的普遍存在和現實意義一直是不言而喻的。宗教復興席卷了從阿爾巴尼亞到越南的許多國家,填補了意識形態崩潰后所留下的空缺[13]77。
在早期社會主義國家那里,“集體權力輔以分配權力”在那里被視作效率的表現,而市場與經濟之間的關聯則須視情況而定[9]171。計劃經濟在戰后能迅速給國家帶來經濟奇跡確實有一種神秘色彩,只可惜它不能長久。隨著經濟發展的深化,金融作為高級經濟形式的興起,計劃遇到了金融資本與國家權力之間注定要融合的歷史難題。早期的社會主義試圖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公平主義出發抵制這種經濟發展趨勢,結果卻是鎩羽而歸。然而,與二戰爆發時的情形相比,資本主義世界盛行市場主義之道,恰好順應了金融化的規律,從而取得了更為長久的經濟奇跡。這使得社會主義陣營在經濟領域吃了大虧。
在“自由”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所出現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早已不是意識形態權力所能解決的問題。經濟的問題須用經濟的手段解決。凱恩斯敏銳地意識到這點。他給西方的資本主義陣營國家帶來了新自由主義,這種演化的意識形態本質“迫使人們放棄福利,然后轉向‘工作福利’,也就是只有在人們能找到工作時候才向他們提供有時間限制的福利”[9]195,這正是資本主義世界批評社會主義國家集權過度的地方。意識形態總會通過國家滲透于其他權力領域,起初正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
總體來看,西方的帝國形態在軍事權力上的一個特征是擴張,是領土的不斷擴大。在英帝國尚未全面衰落時,出現的新的帝國防衛思想主張,“應盡可能集中兵力保衛聯合王國,而把反對外國對帝國遙遠屬地侵略的任務主要托付于帝國的海上霸權”[14]。帝國的另一特征是殖民,并借此來實現文化和經濟的輸出。西方語境中的帝國幾乎等同于一種國際體系:“在人類絕大部分的發展過程與歷史演進當中,帝國一直是典型的政治形態。帝國無意在某個國際體系中運作,它期望把本身建立為一個國際體系。”[15]13事實上,連同英國在內的歐洲諸國在中央集權上做得并不怎么好,他們曾一度想效仿中國歷代王朝大一統的做法,卻本能地把政治權力當作惡魔①在西方學界,很多學者都把國家、政府、公共權力視作公民自由的大害。例如,密爾指出“政府整個來說只是一個手段,手段的合適性必須依賴于它的合目的性”([英]密爾.代議制政府[M].汪蠧譯.商務印書館.1982:17-18.)。利普森特進而解釋:“對于政府權力的擔憂一直困擾著人們。為了避免‘服務的工具’演變成‘奴役的武器’這一‘權力悖論’發生。”([美]萊斯利·里普森等.政治學的重大問題[M].劉曉等譯.華夏出版社.2001:63.)。羅斯金更是認為“政府的任務是為所有公民提供生存、穩定以及經濟的和社會的福利”([美]邁克爾·羅斯金等.政治科學[M].林震等譯.華夏出版社.2001:39.)。等等。,這種矛盾心理注定了歐洲至今不太可能重現羅馬帝國。
三、帝國觀的回應:德化意識與中華帝國
曼在帝國問題的討論上,并未深入探討西方漢學中時熱的“中華帝國”,這是他對帝國分類的理論局限所在。本文關于“中華帝國”的探究不僅用來補充曼的帝國觀,而且還使爭論得以從歐洲(西方)中心重返世界中心。這種由西方學者熱捧起來的“中華帝國”概念實際上是迎合了西方的帝國觀,一種必須擁有殖民地并進行統治的觀念。西方很早就開始稱中國王朝為帝國②馬可·波羅用Catai 稱蒙古帝國,來自契丹(Cathay)這個詞。利瑪竇稱明朝為“大明”,沒用帝國概念。其后,曾德昭(Alvaro Semedo,1585—1658)在其西班牙文著作《中華大帝國志》中稱中國為“中華帝國”(Imperio de la China)。衛匡國(Martino Martini,1614—1661)在其《韃靼戰紀》中將中國稱為“中華帝國”。。中國與德國歷史上都曾建立過普世意義上的帝國,并分別選擇了龍與鷹作為皇權的象征[17]。近代以來相當多的外文著作稱中國為帝國(Imperial China 或the Chinese Empire)(詳見表1)①比較有代表性的英文著作有:J.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London: Charles Knight,1836;H.Ballou Mor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London:Longmans,1910;P.A.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 Press,1970;William T. Rowe,China's Last Empire:The Great Qing,Belknap Press,2012;P.Gue Zarrow,After Empire: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1885—1924,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 Press,2012;Odd Arne Westad,Restless Empire: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Basic Books,2012。。在“中華帝國”問題上,代表觀點有:費正清(2010)認為東亞社會——中國、朝鮮、越南、日本及小島王國琉球——都是由古代中國分衍出來,并在中國文化區域內發展起來的。這個“遠東”世界是以中國為中心的。由天子統率的所謂“天下”(普天之下)有時包括中國(自稱為世界中心的“天朝”)以外的整個世界。但在習慣上,一般是指中華帝國[16]1。“中華帝國”必須是實際的大陸性“東亞帝國”,從帕米爾高原直至釜山,這些地方都是中國每個大王朝力圖控制的[16]3。但是,關于“中華帝國”的存疑考量也一直是學界的訟案。

表1 與“中華帝國”命名有關的部分外文著作
比較早將“Empire”翻譯成“帝國”的是清人嚴復。但嚴復沒有將中國列入帝國行列,這也反映了近代中國學人認識到了中國王朝與歐洲帝國概念的差異。有學者認為傳統中國為“中華帝國”是對中國王朝的誤讀,無論是英文的“Empire”還是古漢語的“帝國”,用來稱呼中國王朝都是誤稱(misnomer)[18]30。中國統一王朝時期的天下秩序與羅馬帝國或不列顛帝國的世界秩序存在諸多差異。錢穆先生也認為不要隨便使用帝國概念描述中國:“我們現在的毛病,就在喜歡隨便使用別人家的現成名詞,而這些名詞的確實解釋,我們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稱中國為大清帝國,又稱康熙為大帝,西方有帝國,有所謂大帝,中國則從來就沒有這樣的制度,和這樣的思想。而我們卻喜歡稱大漢帝國乃及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觀念下,這些都該謹慎辨別的。”[19]此意義上的“帝國”異于彼意義上的“帝國”。
一般而言,歐洲的帝國具有兩大顯著特征:一是具有強大的、超越一般國家的力量去兼并他國或占有殖民地;二是元首稱帝[18]32。不同于歐洲的帝國,中華文明世界雖然沒有類似的帝國概念,但卻有天下秩序及其觀念,并且與前者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即否定了殖民觀。歷史上的中華帝國全盤接受了儒家學說中的德化觀。中國的研究者也常將天下秩序代替帝國秩序。比較典型的一種觀點將“中華帝國秩序”與“羅馬帝國秩序”和“阿拉伯帝國秩序”并列,認為它們存在共同特征是:在一定地域范圍內以帝國中心為統治的圓心;等級制的權力支配體系;強制性的強權統治①尚偉.世界秩序模式研究[D].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12):67。所謂的“強制性的強權統治”特征顯然不符合中國傳統天下秩序的本質。。而區別在于天下秩序是行為體互動博弈達成的共識,并非殖民主義政策的結果。那種借用歐洲“羅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的概念創造“中華帝國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概念的做法是言過其實的②用此概念形容中國構建世界秩序的戰略雄心的文章很多,比如《經濟學人》的“菩提樹”(Banyan) 專欄的一篇文章《中華帝國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認為中國“不僅僅只是挑戰既存的世界秩序,它正在構建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盡管緩慢、亂糟糟,并且顯然沒有最終觀點”。Banyan Columnis,it”Pax Sinica,”The Economist,Vol.412,Issue 8905,Sep.20th,2014,p.39,以及Steve Levine:”Pax-Sinica: Why the U.S. Should Hand over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to China,”Foreign Policy,June 27,2012,see http://for-eignpolicy.com/2012/06/27/pax-sinica-why-the-u-s-should-hand-over-afghanistan-and-central-asia-tochina /,2015-09-10。。傳統東亞的秩序得以維持的雙重要素——權力(治統)和價值觀的大體一致(道統)——與基辛格對歐洲維也納均勢體系的分析具有相似性。基辛格認為,在維也納體系中“權力均衡降低訴諸武力的機會;共同的價值觀減低訴諸武力的欲望”[15]60。在西方漢學者們看來,“中華帝國”統治者在對外關系中使用的主要手段是兩個極端,要么是軍事征伐、行政同化,要么是不理睬、不接觸[16]12。
異于西方帝國的“殖民觀”理論,天下秩序的合法性來源于中國“帝國戰德”的道義制高點,并且在國際秩序維系上達成了與周邊政治行為體的共識。天下秩序合法性的獲得需要有治統和道統雙重認同。王夫之曾認為天下秩序可以抽象地存續。中國參與構建世界秩序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國內治理價值觀與世界主流價值觀之間的關系。古文中的“帝國”代表了中華思想追求的德化天下的高級階段即“帝國戰德”。隋代王通論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20]西方的帝國即類似王通所論的強國與霸國,在道義上遠低于中國語境中的帝國。道義上的中國式帝國觀構成了德化觀的基本內涵。歷代中華王朝精心營建的朝貢體系被認為是一種以中華正統王朝為中心的天下秩序(其實是東亞秩序),周邊附屬國依附的是中華王朝的文化而不是權力,中原王朝對附屬國既沒有治權的介入,也沒有領土(殖民地)的需求,只要遵奉中華王朝的正朔(附屬國之間的糾紛可交由中華王朝進行裁決,中華王朝律法成了一定意義上的國際法)、定期參與朝貢貿易,則就是中國以天下觀、德化意識為內容的帝國觀支配下的中華文化圈之內國家。中華王朝自秦漢隋唐以來歷代都有過軍事征服擴張行動,基本是在傳統中國中心主義的地理范疇之內——西入蔥嶺、東盡朝鮮、北上漠北、南下交趾,更多體現為一個防御性的領土國家,但又對疆域的概念格外模糊。
事實上,在開疆拓土問題上,西方人界定的中華帝國也采取異于西方的征服措施,這正是德化意識的實踐表現形式。“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中國的多民族共治的認同已經使王朝的統治者自認為實現了傳統中國統治者追求的最高目標即“德化天下”①比如,雍正說:“上天厭棄內地無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為內地主。”參見清世宗.大義覺迷錄(第1 卷)[M]//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清史資料(第4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5 。。王爾敏也指出:中國同化四夷“不是設重兵置總督……雖然沒有發展出外交部,卻也沒有轉變為殖民部”,中國只把天下的人分成“教化與無教化二種”[21]。中國歷史研究權威日本學者威堀敏一認為:古代中國(比如隋唐)的世界秩序“并不是由于中國的征服和強制而片面強加于人的。……不同于主要依靠征服而建立的羅馬世界帝國”[22]。當然,并不能因為古代中國對外征服戰爭的開展頻率較低,就認為中華帝國(王朝)只有“德化”沒有“征伐”。中華王朝的深刻內涵反倒使曼的帝國界定及分類出現了一定的困境,除了每一個文明與生俱來的中心意識是共同點外,“中華帝國”采取的是與西方帝國完全不同的統治方式,更關鍵的是中華王朝在歷史上從未像羅馬帝國那樣中斷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