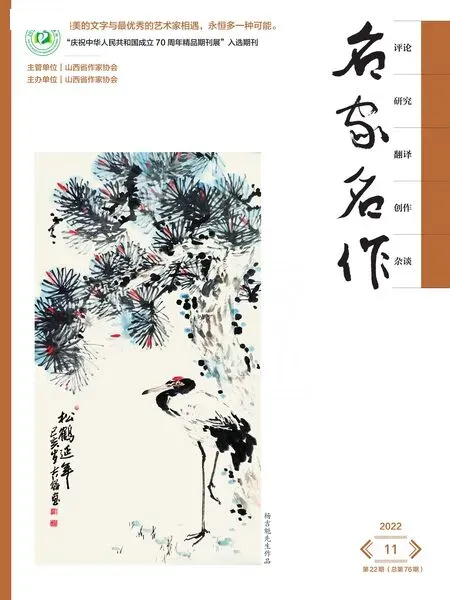流散視閾下V.S.奈保爾《米格爾街》的多維度漂泊
李晨陽(yáng) 韓 秀
一、因流亡漂泊產(chǎn)生的“無(wú)家感”
“現(xiàn)代西方文化在相當(dāng)大的程度上是流亡者、移民和難民文化。”地域的遷移早已成為人們熱切關(guān)注的話(huà)題。而流散書(shū)寫(xiě)所表達(dá)的流亡、尋根主題與全球化時(shí)代巨變不謀而合。流亡,“是一種被外力驅(qū)逐出家園,并且放逐出異地的政治與文化活動(dòng)。”和奈保爾本人一樣,出生在特立尼達(dá)這樣殖民國(guó)家的人,如果他們有機(jī)會(huì)選擇自己的出生地,相信絕大部分人都不會(huì)鐘情于這樣一個(gè)整個(gè)國(guó)土先后被西班牙、英國(guó)殖民的破碎故鄉(xiāng)的。那種無(wú)法選擇歸屬的苦澀與心靈落差也是像奈保爾這樣的“世界公民”一生的羈絆。從牛津大學(xué)畢業(yè)后,他選擇了在倫敦工作,在1954年5月3日給母親的信中他這樣寫(xiě)道:“我不想強(qiáng)迫自己適應(yīng)特立尼達(dá)的生活方式,那里的人們卑微狹隘、目光短淺。您不要以為我喜歡待在英國(guó)。這是一個(gè)種族偏見(jiàn)肆意橫行的國(guó)度,我當(dāng)然不愿意留在這里。”在《米格爾街》中,奈保爾也表示特立尼達(dá)是被殖民文化侵蝕的地方,一個(gè)任何人不會(huì)把眼光放在這里的街道。“任何一個(gè)人無(wú)意間開(kāi)車(chē)經(jīng)過(guò)這里,他肯定說(shuō)一句:‘這里是貧民窟!’”特立尼達(dá)給奈保爾帶來(lái)的創(chuàng)傷可見(jiàn)一斑。
奈保爾的“無(wú)家感”情愫即是上文提到的“遷移”。“在地理層面,遷移通常指從一個(gè)地區(qū)、國(guó)家,或是社區(qū)中驅(qū)逐出來(lái)。”這些被邊緣化的小人物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想在某種單一文化中扎根。現(xiàn)實(shí)是他們深處被殖民的特立尼達(dá),對(duì)于命運(yùn)毫無(wú)選擇權(quán)。小說(shuō)中博加特就經(jīng)歷著空間遷移,難以實(shí)現(xiàn)想依托單一文化的愿望。從拋棄第一任妻子來(lái)到西班牙港,而后失蹤前往魯普盧尼草原放牧,中途再回到西班牙港又失蹤幾次,他一直在模仿攀附中過(guò)著漂泊流浪的人生。出生在特立尼達(dá)可能是造成他們一生文化創(chuàng)傷的開(kāi)端,沒(méi)有一個(gè)人能逃過(guò)這種命運(yùn)的戲弄。
《米格爾街》中有很多像博加特這樣難逃漂泊無(wú)根境地的人。遷移是流散文學(xué)亙古不變的主題,但未曾有過(guò)跨國(guó)經(jīng)歷,卻要飽受本土流散之苦,身居“家鄉(xiāng)”卻深覺(jué)“無(wú)家感”是不是更為可悲呢?“由于殖民者推廣殖民語(yǔ)言、傳播基督教、侵吞土地、實(shí)行種族隔離和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原住民在自己的國(guó)土上被迫進(jìn)入一種“流散”的文化語(yǔ)境。”這一章節(jié)著重刻畫(huà)了街上的群眾角色,也恰恰體現(xiàn)人們不知道該依附于何種文化的荒謬,街上的人們相信瘋子曼門(mén)的話(huà),甚至還產(chǎn)生了一眾追隨者。由于陷入文化的囹圄,人們沒(méi)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對(duì)這些瘋子的言論趨之若鶩。即使沒(méi)有空間上的遷移,他們?cè)谏鐣?huì)層面上也深受種族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等因素的摧殘。他們?cè)谧晕疑矸菡J(rèn)同方面產(chǎn)生糾結(jié);他們的思想受到殖民國(guó)家價(jià)值觀的統(tǒng)攝,卻又難以與本土傳統(tǒng)文化完全剝離,從而在心靈上造成一種既不屬于“此”也不屬于“彼”的中間狀態(tài)。
這樣的“無(wú)家感”,無(wú)論是遷移還是本土流散,都會(huì)成為特立尼達(dá)人一生的羈絆,可以說(shuō)幾乎無(wú)一例外。無(wú)論是因流亡、遷移而產(chǎn)生的無(wú)根思緒,還是因殖民者使用意識(shí)形態(tài)國(guó)家機(jī)器進(jìn)行統(tǒng)治而產(chǎn)生對(duì)家園的糾結(jié)與疑惑,都難以被輕易撫平和治愈。空間層面上兩種流散對(duì)人們已經(jīng)產(chǎn)生難以磨滅的創(chuàng)傷。而在殖民國(guó)家“他者化”的摧殘下,人們流散身份也大多隨時(shí)間推進(jìn)而流動(dòng)、變化。
二、因身份流動(dòng)而產(chǎn)生的“無(wú)家感”
上文提到流散在地緣上的不同形式,而在意識(shí)形態(tài)國(guó)家機(jī)器的統(tǒng)攝下,特立尼達(dá)人的流散身份也會(huì)隨時(shí)間的推進(jìn)而變化。流散身份,即“擁有共同的流亡歷史的人,他們的流散身份隨著時(shí)間和地點(diǎn)而進(jìn)行改變,這是一種流動(dòng)的、會(huì)隨之改變的概念”。在地緣因素之后,隨著時(shí)間的演變他們會(huì)面臨對(duì)身份的疑惑與糾結(jié),對(duì)家尋覓無(wú)果的遺憾與絕望。
身份流動(dòng)帶來(lái)的創(chuàng)傷最痛之處還是“無(wú)家”,而西班牙港最不缺的就是在模仿中迷失自我的流散者。由于外界的影響,愛(ài)德華的人生一直處于一種動(dòng)態(tài)的變化中。最開(kāi)始他和博加特很像,對(duì)于美國(guó)文化有著極端的崇拜。這也與種族主義社會(huì)向有色人種灌輸?shù)陌兹藘?yōu)越論有著密切關(guān)系,內(nèi)化的種族主義應(yīng)運(yùn)而生。愛(ài)德華自我安慰道:“我的作品送給特立尼達(dá)人去評(píng)頭論足,他們懂什么?美國(guó)人才算是人,才是真正在行的人呢。”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后美國(guó)大兵進(jìn)入了米格爾街,愛(ài)德華操著地道的美國(guó)腔,在外形上也徹底模仿美國(guó)的時(shí)髦。愛(ài)德華是米格爾街上部分人的縮影,在他們眼中特立尼達(dá)混沌不堪,相反美國(guó)是天堂般的存在。抨擊同類(lèi)也許就是在尋求某種優(yōu)越,“身份的高尚感”。街上的人對(duì)于他“成功地”模仿美國(guó)人確實(shí)存在一種羨慕的情緒,“我想,也許是我們都在妒忌他。”愛(ài)德華因被殖民者的地位、文化決定了以模仿攀附來(lái)獲取身份認(rèn)同這條路根本行不通,最后只能歸于迷惘與流亡。學(xué)者王岳川說(shuō):“一切忽視文化差異的結(jié)果,一切抹平少數(shù)話(huà)語(yǔ)的立場(chǎng)的做法,其結(jié)果都可能是復(fù)制老牌的帝國(guó)主義的政治和文化。”事實(shí)上,每個(gè)地區(qū)都有自己獨(dú)特的特點(diǎn),忽視自身而盲目效仿只會(huì)徹底喪失前行的方向,一生都陷入漂泊流散的迷惘孤寂之中。
生活在米格爾街的人們是雙重意義上的邊緣人,具有比一般社會(huì)意義上的小人物更復(fù)雜的性格和命運(yùn),“邊緣人的形象占據(jù)了偉大的文學(xué)的一角”。 而在這種壓迫下,人們開(kāi)始有意無(wú)意地由于多種交叉的環(huán)境因素塑造出自己的雜合身份。《慎重》中的博勒,偶然知道《衛(wèi)報(bào)》上可以賭球,從那之后每周買(mǎi)很多份,卻沒(méi)有一次成功。“怪不得黑人過(guò)不上好日子呢”,這是米格爾街上人們常說(shuō)的話(huà),博勒是典型的悲觀主義者,在特立尼達(dá)被騙的經(jīng)歷一步步壓垮他。對(duì)此他選擇了逃離,命運(yùn)像是一直拿他開(kāi)玩笑,就連想離開(kāi)這個(gè)對(duì)他下了“詛咒的小島”都是這樣的難。他們對(duì)于好生活的向往與實(shí)際得到的很難適配,因?yàn)檫@樣一個(gè)殖民主義橫行的國(guó)家是灰暗的、遺世獨(dú)立的。誠(chéng)然,像奈保爾這樣獲得寶貴求學(xué)機(jī)會(huì)的人還是有的,但卻是鳳毛麟角。就算沖破特立尼達(dá)地域的禁錮,也難逃他者化對(duì)他們一生的折磨。因?yàn)槿魏稳说纳矸荻疾皇菃我唤⒃诜N族層面上的,還有各種不同的困境一層層形成了牢固的繭房,任你掙扎也只是白費(fèi)心力。
這些人物趨向于通過(guò)改變自己的穿著、口音等,來(lái)證明自己的文化歸屬感,來(lái)找尋自己的身份。例如博加特等,用模仿美音、賦予綽號(hào)等方式強(qiáng)調(diào)自己的身份特征,實(shí)際上只不過(guò)是自欺欺人罷了。他們也成功中了殖民者的圈套,成為殖民主體,即“那些接受了殖民者向他們灌輸?shù)挠^念,認(rèn)為英美人是優(yōu)秀人種,自己是劣等人種。”這是一本講述弱勢(shì)群體如何自欺欺人的書(shū),因?yàn)橹e言是他們唯一所擁有的。殘缺的文化導(dǎo)致他們很難有身份認(rèn)同感,過(guò)度關(guān)注外部世界和外在自我,失去了心靈的慰藉,因而只能一生都遭受漂泊的迷惘之苦,并妥協(xié)于自己流動(dòng)的流散身份。
三、因文化錯(cuò)位而產(chǎn)生的“無(wú)家感”
其實(shí)在一定程度上特立尼達(dá)擁有獨(dú)一無(wú)二的民俗文化,如傳統(tǒng)的狂歡節(jié)服裝,阿拉瓦克印第安人的陶器、紡織品和裝飾品,低矮的木制建筑,克里普索小調(diào)和被稱(chēng)為“凌波(limbo)”的舞蹈等。在《米格爾街》中,奈保爾也多次提到克里普索小調(diào)。很可惜的是克里普索小調(diào)作為民俗不但沒(méi)有發(fā)揚(yáng)光大,還極其成功地成為街上人互相嘲諷的媒介,比如當(dāng)?shù)厝擞眯≌{(diào)來(lái)傳播街上令人唏噓的八卦軼事。霍米巴巴說(shuō)過(guò)“文化錯(cuò)位是一種政治化的轉(zhuǎn)喻, 關(guān)鍵并不在于錯(cuò)位發(fā)生在何處, 而在于社會(huì)和文化中的哪些結(jié)構(gòu)性的因素系統(tǒng)性地‘制造’著錯(cuò)位”,而造成特立尼達(dá)這種現(xiàn)狀的根本原因就是殖民國(guó)家的文化侵蝕。書(shū)中也提到學(xué)校、報(bào)社、醫(yī)院和監(jiān)獄都受著殖民者的高度管轄。當(dāng)街上人每天聽(tīng)的新聞、看的圖書(shū)等都是殖民者滲透給你的時(shí),恐怕沒(méi)有人能掙脫這種文化囹圄。盡管個(gè)體在追尋文化歸屬感的過(guò)程中可能扮演著主導(dǎo)性角色,卻還是時(shí)時(shí)刻刻遭受著文化錯(cuò)位帶來(lái)的“無(wú)家感”。
文化混亂加劇了米格爾街上有些人近乎瘋癲的行為舉止和漂泊感。例如焰火師墨爾根,對(duì)他來(lái)說(shuō),通過(guò)出洋相而招來(lái)他人的嘲笑才是自己存在的意義。他的身份是焰火師,可沒(méi)人買(mǎi)他的焰火。除了做焰火實(shí)驗(yàn),他無(wú)時(shí)無(wú)刻不在想著怎么吸引大家的注意力,以獲得更多的存在感。事實(shí)上,大街上的人都知道他根本不是真正地快樂(lè)。當(dāng)他出軌時(shí),母老虎妻子把他拎到門(mén)外,打開(kāi)門(mén)燈讓全街人看到他的哀求。諷刺的是,這可能是墨爾根第一次真正把大家逗笑,完成人生的一大奢求。這一章節(jié)最后,他家燃起了一場(chǎng)大火。關(guān)于那次火災(zāi)有一首卡里普索小調(diào)這樣唱 :“多么壯麗的景象,就是那場(chǎng)國(guó)庫(kù)燃起的大火。”他一生最追求的兩件事:一件事是制作出世界上最燦爛的煙火,另一件就是讓人們笑話(huà)他,這回他都做成了。其實(shí)不難發(fā)現(xiàn),米格爾街上的人總會(huì)給自己找這樣那樣的差事,但大部分人都做不成功。而街上多的是信口開(kāi)河,撿笑話(huà)看熱鬧的人。一定程度上看,民俗文化之于當(dāng)時(shí)的特立尼達(dá)人,不是民族瑰寶,而是調(diào)侃取樂(lè)的工具。在每個(gè)章節(jié)的最后,這些小人物都會(huì)離開(kāi)米格爾街,帶著生活的不如意繼續(xù)漂泊游蕩。
除了曼門(mén)、墨爾根和博勒這樣帶有瘋狂思維的人,還有一部分是在盡力維護(hù)特立尼達(dá)文化的。“往昔深邃而奇妙”,這是街上的一位詩(shī)人沃茲沃斯和我交談時(shí)說(shuō)到的。沃茲沃斯的詩(shī)無(wú)人在乎,從書(shū)中母親在他來(lái)賣(mài)詩(shī)時(shí)的粗魯態(tài)度便可看出。只有“我”喜歡聽(tīng)他訴說(shuō)他和一位女詩(shī)人的故事,以及知曉他在籌劃一篇震驚世人的詩(shī)作,已經(jīng)寫(xiě)了五年,還需要二十二年。沃茲沃斯每年靠唱克里普索小調(diào)的季節(jié)去獻(xiàn)唱掙錢(qián),平時(shí)則專(zhuān)注于創(chuàng)作詩(shī)篇。但可悲的是,最后的最后,他向時(shí)光、向命運(yùn)妥協(xié)了。“往昔深邃而奇妙”,我看到他的衰敗后回到家痛哭起來(lái),像個(gè)詩(shī)人一樣看到什么都想哭。其實(shí)這也是一種堅(jiān)守,全書(shū)中只有我獲得了“成功”,離開(kāi)了米格爾街前往英國(guó)留學(xué)。但堅(jiān)守特立尼達(dá)文化的人其實(shí)并沒(méi)有成功,沒(méi)人能改變這個(gè)局面,唯有妥協(xié)以及和自己和解才是唯一答案。
歷經(jīng)流散自我調(diào)和都是被殖民者面臨的文化困境。學(xué)術(shù)上有一種想法是雜合其實(shí)是一種對(duì)于“無(wú)家感”的積極替代。但無(wú)論怎樣,被殖民者依然面臨如何爭(zhēng)取獨(dú)立人格和群體身份,獲得政治權(quán)力和經(jīng)濟(jì)機(jī)遇,擺脫意識(shí)形態(tài)國(guó)家機(jī)器壓迫的問(wèn)題。奈保爾談到自己的出生地時(shí)曾說(shuō)過(guò):“每個(gè)人都是獨(dú)立的個(gè)體,為他在社群中的地位而奮斗,但社群卻并不存在。我們處于不同的種族、宗教、群體和集團(tuán),除了共同的居住地,沒(méi)有什么東西能把我們凝聚在一起。”可見(jiàn),奈保爾對(duì)文化維度的無(wú)家困境是持相對(duì)悲觀的態(tài)度的。《米格爾街》便記敘了街上人們一心想逃離苦難,卻因沒(méi)有文化自信等原因無(wú)法擺脫命運(yùn)束縛的一個(gè)個(gè)鮮活的故事。
四、結(jié)語(yǔ)
在經(jīng)歷地緣、身份和文化多維度流散后,特立尼達(dá)的人們最終找尋不到根,在不同的文化縫隙中失去精神寄托。奈保爾本人最初也是隨著家人從查瓜納斯到西班牙港居住,而后去往英國(guó),再到印度,他也在經(jīng)歷不斷的遷移與流散。細(xì)數(shù)他的一生,他每次從法國(guó)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文學(xué)批評(píng)家查爾斯· 奧古斯汀· 圣伯夫(Charles·A·Sainte-Beuve)等人的作品中所獲得的活水源頭,以及孩提時(shí)代搬到西班牙港,再到后來(lái)去英國(guó)求學(xué),多次回到印度旅行等經(jīng)歷,甚至是他后期所感興趣的非洲、南美洲等,都成為填補(bǔ)他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世界地圖”的一個(gè)個(gè)拼圖。但他創(chuàng)作漂泊流散的主題卻大多數(shù)源于他的孩提時(shí)代,也就是《米格爾街》所描述的他童年的黑暗生活。從《米格爾街》獲得成功開(kāi)始,他找到了自己獨(dú)特的寫(xiě)作主題——加勒比地區(qū)流散文學(xué)。米格爾街上的人物出生在特立尼達(dá),就是他們一生流散的開(kāi)端。如果他們?cè)噲D追隨某個(gè)特定的文化身份,就必須搜尋自己的內(nèi)心,努力重建自我,或是擁抱雜合身份才有可能實(shí)現(xiàn)。但可惜的是,特立尼達(dá)是殖民文化占主導(dǎo)的地域,大多數(shù)人可能注定在追尋中不斷經(jīng)歷失望,最后向命運(yùn)妥協(xié),并且麻痹自己,陷入一生擺脫不掉流散身份的命運(yù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