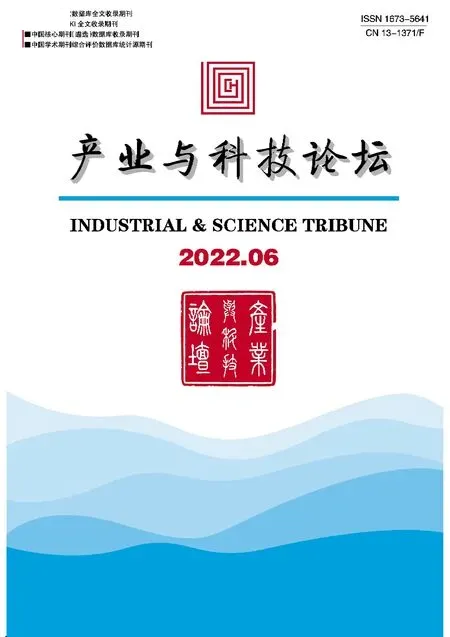多源流模型視角下我國出臺《民法典》的政策議程設置研究
□乙詠一 楊春生
一、問題的提出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一致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回顧《民法典》自最初起草到如今兩會審議通過的歷程不難發現,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就十分重視法制建設,尤其在當前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民法典》的頒布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標志性立法,對推動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具有深遠意義。隨著我國法制化的不斷發展進步,雖然我國民法的建設與應用也日趨完善,但各單行法種類繁多,對于非法學專業的普通公民來說想要厘清每種法律的內涵極具難度。而《民法典》像是一部民法百科全書,讓公眾在發生民事糾紛時會像查字典一樣,查詢自己的問題該如何解決,這在根本上解決了上述難題。
而《民法典》從提出到人大審議通過的整個歷程,其進展不可謂不艱難,其歷時不可謂不漫長,那么究竟是什么在阻礙著《民法典》的“出生”?什么契機和因由在推動著《民法典》的頒布問世?我國重大法律出臺過程中又經歷著怎樣的政策決策過程?本文基于多源流模型視角,整合問題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個主要分析要素,以兩會通過《民法典》為本土案例進行分析,嘗試厘清《民法典》從起草到審議通過的動因及內在機理,以此檢視我國重大法律出臺的政策執行過程,分析我國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披露的問題,以期為進一步推動、優化重大法律出臺過程的政策制定及執行提供建設性意見和建議。
二、多源流模型簡介
多源流模型(MS)最早由約翰·金登基于科恩·馬奇和奧爾森在1972年提出的“垃圾桶模型”而撰寫的其代表作《議程、備選方案與公共政策》一書中提出的一種用于解析政策執行過程的理論模型。有學者認為多源流模型的提出打開了政治系統的“黑箱”,為政策研究者提供了政策過程參與者的全景圖,這可以說是金登對公共政策研究領域的重要貢獻[1]。多源流模型想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在給定的任何一個時間段,到底是什么因素致使政策制定者對某一問題給予關注而對另一些問題置之不理,同時又該如何促使某些問題進入政策制定者的視線或者引起其重視[2]。金登將“垃圾桶模型”提出的問題、解決方案、參與者和選擇機會四大源流整合為政策議程中存在的三大源流,即問題流、政策流和政治流。其中問題流是指有待政策主體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源自三個方面:專門的社會調查研究、突發公共事件或人民關切的亟待解決的重大事件和現行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的問題反饋。政策流是指政策主體在試圖解決政策議題時所提出的若干方案和對策,這些方案對策可能是來自政府官員、專家學者或者利益關聯方,在內部進行討論、整合、修改后,最終形成的最佳政策方案。政治流是指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對圍繞著政策問題、解決方案及其整個過程中可能涉及的所有政治因素的衡量過程,主要包括國民情緒、社會輿論、民主選舉與游說活動等。
大多數情況下,這三條源流相互獨立,彼此平行的按照自己的特定機制運行,但某個時刻,由于某種原因三條源流產生耦合,該政策問題就會被提上政府的議事日程,這樣的時間節點被金登稱之為“政策之窗”。政策之窗開啟后如果不能及時察覺就會轉瞬即逝[3],而政策倡導家也會把握這難得的機會,將自己的政策主張鮮明地表達出來,投入大量的時間、金錢、精力,促使政策的產出按照自己的預想發展,從而推動政策成型。有關中國情境下的多源流模型研究,王紹光將近代以來中國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劃分為六大模式,分別是建國初期的“關門模式”和“動員模式”,毛澤東、鄧小平時代后的“內參模式”、偶爾也會出現“上書模式”和“借力模式”,而現代社會常以“外壓模式”居多[4]。
三、多源流模型視角下《民法典》出臺的政策過程檢視
(一)問題流分析。多源流模型中的問題流主要關注的是政策制定者如何分配注意力的問題,亦即“為什么政策制定者對一些問題給予關注,卻對其他問題視而不見?”[5]。由上述可知,這主要取決于公共危機事件、指標數據和政策反饋等問題是否進入政策主體的視野,從而決定著該問題是否能夠被提上議事日程。回顧《民法典》的出臺過程,推動其立法工作的實施及出臺的問題支流主要有如下幾點。
1.民法立法混亂,缺乏內在一致性。在《民法典》通過之前,我國的民法類目繁多,截至2017年10月1日起實施的《民法總則》開始,我國大陸施行的民商事單行法律已有九大類。表面上看起來,我國的民法系統似乎涵蓋了民商事的方方面面,但從司法層面來看,眾多的單行法讓司法部門在裁決案件時容易出現“瞻前顧后”但又“畏首畏尾”的情況。例如曾經轟動一時的網購熱水器漏電事件,擺在法官面前的相關法律有合同法、侵權責任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等好幾部單行法,最終導致一審中法官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而二審中又適用合同法或者侵權責任法,致使兩次審判的結果大相徑庭。這種事情的發生歸根結底是因為民法的立法混亂,沒有形成統一規范,致使各部單行法之間獨立運作,有些條款甚至自相矛盾,缺乏內在邏輯一致性。該問題已然進入政策主體的視野,成為推動《民法典》通過的問題流之一。
2.現行法律難以適用現代社會問題。我國的諸多現行法是在建國初期或者改革開放初期才建立起來,但是在快速發展的現代社會,許多問題產生的原因已經發生質的變化甚至會出現一些新興問題,此時繼續沿用以前制定的法律注定顯得滯后于時代發展。例如現行的婚姻法至今已經施行40余年,而40年后的今天,婚姻的模式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婚姻中牽涉的財產利益關系也變得更加復雜;又如,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我國的網民數量持續大規模增加,互聯網已經全面影響到公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法律層面說,理應對網民個人隱私、侵權責任等方面給予高度關注,但是網絡侵權、個人隱私保護等法律內容卻尚待立法予以確立、宣示、保護。換言之,現行法律難以適用現實問題自然而然成為《民法典》通過的重要的問題支流中之一。
(二)政策流分析。誠然,近年來隨著我國政府提倡民主化進程的逐漸加快,在處理一些亟待解決的社會重大事件時,公眾的個別意見也有可能被政府參考甚至采納,但政策流的主要來源途徑仍為傳統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或智庫團體,也是上述人群的意見建議形成了《民法典》出臺的政策流。
1.來自政府的政策倡導。完善和發展我國法律制度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關鍵環節,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以來,我國對于《民法典》立法工作的重視被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所以,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的第三年即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便正式啟動了《民法典》的編纂工作,2020年5月28日,《民法典》通過全國人大審議,在2021年正式服務于每一個中國合法公民。回顧《民法典》從提出到通過審議的整個過程,不難看出,這背后和政府部門、政府官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說,也正是在政府部門和政府官員的持續倡導下,才有今日《民法典》的誕生。
2.專家學者的政策主張。1981年,法學泰斗、北京大學的芮沐教授應邀參與了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召開的《民法草案》二稿座談會,基于他的專業性意見,草案的體系從三稿開始做了較大調整;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李培林教授應邀出席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組織的《民法典》編纂工作協調小組第一次會議,對《民法典》的編纂提出了建設性意見;2017年,中國人民大學朱虎副教授作為全國人大法工委民法典編纂專班成員,直接參加了全國人大法工委民法典編纂的工作;201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法室主任、研究員薛寧蘭參加了對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草案的征求意見,并結合自身優勢提出了可行性建議,等等。學界的專家學者憑借自身的學術經驗,對《民法典》的出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3.智庫團體的政策參與。2015年1月21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作為參加單位,共同承擔《民法典》的編纂任務。與此同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國法學會等單位均收到該指派,紛紛成立民法典編纂工作研究小組。此后,該研究小組數次參與《民法典》的編纂、修訂過程,為《民法典》的出臺作出了巨大貢獻。由此可以看出,智囊團體的參與對《民法典》的出臺提供了重要意見參考,跨部門參與的形式為《民法典》涵蓋內容的全面性提供了保障。
(三)政治流分析。
1.社會公眾對現行民法體系的不滿情緒。公眾情緒是政策形成的重要推動力[2],尤其在信息網絡如此發達的現代社會,公眾表達情緒的途徑和方式也越來越多,這也倒逼政策主體在制定政策方案時,必須考慮公眾的實際感受。在《民法典》出臺之前,我國的民法體系十分混亂,存在諸如個別條款自相矛盾、權限不清、一案適用多法等現象[6]。因此對公眾來說,在遭遇民事糾紛時很難厘清自己究竟應該受何種法律的約束,從而會產生不滿情緒。在互聯網如此便捷的今天,網絡也就成了公眾宣泄情緒的共鳴之地,由于網絡強大的信息傳播力以及公共焦點事件的分散性,這也給我國網民在網絡中表達自己的不滿情緒提供了平臺。可以說,公眾的不滿情緒通過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傳播作用對于推動《民法典》的編纂工作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2.政府執政理念的變化。1997年,黨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國”的執政理念,自此而后,我國便開始高度重視法制建設。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編纂民法典”。2015年,我國便宣布重新開啟《民法典》的編纂工作,歷時五年,參與《民法典》編纂的相關單位、專家學者、政府工作人員歷經多次討論與修改,才最終有了我國首部《民法典》的誕生。可以說,政府執政理念的轉變,成為了促進《民法典》編纂工作的重要原因。
(四)三流耦合——政策之窗開啟。國內民法體系混亂、現行法律難以適應現代社會問題形成的問題流,政府倡導、專家學者以及智庫團隊的政策主張組成的政策流,公眾的不滿情緒、政府執政理念的轉變和來自利益關聯方的壓力等因素構成的政治流,三條源流同時具備時,政策之窗迅速打開。通過分析可以看出,最高領導人的直接參與、親自指揮是實現三條源流耦合的關鍵節點。2016年6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關于民法典編纂工作和民法總則草案》的匯報,并作出重要指示;2018年8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關于民法典各分編草案幾個主要問題的匯報,就做好民法典各分編編纂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19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審議民法典草案;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一致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綜上所述,正是由于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高度關注和重視,《民法典》的政策之窗才會如此順暢的開啟,并最終順利出臺。
四、結論與建議
《民法典》通過的政策議程設置過程與多源流模型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其出臺過程受到問題流、政策流、政治流的影響和制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之現實情境下,一項政策想要上升到中央政府的議事日程,國家領導人的關注和重視尤為重要。雖然《民法典》已經被兩會審議通過,但回顧其從首次提出至今,其歷時之長、過程之艱難也暴露出我國重大法律出臺過程中政策議程設置的一個重要問題:存在被動式的政策創新[7],政策議程設置長期延續過去的決策框架和運行軌跡,不愿隨著決策環境的變化做出相應的模式創新,這也是導致《民法典》遲遲沒有出臺的重要因素。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一)要不斷提升政府主體自身的決策理性。政策主體應該在正確的理論導向之下對政策問題進行理性決策,結合我國國體和政體之實際去制定實施政策方案,著力提升政策議程設置的目標共識性、科學性和參與性,推動更多滿足社會公眾需求的政策法律出臺。
(二)要積極發揮公眾的參與作用。公眾作為社會構成的主體以及政策實施的接受者,其對某項政策問題的認識可能更為清晰和深刻[8]。因此,可以健全公眾參與的參政議政通道,讓政策制定者能夠聽到公眾的聲音,加快政策出臺進度,提高各項決策質量,從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