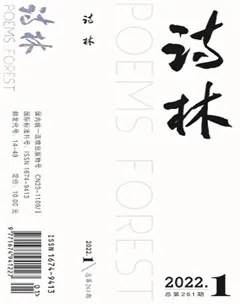重新做一個讀者
唐曉渡

人生只有一世,因而最令人驚詫莫名的是置身那些恍若隔世的瞬間。比如你突然讀到這樣一段十多年前寫下的文字:
我們這一代的幸福在于我們意識到了自己生命的意義和使命,我們因苦難的磨礪而堅韌,并在民族振興的偉大事業(yè)中豐富和完善著自己,從而獲得了一種成熟的理想主義。……帶著個人的獨創(chuàng)性加入傳統(tǒng),加入一代人的創(chuàng)造,是個人實現(xiàn)自身的唯一方式。而詩人是一種加入的最典型的體現(xiàn),因為詩是人生命存在的最高方式。
接下來作者引用《論語》中的一段著名語錄來勉勵和告誡自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
作者是一位上世紀八十年代頗有影響的先鋒詩人。這段文字摘自他致友人的一封信。指明這一點是為了確認其激情的真實性。然而曾幾何時,寫下這段文字的激情之手早已抽身而去;即便它回來,也會認不出以至根本否定當初的激情。這雙手現(xiàn)在在做什么無關緊要,重要的是,這種今昔對比的巨大反差究竟出了什么問題?
我無意講述某個詩人的故事,同樣,上述追問也并非針對某一詩人。誰都看到了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詩的窘境。它像一輛突然熄了火的機車,不但失去了當初的勢頭,而且面臨著乘客們紛紛罷乘的局面。隨著大眾媒介和大牌明星互相爆炒越來越成為這個時代的盛事,詩和詩人的社會地位也一路看跌;時至今日,其公開身份竟已淪落到介乎若有若無、似在非在之間。這就足以讓一些人憂心如焚,或者幸災樂禍了。在前些時候京城某家報紙組織的有關討論中,認為詩的現(xiàn)狀和前景大大不妙者占據(jù)了壓倒性的優(yōu)勢;其中最聳人聽聞、最具現(xiàn)場效果,因而也最能反映此類討論本質(zhì)的說法是,詩壇已“風流云散”,詩歌隊伍已“全軍覆沒”。詩和詩人就這樣在缺席的情況下被宣布“集體下課”。
沒有一個真正潛心寫作的人會把此類說法當回事兒。但不可回避的仍然是:這種今昔對比的巨大反差究竟出了什么問題?
總是為了某種需要(首先是為了實現(xiàn)某種權(quán)力),人們發(fā)明了一些似乎具有魔力的思想和話語方式。今昔對比即是其中之一。它可以是一碗“憶苦飯”,其中半是沉痛半是甜蜜,半是對從前的指控半是對未來的贊美,而綜合效應是對當下心安理得;它也可以是一朵隱藏在既往歲月迷霧中的玫瑰,以其幽緲的暗香引誘你“回歸”某一“黃金時代”,而這樣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返,或許壓根兒就沒有存在過;它同樣可以是一片在頭頂聚散不定的烏云,從陣陣威脅性的雷鳴中不斷篩下“危機”的陰影,以誘發(fā)某種類似受迫害狂式的焦慮,這樣的焦慮會使你下意識地傾向于尋求某種庇護。奇怪的是,在主流詩歌界,至少就最近十多年而言,與“今”相對的“昔”和終將成“昔”的“今”之間似乎完全不存在界限。事實上,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以來,關于“危機”的警告或抱怨一直不絕于耳,即便在表面看上去最紅火的時候也沒有停止過(盡管是另一套說法)。所謂“朦朧詩”面世時如此,所謂“第三代詩”當潮時也是如此。只是在時過境遷之后,“危機論”持有者們才變得稍稍平和些,以致可以流露出一絲懷舊的溫情。這種使危機常態(tài)化的、單向度的、幾近一成不變的今昔對比又是怎么回事?
讓詩和人相互比附是危險的。但詩確實和人一樣,有一半是(經(jīng)由具體的詩人和詩歌輿論)活在記憶里。二十世紀中國詩歌(所謂“新詩”)的特征之一就是切斷了與三千年自我記憶的聯(lián)系,開始新的自我記憶。在這種新的自我記憶中,“革命”的經(jīng)驗無疑是其堅硬的核心部分。新詩的誕生本身就是一場革命;而這場革命又是更大范圍內(nèi)的社會政治—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歷史上還沒有哪一時期像二十世紀這樣,使詩在大部分時間內(nèi)和革命如此直接、緊密地結(jié)合在一起。“革命”是詩最重要的靈感和活力源頭;反過來,詩也是“革命”最忠實的鞍前馬后。詩從“革命”那里認取了它嶄新的信念和使命;而“革命”也賦予了詩以前所未有的價值和光榮。詩和革命的這種親密關系同時也決定了詩和大眾的親密關系。既然“革命是千百萬人民大眾的事業(yè)”,詩當然也是千百萬人民大眾的事業(yè)。革命要求詩首先做到的就是套用蘭波的一句話——“大眾化!必須絕對地大眾化”,而詩確實做到了。
詩和革命在二十世紀所經(jīng)歷的這場浪漫史在新詩的自我記憶中留下的自然不僅僅是浪漫;正如這場浪漫史本身一樣,其中也會有齟齬、錯位、對抗、沖突、游離、出走、迷失,乃至清算、斗爭、苦難、屈辱等等。然而所有這些不但沒有削弱、消解,反而強調(diào)、凸出了“革命”的經(jīng)驗在新詩自我記憶中的地位——讓我再重復一遍:前者無疑是后者堅硬的核心部分。需要補充的只有一點,即必須充分估計這種經(jīng)驗的復雜性。
記憶在任何情況下都比事件本身活得更長久;不但如此,它也活得比我們想象的更積極。它既不只是歲月的遺跡,像博物館里的風景畫;也不只是固定的參照,像史家所說的“鏡子”;它還作為我們思想、行為、評價的某種內(nèi)在依據(jù)和尺度,有效地參與著當下的生活。更能表明記憶有效性的是它(通過文化教育和集體無意識)具有可遺傳和可復制的特質(zhì),據(jù)此記憶能輕易地穿越時間和觀念之墻;盡管在這一過程中,記憶本身也一再變形,成為納博科夫所說的“關于記憶的記憶”。
在文章開頭摘引的那段話中,我們至少可以辨認出三重“關于記憶的記憶”:革命的(在諸如“生命的意義和使命”“因苦難的磨礪而堅韌”“民族振興的偉大事業(yè)”“成熟的理想主義”等用語中留下的痕跡)、外國詩論的(T·S·艾略特關于傳統(tǒng)和個人才能的論述留下的痕跡)和傳統(tǒng)士大夫的(由引用的《論語》語錄及引用這一行為本身所體現(xiàn));但關于革命的“記憶的記憶”無疑起著主導作用。它統(tǒng)攝性地把所有這一切綜合成“我們這一代的幸福”。這段話的語氣也更像是一位革命前輩的遺言或在某次誓師大會上的發(fā)言;除了全景式的語言視野外,還體現(xiàn)了不在場的“大眾”所具有的分量。
或許一段話不足以說明什么問題,但它肯定不是一個偶然的特例。我們也可以在一個大得多的范圍內(nèi)作某種整體性的回顧。例如,關于革命的“記憶的記憶”在所謂“第三代”詩歌運動中顯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第三代”這一意味深長的命名本身所表明的那樣,這場運動從一開始即以一種看似諧謔的方式,自我確認了它與革命的血緣關系。但這非但不影響,反而有助于證明其血緣的純粹性。當然,所有這些都應該被嚴格限制在心理學—審美范圍內(nèi),既盡可能按其本義去理解,又充分考慮到新的歷史語境;換句話說,這里關于革命的“記憶的記憶”與對革命的理解之間并沒有一條不可逾越的界限。
我無法指望通過這樣一篇雜感式的文字厘清詩和革命之間近一個世紀以來的復雜糾結(jié),而只想提示人們注意,這一糾結(jié)并沒有隨著社會—文化語境的變化而自行消失;我的提示與其說意在回答文章開頭所提的問題,不如說意在對所提問題的經(jīng)驗和邏輯前提進行必要的追問。事實上,對這一前提的覺察一直是當代詩歌焦慮的根源之一。早在七十年代末,北島就曾面對“大海”和“落日”寫下過這樣的詩句:“不,渴望燃燒/就是渴望化為灰燼/而我們只想靜靜地航行。”
當代詩歌的經(jīng)驗讀者、標準讀者和隱含讀者(按艾柯的區(qū)分)似乎各自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審美時空;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詩人不得不自己同時兼任標準讀者和隱含讀者;結(jié)果反而是占閱讀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經(jīng)驗讀者(也包括這一意義上的批評家)顯得更為超然。說“超然”是因為他們的閱讀期待受制于另一條中樞神經(jīng),其最敏感的部分奇妙地混合著對“革命”的模模糊糊的記憶、懷舊的需要和文化—審美主體的幻覺。由于有那么多被壓抑的內(nèi)在激情需要被占有、被煽動、被揮霍,他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源源不斷地出現(xiàn)具有“轟動效應”的詩,或詩能源源不斷地制造出“轟動效應”。遺憾的是詩一直沒有滿足、以至越來越遠離他們的美好心愿。在這種情況下,某種類似戀情一再受挫的悲傷,或被迫長期使用代用品的屈辱感幾乎是不可避免的;而為了排遣和平衡這種消極的心理,不失時機地將其轉(zhuǎn)化成詩的“危機”大概是最有效的做法。
詩歌在公眾輿論中的衰敗構(gòu)成了世紀末一個小小的文化景觀;然而,立足詩歌自身的立場看,情況也可能相反:正在衰敗的不是詩,而恰恰是那種認為詩每況愈下的公眾輿論,是這種輿論看待詩的一貫眼光,是形成這種眼光的內(nèi)在邏輯以及將其與詩聯(lián)系在一起的共同記憶。
這里的“衰敗”并不相對于“新生”。它僅僅意味著無效和言不及義。
我無意據(jù)此為詩當前所面臨的窘境強作辯護:一方面,這種窘境是由詩的本性與一個越來越受制于利益原則的現(xiàn)實關系不適以至格格不入所決定的,除非將其視為一種挑戰(zhàn),否則既不值得、也無從進行辯護;另一方面,真正自主自律的詩歌寫作多年來已成熟到不需要任何辯護的程度。從七十年代末的“回到詩本身”,到貫穿著整個八十年代的“多元化”追求,再到九十年代的“個人寫作”,當代詩歌對其獨特依據(jù)、獨特價值、獨特使命的逐步意識和深入過程,同時也是應對和超越自身的持續(xù)困境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詩人們早已積累了足夠多的有關經(jīng)驗。事情很簡單:除非放棄寫作,否則諸如“非中心”“邊緣化”等等,所有這些被公眾輿論和某些批評家看作詩之不幸的,對真正自主自律的詩歌寫作來說卻是題中應有之義。這不是說詩人們必須忍受并習慣于這種“不幸”,而是說它恰好是恪守本義的寫作或?qū)懽鞯谋玖x之所在,恰好為詩保持其內(nèi)在的活力、難度和不可消解性之所需。作為反證,我注意到八十年代熱衷于詩歌運動的詩人后來大多陸續(xù)停止了寫作。由此得出的一個推論是,詩歌運動在九十年代的終結(jié)并不僅僅如其看上去的那樣,是一種被強行遏止的現(xiàn)象,它還體現(xiàn)了詩歌自身發(fā)展的某種趨勢。它在現(xiàn)代詩歌運動似乎已經(jīng)接近尾聲時重申了現(xiàn)代詩歌的一個重要特征,即吉姆費雷爾所說的“少數(shù)派的堅強意志”。
在這個意義上,所謂詩的“窘境”正是它的常態(tài)。
困惑于詩歌“今昔對比的巨大反差”的人們,偏執(zhí)于詩歌“危機”的迷宮游戲而找不到出口的人們,一切關注詩歌發(fā)展的前景而又對此感到心灰意冷的人們,為什么不從你們耽溺的記憶暮色中回過頭來,用你們殘存的熱情聽一聽這成熟的、常態(tài)的詩的聲音呢?
我的工作是望著墻壁
直到它透明
我看見世界
在玻璃之間自燃
紅色的火比蝴蝶受到撲打還要靈活。
而海從來不為別人工作
它只是呼吸和想。
……
那些被炎熱撲打的人們
將再摸不到我
細密如柞絲的暗光
我在光亮穿透的地方
預知了四周
最微小的風吹草動。
那是沒人描述過的世界
我正在那里
無聲地做一個詩人。
這首詩的標題是《重新做一個詩人》。相應地,讓我們重新做一個讀者如何?
1996年9月于北京勁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