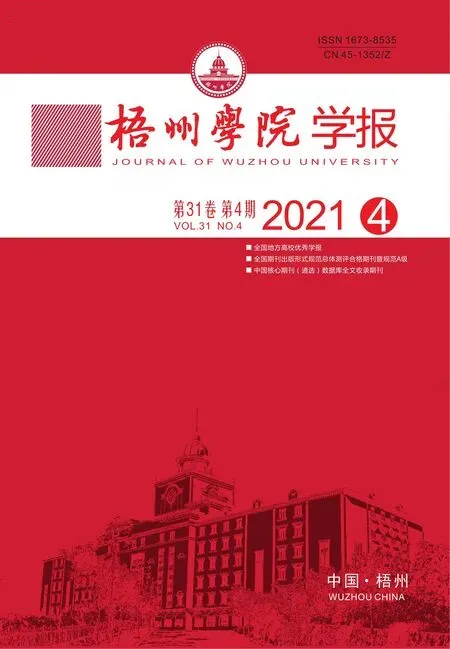皮爾士符號學視域下敦煌舞蹈動作語匯符號探析
2022-01-06 05:03:28李哲昕
梧州學院學報
2021年4期
牛 敏 , 李哲昕
(1.貴州民族大學 外國語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2.泰國西那瓦大學 人文學院,泰國 曼谷 10900; 3.北京舞蹈學院 人事處,北京 100081; 4.泰國西那瓦大學 管理學院,泰國 曼谷 10900)
敦煌舞是一種古老又新興的古典舞,它的舞姿、表情、肢體動作、眼神等均源自敦煌莫高窟內樂舞壁畫舞姿的模仿和再創生,是壁畫舞姿的臨摹、提煉、發展和美化的結果。高金榮先生以“敦煌”命名舞蹈,是根據莫高窟內大量不同朝代的壁畫舞姿,結合現代舞蹈藝術的特點,進行研究、分析及再創造,最終形成今天系統化、規范化的由肢體動作、舞姿、眼神、手勢等符號元素組合而成的敦煌舞蹈動作語匯。以“飛天”舞臺形象塑造為核心的敦煌舞之靈魂在于“飛”,飛得靈動、飛得飄逸是“復活”飛天形象的關鍵。“飛”這一動感舞姿也極具符號的指示意義。“飛天”舞姿不斷地在諸如模仿、指代某物某人的交際活動中重復,最后變成一種規約化、習慣化的動作范式,這些動作范式承載了某一朝代或地域獨特的風土人情,是其特定時代文化形態和意義的表征。敦煌舞獨特的舞蹈語匯、舞姿、舞韻和獨特美學特征的表演體系便是符號的研究主體。符號學是研究符號生成意義的科學,“符號是攜帶意義的感知,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符號的用途是表達意義”[1]。敦煌舞表演是一個被賦予意義的符號過程,是舞步、肢體、表情、眼神等符號行為的編碼。它根據一定的規律性來詮釋舞蹈動作符號的效應,表演者在理解和詮釋舞蹈的過程中不斷地修正和訓練身體的肢體動作,以穩定他們表演中動作符號“交際”的有效性,即讓觀眾通過表演者舞蹈動作的感知來深化對舞蹈表演的理解。……
登錄APP查看全文
猜你喜歡
幼兒園(2021年6期)2021-07-28 07:42:14
小學生學習指導(低年級)(2019年11期)2019-11-25 07:31:48
當代陜西(2019年16期)2019-09-25 07:28:32
金橋(2019年12期)2019-08-13 07:16:18
小學生作文(低年級適用)(2018年3期)2018-04-17 00:58:35
小學生導刊(2017年13期)2017-06-15 20:29:38
作文評點報·低幼版(2017年7期)2017-03-11 20:49:41
少兒科學周刊·少年版(2015年4期)2015-07-07 20:56:37
天津科技大學學報(2015年4期)2015-04-16 04:5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