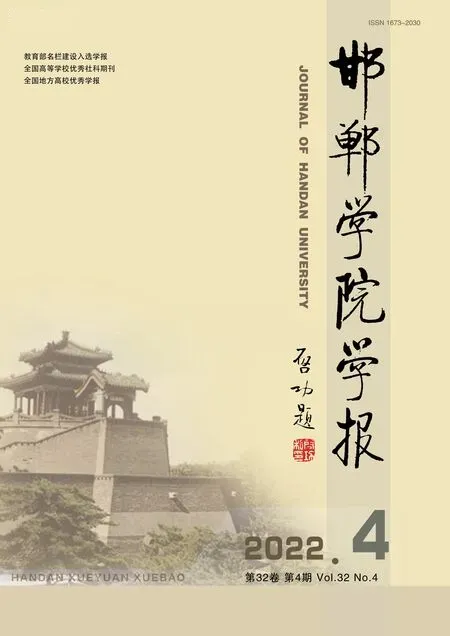日本江戶時期“邯鄲夢”亞型故事新詮
——以早期(1755-1775年)黑本、青本、繪本為中心
虞雪健
(綜合研究大學院大學 人文科學研究科,日本 京都 610-1192)
引 言
唐人傳奇《枕中記》講述了盧生枕青瓷枕入夢,歷經萬般紅塵劫,夢醒而悟的夢幻故事。該作一經傳入日本,便對其文學及藝術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根據該作改編的故事最早可見于軍記物語巨著《太平記》(14世紀中葉)[1]3-4。此后大略百年又誕生了膾炙人口的能樂劇作《邯鄲》(15世紀中葉)[2]106-114。及至江戶時代,藝術形式的多樣化和出版業的極大發展,催生了一批“邯鄲夢”亞型故事。這些作品或以人形凈琉璃、歌舞伎狂言的戲劇形式,或以舞踴、歌謠的形式,或以假名草子、浮世草子、草雙紙等形式,為江戶時代各個階層所熟知。其中《金金先生榮花夢》(1775)(以下簡稱“《榮花夢》”)被譽為黃表紙的濫觴,地位舉足輕重。以此為契機,此后30年間,以“邯鄲夢”故事為原型的黃表紙創作形成了一股熱潮。其中不乏曲亭馬琴、山東京傳、十返舍一九、朋誠堂喜三二等通俗小說名家的力作。這30年是“邯鄲夢”亞型故事創作的全盛時代。
但也正因為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使得今人在論及江戶時期的“邯鄲夢”亞型故事時大多從《榮花夢》論起,其次是列舉其仿作,而往往忽視早于該作的黑本、青本、繪本。前人認為,黑本《浮世樂助一盃夢》、青本《風流邯鄲浮世榮花枕》、青本《風流仙人花胥》與《榮花夢》的問世存在某種關聯性。[3]514-522也有學者提及黑本《初夢邯鄲枕》、青本《由佐七郎榮花夢》、青本《浮世夢介出世噺》。[4]65-77
筆者所見,現存草雙紙中最早的“邯鄲夢”亞型故事是寶歷五年(1755)出版[5]3-4的黑本《初夢邯鄲枕》。寶歷五年(1755)到《榮花夢》問世的安永四年(1775)是江戶時期“邯鄲夢”亞型故事創作的第一階段,此后的黃表紙30年的創作熱潮是第二階段。針對第一階段,前人已做了簡要梳理,但不免有所遺漏和謬誤。本文一則參照前人研究,對現有論斷做進一步評述,二則指出未發現的亞型故事,對江戶時期“邯鄲夢”亞型故事創作的第一階段——黑本、青本、繪本的20年做一個較為全面的說明。
一、黃表紙誕生的前夜
寶歷五年到安永四年是“邯鄲夢”亞型故事創作高峰期的前夜。高木好次、白川和子都注意到了“邯鄲夢”故事框架在各個作品中的作用。高木好次重點關注各個作品中是否已經涉及到了如《榮花夢》中符合成人嗜好的內容,而白川和子則只關注各個作品中的插畫或文本是否可能成為《榮花夢》實際創作的靈感來源。前者側重探討作品風格和立意,后者側重考察作品實際創作手法。針對作品風格、立意及實際創作手法,對已論及作品作進一步確認和修正,并對未發現作品作初步考察和歸類,是本文研究的重點之一。
《榮花夢》的問世與當時的出版業發展、社會風俗趨向,以及初具黃表紙特性的黑本、青本等密不可分。時至寶歷年間,中流町人的出現使各類讀物的讀者群得到擴充,黑本、青本等原本面向青少年的讀物也因此迎來了一批新的固定讀者群。為了滿足他們的嗜好,黑本、青本開始融入符合成人愛好的內容,這些內容大多涉及金錢、酒色,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田沼時代的享樂消費文化。[6]224-226因此,在考察《榮花夢》問世前的“邯鄲夢”亞型故事時,作品中是否包涵此類元素是本文的另一大關注點。

表1 目前可見,1755-1775年間的有關黑本、青本、繪本大致有以下9種
與早期面向兒童的赤本相比,草雙紙中的黑本多面向青少年讀者,題材多涉及人形凈琉璃、歌舞伎狂言等劇作;青本與黑本一般,內容上也多為歷史傳說、神佛靈異故事等。隨著創作技巧臻于成熟及世情風氣變遷,青本的敘述風格趨于滑稽灑脫,內容轉為模寫世情浮華,黃表紙應運而生。黃表紙在早期仍被稱為青本這一事實,恰恰體現了青本向黃表紙演變的過程。此外,本文中的“繪本”主要指上方兒童繪本,其內容與赤本、黑本、青本大致相當。
根據文本特征,可以將表中九種草雙紙作品分為以下三種情況:(一)遵循黑(青)本的基本特征,與《榮花夢》創作無甚關聯的早期草雙紙(以下簡稱:早期“邯鄲夢”亞型草雙紙);(二)融入成人嗜好,對《榮花夢》創作有借鑒意義的過渡期草雙紙(以下簡稱:過渡期“邯鄲夢”亞型草雙紙);(三)被曲解為“邯鄲夢”亞型故事,被曲解為對《榮花夢》創作有借鑒意義的其他草雙紙(以下簡稱:其他“邯鄲夢”亞型草雙紙)。
二、早期“邯鄲夢”亞型草雙紙
(一)異國想象下的“唐人夢”
黑本《初夢邯鄲枕》現藏于大東急紀念文庫,白川和子僅將其歸類為“邯鄲夢”亞型故事,沒有作具體闡述。該作于寶歷五年(1755)出版,是迄今所見最早的“邯鄲夢”亞型故事草雙紙,至今未被翻刻,具有較高的資料價值。作品講述了果蔬行商“蘆生”的夢境故事。蘆生聽聞楚國有仙人隱居,便挑著果蔬登門拜訪。于邯鄲草庵中見到仙人呂翁,得賜邯鄲枕,一夢五十載榮華。夢中蘆生受楚王禪讓、著楚王裝束、乘輿車前往楚王宮。隨著浩浩蕩蕩的唐人隊列,蘆生到達了楚王宮、與公主成婚、得六國珍寶,又舉行重陽宴、同妃子數千人飲酒歌舞。五十載榮華后,蘆生夢醒而悟,修習仙術、得享長生。
該作借用謠曲《邯鄲》詞句處頗多,基本構架也多有沿襲。謠曲《邯鄲》中,盧生倚枕入夢,立時有使者來迎,請盧生乘錦轎入楚王宮。該作巧妙利用了這一故事情節,嵌入了長達六頁的唐人隊列的圖文描述,來表現“蘆生”的邯鄲夢世界。此外,文中還多次運用《國姓爺合戰》《大職冠》等當時流行的人形凈琉璃、歌謠小調等,將“唐人”的夢境世界戲謔地表現了出來。無論是《國姓爺合戰》《大職冠》還是唐人隊列,看似與中國緊密相關,實則形象來源及文本生成背景,都直接受到17、18世紀江戶時代庶民所見聞的朝鮮通信使隊列的影響。[7]285-300該作借用此類受朝鮮通信使隊列衍生而來的戲曲作品及風俗,迎合了時下江戶庶民對異國的幻想,使這部作品在“邯鄲夢”亞型故事中別具一格。
作品正如題名,“邯鄲枕”明確了其為 “邯鄲夢”亞型故事,“初夢”則反映了起源于鐮倉時代、盛行于江戶時代的“初夢(除夕至正月初三期間的第一場夢)”風俗。作品既體現了江戶中后期民間對異國情調的濃厚興趣,同時又以詼諧的表達來渲染正月的節日氛圍,本質上仍屬于面向青少年的內容,對《榮花夢》的創作手法或主題沒有太大的影響。
(二)“醉夢浮世”下的“浮世夢”
關于黑本《浮世樂助一杯夢》(1761),高木好次和白川和子都指出該作應屬于“邯鄲夢”亞型故事。小池正胤曾對其進行翻刻,并做了詳盡的注釋。[8]185主人公名為浮世樂助,顧名思義,取“享樂于浮世”之意。樂助于除夕日中醉酒入夢,遇風神、雷神唱誦豐后節、見阿形、哞形二仁王、久米平內、彌惣右衛門稻荷、閻魔言舊事,諸神佛齊聚宴樂后,夢醒而悟,感嘆與其為瑣事所累,不如一醉一夢。
文末“然智者謂不定世界,歌人詠飛鳥川”一句中,“不定世界”意指佛教無常觀,歌人所詠“飛鳥川”出自第18卷《古今和歌集》雜歌下,即“世上無常住,請看飛鳥川,今朝成淺水,昨日是深淵”。[5]1-13二者所論世事無常與“邯鄲夢”論及之虛妄榮華,似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全文除開頭提到“夢”“一睡”外,沒有其他如“邯鄲”“枕”“悟”“粟(中國為黃粱、黍等)”等關鍵詞,或引用其他“邯鄲夢”亞型故事中的詞句,難以斷定其為“邯鄲夢”亞型故事。從內容上看,該作多有與“邯鄲夢”無關的神佛故事、民間技藝的羅列,與其作為正月出版、面向青少年讀者的特點相吻合。
《浮世樂助一杯夢》故事框架雖有“夢境”作為支撐,但實際上主人公醉酒后與神佛共歡,醒來后并不像 “邯鄲夢”一樣,悟得夢中一切、自己所求不過虛妄,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既然現實中所求一切皆為無常,不若沉醉夢中。因此,不能僅憑其“夢境”敘述結構和反映成人嗜好的元素,便簡單認為其對《榮花夢》創作有借鑒意義。
(三)文本嫁接、融合下的“串燒夢”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青本《風流女山岡》(1765),前人未有論述。與其他“邯鄲夢”亞型故事相比,雖然明確包含了“邯鄲夢”故事結構,但由于夢境作為部分情節,沒有貫穿始終,因此嚴格意義上只能算是偽“邯鄲夢”亞型故事。主人公久米屋豐次郎與游女道芝互生情愫,道芝憑借念力從口中吹出靈魂,想追上豐次郎。伙計莊兵衛嘆服這一神跡,為道芝贖了身。道芝看似與豐次郎原配和睦,但二女夢中不覺,長發已如毒蛇般交纏,豐次郎撞破此事,看破紅塵,前往西國三十三所朝圣。路經多武峰,于友人家待粟飯熟時,夢見自己拜師久米仙人。仙人吊大石于頭頂,欲試其道心。豐次郎獲仙術后,因偷看浣紗女脛部而墜入人間,與其結為夫婦,卻招致岳父外甥今五郎嫉妒,趁夫妻二人參拜神社時殺死岳父。豐次郎追殺今五郎時,母子三人逃至越后,借宿山岡婆家。姐弟被販賣并飽受左太夫奴役。浣紗女因此失明,后與豐次郎重逢,依靠護身符重見光明。豐次郎手刃山岡婆、凌遲左太夫。此時粟飯正熟,豐次郎夢醒而悟。
故事主線由鐵拐仙人、苅萱桑門、久米仙人、費長房、三莊太夫等構成,其中“路經多武峰時”至文末嵌入了“邯鄲夢”的故事框架。該作與《浮世樂助一杯夢》類似,仍囿于民間故事的羅列。其中鐵拐仙人、費長房等故事,多半取自受《神仙傳》影響的歌舞伎或凈琉璃文本。其故事羅列、文本嫁接融合的巧妙與否姑且不論,但是頻率之高、數量之多較為罕見,從文本理解的困難程度可推測,其目標讀者可能包括除了青少年之外的成年讀者。此外,不依托“邯鄲枕”而是通過“炊粟飯”——入夢——出夢——“粟飯正熟”的首尾呼應結構展開敘述,在日本“邯鄲夢”亞型故事中較為少見。《榮花夢》中,金兵衛“等待粟餅”——入夢——出夢——“杵粟餅聲”的結構與之大同小異。本作整體流于文本嫁接融合,“邯鄲夢”在其中的運用也只是因為行文結構上的方便,在立意上甚至稍遜于《浮世樂助一杯夢》,只能算是較為復雜的“串燒夢”。
三、過渡期“邯鄲夢”亞型草雙紙
(一)讀《伊勢》后的“風流夢”
關于青本《風流邯鄲浮世榮花枕》(1772),高木好次、棚橋正博均肯定了其對《榮花夢》創作的奠基作用。從標題可知,故事整體應取材于“邯鄲夢”。少女阿勢居于淺草今戶,渴望嫁與王侯貴胄。某日讀《伊勢物語》后,夢見王宮使者來迎,召至宮中侍奉。阿勢威勢漸長后橫行與侍童私通,為爭奪王位而設計陷害主母親子,直至惡事敗露。將被斬首時,忽聞淺草寺鐘聲,遂從夢中驚醒而悟,不再艷羨榮華富貴。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本根據首頁插畫刻有“伊勢物語”四字的書箱及柱題“榮花枕”三字,在上冊封面里側加注“伊勢物語榮花夢”的標題。從刻有“伊勢物語”四字的書箱可知,少女阿勢大概于午后閱讀《伊勢物語》時,因困意而入夢。此外,文中阿勢威勢漸長、與侍童私通時,黎明前依依不舍,阿勢贈侍童和歌一首,即“待天明兮扔水槽,恨彼破雞亂啼叫,遂令吾愛早出逃”。[9]28作者富川房信將阿勢比作《伊勢物語》第14段中陸奧國的鄉下少女,通過這首極其粗鄙的和歌凸顯阿勢的愚蠢,同時也增添了作品的滑稽性。由此可見,《伊勢物語》第14段對該作的構思意義重大。 該作講述了庶民女子夢想嫁給貴族男子、婚姻美滿,結果卻成一場噩夢的故事。運用“邯鄲夢”來表現女子夢想嫁給貴族男子的構思并非房信獨創,早在寬保—延享年間(1741-1748年)的美人畫中就可略見一斑。江戶浮世繪開山之祖菱川師宣的高徒古山師重之子——古山師政繪有《玉之輿圖》(MOA美術館藏)。盛放的櫻花樹下,床幾上的年輕女子穿著華麗的和服、團扇掩面、欹枕而眠。女子頭頂裊裊升起云靄。云靄中隱約可見抬著錦轎、張著羅傘的迎親隊伍。這幅作品充分反映了適齡女子渴望風光出嫁、婚姻美滿的心境。類似美人畫還有鈴木春信的《見立邯鄲夢》(1765-1770年)。該畫中女子同樣以團扇掩面,夢見自己嫁給武士為妻,迎親的儀仗隊正迎面而來。由此可見,《風流邯鄲浮世榮花枕》的主題在當時的浮世繪中并不鮮見。而“枕書箱而入夢、貫通古今文學”這一奇思幾乎在同一時期也被頻繁運用于美人畫的創作中。礒田湖龍齋作有《夢見相合傘美人圖》《夢見三味線美人圖》《夢見小野小町美人圖》(安永—天明年間)等,山本義信《鷺娘夢》(1771)、鳥居清長《夢見富士山美人圖》(天明年間)亦屬于此類。此外,鳥文齋榮之的《伊勢物語夢》(1781-1801年)與青本《風流邯鄲浮世榮花枕》的構思頗有相似之處。游女所枕書箱上有“伊勢物語”四字,夢境中武士手執火把、追捕躲在野草叢中的女性和私奔男子。該畫作利用“邯鄲夢”的結構,通過書箱及夢中情景,勾連《伊勢物語》第12段“武藏野”。
與此前的草雙紙相比,《風流邯鄲浮世榮花枕》在運用古典文本時,在情節和主旨做了很大改動,也有很多獨創,并沒有局限于簡單羅列或嫁接融合。期待嫁與王候貴胄、私通侍童、玩弄權謀奸計等情節也逐漸轉向成人嗜好。此外,高木好次指出,該作中女主人公在極盡榮華富貴后惡跡敗露的情節,與《榮花夢》中金金先生蕩盡家財、被掃地出門的情節酷似,[3]520這一點也大致無誤。因此,這部作品確實是對《榮花夢》創作可能產生較大影響的重要文本。
(二)沉溺聲色的“青樓夢”
上方兒童繪本《風流邯鄲枕》(一)收錄于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第23卷《繪本集草》,《近世兒童繪本集》上方篇中有影印及翻刻、解說。[10]176-180因封皮缺失,作者、畫者、出版年代等相關信息難以確認。但這類(半紙本型)兒童繪本的鼎盛時期為明和(1764-1772年)、安永(1772-1782年)、天明(1781-1789年)時代;其次,這部作品的趣旨雖與《榮花夢》相似,但情節復雜程度大有不及。從這兩點看,它的創作年代有可能早于《榮花夢》。露情(日語發音與“盧生”相同)夢中乘轎前往島原,因同時收到藝妓夏花、冬菊的情箋而不知所措。又將幫閑當作馬騎,揮金如土、縱情聲色。等餐食備好后,露情被廚娘喚醒,才知一切不過邯鄲一夢。
受兒童繪本的限制,這部作品以簡略詞句和大量插畫為主。解說中只提及其受“邯鄲夢”影響,但這部作品實際脫胎于元文二年(1737)一月于大阪竹本座首演的凈琉璃《御所櫻堀川夜討》第五段“花扇邯鄲枕”。[11]403-410主人公“露情”、藝妓夏花與冬菊、卷首轎輿及島原出口柳樹等設定基本沿襲“花扇邯鄲枕”。此外,文中描述小廝拋撒金幣時高聲呼喊“(小廝)快呀!快撿快撿!梅枝,只此一家咯。”這里的“梅枝”典故,源于元文四年(1739)四月大阪竹本座首演凈琉璃《平假名盛衰記》中,女主人公梅枝以洗手缽作無間鐘,用舀子敲打后憑空落下三百兩的故事。類似的巧用可見于《榮花夢》中,除夕夜單手將升中金銀拋撒、慶祝立春時,萬八感嘆道“(萬八)這可不得了!薩摩屋的源五兵衛大駕光臨哩!宛如梅枝,謝天謝地謝天謝地!”
該作雖僅是凈琉璃劇目“花扇邯鄲枕”的文圖化呈現,本身并不具備太多的獨創性,但其原作內容上與《榮花夢》類似,均刻畫了沉溺花街柳巷的風月聲色的主人公形象,趣旨上比其他任何一部作品都更接近《榮花夢》,而繪本的文圖化呈現,讓它從圖像上也具備了接近《榮花夢》的可能。
(三)攝津私娼的“四季夢”
關于香川大學附屬圖書館神原文庫藏上方兒童繪本《風流邯鄲枕》(二),小林勇的文獻學考察及翻刻具有重要參考價值。[12]50-65該作作者、畫者、出版年代等信息不詳,與國立國會圖書館藏《風流邯鄲枕》(一)同屬半紙本型兒童繪本。主人公“呂洲”(澡堂私娼的別稱)及夢中情節顯然更符合成人嗜好。小林勇指出,要理解這部作品,需要對謠曲《邯鄲》的詞句有足夠的理解。[12]50-51內容大致如下:呂洲居住于攝津國附近,聽聞京都島原山中有位高貴的藝妓,于是不辭辛苦前往拜訪,在夢想屋中得到“契淡枕”,一夢五十年榮華。夢中,敕使迎接呂洲成為他國帝王后妃。呂洲享受了50年四時榮華、飲延壽仙藥后夢醒而悟。
作者將攝津國地區澡堂私娼的呂洲與謠曲《江口》中古代津之國的游女“江口”巧妙結合在一起,賦予了呂洲更為豐富的多重性格。此外,全文基本按照謠曲《邯鄲》結構逐句改寫,可見對謠曲尤其對《邯鄲》詞句的鑒賞能力的確是理解該作的必備條件。該作并沒有止步于機械改寫,結構上根據謠曲《邯鄲》中盧生醉酒獨舞時四時之景同時呈現的情節,將其改寫為描繪近畿地區四時風情的內容,這是該作最具特色之處。舉例來說,春季描繪正月的傳統藝能“萬歲”和“春駒”;夏季描繪大阪的天滿祭、夜游船;秋季選擇藝妓室內舞蹈;冬季則選擇“掃塵”“清雪”等。此外,謠曲《邯鄲》中“粟飯正熟”改為關西獨有的“大唐米飯正熟”,酒盞改為大阪料亭浮瀨郎右衛門藏“貝觴”“銘浮瀨”等,“菊水”改為“伊丹諸白”等,這些都凸顯出了濃郁的京阪風情。
與早期的草雙紙相比,該作不乏以成人興趣為導向的內容,描繪“京阪四時風情”的立意也頗有創意。但也正因如此,其創作囿于羅列地方風俗,注定無法像《榮花夢》那樣,巧妙地運用詼諧文筆、刻畫成人情趣。因此,該作也可歸類為過渡期草雙紙,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四、其他“邯鄲夢”亞型草雙紙
(一)《伽婢子》中的“山桃夢”
白川和子將《初夢邯鄲枕》《由佐七郎榮花夢》《浮世樂助一杯夢》《浮世夢介出世噺》《風流邯鄲浮世榮花枕》《風流仙人花胥》列為利用謠曲《邯鄲》故事背景的草雙紙。[4]68實際上,《浮世樂助一杯夢》中“醉夢”與“欹枕而夢”大相徑庭,文中亦鮮見與“邯鄲夢”有關聯的詞句。《浮世夢介出世噺》雖據說參考《浮世樂助一杯夢》而作,但徒有“醉”而無“夢”,同樣難以確定是否受謠曲《邯鄲》的影響。《初夢邯鄲枕》《風流邯鄲浮世榮花枕》前文已作辨析,不再贅述。《由佐七郎榮花夢》雖已佚失,卻僅憑“榮花夢”三字,不能推斷其與謠曲《邯鄲》有關聯。不過,根據“由佐七郎”“榮花夢”兩個關鍵詞可知,該作實際并非脫胎于謠曲《邯鄲》,極大可能是借鑒了淺井了意所作假名草子第4卷《伽婢子》第3話“游佐七郎一睡卅年榮花事”(以下簡稱“《伽婢子》榮花夢”)。[13]86-87
根據《伽婢子》“榮花夢”,大體可知該作內容如下:游佐七郎本為細川高國家臣,高國戰敗自戕后淪為浪人,欲上京再擇新主。途中詣山崎寶寺,于廊下休憩時入夢。夢中遇一腳夫提一籃山桃,遂問其身份,才知其為交野家家仆,為家中寡女另謀親事而來。七郎憶起叔母恰為交野家主母,便隨腳夫前去拜訪。此后七郎娶寡女為妻、繼承家業。某日得將軍賞識,受任河內守。伴將軍左右兩年有余,威勢一時無兩。30年間育有七子三女,更有八孫。然不意敵軍三千騎來襲,妻子大驚,家人四散而逃。七郎正欲切腹,忽從夢中驚坐起,才知30年如一瞬,恰似邯鄲一炊之夢。此后遁入高野山,潛心修行。
渡邊守邦指出,《伽婢子》“榮花夢”改編自《夢游錄》“櫻桃青衣”,直接出處尚無定論,《五朝小說》一說最具說服力。[14]10-47其中“山崎寶寺”“山桃”“七郎叔母”分別對應“櫻桃青衣”中“精舍講筵”“櫻桃”“盧姓叔母”,“三十年”“七子三女”與“櫻桃青衣”一致。由此可見,青本《由佐七郎榮花夢》應是根據假名草子《伽婢子》“榮花夢”改編而成,歸類為受唐人傳奇《櫻桃青衣》影響的夢游類亞型故事,或可稱為類“邯鄲夢”亞型故事草雙紙。
(二)泥尾子的“槐穴夢”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繪本集草》中收錄一卷題為《枕中記夢之世中》的繪本。該作序末署名為“杏花園主人題”。大田南畝天明末年至寬政初年曾用“杏花園”雅號。因此,該作極有可能創作于天明末年至寬政初年間。序中有“又開元年中呂翁經過邯鄲道,云盧生者同邸舍,舍主蒸黃粱,盧生具言生計困厄,呂翁取囊中枕授之曰,枕此榮適如愿。生枕臥之,未幾登第至將相,五十年榮盛無比,忽欠伸而寤,呂翁在旁,黃粱尚未熟。是世名邯鄲夢”一段。此外,繪本柱題標有“夢之世”。《繪本集草》根據其序及柱題文字,將該篇標題定為《枕中記夢之世中》。但實際上,該作正文故事與“邯鄲夢”并無關系,而源自唐代另一大夢游類小說——《南柯太守傳》。
該作主人公名“泥尾子”,泥尾子朦朧間,隨二使者入槐樹穴內,步十里至一城曰“大槐安國”。王授泥尾子太守之職,招其為婿。王宮壯麗勝于漢宮、長生驪山。20年后,王勸尾暫歸故鄉。尾遂乘輿,效仿司馬相如四馬還邛。出一穴,及夢醒,方知夢臥槐下,卻如渡世。后二客共尋槐樹穴,見大穴上如宮殿般土堆,其中蟻數只,又有大蟻兩只。一時感嘆不知是泥尾化為蟻,還是蟻化為泥尾。 該作的主要內容脫胎于《南柯太守傳》,而“泥尾子”一詞又出自《莊子秋水》第17“曳尾涂中”的典故。泥尾子歸鄉如司馬相如四馬還邛擇,多半根據《蒙求》《史記》等漢籍中“升仙橋”的典故而來。此外,在正文故事外另引有《列子》周穆王篇中“主仆晝夜異工(夢)”的典故,這些都反映了該作有別于少兒及青少年通俗讀物,也不同于其他幾種草雙紙的儒家思想。
(三)游仙窟中的“仙窟夢”
高木好次曾指出,富川房信所著青本《風流仙人花胥》(1774)與其已出版過的《浮世樂助一杯夢》《風流邯鄲浮世榮花枕》相同,都是“邯鄲夢”亞型故事。《浮世樂助一杯夢》投射出作者乖僻的剎那主義思想。《風流邯鄲浮世榮花枕》則從中跳脫而出、試圖過理想的生活,但故事最后還是回歸現實主義。而《風流仙人花胥》則強調只有金錢才能滿足現實生活中的幸福。這體現了房信歷經家道中落之后,沉溺于剎那主義,然后轉向理想主義,進而又回到現實,最終歸結于金錢至上的心境轉變。此外,其刊行恰好在《榮花夢》前一年,可見由青本至黃表紙的蛻變并非戀川春町一人之功,或許也有該作之力。[15]2這一觀點肯定了房信運用“邯鄲夢”創作草雙紙的成就,同時基本確立了該作對黃表紙問世起到的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上述推論的成立有一個必要的前提,即《風流仙人花胥》確定是“邯鄲夢”型故事。而問題就在于,這部作品的構思并不出自“邯鄲夢”,而源自唐人傳奇《游仙窟》。
該作講述浮世仙介立志成仙,夢中得通寶仙指引,前往久米氏隱世仙鄉的故事。為博仙人歡心,仙介喬裝成行商,賣唱蕎麥面。拜求侍女傳情箋被拒后于墻上題詩。久米仙知其才情,便擇吉日招其為婿、宴請諸仙。不料老君遣西王母來,責難久米仙妄招凡人為婿,斥責眾仙耽于酒色、以術作樂。又說費長房磨礪成仙之事。此后通寶仙又現,告知仙介真仙術乃錢術。仙介夢醒而悟,遵循教誨、成為“錢人”。
從內容上看,該作實際為房信利用浮世草子《風俗游仙窟》所作的翻案作品。自寶歷十年(1760)至安永六年(1777)間,房信大量運用浮世草子創作草雙紙。房信關注、利用最多的是八文字屋本(尤其寶歷后期)的“時代物”。[16]1-13前人研究并沒有指出《風俗游仙窟》(1744)與《風流仙人花胥》的關聯。對比兩作,《風流仙人花胥》幾乎完全是縮略圖文版的《風俗游仙窟》。其中不乏自《游仙窟》至《風俗游仙窟》一貫繼承下來的詞句,如《游仙窟》中文生、十娘、五嫂以古詩述情時引用《詩經》中“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折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兩句,《風俗游仙窟》中將之改寫為文生以《詩經》傳情、久米仙以《詩經》做媒。這一情節被房信原封不動地套用到《風流仙人花胥》中。類似的情況比比皆是,但由于房信刪去了所有明確暗示“游仙窟”的元素,因此至今無人得知其“游仙窟”的本質。
與《風俗游仙窟》相比,房信在《風流仙人花胥》中所作的最大改寫,在于“仙人不如錢人”的構思,以及類似“邯鄲夢”的夢境框架。開篇通寶仙人自言“吾于元明時始入錢術,至寬永得萬代不易”。“仙人”在日語中與“錢人”同音。文末通寶仙人再次出現,告知仙介真正的仙術乃是“錢術”,凡世間事當以錢術為尊。“仙人”=“錢人”“仙術”=“錢術”的詼諧表達體現了田沼時代金錢本位的時代風氣。此外主人公名為“浮世仙介”,意為生于浮世但求仙人生活之人。此處仙人并不是指無欲無求的仙人。文中提及“以風水山月為友、游于竹林,只愿不知晦日、但飲鼓瀧諸白,極樂人間”。“仙介”一名反映的也是當時流行的享樂主義。
由此可知,將《風流仙人花胥》視為“邯鄲夢”亞型故事,其實是一種誤解。房信舍“文生”而立“浮世仙介”,去詩棄賦后又套上夢象敘事的框架,成功隱去了游仙窟。加之最終歸于金錢至上的仙介,與《榮花夢》中渴望一夜暴富的金金先生看似有一定關聯,世人才誤以為是邯鄲一夢。只是《榮花夢》的作者戀川春町和世人一樣,不知《風俗游仙窟》、不懂《風流仙人花胥》的可能性有多大?對于這樣一部幾乎照搬浮世草子《風俗游仙窟》的作品而言,要說它體現了房信個人心境變化、對《榮花夢》創作產生了極大影響,顯然言過其實。
結 語
通過對上述九種早期“邯鄲夢”亞型草雙紙的考察,可以發現:(1)如“唐人夢”“浮世夢”“串燒夢”“風流夢”“青樓夢”“四季夢”“山桃夢”“槐穴夢”“仙窟夢”等,江戶時期早期“邯鄲夢”亞型故事(或類“邯鄲夢”亞型故事)已然呈現出豐富多彩的形態、求變多樣的趣旨;(2)創作上采用了套用歌舞伎及凈琉璃等作品、雜糅民間傳說及神怪故事、運用日本經典古典文學、適配地區四時風俗、簡化草子文學作品等多種創作手法;(3)趣旨上逐漸融入青少年通俗讀物范疇外的、反映當時享樂主義時代風氣的內容;(4)混雜其他夢游類故事、夢象敘事結構包裹其他故事等情況,使前人對“邯鄲夢”亞型故事的甄別或有謬誤之處。
上文的梳理不僅對日本江戶時代早期草雙紙中“邯鄲夢”的改寫做出了更為細致全面的闡釋,同時也有助于理解此后的30年,即黃表紙盛行時期“邯鄲夢”熱的產生。正因有了早期“邯鄲夢”亞型故事草雙紙多樣的形式趣味、自由的創作手法、應時多變的內容,黃表紙《榮花夢》的問世才能水到渠成。此后30年經久不衰的“邯鄲夢”亞型故事創作,雖然大抵以《榮花夢》為藍本,但仍不乏與早期這九種草雙紙存在關聯的內容。如房信于安永五年(1776)所作黃表紙《金金仙人通言》,雖由題名可知附會《榮花夢》之意,但其中也有如久米仙人、鐵拐仙人等與上述早期草雙紙類似之處。又如豐里舟于天明三年(1783)所作黃表紙《八景卯來世能夢》,附會了近江八景、描繪了江戶四時風情,與上述描繪近畿地區“四季夢”的情節異曲同工。
此外,通過本文的梳理可知,作為今后的課題,在考慮中國的“邯鄲夢”在日本江戶時期乃至近代以前的流播情況,探查其如何被改寫、如何深入日本文化等問題時,不僅須對江戶早期的草雙紙文本,還必須對江戶時期的歌舞伎、凈琉璃等戲曲,乃至假名草子、浮世草子、灑落本等進行更全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