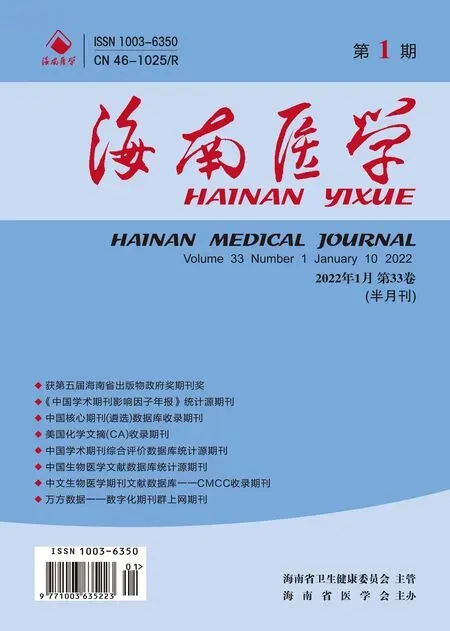白細(xì)胞介素-1β、白細(xì)胞介素-6與腫瘤壞死因子-α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發(fā)展過(guò)程中的作用
趙鵬,金海,朱加興 綜述 庹必光 審校
遵義醫(yī)科大學(xué)附屬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貴州 遵義 563003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是全球范圍內(nèi)最常見(jiàn)的慢性肝病之一,其病理特征為肝細(xì)胞內(nèi)過(guò)量的脂質(zhì)聚積;它的診斷必須滿足兩個(gè)條件:一是通過(guò)影像學(xué)或組織學(xué)檢查證實(shí)存在肝臟脂肪變性;二是排除其他明確病因引起的肝臟脂肪聚積,包括過(guò)量飲酒、藥物(如他莫昔芬)、病毒、自身免疫性疾病或遺傳病(如威爾遜病)等。該病有兩種主要的病理類型,即非酒精性脂肪肝(non-alcoholic fatty liver,NAFL)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NASH),其中NASH可進(jìn)一步發(fā)展為肝纖維化、肝硬化以及肝細(xì)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HCC是該病發(fā)展的最終也是最嚴(yán)重的結(jié)果,合并NAFLD的HCC患者常年齡偏大,且死亡率更高[1]。NAFLD的發(fā)生常伴有多種合并癥,如肥胖、糖尿病、高脂血癥等;流行病學(xué)調(diào)查顯示,在全球范圍內(nèi)NAFLD患者中合并肥胖者占51.34%,在NASH患者中合并肥胖者上升到了81.83%,在某些區(qū)域范圍內(nèi)這一比例甚至超過(guò)了90%[2]。近年來(lái),肥胖所導(dǎo)致全身性慢性炎癥反應(yīng)越來(lái)越被重視,肥胖導(dǎo)致脂肪組織功能失調(diào),促使體內(nèi)多種炎性細(xì)胞因子表達(dá)水平上調(diào),如白細(xì)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細(xì)胞介素-1家族等;在細(xì)胞介素-1家族中,白細(xì)胞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的作用十分重要,其參與了肝病發(fā)展的多個(gè)階段。臨床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在NAFL和NASH患者中,這些因子的表達(dá)水平與病變的嚴(yán)重程度相關(guān)[3-5];NAFLD的發(fā)生和進(jìn)展機(jī)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確。除了造成肝臟功能損傷外,NAFLD對(duì)其他多個(gè)系統(tǒng)(如心血管系統(tǒng),泌尿系統(tǒng)等)也有明顯的影響[6],且目前仍缺乏理想的治療方案。了解這些炎性細(xì)胞因子在NAFLD發(fā)展過(guò)程中的作用將有助于尋找NAFLD預(yù)防及治療的新方法。本文就IL-1β、IL-6和TNF-α在NAFLD發(fā)展過(guò)程中的作用給予綜述。
1 健康肝臟到NAFL階段
在從健康肝臟發(fā)展到NAFL的過(guò)程中,最重要的特征是肝脂肪變性,此時(shí)肝臟僅出現(xiàn)脂質(zhì)聚積,而無(wú)細(xì)胞損傷[1]。脂質(zhì)在肝臟的聚積是由于肝臟中脂肪酸的獲取與消耗之間存在不平衡,即獲取增多和(或)消耗減少;這種失衡可以通過(guò)幾種途徑發(fā)生,包括肝臟脂肪從頭合成(de novo lipogenesis,DNL)的增加;從脂肪組織分解進(jìn)入血漿中的脂肪酸的增加;膳食脂肪攝入的增加;脂肪酸氧化以及酮體生成的減少、低密度脂蛋白顆粒(LDL)向肝外轉(zhuǎn)運(yùn)甘油三酯的減少[7]。
1.1 促進(jìn)肝臟的DNL過(guò)程 DNL是一種復(fù)雜且受到嚴(yán)格調(diào)控的代謝途徑。在正常情況下,機(jī)體通過(guò)DNL途徑將多余的碳水化合物轉(zhuǎn)化為脂肪酸,之后進(jìn)一步將脂肪酸酯化為甘油三酯進(jìn)行存儲(chǔ),這些甘油三酯在需要時(shí)可以通過(guò)β-氧化途徑為機(jī)體提供能量。在人體中,DNL途徑主要活躍于肝臟和脂肪組織[8]。NEGRIN等[9]發(fā)現(xiàn)即使僅使用生理濃度水平的重組IL-1β處理體外培養(yǎng)的原代肝細(xì)胞,經(jīng)處理的肝細(xì)胞中脂肪酸合成酶(fatty acid synthase,F(xiàn)ASN)、乙酰輔酶A羧化酶-2(acetyl-CoA carboxylase-2,ACC2)等與脂質(zhì)合成密切相關(guān)的酶基因表達(dá)水平也呈上調(diào)趨勢(shì);肝細(xì)胞中甘油三酯的累計(jì)量增加,并且其增加量隨著IL-1β濃度的升高而升高,當(dāng)重組IL-1β濃度達(dá)到10 ng/mL時(shí),經(jīng)處理的肝細(xì)胞中甘油三酯總量與未處理的細(xì)胞相比增加了50%;而在使用阿那白滯素(Anakinra,重組型人IL-1受體拮抗劑)處理飲食誘導(dǎo)的肥胖小鼠模型后,實(shí)驗(yàn)組小鼠的肝臟脂肪變性明顯減輕,其肝臟重量占體質(zhì)量的百分比與生理鹽水處理的對(duì)照組小鼠相比減少了約20%[9];這提示IL-1β能通過(guò)上調(diào)肝細(xì)胞新生脂肪生成進(jìn)而促進(jìn)肝臟中的脂質(zhì)蓄積,在肝臟的脂肪變性中起重要作用。與IL-1β相似,TODORIC等[10]發(fā)現(xiàn),使用TNF刺激體外培養(yǎng)的人肝細(xì)胞時(shí),果糖和葡萄糖驅(qū)動(dòng)的肝細(xì)胞脂滴積累明顯增強(qiáng)。TNF也能促進(jìn)肝細(xì)胞中乙酰輔酶a羧化酶α(acetyl-CoA carboxylase alpha,ACACA)、脂肪酸合酶和固醇調(diào)節(jié)元件結(jié)合轉(zhuǎn)錄因子1(sterol-regulatory element-bin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1,SREBF1)等與脂肪合成相關(guān)酶的mRNA表達(dá)水平上調(diào)[10]。
1.2 促進(jìn)脂肪組織的脂質(zhì)分解 除肝內(nèi)的DNL外,肝臟中的脂質(zhì)蓄積另一個(gè)重要途徑是血漿中的脂肪酸隨著血液流動(dòng)經(jīng)肝門靜脈進(jìn)入肝臟。血漿非酯化脂肪酸(non-estesterified fatty acid,NEFA)池貢獻(xiàn)了大部分流向肝臟的脂肪酸,尤其是在禁食狀態(tài)下;非酯化脂肪酸池中包含來(lái)自飲食的脂肪酸以及脂肪組織中的脂肪分解產(chǎn)生的脂肪酸,并且脂解過(guò)程所動(dòng)員的甘油三酯對(duì)于維持NEFA池的功能穩(wěn)定起主要作用[11-12],當(dāng)脂肪細(xì)胞的脂質(zhì)分解增加時(shí),血漿中脂肪酸水平隨之上升;并且同位素人體代謝追蹤研究發(fā)現(xiàn),來(lái)自脂肪組織的脂肪酸占NAFLD患者肝臟中甘油三酯來(lái)源的很大一部分,提示脂肪細(xì)胞脂解失衡是膳食誘導(dǎo)NAFLD的重要機(jī)制[11];脂肪組織中的脂質(zhì)分解是一個(gè)受到多種因素嚴(yán)格調(diào)節(jié)的過(guò)程,這些調(diào)節(jié)信號(hào)包括兒茶酚胺、胰島素、生長(zhǎng)激素、利鈉肽和一些脂肪細(xì)胞因子等,這些信號(hào)作用于下游的脂肪酶,進(jìn)而對(duì)脂質(zhì)分解發(fā)揮調(diào)節(jié)作用[12]。在脂肪組織中,脂滴的大小反映脂質(zhì)的生成與分解之間的相對(duì)速率關(guān)系,MIYOSHI等[13]發(fā)現(xiàn),在過(guò)表達(dá)脂肪細(xì)胞中的甘油三酯脂肪酶(adipose triglyceride lipase,ATGL)后,脂肪組織的脂滴較對(duì)照組明顯減小,即ATGL表達(dá)增加促進(jìn)了脂肪組織的脂質(zhì)分解;后來(lái)YANG等[14]發(fā)現(xiàn),在使用TNF-α處理脂脂肪細(xì)胞后,G0期G1期轉(zhuǎn)換基因2(G0S2)的mRNA表達(dá)水平顯著降低,而G0S2蛋白能夠抑制ATGL,減少脂肪組織的脂質(zhì)分解;VAN等[15]的一項(xiàng)實(shí)驗(yàn)發(fā)現(xiàn),在向健康成年男性注射重組人白介素-6后的2 h開(kāi)始,其動(dòng)脈血中的脂肪酸濃度開(kāi)始上升,尤其是低劑量注射時(shí),其濃度可超過(guò)對(duì)照組60%以上。以上證據(jù)表明IL-1β、IL-6和TNF-α通過(guò)上調(diào)肝臟中的新生脂肪生成以及促進(jìn)脂肪組織的脂質(zhì)分解升高血漿脂肪酸水平進(jìn)而加重肝臟脂質(zhì)蓄積,在肝臟肥胖性脂肪變性的發(fā)病機(jī)制中起重要作用。
2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階段
美國(guó)肝病協(xié)會(huì)發(fā)布的指南對(duì)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的定義是:超過(guò)5%的肝細(xì)胞出現(xiàn)脂肪變性,伴有肝細(xì)胞腫脹等肝細(xì)胞損傷,并伴有或不伴有纖維化[1]。除了單純的肝脂肪變性外,肝細(xì)胞腫脹和小葉炎癥是NASH的特征性病理改變。特別是肝細(xì)胞氣球樣變是診斷NASH的關(guān)鍵特征,也是目前使用的NAFLD組織學(xué)分級(jí)和分期系統(tǒng)的一部分[16]。病理研究證實(shí),肝細(xì)胞氣球樣變與脂肪滴的積聚有關(guān)。脂滴在肝細(xì)胞胞漿中的積聚可進(jìn)一步導(dǎo)致內(nèi)質(zhì)網(wǎng)的擴(kuò)張和細(xì)胞骨架的損傷,從而促進(jìn)肝細(xì)胞球囊化的過(guò)程[17],這種由于脂質(zhì)積聚對(duì)肝細(xì)胞產(chǎn)生的損傷作用被稱為脂毒性。肝細(xì)胞腫脹是脂肪毒性的重要表現(xiàn)。脂毒性使肝細(xì)胞處于脂質(zhì)應(yīng)激狀態(tài),并釋放出含有多種物質(zhì)的細(xì)胞外囊泡。這些囊泡中所含的CXCL10、神經(jīng)酰胺、線粒體DNA和腫瘤壞死因子樣凋亡誘導(dǎo)配體(TRAIL)等,這些因子可促進(jìn)巨噬細(xì)胞的活化,并促進(jìn)巨噬細(xì)胞向肝臟的轉(zhuǎn)移和浸潤(rùn)[18]。MIURA等[19]發(fā)現(xiàn),長(zhǎng)期高脂肪飲食會(huì)使常駐肝臟的巨噬細(xì)胞(即庫(kù)普弗細(xì)胞)向促炎的CD11c+表型(也稱作M1表型)分化數(shù)量增加,并增加促炎細(xì)胞因子的生成,如IL-1β、IL-6、TNF-α等,加重肝臟脂肪變性和局部炎性反應(yīng)。HADINIA等[20]的研究發(fā)現(xiàn),與單純非酒精性脂肪肝和健康人相比,NASH患者體內(nèi)的IL-1β和IL-6水平顯著升高。當(dāng)使用NOD樣受體蛋白3抑制劑降低NASH模型小鼠體內(nèi)的IL-1β以及IL-6表達(dá)水平后,肝臟中浸潤(rùn)的巨噬細(xì)胞和中性粒細(xì)胞數(shù)量降低,肝細(xì)胞的損傷也得到了顯著改善[21];也就是說(shuō),IL-1β等炎性因子促進(jìn)肝臟脂肪變性,如繼續(xù)進(jìn)展則會(huì)進(jìn)一步引起肝細(xì)胞損傷,如肝細(xì)胞腫脹,從而進(jìn)一步促進(jìn)肝臟炎癥的出現(xiàn)。肝臟炎癥與肝臟脂肪變性互為因果,形成惡性循環(huán)。
3 肝纖維化以及肝硬化階段
在前面已經(jīng)提到,肝纖維化對(duì)NASH的診斷是可有可無(wú)的,但纖維化是NASH進(jìn)展的一種表現(xiàn)。當(dāng)纖維化發(fā)展為晚期纖維化時(shí),可導(dǎo)致肝硬化,最終發(fā)展為肝細(xì)胞癌[22]。肝纖維化過(guò)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是肝星狀細(xì)胞(HSCs)的活化。此后狄氏間隙中的Ⅳ型膠原被Ⅰ和Ⅲ型膠原所取代,并開(kāi)始出現(xiàn)細(xì)胞外基質(zhì)(ECM)過(guò)度沉積。當(dāng)病情進(jìn)一步發(fā)展,肝纖維化隔形成及相關(guān)的血管改變會(huì)逐漸導(dǎo)致肝實(shí)質(zhì)整體結(jié)構(gòu)的改變,開(kāi)始出現(xiàn)門脈高壓及相關(guān)的病理生理事件,進(jìn)而轉(zhuǎn)變?yōu)楦斡不A段[23]。體內(nèi)多種先天性和適應(yīng)性免疫細(xì)胞及其分泌的細(xì)胞因子參與肝纖維化的過(guò)程。庫(kù)普弗細(xì)胞是位于肝竇腔的常駐巨噬細(xì)胞,約占肝竇細(xì)胞的30%。它們?cè)诟闻K炎癥中起著關(guān)鍵作用[24]。前面已經(jīng)提及,長(zhǎng)期高脂肪飲食會(huì)使庫(kù)普弗細(xì)胞向M1型轉(zhuǎn)化的比例增加,促炎細(xì)胞因子如IL-1β、IL-6、TNF-α增加,加重肝臟脂肪變性和局部炎性反應(yīng)。IL-1β可促進(jìn)肝星狀細(xì)胞增殖,顯著增加基質(zhì)金屬蛋白酶抑制劑-1(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inhibitor-1,TIMP1)分泌,TIMP1能抑制細(xì)胞外基質(zhì)降解,從而促進(jìn)肝纖維化。在TIMP1高表達(dá)的小鼠模型中,肝臟出現(xiàn)嚴(yán)重纖維化[19,25]。靜息狀態(tài)的肝星狀細(xì)胞經(jīng)IL-6處理后表型轉(zhuǎn)變?yōu)榧〕衫w維細(xì)胞樣細(xì)胞,肝肌成纖維細(xì)胞能促進(jìn)細(xì)胞外基質(zhì)的合成[23,26]。
4 肝細(xì)胞癌階段
與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癌相比,非酒精性脂肪肝引起的肝癌患者多為年齡較大的女性[27]。此外,有研究發(fā)現(xiàn),即使在沒(méi)有肝纖維化或肝硬化的情況下,NAFLD患者也可出現(xiàn)肝細(xì)胞癌[28-29],并且無(wú)肝硬化的HCC患者更容易發(fā)生更大的腫瘤,腫瘤復(fù)發(fā)率也更高[30]。FU等[31]研究發(fā)現(xiàn),高脂飲食顯著降低了二乙基亞硝胺(DEN)誘導(dǎo)的肝癌小鼠的存活率,并導(dǎo)致嚴(yán)重的肝功能障礙。高脂喂養(yǎng)小鼠肝內(nèi)脂肪滴和肝癌細(xì)胞數(shù)量多于對(duì)照組,肝癌溝及周圍無(wú)膠原蛋白,巨噬細(xì)胞等大量炎癥細(xì)胞浸潤(rùn),炎性細(xì)胞因子的表達(dá)水平更高[31],這提示由NAFLD發(fā)展來(lái)的肝細(xì)胞癌患者病情加重風(fēng)險(xiǎn)更高。IL-6、TNF-α、IL-1β對(duì)腫瘤均有促進(jìn)作用,它們可以促進(jìn)癌前細(xì)胞的增殖和存活,并在缺氧情況下促進(jìn)血管生成[32]。IL-6通過(guò)激活肝細(xì)胞STAT3通路促進(jìn)肝癌細(xì)胞在體內(nèi)外的生長(zhǎng)[33]。一項(xiàng)關(guān)于IL-6與肥胖和癌癥死亡率的大規(guī)模前瞻性研究表明,高體質(zhì)量指數(shù)(BMI)與肝癌相關(guān)死亡率顯著相關(guān)。與BMI正常患者相比,BMI為35 kg/m2的女性肝癌死亡相對(duì)風(fēng)險(xiǎn)高1.68倍,男性肝癌死亡相對(duì)風(fēng)險(xiǎn)高4.52倍[33]。與IL-6類似,TNF-α也與細(xì)胞轉(zhuǎn)化、增殖、侵襲、血管生成和轉(zhuǎn)移有關(guān)[34-36]。IL-1β可以通過(guò)多種途徑介導(dǎo)肝癌細(xì)胞的惡性行為,例如,IL-1β介導(dǎo)同源盒C10(人類肝細(xì)胞癌組織中上調(diào)最多的同源基因之一)過(guò)表達(dá),上調(diào)3-磷酸肌苷依賴蛋白激酶1(PDPK1)和血管擴(kuò)張劑刺激磷酸蛋白(VASP),促進(jìn)肝癌轉(zhuǎn)移[37]。在肥胖的NAFLD患者中,巨噬細(xì)胞向脂肪組織聚集,并向促炎的M1表型分化[38],M1表型巨噬細(xì)胞可通過(guò)IL-1β信號(hào)通路導(dǎo)誘導(dǎo)表達(dá)的細(xì)胞程序性死亡配體(PD-L)1,從而調(diào)節(jié)肝細(xì)胞癌免疫逃避和促進(jìn)肝細(xì)胞癌的發(fā)展[39]。通過(guò)基因敲除抑制IL-1β通路的激活,可以防止肝細(xì)胞癌的增殖、侵襲、遷移、上皮-間充質(zhì)轉(zhuǎn)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等行為[40]。
5 結(jié)語(yǔ)
總的來(lái)說(shuō),IL-1β、IL-6和TNF-α在NAFLD的初期加重脂質(zhì)在肝臟的聚積,脂質(zhì)過(guò)度聚積通過(guò)脂毒性造成肝細(xì)胞損傷,并加重了肝臟中炎性細(xì)胞的激活與浸潤(rùn),炎性細(xì)胞因子水平升高,引發(fā)肝臟炎癥;之后通過(guò)促進(jìn)肝臟星狀細(xì)胞的活化使疾病進(jìn)一步發(fā)展為肝纖維化及肝硬化;在肝硬化加重為肝癌之后,它們會(huì)促進(jìn)癌細(xì)胞的增值、侵襲及轉(zhuǎn)移等惡性行為;目前NAFLD發(fā)病機(jī)制尚不完全明確,因此,通過(guò)尋找新的靶點(diǎn)來(lái)推進(jìn)該病的預(yù)防和治療是十分有必要的。目前,通過(guò)抗炎方法治療NAFLD的研究取得了重要進(jìn)展,例如已有研究證實(shí),在使用藥物等方式使IL-1(α/β)驅(qū)動(dòng)的自身炎癥被抑制時(shí),模型動(dòng)物體內(nèi)的炎性因子、血脂水平及肝功能指標(biāo)水平下降;肝脂肪變性和肝細(xì)胞膨脹等也得到了改善[41-42];雖然要實(shí)現(xiàn)臨床應(yīng)用,還需要更多的動(dòng)物實(shí)驗(yàn)和臨床研究支持。但該領(lǐng)域的進(jìn)一步研究將對(duì)NAFLD的治療有很大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