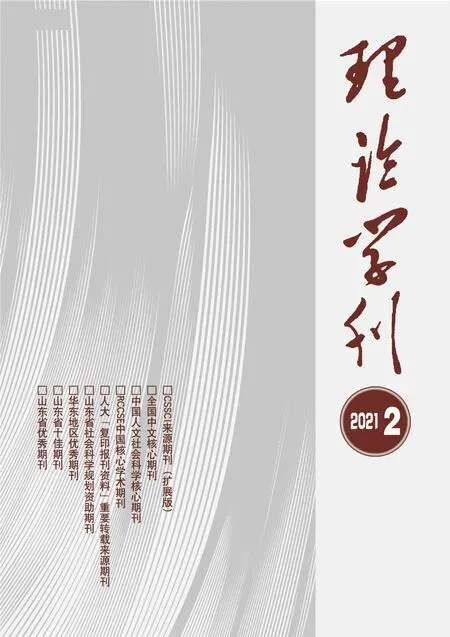論漢代“官非其人”現象的指摘與糾治
王子今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北京 100872)
清代學者趙翼在所著《廿二史札記》卷2“漢初布衣將相之局”條中寫道:“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戰國至秦“已開后世布衣將相之例”,然而“下雖無世祿之臣,而上猶是繼體之主也”。自“漢祖以匹夫起事”,“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者,此氣運為之也。天之變局,至是始定”。基本政治格局的變化,使得“三代世侯、世卿之遺法始蕩然凈盡”,于是生成了新的政治人才選舉制度,“而成后世征辟、選舉、科目、雜流之天下矣”(1)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證》(訂補本),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6—37頁。。自秦代統一的高度集權的政治格局形成之后,漢王朝執政者繼承了這一體制并有所創新和完善。察舉制“賢良文學”之選以兼重德才為出發點,繼而又有實習實踐的要求,官吏隊伍的成分于是得以更新,行政機構也因此提高了執政效能和管理質量。然而官僚機構仍普遍存在“官非其人”的情形。對所有官員的監察、考校,對不法官員的舉劾、彈治,遂成為逐步確定的制度。對于選官形式以腐敗為主要表現的嚴重弊病,也通過政治引導、道德教育、法律約束和輿論評議而有所糾治。“舉非其人,并正舉主之罪”的方式,成為推行察舉選官制度發生“官非其人”現象的有一定效力的責任追究政策。除了議政者對于“吏職多非其人”情形的直接指摘之外,社會輿論多種監督方式也發生了積極的效用。漢代民謠直接的黑暗吏治批判,以及“月旦評”等官員德行品評機制的運行,都對不符合德行要求的從政者形成社會輿論壓力。這些對“官非其人”現象有所糾治的方式具有有益的歷史借鑒意義,我們今天依然應當予以珍視。
一、察舉:選官形式的歷史性進步
中國古代選官制度的演變,大體可以概括為“世官制”“察舉制”“科舉制”三種形式的遞進。“世官制”也就是世系官職的制度,在漢初依然有所遺存。《史記·平準書》說:漢初社會安定,“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裴骃《集解》引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2)《史記》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420頁。。管理倉儲的官員以“倉”“庾”“為姓號”,就反映了這樣的情形。漢文帝時,已經有從社會基層選用“賢良”“孝廉”的做法,指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得從社會下層推薦從政人員。《史記·孝文本紀》記載,因“日有食之,適見于天”,以為“菑孰大焉”,漢文帝遂宣布:“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同時要求“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名臣晁錯就是曾經以“賢良文學”之選,又經帝王親自策試,而得以升遷為中大夫的,即如《漢書·晁錯傳》所言:“后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所謂“賢良文學”,強調道德和才能的標準。不過,當時“舉賢良文學士”這種選官形式還沒有成為完備的制度。漢武帝在即位之后的第一年,就詔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長官“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漢書·武帝紀》記載:“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據此可知漢武帝即位之初實行的“舉賢良”事,因丞相衛綰奏言“所舉”人物學術背景的問題導致“亂國政”而“皆罷”。衛綰于“建元年中”“免之”(3)《史記》第9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770頁。按:《漢書·衛綰傳》作“建元中”“免之”。,御史大夫趙綰等高層助手則因“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的政治傾向而被處置(4)《漢書·武帝紀》記載:“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顏師古注:“應劭曰:‘禮,婦人不豫政事,時帝已自躬省萬機。王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黃老術,非薄五經。因欲絕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殺之。’”。《史記·封禪書》說,漢武帝“初即位”,“漢興已六十余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奸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
六年之后,在“太皇太后崩”的背景下,儒學勢力再次抬頭,漢武帝又下詔“舉孝廉”。“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顏師古注:“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5)《漢書》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60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年明確規定了郡國必須選舉的人數。正是在漢武帝時代,察舉制得以基本成為正統的政制。這一舉措,歷史進步意義十分重大。勞榦曾經指出,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前134),是“中國學術史和中國政治史的最可紀念的一年”(6)勞榦:《漢代察舉制度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7本(1948年)。。這是因為,這一詔令表明察舉制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比較完備的仕進途徑,察舉制作為選官制度之主體的地位已經得以確立。察舉制既重德也重能,而并重德能,可以避免其他因素對官員任用的影響,這對于防止選官腐敗無疑是有效的。
漢代選官制度中有的做法,體現出對行政實踐能力的重視。《后漢書·和帝紀》記載,當時規定“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李賢注引《漢官儀》稱之為“務實校試以職”(7)《后漢書》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76頁。。“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8)《后漢書》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018頁。,意即在行政崗位上先行試用,實踐一年之后,才可以向上級推舉。對于德行人品和工作能力確定具體的實踐方式和考察時限,應當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然而,在吏制嚴重腐壞的大背景下,有一定合理性的選官方式在操作中依然逐漸暴露出一些弊病。東漢時,“選舉不實,官非其人”(9)《后漢書》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61頁。的情形已經相當普遍,導致“政化衰缺”,劉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10)《后漢書》第9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431頁。。選官方式的調整和更新,所謂“清選”,又稱“妙簡之選”,即如《后漢書·儒林列傳上》所載:“時樊準、徐防并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于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
二、監察·舉劾·彈治:對于犯罪官員的行政處罰方式
秦代已經設計了初步的監察制度。郡級行政單位設監御史之職。《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裴骃《集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11)《史記》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39—240頁。《漢書·百官公卿表上》:“監御史,秦官,掌監郡。”秦代任職監御史的具體人物有嚴安上書回憶秦史時說到的“監祿”:“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裴骃《集解》:“韋昭曰:‘監御史名祿也。’”(12)《史記》第9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958—2959頁。中央則有御史大夫。《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祿比丞相,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漢武帝時曾經根據具體需要特設“繡衣直指”(或稱“直指繡衣使者”“直指使者”等)作為皇帝的特派專使,主管貴族高官的監察。《漢書·武帝紀》記載:“泰山、瑯邪群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漢書·王傳》記載:“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群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漢書·雋不疑傳》亦載:“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所謂“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所謂“誅二千石以下”,以及所謂“督課郡國”,即體現了“直指繡衣使者”整飭官場“奸猾”的職責。《漢書·江充傳》記載:“上以充為謁者,使匈奴還,拜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逾侈。”此之“禁察逾侈”,顯然指向的是官場中人。《漢書·趙充國傳》所謂“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顏師古注:“繡衣謂御史”(13)《漢書》第9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985頁。,說明這種監察方式也把軍事指揮官“將軍”納入了監察對象。
“遣直指使者”雖然并非常制,但是與漢武帝時任用酷吏的行政風格相應,用法極其嚴峻。在“直指使者”的“督課”“禁察”之下,“誅二千石以下”或者“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的情形,不能不給人以吏治酷烈的深刻歷史記憶。
漢元帝時,曾經有“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的做法,對此,顏師古解釋說:“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14)《漢書》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87頁。所謂“考校”,與現今“考察”“考核”義近。當時選用官員和考察官員,完全以道德水準為標尺,即所謂“質樸敦厚遜讓有行”“四科”,體現了對于選官制度予以健全完善的一種行政動向。
監察官“禁察逾侈”,即懲罰違反制度的貴戚近臣。查處究辦稱作“舉劾”,最終處分雖然要“奏請”皇帝,但是這些時稱“直指繡衣使者”的特使畢竟擁有很大的權力。例如《漢書·江充傳》記載:“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后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一般官員也可以相互揭發舉報,史稱“彈治”(15)《漢書》第10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226頁。。對于犯罪官員當“舉劾”而“故縱”“阿縱”“不舉劾”者,或者說“阿從不舉劾”者,也要受到處罰,嚴重者甚至同坐。《史記·平準書》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唆文決理為廷尉,于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所謂“見知之法生”,裴骃《集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漢書·食貨志下》顏師古注:“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16)《漢書》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160頁。,具體事例有《漢書·夏侯勝傳》所載“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漢書·循吏傳》所載“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黃)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等等。
《晉書·刑法志》在對秦漢法律制度進行總結時,言及“增部主見知之條”這一行政法的重要創新:“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 雖然“參夷連坐之罪”被廢除,但是官員犯罪,主管負責的上級是要承擔連帶“見知”責任的。有必要一提,此處說“增部主見知之條”始于“蕭何定律”,目前看來,似乎并沒有確切的律文依據。
三、“舉非其人,并正舉主之罪”
據史籍記載,漢代選官制度逐步明確了這樣的原則:薦舉候選人才者,如果其推選對象瀆職犯法,薦舉者也要承擔相應的罪責。漢明帝于建武中元二年(57)剛剛即位,十二月甲寅即頒布詔書,要求“有司務順時氣,使無煩擾”,宣布“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針對吏治方面暴露出來的問題,則表示要予以切實解決:
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托,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
同時,漢明帝還要求郡縣“征發”“務在均平,無令枉刻”。詔令指出了吏治的嚴重危機在于“邪佞”“殘吏”當權,以致下民愁苦,無從申訴,究其根源全在于“選舉不實”,于是他要求主管部門“明奏罪名”,予以懲處。詔令還明確“舉者”也必須同樣嚴厲責罰。所謂“并正舉者”,李賢注有明確的解釋:“舉非其人,并正舉主之罪。”(17)《后漢書》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98頁。漢順帝即位之初,“司空劉授免”。李賢注引《東觀記》曰:“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罷。”(18)《后漢書》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51頁。漢桓帝延熹九年(166),“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光祿勛陳蕃“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托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19)《后漢書》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166—2167頁。。對于選官程序中發現的“舉非其人”“辟召非其人”之類的問題,“舉者”即推薦者及其他責任人必須承擔罪責。這一舉措,顯然已成為確定的制度。
《后漢書·和帝紀》記載了永元五年(93)三月戊子漢和帝關于選官的詔書。詔書曰:“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然而相關制度卻未能切實推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有鑒于此,漢和帝嚴厲宣布:“今新蒙赦令,且復申敕,后有犯者,顯明其罰”。當時執政集團上層已經發現,政治危局的出現與選官腐敗密切相關,于是明確指出:“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奸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李賢注引《漢官儀》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書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決斷,才任三輔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已后,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孝廉吏,務實校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曹事,正舉者故不以實法。’”(20)《后漢書》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76頁。強調選官的基本原則是“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要求“有非其人,不習曹事,正舉者故不以實法”。這里所說的“正舉者故不以實法”,就是嚴格執行對舉薦者提供虛假信息予以追責并嚴厲懲處的法律。
《后漢書·百官志一》劉昭注補引應劭《漢官儀》也強調了“四科取士”的原則,同時指出“有非其人”,“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并正舉者”成為堅持選官合理公正的行政原則。有研究者指出,兩漢察舉制盡管“曾起過不少積極作用,但其流弊也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東漢以后,這一制度的弊端暴露得更為明顯”(21)黃留珠:《中國古代選官制度述略》,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110頁。。相關研究者還特別注意到,“兩漢察舉的許多科目,每每也是對現任官吏考課的項目”(22)黃留珠:《中國古代選官制度述略》,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110頁。。然而對于官吏選用“有非其人”的情形,所謂“并正舉者”,即對“舉非其人”“辟召非其人”的予以嚴肅處理的方式,似乎未予必要的肯定。有的以“官吏法”為主題的學術論著,贊賞“漢代的察舉法在漢代選舉法規中是極其重要的”,“為封建國家提供各方面的人才確立了法律依據”(23)安作璋、陳乃華:《秦漢官吏法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版,第48頁。,但是對于去除察舉制度“有非其人”現象的這種積極的政策措施似也有所忽略,沒有予以具體評價。
其實,秦制已早有“任人”有失即予以嚴厲追究的傳統。《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寫道,鄭安平、王稽都曾經由魏入秦引致范雎,后來又因范雎舉薦得到更高權位。“(范雎)入言于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于函谷關;非大王之賢圣,莫能貴臣。今臣官至于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于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然而,“(范雎)任鄭安平,使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稾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于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后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這就是后來蔡澤以為機會的所謂“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于秦,應侯內慚”的秦國上層政治氣象的變化(24)《史記》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415—2418頁。。秦昭襄王對范雎的寬容,是偶然的個別的情況,而“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是“秦之法”即秦國實行的制度。周海峰對此指出:“被保舉者犯罪,保舉人與之同等處罰。事實上,倘若保舉人犯罪,被保舉者也會被免職”,鄭安平、王稽與范雎是互為“保舉人”和“被保舉人”的。他還指出,此非孤證,“出土秦律條文也有相關記載”(25)周海峰:《岳麓書院藏秦簡〈置吏律〉及相關問題研究》,王捷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6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43—145頁。。顯然,考察秦之吏制,并說明漢代相關制度的歷史淵源,是有其必要性的。
四、議政場合對“吏職多非其人”的指責
漢代朝廷議政時,常常可以看到對“舉非其人”“辟召非其人”之類情形的公開揭露和指責。《后漢書》即多有相關記載,比如《朱穆列傳》曰:“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張酺列傳》稱:“三府辟吏,多非其人”;《陳忠列傳》云:“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楊秉列傳》有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征,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埶,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李固列傳》亦稱:“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儒林列傳上》同樣表示:“儒職多非其人”;等等。凡此,都說明了這種常見的情形。
《史記·夏本紀》中有一段關于“皋陶作士以理民”,而“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的文字。皋陶陳說了他選用人才協助執政的設想,特別說道:“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司馬貞《索隱》指出,這里取用了《尚書·皋陶謨》的文字,但是太史公有所調整,與通常“次序”不同,“班固所謂‘疏略抵牾’是也”(26)《史記》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7—79、298頁。。對于這種語言“次序”的文字處理,我們或許可以理解為司馬遷結合西漢時期官場境況表達了對于當時吏治“非其人居其官”情形的態度。《史記·周本紀》記載,周穆王在與甫侯對話時,責問他:“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也說到選用執政集團成員“擇非其人”的問題。秦末社會動蕩,對于軍事領袖的選擇,陳嬰也曾經講過“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27)《史記》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77—79、298頁。的話。董仲舒嘗言:“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28)《漢書》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499頁。。《漢書·于定國傳》中也有“其勉察郡國守相群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的說法,表達了同樣的理念。
《漢書·鮑宣傳》載錄了諫大夫鮑宣的上書,從中可見對漢哀帝行政的批評,其中就有直接指責選官問題的文字:“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的表述,體現出非常開明的政治意識。所謂“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顏師古注:“此官不當加于此人,此人不當受于此官也。”(29)《漢書》第10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089、3175—3176頁。
漢元帝時,中郎翼奉上疏言“得失”,曾高度頌揚周政曰:“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比較而言,漢王朝“亡周召之佐”乃是大弊。他進而指出當時社會危機之嚴重:“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不過,他提出的建議是“因天變而徙都”(30)《漢書》第10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089、3175—3176頁。。這或許是出于就近管理“東方”(31)西漢晚期,關西與關東的經濟文化地位已經有所變化,故王莽曾提出經營“東都”的規劃。參見王子今:《西漢末年洛陽的地位和王莽的東都規劃》,《河洛史志》1995年第4期。劉秀定都洛陽,標志著行政中心轉移的實現。的考慮,而并未就“在位”多“非其人”的腐惡政治開出救治的藥方。
五、“天心未得”:災異的警告
漢代對于選官“有非其人”所作的政治批評,有時是利用災異的出現而提出,從而擴展了影響力。如《后漢書·五行志二》“災火”條說,漢靈帝中平二年(185)南宮云臺和樂城門發生的嚴重火災,是上天對政治黑暗的警告。當時政治危局的具體表現,便包括了“官非其人,政以賄成”。是時黃巾暴動,“變亂天常,七州二十八郡同時俱發”,究其原因,乃在于“靈帝曾不克己復禮,虐侈滋甚”,“官非其人,政以賄成,內嬖鴻都,并受封爵。京都為之語曰:‘今茲諸侯歲也’”(32)《后漢書》第11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297頁。。《后漢書·順帝紀》也記載,陽嘉元年(132)閏十二月辛卯詔書曰:“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以“天心”與“人情”的相應關系,提示了體現“天人之際”神秘關聯的“天文”與“人文”的比照。
指摘高級官吏“非其人”,結合“日月少光”等嚴重災異而發聲,必定會對執政集團高層形成沖擊。如《漢書·蕭望之傳》記載,“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而蕭望之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顏師古注:“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咎在臣等,是其意毀丞相。”(33)《漢書》第10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280、3357—3358頁。可見,“日月少光”已然成為政爭中攻擊對方的手段,而所謂“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的說法,在當時是確實可以在上層形成極大震撼力的。
《漢書·孔光傳》記載,漢哀帝策免丞相孔光:“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群職曠廢,奸軌放縱,盜賊并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為。是以群卿大夫咸惰哉莫以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于虖!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其中也說到“日月無光”。所引述《尚書》文字,顏師古注:“位非其人,是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材。”(34)《漢書》第10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280、3357—3358頁。這里所謂“位非其人,是為空官”以及“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材”,體現出一種積極的政治意識,可以與前引“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對應理解。這兩種說法各有高明處,雖然一言“天下”“官”,一言“天官”,看起來立足點并不相同。
《漢書·元后傳》載有王鳳因“陰陽不調,災異數見”上疏謝罪的言辭,也反映了當時政壇公認的責任追究定理:“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于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最后有“唯陛下哀憐”語。據說“其辭指甚哀”,以致“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王鳳所謂“此臣一當退也”和“此臣二當退也”,其實都強調了“災異數見”是上天對“大臣非其人”的警示。
東漢時,“庶官多非其人”(35)《后漢書》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76頁。已經成為公認的社會政治現實。而與“災咎”“天心”相聯系,體現了影響比較廣泛的社會層面的政治理念。如前引《后漢書·順帝紀》詔書所謂“吏政不勤”“選舉不實,官非其人”與“災咎屢臻,盜賊多有”的關系。由于“吏政”弊病,“選舉不實,官非其人”,以致“天心”和“人情”都有惡性反響。“吏政”的腐壞致使“災咎”有嚴重的表現,乃是當時社會共同的政治意識。這樣的觀點雖不能得到自然與人文關系的科學說明,卻有利于對不合理政治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糾治。
六、陳寔故事
前引《后漢書·五行志二》寫道,漢靈帝時代,“官非其人,政以賄成,內嬖鴻都,并受封爵”。官場“賄”現象之嚴重,是導致“官非其人”的重要原因。《后漢書·五行志一》“謠”條指摘當時“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36)《后漢書》第11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282頁。之情形,直接批評最高執政者竟然主持“賣官”。這當然是極端的例子。“政以賄成”,是王朝末年政壇上下非常普遍的惡習,而高層權力影響下級,一層危害一層,一級腐蝕一級,也是“官非其人”情形嚴重泛濫的重要因素。
“選舉牧守,多非其人”(37)《后漢書》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082、2210、2203頁。,“刺史非其人”(38)《后漢書》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082、2210、2203頁。,“刺史”“用非其人”(39)《后漢書》第9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431頁。,“郡守非其人”(40)《后漢書》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082、2210、2203頁。,總之“州郡多非其人”,時人以為“世濁”(41)《后漢書》第5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59頁。,乃是清醒的判斷。對政情有所了解的人們普遍注意到,“議郎、大夫之位”“今多非其人”,“宰守非其人”(42)《后漢書》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462、1533、1562頁。,“三府辟吏,多非其人”(43)《后漢書》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462、1533、1562頁。,“辟召非其人”(44)《后漢書》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167頁。,又可以統稱之曰“位非其人”(45)《后漢書》第6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462、1533、1562頁。,“內外吏職,多非其人”(46)《后漢書》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772、2065頁。。“吏政”腐敗,已經形成全面的社會影響。
《后漢書·陳寔傳》講述了陳寔有關郡太守“用吏”,面對復雜情形,以個人智謀提出特殊建議的故事,其云:“(陳寔)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托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于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后被征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臨別時高倫說明其中情由,深心致謝。“倫謂眾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于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強御,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后漢書》執筆者寫道:“寔固自引愆,聞者方嘆息,由是天下服其德。”所謂“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李賢注:“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于檄而懷之者,懼泄事也”;“請從外署之舉,不欲陷倫于請托也”(47)《后漢書》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772、2065頁。。
陳寔的做法,掩飾“為侯常侍用吏”事,轉移了輿論視線,上司以為得體,于是有“比聞議者以此少之”的贊賞。所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見于《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風俗通義·過譽》有一段關于地方官員政績與政聲的文字,也引錄了“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一語。大概這樣的說法,在漢代政治生活中有相當廣泛的影響。
七、《書》“歌”《詩》“刺”及謠諺的輿論批判作用
漢代對于選官腐敗的社會輿論譴責,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前引漢順帝陽嘉元年(132)閏十二月辛卯詔書“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句后,隨即說到“《書》歌股肱,《詩》刺三事”(48)《后漢書》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62頁。。《書》“歌”和《詩》“刺”,是古來通常出現的社會輿論表達方式。
《后漢書·五行志一》記載:“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舂黃粱。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案此皆謂為政貪也。”認為“童謠”的內容,是對“政貪”的揭露和譴責。又解釋說:“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主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這里所說的“童謠”,與上文說到的“京都為之語曰:‘今茲諸侯歲也’”同樣,都是民眾口傳的輿論方式。所謂“所祿非其人”之“丞卿主鼓者”們,皆由“政貪”而得權勢,即“以錢為室金為堂”。《抱樸子外篇·審舉》說,東漢靈帝、獻帝之世,選官體制敗壞,“臺閣失選用于上,州郡輕貢舉于下。夫選用失于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于下,則秀、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所謂“故時人語曰”,《太平御覽》卷496引《抱樸子》作“桓靈曰”,《喻林》卷12據《太平御覽》寫作“桓靈諺曰”,可見也是以民間謠諺為形式的批判“舉”“察”“秀、孝不得賢”,即選官腐敗的社會輿論。《后漢書·劉玄列傳》記載,兩漢之際,農民軍控制關中,“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長安為之語曰:灶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49)《后漢書》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471頁。按:后代文獻中還可以看到相關現象的久遠歷史記憶,如《舊唐書·鄭畋傳》:“竊據宮闈,偽稱名號,爛羊頭而拜爵,續狗尾以命官,燕巢幕以夸安,魚在鼎而猶戲。”。雖然并非正統王朝的選官體制,卻同樣因為選舉“非其人”,遭到以歌謠為形式的社會輿論的批判。呂宗力指出:“民間的即興歌謠對時政的反應可以相當敏感與直接。”(50)呂宗力:《漢代的謠言》,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8頁。而童謠的生成與傳播,雖然情況比較復雜,然而也是社會輿論表現的一種特殊形式(51)王子今:《略論兩漢童謠》,《重慶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
八、關于“月旦評”
面對吏治的黑暗,一種時日周期相對確定的政治輿論形式——“月旦評”得以出現。《后漢書·許劭列傳》最初說到這種以政治人物為主要對象、方式比較特殊然而社會影響甚為鮮明的輿情“核論”“人物”的形式時云:“初,(許)劭與(許)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52)許劭的人物品評,為一時所重。《后漢書》本傳記載:“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孫盛《異同雜語》也記載:“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太祖大笑。”
前引《風俗通義·過譽》引錄“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語,見于郅惲故事:“長沙太守汝南郅惲君章,少時為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赍牛酒到府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歙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沖,摧破奸雄,不嚴而治。”歐陽歙還說:“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隨即“主簿讀教,戶吏引延受賜”。郅惲對歐陽歙的說法公開駁難,其云:“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奸,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慝并作,百姓苦之。而明府以惡為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與偏有。君雖傾危,臣子扶持,不至于亡。惲敢再拜奉觥。”一番話說得歐陽歙“甚慚”。應劭針對此事作了評論,認為郅惲“暴諫露言”似有不妥,不過對于歐陽歙的妄言妄語,直接予以反駁也是合理的:“謹按:《禮》,諫有五,風為上,狷為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歙于饗中,用延為吏,以紫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觥強歙可行也。”然而應劭又說:“今惲久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為官擇人,知延貪邪,罔上害民,所在荒亂,怨慝并作,此為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認為繇延的惡劣表現“非一旦一夕之漸”。又說:“汝南,中土大郡,方城四十,養老復敬化之。至延奸舋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見無禮于君者,若鷹鹯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不即彈黜奸佞,而須于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為陷君。君子不臨深以為高,不因少以為多,況創病君父,以為己功者哉?而論者茍眩虛聲,以為美談。汝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決。然自君章之后,轉相放式,好干上怵忮,以采名譽,末流論起于愛憎,政在陪隸也。”(53)吳樹平:《風俗通義校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頁。對于郅惲的表現雖予肯定,又有頗多保留。所謂“汝南”“其俗急疾”而追求“虛聲”“名譽”的說法,是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汝南俗有‘月旦評’”的意義的。
也許對于“汝南”的地域限定應當予以注意。《三國志·吳志·陸瑁傳》記載,三國時人陸瑁曾表示過這樣的態度:“夫圣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于大道也。”《三國志·魏志·鐘繇傳》裴松之注引太子書言孫權事:“若權復黠,當折以汝南許劭月旦之評。”言“月旦評”發生地在“汝南”,而陸瑁所謂“汝潁月旦之評”,地域則擴展到了“穎”,此當是區域文化研究者所應注意的。
關于“月旦評”,還有一個情形值得關注。《魏書·劉昶傳》寫道:“高祖曰:‘朝因月旦,欲評魏典。夫典者,為國大綱,治民之柄。君能好典則國治,不能則國亂。我國家昔在恒、代,隨時制作,非通世之長典。故自夏及秋,親議條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爾。何者?當今之世,仰祖質樸,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茍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清一朝軌,使千載之后,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俙元、凱。’”所謂“朝因月旦,欲評魏典”,似是說對“為國大綱,治民之柄”的“典”的“月旦”之“評”。但下文又言“清濁”“流”“等”,“君子小人名品”,以及“士人品第”“小人之官”,或許這里所謂“朝因月旦,欲評魏典”,主要還是指與“名品”相關的評定,而“班鏡九流,清一朝軌”的原則,是堅持有益于“國治”的“典”。對“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建議的否定,是要繼承以“九品”為程式的選官制度的傳統。
《晉書·祖納傳》記錄了梅陶和祖納、王隱有關“月旦評”意義的一段很有意思的對話:
(祖)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勛。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污;盜跖引少,則為清廉。朝種暮獲,善惡未定矣。”
本傳稱:“時梅陶及鍾雅數說余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由上面的對談可知,“月旦評”這種對于政治人物的輿論評判形式曾經形成久遠的影響。關于“月旦評”究竟是“佳法”還是“未益”這兩種近乎對立的評價所形成的爭議,似乎沒有必要深入討論,而“月旦評”也并非只看“一月”善惡“便行褒貶”。我們認為應當特別注意的,是“月旦,私法也”即“月旦評”作為民間輿論的性質,以及祖納“君鄉里立月旦評”及“君汝潁之士,利如錐”之說與前引陸瑁所謂“汝潁月旦之評”所表露的區域文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