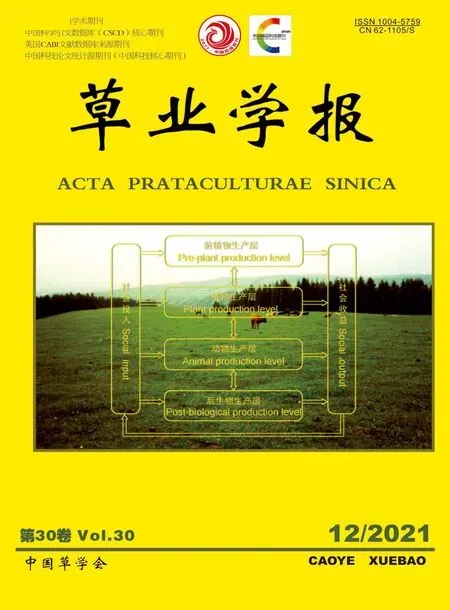懷念考林·斯佩丁
任繼周
(蘭州大學草地農業生態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蘭州大學草地農業科技學院,甘肅蘭州730020)
我知道考林·斯佩丁(Colin Spedding,1925-2012)(圖1)是在1978 年。二戰以后,美國和蘇聯為首,將世界分為兩大陣營,兩者互相對壘,長期封閉。中國執行一邊倒的政策,對西方科學動態幾乎全然隔絕,更談不上科學交流。直到1978 年全國科學大會以后,國家執行改革開放的政策。我可以在內部書店讀到國外出版的書刊,并承擔主編草原、牧草學科外刊文摘的任務。因此,我每周都須瀏覽有關草原、牧草的外文專業讀物。這時我才知道考林·斯佩丁所著《草地生態系統》和《農業生態系統》的信息。

圖1 考林·斯佩丁
我從中國科學院西北分院圖書館借到考林·斯佩丁所著《農業生態系統》(Agriculture Ecosystems),發現他的觀點與我基本吻合,而且這本書提供了許多全球性的資料,這在當時是很難得到的。我立即組織人力翻譯出版,并以此為藍本,結合自己多年的體會,于1980 年在甘肅農業大學開始講授《草地農業生態系統》。此后又輾轉請人從倫敦買到《草地生態系統》(Grassland Ecosystems)。從此我很想見到這兩本書的作者本人。
1985 年,我們獲得農業部批準,由甘肅草原生態研究所在蘭州舉辦“國際草地生態講習班”,主要目的就是邀請考林·斯佩丁前來講學。他的英文名字有些少見:Colin Raymond William Spedding(C.R.W. Spedding),人們習慣簡化為考林·斯佩丁(Colin Spedding)。另外邀請了8 位國外專家在講習班做專題報告。講習班于1985 年7 月25 日開學,至8 月20 日結束,歷時近一個月。
當時我們的草原生態研究所正在初創階段,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也處于農業轉型期,請來這樣一位見多識廣,能說會干的一流農業生態系統學者,恰逢其時。那時我們研究所的辦公樓正在施工,沒有大型集會場所,就在臨近的八一賓館租了一間大廳作為教室。考林·斯佩丁不負所望,他不但愉快地接受了我們的邀請,參加講習班開學儀式,還采納了我們有些過分的請求,罕見的以系統講授的方式講課一周,闡發農業生態系統的理論。每天上下午各授課兩個小時,包括約20 分鐘的答疑和討論。這是我們豐收的一周。
在這一周的教學活動和日常接觸中,考林·斯佩丁教授展示了典型的英國科學家的紳士風度。我見過不少外國專家,像他這樣典雅而又平易,嚴謹而又寬松,在普通交往中透著幽默情趣的人,少而又少,或可堪稱唯一。
他在課堂上講述學術問題,好像在展開一個理論長卷。他一口標準的牛津語音,字句清晰,層次分明,銜接緊密,用詞準確、鮮明而又簡練易懂。尤其他舒緩的聲調,抑揚流暢,飽含韻律感的語言,送來的不僅是邏輯嚴密的知識板塊,還有心理的按摩。即使我這個沒有在西方長期工作和生活過的人,聽來也聲聲入耳,好像在聽我的母語那樣順暢,感受了真正的思想交融。我為了打破多年的思想封閉,多享受一些交流的愉悅,在課余時間的閑談、聚餐或短途參觀旅行時,總是找些話題,談生態系統科學,也談生活瑣事。好在每一個話題,我開個頭,他就不緊不慢地,以他獨有的牛津韻律,講出豐富而有色彩的故事。我體會了這位以“機智迷人的演說家而聞名”的英倫教授果然名不虛傳。也許我們的友誼就這樣,通過頻繁的談話,在不知不覺中,滲透到彼此的心底深處,建立了超乎常態的友誼。一方面,他具備了豐富的知識積存和絕佳的傳播技巧。另一方面,我作為他真誠的科學同道,也有一些陳年體會作為談資。何況凡是老練成功的演說家,必然善于觀察他的談話對象。我習于傾聽,少量反饋的“聲納”習慣,可能引起他的關注,激發了他的談興,助長了我們友誼的發展。
自從2012 年考林·斯佩丁謝世噩耗傳來,我就想寫一篇紀念他的文章。因為他突出的個人特色和優點,值得我個人、我們的中國同道學習和參考。我對他的懷念之情縈繞心頭多年不去。直到40 年后的今天,我主編的《中國農業倫理學導論》告一段落,才動筆完成我的夙愿,在電腦前把考林·斯佩丁介紹給國內同道。
考林·斯佩丁誕生于英國英格蘭一個基督教牧師家庭。二戰時服役于英國皇家海軍電動魚雷艇,戰后退役。經過一段尋覓和思考,他看中了英國草地研究所。這個研究所位于英國英格蘭伯克郡的赫爾利小鎮,近鄰里丁大學。而里丁大學是當時的英國農業科學研究中心。就在這一個典型英國鄉村風光的平緩丘陵坡地上,英國草地研究所建立了一片平房,其中包含辦公室、實驗室、小型牧場和廄舍。規模不大,但規劃周詳,設施齊全,與周圍農村氣氛協調和諧。
這里沒有富麗堂皇的大樓,看起來像個農莊,很不顯眼。但憑著他的創辦人和首任所長威廉姆·戴維斯(William Davies,1899-1986)深厚學養和遠見卓識,卻成為世界草地科學的中心。他提出土-草-畜三位一體的草地科學理論,引導世界草業科學研究近40 年,成為多位草業科學專家的搖籃。考林·斯佩丁就是從這里進入草地科學,并逐步深入草地農業科學殿堂的。最終,他發展了他的前輩威廉姆·戴維斯提出的“土-草-畜三位一體”理論,將草地生態系統的理論率先問世,進而發展為農業生態系統。
如此說來,無論草地的“三位一體”,還是“草地農業生態系統”,都是源自英國的草地研究所,這個研究所是無可爭議的世界草地科學研究思想中心。如今英國的草地研究所已不復存在,威廉姆·戴維斯和考林·斯佩丁也相繼作古。我們懷念他們,欣慰地感到這個草業科學泉源仍未枯竭。
考林·斯佩丁來到這個研究所做實驗室清洗器皿工。這是個極其簡單,沒有任何引發“夢幻”的職業。但奇跡就在這里發生。我們不要忘記,這里正是現代草地科學的泉源。青年考林·斯佩丁敏銳地受到這里科學氣氛的啟迪,決定從這里邁出走向草地科學的第一步。他利用業余時間取得倫敦大學動物學函授學位,然后以實驗員的角色,從1949 年在威廉姆·戴維斯的領導下,從事綿羊放牧生態研究,從而引發他對草地生態系統的濃厚興趣。以他杰出的勤奮和穎悟,數年內取得突出成績。由此一發不可收拾,進而開展農業生態系統研究,先后出版了《草地生態系統》和《農業生態系統》兩書。生態系統的理論在1937 年已由斯坦利提出,但只在生態科學領域被視為劃時代的進展。威廉姆·戴維斯摘取其部分精華,以土-草-畜三位一體的理論移入草地科學而大放異彩。直到20 世紀70 年代,考林·斯佩丁以其廣闊的視野和深厚的社會科學素養,進一步將土-草-畜三位一體的理論延展,把生態系統的理論引入農業領域,由此造就了他在世界農業生態系統奠基人的地位。
說到這里我忍不住要插入一段題外話。世界文化是多元并發的,與斯坦利同時,蘇聯的蘇卡喬夫提出了內涵相似的“生物社會學”理論,并于20 世紀50 年代帶到中國,在中國的西雙版納建立了試驗站。后因中蘇關系破裂,蘇聯專家撤離而該站被荒棄。“文革”后,我國杰出植物區系專家吳征鎰院士看到這個試驗站殘存遺址,為我國無端逝去的流年而潸然淚下。實際上我國對生態系統關心的應不只吳征鎰一人。
由于考林·斯佩丁在科學研究和科學管理的杰出才干,由一個洗滌工人進入研究員系列,并于1972 年,被任命為英國草地研究所副所長。10 年后,1982 年至1988 年兼任塞倫塞斯特皇家農業學院(Royal Agricultural College)院長。1986-1990 年在里丁大學任農業生態系統教授、農業系主任、農業戰略中心主任和副校長。英聯邦國家似有一個不成文的慣例,聲望卓著的專家,在離開實質崗位到退休以前,一般會擔任一段生物研究所所長的過渡期。我曾撰文介紹過的霍奇森就是走的同一過程,他也出自英國草地研究所,歷任新西蘭梅西大學農學系主任、農學院院長,后任自然資源研究所所長直至退休。考林·斯佩丁也循例,擔任了一段生物研究所所長,于1994 年在這一崗位上退休,時年69 歲。他安靜地宅居里丁附近3 英畝的住宅中直到離世,享年87 歲。
考林·斯佩丁從1982 年來到里丁,這個英國農業科學研究中心,直到去世,30 年來再沒有離開過里丁。農業生態系統的科學架構,跨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系統,為考林·斯佩丁發揮不同學科之間的鏈接與協調提供了理想的舞臺。在這里他如魚得水,充分發揮廣泛的科學情趣,使盡全身招數,廣泛開展多方面的學術活動。他1994 年至2000 年任英國科學理事會主席以及多個委員會和組織的主席、副主席,如歐洲綿羊和山羊動物生產研究委員會,國際非洲中心方案委員會人民動物保護協會副主席,伴侶動物福利委員會顧問,蘋果和梨研究委員會委員,甚至曾擔任國家馬術論壇委員等專業和“非”專業職位。在這里我使用了一個帶引號的“非”字,因為凡是與農業有關的活動,對于一個農業系統科學家來說,都屬自己的專業領域而非域外。
考林·斯佩丁是個敏于思而勇于行的人。他不只掛虛名,而是實干。他牽頭制定了英國有機食品標準。于2000 年擔任了家禽品質保證計劃主席(chairman of the Assured Chicken Production Scheme,即現在的Red Tractor Farm Assurance Poultry Scheme),建立了英國家禽產品安全供應系統,覆蓋了約1500 萬只家禽。
不能不著重提出,他還做了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從1988 到1998,整整10 年,他擔任英國家畜福利協會主席,制定了動物福利“五項自由”原則,即保障農業動物免于饑渴、免于不適、免于疼痛和疾病、免于恐懼和表達正常行為的自由,這已成為動物福利學科的理論基礎。
斯佩丁以其文雅的風度,幽默的語言開展廣泛的社會交流,獲得“詼諧迷人的演說家”的稱號。曾發表200 多篇科學論文,撰寫或編輯專著19 部。始終圍繞著“農業生態系統”科學范疇,重點在有關農業結構和土地利用。由于他在農業科學多方面杰出貢獻,于1988 年被授予大英帝國勛章(CBE),1994 年被授予爵士爵位。
對于考林·斯佩丁,我還想突出介紹三點。首先他充分利用了農業生態系統這個學科平臺。農業生態系統本身包含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部分,其固有的科學內涵使人視野廣闊。此外,它提供了較多的外延鏈接界面,可任憑學者根據各自的學術背景和所在環境,發揮特長,做出自己的貢獻。他作為農業生態系統的奠基人,在里丁30 年繁忙、廣泛的科學社會活動,為我們做出了榜樣。筆者本人由草地農業生態系統發展到農業倫理學,也可作為旁證。
其次,考林·斯佩丁本身具有良好的科學家素養。他既富于科學知識,也充滿科學的張力。他使我聯想到當前新冠肺炎病毒的來勢。科學家應有“科學病毒”的勢頭,把相關科學及時、及地向周圍擴散,大力造福于人類。但這離不開個人的人格魅力和語言、文字的表達能力。更難得的是他的踏實的實踐能力。這需要畢生的修煉,考林·斯佩丁全做到了。
第三,考林·斯佩丁的科學足跡為我們勾勒了一條西方通向現代農業的道路。他起步于實驗室器皿洗滌工,從倫敦大學獲得動物科學的學位,直到成為知名專家,擔任英國草地研究所副所長,轉任塞倫塞斯特皇家農業學院院長,里丁大學農業系主任、副校長。我們前面說到的另一草業科學大家,新西蘭的霍奇森,也有大體相同的經歷。這清晰表達了現代農業就是草地農業,而動物科學是現代農業不可或缺的基礎。反觀我國草業科學現狀,動物科學力量明顯不足,離草業科學的合理結構還有不小的距離。
1985 年,考林·斯佩丁圓滿結束了在蘭州一周的講學,我們依依惜別的情景將是我永遠的記憶。我送他一枚雕刻精美的中文篆字名章,并把他的名章印在《農業生態系統》中譯本的扉頁上。作為交換,他送我一本他的原著。8 月20 日,我送他到機場,離蘭回國。蘭州機場遠離市區70 公里。當時還沒有高速公路,足足走了近兩個小時。他斷續而深情地回顧了綿羊放牧生態研究引他走上農業生態系統的歷程,這似乎是他課堂上沒有照顧到的一段補課。這個世界聞名的研究所我有幸訪問過3 次,與他在蘭州相遇時已訪問過兩次。雖然那時他已轉往里丁大學,沒有見面,但作為談話背景,可能多了一些共鳴,縮短了彼此的距離。當隨行人員幫他辦好行李交運和登機手續時,他似乎從回顧中醒來,與我握手告別。他對我說的最后一句話是:“至少每年交換一次圣誕卡!”我回答了一句重復的話,“至少每年交換一次新年圣誕卡!”
我們兩人都履行了自己的諾言。他每年寄我一個很有氣魄的大型新年圣誕卡,我送他一枚富含中國傳統的,中國紅為基調的新年圣誕卡。1990 年他從農業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兼里丁大學副校長職位上退休以后,就改為一個很小的樸素的新年圣誕卡。我最后一次收到的新年圣誕卡是他2012 年11 月27 日簽名發出的。過了不久,侯扶江教授在訪英期間,得知他已于2012 年12 月17 日去世。算來直到他生命結束的前20 天還在惦記著我這個遠方的友人,鄭重地送來他簽名的新年圣誕卡。
著實令人懷念,這個優雅、誠信而又親切的英國好友考林·斯佩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