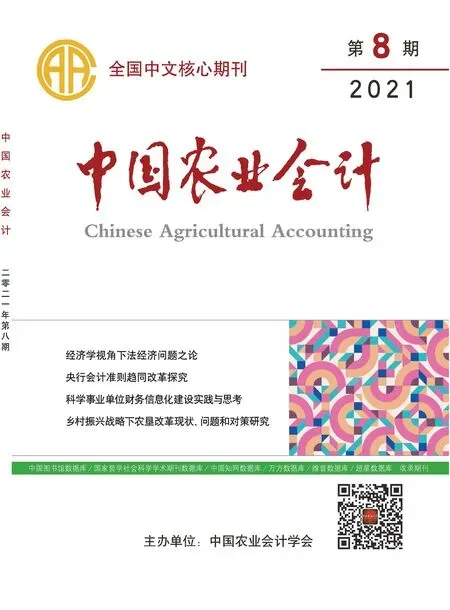經濟新常態下農民市民化灰色預期及化解
劉歆立 靳 戈 陳 娛
城鎮化是實現現代化的重要載體與基本趨向。據有關數據顯示,目前發達國家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70%以上,美國早在2000年農村人口比重就已減至5.3%。在我國,2018年底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城鎮化率)為59.58%,全國人戶分離人口(即居住地和戶口登記地不在同一個鄉鎮街道且離開戶籍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86億人,其中流動人口2.41億人。不過考慮到城鎮化達到一定閾值后,由于各種自然的社會因素疊加而必然放緩速度、停頓甚至出現逆向負增長,我國城鎮化要達到2021年底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5%的目標仍然任重而道遠。其中農民工對市民化的灰色預期,是一個重要而又容易被忽略的影響城鎮化發展的變量。本文擬探討經濟新常態背景下農民工市民化灰色預期的影響因素及其化解。
一、加劇農民工市民化灰色預期的影響因素
黨的十九大明確做出了我國經濟新常態的科學預期,并概括出其基本特征是經濟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變。近兩年來,整個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交往受限,國際形勢中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這些不利方面投射到我國,則是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投資增長后勁不足,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困難較多,穩就業壓力較大。以上影響因素對城市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能力造成直接沖擊,使得具有市民化意愿的農民對進城后生活質量、社會融入、社會保障和社會適應等愿景產生了灰色預期。
(一)習得性無助心理效應強化了農民工市民化灰色預期
心理學實驗表明,經過訓練的狗能夠學會跨越屏障或躲閃實驗者加于它的定時電擊。但是,當遭受不可預期且不可控制的多次電擊之后,它即使有機會逃離電擊,也無所適從與坐以待斃,隨之會出現沮喪、壓抑、缺少主動性等消極心理狀態。這種由于無力預期來自外部傷害而產生的無助感被稱為習得性無助效應。類似地,人如果獲致這種習得性無助后也會陷入絕望、悲哀等負面情緒的陰影中,對未來發展前景因預期灰色而采取消極無為的行動策略。不期而至的外在經濟波動(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就業機會減少、生活成本陡升等經濟傷害,也會在抗經濟打擊能力偏弱的農民工身上產生習得性無助效應,本來有著市民化意愿的農民甚至會遲延或取消這些打算。
基于2016年中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研究,二代農業流動人口市民化水平總體偏低,拖家帶口在外打工幾十年最后仍選擇返鄉生活而非“市民化”的農民家庭不在少數,這同“流動家庭”在外漂泊遭遇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而產生灰色預期直接相關。而我們近期的相關調查也表明,大約有26%的農民工家庭因新冠肺炎疫情這一“黑天鵝事件”影響,取消了進城購房到城市生活的發展計劃。
(二) 當前城市化階段性特點加劇了農民工市民化的灰色預期
研究表明,2013年起我國城市發展出現了“三個反超”和“一個分化”的階段性特點:大城市對中小城市的反超,消費型城市對投資型城市的反超,服務型城市對工業型城市的反超。房地產價格波動出現了由大中小城市“同漲同跌”變成了“大城市大漲,中城市小漲,小城市基本漲”的分化格局。這“三個反超”表明,當前城市由以投資和工業為基本特征的中小城市向以服務和消費為基本特征的大城市轉變,農民城市化路徑由以原初的從農村走向以工廠為主的工業化中小城市,變為當前的從農村直接跨越到以服務和消費為主的大城市。相對于之前較低的制造業就業門檻與中小城市市民化流向,當前農民市民化的門檻、成本付出、進城風險無形地被提高了,例如購房這一剛性需求就讓進城農民望而生畏,使他們對市民化難以產生積極的心理預期。
另外,2019年我國城市化率與工業化率的比值是1.4,世界平均是2.0,發達國家是3.4,這種“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的特征,直接導致市民化進程中的農民工進城后生活成本增加與生活滿意度降低,最終導致城市吸引力對之減弱。例如還處于工業化階段的城市,空氣質量差、接送孩子上學麻煩和居住交通擁擠等城市問題,使許多習慣了鄉村生活方式的農民產生恐懼、厭惡未來的城市生活環境與生活方式等不良心理預期。
(三)社會融合困難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有著明顯不利影響
現在的農民工市民化不是過去“農轉非”式戶籍登記方式的簡單改變,而是要使他們具備對城市深度認同而萌生永久居住意愿的社會經濟條件,能夠對平等享有城市公共服務、就業發展前景、家庭穩定收入等生活愿景有合理預期,減少對可能受到社會排斥、權利受侵和社會沖突等市民化風險的灰色預期。研究表明,相對稀薄的社會網絡、城市的陌生感和社會歧視目光,阻礙了農民從心理上文化上轉向市民化的積極性,周工作時間、風俗習慣、衛生習慣等,也對農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一些負向影響。
在當前全球經濟深度衰退的大背景下,農民家庭市民化決策選擇通常會參照所熟悉與信任的同群者的行為決策。這是因為我國社會至今仍保留著“熟人社會”的大量痕跡,在外來海量信息真假難辨與不可靠的情形下,農民家庭出于減少信息不對稱帶來的決策潛在風險而傾向于認可熟人傳遞的相關信息,使自身決策與鄰近相似個體呈現趨同性。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同群者”可能出于怕落埋怨等自我保護心理而過于言詞謹慎,可能夸大城市融入困難帶來的生活麻煩與隱患。因而,這種“同伴效應”也會直接影響農民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緩解下的市民化灰色預期。
二、減弱農民市民化灰色預期的化解措施
一是立足新發展格局優化市民化發展環境,使農民形成積極的市民化預期。面對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世界經濟深度衰退等多重沖擊,2020年我國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國家,城鎮新增就業1 186萬人,1億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目標順利實現,全國城鄉區域發展格局不斷優化,等等。同時,中央又提出了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與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使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到70%等目標。要廣泛宣傳教育這些發展成就與國家“十四五”規劃,使之成為提振農民市民化信心與形成積極預期的強心劑,使農民市民化成為當前暢通國內大循環、形成城鄉融合發展的高水平動態平衡的有力引擎。
需要強調的是,單靠改變宣傳教育和“農轉非”的戶籍登記方式,不能完全消除農民市民化灰色預期,地方政府還要采取切實措施優化農民市民化發展環境。例如,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加大高價彩禮、人情攀比、厚葬薄養、鋪張浪費、封建迷信等不良風氣治理”,當前新生代農民工正值結婚年齡高峰期,進城買房是農村待婚青年(農村“剩男”居多)成家立業的前提條件,坊間流傳的“農村丈母娘踹動城市房地產”的說法在許多地方越來越成為現實。然而,為婚購房如果完全由農民承擔其家庭負擔會很重。可見,農村婚姻市場擠壓,并不能轉化為農民市民化的有效動力。所以,地方政府宜探索合理的農民市民化成本分攤機制,對于那些有強烈購房剛需的農民家庭,進行必要的政策幫扶、資金補貼等。
二是加快體現共享理念的戶籍制度深層改革,縮小城市內部不同群體間的福利差異。通過分析2017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發現農業轉移人口的人力資本、職業層級、經濟收入、公共服務、融入情況和居留意愿與流入城市的發展規模與行政級別成正比,收入低、就業難、房價高和子女教育問題是農民市民化灰色預期的重要成因,地級及以上市的農民市民化難度大而發展后勁不足。縣城及中心城鎮必然成為當前經濟新常態背景下農民就近市民化的目標靶向地,因而國家要積極構建大中小城市協調發展機制,以有力反制“三個反超”和“一個分化”的階段性特點帶來的負面作用:合理安排中小城市產業布局,增加行政資源供給,優化就業環境等;地方政府要同步跟進落實國家提出的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規劃,完善住房市場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等,采取切實措施有效提高農民市民化后預期收益。同時,還要將農民市民化工作重心由落戶轉向基本公共服務的無差別覆蓋,從改善農業轉移人口的“新市民”城市生活質量入手,把他們尋求穩定工作的成本降下來,提升農民流動家庭城市生活滿意度。現階段新生代農民工已構成市民化的主體,家庭市民化成為市民化的關鍵,因而,要想實現2021年城市化65%的目標,必須解除土地、戶籍、社會保障、收入、房價等影響因素對農民市民化的實際影響,進一步通過政府賦權、市場賦利與社會賦能的協同聯動提高新市民家庭應對城鎮化風險的能力,從而有效對沖市場的非均衡性、地方政策的不連貫及大環境的不確定性等帶來的農民市民化灰色預期。
三是營造開放包容的市民化發展氛圍,增進農民工城市融入的積極預期。農業轉移人口主觀社會融合受遷移模式、社會網絡、生計資本、年齡特征和外出經歷等因素綜合影響。研究表明,宏觀上,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能顯著地增強融入、削弱隔離,淡化戶籍制度造成的融入障礙;中觀上,遷入城市加強社會交往和積極參加組織活動、改善住房和提高收入,能夠有效提高融入程度;微觀上,近距離、長時段和家庭化遷移的流動人口主觀融入程度較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流動人口削弱主觀隔離,更好地融入流入地。為此,地方政府應促進市民化人口客觀融合并使其與主觀融合相匹配,改變以農民融入城市實現市民化的單向思維,真正地縮小城市內部不同群體間的福利差異,有效減弱農業轉移人口或“新市民”同老市民的距離感,增加他們對城市的深度融入感與永久居住的意愿,切不可使農業轉移人口處于身子進入城市新家,而腦子依然留在農村老家的“半城市化”或“偽城市化”狀態,真正實現農民從主觀“愿意”市民化到客觀“能夠”市民化的社會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我國農民市民化大量出現了“一家兩戶”現象:部分青年農民夫妻一方帶著子女入戶城鎮,另一方戶口仍保留在農村;新一代青年農民工安家入戶城鎮生活,老一代父母留守農村守護著其農村戶籍擁有的各項權益。之所以出現這種另類的“半城市化”現象實際上不難理解,一方面,農村既有利益、職業周期風險、故土情結與風險規避等促成了保留農村戶口,反映了安全第一的社會理性和家庭利益優化的經濟理性的中國式城市化邏輯。另一方面,說明我國城鄉關系已從城市中心主義向城鄉一體化轉變,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后,農村開始擁有日益彰顯的比較優勢。因而,對這種“一家兩戶”的二重化戶籍登記現象,宜采取包容發展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