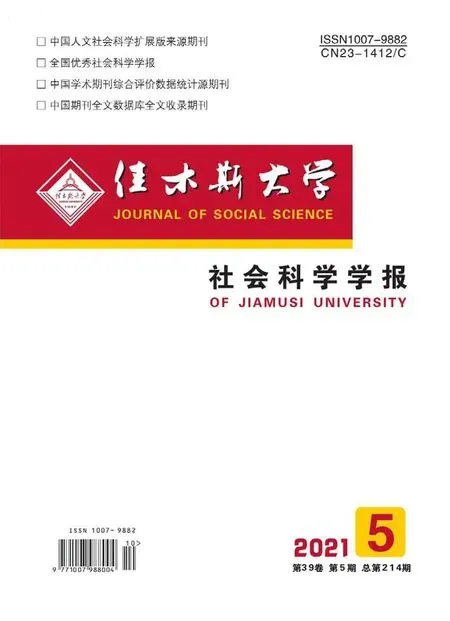朦朧夜色中的人性追尋 *——《夜色溫柔》的倫理啟示
周天楠
(東北石油大學 外國語學院,黑龍江 大慶 163318)
一、序言
《夜色溫柔》的故事背景設置在美國和歐洲,與《了不起的蓋茨比》一樣,展現了美國絢麗浮夸的“爵士樂時代”的社會生活場景。小說主要情節描寫了一對貌似天作之合的美國夫婦——精神科醫生迪克與富有卻身患精神分裂的妻子妮科爾,以及女影星羅斯瑪麗之間的古老的三角戀主題。在這場婚姻中,健康的主人公迪克從最初的積極樂觀、富于魅力卻逐步淪落為精神萎靡、長醉不醒的廢人,最終陷入被康復的妻子拋棄的境地。這一悲劇主題說明了當代物欲膨脹的異化世界對人精神的摧殘與人際關系的虛偽、脆弱。當然,文學經典的倫理訴求向來都是多聲部的,小說圍繞著這一主題預設了致命的倫理結且衍生出錯綜復雜的倫理關系、倫理沖突與倫理選擇,蘊含著深刻的倫理價值,為現代社會追求及時享樂的人們敲響了警鐘,也為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提供了道德指引。
很多評論家認為《夜色溫柔》是《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續篇,而主人公迪克是蓋茨比的翻版。但實際上,兩部著作相隔九年,對于相似的題材,菲茨杰拉德所采用的透視角度是全然不同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揭示了美國夢的浪漫與虛妄,與之相較,《夜色溫柔》情節則更加凄婉動人,人物形象也更貼近生活,對內“深入探析了迪克·戴弗的精神隱憂”,對外“診察了社會和文化的廣泛病態。”[1]70瑪喬里·K·羅林斯高度贊譽《夜色溫柔》:“以超俗、深邃的眼光,形象地再現了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生活圖景,具有永恒的、超越時空的人生意義。”[1]26亨利·丹·派珀亦明確指出:“與許多正統歷史學家的真實陳述相比,他的小說使我們更接近于那個世界。”[2]1
二、異化的代際倫理
“代際倫理”是指家庭關系中父母與子女的關系,代際關系中父母對子女除了履行撫養的責任和義務外,還要在子女的成長過程中起到正向的引導作用,教給他們倫理原則以及做人的道理。但倘若父母出于某些原因沒能稱職地履行對子女的倫理教育便會使孩子的成長出問題。反過來,子女對父母不僅應孝其身,更要孝其心,對于父母來說,沒有什么比繼承祖輩的教導成為立足于社會的“倫理人”更好的報答了。所謂一葉知秋,家庭的代際倫理與整個社會的風尚息息相關。菲茨杰拉德在《夜色溫柔》中書寫了各種代際關系的生活情態為我們呈現了二三十年代的美國社會畫卷和歷史變遷,刻畫了美國日漸惡化的代際倫理的窘境與混亂的社會道德狀況。
“在人類文明之初,維系倫理秩序的核心因素是禁忌。禁忌是古老人類倫理秩序形成的基礎,也是倫理秩序的保障。”[3]15倫理禁忌是悲劇的基本主題,是主人公不幸與痛苦的根源。《夜色溫柔》預設的致命倫理結即妮科爾與父親沃倫打破了亂倫禁忌,致使妮科爾精神錯亂。美麗迷人的妮科爾出身上流社會,家境富庶,惜少年喪母,父親在照看女兒時卻與之發展成有悖倫常的戀人關系,“我們就像是戀人一樣——后來我們突然就真的成了戀人——事情發生后我真想一槍斃了自己”[4]155,沃倫在精神病醫生多娒勒一再追問下坦白道,異化的親子關系毀掉了女兒原本幸福的人生。然而,悲劇發生后,沃倫卻似乎更關心事情會不會傳到美國去,會不會影響他的家族聲譽與社會地位。因此在留下一大筆錢后,“紳士”沃倫就把妮科爾丟在了精神病院。出于對亂倫后果產生的道德恐懼,他逃到瑞士尋求安寧,不顧對孩子的倫理責任和義務,直至臨終也不肯見女兒。而對于尚無判斷能力的妮科爾,父親的冷漠加之對自我本性的憎惡等同于雙重拋棄,致其遭受嚴重的心理創傷。妮科爾的悲劇意義在于教誨,警示人們亂倫會帶來的嚴重后果,讓人們必須遵守這一倫理禁忌。
同樣缺乏父愛的還有第二女主羅斯瑪麗,父親去世后母親是她最好的朋友,在生活與事業上一直引導著她。但父愛的缺失,使她缺乏與男性的正常人際交往,也會導致她自身的性格缺陷。她的母親強悍精明,隨著羅斯瑪麗在電影界一舉成名,埃爾西太太的“投資”熱情被迅速點燃,她在經營女兒的同時功利地為其精心策劃社會關系網,擇選“金字塔”交往對象。在商品社會,“社交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交易,每個人都急于會見高價的商品人,與之接觸從而獲利或換取更高的社會地位。”[5]38-45初遇迪克夫婦,埃爾西太太便看出他們非富即貴,當女兒因愛上迪克這個有婦之夫而痛苦地哭泣時,她慫恿道:“去吧,不管發生什么,權當增長見識。要么傷害你自己,要么傷害他——但不論怎樣都毀不了你的。”[4]46顯然,這位母親并沒有對女兒有正確的教育與引導,沒有教會她自尊與自愛。“教育的目的是抑制子女惡的自然天性,塑造其精神天性,使子女成為有倫理道德的人。以子女的喜好為依據,是有違人性教育的,其結果是唐突孟浪,傲慢無禮。”[6]371
小說中迪克的母親早逝,而父親從頭至尾并未出場,直至逝世。接到父親去世的噩耗,迪克陷入回憶:父親是位善良的牧師,“祖籍美國古老的弗吉尼亞州,去世后被安放在教堂的墓地,與一百個姓戴弗的、姓多爾西的以及姓亨特的人埋在一起”[4]243,這些似乎暗示著父親的美德傳承自古老的祖輩——那些具有誠實勤懇、宏偉氣魄與豪爽精神的老一輩的開拓者。他教導迪克懂得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良知、尊嚴、禮貌和勇氣”[4]242,使迪克從小立下志向:“要做一個正直的人,一個善良的人,一個勇敢又睿智的人,但這都太難了。他還想被人愛,假如他能做到的話。”[4]160論語有云:“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可見,真正的孝道是不改父母的教導。然而,與我國“父慈子孝”的雙向父子倫理模式不同,西方社會“孝親”的概念原本較淡漠,再加上經歷戰爭的迫害與社會突變,就更不要提繼承父輩遺志了。因此,迪克父親的突然離世象征著傳統倫理道德的消亡。迪克在墓園駐足,感到:“在這兒已了無牽掛,相信自己也不會回來了。‘再見了,父親!再見了,我所有的先輩。’”[4]243這一場景標志著他與傳統教化的最終割裂,也預兆了他此后因投身物欲,放縱沉淪而終將招致噩運。他的毀滅,也是因為他渴望被人愛,受人敬仰——成為名人——這種名利的渴望戰勝了父親所強調的誠實、謙恭、勇敢等美德。透過紛繁的、物欲橫流的世界,菲茨杰拉德敏銳地透視了消費文化對傳統文化的顛覆,以及金錢意識對人性的異化和扭曲。
三、奢靡的消費倫理
消費倫理主要研究消費活動中的道德觀念、道德關系、道德規范等問題。傅立葉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充滿罪惡,這些罪惡都是文明制度的產物”[6]476,其特征之一就是消費、享樂的社會風氣,這種新的消費倫理不再勸誡人們克勤克儉以便老來享受,而是以各種方式宣傳鼓勵人們無節制的物質享樂和消遣。戰爭所帶來的身體與精神創傷和隨之而來的肆意揮霍的消費觀,使很多美國青年在人生的迷途中得過且過、悲觀失望。對金錢與財富的追逐造成了人際間的利益沖突,也導致了道德的墮落與社會的混亂。
迪克·戴弗曾有過人生的輝煌時期,醫學博士,獲得過獎學金,也曾著書立說鉆研學術,更重要的是他外表英俊、性格迷人,被人們稱為“辛運的迪克”。他的崇高理想是“當一名自古以來最優秀的精神病醫生”[4]158。然而諷刺的是,當遇到精神分裂的妮科爾后卻改變了他的人生規劃,雖有違職業倫理道德,他還是愛上了他的患者,這與有錢有勢的沃倫一家正打算為妮科爾“買個醫生照看她的計劃”[4]186不謀而合,于是戴弗醫生娶了個精神病人。(《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灰燼谷的巨幅廣告招牌——埃克爾堡醫生的眼睛雖透視了美國社會的病態卻無能無力——因為他是眼科醫生。)他們的結合象征著精神病專家迪克奮不顧身地投入到對“爵士樂”時代出現的人格分裂和精神變態的治療:“在巴黎,他整夜都把她樓在懷里,而她服了苯巴比妥后仍然睡不沉;凌晨,不等她開始精神錯亂,他就用溫存呵護話語安撫她,于是她又進入夢鄉。不等她醒來,他就在隔壁房間通過電話安排好了一切。”[4]198
對于沃倫家那個“婚姻買賣計劃”,他嗤之以鼻,筑起工作的堡壘捍衛自己的家庭與尊嚴:“他單獨外出只坐三等艙,喝最便宜的酒,衣物稍有點奢侈都要責罰自己。這樣,他保持了一定的經濟獨立。”[4]202可當弗朗茲醫生找他投資二十二萬美元合辦診所時,沃倫家立即毫不猶豫地出資贊助,暗地里卻鄙夷:“你是我們的了,你遲早得承認,裝什么獨立性,可笑。”[4]211至于去不去工作他們倒并不在意。“為了擁有他,讓他永遠不思進取,扮演他現在的角色,妮科爾對他的懈怠總是予以鼓勵。她不斷地給他買禮物,給他錢,讓他淹沒在她所提供的物質享受之中。”[4]203小說中對于妮科爾花錢如流水有大量詳盡的描述,通常采用列明細的方式:
“她買了彩色念珠、沙灘上用的軟墊、人造花、給洋娃娃配的袖珍家具,還有對蝦色的一塊新品種布料,此外還有十二套游衣,一個橡皮短吻鱷,一副金子和象牙鑲嵌的旅行象棋,送給阿貝的幾塊亞麻手絹……”[4]63
她買的東西有需要的,但大部分是用不上的或送人的。菲茨杰拉德隨后揶揄道:“妮科爾是大量創造力和辛勞的產物。為了她,一列列火車從芝加哥開始它們的行程……美國的整個體制,隨著它轟轟烈烈地向前推進,為像她這樣的大批購物者提供了一個紅火的局面。”[4]64妮科爾的財富如此之多,使得迪克的工作變得好像實在沒什么干頭,“他在大房間里待著,聽著電鐘發出的嘀搭聲,聽著時間的流逝……”[4]203畢竟,“‘勞動光榮’已經不再是這個社會的主流價值,新的工作倫理是‘自由職業者最幸福’。”[7]
為了打發時間,他們甚至在法國買下部分山村,成為里維埃拉海灘的主人。于是,把海灘打造得極盡奢華,吸引客人來拜訪刷存在感成了他們生活的主題。他們與一群才華橫溢卻又放浪形骸的客人們一起縱情享樂、逃避現實。但有一件事是明確的,即迪克為他的享樂付出了意料不到的代價:他喪失了人格的獨立性與做人的起碼準則,開始感到沮喪,陷入精神空虛的絕境。他發現遁入及時行樂的生活方式顯然行不通,于是他又選擇了遁入酒精,“陶醉的酒一下肚,精神就會放松。”[4]207他新交的朋友大多酗酒,尤其是阿貝·諾斯,經常喝的不省人事,后來阿貝在紐約一家非法酒店給人打死了。迪克傷心欲絕,他喝更多的酒,為了阿貝的死,也為逝去的十年青春,他“不知怎的就像個職業舞男一般為沃倫家賣命,讓自己的能量全部鎖進了沃倫家的地窖里。”[4]239阿貝的死象征著迪克精神的死亡,與蓋茨比的肉體死亡相比,這種精神上的死亡更加讓人感到毛骨悚然。造成主人公信念喪失的,正是這惡濁的浮華世界與上流社會的險惡用心,他們相信,在消費社會,人人都是可以用金錢收買的,在這樣的人事環境中,鮮有人能堅守住勤勞、正直,獨立自主之類美德。當然,“人們自身對金錢的貪婪與對上流社會奢靡生活的向往也會使人變得媚俗,喪失做人的尊嚴,最終只會落得無盡的痛苦與悔恨。”[8]134
四、墮落的兩性倫理
與我國古代“男女授受不親”的理念相同,基督教宣揚的兩性倫理道德的核心就是禁欲主義,然而在中世紀晚期,這種“道德偽善、壓制個性、反對自由”的思想遭到了越來越多的抗議與批判。19世紀20年代的美國,“反傳統的知識青年們感受到了現代意識的沖擊,他們認定,古老的清教主義是舊文化的根源,是時代進步的絆腳石”[9]57,甚至“任何阻止自我表現或妨礙充分享受的傳統、法律或規則都應該被打破并廢止。”[10]55因此,一切道德標準都松弛了,作為這個消費社會的“頭等大事”,性欲的閘門被打開,“幾個世紀及清教傳統標志的羞澀、廉恥或犯罪感對它不再具有影響力”[11]160,那是充斥著性、酒精、毒品和變態的美國,一切都籠罩在爵士樂強烈的光霧里。
小說中最變態的無外乎沃倫與十五歲的女兒妮科爾罪證確鑿的亂倫罪,然而出于對這一事件的深刻印象總會引發人們對此類關系的懷疑,即中年男子與未成年女孩的關系,類似案例隨處可見,幾乎構成了“亂倫主題”。如小說中反復提及的使羅斯瑪麗一舉成名的著名影片《老爸的女兒》,迪克的觀后感是:影片結尾處羅斯瑪麗與父親團聚的鏡頭表現得戀父情結太過明顯。由此可見影片的風靡代表著社會上人們普遍不道德的心理狀態。迪克雖對此有所警覺,但卻依然陷入這種不倫之戀。如迪克與妮科爾初次相見時,彼時迪克28歲,妮科爾16歲,“她的青春和美麗深深打動了迪克。她粲然一笑,那是一種動人的、孩子般的微笑,不由得使人想起所有逝去的青春。”[4]161
這種“戀童”心理在他與羅斯瑪麗的婚外情中就表現得更明顯了,迪克34,羅斯瑪麗17,“她的身體發育微妙地徘徊在孩提時代的邊緣——她差不多長大成人了,但身上仍有那股子稚嫩。”[4]4當羅斯瑪麗跟他表白時,迪克起初慈父般地拒絕道:“晚安,孩子,這是很可恥的事,讓我們把它忘掉吧。”[4]76而當他聽到科利斯談及羅斯瑪麗與一個紐黑文小伙子在火車上的風流韻事后便開始時常神經反射般地產生性幻想:“我放下窗簾你介意嗎?”[4]103最終,三年后,他們成功地“放下了窗簾”,結果迪克發現他并不愛羅斯瑪麗,羅斯瑪麗也不愛他,他和羅斯瑪麗在一起只是放縱自己。他怨恨沃倫一家,也討厭那些虛與委蛇的朋友:“我已經白白浪費了8年時間來教這些闊佬體面做人的起碼知識,不過我還不算全完,我手里還有很多張王牌沒有甩出去。”[4]239他對美麗的女人是見一個愛一個。當妮科爾錯怪他勾引一個病人15歲的女兒時,他產生了一種內疚的感覺。當他和出租車司機打架被帶到審訊室時,一群人誤以為他是奸殺5歲小女孩的罪犯并向他發出噓聲,他稍后叫嚷道:“我要發表講話,這也許是我干的——”[4]278在小說的后半部分,妮科爾還注意到迪克對孩子不大自然的興趣。菲茨杰拉德試圖用原本扮演道德良心角色的迪克·戴弗的極端墮落(鑒于倫理禁忌)象征著歐美國家人們從自尊、自律的生活轉向放縱、放蕩的生活。
這種道德墮落的轉變也同樣發生在妮科爾身上。受到重創的妮科爾一度生活在自責、自卑的情緒中,她的創傷能否被治愈有賴于能否獲得新的倫理身份,使她能夠忘卻傷痛,重構自我。她愛上了給予她溫暖的、帥氣的迪克(也許摻雜著某種對父親的“移情現象”),迪克察覺后曾試圖逃避她,但在追求迪克的過程中,精神分裂的妮科爾卻神奇地表現出很深的心機,她就像荷馬詩句里“詭計多端的塞浦路斯女兒”“巧妙地盜走了聰明人的智慧/不論他是多么小心謹慎”。當他們在阿爾卑斯山最終定情時,這邊是:“迪克真感謝上蒼給了他一個存在,哪怕這只是她濕潤的眼睛中的一個反映也好。”[4]185而另一邊:“妮科爾是成功在握,自制而冷靜,我得到了他,他是我的。”[4]185“突然,湖對面暗紅色的山坡上,傳來一陣轟響,人們正用大炮在轟擊醞釀冰雹的云塊,好把它們驅散。”[4]185大炮聲擊破夢幻,標志著迪克幸福的結束。
婚后,迪克對妮科爾悉心照料,他們的愛使她逐漸忘卻傷痛,重構自我。但妮科爾對迪克過分的依賴卻使迪克疲憊不堪:“最近妮科爾把我整垮了——我要是一天能睡上兩小時,那都是奇跡。”[4]231后來,迪克的生命力似乎逐漸轉移到了妮科爾身上,此種跡象從克特與丈夫弗朗茲的談話中似乎可以得到印證,克特評論道:“妮科爾沒有生病”,而是“把她的病作為一種有力的武器罷了,她應該去演電影”[4]284,而且,“迪克已經成了酒鬼,他已經不是個正經人了。”[4]286再后來,妮科爾越來越不依賴迪克了:“我幾乎是個完全的人了,現在我不就脫離他獨自在這兒了嗎。”[4]341而迪克也似乎抱定繼續沉溺的決心了:“以前他總是想著創造東西——現在似乎只想破壞。”[4]316
健康的妮科爾想要擺脫頹廢的迪克獲得新的倫理身份:“她并不需要永遠和他在思想上保持一致,那她就必須再成為別的什么。”[4]327她想起一直暗戀她的湯米:“別的女人不也有情人嗎——為什么我不能有?”[4]327“整個夏天,她看到多少人受到誘惑為所欲為并未受到懲罰,于是得到鼓舞。”[4]344終于,她和她的情人都得償所愿。此時,賓館外面“一聲巨響撕裂了空氣:啪——砰!是戰艦在召喚美國船員回船”[4]351,船員們紛紛與他們的情人(妓女)告別。于是,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一個女子在湯米和妮科爾所在賓館的陽臺上與情人揮別,她叫喊著扯下自己粉紅色的三角內褲當旗子揮動,“這時,船尾升起了星條旗,與這面粉紅色的旗幟爭相媲美。”[4]351此處的諷刺與象征是不言而喻的,菲茨杰拉德清楚地意識到這個時代的不負責任和道德墮落,毫不留情地揭示了其災難性的后果,那就是湯米和妮科爾之流會使美國變成什么樣子。妮科爾回到家來到迪克的工作室,迪克冷冷地看了看她:“我剛才在想我對你的看法——”“為什么不在你的書上添上這個新的分類呢?”“我想到了——就把它叫作精神變態和神經官能癥病外談'——”“我不是到這兒來讓人討厭的。”“那你為何要來,妮科爾?我無法為你再做什么。我正在想辦法救自己。”[4]356在菲茨杰拉德看來,那些縱情聲色的人們都患有難以治愈的疾病,但對美國這個淫欲熾盛的流行病,精神科專家也束手無策。
五、結語
菲茨杰拉德對小說的結尾處理頗耐人尋味:迪克大抵是搬了幾次家,“不是在這個小鎮,就是在那個小鎮”[4]372上掛牌當普通醫生,回到了最初那種騎車的簡約生活,“給人留下了風度翩翩的印象”并有“很多女性崇拜者”[4]372;學術上也有所建樹,如:“發表醫學課題的重要論文”或在“大眾衛生保健會議上就成癮性毒品問題作精彩的報告”[4]372,種種可喜的跡象似乎呼應了前文迪克試圖自救的說法。但菲茨杰拉德筆鋒忽轉又可疑地寫道:“后來和一個雜貨店姑娘混到了一起,并且還卷入了一起醫學訴訟”,于是又換了個“很小很小的小鎮”[4]372。這個結局與其說是“夜色溫柔”,不如說是“夜色朦朧”。這種模棱兩可的結局使學者們面面相覷,不明所以,但大都認同“沉淪”這一主題:“小說以戴弗醫生的迅速沉淪結束——他的沉淪并非沒有原因,而是有著太多的原因,其中沒有一個是主導原因。”[1]29但好的文學作品往往主題都不是單一的,是要留給讀者更廣闊的闡釋空間的,菲茨杰拉德這種余音繞梁的處理手法反而更加富有藝術魅力并激發著人們不斷揣摩研究的熱情。
如同《了不起的蓋茨比》中,蓋茨比的悲劇使尼克看透了這個“鬼魅般的城市”,于是尼克最終放棄了在紐約學做證券交易的計劃,決定回到中西部的家鄉去,遠離這個浮華的商業社會,迪克的隱退或許也是一種逃離,而逃離并不意味著就是失敗,這是迪克同時也是作者在面對倫理兩難時所做出的倫理選擇。在那個時代普遍的道德敗壞中,逃離是“在經歷倫理無序之后,向原有倫理秩序的回歸。”使“人性因子,即人類的理性意志,在與獸性因子的對抗中重新占據主導地位,人也因此回歸為真正的倫理意義上的‘人’。”[12]68-72(當然,如果不懂得反省自身的沉淪,而一味的指責外部環境的責任,那么逃離到達的終點只能是歇斯底里和迷惘的氣氛。)由此可見,迪克看似悲劇式的結局在倫理意義上并不悲哀。也許,當迪克歸隱前站在沙灘高高的階梯上俯視海灘上的蕓蕓眾生并默默在胸前手畫十字祈求上帝保佑這片海灘時,便已決意去實現梭羅在《自然》中所描繪的愿景:
啊,自然!
我寧愿生活在荒野叢林,
做你的孩子,做你的學生,
也不愿去做人間的皇帝,
或不折不扣的憂患的奴隸;
我愿享有你黎明的剎那,
放棄城市中寂寞的年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