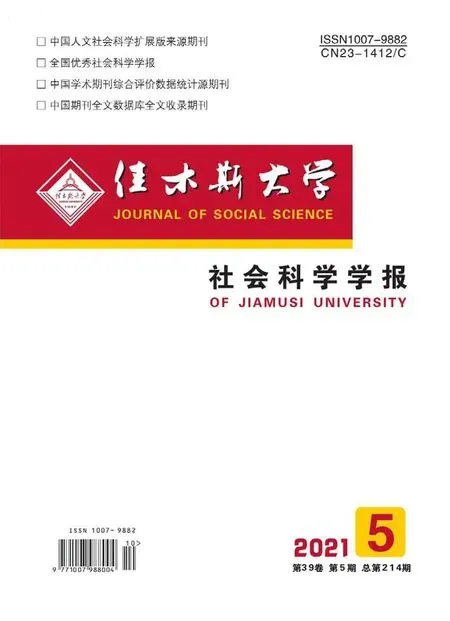中國古典詩歌中“生命情懷”的內涵解讀與外化思考 *
賈 婷
(亳州職業技術學院,安徽 亳州 236800)
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生命體的留存與延續需要遵循一定規則,在規則之上的理性探索與感性體驗,則是生命的額外賦能。作為高級生命形態,人類在自主生存與精神實現的過程中,往往會產生區別于其他生命形態的感悟與反思,并以各種兼具記敘價值與藝術價值的方式進行表述,詩歌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中國經過數千年源遠流長的發展,無數生命體在傳承中衍生出獨特的精神需求,對生命本身的感知與研習也成為諸多詩歌創作的靈感來源,因此,古典詩歌中以“生命情懷”為主題的作品多不勝數,自成一派,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大代表性元素[1]。古典詩歌中,關于“生命情懷”的探討與歸納并非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人類意志的變化而出現一定轉移,在后期呈現明顯的外化特征,與生命體物質精神需求的變遷基本類同。
一、關于“生命情懷”的人文體現
人類在產生生命意識后,會自覺將其間生成的理性思索與感知體驗轉化為一套獨特的情感體系,用于佐證行為本能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對自我生存價值的思索,已成為人類區別于其他生命體的標志性要素,因此衍生出的生命情懷也屬于人類特有的一種精神現象,天然具有高度人文性。從精神現象的角度來看,“生命情懷”的生成是人類普遍意義上的共性,但因文明序列、文化背景的不同,在形態與內涵的傳達上又各有差異[2]。譬如,中西方在迥異的社會場域、歷史地位等環境的演變中,探索人文精神領域的立足點有著天然區別,雖同樣具備自我省察的生命意識,但對于如何表達與體現各有著內核與思路。哲學家牟宗三曾對中西方人文精神文化特征做出如下區分:中國文化的著眼點集中于“生命”;西方文化的著眼點則集中于“自然”或“外在的對象”,這是區分兩者的領導線索。由此可悉,探索“生命”本質自古以來便是中國人文精神的重要內核,是歷代人民建立自我心靈溝通關系的普遍出發點。
而要細論具體的中國人文精神與生命情懷,便需要追溯到自然環境、生活方式、物質水平、地域文化等歷史淵源。錢穆先生也曾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指出,中國文化自形成起,便是在復雜而廣闊的領域上展開,且各個區域間相互獨立隔離,又借著小水系、大水系相互銜接,形成區別于其他國家的農業文明與物質生活方式。也正因如此,“實用理性”在中國古代人文精神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著歷史的必然性。思想家李澤厚較早用“實用理性”來概括中國人文精神本質,認為這一概念構成了儒學甚至總的文化心理中的民族特征,即重實用輕思辨、重理性反盲從、重平衡輕欲望的心理結構,強調以積極進取的生活態度來獲取物質及精神需求[3]。本質上,關于“實用理性”的論點與牟宗三先生對中國文化內核的揭示存在共通之處,如中國文化關注生命的走向與精神的歸宿,承認理性的態度與感性的認知可處于共生共存地位。基于這類基本論調,“生命情懷”始終是中國人文精神的重點傾向,也因此成為歷史文學作品中的宏大命題,被人以各種形式拓印在中國古典文化發展史上。
偉大哲人孔子兩千余年前發出“逝者如斯,不舍晝夜”這一喟嘆,意指時光如滔滔河水般流逝,不因白天或黑夜而停留,再聯系到人的生命在時光長河中雖微弱而短暫,但也因自我主宰而產生意義。至后期,諸多思想家、哲學家在孔子的理論學說中總結出具有實用理性的生命意識,并對其中人文內涵做出總結:首先,人在生命歷程中擁有著絕對的主宰權,不受冥冥之中的其他力量所驅使;同時,人的生命既然有時限,就更應在有限的時間內把握自我實現的諸多可能,虛擲光陰將會使寶貴的生命流失原有的意義。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支柱,在主流行為體系的構建中發揮了重要導向作用,且在后期實踐總結中得以不斷完善、總結、升華,以動態發展性被賦予了長久的生命力,也因此成為“生命情懷”表達的理論載體之一。一定程度上,儒家理論學說中關于生命意識的論述代表了中國古典文化中的人文傾向,也是民族性心理結構的一種真實反映,屬于諸多個體在探究人文精神本質時的起始點[4]。
總的來說,中國歷史堆積而成的人文精神既離不開物質基礎,包含農業文明、工業技術等,也離不開深刻清醒的實用理性,只有在厘清這一本質特征的基礎上,對自我生存的方式進行反思,對生命情懷進行探討,才稱得上自然且富有意義。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中,透過生命意識傳遞出的人文精神理念,一方面是廣泛化感性體驗的提煉,另一方面也是理性化經驗成果的總結,也就是說,它不僅依托于個體生命的生理性存在與完整,同時也看重個體生命在群體環境中呈現出的價值意義,在強調主體性品格的基礎上,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關系,這與中國文化土壤中對“生命”的尊重有著深度關聯。通過回顧中國歷代古典文學作品可知,對生命情懷及其人文精神的解讀與剖析體現在方方面面,且在強烈的尊重意味烘托下,這種表述過程被烙上鮮明的民族印記,以生動而鮮明的藝術特征而著稱于世界,成為中華傳統文化區別于其他文化的典型標志。
二、中國古典詩歌中“生命情懷”的內涵解讀及體現
對于“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實現生命本質的永恒”這一問題,自古以來便眾說紛紜,具體而談,即是“人如何達到死而不朽的境界?”。普世觀點中,財富、權柄的延續與傳承只能被稱為“世祿”,由于缺乏精神層面意義上的高潔情懷,而不能被稱為“不朽”,只有建立在立德、立功以及立言等精神境界上的留存印記,才是真正意義上個體的“不朽”,這也正是個體生命情懷在群體環境下的價值體現。這種價值觀點也在很大程度上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創作有著直觀影響,甚至被直接注入創作脈絡當中,成為藝術表達的補充[5]。
人類產生生命意識后,隨即總結出“生命會逐漸消逝”這一自然規律,而后衍生的情感、情緒、情懷也都建立在這一客觀前提之下,對草木榮枯、陰晴圓缺等物象變遷的觀察視角也更為廣闊而悠長。古代著名詩人屈原曾以“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等句感嘆生命的易逝,但由這種感嘆延伸而來的,并非是屈從于客觀現實的無謂憂傷,而是以另一種形式升華生命價值的決心,如“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而不立”中傳遞的分秒必爭、積極進取的迫切感。所謂“修名”,指通過高潔品格來超脫肉體生命限制,構筑精神層面上的長青生命,擺脫虛浮之名的桎梏。現實中,屈原選擇犧牲自然生命來成全永垂不朽的人格理想,并以詩句昭其心志:“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這種“立德至上”的生命情懷在本質上與“不朽”的理想是共通而統一的,是生命意識經過藝術渲染后,在詩歌文學作品中的立體直觀呈現。
關于“立德”的探討與論述在古典詩歌文學史上出現概率頗高,尤其在屈原等領軍式人物出現后,后世對于生命情懷的“立德”表述上升到了新的藝術化層次。如南宋著名詩人陸游曾在垂垂老去之際,留下“汝雖老將死,更勉未死間。”等詩句用于自勉;文天祥也曾在戰敗期間以寧死不屈的意志寫下聞名于世的《過零丁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有明代政治家于謙留下的千古名句:“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這些寫于生命彌留之際的詩篇,無一不傳達出作者試圖通過“立德”來達到“雖死猶生”境界的意念,在這樣的“忘我”境界中,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不再需要通過肉體的留存而存續,生命的自然長度也因精神的不朽得以延伸,實現特定意義上的永存[6]。縱觀中國古典詩歌長河,對于“立德”的定義也并非是單一性,有人認為投身于家國事業屬于立德;也有人認為堅持自身高潔品行即是立德。總之,如何算是“立德”并不能一概而論,從共性上看,可以歸納為人格高尚的、具有奉獻性的生命特質,這種宏大情懷也通過詩句鐫刻在世人心中。
誠然,“立德”作為實現生命不朽不息的最高層次,被無數人所向往、追尋,但正是由于它的至高無上,在現實中通常可望而不可即,并不能成為大部分人群提升生命價值的路徑。因此,更多人轉而求其次,嘗試通過“立功”來升華精神境界,讓后世銘記自己的功績,來實現留名于史的生命存續意義。譬如,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曹操便是一位重功績輕德性的代表性人物,即便曾發出“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生命體驗喟嘆,也是為了傳達“征求賢才,建功立業”的政治抱負;同時在《龜雖壽》一詩中留下“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等句,旨在弘揚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的進取意識。同樣,“立功”的定義也因個體的不同而呈現出一定差異,有人認為立功的本質在于出將入相,建立政績;有人認為達成人生理想、留下值得記錄的功績即算立功,而功績的類型并非是特定的,可以是政治成就,也可以是功名成就、藝術成就等。歷代詩人在對“立功”的追求表述上,也紛紛以不同的著墨點呈現出不同的個人風格,如以豪放格調著稱的李白曾在《行路難》中如此表達志向:“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在強調宏圖抱負的同時,以酣暢淋漓的詠調,讓讀者直觀感受到其磅礴有力的生命情懷,形成直觀而富有沖擊力的共情效果。
除去“立德”與“立功”層面的生命價值追求外,“立言”也被視作一種探索永恒的不朽實現形式。所謂“立言”,即通過廣義或狹義層面的文章及言論,來建立一種獨立且具有應用價值的理論語境,使之在流傳、延續的過程中實現立言者的精神傳承。從古典詩歌字斟句酌的特性中可以窺見,古代文人精益求精的作詩態度本質上便是對“立言”的追求體現,魏文帝曹丕便曾在《典論論文》中指出:“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鼓勵文人踴躍創作,體現國家文化興盛。在諸多廣為人知的古典詩篇中,可以窺見創作者為家、為國、為己或為他人而試圖傳遞出思想學說,社會世俗的本質也使得這種“立言”過程呈現多元化本質,而真正具有“立言”價值的作品,也經過時間的篩選流傳至今,成為構建當下主流文化體系的基石。
無論是立德、立功還是立言,均是彰顯生命情懷、升華生命價值、構筑不朽靈魂的直接通路,真正達到超脫生死、心境曠達境界的,在歷史上也不乏其人,及至現代,人們借助詩歌這一載體得以窺見一角,再通過解讀其中內涵,汲取關于生命意識的理論養分,這也是古代詩人用“生命情懷”詩篇惠及后人的現實體現。而要從達觀角度來闡釋古代詩人的生命情懷,便不得不提及東晉田園詩人陶淵明,其所作就的詩篇中,傳達出榮辱不驚、順應自然、超脫生死等宏大生命格局,極大地影響著后人,諸如“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等詩句,長久地留芳于后世,構成中國古典詩歌中的獨特景觀。正是在這些情懷高遠的詩歌作品影響下,后人對生命本質的研究與論述有了深厚的思想基石,很多具有現實意義的外化思考也正是來源于此。
三、對中國古典詩歌中“生命情懷”的外化思考
“生命情懷”作為中國古典詩歌史上恒久不變的主題,在呈現過程中可能生成不同形態的外化現象。所謂“外化”,即指在正面表達、傳遞生命情懷感悟的基礎上,借助側面渲染的手法,或含蓄辭藻的包裝,使詩篇以某種特定風格形態存在。縱觀古典詩歌中“生命情懷”的外化現象,可以窺見其中多元性、互通性特征,這與人們對生命現象的認知、敬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現通過簡要歸類,列舉部分關于“生命情懷”的代表性詩歌外化形式略作闡釋。
第一類,懷古詩。歷史朝代更迭過程中,所衍生的文化氛圍、人文土壤因時代的不同各有特質,而文人墨客也慣于通過回顧歷史來總結新的理性精神與價值經驗,這一過程屬于歷史意識的體現,而歷史意識又正是生命情懷的延伸。懷古詩作為詩人們緬懷古人、憑吊古跡的詩歌載體,往往側重于關注人類以群體形式存在的價值意義,并從中提煉出用于慰藉內心的精神底蘊。正如初唐詩人陳子昂在《登幽州臺歌》中所寫:“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講述了詩人在壓抑的心境下登臨于曾象征燕國標志的幽州臺上,極目遠眺,由史及境,生出懷才不遇的悲愴感。但究其根本,詩中傳達的內核又遠非一己榮辱得失之感,而是包含生命體驗、與古人間的精神交融等深層次認知,是通過文學作品破除時間、空間桎梏的生命情懷外化體現。除去因際遇而與古文化產生的共鳴外,還有許多古典詩歌作品從對“物換星移”的感悟出發,透過現下景象寄懷逝去時光,諸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等膾炙人口的名句,便傳達了對物是人非、世事無常的感悟,從“燕子”這一元素切入,講述王公貴族的權勢隨著時間轉移而消逝,曾寄居于堂前的燕子已在尋常百姓人家筑得新巢。無論何種主題的懷古詩,都繞不開對生命、歷史的省察,這也正是人類與生命建立溝通連接的重要文學表達形式。
第二類,飲酒詩。從古至今,中國詩歌文學的創作就常與酒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譬如被譽為“詩仙”的李白便有大量聞名于世的詩歌作品作于酒后,一度被傳為佳話。而詩人對于酒文化的追尋,從根本上看,也與生命情懷關聯甚遠,一方面來源于人對已知流逝時光的悵惘或反思,另一方面則來源于人對未知生活的惶恐或期盼。著名文人孔融曾在詩中稱:“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飲酒作樂對當下人們疏解自我的重要意義。及至文晉南北朝時期,因社會動蕩變遷等因素影響,飲酒之風更為盛行,尤其在詩人群體中,借酒吟詩無疑已成為一種時興的、主流的創作方式,尤以“竹林七賢”等代表性人物為主,如嵇康曾在詩中提出:“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隨著飲酒詩作品的不斷出現,這一題材開始自成一派,成為詩人發出生命情懷詠嘆的外化形式之一。大部分飲酒詩作品中,對詩人生活態度的呈現屬于明顯表征的一種,或以傾訴衷腸為主旨,或以超脫曠達為基調,無法一一囊括,如歸隱田居的陶淵明以“既醉之后,輒題數句自娛。”表達隨遇而安的心境,將飲酒作為生命中的別樣體驗,借之體悟生命“真味”;率性浪漫的李白在名詩《將進酒》中通過“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醒。”一句,抒發人生抱負難以施展的愁苦,但又在愁苦中注入激蕩而磅礴的灑脫之意,使得該詩作在看似矛盾的感情中達成微妙的平衡,流傳為千古名篇。
第三類,山水詩。古典詩歌中的“生命情懷”表達在外化的過程中,除常規意義上的人類生命外,諸多與精神生命相關的元素也被囊括在內,譬如“山水自然”等。自古以來,“天人合一”便是中國哲學體系中的重要觀點,即人類應當順應自然規律,與自然中的萬物和諧相處,將一草一木視為與生命體驗息息相通的細節。也正因如此,對于山水自然的描繪與勾勒,成為詩歌主題中的獨具一格的類別,無論是主觀性還是客觀性的“生命情懷”,都能夠借助山水景象進行深層表述。歷史上較長一段時間內,山水詩大多以自然景色描寫或借景抒情為主題,但直至南朝晉宋之際才算得上形成成熟體系。當時的代表性詩人劉勰曾在詩中以“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等句將自己的生命體驗寄托在內,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山水詩的勃興帶來了理論基礎。進入盛唐時期之后,山水詩的藝術化表達更是邁入一個全新的境界,基本組成了作品類別豐富的詩歌流派,其中重要代表性詩人王維在《鹿柴》《鳥鳴澗》《竹里館》等作品中,將其對光影效果的捕捉天賦融于其中,用寥寥數筆建構出獨立的自然空間,傳達淡泊悠長的人文意境,于無形間描繪生命的具象化形態,古典詩歌“生命情懷”的外化魅力也就此得以呈現。
四、結語
綜上所述,中國文學藝術發展史上,對“生命情懷”的呈現是永恒的主題之一,古典詩歌更是以簡明含蓄的語言與深厚磅礴的底蘊,成為重要的表述載體,與這一主題緊緊串聯。在解讀古典詩歌內涵及思考其外化現象的同時,人們更需要探析的是藝術與生命相融的本質,并以此為契機,在生命長河中不斷進行自我叩問與反思,為詩歌文學的長久性延續與傳承提供豐沃的文化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