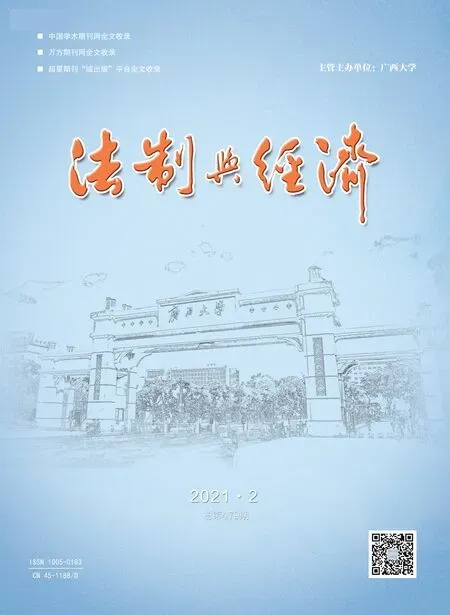我國海洋災害行政應急執法問題研究
陳 瑜,胡琳嘉
近年來,我國各類突發性海洋災害不僅給沿海地區人民群眾帶來嚴重的財產損失,也對沿海地區人民群眾生命安全造成嚴重威脅。海洋災害是指海洋自然環境發生異常或者激烈變化,由此引發的海上或者海岸災害。我國海洋災害主要包括風暴潮、海嘯、海冰、赤潮、熱帶氣旋、溫帶氣旋等。2019年,我國各類海洋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117.03億元,直接導致22人死亡(含失蹤)[1]。為了應對海洋災害帶來的嚴重后果,最大限度減少國家和社會損失,我國不斷完善與改進應急管理體系。2005年,國務院第79次常務會議通過的《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是指導全國突發公共事件應對工作的總綱,在此框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雖然陸續出臺了有關海洋災害應急管理預案,并且在應急預案編制、應急處置、應急保障、應急救援等方面作出了具體規定,但是,有關行政應急執法方面的相關法律文件仍然不夠明確,對政府行政應急限制內容和遵守程序也未作明確闡述。海洋災害行政應急執法相關法律法規同樣對行政執法主體、執法程序和執法監督等常規法律行為沒有作出具體的法律規定。行政應急是行政機關依據憲法及有關法律規范予以應急處置的行政行為[2],行政應急執法則是行政機關為了控制突發公共事件和消除社會危害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3]。當海洋災害發生時,政府將啟動行政應急預案展開救援活動,但政府行政應急往往遵循行政效率原則,這可能會導致行政客體的合法利益被政府行政應急權侵害,使政府行政應急權的運用難以得到有效監督和約束。
一、我國海洋災害行政應急執法現狀
(一)現行行政應急執法法律規定
行政應急執法是海洋災害來襲時,一種非常態的、復雜多樣的、特殊的行政行為。行政應急行為也是具有法律效果的行政行為,需要受到法律的約束。但是當前我國行政應急執法方面的法律規定尚不完善,有關海洋災害行政應急行為的約束細化只規定在應急預案中,并不是系統的法律規范體系,從而導致在海洋災害減災實踐中,行政應急執法工作無法可依。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主要側重于國家正常狀態下的憲政運行,對于非常態下的國家權力行使及行政應急執法并無具體規定,有間接關系的是2004年修正《憲法》時,將“戒嚴”修改為“緊急狀態”。關于海洋災害行政應急執法的法律規定,《憲法》僅提及海洋環境保護,比如第9條第2款“國家保障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保護珍貴的動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自然資源”;第26條“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由此可見,《憲法》并無直接規定突發事件來臨時國家及政府應該實施的具體行政應急執法行為。
目前,我國行政應急執法主要依據單項行政應急立法和行政應急預案,大部分防災減災單項行政應急立法規定依據的是2007年11月1日施行的《突發事件應對法》。僅一部行政應急立法難以構成完善的行政應急法律體系,已有的單項行政應急立法如《海洋環境保護法》《風暴潮、海浪、海嘯和海冰災害應急預案》《赤潮災害應急預案》,仍存在缺乏協調性和統一性的問題[4]。
(二)行政應急預案執法分析
在單項行政應急立法之下,各級地方政府以《突發事件應對法》為總綱并細化行政應急規定,紛紛出臺了適用于各自省份的行政應急預案。行政應急預案屬于行政工作計劃范疇,不能在已有的法律授權外設立新的權利義務。和單項行政應急立法相似,行政應急預案在執法主體、執法過程違法責任承擔以及執法監督方面也沒有作出明確且具體的規定(如表1所示)。在執法主體方面,各級政府在應對海洋災害時以各級行政機關為執法主體的主導者;在執法責任承擔方面,由政府直接承擔責任;在行政執法監督方面,《突發事件應對法》第63條規定由上級行政機關或者監察機關責令改正。其余都是籠統規定為給予行政處罰,并未說明由誰實施監督職能。

表1 我國行政應急預案的執法法律規定
由此可以看出,我國行政應急預案關于執法方面的規定存在一些問題:第一,應急預案缺少責任追究內容。一般而言,海洋災害發生后的救援會因一些執法不當行為產生損害,雖然應急預案有追究違法責任人員的規定,但內容只是原則性描述并無細化,缺少對執法不當時具體責任承擔主體的規定。第二,應急預案缺乏監督。在突發海洋災害的非常態狀態下,政府所行使的行政應急權比正常狀態下的行政權力要大,但相應的監督機制沒有健全,使得行政應急執法很難受到約束與監督。
二、部分國家行政應急執法現狀
美國國土地勢西高東低,遭受的海洋災害不計其數。1990年,加爾維斯敦市遭受颶風與洪水襲擊,導致該市大部分建筑毀于一旦。2006年,卡特里娜颶風導致1833人喪生,造成約1250億美元的損失。2010年,美國墨西哥灣原油泄漏事件被評為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生態災難。正是因為美國自然災害頻發,因此美國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較完備的自然災害防治法律體系及應急機制。美國屬于聯邦制國家,其權力分屬于聯邦政府及各州政府。因此,在自然災害管理及應急處置方面,美國采取從聯邦到州再到地方的分級管理,形成比較高效的應急指揮機制。聯邦政府應急管理有法律依據,由《減災和緊急救助法》授權,同時按照《聯邦響應計劃》部署開展災害及突發事件管理[5]。美國《憲法》也對緊急狀況的應急授權作出明確規定,主要包括:當緊急情況發生時,國會可授權(聯邦)政府指揮各州政府;當各州遭遇緊急情況時,無需等待國會審議通過可立即進入作戰或緊急狀態[6]。除此之外,美國制定多項單行法規管理約束行政應急執法。同時,美國明確規定應急管理部門從上至下分級管理,每一級都有相應的機構處理問題,還明確了行政主體由法律授權,這就使政府在緊急狀況發生時行使權力的合法性有了依據。另外,各項法律法規對于行政應急執法主體的職權作了詳細規定,使得各執法主體之間配合順暢,在高效有序的情況下完成執法行為,符合行政應急的效率規定。
日本四面臨海,屬于島國,常年遭受海洋災害侵害,因此也逐漸摸索出適合自己的應急管理體系,于1947年出臺《災害救助法》,1961年出臺《災害對策應對法》。日本各地方設有自己的防災委員會組織協調應急救援工作,地方發生突發事件時,一般由地方行政首長指揮協調行政應急救援。日本注重行政應急程序的法治化,應急體制對權力分配、應急程序內容、時間安排分別有明確的規定。日本在1967年制定的《公害對策基本法》和1976年制定的《海洋污染和海上災害防治法》,一部屬于應對突發事件的基本法,一部屬于應對突發海洋環境事件的專門法。這兩部法律都對海洋環境污染突發事件應急處理的啟動程序、權限、責任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比如地震之后2個小時內防衛廳(注:現為防衛省)長集結各局局長舉行緊急會議,研究制定應急對策等[7]。同時,日本對于突發環境事件中受到損害的公民,賦予了他們行政救濟權[8]。
英國位于歐洲大陸西北面的不列顛群島,同樣也易受海洋災害侵害。英國2004年發布的《國內緊急狀態法案》對行政應急監督進行了明確規定。英國行政應急監督方式分為兩種,一種是立法監督,一種是司法監督。立法監督是通過對緊急狀態規章的議會審查來確定緊急狀態規章的有效性。根據《國內緊急狀態法案》第27節可知,英國采取的立法監督模式是事后監督,主要是賦予議會審查的權力,于緊急條例頒布后生效,但是應盡快將條例提交議會,如果議會通過決議認為緊急條例應停止生效,則緊急條例停止生效。司法監督是設立特殊法庭,特殊法庭與緊急狀態中的公民權利問題直接相關[9]。司法監督涉及公民權利問題時應咨詢裁判委員會,否則不應當制定設立特殊法庭的緊急狀態規章。對于涉及公民權利的監督,英國采取的是事前監督模式,英國政府在面對突發事件時放手相關機構作出行政行為,但對于涉及公民權利的行為卻又堅持事先審查,避免對公民權利造成損害,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權利。
雖然有新聞報道對相關國家的應對措施效果有各種批評聲音,但還是可以看出發達國家應對海洋災害時已形成一套比較成熟的應對體系。我國可以借鑒美國的常設性應急主體機制,這種常設性組織每經歷一次突發海洋災害事件就能積累一次經驗;在監督方面,英國的司法監督與立法監督保障了公民的訴訟權利,同時議會又進行了事前監督,雙管齊下減少了濫用權力的可能性。因此,要結合我國國情,提取對我國行政應急執法有利的內容,以構建一套更加完善的行政應急執法體系。
三、完善我國海洋災害行政應急執法的建議
(一)完善立法體系,建立綜合性應急機構
一方面,可通過修訂《突發事件應對法》來解決法律與應急預案之間協調不暢的問題。在應對海洋災害時,應急預案成為執行根據,可影響《突發事件應對法》的適用力。應急預案只是具有明顯的行政應用性特點,卻難以完全替代應急基本法的作用[10]。修訂法律可解決二者之間的沖突,以確保今后在進行海洋災害行政應急執法時,執法主體擁有明確的法律授權。另一方面,進一步明晰除政府之外的相關應急主體義務,通過細化相關規定使相關應急主體能夠承擔起對海洋災害的責任。
(二)明確責任承擔主體,培訓相關執法人員
要明確承擔違法責任的主體,就要對已有責任承擔主體的法律規定進行司法解釋,細化責任承擔主體。建立“誰侵權,誰行為,誰承擔”的責任承擔模式,當出現共同侵權行為時,有明確的依據規定共同責任該如何承擔。解釋內容要結合實務經驗,采取列舉式加概括式相結合的方法,確立執法不當時具體的責任承擔主體。
要對執法人員進行培訓,向執法人員貫徹法治理念,樹立其法治觀念,提升其法治素養,以此促進執法的規范化。
(三)構建內外監督制度,創設賠償機制
可以建立內外監督機制,在立法監督、司法監督及內部監督三個方面確立新制度。立法監督方面,在《監察法》中加入針對行使應急行政權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監察;修訂《突發事件應對法》及海洋災害應急預案,明確表述行使行政監督權的機關與組織。司法監督方面,結合應急行政的特點,更改行政訴訟中的證據收集規定,改變以往做法中因證據提取不及時而造成的證據鏈不完整,最后發生難以起訴的情況。創設賠償機制,在實施過限行政行為后,還要擔負民事賠償責任。內部監督方面,實行層級化監督模式,即由中央對地方,上級部門對下級部門的行政活動進行監督[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