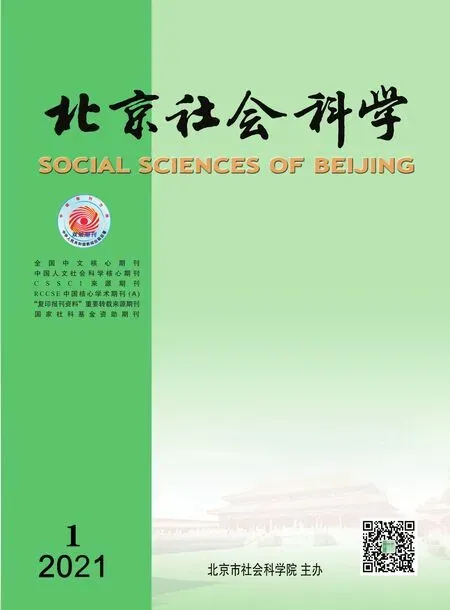姚鼐文章“至境”論的內在意蘊與實現路徑
郭青林
(安慶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安慶 246011)
作為桐城派的開創者,姚鼐的文學觀念在桐城派文論史中的地位向來舉足輕重。在姚鼐有關詩文創作和批評的諸多說法中,有關文章“至境”的表述如“文之至”“文章之至”或“文之至美”等,在不同的篇章中反復出現,是其文論話語中一個較為突出的現象。馬其昶在談其文論時指出:“蓋其學深造自得,故多詣極之言。”[1](P313)姚鼐有關文章“至境”的表述,是其詩文創作經驗的總結,反映了姚鼐對文章最高境界的認識和追求,也體現其力求確立桐城派文章理想以引領后學之意圖。對此,現有研究多有忽略,或有涉及但未作深究,這一表述在姚鼐文論話語中的地位未得到足夠重視。姚鼐所追求的文章“至境”并不是空中樓閣,是有著具體實現路徑的,這對桐城派后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文章“至境”及其判斷標準
姚鼐詩文集中較早有關文章“至境”的表述是在《敦拙堂詩集序》一文中,他說:
夫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為文之至。世之文士,固不敢于文王、周公比,然所求以幾乎文之至者,則有道矣,茍且率意,以覬天之或與之,無是理也。[2](P49)
所謂“文之至”即“至文”,就是說文章已達到“至境”,在這段文字中出現兩次。前一個指出“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就是“文之至”,這是就文章“至境”的判斷標準來說的;后一個說明實現“文之至”是有徑可尋的,但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天,應當重視人力,這是就文章“至境”的實現路徑而言。在姚鼐看來,判斷文章“至境”有兩個指標,一是“道與藝合”,涉及對文章內容與形式、本體與功能的認識;二是“天與人一”,涉及對作者先天稟賦與后天功力的理解。
對于“道與藝合”,姚鼐以為:“夫文技耳,非道也,然古人藉以達道。其后文至而漸與道遠,雖韓退之、歐陽永叔,不免病此,況以下者乎?”[2](P291)這句話有二層意思,一是認為文章在本質上是“技”,而不是“道”,它的功能是“達道”,也就是說文章的使命是為了表達“道”,“道”是文章表現的對象,這是姚鼐對文道關系的基本看法,是“道與藝合”提法的實質。二是著眼于古文創作傳統,認為古人能做到“文與道合”,后世文則“漸與道遠”,即便像韓愈、歐陽修這樣的古文大家,有時都難以做到,說明“文與道合”之不易。在姚鼐的文論語境中,“道”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儒學之義理,即孔孟之“道”;二是指天地自然之節,即老莊之“道”。這里主要指前者,姚鼐強調“道與藝合”,旨在通過“藝”闡明“義理”,使得儒學之義理得以深切著明,這是作文的主要使命。
從后一個含義來看,姚鼐認為文章之所以為貴,是因其“合乎天地自然之節”,[2](P49)而要使文章符合“天地自然之節”,必然在創作上要講究“藝”。因此,所謂“文之至”必然既有“道”方面的要求,又有“藝”方面的要求。“道與藝合”遂成為判斷文章“至境”的重要依據之一。
姚鼐指出:“其貴也,有全乎天者焉,有因人而造乎天者焉。”[2](P49)從創作來看,文章創作既有“全乎天者”,也有“人造乎天者”。前者全靠天工所致,自然化成,這是先天稟賦;后者全憑人力而為,艱難玉成,這是后天努力。這一認識是符合文學史史實的,如陶淵明詩就是“渾然天成”的代表,而謝靈運詩就是“人巧奪天工”的典型,兩者各臻其極,各盡其妙。姚鼐以為“全乎天者”是不可靠的,他說:“且古詩人,有兼《雅》《頌》,備正變,一人之作,屢出而愈美者,必儒者之盛也。野人女子,偶然而言中,雖見錄于圣人,然使更益為之,則無可觀已。后世小才嵬士,天機間發,片言一章之工亦有之,而裒然成集,連牘殊體,累見詭出,閎麗譎變,則非鉅才而深于其法者不能,何也?藝與道合、天與人一故也。”[2](P50)“野人女子”“小才嵬士”有可采之言,一章之工,純粹是“全乎天者”,是不可持續的。而“人造乎天者”,全憑功力也有其不足,姚鼐說道:“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2](P94)作者個人的寫作功力,對創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從創作“至文”的角度說,還是不夠的。因為“至文”是“通乎神明”的,光憑人力是不能實現的,需將“天啟”與“人力”結合起來。他說:“學文之法無他,多讀多為,以待其一日之成就,非可以人力速之也。士茍非有天啟,必不能盡其神妙,然茍人輟其力,則天亦何自而啟之哉!”[3](P79)人若無“天啟”,其文不能“盡其神妙”,即“通乎神明”,但如“輟其力”,“天賦”不能開啟,無法在寫作時發揮作用。姚鼐將“人力”與“天賦”統一起來,強調“人與天一”的重要性,同“道與藝合”一樣,被視為文章“至境”的要件之一。
作為“至境”的要件, “道與藝合”是對文章思想性與形式審美性的整體要求。在姚鼐看來,“道”是文之本,須借助“藝”來實現,“藝”為文之末,為傳達“道”而存在,“道”與“藝”本末相濟,思想性和審美性得到完美契合,進而實現文章之“至境”。這一認識注意到了“藝”在文章活動中的價值,提升了“藝”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將下學之‘藝’和不能入‘道’之‘藝’,升到可以與‘道合’的境界”“突破了傳統儒家特別是程朱理學偏見”,[4](P388)是有其理論貢獻的。“天與人一”則是對主體素養的全面要求。對作者來說,“天賦”不可或缺,但僅憑天賦是不夠的,還要有后天的功力,天賦靠功力開啟,功力靠天賦實現創作上的神妙。這些認識表明姚鼐對“天賦”和“功力”關系的理解具有辯正性,但是,由于他把文章“至境”理解得過于玄虛(“通乎神明”),對“天賦”作用的認識還是略嫌夸大。先天稟賦無奇,但靠后天努力,作品成就不俗在文學史上不乏其人。總的來看,“道與藝合”與“天與人一”分別從作品、作者的角度界定了文章“至境”的標準,體現了姚鼐對文章最高境界的基本認識。
二、文章“至境”的形成要素
從創作的角度看,影響文章“至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這個問題上,姚鼐是從文章之“美”的角度來談的,因為“至文”應當是“至美”的。“言之美”是“文之至”內在之義,不“美”的文章,無論如何都不能算作“文之至”。可見,作為文章“至境”實際上是有質的規定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其一,“當乎理,切乎事”,這是從內容方面作出的具體要求。姚鼐說道:
天下所謂文者,皆人之言,書之紙上者耳。言何以有美惡,當乎理,切乎事者,言之美也。今世士之讀書者,第求為文士,而古人有言曰:“一為文士,則不足觀。”夫靡精神銷日月以求為不足觀之人,不亦惜乎!徒為文而無當乎理與事者,是為不足觀之文耳。[2](P273)
文章是書寫在紙上的“言”,是有“美惡”之別的。判斷文章是“美”是“惡”,有個標準,即看是否“當乎理,切乎事”。所謂“當乎理,切乎事”也就是說文章要和社會生活發生聯系,符合生活實際。姚鼐說:“夫文之道一而已,然在朝廷則言朝廷,在草野則言草野,惟其當之為貴。”[2](P263)作者的身份、地位不同,所知悉的事和理也各異,所寫的文章應當符合他們的身份、地位的實際。在他看來,作者應該寫自己所熟悉的人或事,只有這樣,文章才切合事理,才有價值。那種不從實際出發,勉力著文,這樣的文章是“不足觀”的。這種認識與姚鼐的文章功能觀相關,他說:“夫古人之文,豈第文焉而已。明道義、維風俗以詔世者,君子之志;而辭足以盡其志者,君子之文也。”[2](P89)文章的功能在于“明道義,維風俗”,而要發揮這一作用,就必須“當乎理,切乎事”。而“理”和“事”是與時變化的,因此“當乎理,切乎事”的看法中就隱含著文章與時因革之義。姚鼐雖然沒有直接提出,卻為弟子梅曾亮提出“文章之事,莫大于因時”[5](P38)之說作了理論先導。
其二,義理、考據、文章相結合,這是從文章創作提出的具體要求。他說:“夫文章一事,而其所以為美之道非一端,命意立格,行氣遣辭,理充于中,聲振于外。數者一有不足,則文病矣。”[3]P(115)姚鼐認為文章的“美”體現在不同要素上,如命意、格調、氣脈、遣辭、義理乃至聲色等,在《古文辭類纂》序目中,這些要素又被細化為“文之精”——“神、理、氣、味”和“文之粗”——“格、律、聲、色”[6](P22)兩部分,其中如有一個要素不足,文章就有“病”,也就不美。“文之病”源于“士之病”,“士之病”在于各擅其長、不能避其所短。他指出:“且夫文章、學問一道也,而人才不能無所偏擅,矜考據者每窒于文詞,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士之病是久矣。”[2](P55)“士之病”與其“才”有關,“才”是有其先天缺陷的:“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為貴,而兼之中又有害焉。豈非能盡其天之所與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難得與?”[2](P61)既能盡其才,又不被才的缺陷所縛,這樣的人實在難得。正因為如此,才會存在“矜考據”與“美才藻”者作文之問題。姚鼐說道:
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為考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為文之至美,而反以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過而智昧于所當擇也。[2](P61)
“言理之過者”長于言“義理”,“考證之過者”長于“考證”,共同的問題就是“文章”不行。“義理”“考證”與“文章”屬于學問之三端,姚鼐說:“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茍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茍不善用之,則或至于相害。”[2](P61)而“文章、學問一道也”,寫文章同做學問一樣,必須“義理”“考證”“文章”三者相結合,惟有如此,才能克服才氣之不足而帶來的問題,寫出的文章才有可能成為“文之至美”。
其三,陰陽剛柔相濟,這是從文章風格方面作出的要求。姚鼐說道:
吾嘗以謂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茍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為文章之美。陰陽剛柔,并行而不容偏廢。有其一端而絕亡其一,剛者至于僨強而拂戾,柔者至于頹廢而閹幽,則必無與于文者矣。然古君子稱為文章之至,雖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無所偏優于其間,其何故哉?天地之道,協合以為體,而時發奇出以為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尚陽而下陰,伸剛而絀柔,故人得之亦然。[2](P48)
姚鼐認為“天地”是文章本原,故文章創作要符合天地運行之道。陰與陽、剛與柔相摩相蕩,往復變化是天地運行規律之體現,文章創作自然要處理好它們之間的關系,不可偏廢,這是成為“文章之美”的要件。姚鼐還以為,“文章之至,雖兼二者之用”,但因文章寫作要遵循天地之道,而天地之道“尚陽而下陰,伸剛而絀柔”,所以從文章之美來看,陽剛之美要貴于陰柔之美。
姚鼐從文章之美的角度詮釋了影響文章“至境”的諸多因素,歸納起來,即內容上是否“當乎理,切乎事”;創作上能否做到“義理”“考證”“辭章”相濟;風格上是否具備陰陽剛柔之美。這三個方面凝練了姚鼐主要的文章理論,是桐城派文學思想的核心內容和理論生長點,并為桐城派后學所詮釋、發揮或自糾,使得桐城派文學理論得到進一步豐富和完善。
三、文章“至境”的實現路徑
“至文”通乎“神明”,表面上看,似乎是玄妙而不可及的。姚鼐卻認為:“求乎文之至,則有道矣。”認為實現“文之至”是有門徑的,只是不能把希望全部寄于天,應當發揮人力的作用,非下苦功不可。他說:“欲得筆勢痛快,一在力學古人,一在涵養胸趣。夫心靜則氣自生矣。高才用心專至如此,久當自知耳。”[3](P76)“力學古人”只是一方面,僅憑此還不夠,作者還得“涵養胸趣”,這里實際上指出了實現文章“至境”的兩條路徑。
先說說力學古人。從文章創作來看,“道與藝合”表現為“辭以盡志”,姚鼐指出:“達其辭則道以明,昧于文則志以晦。”[2](P89)古人著文志在“明道義,維風俗”,能夠“辭足盡其志”,如在文中“盡其志”則必須“達其辭”,否則“志以晦”,而道不明,“藝”與“道”就不能結合。這里的“達其辭”與“昧于文”意思相對,所指卻是相同,皆是就形式層面的文法而言。因此,要想實現“文之至”,先要在文法上下功夫,這是“文者,藝也”這一本質規定的內在要求(因為“藝”就是指法的運用),因此要想實現“道與藝合”,就必須重視為文之法,而文法的獲得則必須走師古一路。姚鼐說道:
近人每云,作詩不可摹擬,此似高而實欺人之言也。學詩文不摹擬,何由得入?須專摹擬一家,已得似后,再易一家。如是數番之后,自能镕鑄古人,自成一體。若初學未能逼似,先求脫化,必全無成就。譬如學字而不臨帖,可乎?[3](P129)
姚鼐視“摹擬”為詩文入門之途,認為只有通過“摹擬”,才能“镕鑄古人,自成一體”,師古成為實現文章“至境”重要門徑之一。姚鼐指出:
今人詩文不能追企古人,亦是天資遜之,亦是涂轍誤而用功不深也。若涂轍既正,用功深久,于古人最上一等文字,諒不可到,其中下之作,非不可到也。昌黎不云“其用功深者,其收名遠乎?”近世人習聞錢受之偏論,輕譏明人之摹仿,文不經摹仿,亦安能脫化!觀古人之學前古,摹仿而渾妙者,自可法;摹仿而鈍滯者自可棄。[3](P69)
他將今人與古人對比,今人不及古人,除了“天資遜之”這一因素外,就是“涂轍誤而用功不深”,欲“追企古人”,“涂轍正”是前提條件,失去這個前提,“用功深”也是作無用之功。可見,“涂轍正”的重要性。在姚鼐看來,所謂“涂轍正”就是通過摹仿這一路徑,實現“脫化”,最終擺脫依傍,自成一家。他說:
必欲學此事,非取古大家正矩潛心一番,不能有所成就。近體只用吾選本,其間各家,門徑不同。隨其天資所近,先取一家之詩,熟讀精思,必有所見。然后又及一家,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同者必歸于雅正,不著纖毫俗氣。起復轉折,必有法度,不可茍且牽率,致不成章。至其神妙之境,又須于無意中忽然遇之,非可力探。然非功力之深,終身必不遇此境也。[3](P128-129)
“師古”是有選擇的,在師法對象上“取大家正矩”,也就是強調“入門須正”,以避免入手“即染邪氣,不能洗脫”;[3](P128)在師法方式上,既要“熟讀精思”,知其異同,又要注意“起復轉折,必有法度”。所謂“神妙之境”即文章“至境”,這既“非可力探”(與天分有關),又非“功力之深”不可致(與人力有關)。姚鼐談到“才”與“法”之間的關系時說道:
文章之事,能運其法者才也,而極其才者法也。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無定之法。有定者所以為嚴整也;無定者所以為縱橫變化也。二者相濟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窘吾才,乃所以達吾才也。非思之深、功之至者,必不能見古人縱橫變化中,所以為嚴整之理,思深功至而見之矣。而操筆而使吾手與吾所見之相副,尚非一日事也。[3](P49-50)
對這段話,郭紹虞指出:“才屬于天,天分高者,往往馳驟縱橫,不甘以法度自縛。”“而在姚氏則以為必離于法而逞才,其才不大;必在法度之中而猶能運用自如,才見其才。”[7](P394)在姚鼐看來,惟“法”才能盡顯其“才”,惟“才”才能盡運其“法”,強調“才不離法”“法不離才”。“法”在古人,有“有定”和“無定”之分,只有“思深功至”才能見之。“才”屬于天,無“才”不能運“法”,這樣習得的“法”因沒有用處而失去價值。姚鼐自言:“夫文章之事,望見涂轍,可以力求。而才力高下,必由天授。鼐所自歉者,正在才薄耳。”[3](P80)“法”為門徑,可以 “力求”,“才”由“天授”,不可“力探”,姚鼐對“才”與“法”的理解正是本其“天與人一”之論。
再說“涵養胸趣”,姚鼐指出:
夫內充而后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閎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邃以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閔閔乎!聚之于錙銖,夷懌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以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于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2](P104)
“內充”指主體內在修養,“后發”是指外在創作,“內”不充,后不“發”,主體胸襟不充實,筆下怎有生動的內容和別致的文采?又怎能做到“筆勢痛快”“理得而情當”?在姚鼐看來,文章創作“如雞伏卵”“內候其節,而時發焉”,當主體胸中所蓄達到一定程度,自然文思泉涌,揮筆成文,有如自然形成。他說:
夫古人文章之體非一類,其瑰瑋奇麗之振發,亦不可謂其盡出于無意也;然要是才力氣勢驅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為之也。后人勉學,覺其累積紙上,有如贅疣。故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語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為文家之正傳,而先生真為得其傳矣。[2](P289-290)
這里的“平淡”不是指文章風格,而是指“無意為文而文已至”的創作姿態,這是創作的最高境界。因此,姚鼐才有“文之至者,通于造化之自然”的說法。
姚鼐所說的“胸趣”,除知識、學問之外,主要指一種胸襟氣魄。以詩歌創作為例,他說:
古之善為詩者,不自命為詩人者也。其胸中所蓄,高矣、廣矣、遠矣,而偶發之于詩,則詩與之為高廣且遠焉,故曰善為詩也。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退之、蘇子瞻、黃魯直之倫,忠義之氣,高亮之節,道德之養,經濟天下之才,舍而僅謂之一詩人耳,此數君子豈所甘哉?志在于為詩人而已,為之雖工,其詩則卑且小矣。[2]P(50)
如前文所引,姚鼐以為“一為文士,則不足觀也”,“詩人”畢竟是一介文士,作者如果僅僅做個文士,其詩歌品格不會高,不能說是“善為詩”,詩品出于人品,人品又與其胸中所蓄有關,詩歌史上的重要詩家就是例證。姚鼐指出:“夫詩之至善者,文與質備,道與藝合,心手之運,貫徹萬物,而盡得乎人心之所欲出。”[2](P51)最好的詩歌應當是“道與藝合”,當然也是“天與人一”,因為要想“貫徹萬物”并且能夠“盡得乎人心之所出”,非得有極高的創作造詣和才氣不可。
可見,姚鼐的“至境”論不是一種空洞的說法,是有具體實現路徑的。一是“師古”,但“師古”,不是“襲古”,而是要“脫化”,最終是要實現“成一家之言”的,這個過程強調“人力”與“天分”的結合,也就是“天與人一”;二是“涵養胸趣”,無論是文章內容的選擇,還是文章形式的傳達,都受主體“胸趣”所制約,目的在于實現“道與藝合”。這兩條路徑可以說是實現文章“至境”的不二法門。
四、文章“至境”論的意義
據上所論,姚鼐的文章“至境”論實際上蘊含著一整套理論,具有體系性。它以“道與藝合,天與人一”為綱,從文章本原、功能、創作及主體修養,都有具體的理論主張。為人們所樂道的“義理、考據、辭章”之說、“陰陽剛柔”論以及文之“精”“粗”等理論均含括其內。這種理論體系,從表面上看折中圓融,實際上是有缺陷的,這使得其在桐城后學的創作實踐中屢遭置疑。比如,曾國藩一方面企羨孔孟“道與文俱至”,[8](P183)堅持文道合一之論;一方面又說:“鄙意欲發明義理,則當法經說理窟及各語錄劄記;欲學為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閫奧者,正為兩下兼顧,以至無可怡悅。”[9](P102)又認為“道”(義理)與“文”不可兼顧。吳汝綸則直接指出:“必欲以義理之說施之文章,則其事至難。不善為之,但墮理障。程朱之文,尚不能盡饜眾心,況余人乎!方侍郎學行程朱,文章韓歐,此兩事也,欲并入文章之一途,志雖高而力不易赴。”[10](P138-139)應該說曾、吳所論正是姚鼐“至境”論不足之處,“道貴正,而文者必以奇勝”,[10](P52)“正”與“奇”相反而不能相成,姚鼐所言正是忽略了“道”“藝”之間的矛盾性。這種缺陷隨著桐城派的壯大,其負面作用也愈發突出,最終對桐城派自身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吳汝綸將文道兩置,實際上是動搖了桐城派立論根基,其危害不能說不大。
但是,如就其所統攝的文章理論及其所形成的時代環境來說,對于桐城派乃至清代文論建設無疑是有其意義的。姚鼐在繼承方苞“義法”說和劉大櫆的“能事”論的基礎上,力求將桐城古文理論系統化,其“至境”論,就是這一系統化的結果。借助這一表述,姚鼐從審美理想的高度,對桐城派古文創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桐城文章的學術個性由此得以逐漸形成,這對桐城派的確立和發展至關緊要。
具體來說,首先是確立了桐城派文章創作理想,為桐城派文人的創作在理論上提供了導向。就桐城派內部來看,姚鼐對初祖方苞之論有不滿之處。方苞在讀《史記》時說:“《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緯之,然后為成體之文。”[11](P58)自以為得為文之奧秘,姚鼐卻說“其閱太史公書,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處、疏淡處及華麗非常處;止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之義法,亦不可不講”,[3](P75)他既肯定方苞“義法”說的必要性,又認為以“義法”論文只是“得其一端”,并沒有含括為文之全部門徑。對于業師劉大櫆,姚鼐雖不免阿于私好,多有推崇,但也不是完全茍同。劉大櫆論文側重在“文人之能事”,對方苞“義法”說,只發揮“法”這一端,不免失之于偏。姚鼐在編《古文辭類纂》時曾將方、劉文章刪去,除有避黨同鄉之嫌,也有其文章創作與姚鼐文章理想不合之故。在這種情況下,對于“以古今文章之傳系之己”,[12](P360)企圖構建“桐城文統”[13](P103)的姚鼐來說,有責任另建一套理論話語代替方、劉,作為桐城派古文創作的指導思想。在姚鼐的文論話語中,“文之至”一語的反復出現,就體現了這一心理訴求。盡管他所提出的“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在桐城后學的古文創作實踐中難以實現,甚至被置疑,但仍被桐城派文人視為最高理想,其內含的理論體系已經固化在桐城文人心中,成為所謂的“桐城家法”,為桐城后學奉為圭臬。
其次,這一說法深刻影響了桐城派文人的致思方式,使得他們在文章創作及批評中始終堅持內容與形式并重,思想性與審美性的統一。從文章創作來說,要想實現“道與藝合”,就必須在選題立意上深思熟慮,在藝術形式上精心營造,使得文章內容和形式相得益彰,既富有深刻的思想性,又有豐富的審美性。就思想性來說,桐城派是強調“文以載道”的,他們要求文章發明義理,于世有益。姚鼐所說的“切乎理,當乎事”,梅曾亮強調的“通時合變”,[5](P30)曾國藩將“經濟”與“詞章”相結合等,就是重視文章思想性的體現。就審美性來說,桐城派雖視文為末藝,卻深知文章形式價值之所在,極其重視文辭的表達。姚鼐就指責“有言義理之過者”和“為考證之過者”不講究形式之弊。因此桐城派特別強調要領悟古人為文“深妙之心”,講究格律聲色,重視法度,要求文章寫得神采煥然,具有動人之力量。在文學批評上,桐城派重視從“義理”和“審美”兩個維度開展批評。以詩歌批評為例,方東樹的《昭昧詹言》一向被視為桐城派詩學的代表作,書中主要觀點本自桐城諸老,其中出自姚鼐者尤多。如對王維詩歌,方東樹認為其詩“興象超遠,渾然元氣,為后人所莫及;高華精警,極聲色之宗,而不落人間聲色,所以可貴”。這是著眼于審美維度;又認為其詩:“非不尊貴,而于世無益”“無當于興、觀、群、怨,失風、騷之旨,遠圣人之教,亦何取乎?”[14](P387)則是著眼于義理維度。這種批評方式使其詩歌批評多有歧誤之處,被吳汝綸、吳闿生父子先后拈出。
最后,姚鼐文章“至境”論確立了桐城派文學活動的基本立場,即立足儒學“道統”和古文“文統”,強調“道”“藝”并舉,“天賦”和“人力”并重,以創造一流文章為目標,從而為桐城派的形成提供了統一的思想基礎。姚鼐開創桐城派,首先要解決的是思想統一問題。為此,他以韓愈首創的“道統”和唐宋八家為主的“文統”為依據,標舉方苞,推尊劉大櫆,并融鑄二人理論形成的“義理、考據、文章”之說,以及圍繞這一說法所形成的系列闡釋,如陰陽剛柔論、文之精粗論以及融鑄唐宋的詩學取向等,無一不是對桐城派文學基本立場的細致表達。明確的立場再加上系統的理論,使得其學風動天下。王先謙在《續古文辭類纂》序中說:“ 姚惜抱稟其師傅,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閫奧,開設戶牖,天下翕然號為正宗。承學之士,如蓬從風,如川赴壑,尋聲企景,項領相望。”[15](P1)這種看法在理論和事實上都是有依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