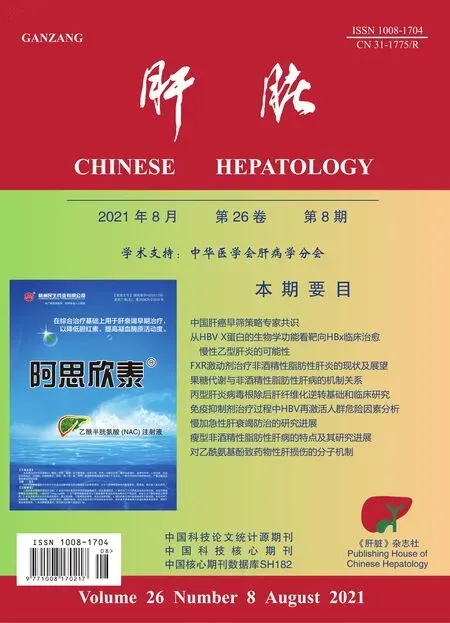FXR激動劑治療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現狀及展望
薛芮 范建高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是一種以肝細胞脂肪變、氣球樣變、炎癥和纖維化為特征的慢性、進行性肝病。隨著肥胖、2型糖尿病和代謝綜合征患病率的上升,NASH已成為全球慢性肝炎和終末期肝病的最常見病因[1]。NASH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疾病譜中病情惡化的關鍵環節,25%左右的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患者可進展為NASH,30%以上的NASH患者有發展為肝硬化或肝細胞癌(HCC)的可能[2],然而至今尚無特效藥物獲批用于NASH的治療[3]。為此,研究NASH的發病機制及潛在藥物治療靶點至關重要。
研究發現,膽汁酸作為信號分子與受體結合,在NAFLD/NASH發生、進展和消退中起關鍵作用[4]。2015年FLINT試驗中期結果“奧貝膽酸(OCA)通過激活法尼醇X受體(FXR)可以降低NASH患者的NAFLD活動性評分(NAS)及纖維化程度”引起業界關注[5]。
一、FXR改善NASH的機制
FXR是一種核受體,在肝臟、小腸、結腸、腎臟、腎上腺和卵巢組織均有表達,以肝臟和腸道的表達最為豐富。FXR活化后通過調節膽汁酸穩態、脂質代謝、炎癥反應以及肝纖維化、肝臟再生等環節參與NAFLD的發生和發展[6]。肝臟FXR激活后主要通過小異二聚體配體(SHP)依賴的方式干擾肝細胞脂肪酸的攝取、抑制脂質合成、促進線粒體脂肪酸氧化和脂質轉運,從而改善肝臟脂肪蓄積[7]。最近一項研究表明,肝細胞內過量的游離脂肪酸(FFA)可以激活法尼醇X受體-環磷腺苷效應元件結合蛋白通路,從而抑制肝細胞自噬;通過抑制甘油三酯的分解和降低FFA和脂毒性物質的產生,從而抑制肝細胞凋亡[8]。Kim等[9]研究發現,腸道FXR激活后誘導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15/19(FGF15/19)表達,并通過門脈系統進入肝臟,導致SHP磷酸化,從而招募DNA甲基轉移酶3a結合到脂質生成基因,抑制其表達并減輕肝臟脂肪蓄積。
FXR通過SHP依賴及非依賴途徑發揮抗炎作用。FXR與配體結合后通過誘導SHP表達,穩定趨化因子2(CCL2)啟動子抑制劑復合物或直接促進核受體輔抑制因子1(NCor1)復合物與促炎基因啟動子結合,下調促炎因子表達,從而減輕炎癥[10-11]。多項研究表明,肝臟FXR激活后通過誘導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21(FGF21)的表達改善NASH的組織學特征[12-13]。FGF21是脂聯素的強調節劑,通過誘導脂聯素的表達上調,從而改善胰島素抵抗和肝臟脂肪蓄積[14]。另一項研究表明FGF21通過抑制肝細胞Toll樣受體和白細胞介素-17信號轉導,從而抑制NASH向HCC進展。
OCA通過抑制NASH動物模型肝臟p53的活化和肝細胞死亡,從而抑制肝冠狀結構和間質纖維化的發生[15]。活化的FXR還可抑制肝星狀細胞轉化生長因子(TGF)-β/SMAD3和JunD/激活蛋白(AP)-1通路,從而防治肝纖維化[16]。因此,FXR及其相關信號通路可能是治療NASH的潛在靶點。
二、FXR激動劑治療NASH臨床試驗現狀
OCA是第一個進入NASH新藥研發II期臨床試驗的FXR激動劑。FLINT的II期臨床試驗結果表明,OCA顯著改善NASH患者肝組織學表現,可降低NAS評分及纖維化程度[5]。隨后III期REGENATE臨床試驗結果表明,對合并中重度纖維化的NASH患者的纖維化程度的減輕作用與安慰劑組有顯著差異,但并未達到NASH消退的試驗終點[17]。鑒于劑量依賴性的瘙癢和潛在的致動脈粥樣硬化風險,血液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降低等不良反應,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在2020年6月的官方回信中指出,OCA治療NASH的預期收益并未超過其潛在風險,至今FDA仍然沒有正式批準OCA用于治療NASH[11]。
近期一項獨特的非膽汁酸型FXR激動劑MET-409的IIa臨床試驗結果顯示[18],與其他FXR激動劑相比,MET-409顯著降低肝臟脂肪含量,其低劑量組(5 0mg)瘙癢及血液LDL-C升高的發生率及嚴重程度較其他實驗藥物治療組顯著降低。當平均相對LFC下降>30%時,低劑量組瘙癢發生率為16%。MET-409治療指數增加且療效增強的原因可能是其獨特的化學結構可誘導不同的受體構象和基因表達譜。然而,MET-409組部分患者在治療開始的4~8周內出現短暫的無癥狀谷氨酸氨基轉移酶(ALT)升高,在治療的第12周31%~50%接受MET-409治療的患者ALT降低亦超過30%。在未來的MET-409臨床試驗中,需要注意對ALT和其他肝臟標志物進行額外監測。此外,由于不同FXR激動劑治療NASH的臨床試驗在試驗設計上存在差異,臨床試驗數據不能簡單地進行比較,最終需要頭對頭的直接比較來明確不同FXR激動劑的潛在差異。
綜上所述,相對于現有的候選藥物,結構優化的FXR激動劑具有更廣泛的治療指數和更高的療效,有可能解決重大的未滿足的需求。FXR激動劑的風險-獲益比可以通過結構優化來提高,但均衡利弊后的最佳劑量需要在更大規模、更長時間的研究中探索。
三、FXR激動劑不良反應的機制
包括甾體和非甾體不同化學類型的FXR激動劑在不同臨床試驗中均出現劑量依賴的皮膚瘙癢和血脂異常,這些是FXR激活后的靶效應。大部分藥物不良反應無法在動物模型中復制,不良反應的明確機制難以有效探討。嚙齒動物和人類的HDL-C/LDL-C代謝存在很大差異,即使用靈長類動物模型進行研究也不能提供可預測的結果。活化的FXR可通過上調肝細胞B類I型清道夫受體以及膽汁酸池FXR激動劑依賴性變化誘導經腸膽固醇流出,從而降低血液HDL-C水平。LDL-C的增加可能是細胞色素P450(Cyp)7A1下調、肝細胞LDL受體表達減少、載脂蛋白-C和-E以及膽固醇酯轉移蛋白改變的結果,但目前尚不清楚哪種機制在其中起主要作用。
FXR誘發皮膚瘙癢的機制更為神秘且復雜,FXR激活后自分泌誘導激活另一種G蛋白偶聯受體(GPCR)型膽汁酸受體TGR5,以及另一種GPCR型致瘙癢受體(MRGPRX4),通過膽汁酸模式的改變,間接參與瘙癢的發病[19]。
四、不同FXR激動劑治療NASH的機制
FXR激動劑的化學類型以及腸道與肝臟FXR激活的相互拮抗是影響治療指數(改善肝脂肪變、肝彈性或肝組織病理學的有益作用與潛在不良反應之間平衡)的決定性因素。不同化學類型的激動劑在與FXR結合時誘導不同的構象,導致基因轉錄譜差異。Harrison等對用過MET-409或“含羧酸的FXR激動劑”的小鼠肝臟進行RNA測序,結果發現兩種化合物誘導不同的基因表達模式。然而該研究只做了主成分分析,未提供具體受影響基因的細節,也未披露正在研究的化合物的確切結構。2003年,Downes等將MET-409的模板fexaramine與GW4064(PX20606、tropifexor、cilofexor和TERN-1016等異噁唑結構類的母體化合物)以及天然配體鵝去氧膽酸比較后確定了一組共同受FXR調控的基因,并確定了三種化合物單獨調控的基因(誘導不同的FXR構象,導致不同的基因轉錄譜)。當前亟需公開MET-409和EDP-305的化學結構,并在野生型和FXR敲除小鼠或細胞系中對所有臨床相關的FXR激動劑的基因表達譜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比較。
構建FXR啟動子驅動的熒光素酶報告小鼠研究發現,FXR在生理條件下僅在腸道被強烈激活,而幾乎不顯示其肝臟激活活性。提示FXR的有效肝臟激活不是FXR晝夜活動自然程序的一部分,而肝臟FXR似乎僅在肝內膽汁淤積等應激狀態下才被激活。FXR通過誘導肝細胞膽汁酸輸出泵(膽鹽輸出泵、多重耐藥相關蛋白)、膽汁酸結合酶以及谷胱甘肽抗氧化防御系統的表達,改善肝內膽汁淤積。
一些研究認為,fexaramine作為一種腸道偏向性的FXR激動劑足以引起所需的代謝變化,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不必要的不良反應。然而也有研究表明,肝臟FXR的激活也是提供肝臟保護潛能的一部分。過度有效的腸道FXR激活觸發了FGF-19的超生理誘導,從而降低肝臟脂肪含量并提供肝臟保護功能。鑒于FGF-19是肝細胞增殖的關鍵驅動因素,FXR激動劑有增加HCC發病的潛在風險。人類HCC和結腸癌組織顯示FGF-19/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受體4(FGFR4)軸的高頻率基因異常或擴增,提示當前應重視腸道FXR激活的程度的潛在風險。臨床研究中應納入更多的轉化標記納入新藥研發及審批,例如:膽固醇流分析、基因表達分析及其與靶組織中化合物水平的相關性、詳細的膽汁酸分析及其與瘙癢發生率的相關性。
最新研究表明,FXR激動劑可顯著降低NASH相關并發癥的發生。FXR激活后降低肝硬化門靜脈高壓,修復腸道屏障減少腸道細菌移位,因此對于肝硬化前期或肝硬化患者,FXR激動劑的應用都將帶來獲益[5]。綜上所述,目前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優化FXR激動劑的結構并確定最佳劑量,在減輕不良反應的同時保持確定性的肝組織學改善和臨床療效,這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兩難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