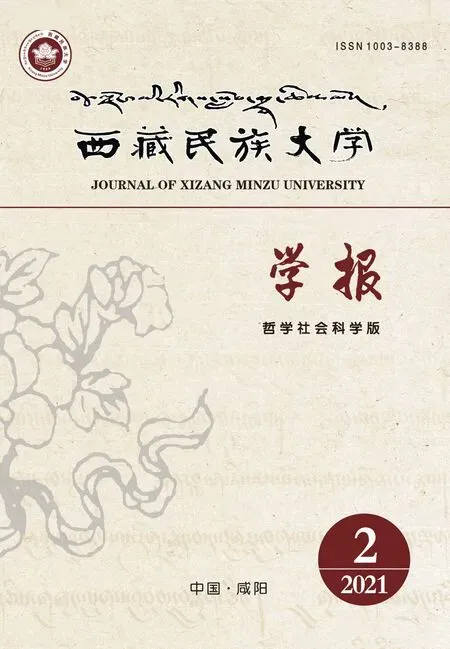清末民初《申報》視域下張蔭棠駐藏官員媒體形象呈現與塑造
蔡 丹
(西藏民族大學文學院 陜西咸陽712082)
作為中國近代報紙開端的《申報》是19世紀晚期到20世紀中期最具影響力的中文報紙。該報秉持“凡國家之政治風俗之變遷,中外交涉之要務,商賈貿易之利弊,與夫一切可驚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聽聞者,靡與畢載。”[1](P1)的辦報宗旨,記錄當時中國的社會變遷和近代化歷程。西藏地方一直是《申報》重點關注對象,無論是1903年之前對《京報》全錄式的報道形式,還是1903年后對《京報》摘錄、評論、譯報、外電及大量自采的內容[2],都說明《申報》對西藏的持續關注,從一個側面勾勒出一部近代治藏史。《申報》對國家在藏主權最直接也是最主要代表的駐藏官員群體的報道篇目眾多,其中對奉旨查辦藏事的駐藏官員張蔭棠在藏期間及前后參與藏事的持續報道,更是呈現出當時駐藏官員所代表的國家形象,也將西藏問題及相關情況展示出來。
目前學界關于張蔭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藏事改革及與此關聯的事件上,而對媒體視域下的張蔭棠,尤其是《申報》對張蔭棠駐藏官員媒體形象的呈現與塑造方面甚少關注。僅在對《申報》駐藏大臣報道的群體研究和以《申報》張蔭棠條目為史料載體的張蔭棠生平、交游研究等中有所涉及,如2019年袁愛中等《舊報刊與新報刊轉換視野中的駐藏大臣報道——以<申報>(1872-1911)為例》、馬忠文《清季查辦藏事大臣張蔭棠的家世、宦跡與交游》。總覽已有張蔭棠研究成果可知,目前有關張蔭棠的研究主要關注方向較為集中,而專以《申報》張蔭棠報道為研究對象,并細致分析近代媒體視域下的張蔭棠駐藏官員媒體形象研究的成果較少。本文擬在學界已有的研究基礎上,通過對《申報》張蔭棠報道文字的考察與剖析,結合清政府對駐藏官員的要求,分析清末民初《申報》視域下張蔭棠駐藏官員媒體形象呈現與塑造及其重要意義。
《申報》對關涉西藏的大事都會有公開、連續的報道,除了一般的公文電奏、宮門抄,川藏奏牘、譯聞之外,還在論說等欄目刊發大量評論性文章。這些評論性文章的內容主要是當時知識分子對西藏事務的看法,表達著對國家命運的憂患意識。這其中有大量是對駐藏官員張蔭棠的連續報道文字,首次報道見于1905年8月2日的《唐京卿請派張蔭棠接英藏議約》記張蔭棠議約藏事,至1913年3月3日《中國之蒙藏敷衍策》是最后一次正式報道張蔭棠參與藏事,共計82篇①。這些報道又集中在1906年初到1909年底,尤其持續跟蹤報道了兩個重大事件,一是1907年到1908年清廷派張蔭棠為全權大臣簽訂《中英修訂藏印通商章程》始末,二是張蔭棠奉命全程參與接待進京覲見的十三世達賴喇嘛。《申報》對當時這兩件牽涉西藏時局的政治大事不遺余力的跟蹤報道,既表明當時官方和民眾對西藏問題的關注和重視,也有對查辦藏事欽差大臣張蔭棠的肯定,可見,張蔭棠的治藏辦法及功績得到了廣泛的認可。這些對張蔭棠的報道文字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總體上塑造了一個駐藏能臣張蔭棠的媒體形象,但在不同時段呈現出不同特征。
一、從《申報》文本中關于張蔭棠官職稱謂的不一致問題說起
《申報》中對張蔭棠官職的稱謂,包括張蔭棠京卿、張大臣、駐藏幫辦大臣張蔭棠(西藏幫辦大臣張蔭棠)、駐藏大臣張蔭棠(駐藏大臣張蔭棠欽使)、全權大臣、駐藏會辦大臣張蔭棠、駐藏辦事大臣、(西藏辦事大臣)、欽差西藏議約大臣、西藏大臣、張蔭棠欽使、張大臣蔭棠、駐藏副大臣②等。其中報道多次稱張蔭棠為幫辦大臣,實為誤解。《申報》1906年12月6日“電傳上諭”有:“十月二十日奉旨有泰著來京當差,駐藏辦事大臣著聯豫補授。張蔭棠著賞給副都統銜,作為駐藏幫辦大臣。欽此。”[3]此為《申報》稱張蔭棠為西藏幫辦大臣、駐藏幫辦大臣的出處。1906年12月8日,清外務部有電文《旨著有泰來京代以聯豫并著張蔭棠為駐藏幫辦大臣電》載:“本日奉旨:有泰著來京當差,駐藏辦事大臣著聯豫補授。張蔭棠著賞給副都統銜,作為駐藏幫辦大臣。欽此。外寄。”[4](P1317)報道內容與電文內容完全一致。但是,張蔭棠《致外務部電請代奏辦事艱難情形吁懇收回成命》訴藏事之難:“顧微臣辦事艱難苦衷,有不得不瀝陳于皇太后皇上之前者。……唯有吁懇天恩,俯準收回成命,別簡賢能,接幫辦大臣之任,以免貽誤。抑或由駐藏大臣聯豫暫行兼署,以一事權,俾臣得以專心籌辦開埠諸事。”[4](P1317)清政府結合實際情況,在回電中同意了張蔭棠的奏請,并收回任命:“奉旨:張蔭棠電奏悉。駐藏幫辦大臣著聯豫暫行兼署。所有亞東關開埠各事宜著張蔭棠妥籌辦理,以專責成。”[4](P1318)可知,張蔭棠在藏期間行使的權利,雖基本與駐藏大臣無異,但實際上,張蔭棠并未赴駐藏幫辦大臣之職,而是始終以欽差大臣之名查辦藏事。③究《申報》中張蔭棠官職稱謂混亂的原因,除西藏與內地的信息溝通不及時的緣由外,還因當時張蔭棠是清廷屬意的駐藏幫辦大臣最適宜人選,而且,他本人也確實以欽差身份由印赴藏查辦藏事。是以,當張蔭棠出任幫辦大臣的消息一經傳出,必然被世人先入為主地將張蔭棠安放于新任駐藏幫辦大臣職位上。且《申報》畢竟不是官媒,其報道難免有失誤之處。而《申報》對張蔭棠官職稱謂的不一致,也成為后人將張蔭棠直接劃歸駐藏大臣群體的一個原因。
駐藏大臣專指清廷派往西藏的駐扎大臣,其任期、員額、衙門駐地等皆有定制。張蔭棠治藏期間并未擔任駐藏大臣官職,也未長期在駐藏大臣衙門辦理公務,更沒能任職三年,完全不符合駐藏大臣官員任命。由此可知,張蔭棠并非傳統意義上的駐藏大臣,而是應時局而派出的治藏特派員。④唐紹儀請辭于議約進行時,其繼任者須有外交能力,又要對西藏事務諸多了解,才足以擔此重任,而張蔭棠正符合此要求,經其師唐紹儀舉薦,由朝廷任命代替唐紹儀繼續與英人議約藏事。在議約中,張蔭棠展露其出色的外交才干和對藏事的獨特見解,得到了朝廷的認可,再次任命張蔭棠為欽差,由印度直接入西藏查辦藏事,就近赴任也符合經濟原則,有利于治藏籌藏。加副都統銜是朝廷議定張蔭棠出任幫辦大臣一職的加封,符合駐藏大臣任職慣例,但后應他個人要求,允其不擔任幫辦大臣職,而是命其為自由且權利更集中的入藏查辦事件欽差,享有駐藏大臣的權利,并參與西藏日常管理,以保清廷在西藏的主權為己任。張蔭棠在藏期間履行了駐藏大臣的義務和責任,無論是關注、搜集與西藏大局有關的信息,還是承擔西藏地方上層與清廷之間的溝通任務,抑或肅清吏治和奉命與英印政府議約,都和駐藏大臣的職責一致。因此,張蔭棠是以欽差的身份入藏查辦事件,任職期間所作所為承擔了部分駐藏大臣基本職責,但其身份卻始終游離于駐藏大臣制度之外,這是當時西藏特殊形勢下的靈活變通。英國打著通商旗號以實現蠶食西藏的目的,通過不平等條約要求在西藏各處設置商務機構,并由此派駐官員以商務委員的名義入侵西藏,企圖削弱西藏與清廷的關系,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關系著國家命運的開埠通商事,就成了當時清廷和西藏地方亟須解決的重大問題,而開埠通商專員的任命也就應時而生。張蔭棠在特殊時期被清政府秉承破格重用人才的原則,任命為以辦理西藏開埠通商事宜為主,統籌西藏事務的查辦藏事欽差大臣,是清廷開始重視西藏的體現。
二、《申報》對駐藏官員張蔭棠的報道和媒體形象的呈現與塑造
(一)駐藏能臣張蔭棠媒體形象的初步呈現與塑造(1905年8月-1907年5月)
據《張蔭棠駐藏奏稿》可知,從1905年9月18日接旨代替唐紹儀正式接議藏約,到1907年7月離開西藏前往印度再次議約,張蔭棠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以議約大臣、查辦藏事欽差等身份參與藏事及對英外交談判,使他對當時西藏面臨的國際形勢有更深刻的認識。張蔭棠出色的外交才能和敏銳的政治觸覺在與英印議約和處理班禪事件中得以初步展露,而之后他以廣闊的國際視野總覽西藏全局,詳陳英人長期覬覦西藏、陰謀圖藏進而圖謀全中國的事實,反復申明整頓藏務、收回政權“有刻不容緩之勢”。而后張蔭棠提出的一系列安邊治藏的政策和措施,得到了藏族民眾的廣泛贊揚和支持,對西藏地方有較大的影響。這一時期是張蔭棠治藏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時期,而清政府正是在這個時期開始關注西藏,正視西藏危機,派遣有志官員駐藏統籌,張蔭棠就是此時期應時而生的駐藏官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清政府對西藏的重視。
然而,由于西藏的特殊性以及張蔭棠在藏時間過短等因素的影響,《申報》并未對這一時期的張蔭棠予以過多的關注,從1905年8月2日首次報道到1907年8月報道張蔭棠奉旨往印度與英國再次議約事,這些報道僅呈現簡單粗略、以點帶面的特點。除涉及唐紹儀、有泰等人連帶性的報道外,僅有《唐京卿請派張蔭棠接英藏議約京師》《催議英藏條約》《查辦英兵圍張大臣之密使起程》《電傳上諭(補授張蔭棠為駐藏幫辦大臣)》《電參西藏大臣》《日下新聞(駐藏大臣張蔭棠電奏前藏糧臺候補知縣余鐘麟)》《電飭慎重西藏交涉》《日下近聞(因張蔭棠經手事件多,暫行擱置西藏改省事)》《中英定期會議藏事》等九篇報道。
以上九篇報道以點帶面,勾勒出此階段張蔭棠的治藏軌跡,呈現并塑造出駐藏能臣張蔭棠的媒體形象。這些報道先后報道唐紹儀的請旨——張蔭棠在印度電覆催議英藏條約——張蔭棠赴拉薩路上遭遇事件——清政府擬授張蔭棠為駐藏幫辦大臣——張蔭棠正式查辦藏事及雷厲風行的察吏行動——清政府電飭張蔭棠須慎重西藏交涉而不得草率從事——張蔭棠因公務繁忙暫不能返京參加清政府因西藏改設行省召開的會議——中英擬派代表于印度會議藏事,將張蔭棠兩年來在西藏的行跡與大事略現于報端,為民眾和讀者初步呈現出張蔭棠符合清政府期許的駐藏能臣形象。以《查辦英兵圍張大臣之密使起程》對甘波洛事件的報道為例,據《張蔭棠駐藏奏稿》所載,1906年9月24日張蔭棠一行抵達靖西時遭遇了甘波洛的無理挑釁,并于27日將此事奏報外務部,而《申報》刊發《查辦英兵圍張大臣之密使起程》的日期是1906年10月22日,時差幾近一月,當屬此事事關重大,又屬機密,故報道較晚。細致分析和考察報道文本可知,清政府對張蔭棠在挑釁事件中據理力爭,維護國家在藏主權的行為是予以保護的:“未派密使之前,先有電致西藏辦事大臣有泰,令其將張京卿被英兵圍困之詳細情形速行查辦,覆以便核辦。”[5]《申報》也將各界對張蔭棠在西藏被圍原因的猜測一一羅列:“至張大臣在西藏被圍之故,或謂系查界,或謂系因張未迎接該英員,或謂系英員與張議藏事不合,莫衷一是。”[5]既是媒體對涉藏事件的關注,也凸顯了張蔭棠異于昔日與英交涉中一味逢迎妥協官員的難得之處。《申報》1907年1月27日有《電參西藏大臣》,報道張蔭棠電參有泰溺職貪婪和清政府命有泰聽候查辦,有泰隨員或革職查辦,或永不敘用情形,是張蔭棠奏章《致外部電請代奏參藏中吏治積弊請旨革除懲辦》的內容要旨。此外,《申報》還報道了張蔭棠對待瀆職官員的不同處罰方式,1907年5月17日“日下新聞”有:“駐藏大臣張蔭棠電奏前藏糧臺候補知縣余鐘麟案招搖查明屬實,擬請旨罰銀六千兩,充地方善舉。該令以縣丞降補以示薄懲。”[6]因為西藏地處偏遠、自然環境艱苦,經費和人才的缺乏是西藏新政改革的最大阻礙,故據西藏當下形勢而察,罪行較輕者以罰款、降職以示懲戒是恰當之舉。
由上可見,《申報》通過對張蔭棠最初治藏期間所涉事件和施政的選擇性報道,包括治藏兢兢業業,嘔心瀝血,以維護清廷在藏主權為己任,以西藏地方自強為目標,制定系列措施和主張等等,初步呈現張蔭棠駐藏能臣形象,并成為構建張蔭棠媒體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真實立體的駐藏能臣張蔭棠媒體形象的深度呈現與塑造(1907年8月-1908年12月)
從1907年8月報道張蔭棠奉旨前往印度與英再次議約,至1908年12月十三世達賴喇嘛離京期間,《申報》對張蔭棠的報道更加頻繁、密集,主要集中在與英國交涉通商開埠議約、力促達賴進京覲見等兩個系列事件上,呈現定期性、連續性特點。
張蔭棠入藏查辦的主要任務是依照1906年簽訂《中英續訂藏印條約》相關條款開通商埠,確定開埠日期、劃定埠界、開埠具體安排等。在與英人交涉相關事宜中遇到眾多阻礙,直接威脅到中國在藏主權,張蔭棠據理力爭,極力抵制,多次磋商未果,在中英政府交涉下擬定于印度再次議約。張蔭棠憑借著杰出的外交才能、敏銳的政治觸覺和強烈的愛國情懷籌辦藏事,為中國在藏主權維護立下汗馬功勞。《申報》對此重大問題自然特別關注并進行系列報道,包括《中英定期會議藏事》《江孜開埠之計畫》《駐藏大臣奏保襄助會議人員》《張大臣電告會議情形》《中印大臣議商藏事》《春丕英兵撤退實信》《詳紀藏印商約》《電諸速派專員會議藏事》等,還刊登了張蔭棠議約期間的專電和籌藏奏稿。通商開埠議約系列報道呈現出殫精竭慮、致力維護中國在藏主權的駐藏官員媒體形象。
對張蔭棠印度議約結束并于1908年6月回到北京后有關西藏的系列活動,《申報》的報道也是巨細無遺。包括回京日期、被兩宮召見密談、面奏西藏辦理事宜詳情、返京原因、奉旨與唐紹儀辦理西藏改省事宜、陪同接待達賴喇嘛并與之商談藏事、任職變遷等等,均一一詳細報道。如張蔭棠返京后蒙兩宮召見事見于1908年6月24日“專電”:“昨日召見張蔭棠屏退侍從,奏對至兩小時之久,極為秘密”[7]、6月30日“緊要新聞”:“二十三日西藏大臣張蔭棠召見兩宮垂詢,頗殷,張大臣將議訂中英藏約一事詳細面奏約二鐘之久”[8]、7月3日“緊要新聞”:“特召張蔭棠回京,該大臣已于……赴頤和園覲見”[9]三則報道,凸顯清政府對藏事的關注和對張蔭棠查辦藏事的首肯。另外,《申報》報道提及張蔭棠對達賴進京事的看法,如1908年7月14日“專電”有:“張蔭棠面告軍機大臣宣召達賴進京于藏事大有裨益,以速為妙”[10],這是他在深入了解西藏內情外勢的前提下,對當下局勢做出的判斷,在某種程度上說達賴喇嘛入京覲見是由他一手促成的。張蔭棠駐藏后期,曾數次電奏朝廷,希望同意達賴、班禪的覲見請求。《致軍機處外務部電請代奏達賴班禪同請入京陛見》申明理由,一為怕英人趁達賴班禪不合挑唆生亂,一則希望達賴班禪能合二為一,冰釋前嫌。即使在清廷下旨暫緩來京后,他仍認為令其陛見,則“主國名義愈見鞏固”[4](P1325)。《致軍機處外務部請飭達賴回藏》中說“現在英兵既撤,似應請旨飭達賴回藏,以維我主權而慰藏情”[4](P1410),《致外部電請諭飭達賴回藏》中述“觀察情形,達賴回藏,藏民當能相安”[4](P1418),認為現在藏事初見端倪,應該讓滯留在五臺山的達賴及時返藏,有利于維護中國在西藏主權和穩定西藏局勢。張蔭棠初到西藏籌謀藏事,準確把握形勢,電奏清政府令達賴暫緩回藏,認為此時達賴返藏會使藏事更復雜,⑤應抓住時機盡快督辦藏事改革具體事宜,將主動權掌握在朝廷和駐藏大臣手中才是首要任務。隨著形勢的變化,張蔭棠具體問題具體對待,認為需要在適當的時候讓達賴返藏,“以慰藏人之望”[4](P1412)。1908年達賴再次奏請讓入京覲見,朝廷多次商討后予以準奏。《申報》跟蹤報道了達賴喇嘛覲見過程及前后情形,從是否強召達賴入京事商之張蔭棠到議派張蔭棠往五臺山迎接達賴、派達壽張蔭棠接待到京之達賴喇嘛、列席軍機政務兩處與達賴會議磋商藏事等等,從這些報道文字中見朝廷對張蔭棠查辦藏事的認可與肯定。
這一階段的報道中,還穿插著多則張蔭棠離藏返京不再赴藏的報道。《申報》1908年6月28日《張蔭棠留部消息》:“西藏幫辦大臣張蔭棠此次來京系為中英藏約事宜,聞大臣有留外務部當差之信,即不再回西藏。”[11]此報道于張蔭棠初回京之時,當不是空穴來風,張蔭棠于6月返京后,當確實有意留任外務部。之后的報道和事實也為明證:《申報》1908年7月17日“電”:“張蔭棠以藏事危急,不愿再往,運動留京。”[12]7月22日《張蔭棠不愿赴藏》再次談及此事:“張蔭棠以藏事異常棘手,擬留京不往。……仍欲令張前往,故張日來極力運動留京。按刻接電傳上諭張已補授外部右參議,大約已達留京之目的矣。”[13]雖報道有主觀猜測之嫌,卻也合乎情理。這一時期的《申報》多次報道張蔭棠在外務部的升遷情況,如1908、1909年連續報道“張蔭棠著補授外務部右參議”,“張蔭棠著署理外務部右丞”,“張蔭棠候補四品京堂”,“軍機處商議外部侍郎一缺提及鄒嘉來、梁士詒、張蔭棠三人”,“張蔭棠以外務部左右丞記名請旨簡放候補四品京堂”,“上諭外務部左丞著張蔭棠署理”,“上諭外務部左丞著張蔭棠補授”等都表明張蔭棠在外務部任職幾成定局。外務部是1901年改原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而來,班列六部之首,是當下清政府最炙手可熱的部門,張蔭棠與外務部眾多官員交往甚密,加上他出色的政治和外交才能已然得到朝廷和外部各官員的認可,故他想要留任外務部的可能性是極大的。返京后,朝廷肯定張蔭棠駐藏期間的出色成就,對其頗為倚重、信賴,著張蔭棠全程參與接待達賴和與之談判的任務,還令其妥籌治藏辦法,并多次申明讓他隨達賴一同返藏,繼續查辦藏事,但最終張蔭棠確實沒有再次返藏。從現實比照印證,可知《申報》新聞報道的來源還是較為可靠的。從有關張蔭棠返京不再赴藏的相關報道可以看出張蔭棠是否再次赴藏,雖是自我抉擇,卻也因朝廷用人制度混亂所致。張蔭棠駐藏生涯自此終結,然其善于處理藏務,致力維護中國在藏主權的駐藏官員媒體形象留存于歷史,也為其他駐藏官員提供了可資學習和借鑒的榜樣。
但翻檢相關史料文獻,并未有張蔭棠就此不愿返藏的記載,因此更顯《申報》此類報道有重要的文獻價值。考察張蔭棠不愿返藏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經過數年對英交涉和西藏實地考察,張蔭棠對藏事的籌謀可謂愈見成熟,善于抓住時機和優勢。但議約過程的舉步維艱,朝廷和西藏形勢的復雜多變,張蔭棠對西藏的嚴峻形勢和籌藏之難也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二是人事關系的復雜,如有泰的誹謗,聯豫的排擠,朝廷的訓誡,藏事改革的難行,議約的反復,英印政府的無理指責,種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張蔭棠對查辦藏事有了退心;三是個人身體原因,張蔭棠高原反應嚴重,在藏期間身體一直抱恙,有泰曾言:“張憩伯身體亦不見好,多喘”[14](P680),“聞弓長病甚重,已不能理公事云云”[14](P691),張蔭棠自己在《致外部電陳治藏芻議》中說“咯血日劇”[4](P1328),在《致外部丞參函述籌藏詳情及參劾番官原委》說“棠自抵拉薩,患咯血氣喘,日食虛粥半甌,夜不成寐”[4](P1359)。結合《申報》對張蔭棠不再返藏的一系列報道的分析,可以見出駐藏官員張蔭棠更真實、全面、立體的形象。
(三)駐藏能臣張蔭棠媒體形象的補充呈現與塑造(1909年之后)
張蔭棠由于個人意愿及其他原因返京后未再赴藏,而是改任駐美欽使。1909年赴美后,因工作重心轉移,張蔭棠幾乎不再牽涉西藏事務,《申報》的報道也由其涉藏逐漸轉向其使美。但是,由于張蔭棠治藏期間的籌藏策略和功績得到了清廷和朝中要員的認可,《申報》在之后的籌藏工作報道中,仍多次提及張蔭棠,被認為是極了解藏中形勢之人,清廷還是認為他可任籌藏要職。例如,《申報》1909年12月5日“京師近事”:“(理藩部)擬在部內設蒙藏事務所一處,……唐紹儀、張蔭棠、伍廷芳則可望簡任會辦藏政大臣”[15];1910年7月4日“電”:“攝政王以藏事棘手,欲派重臣往駐,世中堂保薦唐紹儀,慶邸亦力言唐能勝任,王諭恐其辦事任性,慶邸又保張蔭棠……”[16];1910年8月6日《駐藏大臣更動原因》:“……又聞繼其后者為駐美欽使張蔭棠……均將列保。”[17]
及至民國時期,袁世凱對張蔭棠治藏能力也一直持認可態度,如《申報》1912年4月4日:“大總統以蒙藏問題極關重要,前日特與邊事股諸幕僚會議收撫辦法,據大總統之意,以前駐美外交使張蔭棠曾兩任印藏劃界事務,該地情形頗為熟悉,擬派充蒙藏行政使,以期聯絡聞已電,張迅即回國矣”[18]。在后世所編《最近官紳履歷匯編》和《民國人物大辭典》里,有關張蔭棠的條目有“西藏辦事大臣”[19](P145)和“辛亥革命后,任西藏辦事大臣”之說[20](P968),前者將此職列于張蔭棠任職經歷中的駐美公使后,參政院參政前,大約為1912年或者1913年,后者直接交代是張蔭棠辛亥革命后的職務。然而張蔭棠自1907年離藏之后,便未有史料顯示他再次前往西藏供職,故應為只有任命,而張蔭棠并未赴任就職。除此外,袁世凱還電詢張蔭棠針對目前形勢有何治藏良策,《申報》對此也有報道。《申報》1913年3月3日《中國之蒙藏敷衍策》:“……袁總日前曾電致駐英代表張蔭棠略謂該代表駐藏多年深悉藏事,現在對藏方針應如何施行,希即速覆,以備采擇。日昨張蔭棠已將藏事詳細條陳電覆政府,探其內容,大致分兩種手續:(一)對英政府當根據《印藏新約》,速向英使交涉,此時英廷對藏方針尚持穩健主義,若失此時機,必噬臍無及。(二)對藏政策多一羈縻,徐圖改良,英俄方面由民國直接交涉,務使達賴頃心內向。所陳各節極為中肯,大總統頗然其議。”[21]此條報道內容涉及張蔭棠晚年的籌藏駐藏策略,代表了他晚年對藏事的關注和思考,有重要的文獻資料價值,對于研究完整的張蔭棠駐藏官員形象構建提供了重要憑證。可見,張蔭棠對藏事的關注度并未因其離開西藏不再籌辦藏事而削弱,他以更廣闊的國際視野,對藏事有了更深切的認知,可惜的是,這些措施和之前的新政命運相同,都不了了之。這一時期的張蔭棠涉藏報道鞏固了此前塑造的張蔭棠駐藏官員的正面媒體形象,也從側面見證了清末民初西藏危機的升級和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的變遷,民眾可以多角度更深層了解到西藏問題的嚴峻性。
三、余 論
《申報》系列報道呈現出一位熟悉藏務并為籌藏鞠躬盡瘁的新時期駐藏官員形象,張蔭棠兩次參與英印政府議約西藏,并通過奏稿詳陳其整頓藏務以維護中國在西藏的國家主權和抵御外侮的一系列主張,是后來西藏推行新政的基礎和綱領,對西藏地方乃至全中國都有著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但是,史書對張蔭棠籌藏功績的記載略顯單薄,例如《清史稿》中僅有數條關涉張蔭棠籌藏事宜,其余史料文獻較少提及。世人了解張蔭棠治藏情形除官方文獻,則多是通過他駐藏時期的奏稿電文等窺視其人其才,卻忽視了《申報》中有關張蔭棠涉藏報道。故《申報》對張蔭棠的報道在一定程度上補張蔭棠奏稿和史書等的記載缺失,與駐藏奏稿、史書互證,共同構建出張蔭棠駐藏官員形象。
綜上所述,張蔭棠籌辦藏事的核心思想是對外維護中國在藏主權,對內改革藏事,以圖自強,并以此為原則,籌辦一切藏事。《申報》對張蔭棠的報道文字,既能完整地呈現張蔭棠駐藏期間,以及前后對藏事的籌辦和關注,也展現了當時清政府和國人對張蔭棠及西藏的態度和看法,其史料價值和學術價值不可低估。
[注 釋]
①《申報》“張蔭棠”條目共有151條。
②“駐藏副大臣”張蔭棠1908年回京后,清廷決議簡派時為外務部侍郎的張蔭棠為駐藏副大臣,后未果。
③張蔭棠是否為駐藏大臣一說已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代表性的有:馬忠文《清季查辦藏事大臣張蔭棠的家世、宦跡與交游》《學術研究》(2019年第6期),康欣平《清廷選擇張蔭棠查辦藏事原因探微》《西藏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曾國慶《論清季駐藏大臣張蔭棠》《康定民族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年第5期)等等。
④張蔭棠任職初期經歷與唐紹儀當初如出一轍,《時報》1904年11月18日《擬派唐京卿前往西藏專辦善后》(京師)(政界紀聞):“前放唐少川欽使赴西藏重訂藏約一節,茲探悉政府已與駐京英欽使商訂,俟簽押后,即派唐欽使赴藏專辦善后事宜,以保主權而符名實。”
⑤亞東稅務司韓德森在《韓德森為報印度新修通往春丕谷兩條路及江孜地區不安寧難以開展貿易等事致赫德半官方性函(1904年9月3日第1號)》:“達賴喇嘛被暫時廢黜,俗人等皆感憂慮不安。一旦達賴喇嘛重返拉薩,必將再度引起麻煩。”見于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編:《西藏亞東關檔案選編》(下冊),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年,9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