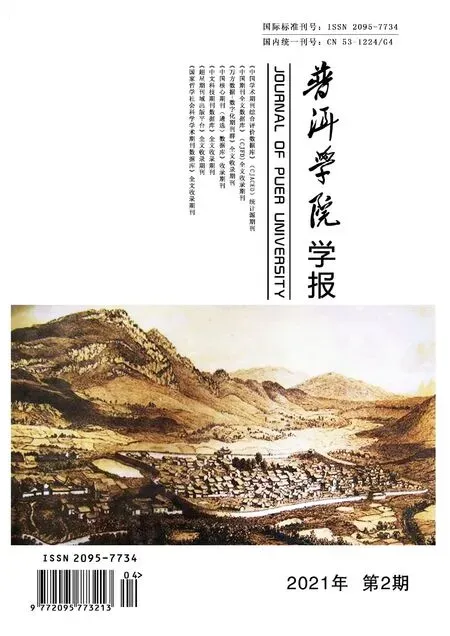劉震云《一句頂一萬句》主題揭示
周順艷
滇西科技師范學院 文學院,云南臨滄677000
劉震云是中國文壇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家,至今已發表9部長篇小說和10余部中短篇小說集,他的作品個性鮮明、人物類型豐富、對小人物的命運遭際描寫細致,善于表現人物的生存困境。2011年,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榮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再次引發世人關注。在作品中劉震云使用了“一出一回”的結構揭示了生命“重復”的主題,用人與人之間“說不說得著”貫穿全篇,揭示了人的“孤獨”主題,用“喜虛不喜實”地書寫揭示了“存在”的主題,最后用“不,得找”揭示了“尋找”的主題。
一、“一出一回”對“重復”生命主題的揭示
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由《出延津記》和《回延津記》兩部分構成,出延津的是楊百順,回延津的是牛愛國,而兩人又是沒有血緣關系的祖孫,可以說,劉震云對此結構的設置是有意為之的,“一出一回”正好表現了“重復”這個主題。
在《出延津記》中,小說講述的主要是楊百順的故事。楊百順還有兩個兄弟,一個叫楊百業,一個叫楊百利,三兄弟跟父親老楊一起生活。楊家主要的謀生手段是賣豆腐,而楊百順不滿于此,加之父親對自己的責難和對老三楊百利的偏袒,楊百順決定逃離楊家莊,逃離自己的原生家庭,做出這個決定后,他的生活就此進入了一種重復的逃離模式。
離家后的楊百順遇到了剃頭匠老裴,經老裴介紹,楊百順和殺豬匠老曾學殺豬,一開始師徒關系很好,但后來因老曾生病,楊百順便一人去村里給人殺豬,因師娘過分苛刻,只分幾件固定的下水給自己,矛盾漸漸產生,跟老曾家生了嫌隙,楊百順選擇了逃離,這是他的第一次“出逃”。楊百順的第二次就業是在蔣家莊,地點是老蔣家的染房,但他不是負責染布,他的工作是挑水,每天要花很大的力氣才能把水缸挑滿。老蔣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不喜歡和人交流,喜歡和猴交流,他養了一只猴子,取名“銀鎖”。但有一天楊百順在逗猴的過程中,上了猴的當,不小心把“銀鎖”放走了,他知道自己犯了大錯,再一次選擇了逃離,這是他的第二次“出逃”。之后,楊百順又去了老魯開的竹業社,但最終也是“逃離”。因參加了社火表演,誤打誤撞被縣長選到縣政府后花園種菜,又因在縣政府“上班”,被寡婦吳香香相中,“嫁給”了吳香香。之后因尋找跟人私奔的吳香香,而在路上丟了女兒巧玲,傷了心的楊百順最終選擇離開延津,在陜西過完了下半生。
代際之間的職業傳遞是中國社會的傳統,子承父業在以農業種植為主的古老中國,可以說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形式,楊百順本來可以跟著父親老楊沿街叫賣一輩子的豆腐,注重“根”的中國人基本上都會選擇這種安穩的現世生活,不會貿然選擇出走。無疑,楊百順是一個傳統中國社會中的異類,他選擇了艱難的逃離。
在《回延津記》中,小說講述的主要是牛愛國的故事。牛愛國是巧玲生的孩子,是楊百順的外孫,同時也是龐麗娜的丈夫。牛愛國的苦惱源于二人的“說不著”,因“說不著”導致婚姻的失敗,妻子出軌婚紗攝影店老板小蔣,因為兩人“說得著”。同樣的“說得著”的人,也被牛愛國遇到了,那就是章楚紅,牛愛國出軌章楚紅,四人都是婚內出軌,但都遇到了“說得著”的人。
不僅同時代的人經歷了重復事件,甚至跟隔代人也存在著驚人的事件重復,楊百順當年被吳香香相中,并與其結婚,改名吳摩西,但實則倆人并無感情基礎,彼此也說不著,吳香香最后出軌老高,倆人在輿論的壓力下選擇了私奔。最終楊百順在陜西安定下來,直到終老,再沒有回延津。同樣的故事橋段重復在牛愛國身上,牛愛國和妻子龐麗娜也是說不著,兩口子貌合神離,龐麗娜出軌其姐夫老尚,倆人最終也選擇了私奔,逃離了延津。楊百順的出走和牛愛國的回來,共同構成了《出延津記》和《回延津記》中地“一出一回”模式,而這樣的“一出一回”所表現出的驚人重復,這正是作者對個體命運的書寫。或許劉震云想表達的是,“重復”是人生命的常態,也是人生命的主題。
二、“說不說得著”對“孤獨”生命主題的揭示
小說《一句頂一萬句》中,劉震云反復寫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對交流的倚靠,是人存在的必然,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希望能夠在交流中,通過他人對自己的看待,來確認自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眾多小人物的話語是小說的一大特色,劉震云很注重對人物語言的描寫,特別是對“說不說得著”尤其關注,可以說,作品中“說話”是一個很核心的內容。“這個我們每天實踐、親歷和不斷延續的最平常的行為,被劉震云演繹成驚心動魄的將近百年的難解之謎。百年在劉震云這里,只是一個關于人的內心秘密的歷史延宕,只是一個關于人和人說話的體認”[1]。小說中的剃頭匠老裴,因為老婆老蔡與其吵架時信口胡說他和自己的姐姐一塊兒下流而發火,便動手打了老蔡。小說里寫到“老裴怒從心頭起,拿起砍刀,就要殺人,但不是要殺老蔡,而是要到鎮上殺她娘家哥”[2]。從以上內容不難看出,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存在很大的沖突,根本說不著,這無疑是一種孤獨的體驗。
同樣的沒話說,還表現在夫妻間,而偷情者卻能說得著。吳摩西和吳香香無話可說,牛愛國和龐麗娜無話可說,曹青娥和牛書道也無話可說,但是當說得著的人出現時,一切都變了。夫妻關系本是很親密的關系,但卻無話可說,與他人卻說得著,個體的孤獨和生存困境可見一斑。
三、“喜虛不喜實”對“存在”生命主題的揭示
要么交流存在沖突,要么無共同語言,小說中有一類人把對自我的確認轉向了“喜虛不喜實”。楊百順喜“虛”,他喜歡舞社火,喜歡羅長禮的喊喪,甚至在陜西定居后還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羅長禮,喊喪可以把他放置在另一種身份之中。“一方面是借用死者的權威和恐懼,利用鬼魂的超自然超現實的力量,來規劃和構建親屬的共同體;另一方面,喊喪的人卻有一種他者的地位,他幾乎靈魂出竅,他成為一個旁觀者,他指使別人來到死者面前,而他超然于死者的權威之外”[3]。楊百利也喜“虛”,他喜歡噴空,而且還噴得特別好,“所謂的噴空,就是有影的事,沒影的事,一個人無意中提起一個話頭,另一個人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語,把整個事情搭起來。”噴空,可以天馬行空地發揮自己的想象力,不按常理編故事。縣長老史也喜“虛”,他特別喜歡聽戲,其實就是因為戲中的人都不是真實的人。其實,除了喜歡聽戲,老史更是把自己融入到了角色之中,假裝自己是另一種虛擬的身份,實現了對縣長身份的逃離,也擺脫了精神的困苦。喜歡戲的人還不止老史一個,還有開竹業社的老魯,老魯也喜歡“虛”,他喜歡的戲不是聽戲看戲,而是喜歡在自己的腦子里走戲,隨著走戲漸入佳境,由此完成了自己對現實身份的隱藏。無論是喊喪、噴空還是聽戲、走戲,他們都從自己的真實身份中抽離了出來,把自己放入了一個非常愉悅、安全、自由的‘虛“的空間里。
除了選擇“虛”的方式實現對自我存在的確認,小說中還有一些小人物把對自我身份的確認放在了動物身上。在上部《出延津記》中開染房的老蔣和下部《回延津記》中開汽車修理鋪的老馬都是典型。老蔣喜歡養猴,喜歡跟猴打交道,對猴也特別的寵溺。老蔣平日里對染房的人很苛刻,也不喜歡與他們多說半個字,但對猴卻是萬般喜歡,因為他不能缺少了猴的陪伴。汽車修理鋪的老馬,也不喜歡與人交流,原因是找不到可以“說得著”的人,所以他也養了一只猴,每天除了捯飭車,就是跟猴耍,沒有了傷心、沒有了人際交往中的苦楚。
小說中的這些小人物,都是因為生活中尋不到說得著的人,才喜歡“虛”的東西和以猴為伴。其實在人類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與對話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說交流是人存在的一種證明和意義。但是當交流過程中只有沖突、矛盾、不理解、無法溝通等字眼時,他們的精神上實則承受著巨大的痛苦和內心的孤獨,這樣的生存困境使得這些小人物不得不把自己的交流對象轉向“虛”的東西和動物身上,以借此獲得自我身份的確認以及生存的意義和價值。
四、“不,得找”對“尋找”生命主題的揭示
在現代漢語詞典里“找”的定義是“為了要見到或得到所需求的人或事物而努力”[4]。在文學作品中,“尋找”一詞,可理解為對生命意義及出路的探尋。可以說作家的經歷影響了“尋找”主題的創作。劉震云小時候曾跟姥姥一起生活,父母的缺席,給他的內心帶來了一些孤獨的體驗。14歲時劉震云到甘肅入伍,走出了自己的家鄉,故土是作者永遠的掛念,作品中小人物們的尋找,其實也是作者自己的尋找。楊百順和牛愛國這些小人物,都是傳統農耕社會中的一員,他們的精神生活極度貧乏,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他們都很孤獨。他們的尋找,都是對生命意義的探尋,渴望尋到一個出路與一個“說得著”的人。
不同的是,楊百順最后放棄了尋找,選擇在陜西終老;而牛愛國則堅持尋找。牛愛國的前半輩子,可以說跟楊百順很像,跟身邊的人都說不著,妻子還跟人私奔了,但在小說結尾處,牛愛國堅定地說:“不,得找”。而小說中牛愛國的母親巧玲和楊百順的孫兒媳何玉芬都對牛愛國說過一句話“日子是過以后,不是過從前”。無疑,“以后”、“從前”這兩個詞給牛愛國帶來了一些思考,特別是“以后”,所以牛愛國非常確定地說“得找”。其實,這也正表明了劉震云的希冀,他對作品中小人物的精神困苦充滿了同情與理解,并對他們寄寓了一些期待,那便是直面人生的困難與苦痛,并勇敢的去超越與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