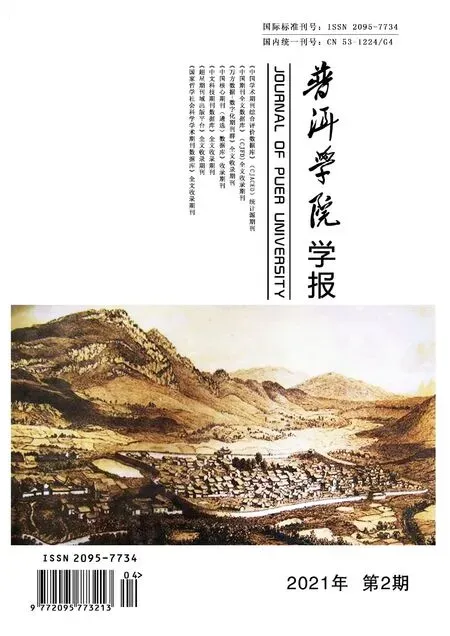民國時期佤族的社會經濟和生活文化圖景
楊寶康,娜響
1.滇西科技師范學院 國際佤文化研究院,云南 臨滄 677000;2.普洱學院 民族文化研究中心,云南普洱665000
佤族是我國西南地區歷史文化悠久的少數民族之一,“至遲在11世紀的時候,佤族作為一個單一的民族已經初步形成”[1]。清朝時期,相關的史志著作提到了“嘎喇”“卡瓦”(“卡利瓦”)“哈瓦”等稱謂,還有“卡瓦有生熟二種。生者劫掠,熟者保路”的記載。大多數學者認為,“嘎喇”“卡瓦”(“卡利瓦”)“哈瓦”這些族稱指的都是佤族[2]。民國時期,方國瑜和彭桂萼是佤族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方國瑜認為,佤族名“卡瓦,亦曰哈瓦,又稱卡剌”,“從其大者而分之,則為卡瓦與卡剌:卡剌文化程度較高,不殺人頭祭谷,信仰佛教;而卡瓦則較粗野,不信佛,殺取人頭祭谷。此其大較,婦女裝束及村落之設備亦異”[3]。彭桂萼認為,“卡瓦有熟生或稱為純野兩種,純卡受漢人同化較久,野卡則較少往來,極兇暴”[4]。總體上看,民國時期,佤族的族稱已經呈現出集中和統一的趨勢,不同的稱呼更多反映的是社會發展情況的區別。就民國時期佤族社會經濟和生活文化的時態而言,其社會經濟大抵表現為農業上多種旱谷、鴉片等作物,耕作方式為刀耕火種和鋤犁撒種;手工業以紡織、釀酒等行業為主,但更多的是作為農業的副業而存在,多在農閑時進行;商品交換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與漢族、傣族、拉祜族等的經濟聯系不斷加強。生活文化則主要體現在衣食住行、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從不同角度折射著佤族民眾的日常生活時態。民國時期佤族的社會經濟和生活文化圖景,集中反映了佤族社會傳統與變化的諸多面相,值得深入考查和研究。鑒于學術界對民國時期佤族社會經濟和生活文化的研究成果數量有限且比較零散,因此,本文以方國瑜、彭桂萼的調查研究為核心資料,對民國時期佤族的社會經濟和生活文化圖景作一初步但力求全面的考察。
一、佤族社會經濟
(一)農業生產
農業生產是佤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主要生活來源。方國瑜對滄源班洪地區的佤族有過具體的調查和深入的研究。班洪的佤族“多為卡剌,通稱為臘家,以卡剌呼之不悅,呼卡瓦則若遭大辱者”[3]。其農耕地主要是旱地,“山地無主,任人開荒。初辟山田,縱火燒山,鋤而撒種。次年則須耙犁數次,坡峻則鋤之。種三年而荒,荒二三年復耕種,一年復荒。種田,不知計畝數。惟曰:一家所種,一家足食而已。田地業權視為土官所有,百姓開荒領佃,故每年所納門戶課以戶計,其數相等,不以所種田之多寡別也。鰥、寡、孤、獨者,則雖種田,得免課”[5]。“班洪有大衙門小衙門之分,總管署為大衙門,二老爺、三老爺、六老爺、七老爺為小衙門,每年所收門戶稅,由大衙門征之,當酌分若干與小衙門”[3]。“班洪居民,每戶年納一盧比(按:約合國幣一元)或少數之臨時征收,年約得二千盧比,酌量分與小衙門及頭目若干,養兵40名,所獲猶不足用。”班洪“土署前有隙地,牛豬糞堆積,穢氣不堪,晚飯后,寨中老幼蹲而談天,忠漢亦時雜其間,未以貴族自矜也”[3]。據《班洪風土記》(上卷)記載:班洪總管胡忠漢家“見其家中男婦操作,一如平民,其夫人每日舂米,夜切芭蕉喂豬,終日忙碌無倦容”[3]。山地“初雖任人開荒,然種一年后,此田有耕種權,非原主情愿放棄權利,他人不能于次年種之”,如果“一坡而分數家種者”,則鋤一溝以作分隔,“界限分明”[5]。在班洪,山地多種旱谷,把田土鋤松,待雨后撒種。下種約在清明節前后。既種,不耰不蓐,雜草隨生,待秋熟而剪其穗,谷干雜草刈而焚之,以備明年耕種[5]。水田種植水稻,但班洪部落的水田很少,僅南臘的戶乃村寨有水田,稱為水田寨[5]。通過調查研究,彭桂萼對滄源、雙江、瀾滄、西盟、孟連佤族的農業生產情況也有客觀的反映。滄源永和、大蠻海等地的佤族“種鴉片及旱谷,強悍耐勞,好獵人頭,喜劫掠”[6]。雙江的佤族“概為純卡瓦,住居歷史很久”[7],“散居小黑江沿岸,種旱谷,習牧畜,強悍而忠勇”。瀾滄、西盟、孟連的佤族“聚居安康糯波、木戛、西盟、拉巴諸山頭,分純野二種,種旱谷、獵人頭,披發裸身,儼然原人狀態”[6]。可以看出,佤族的山地農業以種旱谷者為最多,次則為經濟作物鴉片、煙草、玉蜀黍、芝麻等,也種水稻、豆、麥、蕎糧、薯、芋,但數量不多。
(二)手工業
民國時期,佤族的手工業還沒有形成單獨的部門,通常是作為農業的副業而存在,多在農閑時進行。主要的種類有紡織、釀酒等。佤族地區多種棉、麻,因近處多種旱谷,所以棉、麻多種在距離村寨較遠的地方,種植之后,“春季鋤土刈草,任其榮實,按時收成,不多勞力,亦無肥料”。紡織是婦女從事的家庭手工業,“每晚紡線一團為度,約重一兩,不知紡輪,用手撚之,垂互引線,粗細不均”。織機甚簡陋,經線丈余為一匹,舉動甚緩,農閑時從事紡織。織就的棉布用土產藍靛染色后縫衣。這一時期,因棉、麻種植不多,加之紡織工具落后,佤族地區有不少人缺衣少穿,衣不遮身。佤族酒風很盛。據彭桂萼《雙江一瞥》記載:“卡瓦不論男女都愛吃旱煙,隨時把尺長的銀皮煙袋斜插在背項里。而嗜酒如命,更為卡瓦人的特性”[7]。方國瑜《班洪風土記》(下卷)也記載:“在孟定、耿馬、猛角、猛董市上,有自班洪來趕集者,余錢狂飲,呼嘯而去”[5]。酒有白酒和水酒兩種,以水酒的制作最具代表性。原料用小紅米、高粱、玉米等為主,煮熟后拌入適量酒藥發酵而成。凡議事、待客、祭鬼、節日等都要“泡酒”,即把發酵后的酒飯中摻入生水,用細竹管吸出,即成水酒。彭桂萼《邊地之邊地》詳細記載了他在滄源巖帥喝“泡酒”的情況:“小屋的一角,支著一個盛有酒飯的大壇子,上面插了一顆彎竹棍,酒汁便由竹孔里壓升了出來,完全是物理學中虹吸的裝置。我因酒量太小,呷了兩口想停留不吃了,被他們按倒頭硬灌。吃了一杯又送來一杯,吃得衣襟也潑濕了,頭臉也弄紅了。正站起要走,另一家已用人伺候在門外,‘請’的一聲,不由分說又被拉了去,一進門就灌給你幾杯水酒,幸而這水酒性不力,不然真要被灌得不省人事呢”,“這是他們的敬客之禮,是要老實高興才來這套的,你若不吃,他就以為你看不起他,不接受他的誠敬了”[4]。
(三)商品交換
民國時期,佤族的商品交換關系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據方國瑜的考察,“卡瓦山出產品之輸出者,鴉片、紫膠為最多”[8]。班洪總管“無暴斂,然善賈,收賈民間紫膠鴉片出境,年獲數千金,無可用,盛于罐而埋之”[3]。1937年1月,彭桂萼考察發現,“在募乃廠山前后的箐邊石縫里,一有隙地就種滿芙蓉,這幾日正紅白相映地開著鮮花。瀾滄農產物中,鴉片的數值相當的大,連煙畝都有三千多呢!種煙的,多半是倮黑及卡瓦”[4]。西盟鴉片的種植也很普遍,并有嚴重的高利貸盤剝現象。1937年3月,彭桂萼一行離開猛梭時,“上通坡,迎面遇見了拉巴縣佐的夫人長袍奔來,知是要到路邊煙地上向卡瓦督收她重利放下的煙土”[4]。據統計,佤族種植鴉片的數量很大,在他們的收入中也占有較大的比重。如1947年,西盟馬散大寨平均每戶收大煙25兩,約占總收入的24%;翁戛科平均每戶收大煙24兩,約占總收入的25%;中課寨平均每戶收大煙18兩,約占總收入的22%[8]。不難看出,民國時期,佤族地區種植鴉片比較普遍。需要說明的是,佤族雖然廣泛種植鴉片,但卻很少吸食,主要是把其作為特殊的商品與其他民族進行商品交換。就佤族地區的集市和商品交換而言,“班洪全境80余寨,惟南臘有集市,在其村南崗頭,草鋪20余間,5日一街,四方來者頗眾,有自百余里至者。南臘居民多自鎮康遷至,以劉、高二姓為望族,習俗與漢人同,惟婦女裝束為卡剌化”[3]。雙江、瀾滄設縣之初就有街天(即內地所稱的集市)。滄源的猛角、猛董、巖帥等地街市的出現也很早。西盟街約在20世紀初葉由佤族和拉祜族共同建立,西盟馬散街則在1940年前后產生,都為5天一街[2]。“卡瓦山所產水果,質美且數量最多者為柑子,價廉,現銀一元(合國幣伍角)即可購60枚”[9]。每逢街天,趕街的佤族人往往比較多,以物易物是其重要特點。比如,若干兩鴉片換一頭牛,10個黃果換2兩白酒,一筐旱谷換若干食鹽等等。隨著佤族商品交換關系的發展,貨幣的使用逐漸普遍,在較大的交易活動中還產生了中間人“打牙”。佤族的商品交換活動不僅加強了與漢族、傣族、拉祜族等民族的經濟聯系,也促進了自身社會內部的變化,使社會生產得以不斷進步發展。
二、佤族生活文化
(一)衣食住行
1.服飾方面:佤族崇尚黑色,服飾多以黑色為基調。據彭桂萼的田野調查,中緬南段未定界的佤族“女人有披長發的,有戴帽子的;耳塞有木的,有銀的,粗如大手指,長約四五寸,下端成花瓶口形。黑粗布短衣,以線結合代紐扣,下身束桶裙,膝以下扎有脛褲。處女在臀部箍滿了髹漆藤環數十圈。男子,有包布巾的,有科頭長發或剃去外周單留中頂一勺毛的;上衣粗糙黑色,在背脊的一股現出兩指寬的縫痕,褲極短,褲袖大在一二尺,與襠底合成一擺。中有一半左右的野卡是徹底赤裸著全身的,只用一條長布帶環繞在腰上,由臀部兜了下去,從胯縫上掩護上來。他們除了武器,每人都橫掛著一支鑲紅條的袋掛。而且不論男女,口里時時都銜著草煙桿”[4]。滄源巖帥的佤族“男的短衣黑巾,黝黑粗壯,女的大耳環,銀項圈,黑底紅白邊的岔裙,腳肚上還箍滿了藤環”[4]。方國瑜對佤族服飾的觀查也呈現出類似的情況,“公明山附近野卡,有不穿衣服,惟以一幅粗布遮羞者。耳戴環,篷首,男女無別,幾不能辯”[10]。滄源甘乃寨、漫波寨、高多寨“野卡男子,出必掛刀負矛,裝束與馴卡同,惟污垢甚。女子上衣亦類馴卡婦,裙則紫色,雜以紅黃條紋。跣足篷首,不理發結,以線自額頭纏之,銀片如蒲葉者飾其前,耳環銀質或藤圈”[9]。
2.飲食方面:方國瑜、彭桂萼的調查研究結果表明,民國時期,佤族的飲食特別簡單。如滄源班洪的佤族平時儲存谷物,用石臼杵,隨舂隨食,天明后,家家舂米,操作者多為婦女,一人或二人舂之[5]。家有火塘,米肉混煮熟食,以竹節或葫蘆為碗,有的則盛飯于筐,用手抓食。家家養豬于草樓下,清晨啟欄放出到山中覓食,傍晚,呼嘯喚豬回家,婦女切芭蕉煮熟,雜以糠稗而喂之。雙江的“卡瓦生活更疾苦,放手抓吃”[7]。生活在中緬南段未定界的佤族也是“吃粗食雜糧,生活真疾苦萬分”[4]。
3.居住方面:佤族多“聚居為寨,村寨錯落參差,險要處設有寨門,貫橫木欄之”[5]。房屋材料,柱樑用木,蓋屋用草,余則用竹。房屋多為干欄式建筑,因其屋須一日完工,故所居多粗陋而矮小。建筑分上下二層,上層中設火塘,四周為吃飯、睡臥、待客之所,房屋一端為扇檐曬臺,室內一側設樓梯至地面。下層無隔,雜置柴草及家畜棲息其中[5]。“巖帥有滄源京城之稱,共管有13大寨,三四千戶人。單就本村而論,都有三百多家,密聚如蟻。房頭多草建,墻壁則用竹笆敲扁編成”[4]。雙江的“卡瓦住屋則人畜伴處,可說是最不講究住所的原人了”,“卡瓦僅有被單草席,甚至滑無一物睡在木板或竹笆頭上者,故他們每睡都靠近火塘,燒火助暖”[7]。滄源董丁、甘乃“野卡所住寨,聚數十百家而居,環如馬蹄形,四周掘深溝,溝內外密種荊棘,護以竹籬,雞犬亦不能穿入,堅固猶勝于城垣”[9]。“土人樓居,設火塘,四周而臥,就火取暖,被墊甚簡”。南坎烏附近野卡,則無所謂床被,眾人圍火塘睡,晨起,各事所事[9]。
4.出行方面:佤山道路隨山坡蜿蜒,依山曲道,下視危崖,路傾無人鋤修,行人匐伏而過。運輸靠肩扛、背負和牛馬馱運。雖然道路崎嶇,坎坷難行,但佤族人不論男女老少,都健步如飛,雖砂礫荊棘載道,亦不能傷足[5]。由于阿佤山區大小河流縱橫,為了方便通行,佤族人民在寬大的河流上往往修建有竹橋。“將竹竿交叉插在水中,竹竿一根挨一根,由此岸直通對岸,形成一個X形槽道,在竹竿交叉的槽底鋪上直徑約15厘米的樹桿,樹桿朝上的一面斫平,一根接一根鋪過去,構成橋面。叉開的竹竿上方,有數根繩索起吊索作用,將竹竿頭彎過來拴掛在索上,減少橋面的壓力。過橋時,可伸手把扶竹竿,保持平衡”[11]。
(二)風俗習慣
民國時期,佤族社會多實行一夫一妻制,但不排除一夫多妻制的存在,并且為社會所認同。佤族青年男女在日常生產、社會活動中相互交往認識,通過“串姑娘”自由戀愛。結婚時,男方要給女方聘禮,俗稱“買姑娘錢”。婦女妊娠期間,照樣參加生產勞動。分娩時,忌諱生人進家門。嬰兒出生2至3天,就要為其取名。名字一般由排行和本名兩個部分組成。男性的排行依次為巖、尼、桑、賽等,女性排行依次為葉、伊、安姆、歐等。名字有的取天干名的,也有的以地支取名。歷史上,佤族的婚姻較為穩固,究其原因,主要是自由戀愛,感情真摯和傳統倫理道德的約束。佤族把死亡分為善終和兇死兩種,善終指老死、病死并且在家中死亡的;兇死指因刀、槍、水、火、自殺、難產等非正常死亡。善終者的喪葬儀式較為隆重,而兇死者的儀式則較為簡單,墓地多在村寨西邊,善終者的墓地在上面,兇死者的墓地在下面。
禮俗方面,佤族有兩句重要的格言,一句為“格拉那格拉揚”,意為“孝敬是禮”,突出體現在禮拜長輩的風俗上,以尊重長輩、孝敬老人為榮。另一句為“格拉莫格拉宏”,意為“相愛是禮”,主要體現在對兒童的愛護與養育上[12]。此外,佤族稱“敬酒酹酒”為“西格布來”,是佤族人際交往、人神溝通的又一重要內容,有“無酒不成禮”之說。阿佤人喝酒之前,首先要滴酒在足前的地上,以敬祖先和天地之靈。眾人集聚喝酒,先敬長者,由長者為大家祝福。每次酹酒,都有其不同的祝禱之詞[13]。佤族在對外交往中“以蠟條、谷花為信物,示其誠意也”[9]。蠟條以蜂巢黃蠟為之,裹于線,長四五寸,谷花則取玉蜀黍叢生之花枝。方國瑜在《卡瓦山聞見記》(續)中記載,“卡瓦習俗,過寨送禮”,方國瑜友楊祝三將周行公明山境時,派人送鹽茶至所有野卡村寨,野卡以芭蕉果、甘蔗為禮,蓋取芭蕉之葉最寬,甘蔗之葉最長,尊其人而送禮物。既送禮物,則不仇視。惟有貪財者,則將入寨,阻于門外索錢,與之,始放行。又或悔前言者,則阻于途,送生硬芭蕉果數枚,告勿來,強之則致動武也。曾有一寨,出一砍柴刀,厚二寸許,說你等所帶武器,能以一彈穿之,則可通過,有劉君,10步外射之,彈穿其刀,土人伸舌服之[10]。送茶則有宣戰之意。方國瑜在《卡瓦山聞見記》中記載,“至高多寨,甘乃野卡火攻阻道,召高多頭目囑往曉諭,頭目說,前日甘乃寨已送茶來。送茶即宣戰之物也。再三與言,頭目不敢往”[9]。“野卡愚直,一意孤行,不計后事”[9]。中方勘界委員過永和境時,先派人送禮物假道,不受,曉以大義且不聽,不得已兵火相見,及其敗而后服。后自猛董至高多,野卡寨外插芭蕉葉,蓋表示歡迎之意[9]。
(三)宗教信仰
民國時期,佤族的宗教信仰有原始宗教、佛教和基督教三種。原始宗教信仰是佤族最具普遍性的信仰,其信仰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主要有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等等。山崇拜、石崇拜、水崇拜、火崇拜、樹木崇拜是佤族主要的自然崇拜形式[14]。“卡瓦境以公明山為特大,故以大山名之,且奉為神山焉……2月29日,猛茅寨男婦登山祭孔明,土人相傳其地為孔明所開,年必祭之,卡瓦山諸部,亦每年相率登山祭孔明,惟其期或先或后,有道遠不能至者,則遙望而祭焉”[10]。石崇拜的表現形式有“梅神”石房子崇拜、牛角樁石崇拜、遠古石器遺物崇拜、“相”石崇拜等表現形式[15]。此外,公明山附近的“野卡寨,有供大石為神者,疾病禱之,節令祀之”[10]。佤族村寨大多建在山頂或山坡的平緩地帶,水對阿佤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佤族一年里的宗教祭祀活動首先從祭水開始。在每年年底,各村寨都要對公用的水溝進行修理維護,拆舊換新筧槽[14]。此外,佤族民間故事《瀾滄江和滾弄江》《姑娘河》《鳥淚泉》等也是佤族水崇拜的表現形式之一。佤族民間習俗認為,進入新的一年,不能用舊火,每年必須舉行迎新火活動[14]。“故祀火神,年必一祭,大都在11月,家出谷或雞,延巫禱祝,共醉一餐而散”[9]。佤族民間習俗還認為,家中火塘的火不能熄滅,人不能從火塘上跨過,不能用腳亂踩火塘的三腳架和柴禾,否則會因褻瀆火神而受到火神的懲罰[14]。建立村寨時首先要選好“鬼林地”,每個佤族村寨附近都有一片長著參天大樹的茂密林子,佤族稱其為“龍梅吉”,即“鬼林地”。此外,大榕樹是佤族自然崇拜的主要植物,村寨邊的大榕樹被認為能保佑平安,山川上的大榕樹則能保佑豐產[14]。鬼神崇拜中,佤族對鬼和神并沒有分開,都指觀念中的靈魂。佤族最崇拜的和最大的鬼神是“木依吉”,他們認為木依吉是創造萬物的,是人類的最高主宰。阿佤人還認為,鬼神有大小之分,發生什么事就祭什么鬼,才能獲福免災[14]。佤族的原始宗教中保存著古老的圖騰崇拜,既存在動物圖騰,也有植物圖騰。佤族的動物圖騰主要是牛。在佤族的傳說中,牛是佤族的救命恩人。民國時期,佤族社會在舉行一些重大活動如拉木鼓和蓋大房子時,都要剽牛祭祀[14]。滄源猛董的佤族鏢牛過程為:驅牛入場中,系其頭,數人牽之,一人執鏢刺其背,約在前足甲骨,牛負痛而狂躍,牽者猛力與抗,隨牛奔馳,約一刻鐘,牛倒于地,氣已絕也,土人視牛所倒之方向與左右側而定吉兇[11]。佤族的祖先崇拜在原始宗教中比較普遍并占有重要地位。在佤族姓氏中,以祖先命名姓氏和以祖先居住過的地方命名姓氏的較為普遍。如西盟馬散的“永歐”姓就是該姓祖先“歐”及其族人經過許多地方后建立了一個寨子,為紀念這位祖先而以他的名字為寨名,稱之為“永歐”,他的后裔也姓“永歐”。“亞木”姓也是為了紀念該姓祖先“亞木”而以祖先的名字為姓[14]。
佤族所信仰的佛教有南傳佛教和漢傳佛教。鎮康、永德佤族地區和班洪、班老、猛角、猛董等地的佤族信仰南傳佛教,雙江、孟連、瀾滄等地受傣族影響較深的部分佤族村寨也信仰南傳佛教。500余年前,南傳佛教由緬甸傳入鎮康、永德佤族地區。其他地方的南傳佛教則自附近的傣族村寨傳入。和傣族一樣,佤族地區的南傳佛教每年都有堆沙節、關門節、開門節三大宗教節日和眾多求佛賜福消災的賧佛活動。信仰漢傳佛教的佤族,主要在巖帥、單甲、安康、四排山的少數村寨一帶。晚清光緒年間,漢傳佛教僧人達董保等10余人進入上述地方傳教,并在巖帥修建了佛寺,祭祀觀音菩薩,燒香、磕頭,祈求菩薩保佑。20世紀40年代,巖帥佛寺被火燒毀,長老搬居瀾滄,佛爺、和尚還俗,該地方的漢傳佛教慢慢隨之消失[2]。
基督教傳入佤族地區始于晚清光緒年間,1949年以前,佤族信仰基督教的約2萬多人,主要分布在瀾滄的糯福、上改心、文東、安康,滄源的永和、猛角、巖帥、猛省,雙江的邦丙、南黑弄、那賽、大猛峨、小猛峨、賀金等地。就基督教對佤族地區的負面影響來說,彭桂萼認為,“拿頭祭谷的野卡能做禮拜,唱圣詩”,“萬里邊荒即有改變顏色的危險。本年(1935年)中英滇緬會勘界務路過滄源地永和時,該地野卡持械拒路,聲言只準大英國官通過,不準中立委員及中國官員通過,便是嚇人的例證,有心人還能不痛哭流涕嗎”[16]?方國瑜對滇邊教會的危害同樣也有清醒地認識,“余固未反對宗教信仰,內地基督教之事業,亦多可取,然滇邊教會,以充分政治意味煽誘愚民,不能以純潔之宗教或慈善團體視之,此則政府當局,須有以有效之約束也”[17]。
三、結語
綜上所述,民國時期,盡管佤族社會整體比較落后,但其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現象已經趨向明顯,出現了所謂“熟生”或“純野”兩種不同的族稱,這主要是指社會發展情況和習俗方面的區別[18]。在滄源的班洪地區,佤族通稱為臘家,佤族社會已經有多種剝削方式的存在。雙江、瀾滄等佤族地區,也不同程度存在一定的社會分化現象。總之,就民國時期佤族的社會經濟而言,其山地農業以種植旱谷、鴉片為主,紡織、釀酒等行業通常作為農業的副業而存在,商品交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從生活文化方面看,這一時期的佤族社會缺衣少糧、居住簡陋、出行不便,折射著佤族民眾的日常生活時態。其宗教信仰有原始宗教、佛教和基督教三種,深刻影響著不同地區佤族民眾的日常生活。綜觀民國時期佤族的社會經濟和生活文化,方國瑜、彭桂萼的調查研究成果集中反映了佤族社會傳統與變化的諸多面相,值得深入的考查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