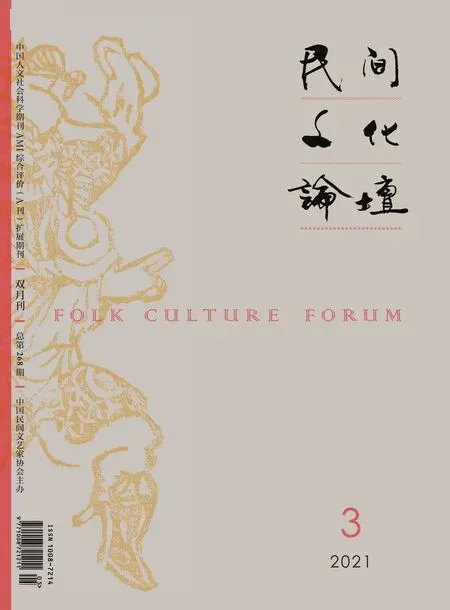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七十年
高 健
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采錄民間文學(xué)已成為一項制度,主要目的即采風(fēng)觀政。“五四”歌謠運動以來,民間文學(xué)的搜集整理由原來的“風(fēng)”之于“政”也更為突出地轉(zhuǎn)向“風(fēng)”之于“民”、“風(fēng)”之于“學(xué)”。其中,“民”指民眾或民族,即通過搜集整理民間文學(xué)來了解民眾生活文化與民族歷史文化,產(chǎn)生出一種新的“民族的詩”,甚至是“向民眾學(xué)習(xí)”;而“學(xué)”則指學(xué)術(shù)或民間文學(xué),即通過民間文學(xué)的搜集整理構(gòu)建民間文學(xué)、民族文學(xué)的學(xué)科體系,為之提供研究文本。尤其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大躍進(jìn)”“普查”“搶救”等話語的影響下,“大規(guī)模”搜集整理民間文學(xué)成為國家、民族、學(xué)界的共同訴求。所以,我們經(jīng)歷了多次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運動、工程,這不僅需要各級地方政府以及全國上下大批學(xué)者、搜集整理者、演述人持續(xù)參與,也需要一個能夠動員、組織、協(xié)調(diào)各方力量的團(tuán)體機(jī)構(gòu)。
70年來,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①1950年,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1987年,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改名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本文分別簡稱為“民研會”與“中國民協(xié)”。由于堅持學(xué)術(shù)立會、群眾基礎(chǔ)深厚、團(tuán)體會員廣泛等,一直深度參與中國民間文學(xué)的搜集整理事業(yè),僅從中國民協(xié)首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可看出:1950年民研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周揚(yáng)、郭沫若、老舍的講話都格外強(qiáng)調(diào)了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并公布了《征集民間文藝資料辦法》。事實上,雖然民研會第一屆理事會下設(shè)民間文學(xué)、民間美術(shù)、民間音樂、民間戲劇、民間舞蹈等七個小組,但是,“在其后的發(fā)展中,由于各藝術(shù)門類的協(xié)會相繼成立,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工作范圍則縮小為以搜集研究民間文學(xué)為主。”②劉錫誠:《雙重的文學(xué)——民間文學(xué)+作家文學(xué)》,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6年,第226頁。1958年民研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期間,正值“采風(fēng)運動”興起,全國上下開展了大規(guī)模搜集整理民間文學(xué)的活動。1979年民研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即中國民間文學(xué)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討論、印發(fā)了《全國民間文學(xué)工作十年規(guī)劃》《關(guān)于加強(qiáng)民間文學(xué)工作的幾點建議》。1984年、1991年、2001年中國民協(xié)的第四、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則正是中國民間文學(xué)三套集成工程(簡稱“三套集成”)啟動、全面開展與陸續(xù)完成階段。2006年、2011年、2016年中國民協(xié)第七、八、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與“中國民間文化遺產(chǎn)搶救工程”“中國口頭文學(xué)遺產(chǎn)數(shù)字化工程”密切相關(guān)。可以預(yù)見,在即將召開的中國民協(xié)第十次代表大會上,《中國民間文學(xué)大系》出版工程又會是一個主要議題。
一、從個體到共同體
搜集整理者是上述運動、工程中的主要力量。過往的搜集整理者基本上是“單兵作戰(zhàn)”,如《歌謠》周刊的投稿者多為個人。1949年后,“大規(guī)模”的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則主要依靠調(diào)查隊、調(diào)查組等形式。雖然以集體的形式開展搜集整理工作,但這個群體內(nèi)部極為復(fù)雜。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并非一項專職工作,即使在三套集成時期,中國地方各級政府都成立了“集成辦”,但后期“集成辦”相繼解散,原工作人員被重新分配到當(dāng)?shù)仄渌块T。搜集整理者的自我定位往往也是多元的:文學(xué)的記錄員、地方文化的傳播者、文本闡釋者、民族文化代言人,等等。所以,在具體的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工作中,則需要搜集整理者有相對統(tǒng)一的認(rèn)識論與工作規(guī)范。一個重要的方式是舉辦講習(xí)班,據(jù)筆者不完全統(tǒng)計,20世紀(jì)80年代,民研會云南分會分別在德宏、大理、昆明、麗江、楚雄、文山、紅河、曲靖、昭通、思茅、保山、中甸、玉溪、通海等地舉辦民間文學(xué)講習(xí)班近20次。
這些講習(xí)班一般分為三部分:首先,學(xué)員學(xué)習(xí)民間文學(xué)基礎(chǔ)知識,如民間文學(xué)特征、民間文學(xué)各文類特征、民間文學(xué)與作家文學(xué)關(guān)系以及當(dāng)?shù)氐牡胤轿幕c歷史。當(dāng)然,最主要的是學(xué)習(xí)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原則與技術(shù);其次,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實踐,或請演述人到講習(xí)班上對其直接采錄,或?qū)W員到民間進(jìn)行實地搜集,有時則先在講習(xí)班上采錄練習(xí),由授課教師指導(dǎo),再赴實地搜集;最后,講習(xí)班學(xué)員匯合,進(jìn)行文本整理和工作總結(jié)。許多民間文學(xué)作品都是在講習(xí)班上產(chǎn)生的,如在大理舉辦的講習(xí)班,共搜集了二十多萬字的民間故事以及八萬多行的詩歌。
此外,中國民協(xié)及各地民協(xié)還翻譯、編纂了《征集民間文藝資料辦法》《民間文學(xué)工作者必讀》《民間文學(xué)實習(xí)手冊》《中國民間文學(xué)集成工作手冊》《民俗調(diào)查提綱》等論著與工作手冊,用于指導(dǎo)基層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者。民研會甚至于1985年創(chuàng)辦了民間文學(xué)刊授大學(xué)。
這些講習(xí)班的主講人、工作指導(dǎo)手冊與調(diào)查提綱的撰寫者大多為民間文學(xué)、民俗學(xué)等領(lǐng)域?qū)W者,中國民協(xié)雖為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但主要工作并非學(xué)術(shù)研究,所以需要聯(lián)合大量學(xué)者開展工作。20世紀(jì)80年代初,民研會云南分會剛剛成立,由于缺乏專業(yè)研究者,于是同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研究所云南分所、云南省民族民間文學(xué)研究所合署辦公,即云南民間文學(xué)界經(jīng)常提及的“兩所一會”,三者既分工又合作,“兩所”主要側(cè)重于民間文學(xué)研究與編輯《山茶》雜志,“一會”主要側(cè)重于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兩所”的學(xué)者為搜集整理工作做了理論支撐,“一會”也為學(xué)術(shù)研究提供大量的田野資料,《山茶》雜志當(dāng)時主要稿源也正是出自“一會”所組織的搜集整理者。
所以,我們看到學(xué)者與基層搜集整理者這兩個群體并非相互隔絕,而存在著諸多的交流——面對面或書面的——而中國民協(xié)正是二者之間的“中介機(jī)構(gòu)”,二者在一定限度內(nèi)達(dá)成共識與合作,從整個學(xué)科的角度來看,二者也共同組成了民間文學(xué)這個學(xué)術(shù)共同體。
二、從“十六字方針”到“三性”
在“規(guī)范”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的各種手段中,最有效的方式應(yīng)為制定與普及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原則。
1955年,民研會主辦的《民間文學(xué)》創(chuàng)刊,除發(fā)表民間文學(xué)書面文本、個案研究與理論探討外,還發(fā)表了一系列關(guān)于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問題討論的文章。1955年,董均倫、江源在《民間文學(xué)》上發(fā)表《搜集、整理民間故事的一點體會》一文;1957年,劉魁立發(fā)表《談民間文學(xué)搜集工作——記什么?如何記?如何編輯民間文學(xué)作品?》一文與之爭鳴,隨后引發(fā)一場大討論。此外,當(dāng)時還有劉守華、李岳南、巫瑞書圍繞著李岳南整理的《牛郎織女》的討論。民研會將這些文章集結(jié)成冊出版《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問題》,其中圍繞著調(diào)查、訪談、記錄、翻譯、編輯、潤色、出版等搜集整理環(huán)節(jié)以及民間文學(xué)的人民性、整理與再創(chuàng)作的界限等問題都展開了討論。
這本論文集的首篇文章是《民間文學(xué)》1956年8月號社論,題為《民間文學(xué)需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此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當(dāng)時民研會在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問題上的立場,文章總結(jié)了當(dāng)時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存在“腐朽的學(xué)院氣”與“庸俗社會學(xué)”兩種傾向,并且認(rèn)為“民間文學(xué)的搜集整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危險不是一字不動論,這種迂腐的學(xué)院氣倒還好些;而是庸俗社會學(xué)在作怪。庸俗社會學(xué)在‘左’的詞語的掩護(hù)下,往往可以把讀者唬住。而且庸俗社會學(xué)的觀點也是很容易產(chǎn)生的,它可以產(chǎn)生在‘詞嚴(yán)義正’的教條主義者身上;也可以產(chǎn)生在僅僅是由于政治熱情很高、而又對文藝缺乏基礎(chǔ)知識的人們的身上。”①佚名:《民間文學(xué)需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民間文學(xué)〉1956年8月號社論》,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編:《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問題》第一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年,第5頁。文章還強(qiáng)調(diào)“一起參加民間文學(xué)的搜集、整理工作的人,應(yīng)當(dāng)把它們②指忠實記錄、慎重整理。——筆者注看的像法律一樣尊嚴(yán)”③佚名:《民間文學(xué)需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民間文學(xué)〉1956年8月號社論》,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編:《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問題》第一集,第7頁。。
1958年7月,中國民間文學(xué)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同時也是民研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賈芝作了題為《采風(fēng)掘?qū)殻睒s社會主義民族新文化》的大會報告,這篇后來被不斷引用的文章確立了當(dāng)時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的基本原則:全面搜集、重點整理、大力推廣、加強(qiáng)研究。這“十六字方針”也奠定了中國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工作的基本范式。“采風(fēng)運動”時期,各地搜集整理者并沒有受過太多民間文學(xué)系統(tǒng)訓(xùn)練,但出發(fā)前大都知道這“十六字方針”。
1981年民研會常務(wù)理事會擴(kuò)大會議上,賈芝代表常務(wù)理事會作工作匯報,提出在普查的基礎(chǔ)上編輯《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民歌、民謠集成》《中國諺語大觀》。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國家民委與民研會聯(lián)合簽發(fā)《關(guān)于編輯出版〈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中國歌謠集成〉、〈中國諺語集成〉的通知》[文民字(84)808號],即學(xué)界經(jīng)常提及的“808號文件”,這標(biāo)志著中國民間文學(xué)三套集成工作正式啟動。此時搜集整理者更多,學(xué)界對民間文學(xué)的認(rèn)識論也發(fā)生了轉(zhuǎn)換。所以,科學(xué)性、全面性與代表性的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與編選原則被提出與推廣。
顯然,“三性”原則是“十六字方針”的延續(xù),全面性大致對應(yīng)全面搜集,代表性大致對應(yīng)重點整理,而被置于“三性”之首的科學(xué)性則代表著此后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的重要轉(zhuǎn)向。正如云南民協(xié)的佘仁澍所說:“科學(xué)性是核心,這個基點解決了,全面性、代表性也就容易做到了。”④佘仁澍:《關(guān)于民間文學(xué)集成的“三性”問題》,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云南分會、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學(xué)會云南分會編:《云南民族民間文學(xué)通訊》,內(nèi)部資料,第6期。
科學(xué)性不僅意味著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流程要符合科學(xué)規(guī)范,還意味著要加強(qiáng)對民間文學(xué)的科學(xué)研究,更是在民間文學(xué)的民俗學(xué)轉(zhuǎn)向背景下,強(qiáng)調(diào)民間文學(xué)與民俗、宗教、歷史事件的關(guān)系。換言之,科學(xué)性在此更意味著新的學(xué)科性。甚至此后“‘搜集’‘整理’‘改編’等話語漸趨隱匿,田野研究逐漸取代采風(fēng)模式”①毛巧暉:《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七十年》,《民間文化論壇》,2019年第6期。。
1985年6月,民研會云南分會在昆明召開了第一次民俗學(xué)學(xué)術(shù)討論會。江應(yīng)樑在會上說:“搞民間文學(xué)的人不掌握民俗學(xué),民間文學(xué)中的許多問題就無法解釋。就是說,民俗學(xué)與民間文學(xué)有很密切的關(guān)系,它對民間文學(xué)起很大的作用。”②江應(yīng)樑:《談民俗學(xué)研究》,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云南分會、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學(xué)會云南分會編:《云南民族民間文學(xué)通訊》,內(nèi)部資料,第6期。《白族神話傳說集成》被作為三套集成工作的優(yōu)秀范例優(yōu)先出版,并獲得一致好評,其中主要原因正是書中64篇神話傳說作品均附有附記,還提供了27篇異文。這些附記提供了與作品相關(guān)的演述人、民俗、宗教、歷史背景資料。如書中《狩獵神話》文末又描述了云龍白族祭祀獵神的流程與祭文,又如《繞山林》這個文本只占一頁篇幅,文末的附記卻占兩頁多。
當(dāng)然,制定搜集整理原則本身就意在強(qiáng)調(diào)搜集整理活動的科學(xué)性,這些原則將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活動制度化,并與其他領(lǐng)域的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如作家、編劇采風(fēng))區(qū)分開來。這些原則的制定者與闡釋者宣稱搜集整理者只有依靠這些原則才能更加有效地、科學(xué)地開展搜集整理工作,而只有通過這些原則制作出來的文本才可被稱為科學(xué)或?qū)W科意義上的民間文學(xué)。大部分搜集整理者對民間文學(xué)的認(rèn)識也是透過這些搜集整理原則達(dá)成的,搜集整理原則在此成為一個透鏡,即通過這些搜集整理原則發(fā)現(xiàn)有價值的民間文學(xué)文本。
三、從“科學(xué)性”到“文學(xué)性”
然而,民間文學(xué)書面文本的價值從來不僅僅是為了學(xué)術(shù)研究,1922年《歌謠》周刊發(fā)刊詞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時搜集歌謠的目的共有兩種:一是學(xué)術(shù)的,一是文藝的。20世紀(jì)50年代末的新民歌被認(rèn)為是一種“嶄新的文學(xué)形式”,是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jié)合的詩歌。三套集成時期,雖然“科學(xué)性”被置于核心位置,但“可讀性”也成為一個重要的編選標(biāo)準(zhǔn)。曾任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的董森也談到:“胡喬木同志曾經(jīng)打過一個比方:民間文學(xué)就像一枚銅板,一面是文學(xué)性,另一面是科學(xué)性,兩者是絕對不能分開的。離開了文學(xué)性就不是故事了,離開科學(xué)性就不是民間的了。”③董森:《閱盡千帆始識君,褪去浮華歸本真》,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編:《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70年學(xué)術(shù)史》,北京:學(xué)苑出版社,2020年,第27頁。
中國民協(xié)在組織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工作中,也在不斷探索科學(xué)性與可讀性、資料與作品、學(xué)術(shù)與大眾之間的平衡,“二者兼具”被認(rèn)為是成功的民間文學(xué)書面文本。陶陽在評論前文提到的《白族神話傳說集成》時說:“總之,‘云南民間文學(xué)集成’既有可讀性,又有很高的研究價值。我認(rèn)為這是一次成功的嘗試,值得參考。”④陶陽:《一次成功的嘗試——讀〈云南民間文學(xué)集成〉》,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云南分會、云南民間文學(xué)集成編輯辦公室、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學(xué)會云南分會編:《云南民族民間文學(xué)通訊》,內(nèi)部資料,第9期。
為了使由口頭文本轉(zhuǎn)換過來的書面文本具有可讀性,“采風(fēng)運動”中各調(diào)查隊的主要成員往往是高校中文系學(xué)生,他們被認(rèn)為具有比較強(qiáng)的文字功底與文學(xué)素養(yǎng)。三套集成時期的搜集整理者中有大量的文學(xué)愛好者,甚至是已經(jīng)發(fā)表過作品的作家。事實上,這其中有相當(dāng)一部分人將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看作是一種文學(xué)創(chuàng)作實踐,想要從中尋找靈感與素材。陶陽在大學(xué)畢業(yè)后被分配到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但后來他又主動選擇到《民間文學(xué)》做編輯工作,他說:“雖不是理想工作,但可下鄉(xiāng)采風(fēng),有了生活也可創(chuàng)作,另外,還可像普希金一樣運用民間故事素材創(chuàng)作童話詩。”①陶陽:《我與民間文學(xué)》,賈芝主編:《新中國民間文學(xué)五十年》,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509頁。一些被認(rèn)為重要的民間文學(xué)在整理的最后階段甚至專門邀請作家加入整理團(tuán)隊,如《阿詩瑪》1954年版、《梅葛》1960年版分別請來公劉、李鑒堯做了修改潤色。
民間文學(xué)書面文本的文學(xué)性不僅指其語詞達(dá)雅、情節(jié)豐富、結(jié)構(gòu)完善,還需要將之傳播到大眾,以供民眾閱讀。鐘敬文曾總結(jié)民間文學(xué)書面文本的功用:“首先,它是民間文藝學(xué)者、一般文學(xué)研究者、文學(xué)史家、民族學(xué)者、民俗學(xué)學(xué)者、文化史學(xué)者以及語音學(xué)者等的研究資料(全面的或部分的)。他們要從它上面發(fā)現(xiàn)各種人民所希望知道的規(guī)律。其次,它是提供編纂廣大群眾,特別是億萬青少年學(xué)習(xí)的文學(xué)讀本的重要資源。再次,它是我們各種文學(xué)體裁的作家創(chuàng)作上取材的來源之一……”②鐘敬文:《關(guān)于故事記錄的忠實性問題》,《山茶》,1980年第2期。
作為學(xué)術(shù)研究資料的民間文學(xué)被書面文本化后,自有研究者主動查找、檢索與使用,但作為文學(xué)讀本的民間文學(xué)作品卻需要對其進(jìn)行推廣與傳播。中國民協(xié)出版了大量的民間文學(xué)作品,如《民間文學(xué)》雜志、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等曾經(jīng)都是發(fā)表民間文學(xué)作品的主要陣地,“民間文學(xué)叢書”“中國民間文學(xué)三套集成”《中國民間故事全書》等也集中出版了大量的民間文學(xué)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jì)80年代初,各地民研會分會也開始創(chuàng)辦各自的民間文學(xué)報刊,如《民間故事選刊》(河北)、《山西民間文學(xué)》(山西)、《塞風(fēng)》(內(nèi)蒙古)、《遼寧民間文學(xué)》(遼寧)、《吉林民間文學(xué)叢刊》(吉林)、《黑龍江民間文學(xué)》(黑龍江)、《采風(fēng)》(上海)、《江蘇民間文學(xué)》(江蘇)、《山海經(jīng)》(浙江)、《鄉(xiāng)音》(安徽)、《故事林》(福建)、《故事家》(河南)、《楚風(fēng)》(湖南)、《天南》(廣東)、《百越民風(fēng)》(廣西)、《南風(fēng)》(貴州)、《甘肅民間文學(xué)叢刊》(甘肅)等。這些刊物都立足本地,兼顧民間文學(xué)作品與理論研究文章。而且,其中許多刊物與當(dāng)時的三套集成結(jié)合,其主要稿源正是三套集成工作的成果。
我們會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形容民間文學(xué)的搜集路徑,70年來,中國民協(xié)貫通了這條路徑③僅從機(jī)構(gòu)構(gòu)成來看,中國民協(xié)現(xiàn)有團(tuán)體會員32個,能夠充分做到上下連接、通暢溝通,甚至地處中緬邊境的瑞麗縣1979年就成立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瑞麗小組。,通過民間文學(xué)將國家與民間、學(xué)者與基層搜集整理者、學(xué)術(shù)與文學(xué)關(guān)聯(lián)起來,也就是說,民間文學(xué)成為了國家的公共文化,基層搜集整理者與學(xué)者共同組成了民間文學(xué)的學(xué)術(shù)共同體,民間文學(xué)書面文本既是學(xué)術(shù)研究的資料,又是大眾的文學(xué)讀物。布迪厄曾將知識場域分為“有限生產(chǎn)”與“大生產(chǎn)”,前者主要針對專業(yè)研究,后者則是滿足政治、經(jīng)濟(jì)、大眾的需求。④參見[法]皮埃爾·布爾迪厄:《藝術(shù)的法則——文學(xué)場的生成與結(jié)構(gòu)》,劉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264—265頁。中國民協(xié)也在一定程度上連結(jié)了這兩種生產(chǎn),一方面,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既是一項技術(shù)性活動,又是一項學(xué)術(shù)性活動,搜集整理過程也是知識生產(chǎn)的過程,民間文學(xué)的若干學(xué)科問題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生發(fā)出來的,如書面文本的“格式化”、文類的模糊性、“以傳統(tǒng)為取向的文本”等等;另一方面,中國民協(xié)通過對民間文學(xué)的搜集整理,民眾的口頭藝術(shù)被帶入到更為廣闊的現(xiàn)代、政治、商業(yè)語境中,從而被確立為“民族經(jīng)典”,被命名為“非遺”,被跨文化重述,被跨媒介傳播等。“‘搜集整理’是中國特色的學(xué)術(shù)話語,彰顯了民間文學(xué)文藝價值、文化遺產(chǎn)價值、社會認(rèn)同價值和學(xué)術(shù)價值的多棱面向。”①漆凌云:《新文藝·民族遺產(chǎn)·學(xué)術(shù)研究——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的三重旨向》,《民間文化論壇》,2020年第4期。從學(xué)術(shù)團(tuán)體的角度觀照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歷史,我們更能發(fā)現(xiàn)這些價值的彰顯。
本文作為一篇筆談,無意全面梳理中國民協(xié)70年來民間文學(xué)搜集整理工作的重要事件與成就,如格薩爾史詩的搜集整理、民間文學(xué)數(shù)字化建檔工作等重要活動本文就暫未述及,但是通過片段性的采擷,我們?nèi)匀豢梢钥吹街袊駞f(xié)對民間文學(xué)的搜集整理構(gòu)成了中國民間文學(xué)重要的學(xué)科傳統(tǒng),培養(yǎng)了大批搜集整理者,一些人甚至“搜而優(yōu)則研”,成為專業(yè)的研究者,而積累起來的書面文本也成為學(xué)界與民眾最為豐厚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