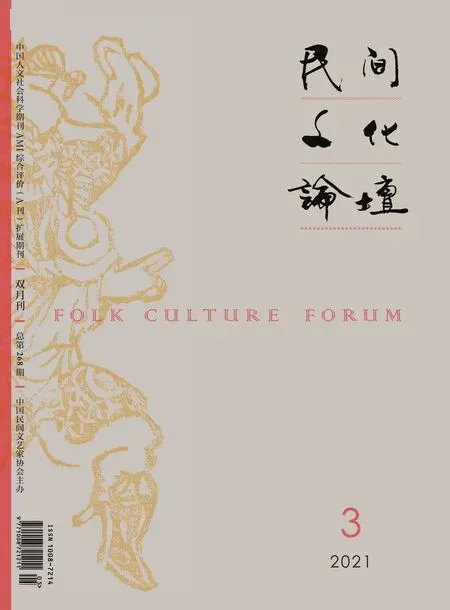影視人類學(xué)發(fā)展的四個(gè)時(shí)期及其觀念基礎(chǔ)
龐 濤
一、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的觀念之爭(zhēng)與影像民族志方法的演進(jìn)
民族志電影一問世就背負(fù)著人們對(duì)他的種種期望:民族志電影能夠提示出其他手段很難把握的原始文化的某些特征,甚至最終能呈現(xiàn)出文化的全貌,民族志電影通常被定義為表現(xiàn)文化模式的影片。①[英]艾米麗·德·布里加德:《民族志電影史》,載[美] 保羅·霍金斯主編:《影視人類學(xué)原理》,王筑生等編譯,昆明:云南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第3頁。
早期人類學(xué)家意識(shí)到攝影機(jī)有助于他們的田野工作,像古典進(jìn)化論代表人物阿爾弗雷德·哈登和鮑德溫·斯賓塞,以及早期在北美研究因紐特人的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等相信攝影機(jī)是一種客觀的圖像資料記錄手段。格雷戈里·貝特森與瑪格麗特·米德也在田野工作中利用電影攝影機(jī)觀察心理的和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內(nèi)容。民族志影片(Ethnography Film),也被稱為人類學(xué)影片(Anthropology Film),始終伴隨著人類學(xué)學(xué)者的田野調(diào)查和民族志的撰寫,在整個(gè)20世紀(jì),民族志電影在西方社會(huì)掀起過幾次熱潮,進(jìn)入電影院,形成公眾話題,出現(xiàn)了法國(guó)巴黎人類學(xué)電影節(jié)、美國(guó)紐約瑪格麗特·米德電影節(jié)等多個(gè)著名人類學(xué)電影節(jié)。20世紀(jì)后期,影視人類學(xué)(Visual Anthropology)開始出現(xiàn)在文化人類學(xué)的學(xué)術(shù)共同體。民族志電影(Ethnographic Film)、人類學(xué)電影(Anthropology Film)和影像民族志(Visual Ethnography)這幾個(gè)名稱所指內(nèi)容都是一致的;關(guān)鍵詞影像和民族志,是影視人類學(xué)最核心的方法和成果。為了便于在影像民族志演進(jìn)過程中把握影視人類學(xué)發(fā)展脈絡(luò),我們可以參照高丙中對(duì)民族志發(fā)展的三個(gè)時(shí)代的表述:“業(yè)余民族志、科學(xué)民族志和反思民族志”②高丙中:《民族志發(fā)展的三個(gè)時(shí)代》,《廣西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bào)》 (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6年第5期。,把影像民族志發(fā)展過程劃分為:“業(yè)余影像民族志”“專業(yè)影像民族志”“后現(xiàn)代實(shí)驗(yàn)影像志”和本文討論的“后現(xiàn)代后”或“新時(shí)期影像民族志”幾個(gè)時(shí)期,以方便討論以影像民族志為主要方法的影視人類學(xué)理論和觀念的演進(jìn)脈絡(luò)。
文化人類學(xué)自從誕生之日起,就以社會(huì)文化為研究對(duì)象,力圖通過對(duì)異文化的研究,揭示出人類一些普遍性的東西。像人類學(xué)一樣,也是先有影像民族志很久才有了影視人類學(xué)。①高丙中:“先有民族志很久了才有人類學(xué)。但是經(jīng)過專業(yè)訓(xùn)練的人類學(xué)者來撰寫民族志,民族志的發(fā)展就進(jìn)入了一個(gè)新的時(shí)代,也就是通過學(xué)科規(guī)范支撐起‘科學(xué)性’的時(shí)代”。參見高丙中:《民族志發(fā)展的三個(gè)時(shí)代》,《廣西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6年第5期。受過專業(yè)訓(xùn)練的人員開始使用影像民族志方法進(jìn)行田野工作,影像民族志就進(jìn)入了所謂的“專業(yè)影像民族志”時(shí)期。當(dāng)時(shí),“民族志電影通常界定為表現(xiàn)文化模式的影片”。我們可以表述為:專業(yè)影像民族志時(shí)期的“呈現(xiàn)社會(huì)文化模式”階段,具有較強(qiáng)的理性主義目的和追求普遍性的動(dòng)機(jī)。早期人類學(xué)家意識(shí)到攝影機(jī)有助于他們的田野工作,可以進(jìn)行更全面的民族志描寫。但在這之后,人類學(xué)有了顯著的變化,從呈現(xiàn)大量詳細(xì)的民族志材料,轉(zhuǎn)向更加理性化的探討,即科學(xué)主義時(shí)期。但影像民族志的科學(xué)性嘗試并不那么成功,因?yàn)閿z影機(jī)是資料收集設(shè)備,把它作為理論思考的媒介似乎有很大局限性。“從根本上說,這是因?yàn)槟菚r(shí)人類學(xué)理論雄心與民族志電影所能傳達(dá)的知識(shí)之間有根本的不協(xié)調(diào),所有戰(zhàn)后主要的理論模式,不管是功能主義、結(jié)構(gòu)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huì)生態(tài)學(xué)或他們中的一個(gè)或多個(gè)的混合都是限制于抽象和概括的原理之上的”②參見[英]保羅·亨利:《民族志電影:技術(shù)、實(shí)踐和人類學(xué)理論》,載莊孔韶主編:《人類學(xué)經(jīng)典導(dǎo)讀》,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第579頁。。在這樣的境況下,作為描述異文化模式的這些“他者”的影像被質(zhì)疑是否只適于描述現(xiàn)實(shí)事項(xiàng),或表現(xiàn)主觀感覺和個(gè)體情感。它的辨析能力,即辯證地呈現(xiàn)材料,發(fā)現(xiàn)、提煉和概括一個(gè)體系的概念的能力并不被科學(xué)主義認(rèn)可。影像民族志陷入人類學(xué)家理論野心造成的迷失之中。
在人類學(xué)理論發(fā)展的過程中,始終伴隨著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爭(zhēng),普遍主義追求普遍化的科學(xué)式結(jié)論,目的是發(fā)現(xiàn)人類文化的同一性本質(zhì)和普遍性規(guī)律。而特殊主義強(qiáng)調(diào)重視各種不同文化對(duì)普適性問題的特殊性回答即文化間的差異性,主張進(jìn)行具體細(xì)致的田野個(gè)案考察,重視經(jīng)驗(yàn)研究,相對(duì)輕視做宏大的理論性建構(gòu)。20世紀(jì)前半期,美國(guó)文化人類學(xué)家弗朗茨·博厄斯提出歷史特殊論,主張“各個(gè)種族或民族的智力在本質(zhì)上沒有差別,各個(gè)民族的文化也沒有高低與好壞,進(jìn)步與落后之分,任何一種文化都有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獨(dú)特之處,都有其存在的價(jià)值和尊嚴(yán),因而不同民族文化之間沒有普遍的絕對(duì)的衡量標(biāo)準(zhǔn),一切評(píng)價(jià)標(biāo)準(zhǔn)都是相對(duì)的”③[美] 弗朗茲·博厄斯:《人類學(xué)與現(xiàn)代生活》,劉莎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年,第131頁。。文化相對(duì)主義逐漸成為當(dāng)代人類學(xué)的主要思想觀念,也是人類學(xué)進(jìn)行異文化或本土文化研究的方法和理論。在“我者—他者”“本文化—異文化”這樣的跨文化二元認(rèn)識(shí)模式中,尋求人類生活的意義和邏輯,反思各種文化中心主義、種族主義乃至霸權(quán)主義。在文化相對(duì)主義觀念下,影像民族志更注重在田野中對(duì)“異文化”進(jìn)行細(xì)致深入的觀察與描寫。這個(gè)階段可以稱之為專業(yè)影像民族志時(shí)期中的“觀察式”影片階段。觀察式影像民族志強(qiáng)調(diào)田野中的同步參與和深入的觀察,這些特征都與文化人類學(xué)的研究方法基本相似。
二、文化相對(duì)主義建構(gòu)了專業(yè)影像民族志的基本觀念
文化相對(duì)主義在普遍與特殊之爭(zhēng)中逐漸成為主導(dǎo)西方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近百年的思想理論,“成為文化民族主義、文化多樣性理論、文化多元論、多元文化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等的一個(gè)重要理論來源”①參見楊須愛:《文化相對(duì)主義的起源及早期理念》,《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意大利哲學(xué)家維柯(Giambattista Vico)曾說,“生活經(jīng)驗(yàn)或許依舊是‘不可讓渡的’,所以我們不能直接分享他人的經(jīng)驗(yàn)”②[英]奈杰爾·拉波特、喬安娜·奧佛林:《社會(huì)文化人類學(xué)的關(guān)鍵概念》,鮑雯妍、張亞輝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年,第251頁。。人類學(xué)家也希望影像能促進(jìn)跨文化理解。沃爾特·戈德施米特提出:“向?qū)儆谝环N文化的人們解釋屬于另一種文化的人們行為的行為,這樣的電影就是民族志電影。”③[意]保羅·基奧齊:《民族志電影的起源》,知寒譯,《民族譯叢》,1991年第1期。大衛(wèi)·麥克杜格也曾表示,“民族志電影可以寬泛地定義為向一個(gè)社會(huì)揭示另外一個(gè)社會(huì)文化的任何電影”④轉(zhuǎn)引自徐菡:《西方民族志電影經(jīng)典》,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頁。。跨文化理解一直是人類學(xué)的主要課題,大衛(wèi)·麥克杜格認(rèn)為“一種文化的要素有時(shí)無法用另一種文化的思想方法來描述,為此民族志電影的拍攝必須設(shè)法讓觀眾體驗(yàn)和了解其拍攝對(duì)象的社會(huì)經(jīng)驗(yàn)”⑤[澳]大衛(wèi)·麥克道格:《跨越觀察法的電影》,王慶玲、蔡家麒譯,載[美] 保羅·霍金斯主編:《影視人類學(xué)原理》,王筑生等編譯,第134頁。。影像民族志在田野工作時(shí)強(qiáng)調(diào)浸入他者的精神世界,以“主位”視角理解人們的觀念,“參與式觀察”成為這個(gè)時(shí)期影像民族志工作的主要田野工作方法。
伴隨著二戰(zhàn)后西方學(xué)術(shù)界出現(xiàn)的多元文化主義和文化多樣性理論,文化相對(duì)主義在多民族國(guó)家內(nèi)部完成了從學(xué)術(shù)觀念向政治倫理層面的擴(kuò)展。影視人類學(xué)也從呈現(xiàn)文化模式樣貌轉(zhuǎn)向闡釋文化差異的文化相對(duì)主義知識(shí)模式。因?yàn)槠毡橹髁x易使影視人類學(xué)建構(gòu)的學(xué)科知識(shí)體系傾向文化中心主義,影視人類學(xué)開始基于象征符號(hào)等理論來建構(gòu)文化表征論的影像民族志文化闡釋模式。因把文化當(dāng)成意義系統(tǒng),所以影像民族志重視呈現(xiàn)“本土人的思想觀念”來達(dá)成“主位”視角。文化相對(duì)主義對(duì)影視人類學(xué)的進(jìn)一步促進(jìn),使一種分享人類學(xué)影像志類型出現(xiàn),目的是使得人類學(xué)家及其研究對(duì)象之間建立起一種新型的合作關(guān)系。“觀察者終于走下了象牙塔,他的攝像機(jī)和他的放映機(jī)使他開創(chuàng)了一條進(jìn)入知識(shí)核心的道路,他的成果首次不是由一個(gè)學(xué)術(shù)委員會(huì)來評(píng)判,而是由他所研究的人來評(píng)判。在這個(gè)方法里,電影將幫助我們分享人類學(xué)”⑥參見[法]讓·魯什:《攝影機(jī)和人》,蔡家麒譯,載[美] 保羅·霍金斯主編:《影視人類學(xué)原理》,王筑生等編譯,第98頁。。這樣“分享”就與“參與”和“觀察”一起構(gòu)成“專業(yè)影像民族志”后期的主要形態(tài),這個(gè)時(shí)期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后現(xiàn)代思潮帶來的對(duì)科學(xué)主義的進(jìn)一步反思。
從科學(xué)主義轉(zhuǎn)向人文主義,人類學(xué)家從抽象的理論轉(zhuǎn)而解釋具體的文化事實(shí),使他者化影像表述具有了知識(shí)的辯護(hù)和生產(chǎn)能力,影視人類學(xué)由此真正獲得了學(xué)科意義,民族志影片逐漸具有了其“獨(dú)立的學(xué)術(shù)人格”(羅紅光語)。這樣,影視人類學(xué)開始在理論雄心挫敗的焦慮中尋回探知人性的初心。
影像民族志發(fā)展的第三個(gè)階段是“后現(xiàn)代實(shí)驗(yàn)影像志”時(shí)期,即源自所謂的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領(lǐng)域的“表征危機(jī)”之后的人類學(xué)文化批評(píng)運(yùn)動(dòng)。它源于人類學(xué)面臨的新挑戰(zhàn):“社會(huì)科學(xué)是否能夠充分而又恰切地描述社會(huì)?以及對(duì)描述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的手段之充分懷疑”①參見[美]喬治·E·馬爾庫(kù)斯、米開爾·M·J·費(fèi)徹爾:《作為文化批評(píng)的人類學(xué)》 ,王銘銘、藍(lán)達(dá)居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第 159頁。。在人類學(xué)則是由科學(xué)民族志引發(fā)的“表述的危機(jī)”。后現(xiàn)代人類學(xué)提出要以實(shí)驗(yàn)民族志代替現(xiàn)實(shí)主義民族志和闡釋主義的民族志,實(shí)驗(yàn)的動(dòng)機(jī)來自于對(duì)民族志解釋方法對(duì)文化差異表述能力的不滿足。帶有強(qiáng)烈反思性的實(shí)驗(yàn)民族志,更加強(qiáng)調(diào)民族志文本形式的重要性,提倡民族志寫作過程中將詩(shī)學(xué)、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和史學(xué)等結(jié)合,以描述民族志對(duì)象與更廣泛的社會(huì)歷史政治經(jīng)濟(jì)過程的聯(lián)系。大衛(wèi)·麥克道格曾認(rèn)為:“與其爭(zhēng)取滲透了人類學(xué)原理的成熟的影視人類學(xué),還不如解釋一個(gè)田野工作者通過運(yùn)用視覺媒體反思人類學(xué)時(shí)所涉及的原理”②[英]保羅·亨利:《民族志電影:技術(shù)、實(shí)踐和人類學(xué)理論》,載莊孔韶主編:《人類學(xué)經(jīng)典導(dǎo)讀》,第578頁。。反思民族志表現(xiàn)為實(shí)驗(yàn)民族志形態(tài),這是20世紀(jì)70年代中期興起的一種后現(xiàn)代主義人類學(xué)轉(zhuǎn)向,通過對(duì)民族志知識(shí)的本質(zhì)進(jìn)行追問,實(shí)現(xiàn)反思本文化的目的。實(shí)驗(yàn)影像民族志一般通過建構(gòu)對(duì)話或合作式文本書寫形態(tài),進(jìn)行自我反思,建構(gòu)多聲道發(fā)聲的多主體敘述。③參見富曉星:《作為行動(dòng)者的攝影機(jī):影視人類學(xué)的后現(xiàn)代轉(zhuǎn)向》,《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
在我國(guó),影像民族志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對(duì)田野工作和專業(yè)影像民族志撰寫中忽略的各主體權(quán)利關(guān)系。而基于文化批評(píng)提出的較嚴(yán)苛的相對(duì)主義條件,影像民族志多選擇回避的態(tài)度,因?yàn)橄鄬?duì)于文本,影像志民族志還沒有建構(gòu)起成熟的思辨模式,并且民族志對(duì)象在影像志表述過程中能得到更多的主體性展示。后現(xiàn)代主義人類學(xué)把重點(diǎn)放在民族志的寫作方式和文化批評(píng)上,期望通過各種包含有多種聲音的對(duì)話模式和多樣化寫作方式的實(shí)驗(yàn)民族志文本,反映被研究者個(gè)體內(nèi)在的觀念世界,取代追求建構(gòu)宏觀理論、整體觀、客觀性而忽視主體性的傳統(tǒng)民族志。后現(xiàn)代主義影視人類學(xué)的重要貢獻(xiàn),是為影像民族志從傳統(tǒng)的遠(yuǎn)方他者文化轉(zhuǎn)向關(guān)注我們自己,并為影像民族志本土化研究提供文化批評(píng)的理論和實(shí)踐方法。④參見龐濤:《影像民族志本土化研究的兩種路徑》,《廣西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8年第6期。后現(xiàn)代影像民族志不再追求科學(xué)實(shí)證的意義,而是轉(zhuǎn)向一種帶有文學(xué)修辭色彩的詩(shī)學(xué)和隱含政治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話語。雖然現(xiàn)代經(jīng)典民族志作為文體也是敘事性的,但因其“元敘事(大敘事)”色彩——一種權(quán)威性話語,被后現(xiàn)代主義抵制。“過去二十多年間,作為研究方法的影視人類學(xué),越來越多地成為了研究者、‘主人公’和(想象的)觀眾之間批評(píng)性協(xié)商的表述過程”⑤[荷蘭]梅婕·帕斯特瑪:《影視人類學(xué)的趨向:政治、美學(xué)和認(rèn)識(shí)論》,張靜紅譯,《電影藝術(shù)》,2020年第1期。。
三、后現(xiàn)代文化批評(píng)與文化相對(duì)主義絕對(duì)化
“現(xiàn)代人類學(xué)所堅(jiān)持的是淺層文化相對(duì)主義,即承認(rèn)并尊重世界上存在多種文化,認(rèn)為文化的形式和路徑有不同,但是多種文化的背后,規(guī)律和法則應(yīng)該是具有統(tǒng)一性的;后現(xiàn)代人類學(xué)則主張深層文化相對(duì)主義,既堅(jiān)持文化形式的多樣性又否定文化規(guī)律的統(tǒng)一性”⑥張連海:《從現(xiàn)代人類學(xué)到后現(xiàn)代人類學(xué):演進(jìn)、轉(zhuǎn)向與對(duì)壘》,《民族研究》,2013年第6期。。后現(xiàn)代民族志的論述是建立在一種將權(quán)利與知識(shí)相關(guān)聯(lián)的基礎(chǔ)上,這種知識(shí)論的泛權(quán)力主義觀點(diǎn)往往衍生出絕對(duì)化的相對(duì)主義,這種相對(duì)主義聲稱除了本文化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不能用其他文化的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判斷,也稱“倫理相對(duì)主義”。受后現(xiàn)代以及“東方學(xué)”的影響,本土性和地方性作為對(duì)抗現(xiàn)代性的工具,“‘權(quán)力關(guān)系’也被用來替代包括地方知識(shí)或本土知識(shí)與外來知識(shí)之間的關(guān)系。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一個(gè)根本缺陷是將多樣的關(guān)系特征化約為‘支配/抵抗’關(guān)系”①朱曉陽、譚穎:《對(duì)中國(guó)“發(fā)展”和“發(fā)展干預(yù)”研究的反思》,《社會(huì)學(xué)研究》,2010年第4期。,從而走向絕對(duì)化的相對(duì)主義。絕對(duì)化的相對(duì)主義表現(xiàn)為對(duì)地方知識(shí)的理想化幻想,以反抗現(xiàn)代文明,以“他者的智慧”對(duì)抗普遍性經(jīng)驗(yàn)。極端相對(duì)主義強(qiáng)調(diào)個(gè)殊,拒絕普同,自我封閉,容易陷入我族中心主義。
文化相對(duì)主義認(rèn)為人類學(xué)的知識(shí)都是地方知識(shí),本土化、地方性和多樣化成為影像民族志文化描寫的學(xué)術(shù)取向,因而“地方知識(shí)”也就成了影像民族志的核心內(nèi)容。在“地方性(特殊性)”與“普遍性(普適性)”這對(duì)二元關(guān)系中,影像民族志受其具體化而非概括性的人文主義敘事方式的制約,自然地選擇了“地方知識(shí)”來形成學(xué)術(shù)意義,容易忽略建構(gòu)地方知識(shí)與普遍性經(jīng)驗(yàn)的對(duì)話的努力。當(dāng)這種二元關(guān)系傾向一方時(shí),影像民族志開始在有意無意地建構(gòu)“神圣的他者智慧”。
相對(duì)于文本民族志,后現(xiàn)代影像民族志更注重地方知識(shí)的描述與呈現(xiàn),避免概括闡釋,強(qiáng)調(diào)主位觀點(diǎn),抑制客位表達(dá),以期形成客觀性文體。在影視人類學(xué)里也多少注入了這種預(yù)設(shè):嘗試在外部視角進(jìn)行解釋性努力,實(shí)際上是某種文化霸權(quán)。認(rèn)為地方知識(shí)只有本地人才能認(rèn)識(shí)和持有,只能由他們自己來表述。觀察者敬懾“神圣的他者智慧”而不作為,只能直接記錄。這樣,作為影像民族志對(duì)象的地方社會(huì)及其特征,我們稱為“地方性”,在后現(xiàn)代語境下容易被影像志絕對(duì)化。即地方性文化只存在于“地方”,而不存在于“世界”。
另一方面,由于跨文化判斷的鴻溝,即維柯所言經(jīng)驗(yàn)是不可讓渡的,專業(yè)影像民族志希望的跨文化解釋行為,在實(shí)踐中總是停留在異文化現(xiàn)象的呈現(xiàn)上,受眾在文化差異的震撼中,依然缺乏一些“點(diǎn)撥”來頓悟他者生存的邏輯,或者說影像民族志缺乏在“理性”方向上努力。民族志電影發(fā)展到20世紀(jì)后期開始表現(xiàn)低迷,依民族志電影發(fā)展起來的影視人類學(xué)(Visual Anthropology)也一直沒有闡明學(xué)術(shù)本體。在西方,Visual Anthropology也包含著影像民族志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與視覺文化研究的“分杈”②參見鮑江:《本體論分杈: 影視人類學(xué)與文字人類學(xué)》,《中央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8年第6期。。“視覺人類學(xué)”關(guān)注的是人類社會(huì)中通過視覺手段溝通的表意系統(tǒng)。在中文語境下,“影視人類學(xué)”與“視覺人類學(xué)”反映了兩種不同的學(xué)術(shù)旨趣,區(qū)別是是否強(qiáng)調(diào)影像民族志實(shí)踐。“視覺人類學(xué)”是以 “去情景化”(如 “文化”“關(guān)系”“生計(jì)”“日常”“空間”“傳統(tǒng)”等)追求理論一般化。相比視覺人類學(xué)的理論雄心,影視人類學(xué)更多的是以經(jīng)驗(yàn)研究方式從實(shí)踐的角度尋找從田野工作獲得知識(shí)的方法。
最近視覺人類學(xué)經(jīng)常被放在人類學(xué)感官轉(zhuǎn)向的話語下加以討論。感官人類學(xué)是以“人類學(xué)身體”為研究對(duì)象,認(rèn)為人類的感覺既是身體行為,也是文化行為。人們的潔凈感、性感、饑餓感、美感等知覺現(xiàn)象,在文化意涵上與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等生理現(xiàn)象相關(guān)聯(lián),其中視覺研究是重要的文化研究途徑。感官民族志強(qiáng)調(diào)田野中的感官體驗(yàn)和策略性實(shí)踐,所以感官民族志是一種文化批評(píng)。③參見張連海:《感官民族志:理論、實(shí)踐與表征》,《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感官人類學(xué)面臨的挑戰(zhàn)在于“將單一感官脫離人們?nèi)粘I顚用娴难芯糠椒ǎy以迎合人類學(xué)從日常生活層面探討文化理論的旨趣”①?gòu)堖B海:《感官民族志:理論、實(shí)踐與表征》,《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身體感的研究視角很大程度挑戰(zhàn)文化相對(duì)主義傳統(tǒng),由于身體技能因文化而呈現(xiàn)差異,掌握身體技能之高低有無,影響到社會(huì)階層秩序以及權(quán)利和資源的分配。感官民族志對(duì)多感官的探索使學(xué)術(shù)任務(wù)變得復(fù)雜,從而凸顯現(xiàn)有的民族志表征方法和流派的不足,如何表征與知覺相關(guān)的知識(shí)成為難題”。②同上。
在西方,Visual Anthropology一詞既包含有人類學(xué)影像民族志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又含有后來衍生出的從文本人類學(xué)分離出來進(jìn)行學(xué)科化理論化的抱負(fù)和追求。這就是為什么西方人類學(xué)在有影像民族志方法很久才出現(xiàn)Visual Anthropology一詞。在中國(guó),Visual Anthropology被引入時(shí)被翻譯為“影視民族學(xué)”和“影視人類學(xué)”,可以理解為當(dāng)時(shí)我國(guó)學(xué)者把影像民族志方法作為學(xué)科的本體。近來國(guó)內(nèi)有學(xué)者按英文字面直譯為“視覺人類學(xué)”,目的是利用視覺研究的科學(xué)主義色彩來發(fā)展學(xué)科理論。在學(xué)科本體上,“影視人類學(xué)”與“視覺人類學(xué)”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學(xué)術(shù)取向和研究路徑,“影視人類學(xué)”是基于文化相對(duì)主義的二元認(rèn)識(shí)論和人文主義觀念,尋求影像化的跨文化理解方式。“視覺人類學(xué)”傾向于科學(xué)主義的一元論認(rèn)識(shí)框架,采用的是文本式的辨析方式,其無法涵蓋英文Visual Anthropology所包含的人類學(xué)民族志的經(jīng)驗(yàn)研究傳統(tǒng)。
國(guó)內(nèi)有學(xué)者解釋近來影像民族志在西方人類學(xué)界邊緣化現(xiàn)象,認(rèn)為人類學(xué)的文化相對(duì)主義觀念是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領(lǐng)域里消解西方理論特權(quán)最有效的工具。在逐步失去了到傳統(tǒng)的田野地開展研究的原有特權(quán),失去了以民族志為地方知識(shí)來源的情況下,西方人類學(xué)者不自覺地重回西方知識(shí)中心主義,后現(xiàn)代文化批評(píng)像實(shí)驗(yàn)民族志和感官人類學(xué)轉(zhuǎn)向等依然具有鮮明西方文化的樣貌,“雖然刻意擺出了逃離表述霸權(quán),卻又落入西方中心話語”③參見趙丙祥:《人類學(xué)作為文化批評(píng)?》,《社會(huì)學(xué)研究》,2005年第2期。,聽不到對(duì)象世界的聲音,表述的感官世界依然是自我的想象和投射。視覺人類學(xué)也是來自西方理論的話語,無法呈現(xiàn)對(duì)象的主體性,抵消掉了影像民族志為彌補(bǔ)文本式民族志他者的主體性缺失這一缺陷所做的貢獻(xiàn)。這種“去場(chǎng)景化”的理論追求,背離了人類學(xué)從在地化到世界化的整體觀,以及知識(shí)去中心化和去等級(jí)化的努力。影視人類學(xué)不應(yīng)是為理論而理論的產(chǎn)物,理論發(fā)展需超越學(xué)術(shù)本位而面向現(xiàn)實(shí)問題。影視人類學(xué)不應(yīng)主動(dòng)放棄看家本領(lǐng),研究應(yīng)當(dāng)回歸情景化。在中國(guó),因文化多樣性的國(guó)情和影像民族志(少數(shù)民族科學(xué)紀(jì)錄電影和主體性影像等等)發(fā)展的特殊歷史過程,影視人類學(xué)表現(xiàn)為超然于西方學(xué)術(shù)話語的獨(dú)立性學(xué)科存在。
影像民族志在不同時(shí)期都是在面臨表述困境時(shí)發(fā)展了新的理念和方法,從而邁向新的階段。早期傳教士和探險(xiǎn)家在面對(duì)陌生世界時(shí),從開始的新奇感到相處時(shí)的無措感過程中產(chǎn)生了理性化需求,這樣呈現(xiàn)社會(huì)文化模式的理性主義愿望使業(yè)余民族志電影拍攝轉(zhuǎn)向了科學(xué)主義式的專業(yè)影像民族志時(shí)期。當(dāng)對(duì)文化差異的表述和尋找普遍性文化規(guī)律熱情被阻隔在文化間的“不可公度性”(incommensurability)和經(jīng)驗(yàn)間的不可讓渡性這樣的跨文化理解障礙上時(shí),專業(yè)影像民族志從客位的科學(xué)主義表述模式轉(zhuǎn)向參與式的、主位觀的、觀察式電影這樣的文化相對(duì)主義形態(tài)。科學(xué)民族志引發(fā)的“表征危機(jī)”使觀察式影像民族志轉(zhuǎn)向分享、合作和反思式實(shí)驗(yàn)影像志形態(tài)。后現(xiàn)代思潮下的影視人類學(xué),體現(xiàn)的是一種知識(shí)論轉(zhuǎn)向的結(jié)果,特征是表述政治、表述協(xié)商性寫作過程、實(shí)驗(yàn)性影像志和文學(xué)性等,民族志作品開始追求人文主義關(guān)懷。我們發(fā)現(xiàn)專業(yè)影像民族志受其現(xiàn)實(shí)主義或存在論觀念的局限,容易忽略知識(shí)與權(quán)力的關(guān)系,及“客觀記錄”影像的虛構(gòu)性。但后現(xiàn)代主義過于強(qiáng)調(diào)文化的“不可公度性”,引起對(duì)文化相對(duì)主義走向絕對(duì)化的質(zhì)疑:停留在空談,缺乏建設(shè)性,制造不可知論,無法走出倫理困境等。后現(xiàn)代主義者的極端化解構(gòu),把它推向了否定一切本質(zhì)和普遍原理的虛無主義。“后現(xiàn)代人類學(xué)多主題、多中心、多層次、不確定的實(shí)驗(yàn)傾向使得自身難以有什么具體特征。正如馬爾庫(kù)斯和費(fèi)徹爾所說,實(shí)驗(yàn)時(shí)代具有脫離權(quán)威范式而進(jìn)行觀念游戲的特點(diǎn)”①參見張連海:《從現(xiàn)代人類學(xué)到后現(xiàn)代人類學(xué):演進(jìn)、轉(zhuǎn)向與對(duì)壘》,《民族研究》,2013年第6期。。感官人類學(xué)及視覺人類學(xué)的濫觴也被質(zhì)疑以文本主義和知識(shí)中心主義替代人類學(xué)的文化相對(duì)主義,造成民族志對(duì)象的主體性缺失。
四、回向田野的新姿態(tài)——影視人類學(xué)的日常生活世界本體論轉(zhuǎn)向
后現(xiàn)代主義影像志出現(xiàn)兩種趨勢(shì),一種是在田野工作中的文化相對(duì)主義絕對(duì)化傾向,特點(diǎn)是以“小敘事”替代“元敘事(大敘事)”的敘事轉(zhuǎn)向,以“權(quán)利關(guān)系”解釋從現(xiàn)象到實(shí)在的各個(gè)層面問題,并解構(gòu)任何理性化的影像民族志敘事方式。另一種是脫離傳統(tǒng)田野的趨勢(shì),讓影像民族志陷入“對(duì)話性文本”和“觀念性游戲”的認(rèn)識(shí)論旋渦中。然而,“人類學(xué)本身所具有的傳統(tǒng)意義的獨(dú)特的學(xué)術(shù)魅力,并沒有湮沒在似是而非的文本主義的泥潭之中,而是在繼續(xù)書寫屬于自己的歷史。畢竟,人類學(xué)理論研究的終極目標(biāo),不在于解構(gòu)傳統(tǒng)研究范式,而在于建構(gòu)具有強(qiáng)大的再生產(chǎn)能力的新理論體系”②呂俊彪、周大鳴:《實(shí)踐、權(quán)力與文化的多樣性闡釋》,《廣西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9年第7期。。20世紀(jì)末以來,人類學(xué)中出現(xiàn)的一個(gè)重要現(xiàn)象是“本體論轉(zhuǎn)向”(ontological turn),人類學(xué)希望從“本體論轉(zhuǎn)向”中尋找反駁后現(xiàn)代相對(duì)主義觀點(diǎn)的某些理據(jù)。人類學(xué)本體論轉(zhuǎn)向是從知識(shí)論即對(duì)理念、世界觀及文化的關(guān)注,轉(zhuǎn)向?qū)ψ匀慌c存在重要性的認(rèn)可的實(shí)在論。對(duì)持文化相對(duì)主義而言,“文化”是對(duì)普遍性問題的相對(duì)性回答,本體論轉(zhuǎn)向則是對(duì)相對(duì)主義的普遍預(yù)設(shè)進(jìn)一步相對(duì)化。本體論轉(zhuǎn)向意味著“文化”這個(gè)最基本的人類學(xué)概念被當(dāng)做形而上學(xué)負(fù)擔(dān)而擱置。本體論轉(zhuǎn)向要求人類學(xué)家重新思考他們關(guān)于差異的最基本的思考方式。“它對(duì)基于文化和文化相對(duì)主義概念提出的民族志的挑戰(zhàn)尤其重要,不僅對(duì)人類學(xué)家來說如此,對(duì)一切關(guān)注‘文化’和‘社會(huì)’概念在今天世界上的地位的人來說也如此”③保羅·海伍德:《什么是人類學(xué)的本體論轉(zhuǎn)向》,王立秋譯自Paolo Heywood,“The Ontological Turn,”19 May, 2017,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http://doi.org/10.29164/17ontology,19 May,2019。。
王銘銘歸納“民族志新本體論”轉(zhuǎn)向的路徑主要有三種:“重新整理‘民族志書寫的區(qū)域傳統(tǒng)’、深化宇宙論研究以及哲學(xué)化‘土著觀念’”④參見王銘銘:《當(dāng)代民族志形態(tài)的形成:從知識(shí)論轉(zhuǎn)向到新本體論的回歸》,《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認(rèn)為民族志對(duì)于“對(duì)象世界”的客觀化(本體化)既不可避免又有其價(jià)值。人類學(xué)本體論轉(zhuǎn)向的觀念來源一般有兩種,一種是對(duì)民族志書寫區(qū)域傳統(tǒng)的重新發(fā)現(xiàn)。主要是以巴西的人類學(xué)家卡斯特羅(Eduardo Vieira’s de Castro)和法國(guó)的德斯科拉(Philipe Descola)為代表的亞馬遜人類學(xué),以及英國(guó)人類學(xué)家蒂姆·英戈?duì)柕拢═im Ingold)為代表的棲居路徑人類學(xué)等。另一種是哲學(xué)化路徑,諸如法國(guó)科學(xué)哲學(xué)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的科學(xué)技術(shù)研究(STS)和美國(guó)分析哲學(xué)家唐納德·戴維森(Donald Davidson)的徹底解釋的語言哲學(xué)思想。①龐濤:《新時(shí)期中國(guó)影視人類學(xué)的使命與實(shí)踐維度》,《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報(bào)》,2020年11月11日,第8版。其中,英戈?duì)柕潞屠瓐D爾等都以不同的路徑把研究引向人類生活最大實(shí)在,也就是我們當(dāng)下所處的時(shí)空“人類世”,即關(guān)注人類與自然(非人類)的相處境遇。
在后現(xiàn)代實(shí)驗(yàn)影像志之后,影視人類學(xué)如何發(fā)展?筆者認(rèn)為影視人類學(xué)應(yīng)重回民族志書寫的傳統(tǒng)領(lǐng)域,并賦予這個(gè)回歸過程以新的內(nèi)涵。其特征是,影視人類學(xué)回歸于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與觀念世界,轉(zhuǎn)向反映客觀實(shí)在的本體論。這也可以說是“新時(shí)期影像民族志”的形成階段。不同于文本式研究,影像具有呈現(xiàn)田野過程中各主體能動(dòng)性及互動(dòng)關(guān)系,以及情景化和語境化的優(yōu)勢(shì)。所以一種哲學(xué)化的“日常生活世界”理路被納入到影視人類學(xué)新本體論轉(zhuǎn)向的視野中,希望通過懸置文本式文化研究的表征主義范式,超越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性的爭(zhēng)論,直接進(jìn)入實(shí)在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主體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同時(shí),通過懸置主流影像敘事方法,以主體性及主體間關(guān)系性敘事來建構(gòu)民族志對(duì)日常生活世界的影像化表達(dá)。②參見龐濤:《影像民族志本土化研究的兩種路徑》,《廣西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8年第6期。鮑江也提出“通過懸擱‘文化’‘社會(huì)’‘民族’概念,重新把握人類學(xué)的歷史和邏輯起點(diǎn),將胡塞爾‘生活世界’概念引入影視人類學(xué);提出微型社區(qū)研究的一種生活世界影視人類學(xué)實(shí)踐進(jìn)路”③鮑江:《生活世界影視人類學(xué)理論》,《電影藝術(shù)》,2020年第1期。。
本體論是繼認(rèn)識(shí)論之后的哲學(xué)轉(zhuǎn)向,主要探討存在本身,以期建構(gòu)更有再生產(chǎn)能力的理論。文本人類學(xué)以分析哲學(xué)與科學(xué)哲學(xué)為本體論轉(zhuǎn)向的觀念基礎(chǔ),而影視人類學(xué)以“現(xiàn)象哲學(xué)”為回向新本體論的觀念基礎(chǔ)。從業(yè)余民族志時(shí)代開始,影像民族志一直都具有面向存有的本體論基本形態(tài),只是一直被動(dòng)地接受文本人類學(xué)文化研究的認(rèn)識(shí)論觀念。筆者曾討論過“發(fā)現(xiàn)‘日常生活’——影像民族志的本土化路徑”這一主題,即以一種去范式的姿態(tài)建構(gòu)“日常生活世界影像民族志”。④影像民族志本土化的路徑有:1.朝向事實(shí)本身——影像民族志面向“日常生活”的方法與策略;2.“去蔽”——影像志三重懸置——理解本土生活的意義。參見龐濤:《影像民族志本土化研究的兩種路徑》,《廣西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8年第6期。“生活世界”是現(xiàn)象學(xué)創(chuàng)始人胡塞爾給予現(xiàn)象學(xué)的首要主題,意在反駁近代自然和社會(huì)科學(xué)對(duì)于我們所處的世界的抽象化。胡塞爾認(rèn)為“生活世界(life-world)”是自然而然的世界,生活世界是人們?cè)谄渲卸冗^其日常生活所直接經(jīng)驗(yàn)的文化世界,它是“預(yù)先被給予的世界”,即先于經(jīng)驗(yàn)的存在。舒茨將現(xiàn)象學(xué)運(yùn)動(dòng)拓展至社會(huì)學(xué)領(lǐng)域,“將胡塞爾的現(xiàn)象學(xué)觀點(diǎn)和方法運(yùn)用于研究社會(huì)現(xiàn)象和日常生活世界,以理解日常生活世界中行動(dòng)者的主觀意義和行動(dòng)者之間的主體間性”⑤何雪松:《邁向日常生活世界的現(xiàn)象學(xué)社會(huì)學(xué)——舒茨引論》,《華東理工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0年第1期。。哈貝馬斯將交往活動(dòng)與“生活世界”相互闡釋,構(gòu)成了交往行動(dòng)理論的基礎(chǔ)。
影視人類學(xué)轉(zhuǎn)向“生活世界”的路徑是“反表征論”,即不再堅(jiān)持我們與對(duì)象之間存在概念性“認(rèn)識(shí)中介” ,以“世界”的概念替代“社會(huì)和文化”概念。“生活世界民族志通過將‘地方’歷史化和世界化,指出了被社區(qū)、群體、民族、社會(huì)、文化等等概念‘縮小了’的‘世界’之難以化約的豐富”①王銘銘:《當(dāng)代民族志形態(tài)的形成:從知識(shí)論轉(zhuǎn)向到新本體論的回歸》,《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對(duì)于后現(xiàn)代主義來說,生活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知識(shí)形態(tài)也是多種多樣的,這里沒有統(tǒng)一性和普遍性可言。但如果完全否定了本質(zhì)和普遍性,交流會(huì)發(fā)生困難。胡塞爾曾說過:沒有本質(zhì),也就沒有科學(xué)。胡塞爾“將有關(guān)生活世界的多樣性中存在統(tǒng)一性的觀點(diǎn)集中體現(xiàn)在他的‘生活世界的本體論’的概念中,即生活世界中存在理性交往和理性統(tǒng)一的可能性”②參見張慶雄:《譜系與本質(zhì):生活世界的本體論》,《哲學(xué)分析》,2016年第6期。。
影視人類學(xué)在經(jīng)歷后現(xiàn)代“共同敘事”的實(shí)驗(yàn)民族志以及建構(gòu)“反身性”文化批評(píng)思潮之后,應(yīng)更關(guān)注“主體間性”的影像志書寫在跨文化交往和理解中的作用。因?yàn)橛跋裉烊痪哂形谋静豢杀葦M的主體能動(dòng)條件——生動(dòng)的“主體表達(dá)”,以及影像在民族志作者與“被書寫者”及觀者三者之間建立主體相互關(guān)系時(shí)的能動(dòng)性。影視人類學(xué)的“生活世界”的認(rèn)識(shí)路徑,不是表征分析的文化研究方式,而是把對(duì)象世界“客觀化”的本體論路徑,是基于主體間的交往行動(dòng)來相互確認(rèn)經(jīng)驗(yàn)的體認(rèn)和理解過程。其核心是如何在主體的相互行動(dòng)中確認(rèn)和擴(kuò)展共享的經(jīng)驗(yàn)基礎(chǔ),并在此基礎(chǔ)上建構(gòu)的關(guān)系式民族志影像敘事和寫作。影像民族志的意義不只在于知識(shí)生產(chǎn),也是為實(shí)現(xiàn)跨文化分享經(jīng)驗(yàn),而發(fā)現(xiàn)共同的經(jīng)驗(yàn)世界(the common world of experience)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