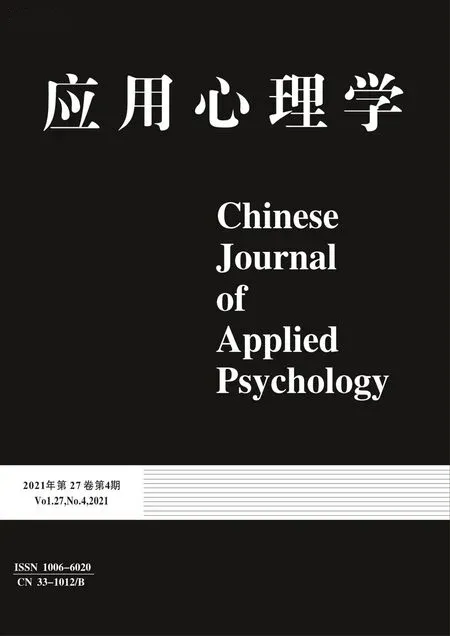類指語言的特征及其習得與影響*
汪運起 辜佩琪
(浙江大學 外國語言文化與國際交流學院,杭州 310058)
1 引言
兒童在發展中不斷學習范疇(category),形成概念(concept)。這些范疇和概念對兒童的認知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Medin&Smith,1984)。范疇和概念的形成與發展是兒童自身的認知傾向(bias)和經驗相互作用的結果(Kendler,1961;Spelke&Kinzler,2007),其中的經驗顯得尤為重要(Siegler,Im,Schiller,Tian,&Braithwaite,2020)。兒童范疇和概念的形成不僅依賴于直接經驗,往往也需要借助他人所傳遞的間接經驗。在日常交際中,使用類指語言(generic language)是他人陳述和傳遞間接經驗的重要方式之一。類指語言一般用于描述一類事物的某一屬性或特征,涉及的是事物經常性的、規律性的表現(如,類指句“鳥會飛”描述的是鳥這一群體的普遍性、規律性特征)。換句話說,類指語言不描述某一具體個體的特征,而是某一類事物整體層面的抽象特征(Gelman&Tardif,1998)。類指語言是類概念發展的產物,體現了人們對日常知識和經驗的范疇化思維過程,為了解人類概念形成和發展提供一個重要的語言窗口(Cohen,1999)。自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學界從不同視角對類指語言進行了較為廣泛的考察,對類指語言的了解不斷深化。本文將從類指語言的特征、習得及其對兒童概念發展的影響等幾個方面綜述這一領域的研究進展。
2 類指語言的形態及其使用
2.1 類指語言的形態
類指句和全稱句通常都可以用來表示對類別屬性的概括。含有全稱量詞(如漢語中“所有”、英語中的“all”)的全稱句所概括的屬性或特征必須適用類別中的所有對象(吳炳章,2010)。而類指句所概括的類別屬性可以容忍反例(周北海,2004)。例如,“鳥會飛”通常看作是對“鳥”這一類動物的概括,即便存在反例,如企鵝、鴕鳥等,也不影響這個句子的結論成立。
雖然類指句的句法結構簡單,一般只有一層主謂結構,分為主項和謂項,但其在句法形式上表現豐富,主項和謂項均可由不同的句法形式來充當。漢語中主項多為光桿名詞(如“母雞會下蛋”),而英語中主項除光桿復數名詞(如“Bears climb trees”)外,還可以由不定指單數名詞(如“A bear climbs trees”)和定指單數名詞(如“The bear climbs trees”)等來充當。謂項的常見格式有動詞式(如“雞生蛋”)、助-動式(如“狗會吠”)、是-表式(如“大象是哺乳動物”)等(徐盛桓,2010)。由于類指句涉及的是事物的一般性質或規律,其謂項通常不含時間指示詞和體標記。類指句既沒有專屬的主項或謂項標識,也不存在一種特定的句式。事實上,判斷類指句的主要依據是其表述的內涵,而不是其句法形式(Cimpian&Markman,2008)。
2.2 類指語言的使用
類指語言在人們語言交流中使用的頻率較高(Gelman,Taylor,Nguyen,Leaper,&Bigler,2004;Gelman,Coley,Rosengren,Hartman,Pappas,Keil,1998;Gelman&Tardif,1998;Pappas&Gelman,1998)。例如,當母親與3到4歲兒童一起看圖講故事時,92%的母親和65%的兒童會使用類指語言,并且母親講故事時使用的句子中平均有11%是類指句,甚至兒童在這個過程中使用的句子中平均也有3%是類指句(Pappas&Gelman,1998)。除了日常的交際外,人們在學術交流中也經常使用類指語言。2015年和2016年發表在11本高影響力的英文心理學期刊上的實證論文中,89%的論文在標題、研究熱點或摘要中使用過類指句。并且,在標題、研究熱點和摘要三個部分中,分別有87%、40%和16%的完整句子是類指句(DeJesus,Callanan,Solis,&Gelman,2019)。
類指語言的使用與情景有一定的關系。“類指—學習假設”(generic pedagogy hypothesis)認為,人們在知識傳授的情景(pedagogical contexts)中傳遞的信息更有可能是事物的類別特征,并且在這類情景中人們更傾向使用類指語言來描述物體的特征(Csibra&Gy?rgy,2009;Gelman,Ware,Manczak,& Graham,2013)。實證研究發現,在兒童書籍中,知識類書籍相比故事類書籍含有更多的類指語言,前者使用類指句的頻率是后者的7倍之多(Gelman,et al.,2013)。在日常交流中,當5~6歲兒童或成年人認為自己在傳授知識時,他們會比與朋友或同輩交流時使用更多的類指語言(Gelman et al.,2013)。
類指語言的使用還可能與討論的話題有關。研究發現,兒童和成人在談論動物時要比在談論人工制品時更多地使用類指語言,這一現象被稱為動物偏好(animal bias)(Gelman,Goetz,Sarnecka,& Flukes,2008;Brandone& Gelman,2013; Goldin-Meadow, Gelman, &Mylander,2005)。例如,當被試被告知某一物體是動物時,他們會使用更多的類指語言來對其進行描述;而當物體被描述為人工制品時,被試談論這一物體時則不會使用那么多類指語言,這一類指語言的使用傾向可能揭示了動物類別和非動物類別在本質概念上的差異(Brandone&Gelman,2013)。但基于更大規模兒童語料的研究顯示,兒童在使用類指語言時并沒有呈現出這一動物偏好(Mehrotra&Perfors,2019)。
類指語言的上述使用頻率和使用規律方面的特點在人類語言中具有普遍性。例如,類指語言在不同語言(如漢語、西班牙語、巴西葡萄牙語和克丘亞語等)中普遍存在,并被廣泛使用(Gelman&Tardif,1998;Goldin-Meadow et al.,2005;Mannheim,Gelman,Escalante,Huayhua,&Puma,2010;Ionin,Montrul,&Santos,2011)。又如,類指語言的使用不僅局限在正常發展的人群當中。從未接受過口語和手語輸入的中美聽障兒童也能夠使用自發創造的手勢來表達類指含義(例如,當呈現一張沒有象鼻的大象圖片時,聽障兒童能夠做出大象用鼻子灑水的手勢,說明他們是在描述大象這類動物的普遍特征),并且他們使用表示類別的手勢的頻率與正常兒童口語交際中使用類指句的頻率相仿(Goldin-Meadow et al.,2005)。再如,這些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語言使用者,以及不同生理狀態的人群(如聽力正常兒童和聽力障礙兒童)在使用類指語言或表達類指含義過程中都呈現出動物偏好。
3 類指語言的習得
雖然人們語言交際中頻繁使用類指語言,但類指語言的習得似乎具有一定的挑戰性(Prasada,2000)。正如前文所述,類指句和非類指句在句法和形態上的區別并不明顯,難以為兒童習得類指語言提供明確的語言線索(Gelman&Raman 2003)。并且,類指句的指稱對象是抽象的類別概念,無法從指稱情境中直接感知到(Cimpian&Erickson,2012)。盡管存在著上述種種困難,兒童習得類指語言的時間卻比較早。兩歲兒童在語言交流中已經開始使用類指語言(Gelman et al.,2008;Pappas&Gelman,1998)。另外,雖然含全稱量詞和存在量詞(如“一些”、“許多”等)的名詞短語比類指名詞有更明確的語義,且有明確的語言線索來幫助識別,兒童習得類指語言卻要早于習得全稱量詞和存在量詞(Hollander,Gelman,&Star,2002;Leslie,Khemlani,&Glucksberg,2011)。隨著年齡的增長,兒童還可以區分類指句、全稱命題和特稱命題。雖然類指句與全稱句在語義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都表示某個類別所具有的普遍特征,但英語母語兒童在4歲時就已經能夠對這兩種類型的句子進行區分(Hollander,et al.,2002)。而漢語母語兒童和克丘亞語母語兒童分別在7歲和10歲左右也能夠區分類指句和全稱句(Tardif,Gelman,Fu,&Zhu,2012;Mannheim et al.,2010)。同樣地,雖然類指句與帶有存在量詞的特稱命題在語義上也有相似之處,即都能夠容忍反例,但英語母語兒童和克丘亞語兒童在4歲左右就能夠識別類指句和特稱命題之間的差異(Hollander et al.,2002;Mannheim et al.,2010)。
那么,兒童是如何習得類指語言的呢?實證研究表明詞匯線索、形態句法線索、語用線索和世界知識線索可能會幫助兒童識別和習得類指語言(Cimpian&Markman,2008)。
從詞匯層面看,一般來說使用全稱量詞或存在量詞的句子不是類指句(Gelman,Star,&Flukes,2002;Hollander et al.,2002)。此外,有些系動詞(如西班牙語中的“ser”)和形容詞(如等級形容詞“大的”“高的”“矮的”等)更常在類指句中使用(Beausire&Miller,2015)。
形態句法線索,包括限定詞、名詞的數、動詞的時態和體等也能夠幫助判斷一個句子的指稱范圍。比如在英語中復數光桿名詞可用來表達類指概念,但定冠詞加復數名詞常用來表示特指某些個體(Gelman&Raman,2003)。3到5歲的兒童已經可以利用限定詞、動詞的時態和體等形態句法線索來識別類指句(Cimpian,Meltzer,&Markman,2011)。
語用線索為判斷類指語言提供了重要的依據。聽者可以根據具體語境和說話者的知識背景等來識別類指語言。例如,當聽到在指稱上模棱兩可的句子(如“They are afraid of mice”),3歲的兒童能根據前文提供的語境(如“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birds”和“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these birds”)判斷其為類指還是特指;4歲兒童還能根據說話者的身份和場景來進行判斷,如同樣是關于狗視力的陳述,他們會認為由獸醫做完檢查之后說出更有可能是特指,而由教師指著課本說出則更大概率是類指(Cimpian&Markman,2008)。交際中所談論的物體的表征形式也是識別類指語言的一條重要語用線索。研究發現2到3歲的兒童在談論物體的圖片時會比談論物體的仿真模型時更多地使用類指語言(Gelman,Chesnick,&Waxman,2005),這說明物體的表征形式在我們的知識建構中起重要作用,圖片更有可能被理解為代表一類物體(DeLoache,1991;Gelman et al.,2005)。
兒童自身儲備的世界知識也有利于識別類指句。例如,有些特征的類推范圍較廣(如“They grow in dark places”),而有些特征僅適用于某些個體(如“They are sick”)。3歲的兒童能夠根據對特征類推范圍的認識來解讀語義模糊的句子是否是類指句(Cimpian&Markman,2008)。又如,先天遺傳的特征一般是整個群體共有的,而后天習得的特征則不一定。當句子沒有明確的指稱對象時,成人更傾向于認為描述先天遺傳特征的句子為類指句(Gelman&Bloom,2007)。
需要指出的是,與類指有關的語言線索在不同語言中豐富程度并不相同。例如,漢語普通話通常不具有強制的數和時態變化,且動詞的體標記也不常用,因此在這些方面不能給兒童提供識別類指語言的有效線索(Gelman&Tardif,1998;Tardif et al.,2012)。雖然不同的語言給兒童提供的用來識別類指語言的線索不盡相同,但已有的研究表明不同語言的兒童都可以根據其世界知識和/或部分語言線索(詞匯、形態句法、語義或語用等方面的線索)來識別類指語言(Mannheim et al.,2010;Tardif et al.,2012)。這也說明兒童對類指語言的識別和習得是基于不同線索或綜合多個線索來實現,并非依賴某一個或多個具體穩定的線索。
除了上述語言線索和兒童的世界知識外,兒童學習中固有的認知傾向也可能是習得類指語言的重要機制。在兒童的概念發展和語言學習中,類別信息比個體信息更能激發兒童的好奇心(Cimpian&Park,2014);相比冠以全稱或存在量詞的個體信息,兒童的認知系統能更早、更有效地加工類別信息(Hollander et al.,2002;Mannheim et al.,2010;Tardif et al.,2012;Leslie&Gelman,2012)。因此,類別概念似乎在人類的認知系統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如果沒有明顯的線索提示一個句子的指稱對象是個體,那么兒童會默認這個句子指向的是類別,這種現象被稱為類指缺省(generics-as-default)(Leslie,2008;Meyer&Gelman,2016;Sutherland&Cimpian,2015)。類指缺省能較好地解釋兒童為什么能較快地習得如此復雜的類指語言(Gelman et al.,2008)。
4 對兒童概念發展的影響
類指語言在兒童的發展環境中頻繁出現,并且兒童能夠快速習得和識別這類語言。那么類指語言對兒童概念發展有怎樣的影響呢?我們將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探討:①凸顯類別特征的重要性,使其在特征網絡中核心化;②強化兒童的本質主義信念;③增加概念的可推理性;④增加概念的可記憶性。
4.1 強化類別特征的重要性和核心化
類指語言和非類指語言都可以用來描述事物的特征,但兩者的區別不僅在于類指語言描述的特征(如“鴨子會游泳”)通常比非類指語言(如“這只鴨子會游泳”)適用于更多的個體,而且這兩種不同的語言會讓人們覺得其描述的特征在類別概念中的重要性不同。與非類指語言相比,使用類指語言描述事物的特征時,學前兒童和成人都會認為這些特征是類別概念中更深層、更重要的特征(Cimpian&Markman,2009;Cimpian&Markman,2011;Gelman,Ware,&Kleinberg,2010;Gelman,Raman,&Gentner,2009;Rhodes,Leslie,&Tworek,2012)。例如,在學習一個事物的新特征時,通過類指語言學習(如“Fish have a bag full of air inside them”)的學前兒童更多地認為這些新特征是引起其他關鍵特征或行為的原因(如“to help them swim”);而通過非類指語言學習(如“He has a bag full of air inside him”)的學前兒童更多地認為這些新特征是由之前發生的某個事件、行為或特征造成的(如“because he swallowed too much air”)(Cimpian&Markman,2009)。換言之,類指語言描述的特征往往與其所指向的類別緊密相關且更具重要性,而非類指語言描述的特征多為偶發事件造成(Rhodes et al.,2012)。
當一個類別的新特征以類指句的形式呈現時(如“Zarpies like to sing”),成年人會更多地以這個新特征為依據將事物歸類;而當類似的內容以特指(如“This Zarpie likes to sing”)或不帶指稱標簽的形式(“This likes to sing”)呈現時,聽者則更多根據感知覺特征的相似度來進行歸類(Gelman et al.,2010)。這些發現表明,類指語言能夠強化類別與特征之間的聯系,從而引導兒童類別概念的學習(Gelman et al.,2009,Rhodes,Leslie,Bianchi,&Chalik,2018)。并且,在提供合適刺激的前提下,類指語言也能更好地幫助5歲兒童和成人進行交叉分類(cross-classification),即當用類指語言描述一個物體時被試能更準確地把它歸屬到不同類別中(Nguyen&Gelman,2012)。
4.2 強化兒童的本質主義信念
人們在認識自然和社會時會有一種直覺或認知傾向,即認為一個類別有其內在、穩定、不易被直接觀察到的本質特征(essence),且這個(或這些)本質特征不會隨著時間、情境的變化而變化(Gelman,2003;Medin,1989;Rhodes&Mandalaywala,2017)。盡管類別成員之間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差異,但正是這種內在的本質讓它們共同歸屬于一個類別。研究發現,類指語言能夠強化人們的這種本質主義認知傾向。例如,相比于使用非類指語言,成人,甚至是兒童,會更多地認為用類指語言描述的類別具有更穩定和內在的特征,并且認為這些特征也更有可能是可遺傳的,從而更傾向根據類屬關系而非主題關系或形狀進行分類(Cimpian&Markman,2011;Gelman et al.,2010;Rhodes et al.,2012)。類指語言的這一效應對自然類別和社會類別都適用(Rhodes,Leslie,Saunders,Dunham,&Cimpian,2018;Cimpian & Markman,2011),且隨著類指語言輸入的增多呈現出增強的趨勢(Gelman et al.,2010;Rhodes et al.,2012)。另外,類指語言的這一效應似乎在成年人中表現得要比兒童更強一些(Cimpian&Markman,2011;Gelman et al.,2010)。
本質主義的認知傾向既會給兒童習得知識帶來正面影響,也會帶來負面影響。正面影響主要體現在對于自然(生物)類別而言,這種本質主義認知傾向能夠幫助兒童突破直接觀察的局限性,更好地構建對新知識的深層認知(Medin&Atran,2004)。例如,由于本質主義認知傾向會使得兒童認為同一類別的成員具有本質特征,并且這個(或這些)本質特征使得該類別的成員具有其他一些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因此當兒童已知某個類別的某些成員具有某一特征時,本質主義的認知傾向會幫助兒童推斷該類別的新成員是否也會具有這個特征。并且,即使研究者控制類別新成員與已知成員具有不同的外部特征(Gelman&Markman,1986),或者新成員目前還不具有這個特征(Gelman&Wellman,1991;Rhodes et al.,2012;Waxman,Medin,&Ross,2007),又或者新成員是由另一個類別的成員撫養大的(Gelman&Wellman,1991;Rhodes et al.,2012;Waxman et al.,2007),類指語言也有助于兒童推斷出新成員也擁有已知成員的某一特征。當然,對自然(生物)類別的本質主義認知傾向也會阻礙兒童對某些自然規律的理解(Shtulman&Schulz,2008)。例如,Shtulman和Schulz(2008)認為,本質主義認知傾向會讓兒童認為某些本質特征是群體內部成員都共有的,從而形成對某一群體的固有認知,進而忽略了同一物種在進化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變異。
在社會類別領域,本質主義的負面影響表現得更為明顯。本質主義的認知傾向使得兒童和成人更容易形成刻板印象和偏見(Prentice&Miller,2007),從而影響兒童的認知、情感和行為。家長、老師或同伴使用類指語言(如,“You are a good drawer”)表揚兒童時,因為其陳述的是一個一般規律,而非一個具體的事實或事件,這類表揚強調的通常是兒童經常性的、穩定的特質,這會讓兒童覺得成功或優秀是源自個人所具有的某種穩定的、本質的、自己無法控制的特質。一旦做某件事碰到挫折則說明自己并不具有這些特質,從而形成自己能力不行的認知。相反,如果使用非類指語言(如,“You did a good job drawing”),則強調的是兒童在某一具體事件上的表現,這會讓兒童覺得成功或優秀是個人努力的結果。若遭受挫折只說明自己的努力還不夠。研究表明,在遇到挫折之前,這兩類表揚方式對兒童動機的影響基本相同;但當兒童經歷挫折或失敗后,受到類指語言表揚的兒童的自我評價會更低,繼續做某一任務的意愿會更低(Cimpian,Arce,Markman,&Dweck;2007;Kamins&Dweck,1999)。如果兒童得到的表揚中同時包含類指語言表揚和非類指語言表揚,類指語言表揚的比例越高,兒童的自我評價和繼續做某一任務的意愿就會越低,并且類指語言對后者的影響更大(Zentall&Morris,2010)。
不僅在表揚時使用類指語言會對兒童的自我評價和任務參與意愿產生消極影響,在介紹某項任務時,使用類指語言對完成這項任務的能力進行評價會比使用非類指語言進行評價對兒童參與任務的動機影響更大(Cimpian,2010)。具體而言,研究者給4到7歲的兒童講五個小故事。前三個故事中描述了被試在玩游戲并成功的場景,后兩個故事則描述了被試玩這個游戲并犯錯誤的場景。在講故事的過程中,研究者會使用類指語言或非類指語言對完成這個游戲的能力進行評價(如“Girls are really good at this game”或“There’s a girl who is really good at this game”)。研究發現,聽到用類指語言描述能力的4到5歲兒童在聽到犯錯版本的故事后完成任務的動機會低于聽到用非類指語言描述能力的兒童;而6到7歲的兒童完成任務的動機甚至在沒有聽到犯錯版本的故事之前就會受到類指語言的影響。并且,即使這種對能力的類指描述對某些群體來說是正面的(如上文提及的“Girls are really good at this game”),這一群體(如女孩)參與任務的動機依舊會降低(Cimpian,2010)。除此之外,類似的類指表述還會直接影響兒童的表現,甚至當說話者離開現場,這種消極影響也會持續存在(Park,Schaeffer,Nolla,Levine,&Beilock,2017)。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使用類指語言會讓兒童覺得說話人更有知識(Koenig,Cole,Meyer,Ridge,Kushnir,Gelman,2015)以及人們在傳授知識時更傾向使用類指語言(Gelman et al.,2013),因此家長和教育工作者與兒童在日常交流和教育中注意類指語言帶來的刻板印象和偏見顯得尤為重要。研究發現,在介紹科學家和科學活動時,從強調具體行動的角度來介紹科學活動(如“When people are doing science they use their five senses to learn about the world”)會比使用類指語言來描述科學家這一群體(如“Scientists use their five senses to learn about the world”)更能提高女孩在科學任務中的持續參與度(Rhodes,Leslie,Yee,&Saunders,2019)。另外,在兒童聽到類指語言之后,即使僅增加一句強調努力重要性的解釋,也能夠有效地降低類指語言對他們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提升他們在任務中的表現(Park et al.,2017)。
4.3 增加概念的可推理性
概念是人類組織知識的基本單位,也是擴充知識的重要方式(Smith&Medin,1981)。4歲兒童就已經認識到可以利用已知的類別知識來增加新的知識,推測一個類別的新成員是否具有(或將來是否會具有)某一特征或行為(Deák&Bauer,1996;Gelman&Markman,1986;Waxman et al.,2007)。在這個過程中,類指語言能夠影響人們根據類別概念進行推理的程度。類指與特指對概念推理的影響在兒童2歲半時就開始表現出差異(Graham,Nayer,&Gelman,2011)。同樣是描述關于兒童熟悉的某一自然類別的特征,與聽到含有存在量詞的句子相比,4歲兒童在聽到類指句之后會更傾向于將特征推理到更多的新成員上,表明類指語言會使得概念特征具有更高的可推理性(Gelman et al.,2002)。即使當兒童對所提及的自然類別或社會類別并不熟悉時,他們依然會呈現出基于類指語言的推理傾向(Chambers,Graham,&Turner,2008;Rhodes et al.,2012;Riggs,Kalish,&Alibali,2014)。而5歲的兒童在面對人工制品類別時也能夠基于類指語言進行推理(Cimpian&Cadena,2010)。
類指語言對兒童推理的這一影響與范例呈現多少以及是否存在反例無關(Chambers,et al.,2008)。研究人員在用類指語言介紹新知識(如“Pagons are friendly”)之后,給一組兒童呈現五個范例(即五個Pagon的模型),給另一組兒童僅呈現兩個范例(即兩個Pagon的模型)。結果發現范例呈現的次數并不會影響兒童推理的傾向。另外,當研究人員用類指語言介紹之后再呈現反例(如“Except this pagon,this pagon isn't friendly”),也不會影響兒童的推理。但這種類指推理傾向與說話者使用類指語言時的信心有關,只有當說話者對描述的內容表現出較強的信心或者不表現出自己的確信程度時,4歲兒童才會將類指語言描述的類別信息泛化到該類別的其他成員中(Stock,Graham,&Chambers,2009)。
4.4 增加概念特征的可記憶性
在描述事物的特征時,類指語言不僅會強化這些特征在類別概念中的重要性、穩定性、內在性和可推理性等,還會使得這些特征更易于保存在長時記憶中。研究發現,當讓兒童回憶先前聽到過的句子時,他們能夠區分句子的形式是類指句還是非類指句(Gelman&Raman,2007)。且4到7歲的兒童在記憶一些與動物或人有關的事實時,往往對用類指語言呈現的事實比對用非類指語言描述的內容有更準確的記憶(Cimpian&Erickson,2012;Riggs et al.,2014)。就連3歲兒童也對用類指語言描述的事物名稱的記憶更深刻(Gelman&Raman,2007)。此外,這種記憶優勢還體現在類指與全稱句的對比中。用類指句所傳遞的信息會比用全稱句描述的內容給聽者留下更深刻的記憶(Leslie&Gelman,2012)。這一記憶優勢并不是由于英語中全稱句和類指句的長度不一致造成的,因為在這兩種類型句子長度一致的語言中也發現了同樣的規律,如西班牙語(Gelman,Sánchez Tapia,&Leslie,2016)。雖然類指語言對類別特征記憶的強化作用還需在更多類型的類別以及更多的語言中加以驗證,但上述研究表明類指語言對兒童的概念發展的影響可能是持續性的,而非僅僅在類指語言使用的即時語境中發揮作用。
5 結語
類指語言是人類保存和傳遞知識的重要載體,在兒童成長的語言環境中廣泛存在。雖然類指語言在語義上有其復雜性,在形態句法上有其不確定性,但兒童很早就能習得、識別和使用類指語言。兒童成長語言環境中的類指語言會影響兒童的概念形成和發展,進而影響他們的知識習得、動機和行為等。因此,研究類指語言可為了解兒童的概念形成和發展提供一個重要的語言窗口,為考察語言與認知及行為之間的關系提供一個重要視角,并對理解和改進兒童早期教育提供有益的啟發。我們認為,對類指語言進一步深入研究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例如,通過采集較大規模的多語種、多體裁的自然語料,探究不同語言中和不同體裁中類指語言的使用頻率,從而進一步考察類指語言的普遍性。又如,因為不同語言中用于識別類指語言的線索不盡相同,而這些線索可能會影響到兒童識別和習得類指語言,因此有必要考察不同語言中兒童習得類指語言的機制有何異同。再如,類指語言和兒童概念發展之間存在較為復雜的關系,并且兒童的認知發展(如,抑制控制能力)能預測以語言為媒介的間接經驗習得的能力(梁英,曹瓊,李竺蕓,&何潔,2021),因此,除進一步考察類指語言對兒童概念發展的影響外,有必要考察概念發展及其他認知能力發展對兒童習得和使用類指語言的可能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