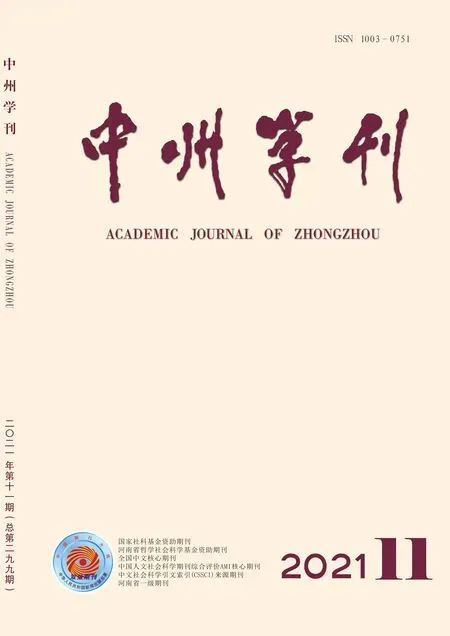康有為“壁中書出自劉歆偽造”說論辯述評*
姜 廣 輝 肖 永 貴
“壁中書”系漢代今、古文經學之爭的主陣地,是破解漢代經今、古文之爭這一學術公案的關鍵。光緒十七年(1891)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付梓,將《史記》《漢書》所載“壁中書”事全歸劉歆偽竄,全力以今文經學非難古文經學,直接引發了晚清、民國對漢代經今、古文的再爭論、再認識。其時,學界圍繞康有為的“新學偽經”命題展開激烈論辯,其“壁中書出自劉歆偽造”論更是成為爭論的焦點。既有崔適、錢玄同、顧頡剛等“疑古派”學者大力推崇和闡揚康說,也有洪良品、朱一新、符定一、錢穆等駁正者從康說的立論依據、論證邏輯以及具體論據,駁正其謬誤,瓦解其論說。雙方的激烈論辯,在晚清、民國學術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推崇與闡揚者無非是為康氏搖旗吶喊,駁正者雖然對康說進行了嚴正駁斥,但仍待進一步完善,方可宣告康有為“壁中書出自劉歆偽造”說謬誤的終結。故此,本文立足康氏“壁中書出自劉歆偽造”說,梳理晚清、民國學界對康氏的推闡與駁正,評述其中是非,彌補學界對康氏“壁中書出自劉歆偽造”說及其論辯缺乏全面梳理的缺憾①,為破解漢代經今、古文之爭的學術公案提供裨益。
一、康有為所謂“壁中書”及其真偽論辯
《偽經考》中“壁中書”僅出現七次,康氏論說僅三次,另四次是其辨偽對象。據此,“壁中書”似乎不是康氏“新學偽經”說的重心。但細讀全書,“壁中書出自劉歆偽造”實為康氏力證“古文經典系劉歆偽竄”的核心。所以,須弄清“壁中書”的初始概念與內涵,對比康氏所謂劉歆偽造的“壁中書”,分梳晚清、民國對此形成的論辯,述評其得失。
1.“壁中書”的初始概念與內涵
“壁中書”首見《說文解字·敘》。許慎說:“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②所謂“古文”,是相對于秦漢流行的“今文”字體而言的。秦漢流行的“今文”字體是隸書,而“古文”乃是曾經流行于六國的篆體文字,孔子舊宅壁中所出之《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皆用此種文字書寫。這些經典不僅書寫字體不同,篇章內容也有差異。許慎編撰《說文解字》,曾從這些書中選擇文字材料,列舉古代篆書、籀文的寫法。
唐代的顏師古注《漢書》,兩次提到“壁中書”。一是注“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時說:“壁中《書》者,多以考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③此“壁中書”專指孔安國所得孔壁古文《尚書》,屬經學體系。二是注“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時說:“古文,謂孔子壁中書。”④與許慎所說相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此處所稱“孔子壁中書”是一種獨特的書體,既不同于秦漢流行的隸書,也不同于時人曾見的繆篆和秦小篆,故籠統稱之為“古文”。當時學人所謂“古文”,其意是較“篆書”和“繆篆”更古老的文字,甚至以為是倉頡最初所造的書體,如《晉書》卷六十《索靖傳》載:“(索靖)作《草書狀》,其辭曰:‘圣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為。蝌蚪鳥篆,類物象形。’”⑤“古文”又被稱為“科斗文”或“蝌蚪文”,因其書體中時見蝌蚪狀筆法而得名。孔安國古文《尚書序》稱:“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⑥《后漢書》卷九十四《盧植傳》載盧植上書有云:“古文科斗,近于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并敦悅之。”注:“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形似科斗,因以為名。”⑦晉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后序》敘及晉太康元年發現的《汲冢竹書》時說:“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見之。”⑧古代談論“科斗文”的學者中,杜預曾親見“科斗文”的實物,因此我們可以說,所謂“古文”或“科斗文”并非空穴來風。由于孔子舊宅古書及《汲冢竹書》后皆失傳,后世學人包括康有為皆無由得見“古文”(或“科斗文”)書體,因此轉而懷疑“古文”(“科斗文”)文獻之有無。
關于“古文”(“科斗文”)書體,直到近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簡》《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圖版公布,學術界才重見這一書體。原來許多字今日楷書寫成橫與豎或捺的結合,此種書體則寫成大圓點與豎或捺的結合,這樣便滿篇多見“小蝌蚪”了,“科斗文”之名當是由此而得。宋代朱長文《墨池編》說:“蝌蚪篆者,其流出于《古文尚書序》,費氏注云:‘書有二十法,蝌蚪書是其一法,以其小尾伏頭似蝦蟆子,故謂之蝌蚪。’昔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宮室,得蝌蚪《尚書》。又《禮記》《論語》足數十篇,皆蝌蚪文字。”⑨《墨池編》所謂“費氏注”,概指南朝梁國子助教費甝,費甝曾撰《尚書義疏》十卷,其書今不傳。“蝦蟆”,今人稱為“蛤蟆”;“蝦蟆子”即俗所謂“蛤蟆骨朵”。實際上這是一種曾經流行于六國的篆書文字。當時漢代諸儒所稱之“古文”經典,多由此種書體書寫。
“壁中書”史實載于《漢書·藝文志》。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說:“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⑩《漢志》進一步明確恭王壞宅所得,有“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近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簡》《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可以實證漢晉時代所出之古書確曾有不同于隸書、繆篆和秦小篆的“古文”書體,《漢書》所記并非虛構。而劉歆責讓今文博士,主要并非強調此種書體的特異之處,而是強調“壁中書”的經學價值,以期立古文經博士,辟今文經學之弊端。
2.康有為所謂劉歆偽造的“壁中書”及其真偽
康氏認為劉歆偽造的“壁中書”包括三類:一是古文《尚書》,含伏生所藏、孔壁所藏、河間獻王所得;二是壁中古文經典,即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三是“古文字”材料“壁中書”。康氏《偽經考》將三者全力證成偽經,激起晚清、民國最激烈的論辯。
首先,孔壁古文《尚書》。康說:“《漢·志》所謂魯共王壞壁所得之《書》也,《史記》于《魯共王世家》何以無之?且其時河間獻王亦得古文《書》,同異若何?史公于《河間世家》何以無之?”繼而論證《漢書·藝文志》所載魯恭王壞壁得《書》事是劉歆為了偽亂《尚書》而竄入,并引劉逢祿說:“蓋此十六篇亦《逸周書》之類,未必出于孔壁,劉歆輩增設之以抑今文博士耳。”錢玄同認為,“河間獻王及魯共王無得古文經之事”是《偽經考》最重大的發明之一。康氏甚至懷疑伏生壁中《書》,“考六經之傳,有書本,有口說……伏生于《尚書》是其專門,即有百篇,皆所熟誦”,《詩》與《春秋》等篇幅較長的都可依賴口傳保存,伏生又是秦博士,其《尚書》本沒有被燒,為何非要依賴壁藏?于是得出“壁藏亡失之說更不待攻”的結論。
壁中古文《尚書》多出十六篇是否劉歆偽造?經符定一考證,《孟子·萬章》《孟子·盡心》《禮記·緇衣》《尚書大傳》《史記·殷本紀》《漢書·律歷志》等文獻皆曾引此十六篇中之事。符定一說:“總核諸證,知十六篇中已有十一篇見于經典,足以征其不偽矣。”今文經學家認可的《孟子》引《伊訓》《武成》,《禮記·緇衣》引《尹吉(告)》,《尚書大傳》引《九共》,《殷本紀》言“作《湯誥》”“作《伊訓》”“作《典寶》”“作《原命》”,都是“康不能誣為歆竄、歆竊,亦莫由詆為歆造、歆紿者”。足見今、古文經學家都認可十六篇古文《尚書》。清前期考證學家閻若璩在其《尚書古文疏證》第八卷第一百一十三條明言:“予之辨偽《古文》,吃緊在孔壁原有真《古文》。”康有為對這一重要考證結論故意視而不見,否認歷史上曾有真《古文尚書》十六篇出現。
這里,我們認為還有兩個關鍵人物:魯恭王劉余和河間獻王劉德,需要略做介紹。漢景帝共有十四子,魯恭王劉余為漢景帝第四子,河間獻王劉德為漢景帝第二子。兩人都是漢武帝的庶母兄長。司馬遷與漢武帝、魯恭王、河間獻王是同時代人而略晚,因他為李陵辯解而遭受宮刑,其后發憤著《史記》。雖身為史官,但著《史記》之事并非受命于上,而是出自其私人意愿。由于當時的遭遇,對當朝之事無論從資訊來源或形勢避忌方面,多有掣肘之處,難免有詳古而略今的不得已難處。因而他記敘漢景帝十三子之事極其簡略,只記敘“景十三王”的愛好和世次,寥寥數語帶過。即便如此,司馬遷還是在《史記·儒林列傳》中提及:“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余篇。”此處記載正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經之事相應。司馬遷惜墨如金,既然在《儒林列傳》中提及此事,又何必在《魯共王世家》中再提此事?正因為《魯共王世家》沒有重提此事,康有為便斷言這條是劉歆竄入《史記·儒林列傳》的。康氏不能自圓其說的是,劉歆既然能竄入《儒林列傳》,為杜絕世人懷疑,再竄入《魯共王世家》應該也不難。所以,康有為這種說法較為牽強。另外,康氏由當時經師能背誦《詩三百》使《詩經》得以傳世,推論伏生也能背誦《尚書》之文,不必依靠壁藏之《書》傳世。從學術規范來說,這不過是一種推論而已。其實《詩經》諸詩都是有韻之文,便于背誦,且傳習甚廣。《尚書》乃是上古官方的政治檔案,佶屈聱牙,本不便于記誦;且古字古音,一字之差,謬以千里。若無文本,如何傳習?即使秦博士所職之書可以不燒,秦末兵荒馬亂之際,秦博士們逃難四方,誰會帶著許多竹書逃難呢?
其次,壁中古文經典。在《漢書藝文志辨偽》上、下篇中,康氏先說劉歆亂《史記·儒林傳》,以便坐實伏生壁中藏《書》,得出“壁中古文之事,其偽凡十”,以證壁中古文《尚書》皆為劉歆偽托。進而將《禮》《記》《論語》《孝經》全歸劉歆偽造,分述于“禮記”“論語”“孝經”類,強調“劉歆為《七略》、修《漢書》,于是雜竄古文諸經于《藝文志》《河間獻王魯共王傳》中”。
古文經典是否劉歆偽造?洪良品對比《漢書·王莽傳》《西京雜記》《史通》,駁正“劉歆偽造古文經典”并無實據,因《漢書》載劉歆“顛倒五經”而非偽造。《王莽傳》載公孫祿說:“太傅平化侯(唐尊)飾虛偽以偷名位……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公孫祿說唐尊“飾虛偽”與劉歆“顛倒五經”,明顯不同。因為“‘顛倒’二字,訓詁不作‘造竄’解,于是非則曰‘顛倒’……若‘造竄’,則當論有無,不必計是非也”。公孫祿指責劉歆“顛倒五經”,主要針對其想立古文經學。符定一、錢穆專門尋找證據闡明《周禮》《左傳》早在劉歆前已有之,故必非劉歆偽造。第一,《周禮》行于周、秦、漢。符氏找到《周禮》行于周之證十四條,行于漢之證十條。第二,劉歆之前已有人引《左傳》,分別為子夏、荀卿、劉向、翟方進(劉歆師)、班彪諸人,以及《孟子·萬章下》《韓詩外傳》《外儲說·右上》《外儲說·左上》諸書,尤其是漢代今文學家和漢朝禮制都有引《左傳》。錢穆也認為:“路溫舒、張敞等引《左氏》尤在前,而方進之傳《左氏》,則有明證矣。”
我們知道,古文《尚書》較今文《尚書》二十九篇多出十六篇,久已不傳。古文《禮經》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與今文《儀禮》十七篇相同,多出三十九篇,禮文久佚。康氏并未見到其書,不知何以便斷定其為劉歆偽作?《論語》《孝經》既有今文本,也有古文本,內容上的差異本不很大,姑置不論。至于《禮記》只有古文本,并無今文本。《禮記》各篇明顯非成于一人之手,前人推斷是七十子之徒散佚之作,漢儒將其匯編成一書。其中《大學》《中庸》《禮運》之篇為儒學的經典文獻,康有為所作《中庸注》《大同書》依托的就是后二篇。他雖然沒有關于《大學》的專門著作,但在其著述的其他地方有不少論述。康有為在《偽經考》中將《禮記》定為劉歆偽作,自相矛盾,康氏何以自圓其說?
最后,古文字材料“壁中書”。在《漢書藝文志辨偽》下篇中,康氏將涉及古文字的所有材料都歸于劉歆偽造,不僅這些用古文書寫的經典版本是劉歆偽造的,這些“古文字體”也是劉歆偽造的,為的是要推行“小學”。
古文字是否劉歆偽造?錢穆認為,康氏對《史記》所載古文字“均詆為劉歆所竄改”,而對《漢書·地理志》載十一次“古文字”、三十八次“禹貢字”,“則一字不提及”,因后者屬今文經學,“不但證明有古文《尚書》,且證明有《周官》……且證明有《左傳》矣”。符定一以《史記》《中庸》載“書同文”和瑯玡臺石刻為據,認為“孔子書六經,勢不能不用古文”。逐一辨證《說文》有古文、有今文,還有古今共用之字,“用之于今文經不偽,用之于古文經則詆為偽,豈理也哉?”古文、小篆、今文一貫,“小篆與今文經字不偽,則古文亦不偽”,并且《說文》所載古文、籀文、小篆,符合文字發展的繁簡演變規律和原則,足證古文字不偽。
錢穆、符定一所言甚是。漢晉以后學者雖然未曾見到這種“古文”字體,但都相信它是歷史存在,很少有人存疑。康有為勇于疑古,斷然否定它是歷史存在,認為一切所謂古文經典連同它的文字載體全都是劉歆偽造的。這種做法實在魯莽,對中華文化的繼承傳播極為有害。
二、康有為推論“劉歆偽造壁中書”及其論辯
康有為以為,劉歆作偽是一個全面系統的工程,他善于制造和利用偽經前提、佐證,并且他有偽經的能力、能量和憑依。為了證明“壁中書”都是劉歆偽造,康有為還有一套自己的論證體系,晚清、民國學界就此也形成了激烈的論辯。
首先,康有為認為,“秦焚書”是劉歆竄亂諸經的前提。《偽經考》載:
(劉)歆欲偽作諸經,不謂諸經殘缺,則無以為作偽竄入之地,窺有秦焚之間,故一舉而歸之:一則曰“書缺簡脫”,一則曰“學殘文缺”,又曰“秦焚《詩》《書》,‘六藝’從此缺焉”,又曰“秦焚書,書散亡益多”。學者習而熟之,以為固然,未能精心考校其說之是非,故其偽經得乘虛而入,蔽掩天下,皆假校書之權為之也。
將《史記》載“秦焚書,書散亡益多”視作劉歆“乘虛而入”、偽竄六經的竄入之地。據此,劉歆才能冠漢代學術以“書缺簡脫”“學殘文缺”,以便“假校書之權”,全面偽經,推行古文經學。其實,這里有一個秦焚書對文化破壞程度的評估問題。康有為的潛臺詞是,雖然有秦焚書在先,但秦博士所藏圖書依然完整,不存在“書缺簡脫”“學殘文缺”的問題。所以“書缺簡脫”“學殘文缺”云云,都是劉歆人為制造偽經的借口。
其次,康有為認為,劉歆亂《史記》、撰《漢書》,為偽造古文諸經做鋪墊。對于后世學者而言,有關漢代的背景材料,只有記載國史的《史記》《漢書》為人信據。康推測劉歆的心理:劉歆為了兜售古文經典使人相信,先在《史記》《漢書》上下功夫,有意在司馬遷《史記》中竄入了古文經之事。在康有為看來,歷史上從來不曾有古文經之事,所謂古文經之事純粹是劉歆制造出來,加入歷史中來的。而《漢書》中記載古文經的材料非常之多,所以康有為破天荒提出“《漢書》為(劉)歆所作”而非班固所作。
《史記》《漢書》所記之言、所記之事,晉代以后之人已不能盡明,因而有南朝裴骃的《史記集解》、唐代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司馬貞的《史記索引》,以及唐代顏師古的《漢書注》等。諸人皆為一流的學問家,皆不曾言及劉歆偽竄《史記》、親撰《漢書》。況且與《史記》《漢書》時代相近的文獻資料甚少,像劉歆偽竄《史記》、親撰《漢書》這類議題本無資料加以證實,康有為以臆斷式的推論來立論,是欺世人難以證偽其說。然而,與康有為同時代的洪良品即起而反駁,他根據《史記》《漢書》記載,結合《史通》《二十二史札記》等后人考證,論證劉歆曾續撰《史記》,而非竄亂《史記》;《漢書》作者確系班彪、班固父子,而非劉歆。
在我們看來,康有為為證劉歆偽經,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但他這樣說的結果,卻間接把劉歆塑造成了文化巨人。你看,以劉歆一人之力,能夠偽造多種古文經典,能夠創造出一套系統的“古文”字體,能夠編撰出前四史之一的《漢書》來。若非文化巨人,誰能有如此宏大的文化成就?以至章太炎說:“孔子死,名實足以伉者,漢之劉歆。”這是不是對康有為的反諷呢?
最后,康氏為了證明劉歆的能力和能量,論證劉歆憑其家學淵源與絕人之才,借王莽之權與私人、私黨、故智之力“傾售”偽經。劉歆“上承名父之業,加以絕人之才,故能遍偽諸經”。劉歆、王莽互相利用,“歆既獎成莽之篡漢”“莽又獎成歆之篡孔”。康氏推論,兩漢倡導和推行古文經學的,都是劉歆的私黨、私人、故智,私人百數、故智千數。“私黨”主要是與劉歆同事一朝者。歆為國師,受莽尊信,故《說文序》列“爰禮、楊雄、甄豐皆其私黨”。“私人”,即“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此百數人被征者,必皆歆之私人,奉歆偽古文、奇字之學者也”。“故智”乃王莽所征通古文經者。因“劉歆工于作偽,故散之于私人……如古文經傳,授之私人,及王莽奏征天下通《逸禮》、古《書》《毛詩》《周官》……詣公車,至者千數,皆其故智也”。
就此,洪良品、符定一、錢穆三人直言,漢代今、古文經學之間如冰炭般互不相容,今文家何以不直指劉歆偽經?洪良品認為,劉歆責讓的太常博士為何只說劉歆“非毀先帝所立”經典,對康氏所謂劉歆“私改詔書”之罪,夏侯勝、師丹等對劉歆“懷恨怨怒”之人,“何不發其增改詔書之罪,甘受其責”。符定一也說:“太常為大庭廣眾之地,歆即膽大妄為,決不能向太常博士任意虛構,將無說有,假使捏造事實,而博士怨恨,三公大怒,豈有不指摘其作偽者。”就康氏所謂劉歆“預布”售書之人,錢穆指出:“此數千人者遍于國中四方,何無一人泄其詐?”尤其是與劉向、劉歆父子同校書的尹咸、班斿、蘇竟、校書天祿閣的揚雄,桓譚、杜林,以及師丹、公孫祿、范升等深抑古文諸經者,既無一人說劉歆偽經,也無人發現其偽經跡象。且“《偽經考》謂所征通小學者皆歆偽遣,又謂(揚)雄從歆學,則奇字亦出歆手,(劉)棻何忘其家丘而轉學從雄?”
我們以為,如果真如康有為所說那般,王莽、劉歆互相利用,劉歆能量巨大。為什么王莽不久敗亡,遭到清算,而劉歆卻沒有遭到清算,他所倡導的古文經學反而在東漢時期如日中天一般發展起來,涌現出如鄭興、鄭眾、賈逵、許慎、馬融、鄭玄、服虔等著名古文經學家,難道他們都是誤信劉歆偽經的受騙者嗎?可見,康有為為了使今文經學發皇光大,向古文經學發起瘋狂的挑戰,并且造成巨大的文化影響。應該說他借助了晚清社會要求變革的時勢力量,不能說他手里掌握了真理。
三、關于康有為坐實“劉歆偽造壁中書”及其論辯
如何坐實劉歆偽造“壁中書”?康有為有其論證的邏輯起點、論證原則。然而,其邏輯起點和論證原則都不能成立,而且自相矛盾。
第一,邏輯起點——“秦焚書未嘗亡缺”。康氏先認定秦雖有焚書之令,“若博士所職,則《詩》《書》百家自存”。繼以《史記·儒林列傳》為基礎,定“六經”未曾亡缺,故后世新出古文就是偽作。他還先假定“劉歆偽作諸經”。《偽經考》開篇就說,“始作偽,亂圣制者,自劉歆”,“后漢之時,學分今、古,既托于孔壁,自以古為尊,此新歆所以售其欺偽者也”。后又力證“西漢新學皆系于偽”。
其實,康有為這一邏輯起點并不能確立。先不說“博士所職,則《詩》《書》百家自存”是否事實,即便如此,也不能預判古文經典一定不會問世。國家秘府所藏,一部典籍就可能有多種寫本,而有秘府校書確立定本的事務。而一經校訂成為定本,便以今文——隸書的形式在社會上傳寫流布。此后,由于各種因緣,原來藏在山巖屋壁的六國時期的簡帛文獻寫本就有可能陸續出現,因為文字書體與今文不同,而被稱為“古文”經典,它不僅文字書體不同,篇章內容也有所不同。漢代已是“尊經”時代,“古文”經典因為距孔子時代更近,更接近孔子原意,所以受到熱愛古文經學的學者的重視和推崇。這本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康有為認定“六經”未曾亡缺,后出古文經典皆是偽作,這種推論是相當武斷的。
第二,論證原則——凡《史記》《漢書》記載不同,全從《史記》,以“史遷不載”為金科玉律,力證《漢書·藝文志》所載壁中古文為劉歆偽造。一是不容司馬遷有失,其未見、未說的,都不足信。康氏認為,史遷曾親登孔子堂,“未嘗言及孔廟所藏之六經有缺脫而嘆息痛恨之”。遷既親見,“若少有缺失,寧能不言邪?”更有甚者,“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不容不見矣”。二是對比“壁中書”與今文經,史遷不載,即為偽經。他說:“(《詩》)三家之外,史公無一字。”“史遷征引《左氏》至多,如其傳經,安有不敘?”足見康氏以《史記》為辨偽的根本參照,將《漢書·儒林傳》所涉古文舊事,如“綴周之禮”“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中的“為之傳”“六學從此缺矣”,視作劉歆“增竄”“暗竄”“復竄”,得出“《史記》不著,蓋出劉歆之所偽”的結論。對此,贊同者如顧頡剛認為:“我們可以用康長素先生的方法,拿《史記》《漢書》的兩篇《共王傳》來比較……這真奇怪:為什么《漢書》全鈔《史記》,卻多了‘壞孔子舊宅,于壁中得古文經傳’的一事呢?”足見其不僅贊同康說,更推崇其對讀比較的方法。顧頡剛將康氏所謂劉歆“征天下異能之士”以售經視為“毒辣”,說:“這件事情,手段非常毒辣,一方面把古文學的種子散播到民間,一方面又令今文學增加許多敵人,凡古文學家的眼光中感到的‘乖謬’和‘異說’都掃空了。”痛恨之情可見一斑。
反對者則竭力駁正康氏《史記》《漢書》對勘法。因為,康氏既認定《史記》是劉歆偽竄之書,又在《史記》《漢書》比勘中唯《史記》是從,以偽證偽,實難令人信服。《史記》是否劉歆偽竄,朱一新認為:“若《史記》言古文者皆為劉歆所竄,則此二傳(《河間獻王傳》《魯共王傳》)乃作偽之本,歆當彌縫之不暇,豈肯留此罅隙以待后人之攻。”符定一則認為,《史記》不止一人一家,“歆何能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遍改民間所有之《史記》?”
比勘《史記》《漢書》,唯《史記》是從,康氏論證謬誤有二。其一,朱一新、洪良品都認為康氏對于《史記》所載“合己意者則取之,不合者則偽之”。故康氏以《史記·儒林傳》立論,卻有意無視《史記》所載“孔氏古文逸《書》十余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起其家”。其二,康氏以其所謂劉歆偽竄之《史記》證劉歆撰作之《漢書》,謬誤更甚。故洪良品對梁啟超說:“信如尊言,則《史記》為竄亂不可辨之書矣。何以貴師(康有為)必專據此書,但于其中有合己意者,則曰鐵案不可動搖;有不合己意者,則以為劉歆所竄入。”批判康氏對《史記》的取舍,態度極不客觀。符定一也認為:“康(有為)謂《史記》(劉)歆竄,《漢書》(劉)歆撰,焉用引之;《別錄》(劉)歆依托,焉用援之。既張其盾,復建其矛,以矛攻盾,遁詞知其所窮矣。”更有甚者,“《西京雜記》為偽書,姚際恒《古今偽書考》辨之已詳”,康氏大量引用姚說,又以姚氏所辨“偽書以攻人之偽,謬妄實甚”。
漢初推行黃老之學,直到漢武帝時才推行董仲舒“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建言。這時朝廷所能做的,只是網羅儒學耆舊,對于儒家經典的研究才剛剛啟動和展開。司馬遷是漢武帝時代人,所以《史記》中只有《儒林列傳》,專注于當時傳經之儒的記敘,而沒有如《漢書·藝文志》那樣的篇章,詳述典籍的匯集和概述。以《史記》所未載斷言后世文獻皆偽作,那《漢書·藝文志》所載,豈不全是偽書!康氏這個論證原則顯然是說不通的。
四、結論
康有為撰《新學偽經考》,將漢代所出古文經典,關系漢代經今、古文之爭的核心內容——“壁中書”全歸劉歆偽造,實際是為其倡導變法的政治目的張本。就此而言,康有為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其政治目的。在今人看來,康有為倡導變法的政治目的是正當的,因而對其《新學偽經考》中武斷的學術見解多持一種寬宥的態度。但是我們更欣賞馬克思的觀點,一個正當的目的,不能使用不正當的手段來達到,因為“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當的,目的也就不是正當的”。因此,我們并不應當寬宥康有為的這一思想方法。
也有學者提出康有為所使用的“疑古辨偽”的考證方法,對“古史辨派”產生了重大影響,這的確是一個事實。現代“古史辨派”的領軍人物顧頡剛就特別推崇《新學偽經考》考辨古史的方法。“古史辨派”沖擊并矯正了盲目信古的史學痼疾,對于科學研究古史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古史辨派”的過分疑古,也對史學研究產生了負面作用。這是學術界所應認真反省和檢討的。
從經學歷史的實際情況和康有為的論證來看,康有為的“壁中書出自劉歆偽造”之說,既不符合經學歷史的實際情況,在論證過程中又存在主觀臆斷、牽強附會、自相矛盾等種種錯謬,自然會激起晚清、民國關于經今、古文全面之爭的激烈論辯,促成晚清、民國的經今、古文之爭。其實,中國傳統典籍和歷史中有非常豐富的社會變革思想可供倡導社會改革之用,康有為未能從傳統經典中吸收這些養分,殊為可惜!而其隨意借用經今、古文之爭的歷史倡導變法,以致故意迂回曲折地歪曲史實,則是吾輩學人應當引為鑒戒的教訓。
注釋
①現有關于《新學偽經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來源、初刊、古籍辨偽價值、論說邏輯、反響、禁毀、康有為今文經學與晚清政局之間的關系,以及對《新學偽經考》的重新審視等方面,主要成果有:李耀仙:《廖季平的〈古學考〉和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5期;胡建華:《首請禁毀〈新學偽經考〉者非安維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陳占標:《〈新學偽經考〉初刊年月考》,《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朱維錚:《重評〈新學偽經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2期;張勇:《也談〈新學偽經考〉的影響——兼及戊戌時期的“學術之爭”》,《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吳仰湘:《朱一新、康有為辯論〈新學偽經考〉若干史實考——基于被人遺忘的康氏兩札所作的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1期;賈小葉:《戊戌時期的學術與政治——以康有為“兩考”引發的不同反響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於梅舫:《以董生正宋儒:朱一新品析〈新學偽經考〉旨趣》,《廣東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孟永林:《安維峻首請禁毀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補正》,《文史檔案》2014年第3期;張欣:《康有為今文經學思想與晚清變局》,南開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6月;李少波:《〈新學偽經考〉古籍辨偽平議》,《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黃開國、黃子鑒:《〈辟劉篇〉與〈新學偽經考〉的比較》,《孔學堂》2017年第2期;於梅舫:《〈新學偽經考〉的論說邏輯與多歧反響》,《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5期;申海濤:《求真與致用:〈新學偽經考〉的重新審視》,《理論月刊》2019年第11期;皮迷迷:《以“今古之辨”解“漢宋之爭”:一個考察〈新學偽經考〉的視角》,《人文雜志》2020年第5期。對康有為以今文經學非難古文經學的核心——“壁中書”出自劉歆偽造的論辯,則幾無論及。②〔漢〕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年,第315頁。③④⑩〔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1707、1722、1969、212頁。⑤〔唐〕房玄齡等:《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第1649頁。⑥〔唐〕孔穎達:《尚書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115頁。⑦〔南朝·宋〕范曄:《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第2116頁。⑧〔晉〕杜預:《春秋左傳集解》,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897頁。⑨〔唐〕朱長文:《墨池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八一二),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615頁。〔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1706頁。按,《漢書·藝文志》作“《禮記》”,但段玉裁結合《漢志》《說文解字》記載,認為是《禮》《記》,并說:“所謂《禮》者,禮古經也……《記》者,謂《禮》之記也。”《漢書》,第1318頁。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中華書局,2012年,第31、57、391、29—30、30、55、71、5、47、60、143、111、103、103、5、2、3、10、19、19、22、38、127、36頁。符定一:《新學偽經考駁誼》,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18—19、19、55、2、65、64、10、5、1、7頁。〔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 附古文尚書冤詞》(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02頁。〔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第3125頁。〔清〕洪良品:《洪右丞給諫〈答梁啟超論學書〉》,葉德輝編:《翼教叢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57、51、53頁。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61、8、2、108、48頁。章炳麟著,徐復注:《訄書詳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1頁。顧頡剛:《古史辨序》,《古史辨》(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頁。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32頁。〔清〕朱一新:《朱侍御答康有為第二書》,葉德輝編:《翼教叢編》,臺灣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14頁。馬克思的德文原話為:“Wenn der Zweck die Mittel heiligt, dann ist der Zweck unheilig.”又翻譯成“需要不神圣的手段的目的,就不是神圣的目的”,或者“用不正當手段達到的目的,不是正當的目的”。參見中共中央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