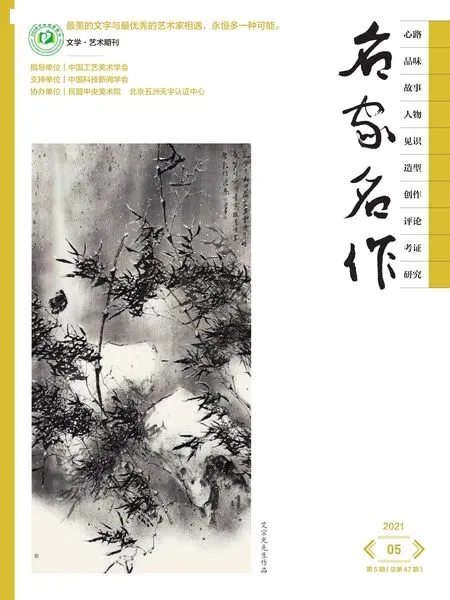探討杜尚“羅絲·瑟拉薇”中的哲學理念
陳星儒
一、“羅絲·瑟拉薇”:愛神就是生活
“羅絲·瑟拉薇”的藝術形象早在杜尚給蒙娜麗莎畫上胡子等一系列雌雄同體作品中已有端倪。1915年,杜尚在電影院觀看卓別林的電影《女郎女狼》,在電影中,卓別林用以假亂真的方式扮演女人以避開是非,耍弄了女朋友的父親。杜尚從中獲得了靈感。在這之前,杜尚曾想過創造一個擁有猶太人名字、帶有宗教色彩的身份,但雌雄同體形象似乎更有震撼力。“羅絲”無論在美國還是法國,都是一個大俗名,“瑟拉薇”是c’est la vie的雙關語,意思是“這是生活”。在《杜尚傳》中“羅絲·瑟拉薇”還隱含生活就是美好、玫瑰就是生活,這顯然是愛神,愛神就是生活的意思。這顯然還隱喻《會飲篇》里凡間的阿佛洛狄特(愛神),她本性上一部分是女性,一部分是男性。
在傳說中,人類應該有三個性別,男性最初是由太陽生的,女性是由大地生的,而第三個性別,亦是陰陽人,是由月亮生的,因為月亮是太陽和大地的結合體,同時也是人類的本性。陰陽人后因試圖攻擊諸神,被宙斯劈成兩半,一為男,一為女,終生需要尋求另外一半。但這里的另外一半,最初不是指兩個人,而是指每個人能融合為一體的另一半。其原因就是這是我們最初的自然狀態,我們過去是完整的個體。“羅絲·瑟拉薇”之于杜尚,就像找到了自己的愛人并恢復最初的本性,這是理想的狀態。因此,在曼·雷的鏡頭下,裝扮優雅、頗具女人味的“羅絲·瑟拉薇”應運而生,并作為人物肖像成為《名利場》雜志標桿性的圖片。
二、文字游戲:藝術與語言
“所有的這一切不過是文字游戲罷了。”文字的趣味性讓藝術成為“文學”,杜尚認為思想和語言能讓藝術變得富有智慧,雖然他的語言哲學也是戲謔的,就跟他的“戲謔物理學”一樣。“羅絲·瑟拉薇”從字面意思到她的行為舉止都跟文字游戲分不開,她是杜尚的語言“繆斯”。有了羅絲·瑟拉薇這個身份之后,他就創作了《新寡》(版權歸羅絲·瑟拉薇所有,1920年),作品原標題為“法式窗戶”,用英文表達則是“French Window”,但后來從每個詞中拿掉了一個“n”,使語言轉變,最終演變成一個文字游戲,即為“fresh widow”(新寡),隱含快樂的寡婦,在俚語里就用“寡婦”來表示斷頭臺,這也是杜尚一向慣用的話題。
在福柯的話語理論里,提出話語狹義上指語言的具體運行,它體現了一種力量,包含著權力、意向和價值取向,而且顯示了話語主體的社會位置、社會關注和社會身份。杜尚通過文字游戲進一步完善“羅絲·瑟拉薇”的形象,使這個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也是為接下來的創作埋下伏筆。接下來,杜尚應卡特琳·德利埃的要求,創作了一個名為《羅絲·瑟拉薇為什么不打噴嚏?》的現成品,這是一個小鳥籠,里面裝滿了石制的“方糖”,還放了一塊墨魚骨和一支溫度計。沉重的“方糖”給人一種三維的假象,似三維的象棋盤,也似是對立體主義那些空間理論的玩笑。而溫度計顯示的低溫則給人一種冷冰冰的感覺。標題寫在鳥籠底下,這暗示著感冒(溫度計顯示低溫的隱含),但也暗示著射精,這又是他慣用的伎倆。
杜尚為了認可“羅絲·瑟拉薇”這個形象,在《紐約達達》上刊登了由曼·雷拍攝的一張她的頭像印在香水瓶標簽上,極具現代裝飾藝術風格的照片,標簽上還寫著這樣的文字:“美妙的氣息/短面紗香水/R.S./紐約—巴黎”文字中隱喻著女性的特征,短面紗與紫羅蘭寫法相似,在20世紀20年代初,紫羅蘭是香水制造業最常用的香型。杜尚在文字上的運用,基于藝術就像語言的語境下,藝術的本質就是“思想”,有了思想或語言,藝術就能為心靈服務,且讓藝術變得富于智慧。“羅絲·瑟拉薇”之于杜尚的藝術話語中具有語境的意義,使現成品成為一種具有社會文化心理深意的綜合性構建與表達。
三、身份“次厚度”:性別的分界線
在《杜尚密碼》中提出揭示杜尚的身份游戲,探究“羅絲·瑟拉薇”的創作階段對應的“次厚度”,對杜尚藝術創作轉向本質性的思考。書中提到“次厚度”是一種厚度,這種厚度是無限的薄,幾乎摸不著,但是確實是真實的存在。杜尚的筆記中曾提到幾十種“次厚度現象”,例如,影子的“次厚度”,嗅覺的“次厚度”等等。而阿美利亞·瓊斯在《后現代主義和馬塞爾·杜尚的性別生成》中重點闡述了“次厚度”這個概念。她提出,杜尚很多作品都是關于性別界限的,在杜尚那里,性別界限是不停變動的,男女性別不是由固定界限分割的對立場,而是相互交織、相互滲透、相互依賴的非確定域,而“次厚度”這個概念尤為體現杜尚的性別觀。“次厚度”界定區別又排除區別,其意味區別是自身與他者的聯系,尤其在性別方面,但是“次厚度的區別”揭露了自身與他者之間界限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
杜尚用“次厚度”消融了界限,解構了自身與他者、制作者和觀者、在場與不在場之間的穩定條框。“羅絲·瑟拉薇”作為杜尚的性別藝術,顛覆了現代藝術家英雄式的男權形象,且處于“次厚度”的第一層含義中,成了男女性別的分界線。在《杜尚密碼》中提出了“次厚度”的三層含義,其中第一層含義指自身與他者之間的分界線不是一維的,而是帶有一定厚度、身份模糊的過渡地帶,它既含有自身又含有他者,既不是確定的自身也不是確定的他者,它連接著兩個異質體,是自身與他者的橋梁。
“羅絲·瑟拉薇”這個身份是杜尚在承受“身份”所帶來的苦惱(杜尚母親喜歡女孩,但杜尚卻是個男孩;杜尚喜歡妹妹,卻不得不面對妹妹嫁人的現實,因為他是妹妹的哥哥,以及因作品不符合立體派的規矩而被拒)之后,為否定自身與他者的區別,制造出來的“次厚度”分界線。在香水瓶的商標上,“羅絲·瑟拉薇”名字的縮寫“R.S.”中的“R”以反字的形式出現,就像字母“R”的印刷模板。模板上是反字,印上去卻是正字,看似二元對立的性別卻是相互生成的關系。這似乎暗示了“玫瑰”具有向他者轉變的可能性,自身向他者過渡,發生在“次厚度”中。“羅絲·瑟拉薇”可謂是典型的“次厚度”性別分界線。
四、杜尚“羅絲·瑟拉薇”與禪宗哲學
杜尚給朋友、家人寫的信封上都會簽上羅絲·瑟拉薇的名字。從一開始把她當作一個現成品,到后來,經過杜尚對她的人物形象的不斷完善 ,“羅絲·瑟拉薇”活了過來,作為另一個杜尚,抑或就是杜尚本人。杜尚作為一個將藝術和生活結合在一起的波希米亞人,他一生隨波逐流,對事物“漠不關心”,除了“呼吸”之外沒有更大的野心。杜尚的藝術哲學觀念不同于西方傳統一貫的哲學觀,反而更加傾向于東方禪學中視生活為藝術的哲學理念。杜尚的為人和藝術都貫徹著禪的真理:一種單調乏味的生活,索然的平凡生命,變成一種藝術的、充滿真實內心創造的真理。
“羅絲·瑟拉薇”除了在文字游戲中和藝術品上作為署名外,她還出現在杜尚日常的言行中,例如,羅絲·瑟拉薇一直要睡到午后才起床,然后給朋友們寫幾封信:“我把大玻璃弄回來了,還要一直做下去。真讓人厭煩!看不了電影,沒有任何娛樂活動!”這就如同禪意義中的無意識,也是禪宗宣稱的“平常心”。關于禪宗的無意識,以下一對問答足以明了——當一位和尚問一位禪師,什么是“平常心”,他回答說:“餓了吃,困了睡。”杜尚雖然從來沒有參過禪,也表示過對東方的事物不感興趣,甚至不是一位哲學家,但他的哲學觀念卻近似中國老子的有無相生、是非混淆的哲學。他秉持著這樣的觀念踏進藝術的領域,并且把這種混淆區別,以無牽無掛的人生態度對藝術進行一個大改造。杜尚自己也說過:“如果你愿意,我的藝術就是我的生存,在每一瞬間、每一次呼吸之間都是一個作品,一個不露痕跡的作品,那既不訴諸視覺,也不訴諸大腦,那是一種持續的快樂。”杜尚的這種精神就是禪的精神。
五、結語
綜上,“羅拉·瑟拉薇”之于杜尚,始于身份游戲,但不僅如此。她涵蓋著杜尚的生活哲學,她既是杜尚的現成品,也是“杜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