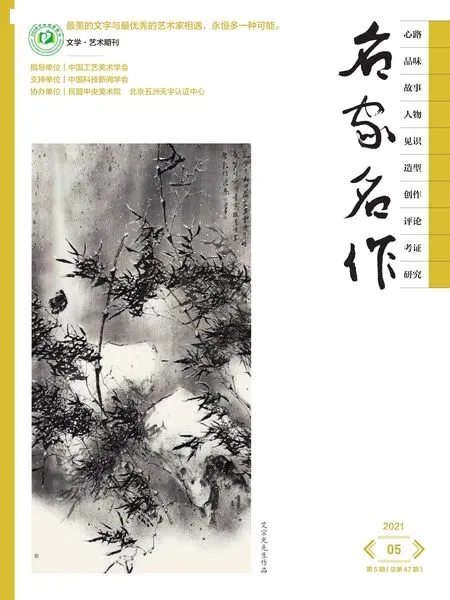迷霧中生長的“惡之花”—影片《風中有朵雨做的云》中小諾人物形象轉變與時代反思
王一順
《風中有朵雨做的云》這部影片是婁燁藝術影片創作與類型敘事結合的一次嘗試,故事背景設定在改革開放期間,小市民奔走于多地尋找出路,處于城市邊緣空間的社會底層人物,為了追逐金錢與名利而陷入復雜的情感糾葛及利益沖突中。
小諾作為獨立的“第三只眼”,是影片暗含的關鍵因素,她既是隱匿在事件中的參與者,也是事件發生的旁觀者。小諾的成長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少年、處境優渥的成長期及逐漸異化的青年時期。小諾少年時得知原生家庭支離破碎,目睹母親被家暴并受制于男權規訓無力反抗;成長期的小諾伴隨快速閃過的富人景觀空間鏡頭逐步擺脫乖乖女的形象,而她頭戴的假發也賦予她一種身份的替換和他者的頂替;云阿姨死后,小諾對于金錢利益及虛假情感的厭惡由內心的壓制轉向爆發,在承受了超過自己承受范圍的感情和利益的人性旋渦后,小諾走向深淵,善與惡的是非界限在社會侵蝕下瓦解。
一、小諾與“父親”:性格初期的扭曲
在主流秩序中,男性無疑占據著主導地位,而女性則處于“被動的”“被觀看的”從屬位置。影片中唐小諾十歲就深知自己的真實身世,卻只能稱養父為父親,稱生父為叔叔,在這種扭曲的認識下自我的價值觀開始形成。
小諾的生母林慧作為弱勢女性對于唐奕杰情感的背叛終究會遭受懲罰,“由于這種‘下意識’的本能沖動(即libido,‘力必多’)和社會倫理的外在約束形成了一種張力,要突破這種張力,本能的沖動最終實現自己的欲望時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創傷,其反映出來的形式就是精神病”,林慧被當作間歇性精神病患者,關入帶有現代精神規制意義的精神病院,而尚處少年時期的小諾目睹事件經過,卻不得不受約束于“父親”的管制,這也構成小諾最初產生殺人動機的因素。當楊家棟在瀏覽小諾的私人信息時,發現小諾的“陰暗面”,暗黑色調的網絡空間映射出小諾內心的扭曲異化,置頂文章《關于惡人的一千種死法》更是毫不掩蓋地表現暗藏已久的報復心理:“我更喜歡古代,死刑有好多種花樣……”這種帶有原始野蠻色彩的極端化方式暗示了女性意識的覺醒,也為真相的解開埋下伏筆。當小諾得知“云阿姨”是被自己最信任的親人殺害時,小諾最后一道心理防線被沖破,將這種恨意轉向使她內心受到傷害的“父親”身上。
小諾的經歷無疑是悲劇性的。姜叔叔在小諾心中扮演著理想型父親的形象,但在小諾的童年時期,姜紫成始終處于“不在場”的位置。林慧意外懷有他的孩子,卻因利益關系不得不與“老實人”唐奕杰結為夫妻,“家庭則被形構為一種擠壓差異性、異質性個體抑或群體的被賦予了文化話語的城市空間意象”,小諾在目睹母親林慧被親生父親姜紫成利用,用女性身體算計他人,而與自己有深厚情感的另一女性云阿姨也難逃死亡的命運時,對于父性權力的反抗早已暗自生根。影片結尾,姜紫成因多項罪名被起訴,小諾是傷害養父唐奕杰的真兇的謎題揭開,她的“報復”得以實現,卻終究難逃法律的制裁,這也是人物命運的最終歸宿,不存在絕對的勝利與善惡本性,固有權力依舊是橫在人物關系之間難逃的準則。
二、小諾與楊家棟:成長期的懵懂情感
年輕警官楊家棟對于小諾而言是陌生的外來者,楊家棟帶有調查真相的使命,而小諾則是真相本身最重要的一部分,這層關系使得二人之間必然發生矛盾糾葛。當她發現原本處于正面的楊家棟也被迫陷入陰暗中——“艷照門”事件,她的價值觀也在逐漸崩塌,“你們自己臟就算了,為什么把別人拖下水”,小諾此時產生共情因素,所謂的“別人”同時也在觀照自我,自出生起便帶有混亂的身份符號,以至于無法形成完整人格。這種命運的交織也使小諾對楊家棟產生特殊情感,同時也隱含對自我悲劇命運的暗自憐惜。
弗洛伊德將人格分為三重,即本我、自我與超我,“超我”是小諾缺失的成為完整主體的部分因素,她所認識到的人物關系均帶有復雜的利益糾葛,為了實現目的利用肉體及暴力等手段,無法通過符合道德良心及自我理想的約束做出行為選擇,這也是小諾最終變為殺人兇手的關鍵誘因。而小諾身份中隱含的本我力量是強大的,本我中帶有的潛意識即是一種本能欲望,小諾私下單獨約見楊家棟,公然外放媒體對母親林慧的圍追堵截,深夜發送曖昧信息,這也印證了弗洛伊德所得出的悲觀主義結論:“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其身上各種非理性力量無比強大,只有極少數堅強的人才能過上理性的生活。”在燈紅酒綠的都市夜店,小諾衣著露骨、頭戴假發,特寫鏡頭下看到她望著楊家棟暗自流淚,在無人的街邊,小諾終于發問:“你愛她嗎?你會跟她上床嗎?你有女朋友嗎?你有喜歡的人嗎?”語言指向逐漸由他人轉向自我,利益互換式結合的原生家庭讓小諾迫不及待地尋找內心渴望的純粹情感,目睹母親被施暴并得知家庭錯綜復雜關系的小諾對性產生了疑問和恐懼,對男女關系的認識產生了畸變。
小諾與楊家棟之間的關系是畸形的,楊家棟的身份對于小諾而言含有壓制性,而在相處過程中卻產生了別樣的情愫。這種情感在楊家棟看來包含一層利用關系,借以獲取更多對偵破案件相關的信息,而對于小諾,這種像云一般虛無縹緲的聯系隨時面臨毀滅,她所得到的欲望的釋放也因此展現出珍貴的、超脫于傳統理念束縛的一面,小諾對于純粹情感的向往,也展現出她人性的單純的一面,而人物在經歷過痛苦后對于美好的嘗試卻更顯凄涼與傷感。
三、小諾與女性角色:異化人格形成
家庭的倫理錯位參與構建了小諾的陰影原型,陰影中“惡”的因素并沒有被消滅,她所以為“善”的一面也在逐漸消解,這種復雜認識退回無意識中,并融合進限知視角敘事并最終在故事結尾實現小諾的身份轉換。
小諾作為多元力量發生碰撞后形成的結果符號出現。母親林慧在小諾看來是帶有缺陷的個體,因為她不但給自己營造了畸形的家庭環境,更可悲的在于面對父親唐奕杰的施暴,林慧做出的選擇只有順從與忍耐,在物質上給予小諾滿足,這也使長大后的小諾混跡于各種雜亂的圈層,產生低水平的炫富行為。
影片中小諾生母林慧被從精神病院接出后,她與連阿云、姜紫成、唐奕杰相繼實現了利益膨脹。在一連串交代事件的快剪鏡頭后,一場面具舞會以狂歡式的形式出現。值得注意的是,云阿姨以魅惑的成功女性形象出現在小諾面前,小諾第一次注視連阿云的假發,充滿著新鮮感與仰慕,小諾第一次戴假發自拍也是在復刻連阿云為其營造的富人景觀,依托財富找到短暫的精神補償。
雖然小諾目睹云阿姨與養父唐奕杰之間的茍合,但是云阿姨對小諾的溫柔與關愛是小諾迫切需要且獨有的。二人單獨存在的空間縈繞著暖色調的舒服自在的氛圍,在布滿霧氣的鏡子前,她們寫下了自己的名字,阿云告訴小諾:“小諾長大了要懂得保護自己,不要受人欺負。”這種鮮明的自我認知觀念對于小諾而言是具有成長意義的。在拉康的鏡像理論中,“主體與它的形象之間的動態關系表示的是人類個體一種孜孜以求的永久趨向,這種趨向引導人類個體終其一生都會追尋并培育一種理想自我的、想象的完整性”。兒時的小諾衣著普通,看起來與尋常人家的孩子并無太大差異,而長大后的小諾習慣性地戴著色彩靚麗的假發,性情乖張又叛逆,在最終的行兇時刻,她扮起了云阿姨的模樣,這是一種自我認識的轉變,她真的像阿云所說,在對抗中形成保護的力量,此時的形象塑造包含“他者”在成長過程中對本來面貌的影響產生的異化。
四、總結
婁燁的影片充斥著對人性的探討,在工業化生產對自然的侵蝕中,貪婪的物欲也在侵蝕人心。影片原型即是廣州冼村強拆案,這個破舊不堪的城中村隨時會消失,諷刺之處在于利益的糾葛是它依舊存在的原因。片頭一連串晃動的手持跟拍鏡頭將這片殘破磚瓦嶄露無遺,誰又能想到此時距離唐奕杰、姜紫成及林慧三人第一次舞會相遇已經過去將近30年時間,在這段時間內,唐奕杰官運亨通,拿下舊城改造區主任一職,而姜紫成憑借唐奕杰的政府關系在地產行業做得如日中天,林慧也憑借著資本積累大開酒樓,臺上風光的人物背后做盡齷齪之事。而可悲之處在于,小諾作為時代的新生命,卻又成為命運的犧牲品。
影片即將結束時,小諾低頭倚在河邊,條紋襯衣、黑色短發,一切仿佛歸于常態。她原本只是用雙眼觀察現實的局外人,卻被迫牽扯其中,喚醒主體的力量改變遭遇。然而她本身不具有足夠的力量,主體在惡性社會引導下的自主性選擇注定會釀成悲劇結局。小諾的身份代表著特殊時代背景下部分急功近利的人造成的情感缺失與人性泯滅,在電影時代敘事模式的探索下,現實得到反思,期望下一個小諾不再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