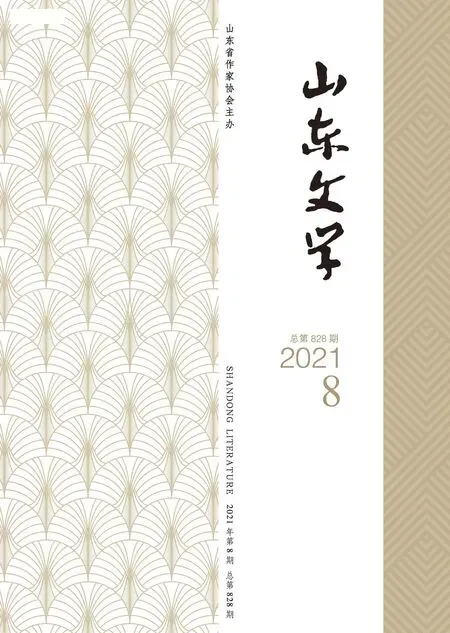居于幽處
呂 峰
1
舉頭三尺有神靈。
民間的信仰真是奇怪,日月星辰,金木水火土,風雪雷電,都有危害或庇護人的能力,也都藏著一位位神靈,值得人們祈禱、祭祀。民間信仰的生命力也極為旺盛,像運河水般綿長堅韌,也如同河灘上繁茂的茅草,砍不盡,燒不盡。在漫長的時光里,運河邊的村民們祭祀了多少神靈,誰也說不清,像河里的魚,不可數。
最早聽說的神靈,大約是樹精水怪,下河灘,進山林,大人們常在身后一遍又一遍叮囑,若是聽到有人叫你的名字,千萬不可回答,你一應答,魂就跟著那些精怪走了。在林子里也不能呼喚同伴的名字,都是“哎——喂——”地呼叫,免得讓那些精怪聽了去。其實,在幼小的心靈中,根本不知道害怕為何物,甚至幻想著能遇到一位精怪,看看它到底長什么模樣!
“混沌初開,乾坤始奠。氣之輕清上浮者為天,氣之重濁下凝者為地。”幼時,祖父讓我背,對我說這是天地的起源,后來才知道是舊時私塾的啟蒙書。對于千萬年、百萬年后的人來說,天地起源實在是太遙遠,太撲朔迷離。最熟悉的還是身邊的神靈、精怪,常常睜大了眼睛,從萬物之中尋找它們的身影。
每個村子都有自己獨有或與其他村子共有的神明,每個神明都有自己的生日或成道日,這些日子就成了黃道吉日,也成了廟會的緣起。每逢這些黃道吉日,整個村子便浸潤在狂歡之中。小孩子被大人裝扮成神話中的人物,穿上色彩斑斕的戲裝,紅臉,黑臉,白臉,花臉,也說不清是哪路神仙,有時禁不住想,這些不知來自何方的神靈,是因為什么機緣走進了村落,走進了人們的生活中。
村里人祭祀的神靈多不勝數,道家的玉帝、天師,佛家的如來、觀音,歷史上的張良、關公,乃至槐樹、龍王,統統成了膜拜、供奉的對象。它們可以同處一室,共享奉祀,共享人間香火。村里人的神靈崇拜,看似雜亂而沒有章法,實則有序可循。人們所跪拜的神靈均是真善美的化身,體現了人們所渴望的美、善、慈愛、力量以及智慧等。
灶王爺,顧名思義是灶臺上的神,也是最民間的神,他最懂得鄉間的疾苦。臘月二十三是辭灶的日子,一大早就聽祖母念叨:“人生天地間,莊農最為先。早晨二十三,辭灶在眼前。”這一天,要送灶王爺上天,向玉帝匯報百姓的生活。為了讓灶王爺多多美言,要殺一只大公雞,給灶王爺當坐騎。大公雞要那種紅冠、紅羽、金足的雞,還要好吃好喝地伺候著,燒一爐香,以保證來年鍋灶飄香,能吃飽肚子。
雞是村莊的居民,也是村里人最親密的伙伴,沒有一戶人家不養雞的,公雞,母雞,白羽雞,蘆花雞。公雞打鳴,負責叫醒村民,黎明即站在樹杈上望著東方,“喔喔喔,喔喔喔”,新的一天在它們的打鳴聲中拉開了帷幕。相傳茫茫東海有一座大山,山上有棵巨大的桃樹,樹根向周圍伸展,足足有三千里方圓,樹頂有一只金雞,謂之天雞,每天太陽剛剛升起,照到這棵樹上時,天雞便啼鳴了,它一啼,天下的雞都跟著叫起來。為此,公雞被視為迎接光明的象征。
母雞負責下蛋,下完了蛋,在院子里來回溜達,“咯咯噠,咯咯噠”,毫不掩飾自己的成果。村里的嬸嬸、大娘,沒有一個不養雞的。每年春天,村子里響起賣小雞的吆喝聲,“買小雞了,賒雞,買雞嘍!”她們聽了,蜂擁而至。新買來的小雞要用黃澄澄的小米喂養,要不了多久,它們就長到拳頭大小,公雞,母雞,一清二楚。家家都養雞,且都是放養,常有走錯家門的可能,主婦們有的是招應對,買來紅的、黃的、青的染料,在它們的翅膀、頭部或腹部點上標記,花花綠綠的小雞便在房前屋后瘋長。
養雞是母親必不可少的副業,下地勞作,不忘捉些蟲子,回來喂雞。家里的雞長得又快又壯,那幾只公雞,羽毛锃亮,像涂了一層油,光彩照人,是捆扎雞毛撣子的絕佳材料。宰殺,供奉灶王爺時,雞毛被母親精心收藏起來,以便閑了扎撣子。對生活的渴望,在一年一度的送灶中延續,生生不息。當然,雞也是可以成為神靈的,昴日星官,毗藍婆菩薩,都是民間有名的神靈。
過年了,門神年畫是少不了的。門神可驅邪迎祥,護佑平安。那時,對神荼、郁壘,對秦叔寶、尉遲恭,沒有什么概念,只知道花花綠綠的,特別好看,桃紅、粉紅、夕陽紅,黛紫、醬紫、葡萄紫,橙黃、鵝黃、檸檬黃,鴉青、天青、鴨卵青,豆綠、柳綠、松花綠等色,在一張紙上匯聚,洋溢著華麗的氣息,讓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
貼門神前,父親先將屋里屋外打掃一番,撣去積塵,掃去蛛網。打掃完,我端著一盆漿糊跟在父親屁股后頭。父親的樣子很虔誠,不像在貼年畫,反倒是把希望全部貼在那一扇扇不大不小的門上。貼過年畫,宅子洋溢著溫暖的氣息,流淌著闔家團圓的幸福。我喜歡看花花綠綠的年畫,每到一戶親戚家拜年,年畫是鐵定要看的。在這些年畫中,我熟悉了一段段歷史,享受了一個個傳說,結識了一位位人物,當然也對未來充滿了幻想與期待。
大年初一,穿上新衣,隨著父母,摸黑趕去幾十里外的奎山塔,搶先燒第一炷香,在煙火的繚繞中開啟新的一年。奎山塔為磚砌,毗鄰大運河漕糧廣運倉。相傳為紀念文曲星而建,可大振文風。塔身古樸蒼勁,巍峨挺拔,氣沖霄漢。塔旁有舊時的石碑,經過風雨的侵蝕,碑文已不易辨認,只能通過那些深淺不一的文字,去印證遠去的歷史。青煙繚繞,香氛彌漫,每個人的臉上都煥發虔誠的光輝,以期自家的孩子出入平安,出人頭地。
在運河邊謀生的人,對水有著天生的依賴,自然而然,掌握行云布雨之事的龍王爺也成了村民們祭祀的神靈。村子后頭有一座香火旺盛的龍王廟,廟里的龍王爺由上好的木料雕刻而成,臉膛紅里透黑,怒目圓睜,五綹黑髯飄在胸前,身著黃色長袍,端坐于神臺之上,不怒自威,讓人心生崇敬之情。龍王爺平時高坐于廟宇之內,接受村民的進香跪拜,所祈求的不外乎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六畜興旺。
每年伏天,村里人會把龍王爺請到村子里來,舉行龍王爺出行活動,場面極為隆重。隨著“噼里啪啦”的鞭炮聲炸將開來,浩浩蕩蕩的隊伍出發了。龍王爺坐在轎子上,鑼鼓喧天,鐃鈸齊鳴,人潮擁擠,爭先恐后搶著觀看龍王爺的尊容。龍王爺在村子里轉一圈,回到廟里剛落座,進香跪拜的人像潮水般涌來,齊刷刷跪在廟門內外,燒紙點香,口中念念有詞,祈求龍王爺保佑。
玉皇大帝,觀音菩薩,三太子,龍王爺,財神爺,灶王爺,華佗老爺,所有的神靈都是前人留下的寶貴遺產。在櫛風沐雨的年代,人與神靈之間,相濡以沫,生死相依,一起走過幽暗的歷史。人們像夜晚行路的孩子,正滿懷恐懼時,忽然看到了閃爍在遠處的燈,那種喜悅無法言表,渾身上下又充滿了前行的力量。
2
千年松,萬年柏,遠古歷史問老槐。
槐樹是最具滄桑感的樹,也是容易成精成神的樹。村口有一棵老槐,是村子里的風水樹。遠處看,像一把綠色的巨傘撐在那里。在陽光白云下,生機勃勃。立于樹下,樹冠如蓋,濃蔭蔽天。槐樹真如老者,反應有些遲鈍,或者說比其它的樹都沉穩。春日里,柳樹、楊樹已翠葉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小的嫩芽,星星點點,一層隱綠悄悄然,決不喧嘩,像養在深宅大院里的大家閨秀。
一日,從村口進進出出的人忽然嗅到了一股沁入肺腑的香氣,才驀然發現,老槐樹竟掛滿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槐花裊裊低垂,如瀑布般傾瀉四濺,花香熏人,人也沉醉。“暮春宅門前,槐花深一寸。”深一寸或許有些夸張,不過槐花是很香的,站在樹下,立時淹沒在堆疊的清香里。樹影婆娑,清香陣陣,人的心肝脾膽也微微沉醉地搖曳。
在村里人眼中,那棵老槐是通了靈的,給村子提供了無窮無盡的庇護。誰家的孩子若是受了驚嚇,到槐樹下祈禱一番,睡一覺,第二天就好了。有的孩子出生了,五行缺木,于是便認老槐樹為干爹,以期得到它的護佑。初一、十五,樹上系滿了紅綢帶,飄在風中,飄在白云下,如一面面旌旗招展,像突然長出來的翅膀,似乎在下一個瞬間,就會振翅飛去。
老槐樹下是村里人的聚集之地,人情冷暖,煙火故事,如同槐樹上的葉子,茂盛葳蕤。在那棵老槐樹下,我知道了山西洪洞這個地方,知道了那棵祖槐的傳說。那棵槐樹是天下槐樹的祖先,也是遷居人的見證。外遷時,人們從那棵古槐樹上折了一根樹枝,揣在懷里,隨著他們一起遷移。一路走,一路望,一路念,最后,扁擔斷了,腳板累了,雞鴨也飛了。人們停下了腳步,一個個初生的村莊就這樣拱出了稚嫩的頭顱。
村莊的誕生極具隨意性,或依著山,或傍著水,或偎著林子。人們對待那根槐樹枝卻無比的虔誠,將之插進土里,靜待發芽,然后看著它一天天長成蒼天大樹。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呵護下,那根樹枝終于長成了祖先樹般的高大、葳蕤。祖父常說,村子里的槐樹都是村口那棵槐樹的子孫后代,它們一起護佑著村莊,護佑著村莊里的老老少少。
村里人家的院墻內外,幾乎都栽有一兩棵槐樹。春夏之際,整個村子清香飄拂,溢滿鼻官。眼目觸及之處,一棵又一棵槐樹在綻放,滿樹繁花,閃著銀光。花朵綴滿高樹枝頭,一直開到高空。年幼的我,經常陶醉于槐花氤氳的香氣中,耳邊響起祖父經常哼唱的來自山西的民歌,“高高山上一樹槐/手把欄桿望郎來/娘問女兒你望啥子/我望槐花幾時開……”
窗外有一棵粗壯的槐樹,坐于書桌前,一樹濃蔭收入眼底。從春到秋,由晨到夜,任是經意或不經意的抬頭,都是滿眼的賞心悅目。槐花開時,我被來自夢中的花香喚醒,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卻又若有若無。睜開眼,望著滿滿一樹雪白,眼睛一亮,身心一震,眼前的世界燦爛而壯麗。
槐花好吃,可惜槐樹的枝杈很高,徒手不易摘到,且有被刺傷的危險。村里人也有絕招,用長竹竿綁粗鐵鉤,把鉤子掛在枝條上輕輕扭動竹竿,枝條應聲而斷。這時,用手在槐花串上一捋,掌心里滿是槐花,往嘴里一送,又香又甜。回到家,將槐花清洗、晾干、拌面,上鍋蒸吃。蒸吃外,可將槐花掛面糊拍成餅,用油煎至七八分熟,最后勾湯燉熟,有湯有水,當飯又當菜。
槐花開過,槐樹的葉子也日復一日的葳蕤、油潤。夏日的槐樹,巍巍然,郁郁蔥蔥,生機迸發,哪怕是驕陽當空,槐樹下依舊華蓋蔽日,再烈的太陽也不能穿透一片片細葉構筑的空間。到了秋季,隨著一場風的揚起,隨著一場雨的降臨,那一樹綠葉開始變成金色,如雨般紛紛飄落,我時常被樹葉的沙沙聲響吸引。
等一場呼嘯的北風吹過,樹葉落盡,黑褐色的樹枝粗壯有力,上面的鳥窩開始顯現出來,雖不知是什么鳥兒的窩,卻很容易讓人敬畏。冬天的槐樹上棲息著這樣那樣的鳥兒,都是屬于村子的鳥,最多的是麻雀、喜鵲,少見的有啄木鳥、白頭翁等。它們在樹上聚集、跳躍、鳴囀,說著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語言,營造出一派生命的氣氛。
一棵老槐樹,風中會跳舞。雨里能畫圖,天無絕人路。
在村口那棵老槐樹下,有一座簡易的小廟,供奉著土地老爺。廟是青石砌成的,長寬高也就一米多,里面是一尊石刻像,像前有香爐,香爐前有一塊青石板作神案之用,用來供放村民的供品。樹下,廟前,常年香煙繚繞,然后飛散,漫過山林,漫過河谷,最后浸入村莊,浸入大地深處,讓天空與大地變得更加慈悲而安詳。
廟小神大,土地爺是地方神,也是萬能的神,什么煩惱和希望都可以給他說,它與人無比親近,像自家的長輩。村運,災異、稼穡、出行、婚喪,乃至村子與村子、村里人之間的交往交惡,統統可以去問他,足見人們對它的信任。從廟前經過,時常見人在小廟前上香、磕頭、祈禱,燒上些火紙,給老爺許個愿,或許能消除災禍,實現愿望。那虔誠的神情,不由得讓你從心底深處滋生出一份虔誠。
土地廟旁邊是一口老井。夏天的晚上,男女老少都在井邊乘涼、聊天,孩子們圍著老井四處亂跑。玩累了,小心翼翼地趴在井臺上往下望,井水在月光的照射下,明晃晃,白亮亮,可清楚地看到我們的倒影。月光透過井邊那棵老槐樹的葉子斑駁地灑在井臺上,依稀看到井臺磚縫間長滿了濃密的苔蘚。井欄被歲月磨平、磨光,在黑暗中閃著神秘的亮光。井邊有蛐蛐在鳴唱,宛似天籟。
每一方水土都有一位土地神。每個村子的土地神都不一樣,但無一不慈眉善目,和藹可親。土地廟多位于村口,肩負著守護村子、守護一方水土的重任,也由此得到了村里人的虔誠敬奉。有時,去其他村子轉悠,總忍不住去看那些上了年紀的老樹,去看土地老爺的廟以及廟里的神像,看別村的土地老爺和村子里的土地老爺有啥不一樣的。
逢年過節,初一、十五,家家戶戶輪流到老槐樹下,到土地廟前,點上香燭,祈求老槐樹和土地老爺的保佑。繚繞的香煙中,村人似乎與老槐樹、與土地爺有了感應,似乎得到了它們的護佑。于是,祭拜完,歡天喜地地回家了。祖父說,過去還有隆重的祭祀儀式,全村男女老少,穿戴整齊,一起虔誠地叩拜,有德高望重的長輩念祭祀詞,“伏以土德厚深,萬民沾養育之恩……”
風中有棵滄桑的槐,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我為它幽幽地滋生出一種感動,一顆被世俗包裹的心也變得干凈澄明,思維也變得清晰。我與它無言相對的時間是幸福的、快樂的、滿足的,它讓我有了一種莫名的歡愉與心安。
3
對村里人來說,祖先永遠是最親近的神靈。
祖先逝去了,他們的肉體或骨灰埋在了河灘上或地溝頭,他們的靈魂依舊居住在宅子里。每家每戶都有一個長條幾,也就是神案。神案上有一個瓷質或銅質的香爐,中間供奉著祖先的靈位,以及觀音、佛祖的掛像。神案前終年氤氳著一縷香煙,在廳堂里,在院落里,在人的心上,在時空的深處,繞來繞去,不曾散去。
祖先居于天棚之上。在一間屋子里,將葦席掛于屋梁下,用于祖先們休憩。葦席是祖父用河灘上的蘆葦編織而成,閃著黃澄澄的光。每天晚飯,祖母要先將第一碗飯放于條幾上,敬獻祖宗。祖先享用完后,全家人才開始動筷吃飯。初一、十五,全家人要向祖先、神靈跪拜祈求保佑。若改善了伙食,祖母要把第一鏟菜,放到神案上。
從我懂事起,父親手把手教我的第一件事是祭拜祖先。面朝神案,磕三個頭,神案上香火繚繞,飄溢著一種神秘的香味。父親在一旁念叨著,“祖先保佑,祖先保佑”。我抬起頭,稚嫩的眼神在神案上來回游走,努力找尋祖先們的身影。父親那種虔誠,那種神圣,早已感染了幼小的心靈。
再后來,我開始力所能及地幫父親做些祭拜祖先的事兒,如把受潮的香一根根地掰開,如把供奉的水果洗凈晾干。父親邊忙乎邊說,你多學著點,以后要獨立祭拜,等你成了家,祖宗就帶在了身邊,他們會一直看護著自己的子孫后代。等你有了孩子,要傳給孩子。不論走到哪里,祖先以及居家的神靈都與他們同在。在香煙的氤氳中,我冥冥之中感受到了一種血脈相傳的力量。
父親講得最多的是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曾祖父是一位有著傳奇色彩的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村子里一些上了年紀的人,茶前飯后總離不開曾祖父這個話題。曾祖父身材魁梧,年輕時習過武,有一身的功夫,在那一帶極有名聲。相傳,有一伙土匪順著運河來到了村子里,橫行之時,曾祖父從外歸來。他看村子里亂成一片,急忙進村看個究竟,一聽是這事兒,二話沒說,走到那幫土匪中間,叉著腰說:“滾!否則,別怪我不客氣。”
那幫土匪哪能瞧得上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曾祖父,便一齊上陣,圍攻他。曾祖父揮起手腳,不到一鍋煙的工夫,那伙人全躺在了地上,見勢不妙,爬起來一溜煙地逃走了。后來,日軍入侵時,村子也不可避免地落入了他們的手里。在村外的橋頭上,駐扎了兩個日本兵。有一天中午,曾祖父持著雙槍,一槍把他們打死了。沒承想,最后被調查出來了,曾祖父由此被日本人槍決了。父親說,細究起來,你曾祖父應被追評為烈士,我們家應該屬于烈士之家。可惜,時光流逝,那段往事早已無從追溯了。
供奉神靈祖先的香是松木做的,那時常有制香的手藝人光顧村子。香是供奉之用,故不能說買香、賣香,要說請香,她們拖著頓挫的聲調在村子里來回吆喝,“請香——嘍,請香——嘍!”她們知道誰家需要請香,有時吆喝著就來到了家門口。每次她們來,祖母早已等在了門口。祖母把香細細端詳一番,然后放在鼻端聞一聞,用她的話說,這是供奉祖先的,容不得半點馬虎。
那些手藝人沒絲毫的不耐煩,最多說一句,“老姊妹,你放心吧,都是十幾年的老顧客了。”聽到此,祖母笑了笑,才將手上的香放下,請上一些。祖母有一個專門用來放香的香筒。香筒是梧桐木的,防潮防灰,上面雕著喜鵲登梅圖,喜氣洋洋。平日里,祖母十分珍惜那個香筒,比她的那個食盒還要寶貴。
松香的氣味可勾引起人的想象,即使是一個頑皮的孩子也會被吸引得意興飄飛。順著神案上煙香的紋路,似乎能游到童話里,游到夢境里。香煙中,我看到了虔誠無比的祖母,俯首低眉,雙手合十,靜心祈禱。祖母喜歡用手撫摸我,不分時間,不分地點。我喜歡在她的衣兜里歇息、打滾。睡覺時,她一邊隔著被子撫拍著我,一邊哼著不成調的曲子,偶爾打怔,吐出一句:“菩薩保佑,祖先保佑,長啊,長啊!”
村子里流傳著一種喚魂的習俗,孩子生病了,發燒了,被意外驚嚇到了,就要喚魂。晚上,家里長輩拿著孩子穿過的衣服,去村口,兜著衣服呼喚孩子的名字往家走。頭頂上的月亮透出點點昏濁的光,朦朦朧朧的,像瞌睡人的眼。那聲音有些飄忽,仿佛孩子的魂兒就在眼前飄蕩,然后被兜進衣服里,托回家了。
一年冬天,我和小伙伴在河面上玩耍,不小心掉進了冰窟窿,拉上來時,已經感覺不到疼痛。身子內外被凍透了,手不是自己的,腳不是自己的,連呼吸也不是自己的,岸冷,樹冷,天冷,地冷,房上的瓦都冷得哆嗦。晚上,我持續高燒。祖母拿著我的衣服去村外喚魂。雪地里,深一腳淺一腳,淺一腳深一腳,祖母來來回回地走,來來回回地喊,把天走個蒙蒙亮,把天喊個蒙蒙亮。
后來,常聽祖母給母親嘮叨,喚魂時,心要誠,心不誠,魂兒是找不著路的。母親在一旁連連點頭。她們的樣子,仿佛把人帶向生命的另一個維度。祖母健在時,常掛在嘴邊的是,人死了,都在天上點個星星。這是祖母的善念和祈愿。她去世后,我開始情不自主地遙望星空。我盼著看見祖母在夜空里閃光,那樣我就不會再那么想她,不會總在背人的時候哭。
敘昭穆,明人倫。
供奉祖先是一種銘記的方式,修訂家譜則是另外一種方式。
村子頗有些年頭,以至于第一戶來此落腳的人也無從考究,有可能是挖掘運河的人,有可能是皇家南巡時的纖夫,也有可能是從洪洞大槐樹下遷移的人,他們病了、殘了、累了,無力再遠行,就在此開枝散葉,繁衍成一戶又一戶人家,最后聚居成村、成莊。一縷香火,一聲鄉音,傳承慎終追遠。
家譜的修訂是一件大事,字字都要求其來處,唯恐疏漏了祖先的功德,有的家譜、族譜需前前后后經歷數年方成。家譜是維系家族血緣關系的重要紐帶,通過一份家譜,可感受到先人流傳下來的血脈親情。幼時,村子里孩子的名字,尤其是男孩子的名字一定要按族譜上的輩分來,走在村子里,只要知其名字,即可知如何稱謂。
新生的孩子入譜也是一件隆重的事情。人到齊了,族中的最長者拿出家譜、黃燒紙和幾掛鞭炮,放完炮,燒完紙,再將孩子的名字寫入家譜或族譜。哪怕你以后遠渡重洋,跨過海峽,都可循著族譜,找到回家的路。祖先遠去,留下了一個個名字在紙上泛著幽光,不禁想象起那些從未謀面的老人家的模樣。于是,一種感懷先人的情緒瞬間涌來,一時竟有些語塞。
在祖先的庇護下,我像一只飛鳥,翱翔在運河之上,或逆流而上,或順流而下,有風從遠方吹來,掠過,云自由自在地衍生、飄逸,是不是亙古就是這個樣子,只有風,只有云,只有陽光。然而,風不會忘記,云不會忘記,過往早已深刻進村莊的年輪,成為它生命中的一組細胞、一縷追思。
4
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尋常百姓怕它,達官貴人更避諱它。然而,村里人卻不在意,從從容容地迎接它,用他們的話說,有死才有生。那些上了年紀的老人,在生前就開始張羅自己的后事,親眼看到后人為自己準備好壽衣和壽材,才能安心,好像完成了此生最后一件大事。從此,后顧無憂,可以靜候死神的到來。
家境貧寒的人家,就算生前穿得再破再爛,壽衣也要準備得鮮亮,如此死后才能衣著光鮮地走,如此靈魂才能得以超度。在村里人看來,預先給老人準備壽衣是不用忌諱的,也不是什么不吉利的事情,能沖一沖霉氣,反而給老人添壽,甚至有著“年年曬壽衣,越曬越長壽”的說法。
依照習俗,兒孫輩會提前給上了年紀的老人縫制壽衣。到了伏天,老人將及早準備好的壽衣拿出來晾曬。左鄰右舍的老人以一種外人的角度對那些壽衣評說一番,比如誰的壽衣顏色好看、做工考究,誰家的小輩孝順等等。平日里熟視無睹,一年也難得碰上幾回的樟木箱,只有在此時才獲得少有的禮遇,被抬出來,放在長條凳上置實了,“啪”地一下,像陽光下成熟的豆莢,歡欣鼓舞地打開了。
這一天,日頭下、門里門外進進出出的主婦,早早就在院子里、院墻外、曬谷場拴好了曬衣繩,然后像約好似的,彎腰曲背,從屋里搬出盛放衣物的箱子,不約而同地將雨季里吸足了潮氣的被褥、棉襖、棉褲、夾衣單衫等,放到火辣辣的太陽底下暴曬。平淡的村莊,像舞臺似的布置了起來,空氣中彌漫著樟腦丸澀澀的清香。所有的箱子都趕在太陽落山前撤出生活的場景,重新回到大櫥頂上,閣樓上,開始它們沉寂的漫長時光。
曬伏時,母親要去幫五叔婆曬壽衣。五叔婆是村子里的神婆,對于她,我有一種天然的依戀。五叔婆無兒無女,祖父常念叨,你五叔公這一支人算是沒了。可是他從不在五叔婆面前提及,生怕觸碰了她痛失五叔公的神經。五叔婆是鎮上的大家閨秀,與五叔公門不當,戶不對,但這并不影響他們的結合。
五叔婆出嫁時,給五叔公提了一個要求,娶親時,不用大花轎,要五叔公背著她回去。五叔公二話沒說,當即應下了。娶親那天,五叔公帶著迎親的隊伍,敲敲打打,浩浩蕩蕩來到五叔婆家,唯獨沒有轎子。鎮上的人見了,很是不理解,娶親竟然沒有花轎。當嬌小的五叔婆戴著紅蓋頭、趴在五叔公的后背上時,圍觀的人才恍然大悟,發出了一遍又一遍的喝彩聲。
五叔婆家離村子有十幾里路,這是何等的氣力啊!五叔公硬是背著他的新娘,一口氣回了家。從此,五叔婆將她的心交給了五叔公,與他榮辱與共,不離不棄。當五叔公過早地離世,五叔婆也沒有改嫁,守著五叔公的照片過活。讓人遺憾的是,五叔公沒有留下一兒半女。
可能是因為那份虔誠,神靈選擇了五叔婆作為他在人間的代言人。我出生時,五叔婆看了我一眼說,這孩子不好養,得認門口的石碓為干娘。因為五叔婆的話,我多了一位干娘,也多了一份護佑,如門口的樹苗,噌噌往上長,無病也無災。每年除夕,我都要給干娘燒香、磕頭。哪怕是遠離老家,也要打開門,對著老家的方向,“砰砰砰”磕下三個響頭。
因為這份機緣,我和五叔婆尤為親近,人們送給她的點心大多吃到了我的肚子里。曬伏時,看著那光彩奪目的被面,繡了花的枕套,緞子棉襖、紫花床單,一件件掛起來、晾起來,讓我浮想聯翩,似乎在親手抖落五叔婆平時藏著掖著的美麗,低頭抬頭間全是由內而外的柔情。在撲面而來的樟腦氣息背后,充滿著閨閣的心事,像滿箱子綾羅綢緞閃閃爍爍,讓人走神,讓人回味,讓人在東山墻的陰涼里余音裊裊地說起往昔來。
此時,五叔婆回想最多的是新婚時的情景:鋪天蓋地炸響的爆竹,身前身后艷羨的目光,滿眼的花團錦簇。對她來說,這箱子有點像生活的根,頂峰一樣的日子就是在這個根上開出罌粟一樣美麗的花,掀開根上的浮塵,那些花便傾盡所有,平淡的生活紛至沓來。五叔婆的手中始終握著一根黑得發亮的煙袋,那是五叔公健在時用的,五十年后還恒常地握在五叔婆縮皺的手中,讓人不得不驚嘆時光的神奇,這才是真正的生死不渝,才是萬劫不滅的情重!
五叔婆喜歡荷花,去河邊,我必涉水折上一兩枝。五叔婆用一個花瓶供養在條幾上,前方是諸神菩薩,以及五叔公的遺照,一雙劍眉,一雙虎目,張揚得桀驁不馴,目光亮得耀眼。五叔婆常說,你五叔公生前最愛荷花,他說哪怕是身處濁世,也要如荷花一樣,出淤泥而不染。五叔婆的聲音無悲也無喜,荷花的香與點燃的松香,融在了一起,有著盛世的安寧和沉靜。
五叔婆的家里供奉著無數的神靈,有的是畫像,有的是塑像,觀音菩薩、玉皇大帝、三太子、華佗老爺、黎山老母、財神爺、龍王爺、雷公電母、黃大仙,官方的神,民間的神,土生土長的神,在五叔婆的神案上歡聚一堂。有一尊觀音像,臉面飽滿,眉目清楚,螺髻盤旋,結印的手指逼真生動,讓我在心里佩服那些工匠,將古老的泥土賦予了生命和靈魂。
那些神像凝聚著五叔婆對神、對人、對萬物的理解和尊敬。五叔婆把手疊在一起,擱在膝上,空靜地坐在昏暗的燈光下,那姿態儼然一尊菩薩。五叔婆常說:燒香時,心要誠,否則那些神靈聽不到你的訴求,即使聽到了,也會置之不理。遭遇霉運時,也要把不好的心情放在供桌上,燒完香,整個人就平靜了。
五叔婆在村子里頗有地位,孩子嚇著了,大人被“鬼纏身”了,都要請她去瞧瞧。五叔婆善于誦經,誰家老人去世了,都要請她。有些老人生前就給她說,“老姊妹,等我去了,你一定要送我最后一場哈。”五叔婆的誦經聲,像運河流淌發出的聲音,寧靜,安詳,或者說,像是一種符咒,一種語言的符咒,一種意念的符咒,真能驅鬼辟邪。哪怕是多年后,我依然不明白它擁有何種力量。
我從來不刻意去找一座廟宇朝拜,但若是經過一座廟,哪怕是簡陋的只有一個香臺,我都會進去燒炷香。這是幼年養成的習慣。我幻想著寺廟不在于大,而在于是否有一個得道的高人,可能是一位僧者,可能是一位道人,也可能是一位掃地燒火的老人。等他們空閑了,和他們對坐,聽他們訴說平靜中得來的智慧。你坐著,聽著,微風吹拂過大地,心就在那大地里晃晃悠悠地醒來。
或許有人說,世界上哪有什么鬼神。其實,每個人的內心都有一個神靈,他是希望,他是信仰,讓人明悟,教人行善、積德、納福,要與人為善,要與自然為善,要與萬物為善。一生為善的五叔婆,讓我知道了,我們敬畏神明,不如說是一種來自心靈的聲音,提醒我們敬畏自然,敬畏天地萬物。人只有懂得了敬畏,才會懂得取舍,才懂得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