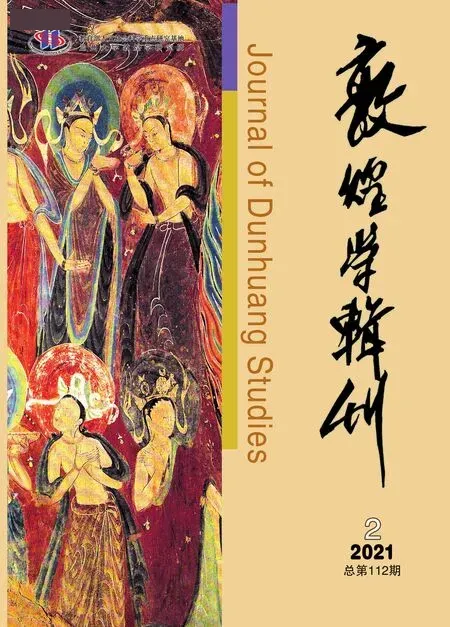涅槃圣地:二十世紀初印度伽西亞佛寺的發掘歷程
鄒 飛 高晶晶
(1.海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海南 海口 571158;2.中南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伽西亞 (Kasiā)遺址,最早于1875年開始發掘。1902年印度考古局重組后,對該遺址進行了多次發掘工作,尤其以1904年、1906年和1910年的發掘最為重要。縱覽這幾次發掘歷程,共計揭露多座佛教寺院和其他佛教建筑物,出土了大量的佛教遺物和各種材質的印章。同時,該遺址早在19世紀時被亞歷山大·坎寧漢爵士 (Alexander Cunningham,1814-1893年)比定為佛陀涅槃圣地——拘尸那迦,阿爾齊巴爾德·坎貝爾·卡萊爾 (Archibald Campbell Carlleyle,1831-1897年)、簡·菲利佩·沃格爾 (Jean Philippe Vogel,1871-1958年)、潘迪特·希蘭南達·薩斯特里 (Pandit Hirananda Shastri)等人的發掘也證實坎寧漢觀點的正確性。
一、伽西亞遺址的發掘歷程
自19世紀以來,歐洲學者、探險家以中國古代朝圣僧人法顯、玄奘等游記為藍本,按圖索驥,對伽西亞遺址進行了多次的調查和發掘工作。1810年左右,布坎南·漢密爾頓 (Buchanan Hamilton)第一次造訪伽西亞并作出簡短記錄,這是歐洲人最早抵達該遺址的記錄。然而,這一條記錄直到1838年才由蒙哥馬利·馬丁 (Montgomery Martin)在《東印度》(Eastern India)期刊上披露①Vincent Smith,The Remains near Kasia,Allahabad,Printed at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and Oudh Government Press,1896,p.3.。
1861年,時任北印度考古總監的坎寧漢爵士,根據玄奘《大唐西域記》的記錄,對北印度大量的佛教遺址進行調查、比定和簡易的發掘工作,伽西亞是其中一處。坎寧漢在伽西亞的主要工作是對其中一處名叫拉瑪巴佛塔 (Ramabhar Stupa)的試掘,該佛塔坐落在拉瑪巴河谷 (Rāmabhar Tāl),距伽西亞遺址西南一英里。拉瑪巴是當地人后來的稱呼,該佛塔應被稱為安格拉佛塔 (Angara Chaitya)②日月洲《佛國行——從尼泊爾到印度》,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7年,第61頁。。佛塔整體用孔雀王朝時期的方形磚塊修砌,呈圓鼓形,坎寧漢在這里標記了佛塔所在封土堆的位置,測量出該塔南北長約600英尺,寬約200到300英尺,揭露了一尊巨大的坐佛雕塑、一口水井。關于巨型坐佛雕塑有這樣的描述:
雕塑用來自迦耶 (Gaya)的深藍色石塊制造,從頭到腳分為兩部分,其中一部分損毀嚴重。在基座上有簡短的銘文……圖像表現的是坐在菩提迦耶菩提樹之下的佛,苦行者。整個雕塑高10.5英尺。③Vincent Smith,The Remains near Kasia,Allahabad,Printed at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and Oudh Government Press,1896,p.4.
坎寧漢根據這些調查,比對《大唐西域記》中關于 “拘尸那揭羅國”的記載,第一次提出伽西亞遺址是古代佛陀涅槃的圣地——拘尸那迦 (Kushinagara)的說法。
1875年,卡萊爾在伽西亞遺址揭露了大量的地面遺存。第一次厘清了各遺存之間的相互位置和分布,揭露了阿育王時期修建的佛塔,鄰近涅槃寺的石柱,蘇跋陀羅(Subhadrs)佛塔,金剛力士 (Vajarapani)佛塔等大量的遺存,其中拉瑪巴佛塔在圣殿塔的西北處,并在涅槃寺中出土了一尊巨大的臥佛雕塑,這是北印度第一次出現這樣的圖像。無疑,卡萊爾的發掘進一步的支持了坎寧漢爵士關于伽西亞遺址即古代拘尸那迦觀點的正確性。
1896年1月底,文森特·史密斯 (Vincent Arthur Smith,1848-1920年)造訪伽西亞,首次提出坎寧漢、卡萊爾所發掘的伽西亞遺址并不是古代拘尸那迦的觀點,認為佛陀涅槃的地點拘尸那迦位于今尼泊爾境內小拉普特河 (Little Rapti)與甘達克河 (Gan-dak)交匯處①Vincent Smith,The Remains near Kasia,Allahabad,Printed at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and Oudh Government Press,1896,p.23.。然而,這種觀點并沒有得到有力的證據支持。
1904年11月28日,英屬印度的聯合省份 (Unite Province)出資1000盧比,印度考古局委任北方區主管沃格爾為發掘主管,薩斯特里、達雅·薩尼 (Dhaya Shani)為發掘助理,工頭巴布·拉恩 (Babu Kashi Ran)負責勞務和其他事宜,對該遺址進行了進一步的發掘②ASI,Annual Report1904-05,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Calcutta,India,1908,p.43.,此次發掘一直延續至1905年2月28日,總計花費998盧比。
1905年冬季,沃格爾在聯合省份資助3700盧比的支持下開啟發掘工作,其中500盧比用于9英畝土地的購買③ASI,Annual Report1906-07,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07,p.44.,800盧比用于碎片的清理。1906年12月3日至1907年2月,沃格爾博士、巴布·古爾薩蘭·達斯 (Babu Gursaran Das Mehta)、照相員古拉姆·納比 (Ghulam Nabi)、第二繪圖員布拉·瑪爾 (Bhura Mall)一道對伽西亞遺址中的寺院D、寺院E、寺院N、佛塔A、建筑物J等遺址展開發掘。同時,1906年的發掘共出土粘土印章895枚,其中856枚有雕刻銘文 (521枚屬于佛教寺院、335枚屬于個人)④ASI,Annual Report1906-07,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07,p.58.。1911年1月至4月,印度考古局再次提供3000盧比用于該遺址的發掘工作⑤ASI,Annual Report1910-11,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14,p.63.。在大約三個月的發掘時間里,希蘭南達·薩斯特里對該遺址的許多點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揭露了兩座較大的佛塔,出土了大量的佛教遺物。
根據上述20世紀初期開展的幾次重要地發掘,可以基本厘清伽西亞遺址的形制布局,也可以證實坎寧漢、卡萊爾、沃格爾、希蘭南達·薩斯特里等人觀點的正確性,即該遺址即著名的佛陀涅槃圣地——拘尸那迦。
二、佛寺形制布局
伽西亞遺址的形制布局是一種北印度較為常見的塔院、僧院組合模式,即塔院在前,僧院在后,且主要的禮拜中心在塔院,僧院多用于僧人居住,或寺院的附屬建筑(如倉庫、廚房等)。根據1911年沃格爾的發掘記錄 (圖1),伽西亞遺址的形制布局為:以涅槃寺A (Nirvāna Stupa A)和涅槃寺B (Nirvāna Stupa B)為中心,其南端是建筑物F,最北端是建筑物I,J和寺院P,其東側是佛塔C;涅槃寺A的東北是被古代城墻圍繞的建筑物H,其東北是佛塔E;涅槃寺B的西北是建筑物Q,其西側是建筑物D,南端依次是寺廟M,N和建筑物L,再往南則是寺廟O;整個遺址的東南角是卡拉丘里寺廟 (Kalachuri Monastery),西南角是拉瑪巴佛塔。在涅槃寺A和B的南邊有一條寬20碼呈排狀的小佛塔 (4,6,11,17等),其形制和尺寸不盡相同;寺院D,M,N,O,E,P周圍都簇擁著成排的僧房,其他建筑物L,I,J,Q周圍同樣簇擁成排的像堂。

圖1 伽西亞遺址全圖(采自ASI,Annual Report1910-11,Plate XXXI.略有修改)
1.涅槃寺A,B
涅槃寺A早在1876年就由卡萊爾進行了一些簡易地發掘工作,1911年的發掘對其進行了徹底地清理。主佛塔外表呈圓形,高25英尺,周長56英尺,佛塔頂端毀壞的部分出土許多雕刻的磚塊和賈亞·笈多 (Jayagupta)時期的錢幣,通過這些磚塊證實該佛塔的材料是二次使用。
在高14英尺處發現一座圓形遺物室,直徑2英尺1英尺,高度2英尺1英寸。在遺物室中出土一些球形外形的黃銅瓶子,口沿處被銅板遮擋。在銅瓶中發現一些砂子、燒灼過的木炭、石頭、珍珠、一條小的銀質管子和一枚鳩摩羅·笈多 (Kumaragupta)時期的銀幣。
銅板在出土之后被送至英籍德國裔東方學家奧古斯塔斯·霍恩勒 (Augustus Frederic Rudolf Hoernle,1841-1918年)處進行檢測①霍恩勒,又譯 “霍爾寧” “霍恩雷”等。關于霍恩勒的詳細信息,參見王冀青《霍恩勒與中亞考古學》,《敦煌學輯刊》2011年第3期,第134-157頁。,銅板長46厘米、寬15.8厘米,厚3毫米,背面銅銹侵蝕較正面少,銘文用一種包含油脂的墨水書寫,變干后在銅板上進行雕刻②ASI,Annual Report1910-11,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14,p.73.。然而,銅板正面漫漶嚴重,只有部分銘文可見,即第一行大部分、第二、三、四行開頭的幾個字母。因此,第一步由霍恩勒拍照、弗雷德里克·艾登·帕吉特爾(Frederick Eden Pargiter,1852-1927 年)開始清理沒有被侵蝕的部分 (圖2),第二步則是對銅銹開始清理①ASI,Annual Report1910-11,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14,p.73.。

圖2 涅槃寺A出土銅板部分(采自 ASI,Annual Report1910-11,Plate XXXIX A,B.)
經清理可見雕刻在銅板上的梵語字母,Nidāna-sūtra,Palichcha-samuppāda②ASI,Annual Report1910-11,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14,p.75.,帕吉特爾通過獻辭和鄰近的字母斷定該銅板被安置在涅槃寺( [pari] nirvānachaitya)前面,譯作:
這是哈利巴拉 (Haribala)虔誠的禮物,許多毗訶羅的供養人。③“This is the pioius gift of Harabala,the superintendent of many viharas.Whatever religious merit there is herein,let it to the acquisiton of the subline knowledge of all creatures.” ASI,Annual Report1910-11,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14,p.77.
通過銅板上的銘文可知獻祭者是哈利巴拉的兒子達爾曼納達 (Dharmananda)。
此外,卡萊爾于1875-1877年在伽西亞遺址發掘了一尊巨石佛像,其供養人同樣是哈利巴拉,雕刻銘文…rvāna-caitye tāmre-patta iti,弗雷特博士將其認定為公元5世紀④F.E.Pargiter,‘ A Copperplate Discoverd at Kasia,and Buddha’ s Death-Place’,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uran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Jan.,1913),p.151.。兩塊碑文的獻祭者同名,說明它們應屬于同一時期。此外,在銅板周圍發現鳩摩羅·笈多時期的銀幣,鳩摩羅·笈多死于公元455年,這也可以證明這塊銅板的時間不晚于鳩摩羅·笈多死亡的時間⑤ASI,Annual Report1910-11,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14,p.75.。因此,弗雷特、帕吉特爾斷定該銅板的時間為公元5世紀末是合理的。
在佛塔A和涅槃寺的南邊,有26座小型遺跡,沃格爾發掘之時只有部分基座遺存。其中編號為14和19的建筑圍繞在厚1英尺8英寸的磚墻內,每邊都有一塊混凝土地板,在最底部雕刻佛教教義。經發掘確認,編號14是一處佛塔基座,編號19則有許多雕刻磚塊的裝飾,卡萊爾認為其是一種早期佛塔的形式。
涅槃寺B在卡萊爾發掘之際保留有三處遺跡,建筑面積較大,但結構比較粗糙,至沃格爾發掘之際,寺廟僅殘余一鑲嵌式角落的兩邊。在寺廟主佛圓寂的臥榻前面,發現三幅表現哀悼場景的圖案,在其中一幅圖案之下發現銘文。由弗雷特復制并認為時間為公元5世紀末期,是比較常見的象征佛陀圓寂的圖案。阿爾弗雷德·富歇 (Alfred Foucher,1865-1952年)則認為該圖案與佛陀最后一位弟子須跋陀羅有關⑥ASI,Annual Report1904-05,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04,p.45.。
其中,在寺廟前廳西北角落處發現一尊坐佛像 (圖3)。佛結跏趺坐于圓形底座上,頭部有輕微破損,圓髻,無白毫相,有背光,著通肩袈裟,胳膊已毀壞,但仍見胸前的雙手施轉法輪印,圓形底座底部雕刻一排小象,花朵的圖案,并刻有公元5世紀笈多時期的銘文。

圖3 坐佛像(采自 ASI,Annual Report 1904-05,fig.2.)
2.寺院D,N,O,E,P
寺院D位于遺址中心區域的西側,卡萊爾稱其為“封土堆中間最高的部分”,但由于農業用地的侵占導致封土堆外形已發生變化,發掘揭露了一座寺院、一條石鋪路和一排水渠。沃格爾博士的發掘證實該遺址是一座常見的佛教寺院,建筑平面接近150平方英尺,包括一個87平方英尺的中心院子,其南邊和東邊均有走廊,外墻處有一排房屋,每7間房屋分4排排列,在南邊和北邊墻體有2個壁龕,其頂部是重疊磚的構造。在寺廟D像堂處發現一枚橢圓形的粘土印章,裂成21塊,雕刻法輪和鹿的形象,上面雕刻銘文(1)ri-Mahāparinirvvāna- (2)mahāvihāriyārya- (3)bhikshu-sanghasya①ASI,Annual Report1910-11,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14,p.71.。
寺院N位于寺院D的南邊,包括一處塔院,其西側有三座像堂、東側有兩座像堂,在西側外墻角落處發現一些破損的大件陶器和一根鐵的匙狀物,應該是廚房所用;東側小室發現一些陶質瓶子和一個粘土印章②ASI,Annual Report1906-07,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07,p.46.,從這個發現可以推斷該建筑物毀壞的年代。在像堂地板之下發現墻體遺存,證實寺院N被毀之后在其遺存之上興建了新的建筑。此外,在該建筑物最大的一座像堂發現兩塊燒制的粘土印章,銘文作Aryāshtavriddhai.③ASI,Annual Report1906-07,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07,p.60.
寺廟O包括一處院子和4排環繞周圍的像堂,平面近方形,每邊長110英尺,有一個平整的赤陶屋頂,修筑所用磚塊同之前發現的早期佛塔柱基的磚塊相同。該寺廟的四面均有五座像堂,像堂之間用壁龕隔開,像堂平面同樣近方形,角落處的像堂則呈橢圓形。其中,像堂13(No.13)是寺廟O的入口,在該像堂發現一尊較大的赤陶佛像、一塊雕刻的石板以及12枚雕刻的粘土印章,用從公元700年至1000年的字母雕刻④ASI,Annual Report1906-07,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07,p.48.。像堂O3保存4幅飛天 (aksharas)圖像,但其中3幅毀壞嚴重,其上銘文漫漶嚴重,沃格爾博士將銘文釋作ya ku a na,最后三個音節應該是Kusana[gara]的原型,因此斷定這座寺廟毀壞的時間應該是迦膩色伽時期⑤ASI,Annual Report1906-07,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07,p.49.。
此外,在像堂的院子外發現許多一尊紅砂巖的立佛雕塑,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抓住長袍,基座上包括兩段獻祭銘文 “Dēyaharmōya[m a]kyabhikshōh(r)Bhadanta-Suvirasya kriti[r](2)Dinnasya”,譯作:
這是佛教徒虔誠的禮物,莊嚴的蘇韋若 (Suvira),來自蒂娜 (Dinna)的作坊。①ASI,Annual Report1906-07,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07,p.49.
這段銘文同弗雷特博士后期發現的巨型臥佛像 (佛涅槃像)基座上的銘文較為相似,Dēyadharmō yam mahāvihārasbaminō Haribalasya( 2 )pratimāchēyam ghalita Dine…māsvarēna。同時,兩尊雕塑基座部分的銘文均包括供養人的名字和制作者的名字,且其中的許多音節也極為相似。沃格爾博士將在飛天圖像上發現的字母na填充在上端,銘文缺失的音節處,作Pratimā chēyam ghalitā Dinnina Māthurēna,譯作 “馬圖拉的蒂娜制造了這尊圖像”②ASI,Annual Report1906-07,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07,p.50.。據此可以判斷這兩尊雕塑其時代和風格相同,是介于貴霜和笈多時期的秣菟羅佛教藝術。
寺院E位于伽西亞遺址中心建筑涅槃寺A和B外圍東北處,該寺院外形呈正方形,四周包括整排的像堂。同時,作為入口的像堂比其他像堂的尺寸較大,且最初是一處木質結構。寺廟E最南端走廊的盡頭是第二處門道,指向涅槃寺A的位置。該遺址發現的遺物數量較少,唯一可以證明年代的遺物是一串光玉髓的珠子和一枚粘土碑,其上雕刻佛教教義。
寺院P位于寺院D西北處,鄰近建筑物I,J,是一座矩形建筑,整體用磚塊修砌,在北邊和南邊均有4座像堂,西邊有3座像堂。其中,房間b發現許多灶臺,可能是一處廚房遺址;房間c北邊是一座祠堂,在基座處發現雕塑。與房間b相對的是一處浴池,發現一條大的石質管道。據此判斷,寺院P在古代被用作一處食堂 (bhōjana ālā)。
3.建筑物I,J,C,H
建筑物I,J位于整個遺存的北邊,其西側是建筑物I,其平面呈方形,四邊有成排的僧房,僧房之間被間隔且有一處深達2英尺的水池,水池用瓷磚鋪砌,在發掘之際破損嚴重。進入建筑物I的主要入口是兩處僧房,該僧房包括一處磚砌平臺,在該遺址發現一尊面朝東的佛像,象征佛陀冥想的時刻。在院子東墻附近出土一些雕刻印章,其時間可以追溯至公元900年。
建筑物J,位于建筑物I的東邊,其年代同建筑物I相同③ASI,Annual Report1906-07,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07,p.53.,是一座寺廟的遺存,包括一處近30平方英尺的院子和周圍簇擁的僧房。兩座建筑物之間通過一條走廊隔斷,走廊處發現大量的陶器碎片。兩座建筑物的用途相似,均是作為僧人居住。
建筑物C,位于涅槃寺A的東邊,坐落于一個較高的封土堆之上。最早由坎寧漢爵士進行發掘,總高16英尺3英寸,然而坎寧漢發掘至4英尺3英寸之時隨即停止,因此僅發現一些破損的磚塊。1875年,卡萊爾的發掘更像是 “一種表面的發掘”,主要對封土堆的西、北和南邊進行發掘,在北邊盡頭處揭露了一個階梯建筑的遺存和一尊象頭神雕塑。
建筑物H,介于建筑物C和涅槃寺A之間,四周被墻體圍繞,其中沿著建筑C西墻的中間部分有一段墻體長約40英尺。建筑物H的北邊是佛塔E,發現12枚黃銅錢幣,4枚屬于卡德菲西斯二世,8枚屬于迦膩色伽時期。此外,在西邊發現的五座小佛塔 (1,2,5,3,4),其中前三座由卡萊爾發掘,均建造在一正方形基座上,佛塔2和5坐落在一長方形的基座上,且每座佛塔都包含一個單獨的鼓形結構和一個圓頂,其形制屬于早期佛塔的典型代表,時間應屬于孔雀王朝時期。
建筑物Q位于涅槃寺B的西北。早年間卡萊爾曾在該建筑西邊發現一處水井。沃格爾、薩斯特里的發掘則是通過探溝的形式,且在深達9英尺的地方發現一座建筑物的遺存,在入口處發現大量的木炭,證實該建筑在很久之前被火毀滅。在建筑物Q北邊的第2座像堂發現一些尺寸較大的經過灼燒的磚塊,可能是用于地面裝飾。在水井的北側和西側發現一條矩形的磚鋪路,發現一枚笈多時期的印章,銘文kēsari.同時,在建筑物的西北角發現一枚笈多時期的粘土印章,銘文kumāramāyasya①ASI,Annual Report1910-11,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11,p.67..在西北角的第3座像堂發現一枚橢圓形的粘土印章和一塊粘土獻祭碑 (圖4),其中印章之上雕刻在兩棵婆羅樹之間的佛陀金棺下雕刻銘文Mahāparinirvāna bhikshu-sangha”②譯文作 “of the commnity of friars at the Great Deccase” .ASI,Annual Report1910-11,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11,p.71.。根據這些出土遺物,建筑物Q的年代不晚于公元10世紀。③ASI,Annual Report1910-11,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11,p.67.

圖4 粘土印章(采自 ASI,Annual Report1910-11,Plate XXXIV,e.)
4.卡拉丘里寺廟
卡拉丘里寺廟,早年間由卡萊爾發掘并認為是一座古代的寺廟,平面呈方形,包括一處塔院,曾發現供奉一尊巨型石質佛像,站立在一棵菩提樹之下。1910年,薩斯特里對該寺廟的內殿再次清理,揭露了一塊獅子基座,證實其上曾有站立的佛像。同時,在寺廟周圍揭露了一座禮拜室,朝向東,在禮拜室北邊發現兩座同樣朝向東的像堂,南邊像堂發現一些雕刻佛教教義的粘土印章和一枚銀幣,且在小室之前有一條寬8英尺6英寸的走廊。
三、伽西亞的歷史沿革
關于伽西亞遺址的歷史,最早出自中國古代朝圣僧人的記載。坎寧漢、沃格爾、希蘭南達·薩斯特里等人則根據這些記載,通過一系列的調查、發掘工作,最終確定了該遺址則是著名的佛陀涅槃圣地——拘尸那迦。
早在公元4世紀,中國東晉高僧法顯途經此地,記錄其為 “拘夷那竭城”:
從東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城北雙樹間希連河邊,世尊于此北首而般泥洹。及須跋最后得道處,以金棺供養世尊七日處,金剛力士放金杵處,八王分舍利處。諸處皆起塔,有僧伽藍,今悉現在。其城中人民亦稀曠,止有眾僧民戶。①[東晉]法顯撰,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76頁。
法顯所載該城為佛陀涅槃處、八王分舍利處,在他到訪之時仍有許多佛教寺院存在,“皆起塔”則是最好的證明,可見伽西亞的佛教圣地地位。
公元7世紀,中國唐朝僧人玄奘造訪該地,記錄此處為 “拘尸那揭羅國”: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頹毀,邑里蕭條,故城磚基,周十余里。居人稀曠,閭巷荒蕪。②[唐]玄奘、辯機著,季羨林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36頁。
玄奘記載該城用磚塊修筑,然而該城城郭荒廢,經濟蕭條。其中,殘存的磚塊在之后印度考古局主持的考古發掘中已經得到證實。
《大唐西域記》載:
城西北三四里,波阿特多伐底河……其大磚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臥……傍有佛塔,無憂王所建,基雖傾陷,尚高二百余尺。前建石柱,以記如來寂滅之事。雖有文記,不書日月……③[唐]玄奘、辯機著,季羨林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第538-539頁。
玄奘所載石柱由無憂王 (即阿育王)敕建,石柱上記載如來涅槃的事件。根據這條記錄,早在19世紀坎寧漢爵士就將伽西亞遺址比定為佛陀涅槃的圣地——拘尸那迦。在20世紀初期的考古發掘中,如前文所述發掘揭露的建筑物C中發現十根殘缺的石柱。
又《大唐西域記》載:
城北渡河三百余步,有佛塔,是如來焚身之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誠求請,或得設立。④[唐]玄奘、辯機著,季羨林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第550頁。這條記載同樣在19世紀初坎寧漢爵士開展地發掘中得到證實,且將其比定為天冠塔(Makutābandhana)①ASI,Annual Report1910-11,Calcutt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India,1911,p.69.,是佛陀荼毗之地。
然而,根據法顯、玄奘的記載可知,該地雖為佛陀涅槃圣地,但在他們抵達時已經人口稀少,可見該城的沒落應早于公元4世紀。
公元8世紀,僧人慧超前往,對佛陀涅槃圣地有這樣的記載:
一月至拘尸那國。佛入涅槃處。其城荒廢。無人住也。佛入涅槃處置塔……此塔西有一河。伊羅缽底水。南流二千里外。方入恒河……此塔東南卅里。有一寺。名娑般檀寺。有卅余之村莊三五所,常供養彼禪師衣食。②[唐]慧超著,張毅箋釋,[唐]杜環著,張一純箋注《往五天竺國傳箋釋·經行記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5-8頁。
根據慧超的記載,在其造訪之際伽西亞城址已然荒蕪廢棄,這比法顯、玄奘記載的人煙稀少更加荒涼。慧超記載佛涅槃處的伊羅缽底水,與法顯記載的希連河,玄奘記載的波阿特多伐底河都指向同一條河流,即今天流經尼泊爾與印度北方邦的甘達克河 (Gandak),也稱納拉亞尼河 (Narayani River)。此外,慧超記載的位于東南的娑般檀寺,即玄奘記載的天冠塔,這一點也得到了證實。
綜上所述,結合前文對各主要遺址發掘過程的考述可知,伽西亞遺址無疑是佛陀涅槃圣地——拘尸那迦。究其形制布局而言,伽西亞佛寺是一種常見的塔院、僧院相組合的模式,且主要的禮拜中心在塔院,這與塔克西拉諸多遺址中的寺院形制布局相似③關于塔克西拉遺址中的佛寺布局,可參見鄒飛《塔克西拉佛教遺址發掘歷程述論》,《敦煌學輯刊》2017年第3期。。其中,塔院建筑為涅槃寺A,B,以及簇擁在涅槃寺周圍的寺院D,M,N,O,E,P等,在這些寺廟的四周均建造像堂;建筑物I,J,C,H則是僧院,其四周同樣建造僧房。另外,在涅槃寺A出土的雕刻銘文的銅板和鳩摩羅·笈多時期的銀幣,涅槃寺B出土的銘文,可證明涅槃寺A,B修建的時間應該在公元4-5世紀。④J.PH.Vogel,‘ Some Seals from Kasia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uran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Apr.,1907),p.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