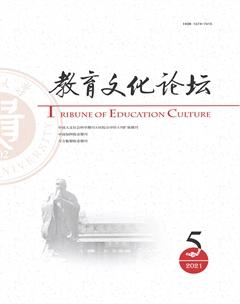清末留日學生與日語教科書的編刊及影響
摘 要:《東語正規》是清末首批留日學生唐寶鍔、戢翼翚在日留學期間,翻譯其所使用的日語教材整理編撰而成。該書最初是自費出版,1901年由譯書匯編社增補再版,后又分別由戢翼翚在上海創辦的出洋學生編輯所和作新社發行。針對當時風行一時的《和文漢讀法》,《東語正規》另辟蹊徑,強調日語口語的學習,對清末日語教科書的編撰以及國人的日語學習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留日學生;日語教科書;《東語正規》;戢翼翚;作新社
中圖分類號:G23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7615(2021)05-0104-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5.015
1896年,甲午戰爭中清政府戰敗,在“以日為師”的口號下,清政府首次派遣13名學生赴日留學。1897年,京師同文館增設東文館,官辦的日語教育正式開始。隨后,廣東同文館、湖北自強學堂等洋務學堂也相繼仿設東文館。自此,東文學堂(即日語學校——筆者注)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日語教育開始在中華大地上生根發芽。起初,由于沒有合適的日語教科書,這些東文學堂大多采用“和文漢讀法”和“漢文和譯法”,或使用中國古代已經被日本人翻譯過的經典著作或使用日本的政治、經濟、歷史等專業書,進行“漢譯日”與“日譯漢”的訓練;或使用日本國內為小學生編的國語讀本進行日語教學。1900年,由首批留日學生編撰的《東語正規》的出版打破了這一局面。正如日本學者實藤惠秀所言,《東語正規》“從日語語法正宗出發,講語法、教會話,研究日語變體假名和助詞,并標明重音,寫得很全面。中國人對日語的研究可以說從這時才走上正軌,是一本供中國人學習日語的劃時代的教科書” [1]。
可以說,《東語正規》不僅是中國人第一部科學地研究日語的書[2]298,而且是中國人學習日語的教材中“打破記錄的名著”[3]16,對后來的留學生有很大的幫助[2]40。遺憾的是,關于《東語正規》的相關研究并不多,既有的研究大都基于語言學史的視角,重點關注《東語正規》的文本內容,對該書的刊行過程及其在清末的影響語焉不詳①。本文擬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通過考察清末留日學校“亦樂書院”學生編撰、刊行《東語正規》的過程,揭示《東語正規》對清末出版機構的創辦、清末國人自編日語教科書及清末國人的日語學習所產生的重要影響。
一、留日學生與《東語正規》的編撰
甲午戰爭后,總理衙門為培養日語人才,曾致函日本文部省稱:“清國學生希望到帝國學校學習日本文及日本語學,請求協助。”[4]經日方同意后,總理衙門便在國內挑選13名學生赴日留學,唐寶鍔與戢翼翚即是其中的兩位。關于這批留日學生的學習情況,有記載稱:
往年清國學生之來者,僅清國公使館私聘教師以學日語二三人而已。其所謂官派留學生者,實以明治二十九年為嚆矢。當時公使裕庚氏經日本政府以十三人學生依囑高等師范學校長嘉納氏。于是氏直使同校教授本田增次郎氏當事,更又聘教師數人開始日語日文及普通學科之教授。此等留學生中或罹患疾患,或因事故致不得已而半途回國者往往有之。惟唐寶鍔、胡宗瀛、戢翼翚、朱光忠、馮訚模、呂烈煌等皆以良績卒三年之業。就中如唐寶鍔、胡宗瀛、戢翼翚等三人,更進修專門之學。及歸國后,在及第殿試,至昨年得賜進士出身。唐寶鍔、戢翼翚兩氏此次隨考察政治大臣載澤殿下行,任調查日本制度之責,克盡力于開發國運,其影響于清國前途者,正未有艾也。[5]
可以說,唐寶鍔、戢翼翚是首批留日學生中的佼佼者。唐寶鍔(1878—1953),族名宗鎏,字秀峰,又字秀豐,廣東省香山縣唐家村人,是近代著名政治家唐紹儀的族侄。戢翼翬(1878—1908),字元丞,湖北房縣人,曾在湖北自強學堂學習,是晚清重臣張之洞的得意門生。1896年,時值清廷總理衙門選派留日學生,唐寶鍔、戢翼翚等人應試入選,并于同年3月赴日,入日本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創辦的亦樂書院學習。
亦樂書院實行的是三年學制普通教育,開設課程含日語、算術、理科、歷史、地理、體操等。據日本講道館所藏亦樂書院資料,明治三十一年(1898)五月十一日至七月六日間,亦樂書院對這批留學生實施學年期末考試[6]13-15。此次期末考試,共測試了算術、歷史、地理、日語、理科等五科。日語科的平均成績是76.8分,在科目中排在第二位,僅次于理科平均成績81.4分。從學生的各科成績來看,除日語科目外,理科、算術、地理、歷史等科目成績均出現了不及格或剛剛及格的現象。而僅有日語成績全體學生均取得了“良”以上的好成績[7]。由此可以看出,亦樂書院的日語教學成效是所有科目中最好的。
唐寶鍔的日語成績為85分,位居全班第一,戢翼翚的日語成績75分,亦名列前茅。日語考試內容分“口試”和“筆試”兩項。筆試是“小論文”,即以命題作文的形式評定學生的日語成績,作文題目是“歲晚敘懷”。唐寶鍔在其作文中使用了如“なぜかというと”等相當于現代日語二級水平的語法知識點,除個別假名可能由于筆誤外,整篇文章文筆通暢,無明顯日語語法方面的錯誤[6]239。戢翼翚的日語雖稍遜色于唐寶鍔,但其文章中除了一兩處語法錯誤外,作文大體能準確表達所要表達的意思[6]236。可見,唐、戢二人通過兩年的留日學習,日語成績取得了很大進步,尤其是唐寶鍔的日語已達到相當于現在的日語二級水平。
1899年,唐寶鍔以第一名的成績從亦樂書院畢業。戢翼翚亦學習刻苦,成績優異。二人畢業后,整理并翻譯其在亦樂書院所使用的日語教材,編寫了清末第一種日語教科書《東語正規》[8]。
二、《東語正規》的刊行、版本與清末的出版機構
關于《東語正規》的刊行,學界尚未有統一的說法。國內學者袁家剛認為,《東語正規》先在日本由愛善社、三省堂印刷,然后帶回國發行[9]。日本學者實藤惠秀認為:“《東語正規》是在明治三十三年7月23日印刷、8月5日發行的,最初似乎是自費出版。明治三十五年以后,由譯書匯編社增補再版。”[2]300而大多數學者認為,《東語正規》由作新社發行[10]。
筆者基本贊成實藤惠秀的觀點,認為《東語正規》于1900年8月在日本東京刊行,為自費出版。1901年,戢翼翚委托日本印刷所印刷后帶回上海,與此同時在上海創辦了出洋學生編輯所,進而陸續發行《東語正規》三版、四版和五版。1902年,戢翼翚在日本人下田歌子、前代議員山田順一的贊助下創辦了作新社。作新社成立之初,發行的第一本書便是《東語正規》[11]。
初版《東語正規》不僅有日本眾議院議長片岡健吉題言,還有日華學堂留日學生唐寶晉的序言及日文序言[12]。《譯書匯編》1900年12月6日第一期“新書告白”中的《東語正規》初版售書廣告稱:
此書專為初學日語者津逮,其中分文言俗語,長句短句,精當便易,由淺入深,誠學日語者必要之書也。寄售處橫濱山下町201番信箱、202號福和號。[13]104
至1901年8月28日第8期為止,《譯書匯編》中仍然可以見到上述內容的廣告。1901年以后,唐寶鍔被調入東京公使館任職,后又兼任宏文學院的日語講師,無暇顧及《東語正規》的刊行,該書的發行業務便交由戢翼翚全權負責。
1901年,戢翼翚與同人在日本東京創辦了譯書匯編社。同年冬,戢翼翚在初版《東語正規》的基礎上刪去原刻古文《聊齋志異》,增補散語數十門,且增加著者自序一項,并以活版形式由譯書匯編社再版增廣發行。自1901年12月21日,《清議報》中始載有譯書匯編社發行之“再版增廣《東語正規》”書目[14]。因“東文之書在中國發印殊未便,故不能不在東付刊”,故1901年戢翼翚才將在日本已經完成的部分“譯述之書”包括《東語正規》,在日本印刷后帶到上海大東門內王氏育材書塾北市拋球場掃葉山房書坊代售。
1902年,戢翼翚完成學業回國后,在上海創辦了出洋學生編輯所,同時繼續再版發行《東語正規》。據出洋學生編輯所1902年刊第五版《東語正規》版權頁,該書于1900年8月5日初版,1901年11月18日再版,1902年3月31日三版,1902年5月28日四版,1902年6月20日五版發行。發行所為上海新馬路余慶里廿號出洋學生編輯所,印刷所為株式會社愛善社,販賣所為三省堂[15]。正因為作新社的前身是戢翼翚在上海創辦的出洋學生編輯所[3]18,作新社成立后,便代替了出洋學生編輯所的出版業務,出洋學生編輯所只編輯而不再兼發行業務。
那么,作新社何時開始發行《東語正規》?學者鄒振環認為,作新社大約于光緒二十七年(1901)秋在上海成立,其印制的第一本書可能就是《東語正規》的第二版[11]。但據日本東京朝日新聞社1902年11月6日載:
前代議員山田順一等二三位同志于本年(1902)7月間在上海英租界四馬路惠福里成立作新社,以翻譯出版新書為目的。該社已備置發動機,數臺印刷機同時運轉,且由該社出版的世界地理、萬國歷史等書籍現已再版三版發行,繼而將會發行以大陸為名的月刊雜志。[16]
由此可見,鄒振環關于作新社創辦時間的觀點與日本東京朝日新聞社的記載稍有出入。清末留日學生張繼在其光緒二十八年(1902)的回憶錄中寫道:“下田歌子說一資本家充眾議院議員者某氏,出資辦作新社于上海,由元丞及貫道主持。”[17]另一留日學生馮自由亦稱:“壬寅(1902年)以后,《國民報》諸友星散,戢翼翚開設作新社于上海。”[18]以上三則史料互相佐證,足以證明作新社成立于1902年7月。作新社成立之際,印制的《東語正規》已是第六版。
日本學者實藤惠秀曾言:“譯書匯編的中心人物是戢翼翚,作新社的重要人物是戢翼翚,出洋學生編輯所的中心人物是戢翼翚,國民社、國民報社的中心人物也是戢翼翚。”[2]307戢翼翚利用其職務之便,不僅通過譯書匯編社,還通過出洋學生編輯所、作新社等出版社再版刊行《東語正規》。自1902年作新社創辦,至1906年,《東語正規》已發行至十版,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銷量,為作新社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并將“語學”作為新近成立的作新社出版的一個重要方面[11]。在《東語正規》的引領下,作新社又陸續發行了《東語大全》《英文典問答》《東中大辭典》《增訂華英字典》等語學類書籍,且均銷路頗好[11]。
可見,戢翼翚借助《東語正規》的刊行創辦了譯書匯編社、出洋學生編輯所、作新社等出版機構。換言之,《東語正規》為清末民營出版社的創辦創造了一定的經濟基礎,為其持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三、《東語正規》與清末國人自編日語教科書
《東語正規》是清末第一種囊括日語假名、發音、單詞、語法、會話、讀本的綜合類日語教科書。在《東語正規》的引導和啟發下,留日學生編撰并發行了一系列日語教科書,對清末國人的日語學習及西學的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該書的編寫對清末國人自編日語教科書起到了重要的引領作用
《東語正規》認為“輸入文明之先導不得不求之于語學”[19]著者識,首次把學習日語的目的與學習西方新知識聯系起來。自此,日語成為獲取西方文明知識的新手段,日語學習被賦予了新的動機,這也是20世紀初大量出版日語教科書的重要賣點[20]。其后發行的日語教科書亦大多模仿《東語正規》的編撰方針,如吳啟孫在《和文釋例》中強調:“然則以個人之學問言不得不學日語,以世界之大勢言尤不得不學日語。至若兩國交際上之關系,更無論矣。”[21]《日語用法匯編》的著者亦在序中言:“語言者,亦科學之媒介,藉以傳種,藉以播精,且藉以孕育者也。”[22]
(二)國人自編日語教科書在音韻、語法、會話等方面繼承和發展了《東語正規》
1.對日語表音體系的整合和發展
從日語發音上看,《東語正規》強調日語發音的重要性。該書的音韻部分包括字母原委、字母音圖、字母解釋、聲調、拼音法、音調、變音等內容。對于假名的發音,書中采取漢字切音和羅馬字母注音兩種注音方式。如:
ウ(假名) 宇(真體) 鳥(官音) u(羅馬字)
え(假名) 衣(真體) 野(官音) ye(羅馬字)
は(假名) 波(真體) 哈(官音) ha(羅馬字)
以往的日語學習書,如《東語入門》[23]、《中東通語捷徑》[24]等書中僅包含日語中的平片假名以及日語中的清音、濁音、次清音。《東語正規》不僅采用羅馬字母標注日語讀音,且對日語的平片假名五十音圖、濁音、半濁音、撥音、促音、合字、變音要字、聲調、拼音法(拗音)、音調、變音(包括長變音、跳變音、雜變音)等內容作了比較全面的介紹。雖然某些專業術語在現在看來未必準確,但著者已認識到掌握這些日語發音的重要性。如其后刊行的《新編日本語言集全·漢譯日本新辭典合璧》把日語假名的各種發音方法統稱為“日本字母”項[25],至《東語簡要》始稱其為“音韻”[26],日語假名的發音開始有了正式名稱。自此,日語教科書競相模仿,并在書中單設“音韻”一章,專講日語假名的發音方法,如《日語新編》設“音韻之部”[27],《日語教程》亦包括“音韻篇”[28]。
2.對日語語法體系的構建
學者沈國威認為,《東語正規》“詳細介紹了日語的語法體系,甚至相當準確反映了當時日本國內語法研究的水準”[29]。日語語法體系的構建,主要關注日語詞類的劃分和日語語法項目的選擇兩方面的問題。
首先,《東語正規》在“文法摘要”中將日語詞類劃分為名詞、代名詞、動詞(附助動詞)、形容詞、副詞、后詞(即天爾遠波)、接續詞、感嘆詞八類。其后的語法類日語教科書,日語詞類的構成成分基本上包括名詞、代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助詞、助動詞、接續詞、感嘆詞等九大類或十大類,如《日本語言文字指南》[30]《東文典問答》[31]《東文法程》[32]等。
其次,區別于專門意義上的語法著作,用于教學的日語教材不需要完整的語法體系,只存在對語法項目的選擇。《東語正規》關注日語中的“虛字”,并重點講解了日語中日常使用頻率較高的テ(2種)、ニ(11種)、ヲ(3種)、ハ(2種)、ヘ(1種)、ト(2種)、ド(1種)、デ(4種)、ゾ(1種)、モ(2種)、ノ(12種)、カ(6種)、ガ(4種)、ヤ(3種)、バ(2種)、ノミ(1種)、バカリ(2種)、ダニ(1種)、マデ(3種)、サヘ(1種)、カラ(2種)、ヨリ(3種)、トモ(1種)、コソ(1種)、ナガラ(2種)、トテ(2種)等語法知識點,突出教學語法的色彩,著眼教學的需要。以后的日語教科書大多模仿《東語正規》將日語中的虛字單設為一項,進行講解。1902年,留日學生王鴻年編《日本語言文字指南》中設置“日本言語各種虛字之用法”一項,重點選取ノ、ケレドモ、ト、ニ、ハ、カラ、ヨリ、テモ、ダケ、バカリ、サヘ、ナガラ等語法項目。吳人達《東語大觀》的“語例”一卷,不僅包括テ、ニ、ヲ、ハ等虛字,還包括“~ニハ及ビマセン”“~越シタコトハ有リマセン”等現代日語教科書中常用語法項目[33]。《日語教程》則直接設置“實用語篇”,專門對各種常見語法124項進行說明與講解,對日語語法項目進行了大量擴充。《日語用法自習書》“語法用例類纂”中則網羅了日語常用語法180項[34]。這些語法知識點很可能是從實用角度出發,而日語教學語法的本質就應該是實用語法。
日本學者實藤惠秀曾說,當時并不缺乏日語學習用書,不過一般書籍都把日語當作中國語看待,書中使用了“アナタ何處行ク(你上哪兒去)”之類不正確的日語句子,并未考究日語助詞(てにをは)的用法[2]40,《東語正規》則不同。“與此前中國人編寫的日語教材僅僅收錄日語單詞和日常用語相比,《東語正規》詳細講解了日語的語音和語法,對日語的品詞進行了細致的劃分,標志著中國人的日語學習開始逐漸走向科學和系統。”[35]
3.對日語“會話”模式的進一步完善
以往的日語學習書,并未單獨設置“會話”一項。《東語正規》模仿明治時期漢語教科書的編纂方式,設置“散語”“問答”等項。尤其是問答部分包括日用語、燕居語、訪友語、游歷語、慶賀語、吊唁語、買賣語、商業語、學校語、天時語、消遣語、辭別語等12項,實為中日互譯的日常短語及會話句子。其后的日語教科書則在《東語正規》的基礎上獲得了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如《新編日本語言集全·漢譯日本新辭典合璧》模仿《東語正規》設置拜訪語、學問語、游歷語、慶賀語、天氣語、購物語、商賈語、游覽語、旅行語、問路語等15章,并把稱謂由“散語”“問答”改為“會話部”。《日語新編》則直接劃分“會話之部”一章,設置應酬、初次會面、酒宴、天氣、訪人、打仗、進學堂、講堂雜話、運動會等40個題目,把日語會話由先前“~語”的固定模式發展到有主題性的會話內容。其后留學生所編日語會話書大多仿照該書,收集留學生留日生活各個場景所需實用會話,不僅選擇各種主題的會話內容,更在情景會話中追求簡捷、自然,更貼近實際環境和當時的生活狀態。為適應清末留學生在日學習、生活的需要,清末的日語會話課本將對話情境鎖定在日常交際、學校生活等方面。此部分內容既反映了留日預備學校的教學內容,又可以窺見留日學生的各種場景和生態,具有生動的史料價值。
正如日本學者實藤惠秀所言:“中國人習日語始自明代的《日本寄語》。最初的日語學習書并非單行本,而是研究日本的書籍中經常會出現的日語。但這些日語大多是日語單詞,而日語句子很少。即使出現日語句子,也并非以日語為主,而是以中國語為主,日語為輔。所以,即使是會話,也都是些漏掉日語中テ二ヲハ的奇怪日語。《東語正規》出現后就發生了變化。《東語正規》以日語為主,與之前出現的書完全不同。該書考察假名的源流,講解語法,教授日語會話內容等,應有盡有。甚至還講解日語的語音、音調。至此,可以說,中國人的日語研究終究走上了正軌。……從此,赴日的留學生人人都購買《東語正規》。《東語正規》屢次再版,無與倫比。”[3]16
四、《東語正規》對清末國人日語學習的影響
《東語正規》由首批留日學生所編,是中國人日本留學效果的體現[2]50。針對當時風行一時的《和文漢讀法》[36],《東語正規》另辟蹊徑,強調日語口語的學習。在中國近代日語教育史上,《東語正規》在日語音韻、語法、會話等方面對清末國人自編日語教科書產生了重大影響,致使清末國人的日語學習和日語教科書的編撰開始了一次由日語書面語學習向口語學習轉型的歷史時期。梁啟超已深刻認識到,《和文漢讀法》僅能“學日本文以讀日本書”,而“治東學者不可不通東語,此亦正格也。蓋通其語則能入其學校,受其講義,接其通人,上下其議論,且讀書常能正確,無或毫厘千里以失其本意”[37]81-82。但因當時日本“言文一致”尚未完成,日本語與日本文是完全分開的,正如他所說:“有學日本語之法,有作日本文之法,有學日本文之法,三者當分別言之。學日本語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學日本文者,數日小成,數月大成。”[37]然而,清末國人的速成心理使日語學習者對《和文漢讀法》格外偏愛。但僅學日本文而不學日本語,其弊端已日益顯現。1901年,曾對《和文漢讀法》大為舉薦的蔡元培購買了《東語正規》[38],同年,南洋公學負責人沈曾植亦寫信建議羅振玉購買《東語正規》[39]。可見,此時的《和文漢讀法》已無法滿足清末知識分子的日語學習需求。清末《直隸官書局運售各省官刻書籍總目》列有《東語正規》一書,卻未見《和文漢讀法》。且其所羅列的幾種日語學習書中,《東語正規》的售價遠遠高于其他書籍[40]。由此可見,在當時為數不多的日語教科書中,《東語正規》可謂一枝獨秀。《東語正規》刊行后,號稱“留學生界雜志之元祖”的《譯書匯編》對該書稱譽有加:“津逮其中,分文言俗語長句短句,精當便易,由淺入深,誠學日語者必要之書也。”[13]104
《東語正規》刊行的年代,“當時日本口語是個新事物,尚處于嫩芽剛剛破土而出階段。如有名的(尾崎)紅葉的小說《金色夜叉》、(德富)蘆花的《不如歸》等都是文語體,只有出場人物的對話是口語體。教科書中當然也是文語體居多。”[41]但留日學生唐寶鍔、戢翼翚在“口語被稱為俗語,尤其是俗語語法被輕視的風氣下”,不隨波逐流,倡導學習日語口語以及語法學習的必要性。可以說,唐、戢二人所編《東語正規》在中國日本語教育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筆,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正如日本眾議院議長片岡健吉所說:“唐、戢二生著此書。殆使東西為一家。其功豈不偉乎哉。”[12]題言
其次,較之《和文漢讀法》,《東語正規》的使用對象更廣。《和文漢讀法》的使用對象為國內已通漢文的成年人[37]81-82;《東語正規》的編撰目的在于“務使學者研究此書即可從事一切普通專門學問”[19]凡例,其使用對象不僅僅限于那些已熟練掌握漢文的學者,而且包括那些不具備漢文素養卻想掌握近代西方知識的年輕人。清末的赴日留學生大多未在國內取得功名,千辛萬苦來到日本,希望掌握日語,進而學習數學、理科、歷史、體操、衛生等中學課程,考入日本的專門學校或大學,然后從事專門的軍事、經濟和法律知識的學習。因此,可以說《東語正規》的使用對象更廣。《東語正規》不僅被清末的日文學堂當作日語入門教材廣泛使用,且是當時留日學生常用的材料[42]。早期中國留日學生大都使用該書,幾乎人手一冊,對當時的留日學生有很大幫助[1]。
自1896到1937年,《東語正規》“多次再版,深受中國學生歡迎”,被5萬名在日中國人和其他人士作為日語學習書所使用[10]。在《東語正規》的啟發下,《東語簡要》《東語大觀》《日語教程》《日語新編》等一系列強調日語口語學習的日語教科書相繼出現,對清末國人的日語學習以及西學的引進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劉禺生說:“《東語正規》《日本文字解》諸書,導中國人士能讀日本書籍,溝通歐化,廣譯世界學術政治諸書,中國開明有大功焉。”[43]由此可見,《東語正規》一書在指導清末中國人“學東語”“讀東文”“譯東書”方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本文初稿曾提交2019年10月在浙江工商大學舉辦的“東亞視域下的中日文化關系——以往來人物為中心”國際學術研討會,感謝評議人的寶貴意見!)
參考文獻:
[1] 唐培堃.中國最早的留日學士唐寶鍔[G]//珠海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珠海文史第7輯.珠海: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88:65.
[2]実藤恵秀.中國人日本留學史[M].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81.
[3]実藤恵秀.中國留學生史談[M].東京:第一書房,1981.
[4]范鐵權,孔祥吉.革命黨人戢翼翚重要史實述考[J].歷史研究,2013(5):173-182.
[5]舒新城.近代中國留學史[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1:15.
[6]蔭山雅博.明治日本與中國留學生教育[M].東京:雄山社,2016.
[7]酒井順一郎.清國人日本留學生の言語文化接觸——相互誤解の日中教育文化交流[M].東京:ひつじ書房,2010:83.
[8]谷口知子.中國人向け日本語教科書『東語初階』·『東語真伝』:伊澤修二と泰東同文局[C]//関西大學亜細亜文化交流センタ―言語文化研究クラス第26回研究例會論文.大阪:関西大學,2009:343.
[9]袁家剛,丁福保.《辛丑日記》釋注:下[C]//上海市檔案館.上海檔案史料研究:第14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286.
[10]馬克·奧尼爾.唐家王朝:改變中國的十二位香山子弟[M].張琨,譯.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6:203.
[11]鄒振環.戢元丞及其創辦的作新社與《大陸報》[J].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6):106-116.
[12]唐寶鍔,戢翼翚.東語正規[M].東京:著者刊,1900.
[13]吳湘相.譯書匯編:第一期[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
[14]譯書匯編社發行書目[N].清議報第100冊,1901-12-21.
[15]唐寶鍔,戢翼翚.東語正規[M].上海:出洋學生編輯所,1902.
[16]清國新書業[N].日本東京朝日新聞社朝刊,1902-11-06(3).
[17]張繼.張溥泉先生回憶錄·日記[M].臺北:文海出版社,1985:5.
[18]馮自由:革命逸史上[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59.
[19]唐寶鍔,戢翼翚.東語正規[M].上海:作新社,1903.
[20]沈國威.近代東亞語境中的日語——從“方言”到文明的載體[J].或問,2009(16):85-97.
[21]吳啟孫.和文釋例[M].上海:文明書局,北京:華北譯書局,1903:序.
[22]畢祖諴,李文蔚.日語用法匯編[M].東京:清國留學生會館,1905:序.
[23]陳天麒.東語入門[M].上海:海鹽陳氏石印,1895.
[24]王惕齋.中東通語捷徑[M].東京:著者刊,1887.
[25]王杰.新編日本語言集全漢譯日本新辭典合璧[M].上海:科學書局,1906.
[26]葛夢樸.東語簡要[M].東京:清國留學生會館,1905.
[27]葉良,李賡桐.日語新編[M].東京:清國留學生會館,1905.
[28]湘漁.日語教程[M].東京:游藝社,上海:廣智書局,1906.
[29]沈國威.關于“和文奇字解”類的資料[J].或問,2008(14):117-128.
[30]王鴻年.日本語言文字指南[M].東京:王惕齋,1902.
[31]丁福保.東文典問答[M].上海:著者刊,1902.
[32]商務印書館.東文法程[M].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
[33]吳人達.東語大觀[M].東京:清國留學生會館,1906.
[34]渡邊直助,楊汝梅.日語用法自習書[M].東京:清國留學生會館,1907.
[35]鮮明.《東語正規》在中國日語教育史上的意義[J].日語學習與研究,2011(6):75-81.
[36]肖朗,孫瑩瑩.梁啟超的《和文漢讀法》及其對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響[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1):56-68.
[37]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M].北京:中華書局,2003.
[38]中國蔡元培研究會.蔡元培全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343.
[39]羅繼祖.我的祖父羅振玉[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47.
[40]王勤謨.王惕齋及嫡孫文集——中日文化交流先行者[M].寧波:寧波出版社,2013:51.
[41]松本亀次郎.隣邦留學生教育の回顧と將來[M]//二見剛史.日中の道、天命なり——松本亀次郎研究.東京:學文社,2016:318.
[42]実藤恵秀.中國人の日本語研究[C]//國語文化講座第六巻國語進出篇.東京:朝日新聞社,1942:277.
[43]劉禺生.世載堂雜憶[M].北京:中華書局,1960:155.
(責任編輯:楊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