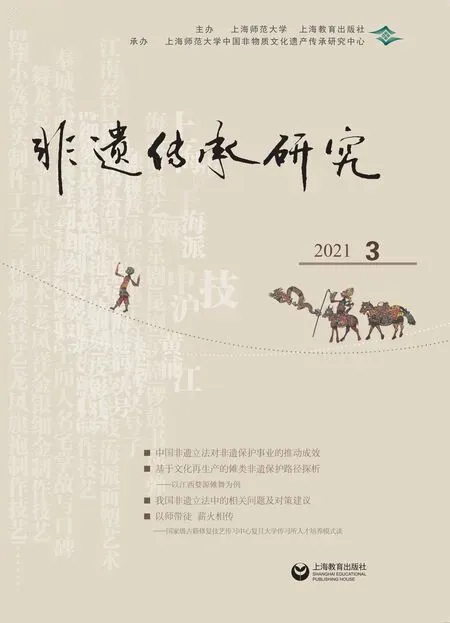先棉祠標賣案始末
郭雪純
清乾隆年間,“衣被天下”的松江府棉布產量高達數千萬匹之多。松江土布的制作離不開黃道婆傳授婦女軋花、彈花、紡紗、織布等技藝。為紀念黃道婆的貢獻,人們建先棉祠以祭拜感恩。到了20世紀初期,上海作為近代工業中心,其棉布紡織產量竟驟減到數百萬匹之下,本土生產出的布匹甚至無路可銷。為了改變這種境況,各界人士紛紛倡議使用土布,以抵制洋布的沖擊。1933年6月中旬,江蘇省立上海中學遷址一事引發熱議,原因是該校舍要進行標賣,而校舍中正好有先棉祠。人們得知先棉祠要被標賣,自是議論紛紛。一段標賣先棉祠案由此發生。

先棉祠

1937年上海中學先棉堂
一、古跡與新物的較量
據考證,元初黃道婆去世后,烏泥涇人趙如珪立祠紀念她。此后,先棉祠屢次被毀又多次重建。清道光六年(1826年),邑人李林松等稟知縣許乃大,因烏泥涇廟在鄉間,地方官祭祀不便,擬在城廂新建一專祠,遂獲準在城廂西門內半段涇李氏吾園右側建先棉祠。同治四年(1865年),蘇松太常兵備道丁日昌倡辦龍門書院。同治六年(1867年),吾園改作龍門書院,書院兼管先棉祠。后來廢科舉興學堂,光緒三十年(1904年),改龍門書院為蘇松太道官立師范學校,又稱為龍門師范學校,擴建校舍時并入了先棉祠,祠則由學校管理。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先棉祠的頭門、戲樓等俱毀,就在梅溪弄(今先棉祠南弄)另造了一祠。宣統二年(1910年),蘇松太道官立師范學校更名為江蘇省立第二師范學校。1927年,該校與江蘇省立商業專門學校等校合并組成江蘇省立上海中學,先棉祠仍保存。改組后的上海中學總辦公室和高中部設在陸家浜路,初中部設在尚文路省二師原址。同年9月,大夏大學教授鄭通和出任上海中學校長。[1]
鑒于初、高中校舍分處兩地,教學管理和活動多有不便,且校舍陳舊、設施不完善,1930年,鄭通和計劃出售舊校舍。他發現上海城區與郊區地價相差甚大,于是考慮將城區初、高中兩處校舍合并出售,另在上海郊區購新地置校,擴大校舍面積。鄭通和把該計劃上報給當時的江蘇省府核準,但未被采納。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事變相繼發生,日軍侵犯我國東北和上海地區。國難當頭,江蘇省立上海中學遷址一事暫被擱置。1932年,《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后,鄭通和又向改組后的新省府與教育廳詳細陳述了遷校的必要性,終于得到了核準。核準后,他第一步做出的行動是將原有二師房屋基地連同先棉祠全數出售。第二步則是購置新地建校。[2]但事情進展并不順利,1933年6月15日,閘北區農會在《申報》上刊登《反對出售先棉祠》一文,竭力反對標賣先棉祠:
本市西門尚文路上海中學,因擴充校舍遷移校址,有將現在校址及陸家浜校址一并出賣。惟尚文路校址即前龍門師范學校,內有應公祠及先棉祠,均為地方公產。而先棉祠更為紀念農業先哲黃道婆者,因此本市閘北區農會竭力反對,昨特具呈市黨部市政府,請嚴予禁止。[3]
標賣先棉祠一案便由此開始了。鄭通和提議標賣先棉祠并不是為一己私欲,作為江蘇省立上海中學的校長,要為學校前途著想,更要沿襲龍門書院“教育救國”的傳統,大力發展教育。但先棉祠是古跡,也是農民祈愿得到黃道婆庇佑之所,標賣先棉祠會破壞人們心中對先棉的尊敬與崇拜。農會是農民的代表,自會發出反對之聲。
二、經濟與文化的博弈
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內戰爆發。又逢天災,農業歉收,手工生產蕭條。加之,1929—1933年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爆發,中國作為帝國主義商品傾銷地受害加深,傳統農業和手工業受到致命沖擊,民眾的國貨購買力嚴重不足。為了提高國民使用土布的意識,增加農民生產,促進本土經濟增長,上海縣農教館舉辦了土布展覽會。“土布運動”在此基礎上應運而生。“土布運動”推進過程中,先棉祠作為傳統棉紡織業的象征性建筑物,標賣一事激化了各方矛盾。
標賣先棉祠的消息一經傳出,先棉祠的產權歸屬引發熱議。閘北區農會認為,“惟尚文路校址即前龍門師范學校,內有應公祠及先棉祠,均為地方公產。而先棉祠更為紀念農業先哲黃道婆者,因此本市閘北區農會竭力反對”[3]。市農會則認為標賣先棉祠有監守自盜的嫌疑,提請特別市政府調查產權:
為愛護農界古跡,迫不得已特再申述理由。查縣志所載,祇由書院(今之江蘇省立上海中學,即昔之書院改名)管理基產權之非書院所有,彰彰甚明。今上海中學從何而取得先棉祠之產權?如以保管而即占為己有,是則無異監守自盜。故以產權言,上海中學亦不得擅自將先棉祠基地標賣……當經本會及閘北區農會先后呈請鈞會,請求制止標賣,以存古跡、尊重公產,并撥歸本會保管,留辦農事陳列所。[4]
市農會力挽狂瀾,有意將先棉祠留于農事陳列所,但未得到市府準許。經市土地局查明,“該項祠產雖為地方公有,載諸邑乘,但已于民國三年由上海縣署給予管業證書,故該項產業已為上海中學校所有”[5]。從產權上講,先棉祠歸江蘇省立上海中學所有,賣與不賣應由學校自行決定。
另一個沖突源于先棉祠的安置地點。上海縣農教館館長張翼,身負推行“土布救國”的壓力。為挽救農村經濟,張翼試圖開拓農村市場,想借此次標賣先棉祠的機會,打開農村民眾生產、服用土布的窗口。于是,他提出“先棉祠進入農村”的主張,當時《新聞報》作了如下報道:
當此上海中學遺址,先棉祠亦有遷往鄉間之必要。先棉祠之所以建立,旨在追念道婆之功,并為農夫村女瞻仰之所,我邑農業有改道必要,生產有增加必要,先棉祠應乘此機會進入農村,而為農業改道生產增加之機也。[6]
張翼表示,上海市場早已今非昔比,棉田不再依傍先棉祠而設,城市中機杼之聲也逐漸消失。先棉祠對農村來說,意義更重大,為此,“先棉祠應乘此機會進入農村,而為農業改道生產增加之機也”,既利于農村經濟的恢復,又可以解決先棉祠留存的問題。閘北區農會聽聞張翼主張先棉入村、不妨出售先棉祠的言論后,發出強烈質疑:
張翼身居農教館館長,應如何尊崇農業先哲,喚起農民瞻往思來,知所改進,而曰先棉祠不妨出售,試問是何理由?……今張某以農教教長身份,竟表示不妨出賣先棉祠,遷往鄉間,殊屬費解。[7]
閘北區農會指出,人們祭拜先棉的熱切和向往,在城區較為明顯,“全國各地均有宗教圣地、賢哲專祠,有紀念性的古跡位于繁盛區域,居民眾多,也易于瞻仰,一旦易地則失其效用”[7]。先棉祠在繁華的城區,就會有更多人去祭拜,但遷往鄉間后,受眾會減少,效用也會隨之衰退。因此,農會一再反對,先棉祠遷往鄉間進展滯緩。
土布展覽會的舉辦,促發了“土布救國”的意識,先棉祠也慢慢被人們所重視。民眾知曉先棉祠要被標賣后,多有不滿。如火龍在《新春秋》上發表《土布運動中的先棉祠》一文,直接指明先棉祠應該修復而非售賣:
該先棉祠因年久失修,已成廢丘。士紳輩之慧黠者不但不設法去修復,抑且連廢基都想賣去。現在土布又在大運動了,這紀念土布發明之先棉祠似當加以修復,用以昭示我們。[8]
先棉祠不應被當作金錢利益的載體,更不是封建迷信的殘留物,它具有一定的文化延續性,正是先棉祠的作用才使人們的集體記憶得以重構。[9]先棉祠一旦被遷址,抑或被拆除,都會讓新潮的城市缺失了一些歷史的積淀,對先棉的感念和敬仰也會隨之蕩然無存。對民眾來講,先棉祠的文化要義遠勝于其經濟價值,所以標賣先棉祠遭到了民眾的反對。
三、過往與當今的交融
元朝之前,松江府沒有人會種棉花,農婦也不會紡織,所需的衣料大多來自外埠。黃道婆傳授播種方法、紡織技藝后,紡紗織布日益成為農村的副業,土布事業漸漸發達,衣料也不用再仰求外埠供給。黃道婆賦予了小農經濟新的希望,先棉祠恰是人們對這段歷史最好的緬懷。不管是古跡與新物的較量,還是經濟與文化的博弈,歷史遺跡都不能因時代變遷而被磨滅,先棉祠的存在是人們對歷史的一種紀念和傳承。
1.當時的結局
先棉祠雖由江蘇省立上海中學措置,但其蘊含了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內涵,所以1933年12月《申報》刊登了特別市府保存古跡的條例。特別市府令江蘇省立上海中學遷址后要建一處先棉堂,以示對黃道婆的懷念:
1934年,江蘇省立上海中學終于在舊滬閔路吳家巷(今上中路400號)購地460余畝,用時七月有余,興建好了新的校舍,與此同時,先棉堂也修建完成。至于那座被標賣的先棉祠,根據1936年《上海報》中汪瘦秋的文章可知,“迨去年,舊校址即拍賣與人。那座含有悠久歷史的先棉祠,即被承購地主與上中校舍同時拆除”。[10]激發了廣泛社會討論的先棉祠標賣一事,還是以先棉祠的拆除告終了,僅保留了“先棉祠弄”的名稱,獨存下了梅溪弄處的先棉祠。
2.當今的重生
20世紀30年代后期,“土布運動”發展緩慢,“洋貨”充斥著市場,土布生存如履薄冰,先棉祠最終落得被拆除的結局。一樁樁、一件件無不展示著傳統手工業的衰微,正因如此,當代上海以史為鑒,將保護傳統手工紡織業提上日程。
2002年3月,上海市徐匯區文化局和華涇鎮人民政府共同出資,在華涇鎮徐梅路700號建造了一座黃道婆紀念館,并對外開放。2006年,烏泥涇棉紡織技藝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2018年又入選了第一批國家傳統工藝振興目錄。我國手工紡織技藝歷史悠久,但相關文獻資料囿于種種原因嚴重缺失,技藝傳承受限,現有的烏泥涇棉紡織技藝的保護意義不言而喻。2020年10月中旬,黃道婆紀念館重新打造和布展。全新的陳列館以黃道婆的生平經歷及其成就為主線展開,分為“絲路女兒”“技術革新”“先棉鼻祖”三大部分,人們參觀的同時也可以體悟傳統手工藝的制作過程。
回溯標賣先棉祠一案,是文化與經濟博弈、傳統與現代較量的產物,它內嵌于時代發展的軌跡中。“土布運動”雖以失敗告終,但也短暫地掀起了人們尊崇先棉的熱忱之情。如今的中國屹立于世界之林,綻放光彩。傳統手工業塵封的歷史也迎來了嶄新的篇章,黃道婆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野,她的功績也再次被人們頌贊。祭拜先棉,重塑歷史,方能看到技藝流傳的脈絡。先棉祠的記憶就這樣在當今以更豐富而生動的方式得到延續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