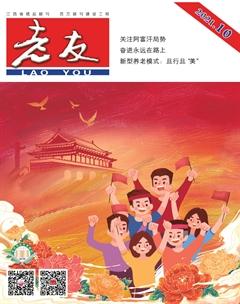我曾參與支農宣傳
詹信呈
我于1968年春應征入伍,部隊駐扎在福建西北山區。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部隊還擔負著“三支兩軍”(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這年冬季,上級命令我們部隊派出宣傳隊,到駐地開展支農宣傳工作。連隊立即選調了10多名有文藝特長的戰士,經過短期強化訓練,組成一支文藝宣傳隊,由一名副排長帶隊,按上級指定的路線,深入農村開展支農宣傳工作。我有幸被選上了。
冬季福建西北山區氣溫很低,上級指派的地點又是最偏僻的區域,我們每人帶著棉被、墊子、雨衣、換洗衣褲和演出用的樂器,背包足有二三十斤重。有一次,我們翻越一座海拔一千多米的山,每人身背沉重的背包,沿著陡峭的山路,低頭弓背吃力地向上攀爬,一個個都汗流浹背。到山頂停下休息時,大家對視后不禁哈哈大笑,因為每個人的眉毛和前額頭發都變得雪白。原來我們低頭彎腰爬山時,呼出的熱氣直沖眉梢,遇到山上的寒氣就凝成白霜,一個個小伙子似乎都變成白眉毛、白頭發的老翁了。
當時福建西北山區基本不通電,我們所在地的村子還有用汽燈做會場照明工具的,那場景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根本沒見過。汽燈用煤油做燃料,充足汽后點燃紗罩,亮度可抵現在的一百瓦燈泡。沒有汽燈的小村子,只能用松樹片火把照明。在我們演出的地方便是如此,往往是舞臺兩邊支起火把籠,生產隊干部負責往火把籠中添加松樹片。我們當時演出的節目都是歌頌毛主席、共產黨,歌頌社會主義、憶苦思甜和擁軍愛民等內容的歌曲舞蹈、說唱快板和短劇,演出中還要插入一段政治宣傳。樂器只有一支笛子、一把板胡、一把二胡和一把三弦。由于人手少,不少人都身兼數職,像鑼鼓等打擊樂就沒有固定的人演奏。我當時負責拉二胡、幫助敲鑼鼓,還要撰寫演出前的致辭和銜接節目的串詞。在那個精神文化生活相當匱乏的年代,特別是在那邊遠偏僻的山區,群眾很難看到文藝宣傳和文藝演出。我們的節目談不上出色,但我們身穿軍裝,聲音洪亮、動作整齊有力、內容通俗易懂又貼近時代,很受群眾歡迎。每次演出有一個多小時,群眾在露天下觀看,中途沒有一個人離場。我們的演出取得了很好的宣傳教育效果。
我們每到一個村莊,都住在生產隊的倉庫里或村子里的老舊空屋里,在地上鋪上稻草、墊上自帶的雨衣充當床鋪,不給群眾增添任何麻煩。吃飯都是在貧下中農家吃派飯,當時群眾生活都很艱苦,一日三餐,有的兩干一稀,有的兩稀一干,干飯上放紅薯絲,稀飯和紅薯一起煮。部隊給我們備好糧票,每餐按規定付糧票。山區群眾很難見到糧票,見到糧票時,他們都相當高興。
我們晚上演出,白天參加生產隊集體勞動,冬季的農活基本是鏟田埂,再就是挖禾蔸,即把割完稻谷的稻草根挖出來把泥土敲碎,減少來年的蟲害。天氣不好干不了農活,我們就打掃村里的環境衛生,幫孤寡老人挑水劈柴。我們這些舉動深受群眾夸贊。
一個多月的支農宣傳工作,我們翻過了一座座山嶺,走過了一個個村莊。大的村子住三四天,小的村子住一兩天。每當離別時,群眾歡送出村外,不少老大爺老大娘久久凝視我們的紅領章紅帽徽,一邊說著方言,一邊用手比畫。生產隊干部“翻譯”他們的話,說我們真像當年在這一帶干革命的紅軍。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那段特殊的經歷還深深地刻在我的腦海里。
責編/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