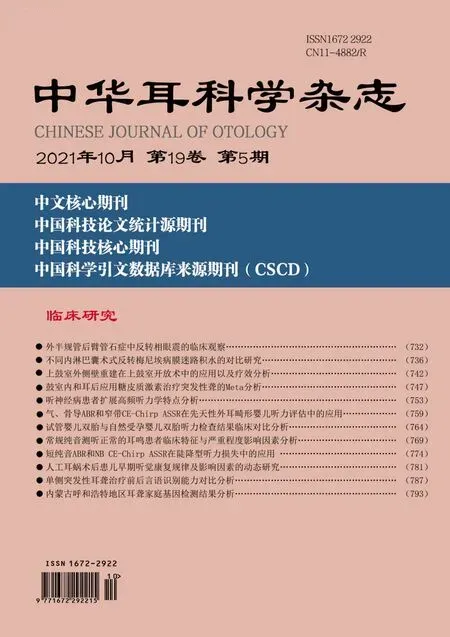多巴胺受體調節聽覺功能及調控耳鳴機制的研究進展
覃江圓 陳慧英 韋廷佳 林曉宇 劉金蘭 葉文華 韋芳玉 蘇紀平
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南寧530021)
耳鳴分為主觀耳鳴和客觀耳鳴。客觀耳鳴較少見,通常來源于體內的生物活動并傳導到耳部,如中耳、咽鼓管或軟腭的血液湍流產生的聲音,脈搏聲以及傳遞到耳朵的肌肉收縮聲[1]。主觀耳鳴指缺乏相應聲源的耳鳴,為平常所指的耳鳴,也是本綜述所指的耳鳴,與許多因素有關,如中耳炎、聽覺通路腫瘤、年齡相關、耳毒性藥物、感覺神經性耳聾、噪聲暴露、神經系統疾病、頭部外傷或顳骨骨折,以及高血壓、糖尿病、心理障礙等其他系統疾病[2],這些因素導致的耳鳴通常伴有聽力損失。耳鳴在人群中的患病率高達21%,其中約1%~3%伴嚴重的心理問題,可導致抑郁、焦慮甚至自殺[3]。目前,我們對耳鳴發病機制仍然知之甚少,缺乏有效的治療方法[4]。
多巴胺是兒茶酚胺神經遞質,是腦內重要的神經遞質之一,參與情感、認知、記憶、運動和內分泌等生理活動的調節。多巴胺分泌減少以及多巴胺受體(dopamine receptors,DR)功能改變與帕金森氏病、精神分裂癥、抑郁癥、躁郁癥等疾病有關[5]。慢性耳鳴患者中,抑郁、焦慮等情緒障礙的發生率顯著高于正常人群[6]。減輕耳鳴患者的抑郁、焦慮等情緒障礙是耳鳴治療的方向之一[7]。在中樞神經系統發現,負責感知耳鳴的大腦結構和多巴胺能通路所在的大腦結構多有重疊,包括:顳區域、前額葉區域、顳頂相關區域、杏仁核、海馬以及邊緣系統,說明多巴胺能通路與耳鳴發病機制密切相關[8]。因此,對聽覺系統中的多巴胺受體進行深入研究有望為耳鳴治療提供新的靶點。本文將重點綜述DR對聽覺功能的影響以及DR與耳鳴的關系,以尋找耳鳴機制研究的新方向。
1 DR在內耳的表達
DR屬于G蛋白偶聯受體家族[9],包含D1-D5共5個亞型,根據是否激活腺苷環化酶(adenylatecyclase,AC)分為 D1家族(dopamine D1-like receptors,DR1)和 D2 家族(dopamine D2-like receptors,DR2)。DR1包括D1、D5亞型,激活后與G蛋白的Gαs/olf亞單位偶聯,活化AC以產生第二信使環磷酸腺苷(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cAMP),從而激活下游信號通路;DR2包括D2-D4亞型,激活后與Gαi/o亞單位偶聯,抑制AC活性,從而降低cAMP,產生信號級聯反應[5]。
在人類中樞神經系統,DR的相對密度是D1>D2>D3>D5>D4[10]。在內耳,DR也有表達。利用免疫組化在產后10-13天的小鼠耳蝸螺旋神經節神經元(spiral ganglion neurons,SGNs)和外毛細胞中檢出D1、D2和D5受體,D4僅在SGNs發現,各亞型在內毛細胞中均未檢出[11]。也有研究發現D1受體定位于內毛細胞底部,并緊密定位于內毛細胞的突觸前區域[12]。在成熟小鼠耳蝸檢測到除D3以外的各亞型的mRNA[11]。在成年大鼠SGNs,5個亞型均有表達,D1、D5的表達高于另外幾個亞型[13]。
2 DR對聽覺功能的調節
2.1 DR1對聽覺功能的調節
2.1.1 DR1對中樞聽覺功能的調節
采用基因敲除技術將小鼠的D1受體敲除,小鼠所有頻率的聽覺腦干反應(auditory brainstem response,ABR)閾值提高5dB-20dB。D5受體敲除后,小鼠的ABR仍然正常,但表現出更高的噪聲易感性[11]。
2.1.2 DR1對外周聽覺功能的調節
研究表明,DR1激活劑SKF38393使豚鼠復合動作電位(compound action potential,CAP)振幅升高,而DR1抑制劑SKF83566則使CAP振幅降低,CAP閾值在所有頻率均升高,認為DR1激活可增強聽神經的活性[14]。Garrett等觀察到不同的結果,發現DR1激活劑SKF38393和SKF81297使豚鼠CAP振幅顯著抑制,總和電位(summating potential,SP)幅度保持不變,認為激活DR1對傳入樹突有抑制作用,抑制了聲音誘發的反應,而DR1抑制劑SCH23390對CAP、SP作用很小或沒有作用[15]。李雪實等則發現,豚鼠耳蝸灌注DR1抑制劑SCH23390后,CAP振幅升高,但隨著時間延長逐漸降低并低于灌流前水平;耳蝸微音電位(cochlear microphonic potential,CM)振幅輕度降低,對畸變產物耳聲發射(distortion product otoacoustic emission,DPOAE)沒有明顯影響,認為抑制DR1可瞬時阻斷多巴胺對傳入神經的抑制作用,而對外毛細胞無影響[16]。Toro等在斑馬魚聲側枝上皮中發現,DR1激活劑SKF38393使CM振幅升高,而DR1抑制劑SCH23390使CM振幅降低[12]。小鼠的D1受體敲除后,耳蝸反應增強,DPOAE閾值在高頻區域升高;D5受體敲除后,小鼠的DPOAE仍然正常[11]。
2.2 DR2對聽覺功能的調節
2.2.1 DR2對中樞聽覺功能的調節
對DR2而言,將小鼠的D2受體敲除后,所有頻率的ABR閾值提高5dB-10dB;與敲除D5受體類似,D3、D4受體敲除后,小鼠的ABR也仍然正常,但對噪聲也更易感[11]。
2.2.2 DR2對外周聽覺功能的調節
D2受體特異性激活劑(+)PHNO對豚鼠CAP振幅影響不大,而D2受體特異性抑制劑L741626導致CAP明顯抑制,并降低SP、CM、DPOAE幅度[15]。豚鼠耳蝸灌注 L741626后,高頻刺激(4、8、16、24kHz)使CAP閾值增加,低頻刺激(1、2kHz)對CAP閾值無影響,DPOAE和CM振幅均顯著降低[17]。盡管D2與D3受體的跨膜結構域具有75%的同源性[18],但 D3受體激活劑 PD128907和抑制劑U99194A對耳蝸功能均無明顯影響[15]。
將小鼠的D2受體敲除后,小鼠的耳蝸反應減弱,DPOAE閾值僅在大于32 kHz的高頻區域才顯著升高。與敲除D5受體類似,D3、D4受體基因敲除后,小鼠的DPOAE也仍然正常[11]。
以上研究可看出,盡管DR1和DR2通過AC介導相反的信號通路,但DR1和DR2對聽覺功能可產生相同的影響,并非完全相反。Niu等認為在低聲級(非強噪聲)條件下,DR1可能起主導作用,增強興奮作用,使CAP振幅增加,而在噪聲條件下,DR2可能起主導作用并增強抑制作用[14]。Maison等認為,DR1對CAP的影響出現矛盾結果的原因可能與DR1僅在突觸后表達、而DR2既在突觸后表達也在突觸前表達有關,但具體機制尚未清楚[11]。多種DR亞型和SGNs、毛細胞等靶細胞的存在使得多巴胺能信號對聽覺功能的調節機制十分復雜。另外,盡管DR各亞型在耳蝸中均能檢出,但D1和D2亞型敲除后對聽覺功能的影響較大,這兩個亞型的作用可能更為關鍵。
3 DR調節聽覺功能的信號通路
眾多研究利用DR1或DR2激活劑/抑制劑對DR1、DR2的下游信號通路進行研究,以探索DR1、DR2對聽覺功能進行調節的可能分子機制。
3.1 DR1調節聽覺功能的信號通路
3.1.1 DR1-cAMP-PKA-DARPP-32途徑
在豚鼠耳蝸中可檢測到多巴胺和cAMP調節的磷酸化蛋白32kDa(dopamine and cAMP-regulated phosphoprotein 32 kDa,DARPP-32),DARPP-32受cAMP及相關蛋白激酶如蛋白激酶A(protein kinase A,PKA)、蛋白激酶 C(protein kinase C,PKC)的調節,提示多巴胺或DR的下游通路是通過cAMP及相關蛋白激酶介導的。進一步發現,PKA抑制劑H-89可以阻斷DR1激活劑SKF38393對豚鼠CAP的增強作用,而PKA激活劑福司可林則可對抗DR1抑制劑SCH23390對CAP的抑制作用,說明PKA介導DR1對CAP的調節[14]。
目前認為,生理狀態下的快速興奮神經傳遞更多由離子型谷氨酸受體中的α氨基-3-羥基-5-甲基-4-異惡唑丙酸(α-amino-3-hydroxy-5-methyl-4-isoxazolepropionic acid receptors,AMPA)受體介導。研究發現,SKF38393可增強PKA對AMPA受體GluR1亞基Ser845位點的磷酸化,說明DR1可通過cAMP-PKA-DARPP-32信號通路調節耳蝸的神經活動。但僅僅激活PKA對GluR1的磷酸化水平增加的幅度并不像單獨激活DR1那么大,說明DR1在耳蝸的信號通路除cAMP-PKA-DARPP-32外可能還涉及其他途徑,如PKC或Ca2+/鈣調蛋白依賴性激酶Ⅱ(calmodulin-dependent protein kinaseⅡ,CaMKⅡ)等[14]。
3.1.2 DR1-Ca2+途徑
為了解多巴胺能信號如何調節毛細胞的活性,用SKF38393激活斑馬魚中的DR1,發現可增加毛細胞的CM振幅,而用SCH23390抑制DR1可降低CM,說明DR1的激活可增加毛細胞的活性。進一步利用鈣成像技術發現,SKF38393可導致毛細胞內Ga2+濃度升高,而毛細胞內Ga2+的增加依賴于L型鈣通道Cav1.3,使用依拉地平阻斷Cav1.3a通道可以阻斷SKF38393引起的Ca2+內流,說明DR1激活后是通過刺激Cav1.3a通道來促進毛細胞內Ca2+水平升高,從而增加毛細胞活性[12]。
3.1.3 DR1-Na+途徑
DR1激活劑SKF38393可劑量依賴性誘導小鼠SGNs的內向Na+電流,導致SGNs動作電位振幅降低,說明DR1激活可抑制SGNs的活性,導致SGNs興奮性降低,對抗谷氨酸過度釋放所造成的SGNs興奮毒性[19]。
但另外的研究發現,DR1激活劑A-68930可迅速抑制大鼠SGNs的Na+電流峰值幅度,這一效應是通過增強對Na+通道的磷酸化而產生:DR1激活后與Gαs蛋白偶聯上調cAMP,使PKA激活,促進Na+通道的磷酸化,導致Na+電流峰值幅度降低[20]。
3.1.4 DR1-受體相互作用途徑
受體相互作用(interaction)或受體對話(crosstalk)在調節受體功能、突觸傳導和神經可塑性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目前已經發現,多個受體與其他受體之間都存在相互作用,如DR1與N-甲基-D天門冬氨酸受體(N-methyl-D-aspartatereceptors,NMDAR)之間[21]、DR2與腺苷 A2A 受體之間[22]、NMDAR與A型γ氨基丁酸受體(γ-aminobutyric acid type A receptor,GABAAR)之間[23]均存在相互作用。目前認為,GABAAR介導的抑制性應答減弱是興奮毒性的部分機制,與耳鳴的發生密切相關[24]。長期、大劑量使用阿司匹林可引起暫時性的耳鳴和聽力損失,在耳毒性聽力損害機制的研究中,阿司匹林的活性代謝成分水楊酸鈉(sodium salycilate,SS)是最常用的工具之一[25]。在大鼠SGNs中發現,SS使GABAAR表面水平降低,而DR1抑制劑SCH23390可減輕SS對GABAAR胞膜表達的抑制作用,提示DR1可能通過與GABAAR的相互作用影響了GABAAR的轉運來參與SS對GABAAR的調節,但具體機制仍需進一步探討[26]。
3.2 DR2調節聽覺功能的信號通路
3.2.1 DR2-Na+途徑
與DR1激活劑類似,DR2激活劑喹吡羅也可誘導小鼠SGNs的內向Na+電流,降低SGNs的動作電位振幅,抑制SGNs[19]。另外,喹吡羅也可抑制大鼠SGNs的Na+電流峰值幅度,但與DR1-cAMPPKA通路不同,DR2激活后是與Gαq蛋白偶聯,通過上調磷脂酶C(phospholipases C,PLC)-PKC信號通路來促進Na+通道的磷酸化,導致Na+電流峰值幅度降低[20]。
3.2.2 DR2-受體相互作用途徑
在大鼠SGNs中,DR2抑制劑依替必利也可減輕SS對GABAAR胞膜表達的抑制作用,說明DR2也可能通過與GABAAR的相互作用影響GABAAR的轉運來介導SS對GABAAR的調節[26]。
以上研究表明,DR1和DR2可通過多個信號通路調節聽覺功能(圖1),并且DR1和DR2激活可產生相同的效應,如DR1、DR2激活均可降低SGNs的動作電位幅度,均可抑制SGNs的Na+電流以及均減輕了SS對GABAAR胞膜表達的抑制作用,但在此基礎上并沒有更進一步的研究,且哪些信號通路更重要尚未清楚。

圖1 多巴胺受體調節聽覺功能的信號通路Fig.1 Signal pathway of dopamine receptors regulating auditory function
4 DR與耳鳴機制的關系
4.1 DR1與耳鳴的關系
在耳聾大鼠中發現,D1受體mRNA的表達降低[27]。然而,在SS誘導的耳鳴小鼠中發現,耳蝸和聽覺相關腦區的D1受體mRNA表達增加[28]。另外,在大鼠中發現,SS可促進SGNs中D1受體mRNA的表達[29]。盡管在動物實驗中發現DR1對于聽覺功能的調節有重要作用,但關于DR1與耳鳴機制的研究較少報道,且目前尚未見到DR1激活劑或抑制劑用于耳鳴治療的相關報道。
4.2 DR2與耳鳴的關系
研究發現,SS可促進大鼠SGNs中D2受體mRNA的表達[29]。在強噪聲暴露過程中,耳蝸內給予D2/D3受體激活劑吡貝地爾可以減輕聲損傷導致的內毛細胞下方的徑向樹突損傷,并使CAP閾值偏移顯著減少。缺血引起的最明顯損傷是突觸后與內毛細胞接觸的放射狀樹突腫脹,在人工缺血之前給予吡貝地爾,可防止放射狀樹突損傷,樹突損傷被認為與興奮毒性有關,提示吡貝地爾對聽覺創傷和缺血引起的興奮毒性損害有某種保護作用,多巴胺能側向傳遞可能通過D2/D3受體調節內毛細胞和SGNs之間的突觸傳遞,在一定程度上保護初級聽覺神經元[30]。Altschuler等發現,吡貝地爾可減少噪聲導致的大鼠內毛細胞帶損失,通過預防噪聲引起的內毛細胞—聽覺神經突觸連接損失來減輕噪聲的興奮性毒性損害[31]。最新的研究表明,多巴胺可通過激活DR2調節聽覺中腦對意外聽覺信息輸入的加工,削弱意外聽覺信號的突觸后增益[32]。
但臨床研究表明,口服吡貝地爾對耳鳴的改善作用與安慰劑組并無顯著差異。或許是因為吡貝地爾口服后能吸收進入耳蝸的程度尚不明確,并且耳蝸中的藥物濃度可能不足以對聽覺神經活動產生相關影響[33]。其他研究發現,同樣作為D2/D3受體激活劑的普拉克索對緩解主觀耳鳴和老年性耳聾有效,治療4周即可顯著降低耳鳴障礙存量得分和耳鳴響度[34]。
在抑制DR2的研究中發現,DR2抑制劑依替必利可引起聽神經腫脹,可能導致早期的興奮毒性[35]。但矛盾的是,有研究表明DR2抑制劑舒必利可緩解耳鳴,舒必利單獨應用可使56%的患者主觀耳鳴知覺下降;羥嗪是抗組胺藥衍生物,具有皮質鎮靜作用,也可降低耳鳴知覺,舒必利、羥嗪聯合應用可使81%的患者主觀耳鳴知覺下降[36]。褪黑素可以抑制多巴胺能神經傳遞,舒必利與褪黑素聯合使用可使85%的患者耳鳴知覺下降[37]。
以上的研究結果說明,DR2激活劑吡貝地爾可減輕興奮性毒性損害,而DR2激活劑普拉克索、DR2抑制劑舒必利均可以改善耳鳴,這說明DR2在耳鳴機制當中的作用十分復雜。
5 結語及展望
綜上所述,DR參與對聽覺功能的調節。DR1和DR2可以通過多個信號通路對聽覺功能進行調節,并且DR1和DR2激活可通過不同的機制產生相同的效應。DR1和DR2也可通過一些信號通路參與興奮毒性損害的過程,部分DR2激活劑或抑制劑在臨床上均可用于耳鳴治療。然而,DR在興奮毒性損害過程中的作用機制并未完全清楚,相關研究也較少。因此,仍需要進行大量的研究,以深入了解DR在生理狀態以及損傷刺激下如何對聽覺功能進行調節,從而為預防和治療耳鳴提供指導意義。